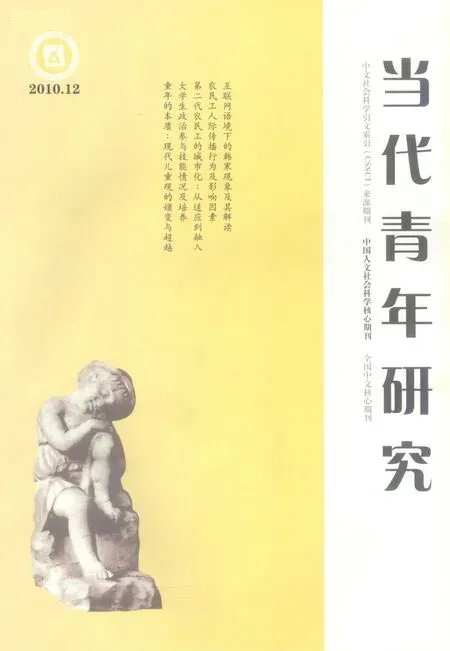童年的本質:現代兒童觀的嬗變與超越
◎程福財 董小蘋
從19世紀后半期開始,人們開始對兒童及其發展進行現代科學研究,逐步形成了理解并解釋童年的現代主義發展范式。在這一范式中,兒童被看作是一個有待發展的、非理性的、不成熟的 “未成年人”(在英文中稱為Human becoming),而非正常的 “人”(在英文中稱為Human being),童年則被視為個體由不成熟向成熟轉化的過渡時期。一般認為,唯有在這個過渡時期獲得良好的知識技能與價值觀訓練,“未成年人”才可能有效進入到成人的社會世界(參見 James,Jenks,&Prout,1998;James&Prout,1997)。這種論述,在生物學、心理學與社會人類學的研究領域都曾盛行。不過,隨著人們對兒童社會性、多樣性與能動性認識的深入,其主導性地位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挑戰。
一、遺傳基因、本能與兒童發展
兒童的發展過程決定于其特有的遺傳基因與本能等生物性因素,這是生物決定論者關于童年的基本理論立場。在他們看來,兒童發展過程即是兒童生理成熟的過程。兒童心智與社會性的成熟過程都取決于其生理成熟的進程。譬如,兒童的智力與個性等品質以及由這些品質所決定的個人成就,深深受制約于他們生殖細胞中的基因。而所謂外在環境或后天教育的影響,僅僅在于促進或阻滯先天基因所決定的潛能展開的速度。美國青少年心理學的先驅霍爾(Stanley Hall)甚至曾經斷言“一兩的遺傳勝過一噸的教育”。
關于遺傳基因之于兒童個體發展的決定性作用,最早由英國人高爾頓(Francis Golton)在其《遺傳的天才》一書中闡明。1869年,也就是在他的表兄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出版十年后,高爾頓出版了《遺傳的天才》。他利用英國一些大家族成員的成長資料作為自己的主要數據,試圖證明塑造了這些家族成員成功的因素正是這些家族的遺傳因素。他宣稱,一個人的能力是由遺傳得來的,它受遺傳決定的程度,如同一切有機體的形態及軀體組織受遺傳決定一樣(Golton,1998)。受啟發于這種遺傳決定論以及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霍爾亦復提出兒童的心理發展主要由遺傳決定的論點。他認為,人類個體的發展,其實只是人類種族進化的復演過程。他提出了個體發展須要經歷的四個相互不同的階段,其中每一個階段都相應于人種進化相應階段。第一階段是從出生到四歲的嬰兒期(Infancy),相當于人種演變歷史最早的動物階段。在這一階段,個體的發展主要體現在感覺及感覺運動技能方面,而其精神心智發展(Mental development)則相當粗糙。第二階段是從4歲到8歲的童年期(Childhood),相當于人種進化過程中的類人猿期。在這一階段,個體在語言與社會交往互動方面會有快速的發展,一如人種在游牧時期的進化特征。第三階段是從8歲到12歲的所謂少年時期(Adolescence),相當于人種進化過程中的半野蠻人階段。在這一階段,兒童開始有意識地實踐并調節自我,特別適合于常規訓練,尤其是對語言與數學的常規訓練。第四階段是從12歲到25歲的青少年時期(Youth),相當于人種進化過程中的文明人階段,這一時期是個體情感發展的狂飆突進時期,是充滿叛逆與反抗的青春期。經過這一時期的順利發展,個體才成為完整成熟的人。霍爾認為,每個個體的發展都要經歷這四個不同的發展階段,而無論在哪一階段的發展,都是決定于人的基因,不可改變,普世皆然。具體環境的影響效應微不足道。例如,霍爾認為,打架斗毆與小偷小摸就是青少年時期不可避免的行為,它們深植于人類的基因之中。他敦促父母不要過分焦慮于孩子的這些所謂越軌行為,因為在后續的發展過程中,在生物基因的作用下,這些行為都會自動消失(Hall,1908)。
霍爾的理論影響深遠。他關于青春期注定是充滿暴風驟雨般的叛逆的論斷迄今仍被世界各地的諸多教育工作者奉為經典。即使是在兒童研究世界,霍爾關于遺傳和生物性因素之于個體心理發展的影響的論述也并不孤單。阿諾德·格塞爾(Arnold Gesell)通過自己的研究以及對兒童發展的觀察,提出了著名的“成熟勢力說”:個體發展的機制主要包括“成熟”與“學習”。成熟主要是個體內在的生物性發展過程,學習則是與外在環境有關。在實驗研究的基礎上,格塞爾指出,兒童心理的發展是內環境生物成熟的結果,生物成熟是影響發展的第一要素。在他看來,兒童發展(特別是其心理發展)是由其內部的基因所規定的不變的規律和順序決定的。這個順序與成熟(內環境)關系較多,而與外環境關系較少,外環境只是給發展提供以適當的時機而已(參見潘茄,1980)。對此,格塞爾有一個著名的同卵雙生子爬梯實驗為證。在這個實驗中,孿生子A從實驗的第48周起每日進行10分鐘爬梯訓練,連續6周;在此期間,孿生子B不作爬梯訓練,他只從第53周起開始作爬梯訓練。根據他的實驗結果,B在爬行訓練2周后,他很快趕上了A的爬梯水平。由于A、B兩人擁有相同的基因,格塞爾指出,個體生物的不成熟就無從產生學習,而學習只是對成熟起一種促進作用,并不能根本改變成熟對于個體發展的影響。基于這樣的實驗發現,格塞爾認為,兒童的發展具有一定的生物內在進度表,它與一定年齡相對應。換言之,因為基因的作用,兒童在每一個年齡階段都有其特定的行為方式和特點(參見王振宇等,2000)。這種論斷與霍爾的論述不約而同,亦對20世紀四五十年代西方社會的兒童教養實踐產生過很大影響。
生物決定論的另一個著名代表是弗洛伊德。略有不同的是,他關注的是本能而非基因。在他看來,決定個人和社會發展的最基本力量是人的本能和欲望。人是一種能量系統,由一種強大的先天力量所推動,這種先天力量來源于身體所產生的需要。以愿望表達出來的這種軀體需要就是一種本能,人的一切行為動機都可以歸結到性欲、仇恨、攻擊、生存與死亡等本能之中(弗洛依德,1996)。社會、文化、意識、道德乃至教育對人的作用都不在他的視線之內。
從上可見,生物決定論片面強調生物因素的作用,強調基因的影響,它忽視了后天環境和教育在兒童發展過程中的角色。因此,它甚至被認為是白人男性中心主義者為自己優越地位所做的合理外衣,遭到了后來的行為主義、文化人類學等的強烈質疑。
二、兒童發展階段論
生物決定論這種關于兒童發展的極端論述很快遭遇到行為主義等心理學理論的質疑。例如,在華生和斯金納等行為主義者看來,個體的行為和兒童的發展過程,其實只是“刺激—反應”公式的實踐,與本能、基因、遺傳毫不相干。他認為,行為的反應總是由刺激引起的,而刺激總是來源于客觀環境,而不是來自于遺傳等生物因素(參見楊麗珠等,2006)。基于此,心理學者對本能遺傳等概念素來缺乏擁抱的熱情。在他們看來,生理的遺傳并不能導致個體機能上的遺傳。因此,在促進兒童發展的過程中,人類應該特別強調環境和教育的作用(參見斯金納,1989;林崇德,1995)。
行為主義的上述兒童發展觀是一種典型的環境決定論。它在否定遺傳基因與本能的作用的同時也否定了兒童自身的能動性。出于對此種局限的警惕,后世的兒童心理學研究努力在生物決定論與環境決定論中取得某種平衡。瑞士心理學家皮亞杰提出的兒童認知發展學說,就是這種努力的最著名結果之一。按照皮亞杰的理論,新生兒是一個有待成長發展的非理性、不成熟的個體。兒童由非理性向理性、由不成熟向成熟發展的過程,內在地含有一種特殊的包含了一系列預設的不可更改的發展階段的結構,兒童唯有依次順利經過這些發展階段,才能成為具有邏輯思維能力的成熟理性的人(Piaget,1929)。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兒童發展研究深受皮亞杰的影響,形成了強調兒童發展的生物性基礎、脆弱性、不成熟性與普遍性的兒童發展階段論。科爾伯格的道德發展階段論、精神分析學派關于兒童發展的論述、以及埃里克森的八階段論都在此一范式之中(參見林崇德,1995;潘茄,1980)。
通過長期的實驗研究,皮亞杰提出了著名的兒童心理發展階段論。按照這個理論,兒童的心智發展大體分成感知運動階段(0-2歲)、前運算階段(2-7歲)、具體運算階段(7-11歲)和形式運算階段(11-15歲)等四個階段。兒童的心智發展在每一個階段中都具有顯著不同特征。但是,這四個發展階段又具有不可割裂的內在連續性。首先,從感知運動階段到前運算階段到具體運算階段到形式運算階段這個發展順序是恒定不變的;其次,每一階段的發展對后階段的發展過程都具有基礎性的作用,每一階段的發展都是前一階段發展的持續和延伸,前一階段發展的失敗,會導致后階段發展的失敗;最后,這四個發展階段之間的區隔并非絕對,階段之間總是存有一定的交叉重疊,體現在每一階段發展的準備期與完成期。
值得注意的是,皮亞杰把他的這種發展過程定義為一種自然的(Natural)過程,受到兒童獨有的生物特征所決定。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兒童理論受到了生物胚胎學的深刻影響,①他十分注重所謂預設的生物性結構在兒童發展過程中的影響,強調兒童發展的自然性。皮亞杰認為,心智的發展,是人的生物適應的表現、延伸與結果。不過,和格塞爾等人在20世紀初提出的兒童的發展系由其生物基因決定的“成熟勢力說”不同,皮亞杰也強調外在社會環境與兒童內在力量的交互影響。個體的生物適應過程(也就是心智的發展過程)是一種動態平衡的過程:環境切實影響著個體的存在,受此影響的個體在心智上產生相應的變化,這種變化反過來影響個體與環境的作用模式,進而形成一種更加有利于個體生存的方式(參見楊慧慧等,2007)。皮亞杰指出:“和生理的成長一樣,心理的發展,實質上就是趨向平衡的活動……發展是一個繼續前進的平衡過程,從較低的平衡狀態走向較高的平衡狀態。”(皮亞杰,1982,第20頁)
另一方面,皮亞杰將兒童的發展過程看作是一種普世性的(Universal)過程,來自于不同社會、經濟、政治、文化背景的孩童具有類似的發展過程。在皮亞杰的論文、專著中,兒童這個詞語,更多的是用單數形式的“Child”表示。不論現實中千千萬萬的兒童有多少區別,皮亞杰極少用復數形式的“Children”去稱呼兒童。在他看來,所有的兒童都是不成熟的、非理性的、有待發展的個體,具有高度的同質性。因此,并沒有必要用復數Children去指代兒童。這種本體論層面的主張,也是皮亞杰慣用實驗研究的方法去探討兒童發展規律的原因之所在。在皮亞杰主義的范式之中,由于所有的孩子高度同質,對單個孩子的實驗研究發現便具有了高度的可推論性。
皮亞杰的理論為兒童研究和兒童教育提供了理論依據,成為后來眾多兒童研究的理論源泉。他對于兒童發展的生物性基礎、兒童的非理性、兒童發展的階段性與普遍性的強調,成為后世心理學關于兒童發展研究的基礎與典范。譬如,作為皮亞杰主義的繼承者,科爾伯格提出的兒童道德發展階段論亦特別突出兒童發展過程的階段性;埃里克森的人生發展八階段論亦未脫兒童“生物—心理發展模式”之于生物性、非理性、發展性、普遍性等核心概念框架的強調。所有這些心理學研究的成果對于兒童發展的研究,對兒童保護、兒童教育、兒童權利運動等產生了深遠影響。實際上,以皮亞杰為代表的發展性范式,在整個人類社會關于兒童成長的實踐中至今仍占據支配地位,以致人們很難跳脫它的框架去思考其他替代性的兒童教養方式。
三、社會化視角中的兒童
20世紀50年代,關于童年的“非理性”、“自然性”與“普遍性”的心理學話語體系,被迅速翻譯到社會學界,并以社會化理論的形式出現,成為社會學研究者認識、理解、闡釋兒童發展的主要理論工具。
按照社會化理論,新生兒起初只是一個生物性而非社會性的動物(Asocial animal)。他要逐步融入到社會環境并成為能夠有效適應和參與社會生活的社會人,就需要經由社會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兒童逐步認識社會生活的規則與秩序并獲得參與社會生活、與其他社會成員互動的必要價值、態度、知識與技能。在這里,一如皮亞杰主義所強調的,兒童和成人具有本質的差異,是一個非社會性、非理性、不成熟的存在。兒童時期的主要任務,則是要通過社會化的過程,逐步獲得理性,逐步成熟,逐步成為所謂正常的成年人。換言之,兒童并沒有如一般社會成員那樣具有其主體的能動性,他們缺乏成熟的理解、解釋、應對社會過程與社會事件的能力,因此是一個依賴性的、需要教育、有待社會化的未成年人。這種對兒童的認識,成為社會學教科書中關于兒童與兒童發展的主流話語。
但是,對于兒童成長過程的解釋,在文化人類學研究成果的啟發下,社會化理論提出了與心理學不同的主張。雖然強調兒童生理的不成熟對其發展的影響,但是社會化理論認為,傳統的生物決定論、生理—心理發展模式無法解釋下面這個事實:來自于不通家庭背景、社會階層的相同年齡的孩子,其身體素質與社會能力往往并不相同。更直接地說,它們無法解釋童年的差異性和多樣性。在文化人類學和大量社會經驗研究的基礎上,兒童社會研究者指出,影響兒童社會化過程的因素主要是包括兒童的家庭、學校與社會文化等外在宏觀因素。兒童的不成熟是一個無可辯駁的生物學事實,但是對于這種不成熟的理解與闡釋則是一個典型的社會文化過程。童年的多樣性,正是來源于社會文化的多樣性。因此,“童年”不應只是作為一個生物學變量或心理學變量而存在,它更應該是獨立的社會分析變量。對于童年的研究,無法脫離包括社會階級階層、性別、種族、文化背景等社會性變量。
現有的對于童年的跨文化研究,已經向人們清楚地展示了童年的多樣化存在。1925年,瑪格麗特·米德在對薩摩亞人的人類學研究的基礎上出版的《薩摩亞人的成年》一書指出,霍爾提出的青少年時期是一個天生的叛逆時期這個一度廣為人們認同的發展性論述,其實并不合符實際。她的研究發現,在薩摩亞,青少年的這種叛逆期根本不存在,薩摩亞人的青春期并非和歐美社會那樣充滿緊張、矛盾和叛逆。相反,青春期是他們一生中最輕松最愉快的時期。因此,心理學研究者關于青春期問題是人在達到成熟期時的生物學過程中必然發生的論斷是缺乏充分依據的。米德的研究清楚地揭示,所謂的青春期問題,根源并不在個體的生物學特征,而在其所存在的社會文化;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下的兒童具有不一樣的童年生活(米德,2008)。這樣的研究發現,后來為本尼迪克特(Benedict)進一步印證。在比較Zuni,Dobu,和Kwakiutl等地的童年時,本尼迪克特(1987)發現,在兒童所需要承擔的責任、兒童需要對成人的服從程度、性別角色的分工等方面,這三個不同地區都具有顯著的差異。本尼迪克特的研究為童年的文化決定論提供了進一步的證據。需要注意的是,無論是本尼迪克特還是米德,不論他們怎樣強調童年的多樣性,他們都認為社會化的過程是一個由成人社會主導的針對兒童的型塑過程。
自帕森斯以后,社會學研究者對人的社會化問題給予了諸多關注。在結構功能主義看來,社會化的過程是個體學習承擔社會角色的過程。作為社會結構的一份子,個體需要通過社會化知道并實踐社會對不同角色的具體要求。在這個“知道并實踐”的過程中,個體能夠逐步明白自己在宏觀社會結構中的位置以及社會結構中其他行動者對于自己的期待,進而順利完成自己擔當的社會角色,發揮有利于社會結構維持、發展的必要功能(帕森斯,1951)。顯然,社會化并不是一個消滅個性、獨揚社會性的問題(龐樹奇等,2000)。兒童的社會化過程,是要在張揚自己個性的同時,明了自己在現存社會結構秩序中的角色。布朗芬布倫娜(Bronfenbrenner)在1979年發表的《人類生態發展學》中提出了關于兒童發展的生態系統理論,對兒童的社會化過程進行了系統分析。他認為,真實自然的環境系統是影響青少年發展的主要因素,兒童發展是生態環境作用的結果。在他看來,這個環境系統一般包括微系統—個體直接接觸和產生體驗的環境(如家庭和學校)、中間系統—兩個或多個微系統環境之間相互聯系和彼此作用形成的環境(如家庭和學校的關系)、外系統—個體并未直接參與但卻對其成長發生實際影響的環境以及這些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 (如家庭成員的工作環境)、宏觀系統—個體所處的整個社會的組織、機構、文化和亞文化的社會背景。布朗芬布倫娜認為,兒童的發展過程是一種在日益復雜的水平上持續認識和建構其生態環境的過程 (參見楊麗珠,2000)。
顯然,兒童社會化理論是皮亞杰主義的繼承。他們都將兒童看作被動的、欠能的(Incompetent)、不完整的依賴性存在。兒童要成長為對社會能有所貢獻的成人,則需要在成人的幫助下實現心智的發展,熟悉并參與社會生活。
四、兒童社會研究新范式的興起
概括地說,現代兒童觀關于兒童發展的論述主要包括以下幾點。首先,非理性(理性不足)是兒童區別于成人的普遍問題。在現代兒童觀的框架之中,童年是個體用來學習適應參與社會生活的知識、態度與能力的時期,是人生的一個準備時期,過渡時期。這一時期個體發展的重要使命是要為未來做準備,其發展的成敗則要看這種準備是否充分。為了未來的生存與發展,童年時期的福利(如對閑暇時光的享受)可以犧牲。我們看到,在日常生活中,眾多的家長在為了孩子的將來的旗幟下,無論孩子多么不情愿,都要求孩子在節假日等課余時間參與各種培訓班。一切為了未來的發展,發展是童年的主題,這是發展性路徑的一個重要內涵。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可見其第二個特點,即現代兒童觀是一種進化模型。由童年向成年的過渡,本質上是從簡單到復雜、從非理性到理性、從依賴到獨立的過渡。這種過渡可以從兒童的語言、游戲、與他人的互動中清晰可見。隨著“發展”的深入,他們的語言、游戲與行動變得越來越理性而復雜。非理性行為與思考的減少、理性行動的增多,簡單概念的減少、復雜觀念的增多,是兒童發展的重要標志。再次,在現代兒童觀中,兒童的發展與成長過程及其結果的評估概由成人主導,兒童自己無權決定自己的發展路徑。因為兒童要適應、參與的是成年人主導的社會,所以,只有那些熟悉成人社會的成年人才能更好地安排、度量兒童的發展。因此,現代兒童觀的實踐必然帶來成人與兒童之間權力關系的不對稱。在“一切為了孩子,為了孩子的一切”的社會口號下,成年人可以“合法”、“合理”、“合情”地安排兒童的生活,在關系到兒童福利的事務中,兒童自己的聲音大多缺席。這正是為什么《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主張兒童參與權近20年,該項權利始終沒有能夠得到普遍實踐的重要原因。
20世紀60年代后期,心理學開始了對現代兒童發展觀的反思。多納德森(M.Donaldson)在其《兒童的心靈》一書中,對皮亞杰主義對于兒童發展一般過程的“客觀性”提出了有力的質疑。多納德森重復了皮亞杰關于兒童心理發展過程的實驗,唯一不同的是主持實驗的不再是成年人,而是他特意選擇來的一位頑童(Naughty teddy)。由這位頑皮少年完成的實驗研究,得出了與皮亞杰們的研究完全不同的結果:成人所謂的兒童,如大人一樣成熟。所以得出這樣的結果,他認為是因為作為實驗者的兒童(非成人)讓實驗活動本身變得對孩子更有意義(Donaldson,1978)。這樣的一份研究雖然沒有顛覆皮亞杰主義的正統性,卻清楚地告訴人們,成人—兒童關系的社會背景、以及把兒童帶到實驗中去的象征意義,都會對實驗結果產生影響。顯然,這個實驗發現,所謂兒童的不成熟性,其實可能只是成人社會賦予自身之于兒童的權力的合法性借口。由兒童主導的研究表明,兒童并不是人們想象得那樣脆弱不成熟。
多納德森的研究開啟了人們對童年本質的反思之旅。在這個旅程中,結構主義和一度興盛發展的符號學發揮了先鋒作用。在結構主義看來,社會的分化、分層,不僅會結構化社會生活的制度安排,也會結構化我們對這種結構化了的社會生活的制度安排的理解。另類觀念、不同意見與霸權(Hegemony)等概念的存在提示我們,特定的社會群體可能具有與主流社會不同的對社會生活的理解。在理解日常生活的表意性行動方面,符號學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語言在型塑社會現實方面的意義為人們廣泛認同。1970年代知識界風向的如此轉變,給人們對于童年的研究帶來了一些重要的啟發。這種啟發首先發生在歷史學領域。菲利普·阿里耶斯(Philip Aries)在1962年激進大膽地說道:“在中世紀的歐洲,所謂童年的觀念,根本不存在。”這個論斷迅速為社會學家所接受。他的論著《千年兒童》(Centuries of childhood)被廣泛引用去證明人類社會生活的多樣性(Aries,1962)。
對于阿里耶斯Aries的激進論述,后來的學者褒貶不一。然而,即使是那些找出具體證據來說明中世紀的歐洲里也存在童年這個概念的人也不得不承認,那時候的人們對待童年的觀念、對童年的理解是大相徑庭于今時今日的我們。童年的多樣性、變異性在他們那里仍然有充分的證據支持。關于童年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后來獲得從事文化與人格研究的社會人類學家早期研究的支持。1990年代,受啟發于建構主義的論述,歐洲兒童社會研究者明確提出了所謂“兒童社會研究新范式”。按照這個范式,兒童并不是脆弱的服務接受者,并不只是社會結構的產物,也不是社會化理論中的“文化傀儡”(Cultural dopes),而是積極能動的社會行動者,建構并創造社會關系;他們不只是按照社會文化規定的方式、規則去行動,而是時時刻刻都在復雜的社會環境中創造性地努力、工作。對于自己、他人、社會以及三者之間的關系,兒童有自己的認識、理解與解釋。此外,從來就沒有所謂的普世皆然的童年,童年含義的形成,不僅受生物性因素的作用,不僅受社會文化的影響,更取決于兒童與其他社會成員之間的權力關系和互動。因此,在兒童研究過程中,我們不能將兒童簡單地集體化,而忽視不同兒童的差異性、獨立性 (James,Jenks,&Prout,1998;James&Prout,1997)。 這些論述給兒童研究與兒童教養實踐帶來許多新的啟示。例如,既然兒童是有主體性的、能動的,那么關于兒童的研究應該由兒童參與、主導,成人與兒童的關系就該是平等的;既然兒童是多元的,那么兒童政策就應該是基于兒童所在的社會脈絡的。這些顛覆性的理論與政策啟示,在實踐中引發了諸多的爭論,值得我們深思。
注:
①將生物胚胎學的模型應用于兒童發展研究的代表人物首推格塞爾。他認為,兒童的生理與心理的發展都是按照其生物基因確定的順序、結構而有規則地進行。因此,兒童的發展,始終有內在的生物進度表。參見威廉.C.格萊因.兒童心理發展的理論[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
1.Aries,P.,(1962).Centuries of childhood: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New York:Vintage Books.
2.Corsaro,W.,(1997).The sociology of childhood.Thousand Oaks,Calif:Pine Forge Press.
3.Donaldson,M.,(1978).Children's mind.London:Croom Helm.
4.Hall,S.,(1908),Adolescence:its psychology and its relations to physiology,anthropology,sociology,sex,crime religion and education.New York:D.Appleton&Co..
5.James,A.,Jenks,C.,&Prout,A.(1998).Theorizing childhood.Cambridge:Polity Press.
6.James,A.,&Prout,A. (1997).Constructing and reconstructing childhood:contemporary issues in the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ldhood(2nd ed.).London:Falmer Press.
7.Piaget,J.,Tomlinson,J.,&Tomlinson,A.(1929).The child's conception of the world.London:K.Paul Trench Trubner.
8.魯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
9.西蒙格德·弗洛伊德.夢的解析[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10.聯合國.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M].1990.
11.林崇德.發展心理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12.瑪格麗特·米德.薩摩亞人的成年[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13.潘菽主編.教育心理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
14.龐樹奇等.普通社會學理論[M].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0.
15.皮亞杰.兒童的心理發展[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2.
16.斯金納.科學與人類行為[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
17.王振宇等.兒童心理發展理論[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
18.楊慧慧等.皮亞杰兒童認識發展理論述評[J].前沿,2007(6).
19.楊漢麟.外國幼兒教育名著選讀[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
20.楊麗珠等.畢生發展心理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1.威廉·格萊因著.兒童心理發展的理論[M].北京: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