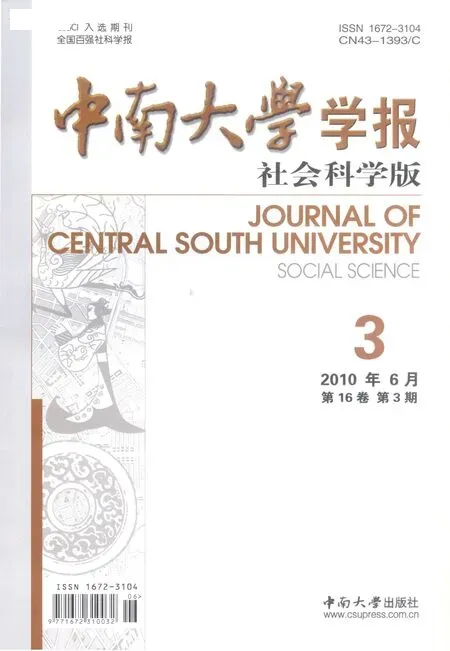論食品安全法律概念的泛化及其法律意蘊
韓永紅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商英學院,廣東廣州,510420)
論食品安全法律概念的泛化及其法律意蘊
韓永紅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商英學院,廣東廣州,510420)
現有的食品安全法律概念呈現泛化的趨勢,以“食品安全”涵蓋“食品質量”不利于構建科學、高效的國內和國際食品安全法律規制體系。為扭轉這一泛化趨勢,我們需平衡食品安全中的科學和價值觀因素,以風險為切入點,以科學為基礎界定食品安全。同時,我們需謹慎對待與食品安全法律概念泛化密切相關的兩個爭議性問題:生產過程與生產方法(PPM)和動物福利,主張只有對最終食品的安全性能夠產生可識別性影響的PPM和動物福利貿易措施才應納入食品安全國際法律規制的范圍。
食品安全;風險;生產過程與生產方法;動物福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自2009年6月1日起生效。在國內外食品安全事件頻發的背景下,該法的出臺無疑是回應現實的立法之舉,意義重大,但筆者更為關注的是該法對食品安全的法律界定。“概念乃是解決法律問題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沒有限定嚴格的專門概念,我們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性地思考法律問題[1]。”食品安全法律概念是構建和完善食品安全法律體系的基石,決定著食品安全立法的現實執行力和發展趨向。《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對“食品安全”的界定存在泛化的趨勢,其背后的法律意蘊不容忽視。
一、食品安全法律概念的泛化趨勢
食品安全作為一個法律概念進入我國立法和學術研究領域基本上是2000年之后的事情。我國現有的法規和學術文獻對食品安全的概念表述不盡一致,但基本屬于一種模式:以食品是否對人體健康造成危害作為結果性標準,以食品安全來統領食品衛生、食品質量、食品營養等相關概念。2006年施行的《國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應急預案》規定:“食品安全:是指食品中不應包含有可能損害或威脅人體健康的有毒、有害物質或不安全因素,不可導致消費者急性、慢性中毒或感染疾病,不能產生危及消費者及其后代健康的隱患。食品安全的范圍:包括食品數量安全、食品質量安全、食品衛生安全。本預案涉及到的食品安全主要是指食品質量衛生安全。”而2009年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第99條則規定:食品安全,指食品無毒、無害,符合應當有的營養要求,對人體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亞急性或者慢性危害。相較于《國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應急預案》的規定,該定義表述簡潔但特別強調了“營養要求”,這恐怕與該法頒布之前發生的“三聚氰胺”奶制品事件密切相關。學者給出的食品安全定義似乎更為寬泛。有學者給出的定義擴展了食品安全的外延,將環境保護納入食品安全需考量的因素。“食品安全在當今時代的定義至少還應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食品的生產、加工、貯運和消費過程應對環境具有友好性;食品被不同膚色、職業、年齡和性別的人群按規定正常食用后,不會對身體產生損害;衡量食品的安全性指標應有明確的計量或感觀等方面的國際通用標準范圍值。”[2]“廣義的食品安全概念是持續提高人類的生活水平,不斷改善環境生態質量,使人類社會可以持續、長久地存在與發展。包括衛生安全、質量安全、數量安全、營養安全、生物安全、可持續性安全六大要素。”[3]總體而言,目前國內關于食品安全的定義代表了廣義的食品安全定義,且外延呈現逐漸擴大的趨勢。
食品安全的概念決定了食品安全法律體系的調整范圍和張力,立法者和學者的初衷無非是想提升食品安全法的基本法地位,擬將食品安全法作為一攬子解決食品安全問題的利器。如學者張守文指出,確立“食品安全”的法律概念,并以此種概念涵蓋“食品衛生”“食品質量” “食品營養”等概念,對于建立一部統一、權威的《食品安全法》,更具有現實意義和長遠意義。但問題是:是否與食品相關的問題都屬于食品安全問題? 是否食品安全的界定越寬泛意味著食品安全法律的效率將越高?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實際上,食品安全的概念不能涵蓋食品衛生、食品質量和食品營養。這里尤其需要區分食品安全與食品質量。
食品質量的內涵和外延大于食品安全,二者是屬種關系。按照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在國際標準ISO9000-2000中的定義,質量是指產品所有相關特性符合用戶需求的程度。即某種產品的“特性”滿足“用戶要求”的程度越高,其質量就越好,反之則認為產品的質量差。質量特性通常被分為以下五類:技術方面的特性、心理方面的特性、時間方面的特性、安全方面的特性和社會方面的特性。為了在實踐中對質量進行客觀測量和評價,必須先將產品的質量特性轉化成標準,符合某一特定標準,即可認為是質量合格,否則就判定為不合格。質量的概念應同樣適用于對食品質量的界定。為了客觀地對食品質量進行測量和評價,在制定食品質量標準時,一般將質量指標具體化為三大類性狀:安全性狀、營養性狀和外觀性狀。所以就客觀方面而言,食品安全僅是食品質量所具有的安全性狀。食品質量還有其主觀方面——滿足消費者的偏好。“食品質量涵蓋了食品營銷、消費者行為研究、科學和營養、食品開發和質量保障,旨在使食品的質量與消費者的偏好相符。”[4]因此,食品質量的外延還可能包含關于標識、環境保護、動物福利及其他倫理性方面的要求。此外,食品安全是不可協商的剛性要求,而食品質量是可以協商的彈性要求。食品的安全性(至少不對人體造成損害)是各國消費者對食品共同性的剛性要求,但因收入水平、價值觀等差異,各國消費者對食品質量的接受度和容忍度卻不相同。嚴格區分食品安全和食品質量的法律意義在于:就食品安全的國內監管而言,如將食品質量的全部要素均納入食品安全法的規制范圍將不利于執法的統一性,使監管機構對風險的控制難以區分輕重緩急,造成監管效率低下;就食品安全的國際法律規制而言,食品安全是各國消費者共同性的剛性要求,相應的國際法律規則可具有強制性。食品質量具有可協商性,有關食品質量的國際法律規則應賦予各國較為寬泛的自由裁量度。另外,因食品質量要求具有很強的市場區分作用,在食品國際貿易中更易被進口國濫用為技術貿易壁壘。從這個角度而言,嚴格區分食品安全和食品質量,抑制國內食品質量法規對食品安全國際法律規制的過度滲透,也有利于減輕食品安全國際合作中的制度性沖突和障礙。
二、相關的兩大爭議
食品安全概念的泛化具有重要的法律意蘊。它不僅影響國內食品安全監管的范圍和效率,還與食品國際貿易密切相關。在食品國際貿易領域,目前出現了與食品安全法律概念泛化相關的兩個爭議性問題:一是各國政府可否基于食品的生產過程和生產方法實施貿易措施? 二是各國政府可否基于國內的動物福利法規實施貿易措施? 這兩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食品安全國際法律規制的發展趨向。
(一) 生產過程和生產方法
生產過程和生產方法(process and production method,以下簡稱 PPM),可以說是國際貿易史上最有爭議的詞組之一。它作為一個法律術語已為 WTO貿易體制所承認,出現在《實施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協定》《貿易技術壁壘協定》、金槍魚—海豚案和海蝦—海龜案的報告中。但上述文件并未對PPM的概念做出明確界定,PPM的法律定位仍處于變動和發展之中。我國學者在已有的研究中基本上把它界定為PPM環境標準。“環境標準按其功能可分為產品本身的標準和生產過程、生產方法標準,后者即PPM。PPM標準是指產品的生產過程和生產方法符合特定的環境要求,比如,在生產中廢氣、廢水、廢渣的排放量符合一定的標準、采用先進的清潔技術、以可持續的方式管理林地、以無害于其他生物的方式獵捕動物等。”[5]有學者還專門論述了WTO體制下的單邊PPM環境措施。[6]但實際上,PPM的外延更為寬泛,至少還包括轉基因生物技術、標識要求、動物福利、社會福利(如不使用童工生產)等旨在滿足消費者偏好的其他質量性要求。在本文中,我們所要關注的是PPM貿易措施,尤其是與食品有關的PPM貿易措施。筆者將PPM貿易措施定義為:一國政府基于產品的生產方法或生產過程中的某些特征而制定實施的管理法規。當進口產品的PPM不符合相應的管理法規時,這些產品的國際貿易就會受到禁止、限制、區別性對待等不利影響。
1. GATT/WTO體制下有關PPM貿易措施的法律問題
在WTO規則體系下,有關PPM貿易措施的法律問題主要為:一是WTO有關規則是否允許成員方以進口產品的PPM為依據而禁止、限制或區別對待最終產品相同的國內產品和進口產品;二是WTO有關規則是否區分與產品特性有關的 PPM貿易措施和與產品特性無關的PPM貿易措施。目前來看,上述兩個問題的答案均存在法律上的不確定性。
第一個法律問題需結合 GATT/WTO體制下與PPM貿易措施有關的案件來分析。第一個和PPM貿易措施有關的案件是1991年的金槍魚?海豚I案。在該案中,美國根據其《海生哺乳動物保護法》,要求向美國出口金槍魚的國家需證明其漁船對海豚的平均附帶捕獲率沒有超出同期美國漁船平均捕獲率的1.25倍,以保護被外國捕獲金槍魚時所威脅的海豚。墨西哥認為美國據此禁止從該國進口金槍魚的行為不符合GATT第3條第11條和第13條。美國則辯稱其禁止進口措施符合GATT第3條規定或者屬于GATT第20條(b)款和(g)款規定的例外范圍。專家組裁定GATT第3條“只管轄適用于產品本身的措施”,美國的措施不在該條的范圍內是因為金槍魚的生產過程和生產方法“不可能影響作為產品的金槍魚”。專家組進一步指出,美國的貿易措施不是規范金槍魚本身,而是規范捕獲這一產品的方式,不符合GATT第3條關于“相同產品”的規定。最終專家組裁定美國的貿易措施違反了GATT第3條第4款或第11條,并且該措施不屬于GATT第20條(b)款和(g)款規定的例外范圍。金槍魚—海豚 I案被認為是首個適用“產品?過程區分準則”(product-process doctrine)的案例。[7](187)這個準則的作用在于:如一國政府基于進口產品的生產過程或生產方法而對該進口產品實施不利的稅收或管理法規等貿易措施,則認為上述措施違反GATT規則。在隨后的與 PPM貿易措施有關的案件中“產品?過程區分準則”得到了明確的適用。但在 1998年的海蝦?海龜案中,WTO在PPM問題上的立場似乎發生了轉變。該案的事實與金槍魚?海豚 I案如出一轍。美國根據其《瀕危物種法》第609條的規定,禁止所有未使用TED海龜隔離器的國家或地區捕獲的海蝦及蝦類產品進入美國市場。印度、馬來西亞、巴基斯坦和泰國等四國向WTO爭端解決機構提起申訴。上訴機構在分析了該案例和美國《瀕危物種法》第609條后,推翻了專家組報告中關于美國第609條不屬于GATT1994第20條所允許的例外的認定,認為第 609條款是GATT1994第20條(g)項意義上的保護“可用竭天然資源”的一種措施。盡管最后上訴機構認定第609條是以不合理、武斷的方式實施而不予支持,但該案確認了美國實施的PPM措施符合GATT1994第20條的例外規定。雖然海蝦?海龜案的裁決不意味著確立了 PPM貿易措施在WTO規則體系中的合法地位,也不足以威脅“產品-過程區分準則”的地位,但“‘產品?過程區分準則’一直是環保組織和其他利益集團最想改變的GATT/WTO法律規則之一。”[7](181)可以預見,在以多邊談判方式達成明確的協議前,關于PPM的貿易措施仍將是國際貿易爭端的導火索。
第二個法律問題需結合《貿易技術壁壘協定》的相關規定來分析。《貿易技術壁壘協定》附件A將“技術法規”定義為:強制執行的規定產品特性或相關的加工和生產方法的包括可適用的行政(管理)規定在內的文件。技術法規也可以包括或專門規定用于產品、生產過程或生產方法的術語、符號、包裝、標志或標識要求。從語義分析的角度,這一定義存在模糊性。在上述定義中,第一個句子中的“生產過程和生產方法”限定為“相關的”,即與產品相關的生產過程和生產方法,而在第二個句子中的“生產過程或生產方法”前并無限定詞,而且明確包括了“標志或標識要求”。于是,關于《貿易技術壁壘協定》中的技術法規是否包括“與產品特性無關的 PPM”,各國會產生不同的解釋。一些成員國認為,上述對“技術法規”的定義意味著禁止成員實施“與產品特性無關的PPM”的技術法規,而另一些國家卻堅持,“與產品特性無關的PPM”應該并且實際上已為該協定所規制,否則一些重要的法規,尤其是正在形成中的與產品質量相關的以生產過程為規制對象的法規將會超出《貿易技術壁壘協定》的調整范圍。[8]
實際上,PPM貿易措施與WTO規則體系的關系大多體現在食品安全領域。“出于對食品質量的追求,對 PPM的規制已成為貿易領域食品安全法律規制中最具爭議性的問題。”[9]現階段與食品有關的貿易爭端大都與PPM有關。如曠日持久的荷爾蒙牛肉案固然涉及舉證責任分擔、風險評估、爭端機構裁決和建議的執行等眾多法律問題,但從PPM的角度考慮,雙方爭執的焦點可歸納為:美、加等國在飼養牛的過程中,添加人工激素,促進其生長速度。但在其最終出口的產品——牛肉中,可能并沒有人工激素被檢出,或者人工激素與牛體內的自然激素可能在檢測中沒有區別。歐盟能否基于牛肉的上述生產過程可能對人的健康造成有害影響為理由,采取最高程度的保護措施?而美國和歐盟關于轉基因食品規制的爭端也可歸結為對PPM規制的不同理念。歐盟認為轉基因技術是一種新的生產技術和生產方法,必須與最終食品分開監管。“一旦食品投放市場的方式、生產過程或生產方法發生了變化或者食品具有了非傳統性成分,這些事實對于消費者關于食品安全性和營養價值判斷的影響應予以考慮。”[10]與此相反,美國對于轉基因食品采取的是“實質相同”原則,即認為轉基因食品應視為與傳統食品相同的物質,除非前者表現出不同的特征。因此,美國對轉基因食品或含轉基因成分食品的監管與對傳統食品的監管無實質性差別。“對食品的規制,不論其生產方法如何,取決于食品的客觀特征或成分。盡管在某些情況下,了解食品的生產方法有助于理解最終食品的安全性和營養特征,但審查食品安全性的關鍵因素應是食品的特征而不是食品生產所使用的新的生產方法。”[11]
2. 實施PPM貿易措施的法律意蘊
第一,將食品的生產過程和生產方法納入衡量食品安全的因素,可能有利于滿足食品進口國的消費者偏好,但會加重食品出口國的生產成本和監管成本。現階段,對于PPM進行規制的立法實踐和主張主要來自發達國家,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由于技術水平相對落后,滿足嚴格的PPM貿易措施需要較高的費用,最終將使發展中國家的市場準入被實質性地取消。第二,PPM貿易措施本身的合法性存在疑問。賦予PPM貿易措施在WTO體制下的合法地位將給WTO整個法律規則體系帶來挑戰。這是因為:第一,現行 WTO法律規則體系建立在對產品而非 PPM貿易措施進行規制的基礎上。GATT第3條是關于如何對待相同產品的規則。兩個“金槍魚?海豚案” “美國?汽車稅案”和“美國?影響酒類和麥芽飲料措施案” “美國?汽油標準案”均確認本國產品和進口產品間的“相同性”基于產品本身的特征,不能根據產品的生產過程或生產方法確定。如WTO最終通過談判明確允許成員國采取基于PPM的貿易措施,無疑將顛覆整個WTO貿易體制的概念基礎。第二,如果PPM的貿易措施在WTO規則體系中的法律地位得以確認,其他與貿易無關的事項,如勞動標準、法治政府等也可能成為實施貿易措施的法定基礎。這等于變相肯定了進口國國內法的域外管轄權,從而使單邊措施合法化。而這已不僅是貿易問題,還直接涉及對出口國的主權侵蝕。
面對PPM對食品安全外延的擴展,我們應持有何種態度? 為便于問題的分析,筆者以為,有必要將食品貿易領域中的 PPM分為兩類:與最終食品相關的PPM和與最終食品不相關的PPM。前者包括那些對最終食品的安全性能夠產生可識別性影響的特征,如危害關鍵點分析和控制管理體系、良好操作規范等。后者指那些在最終食品中不可識別、不可檢測的特征。在法律的規制方面,對前者的規制以降低食品對人體健康的危害為特征,目的在于保證食品的安全性。對后者的規制以提高食品的質量為特征,目的在于滿足消費者的知情權、保護環境、愛護動物等法定性和倫理性要求,規制實施的原因并不直接與人體健康相關或其相關性并未得到國際間的廣泛認可。與最終食品相關的PPM可進入食品安全的法律規制范圍,而與最終食品不相關的PPM因其不可識別性、不可檢測性而具有很強的主觀性,易成為貿易保護政策的實施工具。因此,食品安全國際法律規制應致力于限制和替代與最終食品不相關的PPM。例如,對于轉基因食品的監管采取強制標識制度,但標識的內容僅限于可探察到的食品成分而非基于生產過程中轉基因技術的使用。
(二) 動物福利
晚近,發達國家基于動物福利立法而確立的動物福利標準正在進入食品貿易領域,其潛在的貿易壁壘作用正初現端倪。一般認為,“動物福利”一詞最早由美國人休斯于 1976 年提出,提倡人類在人道、合理地利用動物的同時,要兼顧動物的福利,盡量保證為人類做出貢獻和犧牲的動物享有最基本的權利。其后,英國農場動物福利理事會提出了動物福利的基本標準,即動物的五大自由:動物享有不受饑渴的自由;享有生活舒適的自由;享有不受痛苦、傷害和疾病的自由;享有生活無恐懼、不安和悲傷感的自由;享有表達自然天性行為的自由。[12]如今,在發達國家諸如“善待動物協會”等非政府組織的推動下,動物福利似乎已發展成為一個寬泛的概念,涉及動物的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環境和諧。動物福利被定義為:為了使動物獲得與其環境協調一致的精神和生理健康的狀態而采取的一系列行為和給動物提供的相應的外部條件。
1. 設置動物福利標準的法律依據
在如此寬泛的概念基礎上,發達國家設置的動物福利標準(如認證制度、標識要求等)覆蓋的范圍不僅包括農場動物的喂養、運輸、宰殺條件,而且延伸到社會倫理等文化深層次領域。但這些動物福利標準的設置并無明確的國際法律依據,WTO的所有法律文本都未明確涵蓋動物福利的概念。在多哈回合關于農業的談判中,歐盟曾提出對于與動物福利相關的農業行為給予農民補貼的主張,WTO 農業委員會于2003 年2月提出的《農業談判關于未來承諾模式的草案》第一稿及其修改稿已將“動物福利支付” 列入“綠箱政策” 之中。但由于多哈回合談判的無限期停滯,關于動物福利尚未達成任何多邊協議。目前,設置動物福利標準的法律依據僅來自某些國家的國內動物福利法規,發達國家大多通過苛以進口動物源性食品國內動物福利要求,將其國內的動物福利立法和標準國際化。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歐盟、加拿大、日本和新西蘭已率先建立起較為嚴格的動物福利立法體系。早在1958年美國即通過了《人道屠宰法》,1999年又修訂了其《動物福利聯邦法典》,將關于動物健康、畜牧業和運輸動物過程中的標準納入其中;新西蘭也于1999年制定了在內容上與《動物福利聯邦法典》相似的《動物福利法》;1973年日本制定了《關于保護和管理動物法》,禁止遺棄和殘忍對待動物;1990年的《加拿大動物健康法》規定了對待和運輸動物的方式,并確立了自愿性的“行為規范”;進入90年代以來,歐盟制定了許多有關動物福利的立法,形成了較為完備的動物福利法律體系。這一體系主要包括兩類立法:一是歐盟成員國簽署的相關區域性國際公約,如《國際運輸中的動物保護歐洲公約》規定了運輸過程中動物喂飼的間隔時間和圍欄的空間特征,《保護農場動物歐洲公約》規定了對待農場動物的一般要求,包括提供食物、活動自由、健康檢查、燈光調試、空氣流通和清潔的圍欄;二是基于歐盟基礎性條約授權制定的相關條例和指令。如 2002年 1月 1日生效的Directive 1999/74/EC 規定了生蛋母雞所處的雞籠尺寸不得低于 550 cm2,除此之外,歐盟還針對特定的農場動物,如牛、豬、鴨、鵝等制定了相應的法規。
2. 實施動物福利標準的法律意蘊
由于經濟發展水平和動物保護方面的文化差異,發展中國家普遍不存在系統的動物福利立法。這種立法上的巨大差距和相應國際法律規制的缺位,使動物福利標準問題成為引發相關貿易沖突的潛在力量。從動物福利的視角出發,前文述及的金槍魚—海豚案和海蝦—海龜案實際上也可看作是因美國國內野生動物福利法規在域外適用而引發的貿易爭端。雖然迄今在WTO體制下,尚未出現基于農場動物福利標準而引發的食品貿易爭端案件,但此類案件的發生恐怕已為時不遠。2002年,烏克蘭向法國出售一批生豬,經過60多個小時的長途運輸到達目的地后,卻被法方拒絕入境。理由是這批豬在運輸途中沒有得到充分的休息,沒有考慮到動物福利,違反了法國有關動物福利的規定。[13]我國有學者提出了動物福利貿易壁壘問題,認為我國與發達國家在動物福利的法律條文、標準體系、飼養方式、運輸方式和屠宰方式等方面存在明顯差距,發達國家的動物福利貿易壁壘會加大出口企業成本,加大國際貿易摩擦,我國應積極應對。[14]關于動物福利標準對貿易的消極性影響,我國也有學者利用囚徒困境模型進行數量分析,得出結論: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實施動物福利壁壘的過程中,發達國家始終處于有利地位。其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同時設置動物福利的貿易壁壘是博弈雙方追求最大利益的必然選擇。[15]
發達國家動物福利標準的設置不僅嚴重影響發展中國家食品貿易的市場準入,而且威脅發展中國家的立法和文化自主權。因此,在國內法律規制層面,完善我國的國內動物福利立法是應對之舉。在國際法律規制層面,鑒于國家間在動物福利方面存在巨大的立法差距和文化差異,達成專門性國際協議的機會不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關于動物福利的規則博弈更可能是圍繞GATT第20條的解釋展開。為謀求動物福利在WTO規則中的合法地位,已有西方學者提出建議,將GATT第20條(a)(b)中的“必需的措施”改為“相關的措施”,在GATT第20條(b)中增加“動物福利”的表述。[16]我國應在此過程中審慎、積極地闡明立場:對動物福利及GATT第20條做狹義的界定和解釋。在食品安全領域,反對發達國家倡導的意義寬泛的動物福利概念,提出新的主張:只有那些對最終食品的安全性能夠產生可識別性影響的動物福利標準才可作為實施動物福利貿易措施的依據,其他動物福利標準屬一國的文化范圍,不得以貿易措施的形式對食品出口國施加強制性影響。
三、食品安全概念的法律界定
總體而言,目前已有的食品安全概念呈現某種泛化的趨勢,并已經顯現出重要的法律意蘊。為此,我們有必要從法律的角度對食品安全的概念做進一步的界定。
食品安全是一個綜合性的概念。人們對食品安全的認知存在多樣性,不同的社會群體——消費者、監管者、食品工業界、學術界和特殊利益群體基于各自的出發點,對何謂安全食品有不同的描述和期望。例如,消費者一般對食品安全的理解比較直觀和實際,如正常食用不致生病。但是消費者是由在年齡、生活經歷、健康狀況、知識水平、購買能力等方面存在差異的個體構成的人群,因而個人的“食品安全”概念受到上述因素的影響而存在差異。當食品因貿易而跨越一國國界時,不同社會群體的人們因經濟利益、思想觀念差異,對食品安全的認知就更為多樣。可以說,在食品安全概念的法律確認過程中,充滿了不同群體間利益的博弈和妥協。此外,食品安全也是一個相對性的概念。一種食品對某些人是安全的,但對其他一些人不安全。譬如,對大多數人安全的牛奶、海鮮等食品,也可給過敏人群帶來風險;有些食品在一定攝入量下是安全的,而在超過此攝入量下是不安全的,所謂“劑量決定毒性”;有的食品以一種方式食用是安全的,而在另一種方式下食用則可能給健康帶來危險,如未煮熟的四季豆,柿子和螃蟹一起食用等。食品安全的相對性還在于食品安全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人們對食品安全的認知也并不相同。在現代食品的生產過程中,食品技術和食品安全之間存在某種程度上的悖論——技術的提高在降低某些風險的同時,往往會制造出新的風險。例如,轉基因技術和食品添加劑合成技術的廣泛應用已成為“被制造出來的風險”的主要來源。隨著人類控制食品安全風險能力的逐漸提高,人們對食品安全的期望值也越來越高,如上文提到的某些發達國家已開始主張將動物福利、生產過程和生產方法納入食品安全的考量范圍。因此,一個廣泛接受的食品安全概念要考慮食品安全的綜合性和相對性,致力于在保障公共健康、經濟利益和控制風險的成本之間取得平衡。
從詞義的角度考查,食品安全(food safety)中的“safety”指遠離危險并沒有導致危險隱患。[17]可見,安全總是與危險(風險)相生相隨。因而從判定食品是否會給人體健康帶來損害風險的角度來界定食品安全也就成為一種合理的思路。相較于單純以是否對人體健康造成損害的結果性標準界定食品安全的方法,這種從風險切入的思路有助于實現食品安全的可測度性。近年來,西方發達國家較為普遍地接納了從風險的角度來界定食品安全的思路。美國營養學專家瑪麗恩·內斯特爾就認為,食品安全是指食品的風險在可接受水平范圍之內。“對風險可接受的判斷基于:認識水平、公眾意見、價值觀及科學定義。”[18](15)但問題的關鍵是如何確定風險“可接受的水平范圍”,對此存在兩種風險評估的理念:以科學為基礎和以價值觀為基礎。以科學為基礎的風險評估觀念基于風險是客觀的、可測量的前提,通過危害識別、危害描述、暴露評估和風險描述四個基本要素,平衡風險成本與利益,來決定風險對健康損害的危險性。以價值觀為基礎的風險評估理念在評價風險時不僅基于其損害健康的潛在危險性,同時也基于個人信仰以及心理、文化和社會因素。以科學為基礎的風險評估觀念通常考慮病例數量、疾病的嚴重程度、死亡率、風險的成本和風險的收益等因素,而以價值觀為基礎的風險評估理念還要考慮風險是可見的還是隱性的、已知的或不確定的、熟悉的或陌生的、天然的或人工的、可控的或不可控的、輕微的或嚴重的等因素。應該說,在食品安全的界定過程中考慮某些重要的價值觀因素具有一定的社會基礎,“科學家們口中的風險只是疾病和死亡,‘公眾希望恐懼和憤怒’的因素也被考慮進去。”[18](20)但在實踐中,價值觀因素,如動物福利考量具有主觀性,且大多只影響食品的質量而非食品的安全性。為避免食品安全概念法律界定的泛化,筆者以為,風險“可接受的水平范圍”應建立在以科學為基礎的風險評估理念之上。這意味著食品安全的界定需建立在以科學為依據的風險評估之上,同時要抑制消費者對食品安全產生的過高期望。
綜上,筆者以為“食品安全”應界定為:食品的種植、養殖、加工、包裝、貯藏、運輸、銷售、消費等活動符合國家強制性標準和要求,各環節中的危害經科學的風險評估確認不可能損害或威脅消費者及其后代的人體健康。這一定義確認了食品安全的本質特征是“不可能損害或威脅消費者及其后代的人體健康”,規定了安全性食品的兩個檢驗標準:一是從食品生產到消費各環節的活動符合國家強制性標準和要求。這些標準和要求主要表現為食品安全法規,而食品安全法規是一國在食品領域文化、經濟和技術狀況的綜合反映。二是從食品生產到消費各環節中的危害經科學的風險評估確認不可能損害或威脅消費者及其后代的人體健康。以科學為依據的風險評估,可以為食品安全提供確定性、公正性和連續性的標準。
[1] [美]E·博登海默. 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M].鄧正來譯. 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4: 504.
[2] 孫曉黎, 等. 食品安全及其對國際貿易的影響[J]. 環境與經濟雜志. 2004, (12): 29.
[3] 張守文. 當前我國圍繞食品安全內涵及相關立法的研究熱點[J]. 食品科技. 2005, (9): 3.
[4] Ioannis S. Arvanitoyannis, Stefania Choreftaki, Persefoni Tserkezou. An update of EU legislation (directives and regulations) on food-related issues: presentation and comment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od Science & Technology, 2005, (40): 1021.
[5] 那力, 李海英. WTO框架中的PPM問題[J].法學論壇. 2002, (4): 40.
[6] 鄂曉梅. 單邊PPM環境貿易措施與WTO 規則的沖突與協調[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7.
[7] Robert E. Hudec. The Product-Process Doctrine in GATT/WTO Jurisprudence [C]// Marco Bronckers, Richard Quick. New Direction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Essays in Honor of John H. Jackson. 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0: 187, 181.
[8] Minutes of the Meeting Held on 9 October 2001. Committee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EB/OL]. G/TBT/M/25,http://docsonline.wto.org/, 2001?11?25.
[9] Tim Josling, Donna Roberts, David Orden. Food regulation and trade-toward a safe and open global system [M].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4: 152.
[10] Commission Recommendation of 29 July 1997 concerning the scientific aspects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information necessary to support applications for the placing on the market of novel foods and novel food ingredients and the preparation of initial assessment reports under Regulation (EC) No 258/97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97/618//EC) [Z]. O.J. L 43, 1997:1.
[11] Statement of Policy: Foods Derived from New Plant Varieties [Z]. FDA, vol. 57, 1992: 22, 984.
[12] 孫江. 動物福利立法研究[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8: 9.
[13] [英]彼得·辛格. 動物解放[M]. 祖述憲譯. 青島: 青島出版社, 2004: 196.
[14] 許軍, 等. 警惕新型貿易壁壘——漸行漸近的動物福利壁壘[J]. 中國檢驗檢疫, 2008, (11): 11?13.
[15] 談蕊, 劉碧云. 動物福利壁壘——南北貿易的新焦點[J].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8, (1): 86?89.
[16] Peter Stevenso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Rules: A Legal Analysis of Their Adverse Impact on Animal Welfare [J]. Animal Law, 2002, (8): 107?142.
[17] Bryan A. Garner. Black’s Law Dictionary [Z]. West Group Publishing Co., 1999: 1358.
[18] [美]瑪麗恩·內斯特爾.食品安全——令人震驚的食品行業真相[M]. 程池, 等譯.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4:15, 20.
Legal reflection on improper extension in defining food safety
HAN Yonghong
(School of Busines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Defining food safety is subject to a kind of exten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w. However, such definitions of food safety covering food quality and the other related concepts do no good in constructing a scientific and efficient food safety law in China. With an aim to change such a tendency of extension in defining food safety, legal efforts shall be made in two aspects: food safety should be based on risk, balancing the scientific factors and ethic factors in identifying food safety; the issues of PPM and animal welfare should not be penetrated into the global regulatory system on food safety without distinction.
food safety; risk; PPM; animal welfare
book=16,ebook=176
D966.1
A
1672-3104(2010)03?0045?07
[編輯:蘇慧]
2010?01?18;
2010?01?29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青年項目“食品安全國際合作法律框架構建研究”(08Q32);廣州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內地與香港食品安全合作法律問題研究”階段性成果
韓永紅(1976?),女,黑龍江海林人,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商英學院講師,西南政法大學國際法專業2007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國際經濟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