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轉:民間、地方與傳統
劉 巖
對于任何關注當代通俗文化的人來說,趙本山無疑都是一個難以忽視的對象,除了影響大,受眾廣,流行時間長(二十年的時間幾乎已經可以抵消“流行”這個詞所攜帶的轉瞬即逝的含義),相對于其他娛樂明星,其更為不可替代的意義在于一個為大眾傳媒和知識精英共同建構的神話:“趙本山——劉老根——‘二人轉代表的是農民文化、民間文化、外省市場文化”。在與權威媒體及其代表的主流文化的持續合作又不斷抗爭的過程中,這個來自東北農村的二人轉藝人為“民間”贏得了“地位和尊嚴”。[1]作家王蒙新近命名的“文化革命”或許是這種社會象征意義的最為凝練的表達,只是,其中對趙本山的評價是以一種身份區隔作為前提的:“不論是從靈魂工程角度,還是優秀作品鼓舞人角度,還是從文藝需要魯迅式的大師或是現代社會需要有機知識分子的福柯角度,誰都難以認同趙本山——劉老根式的文藝。”[2]在公眾的印象中,趙本山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小品明星,而具有代言某種民間和地方文化的資質,顯然與他為二人轉所做的推廣和正名密切相關。從舉辦“本山杯”二人轉大獎賽到打造產業化的“劉老根大舞臺”,趙本山不僅奇跡般地使一種鄉土藝術成為都市流行文化景觀,為全國觀眾所矚目,而且為了維護這個行當的“地位和尊嚴”,他甚至敢于公開抨擊作為權力媒介的中央電視臺。2004年著名的二人轉“叫停”事件及趙本山在晚會直播現場抗議央視的舉動,被相當普遍地讀解為民間與體制、文化邊緣與權力中心的沖突,尤其在市場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更是承載著從意識形態的束縛中獲得世俗生活解放的象征意義,以至當年以評選“50位公共知識分子”而聲名鵲起的《南方人物周刊》在“年終特稿”中將趙本山選入了體現“從改革開放的元年1979年至今天”的中國歷史進程的“二十五年,二十五人” [3],這種歷史性的定位與文學史家陳思和關于新時期文藝的“民間的還原”表述暗合,該“還原”的前史是民間文化為意識形態改造和壓抑的漫長時期[4]。然而,倘以今天主要由趙本山展現給公眾的二人轉作為考察對象,除非將其家喻戶曉的表演手段棄置不顧,我們很難尋找到能與意識形態全然剝離的“自在的民間形態”,與“還原”想象剛好相反,其最為顯著的“民間形式”恰是特定歷史和政治情境中的國家創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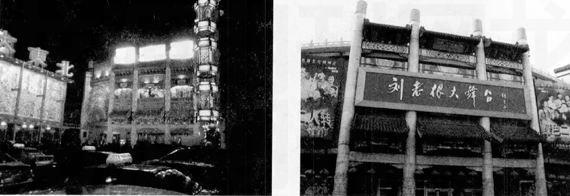
按照有據可考的歷史敘述,二人轉的前身可以追溯為清代出現的蹦蹦戲,系河北蓮花落與東北秧歌融合而成。清末民初,流散于鄉村野店的蹦蹦戲藝人開始進入東北城市賣藝,也正是在此時出現了最早的省級國家機關查禁蹦蹦的記錄(1913年奉天行政公署禁令),此后幾乎貫穿整個民國及偽滿時期,蹦蹦藝人始終處于迭遭禁捕的半地下狀態,當局的打壓主要是在整飭市容風化的名義下進行的,而《盛京時報》、《泰東日報》等東北主要媒體也為這種打壓提供輿論支持,當時語境中的蹦蹦與其說是體制外的“民間藝術”,不如說是正常市民社會的異己。蹦蹦始獲“藝術”之名,是在東北解放戰爭時期:1946年,老藝人徐生帶弟子進哈爾濱獻藝,次年受贈“藝術先聲”錦旗一面。其背景是東北解放區的新政權貫徹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開始大規模調研和建構“民間文藝”,由此為蹦蹦戲藝人塑造了新的身份。195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發出指示:“地方戲尤其是民間小戲,形式簡單活潑,容易反映現代生活,并且容易為群眾所接受,應特別加以重視”(《關于戲曲改革工作的指示》)。
指示下達后,蹦蹦戲藝人紛紛自稱是“唱地方戲的”,除進入新成立的各級“地方戲劇團”和“民間藝術團”,甚至有個別著名藝人到大學任教。在此語境中,“蹦蹦”一名因攜帶歷史中形成的歧視性含義遂為藝人所厭,經討論最終改稱“二人轉”,于1953年正式推廣。[5]從“蹦蹦”到“二人轉”的轉變,無疑在一個細微的局部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建構新的民族國家和民族文化的歷史過程,當代文學學者賀桂梅借用帕薩·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的“政治社會”和“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又譯“公民社會”)概念來闡釋這一過程與此前晚清以降的民族國家建構歷史的本質區別:市民社會的主要特征是“精英分子的獨占空間”,以其為核心的制度權利體系事實上是將廣大的底層(農村)人口排斥在外的,也就是說,在作為政治和文化主體的“公民”與作為治理對象的人口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而‘政治社會則意味著‘人民大眾是為數眾多的‘人口,政治動員的目的就是將他們組織成一個集體”,使“那些很難被國家法律制度和官僚機器組織的鄉村農民,被動員和被組織起來參與社會”。[6]作為“民間藝術”在民族文化中顯影的“二人轉”,既是這種政治動員和組織的產物,同時其本身也成為動員的工具,尤其當二人轉在吉林和黑龍江兩省被進一步建構為“吉劇”和“龍江劇”的時候,它更明顯是在地方性與民族性的辯證關系中擔當共同體想象和認同的媒介。就此而言,一些評論家習慣以“政治工具論”來看待40年代解放區以至建國后的戲曲改革,這一視角下的討論往往單純強調國家對“民間”的“改造”,而忽視了其生產和創造的面向:不僅是命名和身份,而且是今日被視為“民間形態”的表演形式的生產。王蒙這樣敘述他在“劉老根大舞臺”的混雜表演中對“二人轉”本身的指認:“唱歌說外文扭屁股翻跟頭變魔術硬氣功更不要說講笑話脫口秀了,都是小菜一碟,都是他們的‘帽兒戲。真正的藝人之藝,還得看過硬的‘二人轉。一個手絹就能丟得你如醉如癡。”[7]把轉手絹和舞彩綢扇看成是傳統二人轉的標志性絕活,是相當普遍的看法,但事實上,這兩種招牌式的表演都是在解放后的文藝會演中才出現的,尤其前者,據有的老藝人回憶,甚至是為表現“轟隆隆的機器轉得歡”的社會主義大工業生產而發明的[8]。盡管這未必是二人轉手絹的惟一起源(起源往往是多方面決定的),卻能夠反映出“民間形式”的發生發展與特定政治內容表達的密切關系。

“十七年”時期的政治內容及其文藝建構在“文革”中遭到相當程度的否定,就二人轉藝術形式而言,其最大的損失在于主要由丑角承擔的說口、使相等喜劇性表演幾乎被刪消殆盡,在極力突出完美高大階級英雄的樣板戲模式中,二人轉成了“嚴肅的歌舞”[9]。然而,正是“文革”文藝為后來最著名的二人轉丑角趙本山的形象塑造提供了靈感。從早期二人轉拉場戲到今天的春節晚會小品,一頂破舊的八角帽已成為趙氏喜劇扮相的標識,有媒體稱之為“錢廣帽”,因為按照趙本山自己的敘述,這頂帽子乃是從“文革”電影《青松嶺》中的頭號反面人物錢廣那里學來的[10]。倘若仔細比較可以發現,錢廣的耷拉帽舌與趙本山的斜帽舌或直帽舌還是有相當差別的,但后者承襲前者的關鍵并不是帽子的形狀,而是農村“二混子”式的整體人物造型。由于“文革”文藝極端類型化的人物塑造模式,這種滑稽性的造型差不多完全集中在反面角色身上,而趙本山80年代的表演不僅在人物造型上受到錢廣的影響,同時也延續了其角色類型,即主流社會文化規范下的反面典型,所不同者僅僅在于意識形態的具體內容:一個是“以階級斗爭為綱”時期的不可救藥的階級敵人,一個是“現代化”建設中亟需療救的陳風陋俗的浸染者——從1982年在《摔三弦》(二人轉拉場戲,后拍成電視戲曲片)中扮演算命先生一“摔”成名開始,直至1989年《麻將·豆腐》(二人轉拉場戲,獲觀眾評選的遼寧電視臺春節晚會最受歡迎節目)中的農村賭棍“中發白”,趙本山正是依靠這一類角色在80年代享譽東北的。當然,趙本山比“錢廣”幸運得多趕上了適宜的時勢,隨著“三突出”模式在“文革”后被打破,一方面,長期受壓抑的喜劇性表演和反面人物塑造獲得了擺脫邊緣位置的空間,另一方面,作為二人轉的主要滑稽表現手段的使相、說口被充分恢復,使相屬丑角扮功,說口在角色分工上的特征在于丑逗旦捧,以丑為主,以旦為輔。在向新時期主流大眾文化靠近的過程中,這兩種手段漸次從二人轉“四功”(說、唱、扮、舞)中突顯和分離出來,形成了與當時方興未艾的喜劇小品類似的獨立表演模式。因而,盡管趙本山80年代在東北膾炙人口的作品主要還是二人轉拉場戲(小品則只有《如此競爭》、《老有少心》兩個),但真正吸引觀眾的已只是其中“說”與“扮”兩個方面的丑角表演,這正是二人轉演員趙本山后來進而成為央視春晚“小品王”的前提。
趙本山是1990年首次亮相中央電視臺春節晚會并蜚聲全國的,以二人轉說口和使相為基礎的東北小品(以及間或在其中展現的手絹絕活)也由此漸次成為一種地方文化的代表,但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是,趙本山的第一次其實是東北文化工業最后一次全方位的宏偉呈現。1990年的央視春節晚會是以歌舞、曲藝和戲劇三隊擂臺賽的形式進行的,其中從歌舞隊隊長(闞麗君)、曲藝隊隊長(田連元)到擂臺賽總裁判(李默然),以至整臺晚會的總導演(黃一鶴)都是東北籍藝術家,這種人員構成是東北在當時體制的國家文藝格局中的地位的反映。在傳統社會主義時期,這一地區不僅是重工業基地,同時也是文化工業的重鎮,正如東北由于為新中國工業體系的建立和發展所做的突出貢獻而被譽為“共和國長子”,其文藝部門的生產也并非自給自足,而是代表著社會主義文化現代性的前沿,因此,東北的文化形象實際上是與共和國本身的形象高度統一的。但90年代初期以降,作為“老工業基地”在市場化改革中的整體命運的一部分,東北文化工業的光輝歲月隨著所謂“計劃經濟體制”的瓦解而風流云散,昔日屬于國營企業的文化生產空間和那些有形的廠房煙囪一樣漸次凋敝,以至被爆破拆除,零敲碎賣,“共和國長子”被重構為“現代化”共同體的邊緣地帶,由此裸露出一片有待資本墾殖的“黑土地”。正是在這個東北被“東北化”,或者說因“國家退出”而“地方”化的背景下,“地方戲”演員和“民間”藝人趙本山得以在全國觀眾的凝視下放大凸顯為東北文化的代言人。
然而,誠如前述,“民間”本身就是一種國家創制,趙本山的成功正是充分借重了舊有的國家文藝體制。盡管早在1981年二人轉領域就出現了體制改革的嘗試者——沈陽曲藝團的二人轉演員張桂蘭放棄“鐵飯碗”,創辦了自負盈虧的民營劇團[11],但趙本山的路徑與方向卻與此截然相反。正是在同一年,這位蓮花公社文藝宣傳隊的“臺柱子”因為在地區文藝會演中的出色表現被西豐縣劇團借調,次年又因在遼寧省農村小戲調演中獲一等獎而調入鐵嶺縣劇團,四年后又調入鐵嶺市民間藝術團,到1990年首次參加央視春節晚會的時候,他已是完成“農轉非”多年的國營文藝單位的骨干演員。即使考慮到80年代中后期開始的“走穴”式商業演出(這些“體制外”演出的火爆程度往往取決于演員在“體制內”的知名度),仍然不難發現,傳統社會主義的文藝會演和調演體制乃是趙本山最主要的“晉身之階”(中央電視臺春節晚會只是代表了這個階梯的最高也是最后一個層級),他作為“民間藝人”或“農民藝術家”的顯影在20世紀中葉以降國家吸納、組織和建構“民間”的當代史中殊非特例。但趙本山的“史無前例”在于,他適逢其時地將在原有體制中積累的“民間”象征資本成功轉換成了市場化條件下的巨大無形資產,循此邏輯,“農民藝術家”趙本山順理成章地與“本山傳媒”董事長在公眾視野里合而為一。
在趙本山的文化產業當中,二人轉既是最主要的經營商品,同時又呈現為被拯救的瀕危藝術。的確,正是由于趙本山的呼吁和影響,二人轉及其從業人員的生存狀況才逐漸為傳媒和公眾所關注,正是由于他的組織經營,許多流散于酒吧、歌廳、洗浴中心乃至色情場所的二人轉藝人才得以進入正規劇場,并進而通過電視劇和文藝晚會在大眾傳媒上嶄露頭角。但趙本山的二人轉拯救者角色卻也恰好遮蔽了二人轉需要拯救的歷史前提:與他上升為“黑土地”的文化代表幾乎同時,那個曾使他逐級晉身的國家“民間文藝”整合體制已在市場化改革中解體。在無法被傳統體制吸納為“民間藝術家”的前提下,做本山董事長的弟子和員工成了二人轉演員最好的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說,二人轉拯救者趙本山同時也是破敗的東北文化工業的接收者。
趙本山所接收的不僅是二人轉演員,同時也包括昔日相對主流的文化空間,比如今天“劉老根大舞臺”的總部所在地便是擁有百年歷史的京劇和評劇的薈萃之所——沈陽大舞臺,在地方政府、傳媒和資本合力打造新城市名片的情境中,就連本地觀眾也很難感知這里發生的“傳統”的更迭與重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民國年間,蹦蹦戲還無法在沈陽立足,除了前面提到的官方查禁,另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無法抵擋京、評、梆子等劇種的競爭壓力,以至于蹦蹦藝人“紛紛回到農村”,剩下的一些人則“改行唱梆子、評戲”,類似的情形還發生在撫順、鞍山和遼南的許多城鎮[12]。即使在新中國成立后,也不同于吉林和黑龍江兩省對“吉劇”和“龍江劇”的發明,二人轉在遼寧并未被建構為代表性的地方戲,尤其在省會沈陽一直處在文化工業系統的邊緣。然而,自2003年大舞臺更名為“劉老根大舞臺”以來,沈陽工人會堂、沈鐵文化宮、梨園劇場、群眾電影院等不同類型的原國營知名演出場所紛紛為二人轉所“占領”,在老工業基地的廢墟上呈現出“滿城盡演二人轉”的局面[13]。從許多二人轉劇場廣告和媒體宣傳中的“弘揚民族文化”、“發展地方特色”等口號來看,對于今日的沈陽人而言,二人轉已不再是一種外來的藝術奇觀,而是嵌入其身份認同的本地傳統。
當沈陽這樣的重工業城市也以二人轉標識自己的文化身份的時候,這個建國后發明的“地方戲”第一次再現出了同質性的“東北”文化,很大程度上,這種文化“本土”化是對東北老工業基地在市場化改革中的邊緣處境的回應,即通過認同趙本山們令全國觀眾矚目的“東北風”而重新成為關注的中心。但這種喜劇看客目光下的身份認同卻總免不了某種“跑偏”的焦慮,從趙本山的“小草”造型到小沈陽的“委婉”扮相,無不與“共和國長子”雄壯的主體想象相抵牾,“跑偏”的性別修辭的背后是“東北風”在常識化的文化分類和等級體系中的曖昧位置,盡管作為“民間”神話建構的一部分,趙本山的經典化過程一直在繼續,但在日趨激烈的象征資本競爭中,他的喜劇表演仍無法擺脫低俗文化的定位。
自2006年二人轉入選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來,隨著越來越多的“東北民間藝術”專家在媒體上亮相,趙本山的“二人轉傳人”身份也漸起爭議,不少人開始指斥“劉老根大舞臺”混雜的商業演出是竄亂傳統,并力圖揭示純正的典范二人轉圖譜。不過,批評者顯然并不比趙本山的擁躉更接近“地方戲”和“民間文藝”的本質,因為迄今為止的歷史考掘仍以遺忘作為前提,被遺忘的是使對傳統二人轉的想象成為可能的那個傳統——多重力量決定而充滿裂隙的“當代中國”傳統。
注釋:
[1]王蒙:《趙本山的“文化革命”》,《讀書》2009年第4期,第147-148頁。
[2]同上,第147頁。
[3]參見《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12月22日第14、15期合刊。
[4]陳思和:《民間的浮沉:從抗戰到“文革”文學史的一個解釋》,《陳思和自選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200-225頁。
[5]參見耿瑛:《正說東北二人轉》,春風文藝出版社,2008年,第6-41頁;李微:《東北二人轉史》,長春出版社,1990年,第81-87頁;孫紅俠:《二人轉大事紀》,附錄于《二人轉戲俗研究》,中國藝術研究院2007屆博士學位論文,第163-172頁。
[6]賀桂梅:《“當代文學”的構造及其合法性依據》,《海南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4期,第17-18頁。
[7]王蒙:《趙本山的“文化革命”》,《讀書》2009年第4期,第147頁。
[8]參見2008年8月9日鳳凰衛視《走讀大中華》中二人轉表演藝術家張桂蘭的口述。
[9]李微:《東北二人轉史》,長春出版社,1990年,第175頁。
[10]參見2004年2月7日鳳凰衛視《魯豫有約》中趙本山的口述。
[11]霍長和 金芳:《二人轉檔案》,http://www.guandong.com.cn/fealture/errenzhuan/erzda/dsiz13.htm
[12]李微:《東北二人轉史》,長春出版社,1990年,第85頁。
[13]藍恩發:《滿城盡演二人轉,說明了啥》,《沈陽日報》2009年9月22日。
劉巖: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文學院
欄目策劃、責任編輯:張慧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