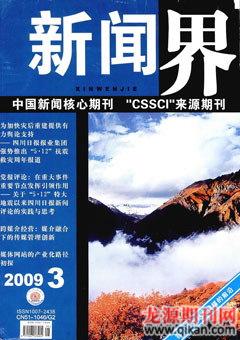《超級女聲》、《快樂男聲》的“類媒介事件”思考
張 建 夏光富 魏 波
摘要“媒介事件”是大眾傳播的盛大節日,是一種具有干擾性、壟斷性的重大電視事件。湖南衛視《超級女聲》《快樂男聲》電視娛樂節目,嚴格意義上說并不屬于“媒介事件”,但它們同時又具有了許多“媒介事件”的特征,我們姑且可以把這些大型電視文娛節目稱之為“類媒介事件”。
關鍵詞湖南衛視娛樂節目媒介事件
中圖分類號G220文獻標識碼A
一、“媒介事件”的界定
丹尼爾·戴揚和伊萊休·卡茨在《媒介事件》一書中對20世紀下半葉出現的一種全新、現代的受眾參與模式——電視媒介事件進行了全方位考察,深入、系統地闡釋其內涵、類型、結構、流程以及效果等等,被認為是“在人們認識電視的影響力方面的一個里程碑”。作者指出“媒介事件”是大眾傳播的盛大節日,是一種具有干擾性、壟斷性的重大的電視事件,通常“都是經過提前策劃、宣布和廣告宣傳的”
在《媒介事件》一書中“媒介事件”分為三種類型:“媒介事件是對電視的節日性收看,指電視直播的歷史事件,國家級事件,劃時代的政治和體育競賽;表現超凡魅力的政治使命;以及大人物們所經歷的過渡儀式——我們分別稱之為‘競賽、‘征服和‘加冕。為電子媒介展示其喚起廣泛而同期的注意,以講述一個始發的時事故事的獨特潛能提供了一種新的敘事方式。這些事件為電視機架起了一道光環,改變了人們的收看經驗”。
隨后,作者又進一步分析媒介事件的協商、表演(電視的角色)、慶典(觀眾的角色)以及薩滿教化,最后從參與者的內部效果與機構的外部效果兩個層次分析了媒介事件的效果。作者認為,媒介事件標志著一個“再生產比原生產更重要的時代”的到來,在這里電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表演空間。更為重要的是媒介事件給予觀眾以全方位的視角,從某種高度俯瞰整個歷史事件的過程,于中尋求一種歸屬感而不致于游離于社會、歷史之外。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正是媒介事件將個人、家庭與社會,過去、現在與未來聯結了起來,增加了觀眾“天涯共此時”的共同時空感和歷史歸屬感,相對而言其他的效果就顯得不重要了。“通過強調規則(競賽),表揚具有超凡魅力的偉人業績(征服),以及慶祝共同價值(加冕)來解決社會沖突”,達到一種人和社會、歷史的和諧,媒介事件真正開創了一個更加開放、民主、精彩而且更加容易溝通的時代。
“媒介事件”(media events)是指“對電視的節目性收看,即關于那些令國人乃至世人屏息駐足的電視直播的歷史事件”。事實上,我們可以稱這些事件為“電視儀式”或“節日電視”甚至“文化表演”。在所有媒介面臨被不同受眾群選擇、分割時,“媒介事件”始終表現出它對空間,時間以及對一國,數國乃至全世界的“征服”。“媒介事件”不同于一般的重大新聞及突發事件,還在于“媒介事件”是通過提前策劃、宣布和宣傳,在一定意義上是大眾被邀請來參與的一種儀式。盡管不同的社會結構與不同的文化傳統,對“媒介事件”會有不同的表達和解讀,但媒介所發揮的作用和影響,在現實生活中產生的巨大沖擊力,乃至在某種時刻“充當引起社會變革的遙控代理”方面卻十分相似,或者說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電視專家們早就發現,電視不但有熱衷追逐社會共同的熱點事件的特點,而且還有一種制造社會公共熱點的特點的獨特能力。
二、“媒介事件”的“儀式化”特征
“競賽”、“征服”和“加冕”是當代社會最具有“儀式化”特征的三種重大事件形態,所謂的“儀式化”,就是這些事件的發生遵循模式化結構,具有很強的先后邏輯性與公眾的展示性,事件始終宣揚一種升華的人類精神或價值。正是“儀式化”事件具有如此的敘述特征,所以在當代社會之中,“儀式化”的重大事件成為一種最為突出的塑造與強化社會記憶的手段。也正是儀式化事件的易“操作性”與無與倫比的影響力。大眾傳媒才會全力以赴地參與其中,把儀式化的重大事件轉化為“媒介事件”。
首先,媒介事件具有非常規性。媒介事件都是經過提前策劃、宣布和廣告宣傳,這是一系列使日常生活變得特殊起來的特殊聲明和前奏,常常在受眾之中引起一個積極的期待期。在這個時期,受眾對媒介事件的參與人物、發生樣式與時間地點等問題都可能進行積極地設想,有的熱心受眾甚至會反映到某一大眾傳媒之中,提出自己的想法與要求。實際上,在這一時期,許多大眾傳媒已經開始進行相關的回顧,激發大眾的想像力,調動受眾有關的“閱讀成規”,社會記憶的某些因素已經被激活并開始發揮作用。其次,媒介事件使儀式本身更具有戲劇性情節的邏輯性,更容易理解和更容易打動人心。我們知道,傳統儀式是一種表演性的話語形式,“說、唱、詩、舞”,合成一體,密不可分,其中每一部分都具有很強的模式化的表演特征,即每一部分都具有實踐的可感性,又具有超越這一層面的象征意義。而在儀式的實踐的可感性方面,儀式經過積淀,可以形成詛咒、祝福、發誓、許愿等話語內容與對偶、排比、反復等特殊話語形式來區分日常生活活動,強化儀式的參與性,制造記憶“共同體”。可見儀式是模式化的綜合活動,在認識方面,它以視、昕、觸、味、嗅的多種感知方式影響參與者的心理感知,強化記憶形象;在社會層面,儀式則宣揚基于心理感知的意識形態的意義和價值,使之成為社會化的記憶形式,進而形成某種支撐社會政權結構的國家意識形態或社會意識。
現代社會之中,傳統儀式活動雖然隨著宗教的衰落而衰落,但是,傳統儀式眾多因素卻被現代重大活動所采用,現代重大活動因此具有一般儀式化的特征。現代大眾傳媒大規模地加入社會重大活動,就此整合出“媒介事件”,儀式化特征也就成為“媒介事件”的重要特征,這樣,“媒介事件”本身蘊涵著眾多傳統儀式因素,同時又具有強烈的現代特征。
三、“商業邏輯”與“媒介事件”
戴揚等人認為:“我們把媒介事件看作是假日——它使某些核心價值或集體記憶的某些方面醒目起來。這種事件往往描繪理想化的社會形態,向社會喚起的是希冀而不是現實”。可見“媒介事件”實質上是一種特殊的“假日”,它整合提升了傳統假日的文化蘊涵,即在娛樂休閑之外,加上國家、民族乃至人類的精神與價值。這樣,“媒介事件”就涉及到了社會文化神圣核心的某些方面,實際上,這一神圣核心很難由某一社會個體來承擔和傳播,它的塑造與傳播需要偶像群體、組織活動與大眾傳媒系統。因此,“媒介事件”所參與塑造的現代“假日”,也成為儀式或者包含儀式的一部分,它要求“參與者”——直接參與者和傳媒受眾盡量減弱游戲休閑的心態,而是要激發起驚訝、贊嘆與虔誠、崇敬的情感。媒介事件“促使觀眾聚集在電視機前進行集體的而不是個體的慶典。在慶典過程中,觀眾常常被賦予一種積極的角色。這些事件以集體的心聲凝聚著社會。喚起人們對社會及其合法權威的忠誠”。
“媒介事件”既然成為一種大型綜合化媒介節目形態,
那么它就要不可避免地融入大眾傳播機制之中,成為一種超級媒介產品。我們知道,由于“媒介事件”的巨大魅力,“媒介事件”是大眾媒介高收視率(高發行量)的法寶,這是各種大眾媒介競爭的焦點,也是吸引廣告商的最亮點;另一方面,“媒介事件”本身需要投入巨大的制作與傳播費用,高投入希望高回報,大眾媒介當然也渴望媒介事件帶來巨大的商業價值,實際上。每一次“媒介事件”都少不了大型公司的經濟贊助。然而與一般媒介節目形態不同,“媒介事件”在內容與傳播形式方面具有神圣性、儀式化與非常規性,這樣,廣告就很難像在一般媒介節目之中那樣“為所欲為”,媒介事件由此又呈現出復雜的媒介經濟特征,對于競賽類媒介事件,尤其是體育競賽類媒介事件,廣告則全面滲透,目前,廣告實際上已經完全“降服”了包括奧運會在內的各種體育賽事,商業邏輯成為這些媒介事件的重要敘述邏輯之一。“作為廣告點的支撐,這一盛會的電視影像業已成為一種服從于市場邏輯的商品,必須采取某種制作方式,以盡可能最長久地抓住并吸引住盡可能廣泛的觀眾”。
其次,利用“媒介事件”的巨大魅力光環,大眾媒介與各種大型組織制造出大量“類媒介事件”。這些“類媒介事件”具有媒介事件制造與傳播的一切特征,大規模的事前宣傳、超大型現場直播、傳播文本的綜合化等等,而在內容方面,這些“類媒介事件”則擴大到重大節日慶典、大型文娛活動、大型組織活動、文物挖掘活動和自然奇觀等領域。僅從內容角度看,這些“類媒介事件”缺乏媒介事件的嚴肅性、儀式化特征,但是,大眾傳媒機構利用自身強大的傳播系統使這類事件非常規化,突出這些事件的喜慶、狂歡、新奇、奢華等特征,強化高收視率與高回報率,使其達到了類似于“媒介事件”的傳播效果,形成一種新型商業化媒介事件形態。總之,商業邏輯已經成為當代媒介事件的重要邏輯之一,政治意識形態的、社會文化的、商業的因素在大眾媒介之中緊密地糾纏在一起。
四、關于娛樂節目《超級女聲》、《快樂男聲》的“類媒介事件”思考
隨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和受眾素質的提高,電視媒體已經不僅僅是歷史的記錄者和傳播者,它已成了一個人人可以參與的公共平臺。從某種意義上說,電視本身就是一個“秀場”,是制造“媒介事件”的很好載體。它完全有條件成為事件的發源地。《超級女聲》、《快樂男聲》的海選活動,就像一座橋梁,貫穿了社會和電視,在受眾心目中成了具有強大吸引力和美譽度的“媒介事件”。它也讓我們看到了作為電視娛樂節目介入社會、介入市場的最佳切合點。
《超級女聲》、《快樂男聲》作為一檔電視娛樂節目,嚴格意義上說它并不屬于丹尼爾-戴揚等人分析的“媒介事件”,但作為近幾年湖南衛視最重要的大型電視直播節目,它們又具有了許多“媒介事件”的特征:
1、《超級女聲》《快樂男聲》是一場“平民加冕”儀式
現代社會之中。許多傳統政教重大主題失去威力,崇敬與崇拜的態度在日常生活中要么產生轉移(如現代偶像崇拜),要么日趨減少。“媒介事件”重塑當代重大事件的儀式化崇敬氛圍,依然要“引用”傳統儀式的崇敬因素,運用大眾媒介技術使其進一步強化。湖南衛視娛樂節目《超級女聲》、《快樂男聲》就注意到了儀式化特征對于電視節目的重要意義,它采用“競賽”的形式,經過提前策劃、宣布和廣告宣傳,激發大眾的想像力,調動受眾有關的“閱讀成規”,節目主持人引導著受眾“參與”各種儀式化的活動,其職責的精華部分在于醞釀與調動大眾情緒,不斷升華這一場全民造星運動從“平民”到“女皇”“國王”的儀式化意義,湖南衛視還運用嫻熟的傳播技巧調動大量的媒介參與到儀式化事件的塑造與傳播之中,從而形成一個更大的多媒介文本,這個多媒介文本體現在電視頻道的超長時段直播、報刊主要版面、網絡的超級鏈接之中,由此,這個多媒介文本就為儀式化重大事件設置了一個超強“議程設置”,產生傳播效果的“倍增”現象,把社會的主要注意力集中過來,使每一個受眾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
2運用“商業邏輯”,定義“節日”,邀請大眾
湖南衛視娛樂節目《超級女聲》一開始就把欄目定位為商業化的大眾娛樂節目,注重高收視率;投入巨大的制作與傳播費用,希望高回報;吸引廣告商的注意力,以求成為一種超級媒介產品。
“媒介事件”本身不是節日,要提升事件的吸引力,突出強調事件的意義和價值,電視就要努力放大和擴張事件,把事件塑造成“節日”,并且把“節日心理”滲透到觀眾內心,促使其產生“節日行為”。通過長達近半年的造勢,“海選”及最后的“總決選”,電視、網絡、報紙等多媒體聯動,《超級女聲》、《快樂男聲》節目變成了大眾“想唱就唱,表現自我,釋放心情”的節日。每逢周五晚八點半的直播又培養了一大批忠實的觀眾,在對“節日”的期待中關注“超女”“快男”的所有事件,從而不斷放大節目的影響力。
另一方面,“媒介事件”的現場觀眾非常有限,大部分的觀眾需要通過電視來參與到事件當中。確認觀眾的“參與”地位,強化其“參與”意識,“邀請”觀眾共同慶祝“節日”,是電視編導的首要任務。《超級女聲》、《快樂男聲》經過策劃和準備,提前進行直播預告,提醒和督促觀眾觀看直播,預告片的頻度和強度逐漸加強,并在直播前夕達到高潮,占據電視節目的黃金時段。觀眾不斷地被邀請和催促,經過觀眾之間的人際傳播,這種“大家都被邀請”的感覺被強化,觀眾對直播充滿了收視期待。觀看直播,成了生活中一件大事,如同節日一般為人們所期待和準備。
3建構“媒介事件”的節日語境,引導觀眾“慶祝”節日
較之丹尼爾·戴揚在《媒介事件》中提出的“禮拜儀式語境”,“節日語境”可能更加通俗易懂。從最初地位看,“媒介事件”矗立于日常生活之外,是對日常生活的外來干擾,電視通過強化觀眾的“節日心理”和“節日期待”,并借助群體傳播、人際傳播等方式形成的輿論環境,把這種“非日常”轉化為“日常”,為“媒介事件”的直播營造了一個特殊的節日語境。這種語境反過來對于“媒介事件”之外的日常的東西顯示出排它性。在大眾媒介的高密度“轟炸”下,《超級女聲》《快樂男聲》娛樂節日成為人們日常談論的熱門話題,觀眾也由自己的喜好形成“玉米”、“筆迷”、“涼粉”、“花生”等“粉絲”團隊,在網絡上大量發表意見,即便只是“準粉絲”或者“非粉絲”,在被電視“要求”收看的情況下,也為自己親身“見證”和“經歷”了比賽過程而驕傲。沒有收看直播的人,在辦公室里失去了發言權。在節目語境中,平時的日常節目被弱化甚至取消。
4利用“傳染性”形象,幫助觀眾體驗“在場”
“媒介事件”對于大多數受眾來說具有遠地點性。相對有限的現場觀眾,電視觀眾有明顯的“不在場”感覺,這勢必影響觀眾的參與熱情。家里的電視觀眾,會因為周圍現實環境與事件的“無關”而受到日常生活的“干擾”,他們很難像現場觀眾那樣全情投入以慶祝節日。為了調動觀眾積極性,電視必須幫助其產生“在場”的感覺,即便只是幻覺。《超級女聲》、《快樂男聲》把競賽的裁判權一分為三,代表權威的專家評委、代表大眾的大眾評委、場外所有的觀眾(只需用手機投票既可),在最后的決賽中更是將評判權交給了手機票數。電視觀眾在節目中找到了自己的話語權,于是拿起手機,親身體驗“在場”的感覺,大量的“粉絲”甚至走向街頭拉票,烘托出了不亞于比賽現場的氛圍,于是觀眾們產生了“在場”的幻覺。
5實現從“家庭空間”向“大眾空間”的轉化
通常,“媒介事件”發生在大眾的開放式空間里,而絕大部分觀眾是在自己的家里收看電視,家庭空間相對私人和閉合。有趣的是,盡管各個家庭相對獨立和分裂,電視卻利用媒介事件“把互動的個體的網絡挨家到戶,跨越極其巨大的邊境聯結在一起”使分散在各個家庭的觀眾,在同一時間共同關注同一個事件,甚至表達出同樣的情感。
大眾媒介湖南衛視利用“媒介事件”的巨大魅力光環,通過自己強大的傳播能力,采用儀式化的特征,使娛樂節目《超級女聲》、《快樂男聲》從選秀到決賽都呈現非常規化,突出自由、個性、民主、新奇、狂歡等色彩,強化高收視率與高回報率,使其達到了類似于“媒介事件”的傳播效果,形成一種新型商業化媒介事件形態,我們姑且可以把《超級女聲》《快樂男聲》這些大型電視文娛節目稱之為“類媒介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