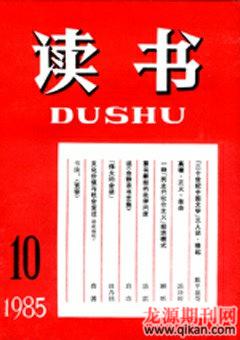讀《許政揚文存》所想到的
程毅中
看到了剛出版的《許政揚文存》,在高興之余,不禁又感慨萬千。政揚同志離開我們已經快二十年了。他在一九六六年遭迫害而辭世,留給我們的只有這一本篇幅不多的文集,還是好幾位朋友煞費苦心收集起來的,真是太少了!在史無前例的十年浩劫中,我輾轉聽到了他不幸的消息,無法表示自己的哀痛,只能默默念誦李商隱的詩句:“平生風義兼師友,不敢同君哭寢門。”
我上燕大時,他已經上研究院了。當時中文系全系只有二十兒個人,我們因此有忘年(年級)相交的機會。今天重讀他的殘稿,還象從前一樣,給我以許多知識和啟發。
政揚對宋元小說戲曲語詞的研究,是化了多年心血的。盡管遺留下來的文稿不多,給我的印象是文辭委婉,立論嚴謹,真是文如其人。他并不是一個專攻考據(以往所謂的樸學)的學者,然而繼承并發揚了清代以來不斷有所發展的優良學風,竭力做到了“例不十,法不立”。他解釋一個詞語,一般地總要找出十來個例證,然后再下判斷。當然,他在論文里并沒有列舉出全部的例證。只要看一下《文存》中《宋元小說戲曲語釋》(三)的“香
政揚的辛勤耕耘取得了收成。他的論文有不少新的突破。例如在“三都捉事使臣”條中,對“三都”的解釋提出了討論。有人把“三都”解釋為刑部、御史臺、大理寺三個部門,《語釋》則從“都”字探索唐代的軍隊建置,一直發展到宋代,“大凡百人為都”,從而考證到宋代開封府防備盜賊的街卒,也分設營、都等編制,所以開封府的捉事使臣也可以按都分置。
“一笏、一錠”條,提出一笏究竟多少的問題。曾有人認為一笏即一鎰,二十四兩。《語釋》引證《墨莊漫錄》和《可書》所載宋徽宗賜給米芾白金十八笏的故事,得知一笏即五十兩。繼而考證“錠”字的起源,并不如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所說的始于元代,而是宋、金時已通行。又據《云麓漫鈔》“煉銀每五十兩為一錠”的記載,證明一錠就等于一笏。接著又考證了元代銀鈔一錠,最初也相等于銀一錠;鈔一貫,相等于銀一兩。不過后來鈔逐漸貶值了。弄清了這些事實,也就糾正了錢大昕的一些說法。歸納起來,才作出結論:“一笏即一錠,也就是一鋌。”政揚把這個結論,寫入了一九五八年出版的《古今小說》注本。一九六四年《人民日報》報道,陜西長安縣發現的唐代丁課銀錠,正是五十兩一錠,其規制正與政揚的假設吻合。可見千載以前的名物制度,經過周密的研究,也是可以比古人弄得更清楚的。
《文存》中的《話本征時》是一篇力作,表明他從語詞的考釋,進而推論作品本身的年代了。《簡帖和尚》,以往文學史家公認為宋代話本,主要依據就是《也是園書目》把它列為宋人詞話,政揚卻從話本中的一句插敘發現了問題。《簡帖和尚》講到皇甫松“叫將四個人來,是本地方所由”,作者表白說:“如今叫做連手,又叫做巡軍。”政揚注意到新詞“連手”、“巡軍”取代了舊詞“所由”的現象,考證出“所由”的名稱流行于南宋之前,而“巡軍”則設置于元代。還根據開封府沒有左右司理院的制度,說明話本并非宋代人所作;而從其他一些細節又表明,它的誕生離開宋亡還不會太遠,應該歸入元人作品的行列。這是一個新的發現。以往我們以《也是園書目》作為唯一的依據,對“宋人詞話”的說法深信不疑,未免有片面性。當然,政揚并沒有忘記作必要的說明:“小說創作于元代這一事實并不妨礙它的題材可以來自宋時。”在這里,我也想插一句話,《簡帖和尚》的題材,大致可以肯定它來自洪邁的《夷堅支志》景集卷三《王武功妻》條,那就在南宋以后。話本作為一種說話藝術的底本,在傳說、傳鈔、傳刻過程中不斷有所修改,是不足為奇的。小說可能始創于南宋,到了元代或明初寫定時,自然會加上一些時代的標記。這對我們區分宋元明三代的話本造成了許多困難。如果說《簡帖和尚》的確切年代還可以作進一步探索的話,那么《戒指兒記》的時代特征就更為明顯了。因為以商人子弟而點報駙馬,只是明代才可能有的事。政揚從典章制度上找出了確鑿的證明,才象老吏斷獄一樣下了判斷:“可以得出結論:象阮華這樣的商販子弟,會去應選駙馬,對宋代的人說來,是完全不能設想的。同樣也可以得出結論:話本《戒指兒記》只能是明代人的手筆。”
政揚并不滿足于對語詞和年代的考證,也努力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分析作品的思想和藝術。如《論睢景臣的<高祖還鄉>〔哨遍〕》也是一篇力作。他從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的特征,說明其為元代現實生活的反映,而不僅是一個歷史題材的演述。“作者所描寫的對象,主要是現實生活,而不是歷史”。通過精細的分析,挖掘出漢高祖和鄉民兩個形象的典型意義,比較深入地探索了《高祖還鄉》藝術構思的特色。本文的某些問題當時曾引起討論,政揚也虛心地表示過,自己“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美學理論和古典文學方面,都還只剛剛起步”。然而,過了三十年之后重讀這篇論文,還給人以新鮮之感,并沒有使人覺得有簡單化、庸俗化的毛病,盡管它決不是完美無缺的結論。《向盤與紅頂子》一文對《老殘游記》作了十分精辟而細致的分析,肯定地指出劉鶚的政治立場是反動的,但書中也有從生活中概括出來的真實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形象。劉鶚在《老殘游記》里所寫的三個封建官僚的形象,“顯示出了自己獨特的、深刻的暴露現實的力量”。政揚認為:“在《老殘游記》一書中,真正激動人心的,不是劉鶚的反動的說教,而是體現在形象中的生活;并不是老殘心愛的那個‘外國向盤,而是那些引起他無窮憎恨和不斷的抗議的站籠、夾棍、拶子……,一句話,那個血染的紅頂子。”政揚這些平允而明快的剖析,是很有說服力的。他提出的問題也是帶有普遍意義的。形象與思維的關系問題,當時還沒有引起評論者足夠的注意,而且在某些簡單化、機械化的思想指導下,往往強調作家世界觀的決定作用到了不適當的程度。政揚在介紹《老殘游記》的一篇短文中,明確提出了形象大于思維的論點,這在當時也是難能可貴的。
政揚對宋元時代的語言、歷史、地理、典章制度、風俗習慣等方面都作了全面的考查,因此除了小說、戲曲中的語詞之外,還研究到了《清明上河圖》里的橋名問題。他對畫中的一座大飛橋作了深入的探討,提出三點理由,說明它并非相傳所說的虹橋;又舉出三點理由,說明它是汴京內城角門子外的下土橋。證據確鑿,論斷精密,這在中國美術史上也是一個新的發現。于此可以看出政揚對中國古代文化的深厚修養。他不僅對宋元小說戲曲有獨到的研究,而且對中國文化史的許多方面以至外國的文學、藝術,都曾廣泛涉獵。我還記得,他在讀書讀到疲倦的時候,往往翻閱一些西洋名畫集之類,欣賞一下美術作品,作為精神調劑。過后,又全神貫注地鉆到書里去了。他讀書很廣,鑒賞力很高,是我十分欽佩而又學不到的。錢鐘書先生的《談藝錄》一書,就是他介紹我讀的,他說:“讀了這樣的書,可以激勵自己多讀一些書。”今天,我讀了他的《文存》,同樣也產生這樣的感想,可以激勵自己多讀一些書。《文存》所收的文章,以宋元小說戲曲的語釋為主,但除了專門研究小說戲曲的同志需要參考,其他愛好中國文學的同志也不妨一讀,從中也可以得到一些啟發并學到一些治學的方法。
政揚平時積累了大量的筆記和資料卡片,有許多只是小紙條,在文化大破壞的一場風暴中隨著他才華未盡的生命一起被毀滅了。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損失!如果不是這場浩劫,他一定會給我們留下更多幾倍的成果,那怕是未曾整理的資料也好。這本《文存》里所保存的一部分成果,都是他四十歲以前做出來的。在我們這個平均壽命不斷增長的國家里,當時他還是一個青年人。周汝昌同志為《文存》寫的代序說:“‘文化大革命完全毀了政揚的心血(最主要的是他多年精力之所聚——驚人數量的網羅宋元一切圖籍的資料卡片功夫),也毀了政揚的精神生命和生理生命。這是一個很大的損失。這種損失,‘大到什么程度?我不必做出什么‘科學估量。我只想說,象政揚這樣的學人,在我們這一代說來,乃是難得多見的極其寶貴的人材,一旦充分發揮了他的作用,在我們的學術史上將會煥發出異樣重要的光采。”我覺得這些話并不是朋友們的私言。現在這本《文存》的價值恐怕不能以現存的篇幅來衡量,它表明我們新中國的第一代學者曾在宋元小說戲曲的領域里進行了辛勤的開墾,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既為后來者鋪墊了路基,也為青年人指引了治學的門徑。
政揚的生平和學術方面的活動,汝昌同志在代序中已有了簡括的敘述。我不能多作補充,只想到一點:政揚體弱多病,在學校時就經常發病,飲食極少,可是他苦學不廢,真到了“衣帶漸寬終不悔”的境界。后來聽說他的病情日益嚴重,還是抱病堅持工作,以致他的身體始終不能康復。如果他在生理上能夠保持健康,也許在精神上還能頂得住那次暴風驟雨的打擊。因此我想到,對于忘我工作而超過自己負荷能力的同志來說,還是要愛惜自己,當然更需要社會的關心和愛護。政揚逝矣,他的學術文章還是有頑強的生命力的。
一九八五年三月
(《許政揚文存》,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十一月第一版,1.0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