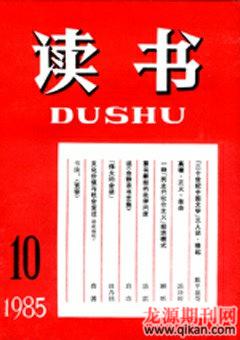文化的轉折 觀念的變更
王晴佳
用某樁事件、某次社會運動抑或某個人物的著作來界定一個時代,這在現代西方的歷史學和社會學理論中,已經不再具有吸引力。然而,對于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發生的震動整個歐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人們卻很難對之熟視無睹。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正是這場戰爭以及隨后出現的十月革命,毀掉了近代以來資產階級一直信奉、并賴以生存的社會歷史觀念,不僅“西歐中心論”搖搖欲墜,而且歷史的“進步”觀念也難以維持。而在戰爭前后發生的物理學上的一系列突破,更為打破以往的傳統觀念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理論背景。以歐洲社會為主體的、近代以來領先于世界的“西方”沒落了,新的多元的世界文化隨之出現(參見〔美〕H.斯圖亞特·休斯《歐洲現代史》中譯本,第49頁)。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位來自德國一所中學的普通教師奧斯瓦爾德·施本格勒(亦譯斯賓格勒)的著作一一《西方的沒落》,贏得了巨大的成功。顯然,施本格勒的吸引力并不全在于那個多少有點聳人聽聞的書名,也不在于那些牽強的類比、杜撰的概念和自作主張的“構畫”;而是因為,在那些生硬、粗糙的提法背后,施本格勒不無天才地發現了以往歷史觀念的缺陷,提出了不少對于現代西方文化思潮仍具影響的思想。
歷史觀念的變更
把人類歷史的發展視為一個統一的走向進步的過程,這是十八世紀以來大部分西方歷史思想家的幾乎共同的特征。作為近代西方歷史哲學的創始人,意大利的維科(一六六八——一七四四)在《關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學原理》中,率先把歷史劃分為三個階段:“神權時代”、“英雄時代”、“人權時代”。德國的赫爾德爾(一七四四——一八○三)則用“詩的時代”、“散文時代”和“哲學時代”來命名。到黑格爾,所謂歷史也就是精神的展現、發展的過程,經歷了從東方世界、古典世界到日耳曼世界的躁動。十九世紀中期,奧古斯特·孔德在實證主義哲學的基礎上,也把歷史的發展分為軍事時期、過渡時期和工業時期三個階段。盡管上述這些人物在時間上有先后,思想背景和理論內涵也各個不同,但不可否認,他們的歷史觀都以相同的觀念為基礎,即歷史首先是統一的、一線的走向進步的過程,同時,這種進步又是循著某種軌道或規律行進的。一般說來,需要經過三個階段(在這點上,唯有孔多塞(一七四三——一七九一)是例外)。對于他們這些自信、樂觀的歷史觀念,施本格勒不無嘲諷地說:“這是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空洞無物且又毫無意義的體系。”(中譯本,第31頁,因現有中譯本只節譯了《西方的沒落》第一卷導言及第二卷,故以下參引英文全譯本)。而對歷史發展的三階段論,他的評論更為刻薄:“顯然,用在世界年齡上的神秘數字三,對于形而上學者的喜好是有高度誘惑力的。歷史被赫爾德爾描寫成人類的教育,被康德描寫成自由觀念的演化,被黑格爾描寫成世界精神的自我擴張,被其他的人用其他的詞描寫著,至于它的基本設計,每個人只要替傳統的三分法想出一些抽象的意義就心滿意足了。”(中譯本,第36頁)施本格勒的此種態度,顯示了二十世紀以來大多數歷史學家對于以前“形而上學”的歷史哲學的基本傾向:鄙視那些貌似宏偉、嚴密,然而卻不無漏洞的歷史發展模式,而力圖尋求歷史本身的“靈性”(克羅齊),或者歷史中的“個體”(李凱爾特)。一句話,歷史不再是某幾個思想家主觀“設計”的產物,更不是單線條的、從低到高、由惡及善的進步歷程。
從上述論點出發,施本格勒指出:傳統的歷史觀念的根本缺陷在于,所謂的“世界歷史”并不是一個整體,而是被選定的一部分。“西歐的土地被當作一個堅實的‘極,當作地面上的一塊獨一無二的選定地區,理由似乎只是因為我們住在這里;而千萬年來的偉大歷史和遙遠的強大文化則都被極其謙遜地繞著這個‘極在旋轉。”(中譯本,第32—33頁)毫無疑問,施本格勒認為,這樣的眼界過于狹隘,而其理論也過于武斷,以致沒有說服力。為此,他提出了這樣一個論斷:“普遍的有效性永遠包含著從特殊到特殊的論證中的謬誤。”(中譯本,第42頁)其含意是:任何思想家都只能在他所生活的條件下進行歷史的認識和理解,不存在什么普遍的、永恒的東西。因此,所謂歷史發展的普遍模式便成了無稽之談。在這里,我們除了見到施本格勒力求打破“西歐中心”的愿望之外,還可發現一種濃厚的相對主義傾向,而且正是后者構成了施本格勒歷史思想的主體內容。
企圖突破西歐為中心的歷史發展的一線進程觀念,是施本格勒歷史哲學的一大特色。他的目的是“在一種包括全部千萬年來歷史的世界形式的遠大的、不受時間限制的遠景中去考察。”(中譯本,第57頁)于是,羅馬帝國的某些歷史現象在現代的歷史中仍不斷再現,而十九和二十世紀也不再看作是世界歷史上升直線的頂點,而是“從每一完全成熟了的文化中都能看到的一個生活階段。”(中譯本,第64頁)人類歷史不外是諸種文化自行生長、衰亡的舞臺。這些文化被施本格勒分成八種,即埃及文化,巴比倫文化,印度文化,中國文化,古典文化,瑪雅文化,伊斯蘭文化和西歐文化。它們自成體系,“同時”演進,經歷大致相似的從鄉村到城市,從文化到文明的過程。這就是風行一時的文化形態史觀。這種觀點從內容上來說,體現了一種宏觀的研究歷史的態度,打破了以西歐歷史為中心的理論框架,反映了西方文化從近代走向現代、從一元走向多元的發展。然而究其實質,施本格勒在理論上所嘗試的突破,本身是歷史發展的產物。很難設想,在資本主義國家之間激烈爭斗,歐洲大陸戰火紛飛的年代,人們還能編織那些“進步”、“美好”的理想。施本格勒著作鮮明的時代特征,是使他迅速成名的重要因素。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一心想打破抽象的、思辨的歷史哲學體系的施本格勒,到頭來仍然擺脫不了傳統的誘惑。他的文化形態史觀雖然不同于以往的歷史發展模式,但實際上還是一種對歷史進程的“體系式”構想。只不過在結構上稍為龐大,內容上更為豐富、復雜一些而已。這是文化轉折時期的一種特殊現象。然而就文化思潮的發展和遞嬗而言,“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馬恩選集》第一卷,第623頁)又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又具有共同性。
兩個“世界”——自然和歷史
把世界作自然的和歷史的區分,這是施本格勒整個體系的出發點。在導言中,他說道,所謂世界歷史的形態學觀,就是指用一種與自然科學方法迥異的思索手段得出的,盡管它也要“檢視世界的形式、運動及其最終意義,但這一次是按一種截然不同的安排去檢視的,不是把它們放在一個無所不包的總圖中,而是把它們放在一個生活的圖景中,不是把它們看作已成的事物(things-become),而是把它們看作方成的事物(things-becoming)。”(中譯本,第17頁)所謂“截然不同的安排”,施本格勒認為就是類比(analogy),唯有通過對地球上各種文化的類比,才能領悟“活的形式”的歷史。
為此,他在書中作了如下的努力:首先,他認為,作為方成的事物,歷史沒有“范圍”(extension)唯有“方向”(directions),它在人們的醒覺意識中存在,不斷流動,如同生命。而自然則相反,它是死的、以往的。因此,研究歷史和研究自然的方法不能等同。“前者通過類比、描畫、象征,后者則靠公式、規律、體系。我們用學習來體驗已成的事物,而對于方成的事物,我們只能通過生活,通過深刻地、不可言傳的理解來體驗。”(C.F阿特金森英譯本,第一卷,第55—56頁)同時,這兩者又如同“精神”和“世界”那樣互相聯系,不可分離。與此相照應,在知識形式上,歷史表現為“可能的”,而自然則表現為“確實的”。
對于自然和歷史,人們的觀察角度也必然是不同的,對于自然,人們能夠站在一種超然的地位上觀察,而對于歷史則不能這樣。由于,歷史的不斷流動,人們即使在年代劃分上也是相對于現在而言的。施本格勒舉例說,十九世紀的人能夠把古希臘稱為“古典時代”,把自己的時代稱為“近代”,而古希臘人也能把古埃及稱為古代,自己是近代。于是,施本格勒進一步推理,自然是由已成的事物所構成,因此可以用規律來概括。而歷史則是由不斷發生,并且不再重現的單個事件組成的,它是有機的、不可逆的、沒有過去和未來之分。任何規律、因果法則都是反歷史的。借諸這些方法無法理解歷史的本質,唯有通過冥思才能做到。自然和歷史的差別,就象歌德與康德、貝多芬與牛頓、倫勃朗與笛卡兒的差別一樣。盡管如此,自然和歷史,已成和方成之間仍有聯系。“歷史如果被確定的處理就不再是純粹的‘方成了。”歷史學家必然要運用一些已成的科學方法進行研究,歷史學家的工作必須含有一定比例的已成的東西。(英譯本,第93—94頁)
施本格勒斷言:“沒有歷史科學,只有服務于歷史的輔助科學,它們確定以往的事物”,在歷史中,資料都具有象征意義,沒有真理,只有事實。(英譯本,第133—134頁)他的這些思想,對以后的歷史相對主義者影響很大。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施本格勒把自然和歷史作了嚴格的區分,但在許多地方,他也發現和指出了存在于自然科學內部的相對性。在物理學中,人們面對的是已成的、確定的事實,但施本格勒認為,即便如此,物理學家在思索、工作的時候,“他不是控制著,而是被一種下意識的形式控制著,因為在活的活動中,他總是作為他的文化、他的時代、他的學派、他的傳統的人而存在。”因此,“每一個事實,即使是最簡單的事實,從一開始就包含著一種理論。”施本格勒甚至這樣斷定,“對自然的所有認識,即使是最確定的認識,也得基于一種宗教信仰而成立。”由此推理,他認為天主教和唯物主義對世界的看法并無二致,只是表述的語言不同而已。(英譯本,第379—380頁)這里表現出施本格勒唯心主義的世界觀。但是,揭示自然科學內部的相對性來發展其認識論上的相對主義,卻是施本格勒高人一頭的地方。他的這種思想不僅在當時領先,而且也超過了他的后人,三十年代美國歷史學家卡爾·貝克爾、查爾斯·比爾德的歷史相對主義觀點。不過,施本格勒的上述論點顯然與其整個理論體系相矛盾,這是他的思想粗疏的表現。
施本格勒對于物理學的見解無疑不能與下列事實分開。在第一卷結尾處,他提到了在他成書前不久物理學的一系列突破,并指出了它們在觀念轉變上的意義。他指出,由于相對論的誕生,牛頓的萬有引力理論和能量守恒定律都失掉了永恒、絕對的意義。同樣,普朗克的量子理論和N.玻爾的結論都指出了牛頓以來質量不變假說的謬誤。在談到熱力學第二定律——熵概念的時候,施本格勒甚至有點不無得意地談到它對自然科學的巨大沖擊。熵揭示了存在于自然科學中的不可逆的、無序的現象,抽去了嚴格的因果關系的基礎,而代之以概率。這樣,自然和歷史、已成和方成便開始混合,活生生的人及其研究角度進入了無機的自然界。(英譯本,第418—422頁)由此,我們可以得知施本格勒有關自然科學相對性論述的現實基礎了。自然科學的更新常常促使哲學改變自己的形式。在某種意義上,施本格勒是有意想適合這種改變了的形式的。但是,也許是他對那些物理學進展注意得太晚,或者是他的理論形成得太早,他的上述論述盡管不無灼見,卻始終不能與他“自然對立于歷史”的反實證主義的總體傾向相合拍,倒反而顯得有些不諧調。
把自然與歷史相對立,這在德國思想家中不乏其人,威廉·狄爾泰和新康德主義哲學家都為之作出了努力,施本格勒在許多方面承襲了他們的觀點,同時又吸收了叔本華、尼采甚至歌德思想中的某些非理性主義的思想。然而,用上述理論重新構造整個歷史哲學體系,用生物有機體來比喻歷史,并與“生命哲學”相溝通,則無疑是施本格勒的“創造”。他的文化形態史觀在西方的歷史思想發展史上,開辟了一個嶄新的認識天地,盡管這一史觀帶上了濃厚的悲觀主義色彩和應命救世的時代特征。
如果把自然和歷史看作兩大對立主題,那么相對主義則是《西方的沒落》的主要基調。施本格勒的歷史相對主義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歷史觀,以勾勒每個文明獨立的發展歷程、摒棄“進步”觀念的文化形態學為特征;二是認識論,對施本格勒來說,一切在流,一切在變。真理只存在于思維領域中,而在無始無終的歷史進程中,唯有事實,而且所謂事實也只是相對的、離不開主觀的。這種理論直至今天仍是現代西方史學理論的主要傾向(參見拙作《試析現代西方史學中的相對主義傾向》,見《華東師范大學學報》一九八四年第六期)。
宿命的文化、有機的歷史
用生物有機體來比擬歷史,這是施本格勒理論體系的主要內容,然而,他對此的表述卻常常是概念重疊、行文含混的。即使是他列出的附表,也同樣十分費解。比較容易概括的地方,體現在如下三條。
第一,歷史是有機體,是活生生的,具有青春、生長、成熟、衰敗的周期性特征,施本格勒宣稱,他的這些思想是從歌德那兒來的。“歌德所說的活生生的自然正是我們在這里所說的世界歷史,即作為歷史的世界。”(中譯本,第45頁)是有機體,就必然有生長和衰老的歷程,因此,地球上所有的文化都是宿命的,現代西方文化亦是如此,“悲嘆它和幻想它是不能改變它的。”施本格勒認為:“每種文化都有它自己的文明,……文明是文化的不可避免的歸宿。”這里體現的是一種周期性的、嚴格和必然的有機連續關系,而“現代是一個文明的時代,斷然不是一個文化的時代。”(中譯本,第54頁,第66頁)他把本世紀開初西方社會的悲觀心理作了直率表達,在當時的情境下,非但沒有引起人們的反感,反而因其坦直而使他名重一時。
第二,文化的“同時代”表征。這是施本格勒最突出的思想。在他的眼中,所有的文化都是同時代的,都經歷過前文化時期、文化時期和文明時期,或春、夏、秋、冬四個演化階段。十九和二十世紀之交的西方文化與古埃及希克索斯人入侵時期和希臘化時代在文化形態上并無二致,而在政治形態上,這段時期又表現為“戰國時期”,即“從拿破侖主義到凱撒主義的過渡。”(中譯本,第658頁)施本格勒的具體論述是:在前文化階段,人類處于原始民族狀態時,沒有國家和政治。一旦出現民族和封建制度,便進入了文化階段的早期,體現的是鄉村和鄉下人的精神,到了文化階段晚期,城市出現了,并與鄉村進行著斗爭,國家形式也從成熟走向頂點直至衰亡。當城市徹底戰勝鄉村,出現大城市或行省的時候,文明階段便到來了。這時諸侯林立、列強紛爭、戰爭頻繁。施本格勒指出,“戰國時期”以后將是大一統的“帝國時期”,他預言,西方文化的“帝國時期”將在二○○○—-二二○○年出現。他對此的總概括是:“如果早期的特點是城市從鄉村中誕生出來,而晚期的特點是城市同鄉村作斗爭,那么,文明時期的特點就是城市戰勝鄉村,因之,它使自己從土地的掌握中解放出來,但走向自己最后的毀滅。”(中譯本,第224頁)“帝國時期”就是城市的毀滅。
第三,與上述觀點相聯系,施本格勒竭力反對歷史發展的因果規律性,而是反復證明歷史中唯有“命運”(Destiny)存在。他指出,與歷史相對應的是時間,與自然相對應的則是空間。時間流動不息,無法運用因果規律,它只能與以往的、死的東西聯系,而作為方成的、活的歷史,則與“命運”相關。“命運”的觀念統治所有的世界歷史的場面,是最原始的存在模式,而因果規律則是客體的存在模式。自然的世界是離開人的感覺的理解的“非我”(alterego)。命運是不可描述的,只能通過圖畫、悲劇和音樂等藝術家的工作才能分有”(英譯本,第一卷,第118—121頁)。施本格勒舉例說,白天與黑夜、青春與衰老、花朵與果實都沒有因果聯系,只有時間聯系。在歷史中,唯有老和新、過去和未來之分,而歷史的永恒活力又決定了命運的永遠年輕。(英譯本,第152頁)有的時候,施本格勒又運用了陰性和陽性來比喻命運和因果律。他說:“男性生動地體驗命運,而且領悟因果律,即領悟已成的因果邏輯。反之,女性本身就是命運、時間和方成的有機邏輯,正是因為這個緣故,因果律的原則對她是永遠陌生的”(中譯本,第528頁)。這些描述,從總體上來說,都是為了表示這樣一種信念:歷史的有機性和宿命性都是生來具有的,因此,西方文化的衰落也是勢不可挽。這無疑是悲觀的。然而,對于身為西方社會一員的施本格勒來說,他揭示這樣的發展態勢,除了承認事實以外,還在一系列“同時代”的類比中提醒他的同胞,西方文化只不過是在重蹈以往諸文化的覆轍,這本身又減輕了這一命運自身的悲劇性。
饒有趣味的是,施本格勒所有理論的出發點是在于強調歷史與自然的不同,反對自然科學理論的簡單搬用。這體現了十九世紀末期以來反實證主義的社會思潮。然而,施本格勒的整個工作也只不過是依靠另一門自然科學——生物學的某些論點而得以建立起來的。這在更大一圈的范圍上來說,仍然脫離不了實證主義哲學的思維傳統。當然,哲學和科學的關系異常緊密也是無可否認的。問題在于,施本格勒對有機與無機、歷史與自然在知識內容和表現形式上的劃分和對立過于武斷,他認為有機界不存在因果聯系的結論也過于自信。
然而,施本格勒的歷史視野畢竟是宏闊的,他把所有的文化都置于“同時代”來觀察,這大大改變了歷史學中的時間觀念,留給后人以許多啟示。他的后繼者、英國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在本世紀中期的聲望之隆也部分地得力于此。顯然,施本格勒的突破還不僅體現在歷史學領域,其更深一層的意義在于,他從歷史研究中獲取的這種方法,體現了一種多元化的研究傾向,而承認多元性、提倡多元化,正是現代西方文明的一大特征。
時代和傳統的交會
施本格勒曾經頗為自負地說:“一個不能同樣領會和掌握現實的哲學家決不會是第一流的哲學家。”(中譯本,第69頁)《西方的沒落》之所以在當時能夠得到如此巨大的成功,也正是在于這種現實感和時代感。固然,施本格勒所能做的一切也只是對于西方文化的實際轉變作了理論上的承認,然而,承認事實也是需要勇氣的。而且,施本格勒這部著作盡管在一九一八年出版,他的寫作卻是在戰前開始的。因此,他的“承認”就多少有點大膽的“預見”了。
但是,如果僅從著作本身的內容來肯定作者的思想,顯然是不行的。施本格勒對當時時代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德國軍國主義政治的要求。他對凱撒、拿破侖式偉人的希冀,是希望他的國家能夠在第一次大戰失敗之后,在以后的“戰國時期”東山再起,成為世界的主宰。這在思想上為德國法西斯主義的出現提供了理論基礎,難怪他在當時被列為主張獨裁主義的主要宣傳家。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指出:任何思想體系既是時代的需要,又是“以本國過去的整個發展為基礎的,是以階級關系的歷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以及其他的后果為基礎的。”(《馬恩全集》第三卷第544頁)施本格勒的思想中有不少“嶄新”的時代內容,但同時又有不少東西植根于他以往的思想土壤。他在著作中一再提到歌德和尼采,事實上,除了他們兩人之外,狄爾泰的非理性主義的歷史認識論與施本格勒的關系也相當接近。狄爾泰嘗言:“我們解釋自然,但是我們理解精神生活”。威爾姆·馮·洪堡特(一七六七一一一八三五)也提出過歷史的認識要憑借猜測和直覺。至于承認每個文化的獨立發展,利奧波德·馮·朗克(一七九四——一八八五)曾一再宣稱:每個時代都直接與上帝溝通。在上帝面前所有的時代都是平等的。反對單一的進步路線。狄爾泰的表述則更為明確:“每一個個人、以及每一文化體系、每一個團體,在自身中都有自己的中心。”這簡直和施本格勒的言語如出一轍。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盡管從康德到黑格爾的德國古典哲學的統治在德國十分強大,德國思想界中從來也不缺他們的反對者。而且,反對者的隊伍在十九世紀后期開始逐漸擴大,以至到二十世紀發展成為西方哲學思潮中的主導傾向。施本格勒就是這一主觀唯心主義思潮在歷史哲學領域的一位代表人物。
施本格勒對歷史發展的多元化描述固然能夠開闊歷史學家的視野,但同時又反映出他本人對歷史連續性、文化繼承性的極大漠視。他強調單個文化的有機聯系,卻不承認整個人類歷史的聯系性。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但事實上,對于一個具有濃烈的種族優越感的德國思想家來說,施本格勒的確不敢正視以下的事實:新的文化曙光正在東方崛起并日漸成為世界歷史的活力源泉之一。
總而言之,第一次世界大戰對于西方社會的影響是巨大的。它標志著現代歷史的開端,也是現代西方文化的開端。從此以后,西方社會的價值觀念、文化觀念等等都起了很大的變化。施本格勒的著作反映了這一轉折時代的文化特征。在施本格勒的后繼者湯因比之后,在西方的歷史學家中已經少見這種宏觀的歷史構畫的人物了。但是,這并不是說人們不歡迎這樣的構畫,《第三次浪潮》、《大趨勢》、《微電子學與社會》等著作的暢銷便是明證。人類永遠不會停止對自身歷史的反思和對未來社會的展望。遺憾的是,我們的社會科學工作者還沒有拿出一本氣魄恢宏、持論有據、論述世界未來和中國未來的著作。我以為,寫出一本具有中國特色的有關世界歷史發展方向的著作,不僅是對我國的文化建設也是對世界文化的一個貢獻。
(《西方的沒落》[德〕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著,〔英〕C.F.阿特金森英譯,齊世榮等節譯,商務印書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第一版,〔精〕4.50元;全譯本,雷海宗譯,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