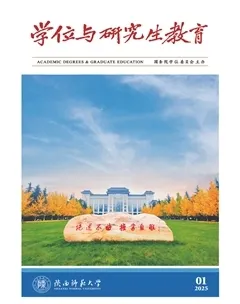博士生導學關系的內涵、建構與異化

摘要:在博士生學習的不同階段,導學關系的重心也會逐步上移、不斷深化,初期體現為基于共同目標的聯盟關系,中期體現為基于身份差異的權利關系,后期體現為基于情感共鳴的伙伴關系。從整個教育過程來看,博士生和導師之間的關系是一個從陌生到理解、從理解到認同,再從認同到共建的逐步建構的過程。伴隨著博士生教育規模的持續擴大,導學關系更加復雜,項目化管理、功利性文化以及導師權威的消解,在不同程度上對導學關系帶來了不利影響,甚至誘發導學關系的異化。為此,在厘清導師職責邊界與角色、維護導學關系中權力平衡的同時,還要健全導學關系的反饋與調節機制,營造導學共生的和諧環境。
關鍵詞:博士生教育;導學關系;導學矛盾
作者簡介:趙世奎,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北京 100191;鄒齊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191;吳雪姣,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191。
導師制是研究生教育的基本制度。人才培養是導師的首要任務,導師是研究生培養的第一責任人。近年來,我國先后出臺了《關于全面深化新時代教師隊伍建設改革的意見》《關于加強博士生導師崗位管理的若干意見》等系列文件,從導師職責、崗位選聘、考核評價等方面做出了全方位部署。廣大導師立德修身,嚴謹治學,潛心育人,為國家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涌現出了一大批教書育人楷模。但在一些時候,導學關系淡漠甚至異化,引起社會的高度關注,這些現象也成為社會輿論的焦點。

 當前,我國正處于加快推進教育強國建設、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關鍵時期,隨著研究生教育規模的進一步擴大,導師和學生的構成將更加復雜、需求更加多樣,導學關系面臨更嚴峻的挑戰。深入剖析導學關系淡化、僵化甚至異化的根源,構建完善保障導學關系健康和諧發展的政策機制,是當前亟待解決的重大課題。當前,學界的討論熱點主要集中在微觀和實踐視角下的導學關系及其所面臨的問題。然而,現有研究往往聚焦導學關系的單一維度,如導生關系類型的解析或導師行為失范引發的顯性與隱性沖突,雖提供了寶貴的見解,但缺乏對導學關系在不同階段的動態演變及其多層次內涵的系統性探討。此外,現有研究的實證案例多停留在結構性影響機制的分析上,較少關注導學關系異化背后的制度性和文化性原因,實踐解釋力也顯得不足。鑒于此,本文從社會建構主義和權力關系理論的視角出發,試圖解構并重構導師與博士生之間的互動模式。
當前,我國正處于加快推進教育強國建設、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關鍵時期,隨著研究生教育規模的進一步擴大,導師和學生的構成將更加復雜、需求更加多樣,導學關系面臨更嚴峻的挑戰。深入剖析導學關系淡化、僵化甚至異化的根源,構建完善保障導學關系健康和諧發展的政策機制,是當前亟待解決的重大課題。當前,學界的討論熱點主要集中在微觀和實踐視角下的導學關系及其所面臨的問題。然而,現有研究往往聚焦導學關系的單一維度,如導生關系類型的解析或導師行為失范引發的顯性與隱性沖突,雖提供了寶貴的見解,但缺乏對導學關系在不同階段的動態演變及其多層次內涵的系統性探討。此外,現有研究的實證案例多停留在結構性影響機制的分析上,較少關注導學關系異化背后的制度性和文化性原因,實踐解釋力也顯得不足。鑒于此,本文從社會建構主義和權力關系理論的視角出發,試圖解構并重構導師與博士生之間的互動模式。
一、導學關系的內涵特征
“導學關系”的概念源于“師生關系”,盡管“導學關系”這一概念廣為人知,但學界對其具體內涵尚未達成共識。有學者提出,鑒于環境與主體的特殊性,研究生階段的導學關系已獨立于傳統“師生關系”范疇[1],也有部分學者認為導學關系本質上仍屬于高校師生關系的一類[2]。此外,導學關系的復雜性不僅僅體現在其內部的互動維度上,還體現在其所處的外部環境中:一方面,研究生及其導師所面對的是專門化的高深知識,導學關系勢必會呈現出很強的個性化特征;另一方面,植根于不同的教育傳統和文化傳統,各國對導學關系的理解認知和制度安排也不盡相同。本研究嘗試提出一個綜合性的“導學關系”概念,作為對這一復雜現象的共識性表達。導學關系不僅是導師與學生之間簡單的互動和交往過程,更是一種多層次、復雜且持續演進的結構性關系體,既包括顯性的學術傳授和指導,也包含隱性的情感支持和價值觀塑造。總體而言,國內外對導學關系的認識和實踐大致可以概括為以下三點。
1.基于共同目標的聯盟關系
隨著時代的不斷演進,傳統的“教”與“學”二元關系框架已日益顯露出其局限性,難以全面而深刻地詮釋當今多元化、多維度的導生互動現象。哈德森(Hudson)指出,現代意義的“導師”與“學生”間的關系已經不再是傳統的師徒關系,而是基于共同目標逐步建構起來的聯盟關系。他們相互依賴、彼此信任,并在尊重與包容的環境中深入探討學術問題,共同應對研究過程中的挑戰,共同致力于實現學術卓越。“信任”和“尊重”是構建導學聯盟的兩大基石,只有在一種友好且非評判性的環境中,導學聯盟才能得以發展和深化,并通過開放且富有支持性的溝通得以不斷滋養[3]。因此,營造和諧的交流環境,允許導師和博士生自由分享彼此的不足、所遭遇的挑戰以及獨到的見解,對于博士生的全面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伴隨著對概念認知的不斷深入,國內博士生與導師之間的關系定位討論已經逐漸從傳統的“導生關系”擴展到了“導學共同體”的概念[4],來描述導師與博士生間基于共同的價值觀、目標和利益,建立在相互尊重、信任和合作基礎上的緊密導學關系[5],包括學術共同體[6]、差異共同體、利益共同體、成長共同體等[7-8]。總體來說,無論是“導學聯盟”還是“共同體”的概念,都倡導形塑導學主體間的平等交流,提倡強化互聯互通的話語情境,這不僅有助于博士生的學術成長,也為導師提供了重要的學術交流和合作的伙伴。也有學者將“責任義務”作為理解和確定導學之間聯盟關系的核心概念,這既包括選拔與分流、學術指導、學術文化塑造等“學術責任”[9],還包括品德修養、人格養成等“非學術責任”[10]。此外,這種基于共同目標的導學聯盟,通常會以正式“協議”的方式,對導師和博士生的責任義務做出規范、明確約定。例如,法國、德國的一些大學要求研究生、導師和學校簽訂三方協議(tripartite agreement),以明確各方在培養過程中的責任和義務。
2.基于身份差異的權力關系
就實然層面而言,基于學術和社會結構的內在權力邏輯[11],導學關系通常體現為一種非對稱的“偏態結構”[12],即導師往往占據較高的社會和學術地位,擁有管理權,而博士生則處于接受管理的位置[13]。有學者指出,師生關系中的“導師權力”的合法性不同于傳統的非強制性的權力關系,更多體現為學術影響力和指導能力[14],該特質在傳統儒家“師道文化”的賦權下得以深化[15]。相比之下,國外研究更關注導學關系中權力運作的動態性與多元權利類型,羅伯遜(Roberson)主張將“權力分配”作為理解和確定導師關系性質的核心概念,并提出了賦權(power to)、專權(power over)與分權(power with)三種權力模式,來解釋導師指導對博士生社會化的影響[16]。顯然,究竟采取何種權力模式,掌控權在導師而不在博士生。在賦權模式下,導師通過傳授專業知識幫助博士生獲取技能和信息,并在學術領域中取得成功。在專權模式下,導師可能會限制博士生的自由,強加自己的觀點和期望,導致博士生在學術實踐中缺乏獨立性和創新性[17]。相比之下,分權模式強調導師和博士生之間的平等合作關系,彼此之間保持開放的溝通和理解,共同進行學術探索和知識建構。這種平等合作的關系,不僅有助于博士生塑造學術身份認同,也有助于博士生以更開放的態度參與專業社交網絡。具體而言,在以個體化知識生產為主要特征的人文社科領域,博士生需要高度依賴導師的引導才能融入學術社群,如果導師僅僅把自己置于支配地位,博士生將面臨被邊緣化、被忽視或不被接納的困境,從而阻礙博士生的學術成長[18]。在需要團隊緊密合作的理工科領域,權力與地位的差異更多體現在導師對項目和資源的控制,以及學術成果和榮譽的分配等環節,這種權力差異如果與功利性學科文化傾向相互交織,無疑會增加導師行為失范的風險,導致博士生面臨著被過度壓榨和任意驅使的困境[19]。因此,理想的導學關系應致力于平衡、協調導學間的權力差異,著力促進導學合作。
3.基于情感共鳴的伙伴關系
隨著共同經歷的積累,導師與博士生之間的關系日漸深厚,從單純的專業互動逐漸演化為包含深厚友誼的共同體。這種轉變不僅體現在學術上的共同進步,更延伸至情感上的相互扶持,從而形成一條超越傳統師生界限的情感紐帶。國外學者引入了“從專業到友誼的連續體”(from professional to friendship continuum)的概念,來描繪導師與博士生關系中從純粹的專業合作到深厚友誼的連續性過程[20]。在這個連續體內,專業合作主要體現在導師和博士生之間正式、職業性的互動,包括導師為博士生提供學術指導和學術資源、指引研究方向等。在友誼性的端點,關系更加親密和個人化。理想狀態下,導師和博士生可以在專業性和友誼性之間自由地進行轉換,體現出導學關系的靈活性,以及在不同情境下適應不同關系模式的能力。國內學者指出,研究生階段的導學關系是在教育教學活動中通過實際的互動和交往逐漸形成并建立起來的一種“人際情感關系”[21]。這種關系不僅僅停留在學術層面的交流與合作,還通過情感體驗和心理契約進一步深化。隨著師生之間互動的加深,彼此的信任感和歸屬感也會得到增強,從而推動導學關系向更為緊密和穩定的方向發展[1]。然而,在現代教育場域逐步發展成為理性空間后,導師和博士生之間的交往過于強調功能性和任務導向,導學關系會呈現出工具理性的特征,缺乏深入的情感聯系和個人關懷。這種關系模式強化了倫理失序特征,導師未能充分履行其關懷博士生的責任,而學生也可能因此感到被忽略或孤立[22]。因此,有學者指出導學關系不應僅停留在學術領域的交流,而是應該積極促進非學術的“感性交往”空間,創造出一個既充滿人情味,又專注于學術探索的導學共同體,使雙方能夠在情感基礎上建立起更加穩固和諧的關系[23]。然而,也有部分學者提出,當師生關系過于個人化時,可能會影響到本應維持的專業互動關系。過度個人化的交往可能導致界限模糊,進而影響指導的客觀性和專業性[24]。因此,為了維護教育活動的質量和正當性,導師和博士生都應明確并尊重專業互動關系的邊界,以學術為導學關系的核心事業,在此基礎上尋求情感的共鳴,建立起更加親密和信任的關系。
二、導學關系的建構過程
復雜性和多變性是導學關系的重要特征,導學關系的建構過程是博士生學術旅程中關系維度的核心要素,也是師生互動多層次動態演變的體現。在初始階段,博士生需要在導師的引導下從“局外人”轉變為“局內人”,實現對學科知識和文化的初步認識。隨著時間的推移,導學關系從適應階段向更深層次的學術認同和專業成熟過渡,導師的角色變得更加復雜和動態。進入成熟階段后,導學關系更是進入了知識共建的高峰期。隨著博士生獨立科學研究能力的增強,導師與博士生在學術探索中扮演互補角色,共同推動研究項目的進展。
1.從陌生到理解
在博士生學術旅程初期,面臨著全新學術環境和特定學科文化的雙重挑戰,博士生既要掌握基本的學科知識和實驗操作等技能,也要盡快融入實驗室、課題組,建立起更廣泛的學術社群。這一過程也被稱為博士生的“入職過程”(induction process),標志著博士生實現從“局外人”到“局內人”的轉換,建立起對學科知識和學科文化的認識[25]。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導師不僅是知識的傳授者,更是學科文化的傳遞者。在這個階段,導師和博士生在學術興趣、工作風格及溝通方式等方面的契合度尤為重要,這不僅是構建穩固導學關系的基石[26],也是構筑師生高效合作關系的橋梁[20]。
一般而言,在博士生招生雙向選擇的過程中,導師和博士生通常會從兩個方面對可能的契合度進行考察。一方面,是導師的專業知識背景、研究方向與博士生未來研究計劃之間學術上的適配性;另一方面,是導師與博士生在人際交往、工作模式和研究方法上的相互適配性。但也有學者指出,導師在選拔和錄取博士生時,常常面臨機構內部缺乏詳盡、規范的審核流程的問題[27]。更為關鍵的是,這些導師可能發現,他們所接受的科研培訓并未全面涵蓋必要的博士生選拔技能,導致在評估申請者時缺乏必要的專業知識與技巧,而是依賴直覺、個性、態度、興趣、對課題的熱情、學術成果以及同行推薦等因素來做出決策。特別在時間資源有限和競爭激烈的背景下,導師的選擇壓力不斷增大,使得挑選最合適的候選人變得愈發困難。
2.從理解到認同
隨著時間的推移,導學關系逐漸進入從理解到認同的“過渡階段”。不同于初始階段,這個階段的博士生已經基本適應了學術環境,并開始深入專業領域的學習和研究,導師的社會化經驗、個人價值觀以及對學術界的理解深度,都直接影響到他們的指導風格和效果。特羅爾(Trowler)[28]基于格倫德曼(Grundmann)[29]提出的社會化理論,探討了導師指導的行為特征和態度特征,提出了14種指導類型的分類,包括學術顧問、助推人、危機管理者、控制者、幻滅者、教育者,等等。一些研究基于社會關系視閾,將導學關系分為門閥式、學徒式、雇員式、親子式、師友式師生關系等五種類型[30]。還有的研究圍繞師生權力關系和指導風格視角,將導學關系分為權威型、松散型、功利型、和諧型[31],或者將其分類為專制功利型、民主權威型、自由探索型、放養放任型[32]。這些實然層面導學關系分類的討論,雖然反映了導師職責的廣泛性和導學關系的多元性,但沒有體現導學關系時間維度的發展變化。
事實上,導學關系在度過初步適應的“蜜月期”后,博士生逐漸進入更深層次的學術社會化階段,這個過程往往伴隨著一些摩擦和掙扎,博士生要理解并適應所在學科的文化與范式,不僅需要知識和技能的積累,更需要價值觀和行為模式的內化。一些學者將導學間的“掙扎和摩擦”稱之為“能夠促使學生自我反思和成長的情境和機制的轉型事件”[33]。這意味著,雙方只有經歷相互磨合甚至掙扎的過程,才能“浴火重生”。一方面,導師要建立和維護博士生與學術群體之間的聯系,進一步促進其學術身份認同的建構,使博士生確立自己在“學術部落”中的地位和角色[34];另一方面,導師也要注重博士生個性、知識和技能的發展,通過個性化的指導和支持幫助他們成長為獨立的學者。由此看來,導師不僅是博士生專業知識的傳授者、學科文化傳遞者、更是社會化的引導者和學術身份的塑造者。
3.從認同到共建
在博士生對學科文化有了充分認識并且專業技能得到顯著提升后,導學關系進入成熟階段,這也意味著博士生實現了從“學術新人”到“學術同行”的角色轉換。在此階段,博士生成長為獨立的知識生產者,并且能夠在學術共同體中展示研究成果,積極參與學術交流和合作,在學術部落中建立起自己的聲譽和地位。此時,導師與博士生之間的互動不再是單向的知識傳授,而是在學術探索中扮演著互補的角色,共同推動著研究項目的進展。導師在學術指導和個人情感支持方面的付出,對于提升處于讀博中期博士生的自我效能感具有關鍵作用。隨著博士生進入學習后期,導師必須謹慎處理“引導”和“放手”之間的平衡,確保在培養過程中充分尊重并激發博士生的自主性。此外,作為支持博士生學術身份形成和社會化的關鍵角色,導師需要幫助博士生對自己的能力和職業前景有清晰認知,從傳統的權威性指導者轉向更加開放和支持性角色。
然而,由于導師、高年級學生及其他權威人士之間的觀點和方法可能存在差異,博士生接收到的信息可能出現矛盾甚至沖突。在面對信息沖突時,導師不僅需要在保證博士生自主性的前提下加強引導,還需要通過自己的專業經驗指導博士生如何在快速變化的學術環境中應對復雜的問題,在學術討論中表達和捍衛自己的觀點,從而促進其專業成長,并為學術職業發展做好準備[35]。國內外學者強調了導學關系磨合階段信息沖突的積極價值,即觀念沖突能夠激發博士生的自主性、批判性思維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當博士生意識到不同導師之間存在觀點差異時,他們會被迫走出舒適區,獨立思考并做出明智的選擇[36]。這種沖突不僅鼓勵博士生對信息進行深度分析和對比,還有助于他們更清晰地認識和確定自己的職業目標和價值觀[37]。因此,面對信息沖突并通過積極溝通達成共識的過程,可以提升導學關系的親密度和關系韌性,是博士生社會化過程中一個不可忽視的積極因素。
從全局視角來看,導學關系在博士生教育過程中呈現出鮮明的動態性和多維性特征,這種關系并非固定不變,而是不斷在環境和互動的影響下進行重塑[19]。導師在博士生的學術生涯中扮演著多變且復雜的角色,從初期的教育者和指導者,到中期的支持者和助力者,再到后期的顧問和同行,這就需要導師不斷調整自己的管理風格和交往方式,以最大化博士生的學術成長和個人發展,助力博士生由“學徒”過渡到“拓荒者”,最后蛻變為“大師”。
三、導學關系的異化溯源
從上述分析來看,現有研究主要是集中于對具體問題現象的描述以及導學關系類型的劃分,盡管有研究嘗試歸納問題現象背后的邏輯,但這些分析將矛盾之源歸結在一個靜態的層面上,未能充分揭示導學互動背后復雜的因果關系。實際上,這種復雜性深刻地揭示了因果關系的多維交織與多向性特征,恰如復雜系統理論所強調的,系統中的多種因素和相互作用往往產生非線性結果(見圖1)。
1.教育規模擴張與政策變革的局限
首先,2018年2月教育部印發的《關于全面落實研究生導師立德樹人職責的意見》明確指出,導師作為研究生培養的第一責任人,應具備高水平的專業素養和積極正面的學術價值觀,并肩負起立德樹人的重要職責。這不僅對導師培養研究生的學術研究能力和學術道德提出了要求,更強調了人文關懷與心理疏導等方面的職責。但是,在博士生數量急劇增加的情況下,導師要維持對每個博士生足夠的關注和指導變得越發困難,這既可能會削弱導師提供個性化指導和深入指導的能力,也可能對博士生的成果產出和整體滿意度產生負面影響。有研究表明,導師師均指導規模與博士生培養質量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在一個最優的師均指導規模(例如10人)下,博士生的科研水平達到最佳[38]。
其次,政策層面的挑戰還存在于博士生招生制度不完善、導師轉換機制和申訴反饋渠道不健全等問題[19]。例如,當前我國博士研究生選拔主要采用“申請—考核”制,該制度在提供靈活性和針對性的同時,也引發了對招生權利邊界的公平性、透明度和評估標準一致性的質疑[39]。這些問題不僅影響了師生互動的質量,也對導師的職能和義務提出了新的挑戰,需要通過具體的政策和制度改進來解決。有學者指出,制度優化對于促進導學共同體的可持續發展和高效運行至關重要,建立更加健全和有效的制度機制,包括選拔機制和退出機制,能夠有效解決導師與研究生之間存在的潛在矛盾[40]。
此外,在全球化和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大背景下,全球大學顯現出一種對外部項目資金愈發依賴的顯著趨勢,轉變了博士生的教育實踐。一方面,基于行業的研究伙伴關系加強了博士生學術網絡的建立,為博士生提供了更為豐富的實踐經驗和職業機會。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指出,因為外部項目資金往往帶有特定的研究目標和時間限制,這種資助結構的轉變,將使得導師在控制研究進度、確保學術質量方面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對此,一些學者指出,當代高等教育正處于一個高度市場化和官僚化的環境中,盡管各國政府的創新政策推動了博士生教育的增長、改革和責任制,但往往效果有限,原因就在于政策制定者過于依賴抽象的概念和思辨的方法,而忽視了博士生和導師的真實需求和面臨的挑戰[41]。
2.項目化管理和功利性文化的引導
首先,在研究生教育現代化的浪潮中,教育價值觀已經發生了顯著的轉變,從對學術探索的熱情和道德修養的強調,逐漸轉向了對更為功利性目標的追求,如項目資金、論文發表和職業成就等可量化的成果。隨著轉變的深化,博士生與導師之間的關系也不再局限于傳統的“授課和控制”模式或師徒制的指導模式,而是轉變為一種雙向互惠的學術共同體。在這種新型關系中,經濟屬性和市場邏輯勢必成為影響師生互動的重要因素,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導師對博士生的期望[42]。與此同時,片面的評價標準,如課題項目和成果轉化等,無疑也強化了這種功利性目標,使得導師和博士生在交往過程中越來越注重結果導向,而忽略了教育的本真和深度。有學者認為,功績主義的學科文化和項目中對效益目標的追求,并未使師生關系完全異化為商品經濟關系,但其中蘊含的功利色彩仍然不容忽視[43]。
其次,高校教師群體的角色結構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變革,在這一進程中,導師不僅要繼續履行其傳統的教學職責,還需承擔起管理者與評價者的雙重角色[44]。多元身份與多重責任既使得導師面臨角色沖突的困厄,也成為導師權威異化和導學沖突的誘因。作為管理者,他們需要精準地組織和管理研究生團隊,確保項目研究的順暢、資源的合理分配以及行政事務的高效處理。而作為評價者,他們則須對博士生的學術進展和表現進行評估與反饋。同時,項目化的管理引入了大量的非學術性的行政事務,如項目申報、資金管理和成果匯報,這就要求導師具備較強的行政管理技能。
第三,在科層制管理模式的影響下,導師更傾向于通過標準化的制度和規定來規范博士生的學術活動,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管理效率,但也可能加劇了師生關系的功利化。例如,在資源競爭與利益分配的糾葛中,科研項目經費的分配、論文發表的競爭以及獎學金的申請等問題,都可能成為引發師生矛盾的潛在因素[45]。簡言之,當學術活動與非學術事務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學術壓力與非學術壓力疊加,以成果為中心的學科實踐可能會催生出一種表面和諧但實則脆弱的“共同體”關系,缺乏深入的思想交流和真正的學術指導。如果導師和博士生無法在學術和非學術場域中找到平衡,確保其角色功能在不同情境中得到合理發揮,師生關系的異化也就在所難免。
3.任務導向型互動與導師權威的消解
導師的個性特質、學術水平、指導策略,以及研究生的期望和需求等微觀因素,構成了導學關系網中的關鍵節點,會以復雜的方式交織在一起,影響師生之間的互動和關系質量。例如,導師的權威性或開放性個性可能與需要自主性的研究生產生沖突,而學術水平和教學投入的不匹配則可能導致研究生的挫敗感或導師的不滿。再如,溝通方式的差異在導學互動中尤為關鍵,不頻繁或缺乏有效溝通的導師,往往無法滿足研究生對及時反饋和指導的迫切需求,從而引發雙方之間的誤解和隔閡。為了避免這些情況,博士生和導師應建立定期且高效的溝通機制,如定期的學術討論會、項目進度匯報等,以確保信息暢通、需求明確[46]。此外,不同的教育背景和文化價值觀差異,也會導致雙方在教育和職業發展的觀念上產生分歧,從而增加矛盾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宏觀制度框架的規范和中觀學科文化的塑造下,導學互動往往受到時間、資源和評價體系等多重限制,從而不可避免地呈現出一種工具理性的特征,導致師生間的互動主要聚焦于完成既定的學術任務,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深入的情感聯系和個人關懷[47]。此外,導師“指令性”的指導方式也會限制研究生的學術自由和創新能力。簡言之,工具理性和任務導向型關系抹殺了導師在育人事業中本應追尋的意義與價值,使得博士生教育逐漸變成一種單維度“生產”學術成果的過程,強化了陌生人關系中的倫理失序特征,博士生可能因此感到被忽略或孤立。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趨勢,在于當代教師權威的消解以及當代博士生主體意識的增強。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師道尊嚴”一直被視為教育的基本準則,強調教師天然的權威和博士生對教師的尊敬。然而,“后喻文化”時代的知識獲取已不再僅僅依賴于個人的年齡或經歷,教師傳統上作為知識權威者的地位面臨挑戰。特別是在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博士生的自主意識日益增強,不再單純接受權威的教育方式,而是更加重視“參與式”交流以及在教育過程中的主體地位,追求導學關系中的“平等”和“知識共創”。因此,雖然現代的師生關系仍基于理性主義的原則進行構建,但在研究生教育過程中,更應努力去除任何形式的導師話語霸權,促進一種基于平等對話的新型師生關系[48]。
四、導學關系異化的紓解
綜上所述,在教育這一由國家、市場和文化共同交織構建的領域中,博士生指導活動是被多重話語體系規訓的實踐,往往會面臨制度化要求與評價體系帶來的壓力、日益沉重的管理和行政負擔以及角色沖突和資源分配的限制。在這些重壓之下,導師可能會采取命令式、功利化甚至冷漠的指導方式,導致導師與博士生之間關系的異化和失序。為此,本文就導學關系的紓解提出以下建議。
一是厘清導師職責邊界與角色。一方面,要引導廣大導師深刻把握、自覺踐行新時代教育家精神,既做學業導師又做人生導師,實現“經師”和“人師”的有機統一。另一方面,要完善導師管理評價監督機制,科學制定評價標準和評價指標,既扎緊導師言行舉止的籬笆,確保導師的指導行為不“越界”,也支持導師嚴格學業管理,把教育權還給導師,實現從考核管理為主,到規范支持為主、考核監督為輔的轉變。因此,相關部門應研究制定實施細則,既要明確導師“第一責任人”的內涵邊界,進一步厘清導師的招生權、指導權、評價權和管理權,也要培養博士生積極健康的心態,客觀認識和理解導師的職責權限。
二是維護導學關系中的權力平衡。為了推進學術共同體建設,倡導“賦權”理念,推廣“分權”模式,學校和部門應鼓勵導師在指導過程中賦予博士生更多的自主權與決策參與權,實現導師與博士生之間的平等合作與權力共享。這不僅有助于打破傳統導學關系中導師主導、博士生被動接受的單向格局,還能促進師生間更深層次的理解與溝通,進而提升學術研究的效率與質量。此外,需要建立健全的導師評價體系與監督機制,減少導師專斷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確保導師在行使權力時能夠遵循學術規范。
三是健全導學關系的反饋與調節機制。博士生和導師面對的是專門化的高深知識,指導過程具有很強的個性化特征,導學關系“千人千面”,出現不一致意見在所難免,關鍵是要讓博士生切身感受到培養單位對公平正義的堅守,信任學校和相關部門解決問題的意愿與能力。為了更好保護博士生和導師的合法權益,把問題解決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就要健全反饋制度,讓博士生能夠在定期的交流中向導師表達自己的意見和需求。同時,學校應提供中立的第三方調節機制,幫助解決導學關系中的沖突和誤解。權利救濟制度的健全也可以為博士生提供必要的支持,保障其合法權益。
四是營造導學共生的和諧環境。隨著研究生教育進入超大規模的發展階段,導師和博士生的構成更加復雜,個體特征和需求更加多樣,出現導學關系緊張的可能性也會大幅提高。為了克服學術生態中的結構性障礙,不僅需要從制度化規范層面著手改善,還需要營造一種非制度化的、和諧科研氛圍。為了促進導師和博士生的溝通與交流,院系可以定期舉行導生交流活動,創設和諧文化建設的活動載體,消解管理模式中的導生對立。同時,需要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通過社會輿論和道德風氣的正向引導,促進形成“平等、包容、理解、尊重”的導學關系價值取向,創新運用多元化的媒介平臺和傳播渠道,構建高效、正面的輿論引導機制,形成公眾對導學關系積極正面的認知與期待。
參考文獻
[1] 王江海, 常海洋, 杜靜. 導學關系基本問題研究述評: 本質、類型與影響因素[J].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24(2): 93-100.
[2] 林偉連, 吳克象. 研究生教育中師生關系建設要突出“導學關系”[J]. 學位與研究生教育, 2003(5): 26-28.
[3] HUDSON P. Forming the mentor-mentee relationship[J]. Mentoring amp; tutoring: partnership in learning, 2016, 24(1): 30-43.
[4] 李春根, 陳文美. 導師與研究生命運共同體: 理念與路徑構建[J]. 學位與研究生教育, 2016(4): 55-59.
[5] 胡洪武. 師生發展共同體: 破解研究生導學矛盾新路徑[J].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21(4): 48-52.
[6] 張榮祥, 馬君雅. 導學共同體: 構建研究生導學關系的新思路[J]. 學位與研究生教育, 2020(9): 32-36.
[7] 張先璐. 導生共創觀: 關于導生關系主體問題的再思考[J]. 學位與研究生教育, 2023(11): 51-57.
[8] 金明飛, 蔡連玉. 從“陌生人”到“共同體”: 高校導學關系的轉向[J].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24(2): 86-92.
[9] BAIR C R, GRANT HAWORTH J, SANFORT M. Doctoral student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a shared responsibility[J]. Journal of student affairs research and practice, 2004, 41(4): 1277-1295.
[10] 鄭衛榮. “首要責任人”視角下的研究生導師德育工作探索[J]. 學位與研究生教育, 2015(2): 45-51.
[11] HANSMAN C A. Reluctant mentors and resistant protégés: welcome to the “real” world of mentoring[J]. Adult learning, 2003, 14(1): 14-16.
[12] 邵成智, 扈中平. 論師生關系的偏正結構[J]. 教育學報, 2018, 14(2): 12-18.
[13] 程華東, 曹媛媛. 研究生教育導生關系反思與構建[J]. 學位與研究生教育, 2019(6): 13-18.
[14] 殷忠勇. 研究生教育中師生一元關系的理解與構建[J].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18(5): 65-69.
[15] 宋耀晨, 劉永虎. 高校導生關系的表征、風險與治理——基于資源視角的分析[J]. 學位與研究生教育, 2024(5): 75-83.
[16] ROBERSON M J. Team modes and power: supervision of doctoral students[J].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mp; development, 2017, 36(2): 358-371.
[17] KARPOUZA E, EMVALOTIS A. Exploring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in graduate education: a constructivist grounded theory[J].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2019, 24(2): 121-140.
[18] PETERSEN E B. Negotiating academicity: postgraduate research supervision as category boundary work[J].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2007, 32(4): 475-487.
[19] 趙麗文, 林煥翔. 博士生與導師關系疏離的生成與歸因[J]. 學位與研究生教育, 2022(9): 71-79.
[20] GRAY M A, CROSTA L. New perspectives in online doctoral supervision: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J]. Studies in continuing education, 2019, 41(2):"173-190.
[21] 李瑾瑜. 關于師生關系本質的認識[J]. 教育評論, 1998(4): 36-38.
[22] 杜靜, 常海洋. 博士生導學關系中交往理性的缺失與回歸[J]. 學位與研究生教育, 2022(4): 28-35.
[23] 鄧啟云. 溫情導學關系的困境與路徑[J]. 現代教育科學, 2023(6): 30-36.
[24] PHILLIPS E, JOGHSON C. How to get a PhD: a handbook for students and their supervisors[M]. London: McGraw-Hill Education (UK), 2022: 315.
[25] BASTALICH W, MCCULLOCH A. Doctoral induction: sociocultural context and the transition to the research degree[J]. Innovations i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ternational, 2024: 1-13.
[26] BURNARD P, DRAGOVIC T, FLUTTER J, et al. Transformative doctoral research practices for professionals[M]. Rotterdam: Sense Publishers, 2016.
[27] 胡詠梅, 周威. 誰會被錄取為教育博士生?——基于2022年全國31所培養單位招錄數據的實證分析[J]. 學位與研究生教育, 2023(8): 61-69.
[28] TROWLER P. Doctoral supervision: sharpening the focus of the practice lens[J].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mp; development, 2022, 41(5): 1743-1756.
[29] GRUNDMANN M. Sozialisation: Skizze einer allgemeinen theorie[M]. Bayern: UTB GmbH, 2006.
[30] 王伯承. “導學關系”失序的學術道德風險誘發、邏輯機理及應對[J]. 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3, 56(3): 50-57.
[31] 張靜. 導師與研究生之間的和諧關系研究[J]. 中國高教研究, 2007(9): 19-22.
[32] 徐嵐. 導師指導風格與博士生培養質量之關系研究[J]. 高等教育研究, 2019, 40(6): 58-66.
[33] TAYLOR C A, HARRIS-EVANS J. Reconceptualising transition to higher education with Deleuze and Guattari[J].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2018, 43(7): 1254-1267.
[34] BECHER T, TRPWLER P. Academic tribes and territories[M]. Maidenhead: McGraw-Hill Education, 2001.
[35] BIEBER J P, WORLEY L K. Conceptualizing the academic life: graduate students’ perspectives [J].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2006, 77(6): 1009-1035.
[36] 毛金德. 導學沖突治理的再審視[J]. 學位與研究生教育, 2023(8): 37-44.
[37] COSO S A, SEKAYI D. Exercising professional autonomy: doctoral students’ preparation for academic careers[J]. Studies in graduate and postdoctoral education, 2018, 9(2): 243-258.
[38] 鮑威, 吳嘉琦, 何峰. 如何適度布局博士生規模——基于導師指導規模與博士生培養質量的關聯性分析[J]. 中國高教研究, 2021(4): 75-81.
[39] 梁德東, 楊哲. 新時期博士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路徑探析[J]. 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 2022, 38(3): 13-16.
[40] 危紅波. 重構與優化: 導學共同體內部失序和外部失聯的破解之道——基于系統治理的視角[J]. 學位與研究生教育, 2022(7): 55-62.
[41] SCHNEIJDERBERG C. Supervision practices of doctor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J].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2021, 46(7): 1285-1295.
[42] GRANT B M. The pedagogy of graduate supervision: figur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supervisor and student[D]. Auckland: University of Auckland, 2005.
[43] 張悅, 段鑫星. 規訓視角下研究生導學關系的異化及修復[J].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23(4): 20-28.
[44] 林杰, 劉業青. 重建巴別塔: 導學隱性沖突的生成與歸因[J]. 清華大學教育研究, 2022, 43(2): 73-83.
[45] 李函穎, 徐蕾. 工科師生關系會受科研項目類型的影響嗎?——對高水平大學工科博士生與導師基于科研項目交往的質性考察[J]. 學位與研究生教育, 2022(4): 43-51.
[46] IVES G, ROWLEY G. Supervisor selection or allocation and continuity of supervision: PhD students’ progress and outcomes[J].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2005, 30: 535-555.
[47] 常海洋, 杜靜. 走向交往理性的研究生導學關系: 價值意蘊與實踐路徑[J]. 高教探索, 2023(2): 94-99.
[48] 蔡瓊, 呂改玲. 后喻文化背景下導師與研究生之間的和諧關系探討[J]. 中國高教研究, 2008(3): 39-42.
(責任編輯 "黃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