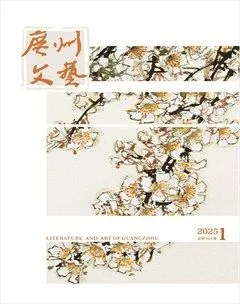“廣州+北京”現代城市的“千城一面”和“一城千面”
郭冰茹:討論城市文學,首先會遇到的還是城市文學概念問題。在城市化進程快速推進的當下,我們該如何定義城市文學?我覺得在中國文學的生產語境中,城市與鄉土是在同一個參照系中互為鏡像的兩個概念。由于中國社會長時間浸淫在鄉土中國的文化現實中,鄉村和鄉土題材一直被有意識地引入小說的創作主流,這使鄉土小說不僅成為中國具體社會生活的反映,也成為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通過文學思考中國現代性問題的起點。也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借助鄉土小說或鄉土文學的定義來理解中國現代文學史與思想史上的“城市文學”。
魯迅對鄉土小說的定義奠定了學界長久以來研究鄉土文學的基本思路。他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中說,鄉土文學是“僑寓文學的作者”“無論他自稱為用主觀或客觀”,都“只隱現著鄉愁,很難有異域情調來開拓讀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此處的“僑寓”即表明鄉土文學是在與城市相對應的地理空間中,以一種回望的姿態來書寫的“鄉愁”,至于如何表達“鄉愁”則與寫作者的立場、眼光以及具體的時代語境相關。隨后,茅盾在《關于鄉土文學》中更進一步將“鄉愁”升華為“在特殊的風土人情而外,應當還有普遍性的與我們共同的對于運命的掙扎”,且“必須是一個具有一定的世界觀與人生觀的作者”才能把超越風土人情的一面“作為主要的一點而給與了我們”。如此看來,如果鄉土文學表現的不光是風土人情,還應該有超越地方性經驗的普遍性和時代性,那么城市文學同樣需要在這一理論框架中去理解和界定。換言之,城市文學要書寫的也不只是城市景觀,城市里的人和事兒也必須能夠反映出某種時代的共性。
當然,話說回來,不論城市或鄉土,首先得有風土人情或是風物景觀,有生活在其中的人物和人物關系,才可能有超越其上的現代性意旨。城市由商賈買賣發展起來,商品、貨幣以及圍繞商品展開的一整套生產、流通和消費的過程奠定了城市的基本品格,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人們處理人與自然以及自我與他人的關系方式,這是一套完全不同于鄉村的生活樣貌和價值觀念。尤其是在現代的工業化都會中,不同行業、不同身份背景的個體因商品而匯聚在城市空間中,組成了一個陌生人的社會。這些超越血親或鄉情的人際交往,形成了完全依賴消費行為和貨幣經濟確立起的價值標準與衡量體系,重新定義了文學創作中的矛盾沖突與情感走向。
由于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是在政府的整體規劃和政策指引下推進的,因而中國的城市顯現出兩個基本特征。一方面,商品流通所帶來的標準化生產、集約化管理和品牌文化使城市的樣貌越來越趨同。特別是體量相當、定位相近的城市之間的差異也越來越小。所以,盡管我們身處不同的城市,看到的卻都是類似的城市景觀。另一方面,隨著流動人口的增加,數量眾多、彼此獨立又相互連接、中心明確卻邊界流動的文化群落布滿了城市。這些群落可以依據消費習慣、生活經歷、興趣喜好、休閑方式等不同名目建立,它們相互疊加,借助城市的包容和擴張,發展并鞏固自身的文化品格,同時其適應性和滲透力也使城市本身無法再保持風格上的統一和完整。每一個市民都有可能同時躋身多個文化群落,城市因此也都成了不定性的城市。由于今天的城市不再是一個純粹的意義空間,所以當寫作者描述他們生活的城市時,不同的處境、立場、視角和眼光看到的城市風貌,以及將城市作為文化符號寄托的精神寄寓也就不盡相同。這便是現代城市的“千城一面”和“一城千面”,這一特性為城市文學提供了多重表達的可能。
張 菁:城市文學是以個人面對現代生活的方式為重點的文學。它開放、動態,關注自身和未來。它意味著在現代化的進程里,文化的多樣與豐富,人們在新經驗、新困境、新倫理中展現出的愛與自由、寬容與理解。它意味著刺破尋常的意識、好奇探索的能力、多元審美的格局。它不像鄉土文學,以宗親和傳統文化倫理為支撐,以家族和熟人生活為重點觀察對象,它注重的是在生存經驗之上,展現文化經驗。
談論文學的呈現,終究離不開作家。作家是主體,作家的呈現是主體。優秀的、偉大的作家會給不同的城市和城市面目塑形。那蓬勃的熱情與好奇,熾熱的愛與信念,那人類擁有的愛的天賦與能力,構成彼此的認同和統一。城市文學的寫作者需要有世界眼光和現代意識,而不是喋喋不休地講述我們耳熟能詳的道理。
郭冰茹:按《廣州文藝》城市文學論壇欄目主持人的意思,我們聚焦一下廣州和北京的城市文學。廣州和北京這兩座城市,分別是以怎樣的方式呈現在文學作品中的?在我們的感覺中,廣州和北京當然是兩個精神氣質非常不同的城市,但文學作品是要表現城市的共性,比如商品邏輯、價值觀念,還是要寫出城市的個性,比如風物民俗,以及如何處理這種共性與個性的關系,都是與作家的文學觀念、寫作目的以及時代主潮相關的。換言之,呈現在讀者面前的城市是被作家制造出來的城市,這也是我剛剛提到的“現代性視域”的問題。在1950年代的《三家巷》中,廣州雖然發生了省港大罷工,是革命的策源地,但歐陽山對廣州的描寫更偏向民俗,比如除夕賣懶、人日登高、七夕乞巧、荔灣泛舟等,而且人物關系也圍繞姻親和鄰里展開,這樣的處理讓廣州的形象比較貼近“傳統”或“鄉土”。而在同一時期的《我們夫婦之間》中,北京則表現得遠為“現代”,李克回到了他闊別十二年的大城市,看到的是他熟悉的沙發窗簾、霓虹燈跳舞廳,他準備用稿費買皮鞋、買紙煙、看電影、吃“冰其林”……這顯然是建立在生產和消費基礎上的城市生活邏輯,也是小說想要批判的“你的心大大的變了”。蕭也牧筆下的北京突出的是城市的消費屬性,但有意思的是當小說被上海昆侖影業改編成電影時,故事的發生地由北京變成了上海,或許在時人的眼中,上海是比北京更“城市”的城市。而上海作為城市的消費性質幾乎也貫穿了整個20世紀中國小說對上海的書寫,這是另一個話題,我們有機會再說。
回到廣州,廣州是改革開放的前沿,也可以說是1980年代最先接受商品經濟和市場文化洗禮的城市。文藝作品中的廣州是《雅馬哈魚檔》中熱火朝天的自由市場,《公關小姐》中的星級酒店和白領麗人,《掘金時代》《浮華背后》中俊男美女的商戰情戰。與之呼應的是融入大江南北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粵語歌、港產片、打口碟、瓊瑤劇和“買單”“打的”這些口語詞。張欣說:“我覺得都市文學是改革開放之后才有的,之前的所謂都市文學其實是農村人穿著都市人的衣服,他們可能也涂著紅指甲,去大酒樓吃飯,也去跳迪斯科,但腦子里還是鄉村觀念,城里人和鄉下人是一樣的。”所以張欣寫廣州,寫的不光是咖啡店、精品廊、寫字樓、Shopping Mall和被各種品牌包裹著的都市男女,而是建立在商品邏輯下的人物關系和生活樣貌。當文藝作品中的廣州舍棄了“鄉愁”或民俗,劉震云、王朔寫北京同樣也撇開了最能體現“老北京”風貌的城市特質。北京是日常生活中的《一地雞毛》和《單位》里的人事周旋,是閑蕩在都市里憤世嫉俗調侃權威,上演著一出出鬧劇的《頑主》們……卡林內斯庫在《現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將現代性分為資產階級現代性和文化現代性兩種,前者崇尚效率、理性、科學、實用主義,是科技進步和工業革命的產物;后者則是在文化或美學上對前者的反思與反叛。也有學者將這兩者分別命名為社會現代性與審美現代性。按照這樣的理解,我們大體可以說文藝作品中投身都市的廣州奔向了社會現代性,而北京則奔向了它的另一面——審美現代性。
當然,這樣的區分也只是大體上的描述,并不確切,也不能總攬所有關于廣州或北京的書寫。而且隨著中國社會越來越被納入到全球化的經濟體系中,無論身處廣州或北京,“環球同此涼熱”的同質化感受也日趨明顯。因此,如何書寫城市,以及寫出怎樣的城市也就更加依賴作家對材料的處理,畢竟如何彰顯寫作個性是寫作者更為關心和關注的問題。我們看這兩三年的城市文學,張欣推開了她能順手拈來的都市麗人,轉而去寫百年前廣州城里三個女人的《如風似璧》,用女性的“韌”寫廣州的城市精神;王威廉則把目光投向遠方,思考科技局限帶給人類的《野未來》。邱華棟回到史料中,以非虛構的方式寫北京這座有著三千年歷史的城市是怎樣慢慢成長起來的《北京傳》;石一楓則從最新鮮、最貼近生活日常的材料出發,把心得感受融入對現實人生的觀察,寫出了白天卷自己、晚上卷孩子的《逍遙仙兒》。寫作者對城市的感覺是具體的,不管他們的作品中是否有廣州或北京的地理標識,他們生活的城市就在那兒,是他們寫作的根基和土壤。而從讀者的角度來看,也正是因為現代城市的“千城一面”和“一城千面”,我們在文學作品中看到的才是一個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廣州或北京。
張 菁:在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的今天,作家們在豐厚的地域文化滋養下生成新時代的個體經驗,以創造性的、細膩溫婉的審美建立自己的文學世界;自己無論身在哪里,靈魂都駐守在這片溫潤的、有靈性的土地上,這樣才會使創作有根,使作品有魂。
侯磊是一位以散文創作為主的80后青年作家,其作品幾乎都是以北京作為背景創作的。與其他寫作者不同的是,他在作為散文作家之前,首先是一位北京歷史文化的研究者,寫過大量北京文史方面的文章,點校整理過北京古籍。所以侯磊的作品中,既有歷史的視角,又有古典的審美,還有著微觀史學的意識。
北京作為一座千年古都,有著深厚的歷史背景,在侯磊筆下,他并不僅僅是寫自己80后所身處的這代人的故事。他會拓展到上三代、下三代的故事。比如,他有不少作品是寫自己祖輩——爺爺奶奶那代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老北京時代的故事,如《德容:北平照相館》《奶奶沒有名字》等;也會寫自己父輩——父母那代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的故事,如小說《女司機》《紡織廠的女兒》,還以知青子女的角度,去寫知青故事,如小說《父親的長生天》,散文《倒數第二個女知青》等,這種現象在當代青年作家中還是不多見的。而隨著作者年齡的增長,他會寫自己這代人,以及自己下一代人的故事,這樣他筆下有了歷史的縱深感,并且充滿了北京這座城市的歷史細節,如衣食住行、風俗風物、人文掌故等。這些從現代歷史學科的角度叫微觀史學。作者也在訪談中說過,讀研究生時的碩士畢業論文是研究北京掌故,談及前輩學者所認為的掌故學,主要包括政治制度史和風俗制度史,自己的創作也很受益于北京掌故。
同樣地,文學藝術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侯磊筆下充滿了對北京的審美,寫出了北京這座城市的顏色和氣味,提煉出北京的美、北京的雅、北京的溫情等古典意味的美學。他筆下展現出北京的色調,如綠樹紅墻琉璃瓦,依依楊柳與舊日斜陽,這在《北京煙樹》這本頗有懷舊意味的書中展現得十分集中。這種審美之下沒有十分劇烈的矛盾沖突,即便是對貧困生活的描寫,也仍舊不失人情味兒。這與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先鋒敘事大不一樣,且與作者所處的年代和成長環境緊密相關。作為80后城市中長大的青年,成長環境變了,當下文學藝術的發展也變了,因此作為個案而言,侯磊筆下的北京城展現得十分突出:既古典,又現代。新北京中永遠帶著點兒舊,老北京中永遠透著新。
同樣是北京,在孫睿的筆下,生活的趣味在毛絨絨的質地和氣息中透露出來,在戲謔的筆觸中透露出溫和,就像日光里的浮塵,有塵的雜,更有光的暖。孫睿有著善于從生活和生命感悟出發,進而“抽象”出寓指意味的能力;有著對生活生命認真真誠的愛,進而“衍生”出悲憫和體恤的能力;有著善于捕捉生活細節,并不斷放大這樣的細節增強其作品說服力的能力。他善于甚至可以說極善于抓住那些有意味和趣味的生活細節,讓讀者“身臨其境”,“感同身受”。
廣州的作家以王威廉為例,在他的筆下,這片地域更多呈現的是文化的交融。在《你的目光》里,我們可以看到客家文化與疍家文化的碰撞、歷史與當下的聯系、人與人的鏈接。在威廉眼中,世界流轉、變化、多維,過往的厚重積淀與當下的澎湃躍動對視,生命的力量在交融中被不斷激發,孕育新的可能,迸發新的活力,更重要的是,人們之所以可以世世代代長久地被給予希望,究其根源在于深沉和厚重的愛。
郭冰茹:我們還可以談談這兩座城市的文學,哪些元素最能表現城市性格。我們都熟悉一句老話——“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好的文學作品中沒有立得住腳的人物形象,沒有真實可感的人物關系是難以想象的。風土是人情的載體,如果沒有人情,只有風土,那大概率不是文學而是說明書或導覽圖。當然,由于寫作者對城市的感知和認識不同,經由人物塑造出來的城市性格也就有了差異。
葛亮寫《燕食記》,說“中國人的道理,都在這吃里頭了”,粵地對“食”的看重讓“食在廣東”成為一張如假包換的地方名片,而圍繞制作點心菜品的大按師傅榮貽生和徒弟陳五舉所展開的故事,以及經由故事和矛盾沖突塑造出來的人物性格也就成為廣州、香港兩地城市性格的體現。《燕食記》里的廣州守成、執著,香港則顯得更為包容、變通。張欣寫《如風似璧》,百年前的廣州城里也有粵菜包點、粵劇小曲、騎樓馬路,她將筆力放在三個不同階層、不同生活境遇、遭遇不同生活之變的女人身上,寫她們在經歷劫難時的“韌”,因為“韌”是張欣認定的廣州性格。北京、上海等城市的書寫也一樣,老舍寫駱駝祥子、王朔寫“頑主”、王安憶寫王琦瑤、金宇澄寫阿寶既是見人見性,也是見人見城。
當然,這里也涉及語言,尤其是方言的使用問題。寫廣州不用粵語詞匯,作品會失去“粵味兒”,用得多了,對非粵語區的讀者會造成不必要的麻煩。寫北京、寫北京人可能也會遇到類似的問題,畢竟用不用,以及怎么用對外地人來說最具北京味兒的兒化音也并非不證自明。因此,如何拿捏這個尺度,對作家來說是個不小的考驗。我在一篇關于方言寫作的文章中談到過這個問題,我覺得除了給敘述中的方言詞匯加注釋之外,其實也可以有其他的處理方法,比如葛亮在《燕食記》中的“同義反復”,就是使用了一個粵語詞,之后再用普通話轉述一下,讓方言詞匯不露痕跡地化在敘述語言中。北京話也許不存在這個轉譯問題,但如何讓本是口語的方言進入我們今天的書寫系統同樣也是寫北京、寫上海、寫任何一個具有地方性特質的城市所遇到的課題。這需要寫作者在實踐中去探索。
張 菁:一座城市和她所涵養的文學,相互觀照,彼此影響。文學和城市文學的品質是城市的軟實力,是城市品格最為纖細而敏銳的反應,是文化認同的內在黏合劑。她照見這座城市里人們的心性、情感和心理寬闊度,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城市的氣質。
最能凸顯城市性格的元素,是作家們的個性差異。在我看來,書寫北京,是否有兒話音、用不用京腔來完成并不重要,寫不寫胡同也不重要,我們希望看到的是更為內里和深刻的意蘊。作為一個在北京出生并一直生活在北京的人,我不在意北京的作家是不是寫出我熟悉的風景,我不會為它而感覺多么興奮。能夠點燃我興奮的,是它對我經歷中那些微妙處的“呼喚”。它讓我突然意識到,我曾有過這樣的感受,原來它的問題在這里,原來它如此值得我思忖或警惕。
北京的城市性格,開放與傳統并包。當代北京的性格:內斂與典雅,中正與厚德。北京從文化教育、日常管理都日趨現代化。它以一個更積極的形象出現了。北京的作家們,內里有著柔軟和潤,在他們筆下,即使在難以掙脫的困境中,也會放出一條縫隙。
同時,隨著傳統文化的復興,北京越來越展現出這座城市傳統的儒家精神。儒家傳統注重道德、注重秩序感,溫和中庸。這些特點在當下北京的作品中,多少都能夠透露出一些來。
廣州的城市性格,在我看來是融合與銳氣。相較北京,它在中正中還包含帶有銳氣的力量感。它更像快進鍵下的人流涌動,居于其中的自洽,來源于努力和進取。相信作家們會繼續寫出真誠的感受、思考和看見,通過城市生活寫下個體的人,喚起更多人的精神記憶,引發共鳴。
責任編輯:朱亞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