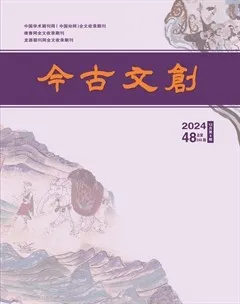田耳懸疑小說的反類型敘事研究
【提要】田耳的懸疑小說以其創新性突破了傳統懸疑小說的框架,展現反類型化特征。通過多重敘事視角并置、緩慢敘事節奏以及生活化場景描寫,洞悉人物心理,展現社會現實。其作品常以宿命感和開放式結局引發讀者深思,小說內容雅俗兼具。同時,反類型化懸疑小說也在形成新的懸疑小說類型,促進了文學的發展。
【關鍵詞】田耳;懸疑小說;反類型;敘事研究
反類型是文學創作的重要助推力,賀紹俊就曾指出:“文學不僅僅存在著文學類型化傾向,而且還存在著創新性傾向,創新性是反類型化的,創新性傾向就避免了因為類型化而導致文學的千人一面。”[1]這種創新力量,讓類型與反類型在碰撞中共同驅動文學發展。田耳的懸疑小說有別于傳統的懸疑小說,它突破了傳統框架的束縛,展現出反類型的敘事特征。因此,探究田耳懸疑小說的反類型敘事特征,不僅能揭示田耳的懸疑小說如何以獨特的敘事手法挑戰傳統,更能推動我們對文學創新機制、審美觀念的深刻理解,具有重大意義。
一、田耳懸疑小說的反類型敘事策略
(一)多重敘事視角的并置
與傳統懸疑小說不同,田耳的許多懸疑小說都是多視角并進的,并且有些視角是有意味的。如《一個人張燈結彩》中的“警察+兇手”雙重敘事視角。在警察老黃的視角中,死者于心亮、啞巴小于、兇手鋼渣、共犯皮絆等作為主要人物,他們之間構成了一張關系網,老黃既是這張關系網的一員,又是明察秋毫、超脫其外的觀察者。兇手鋼渣的視角揭示了社會的復雜人性,包括物欲、情欲及人之惡。小說故事隨著鋼渣與小于戀愛,意外殺害于心亮,直至老黃與鋼渣在超市對峙而逐步推向高潮。“警察”與“兇手”兩種截然對立的身份視角在敘事中激烈碰撞與融合,不僅構建了邏輯嚴密的敘事框架,還通過視角的并置切換,使各個情節嚴絲合縫,為讀者帶來強烈的閱讀快感與邏輯滿足感。
又有《在場》的目擊者視角。作為監控值班人員,“我”目擊了女小偷行竊,又目睹了女小偷遭情緒失控的男子劫持。監控室的獨特視野賦予“我”稀缺的目擊資料,各個媒體爭相抬價求購,“我”也在金錢的誘惑下期待更震撼的現場畫面出現。“我”從一開始對女小偷的關懷,“女賊也有女賊的苦惱,也許她進城做了幾個月的工,卻領不到工資”[2]244,轉變到“往下更精彩,裸鏡都出來了”[2]259的漠視,這不僅是對現代社會個體隱私窺探與獵奇追求欲望的外窺,也是對人性多變復雜性的內窺。
以往的傳統懸疑小說多數采用破案者為敘事視角,例如《盜墓筆記》《地獄的第十九層》等,由親歷者展開故事敘事,而田耳有意于突破這類單一的敘事視角,不僅加入了兇手,甚至也將受害者和目擊者納入了敘事視角,增加了讀者在閱讀中短時間判斷故事發展軌跡的難度,提升了文本的懸疑效果,也提高了文本的探索價值。
(二)緩慢的敘事節奏
相較于傳統懸疑小說追求的刺激與驚險,田耳的懸疑小說中穿插了大量的生活化場景描寫,削弱了故事的懸疑色彩,用質樸呈現民間真情與社會萬象。如《一個人張燈結彩》,開篇即以警察老黃的日常刮臉場景啟幕,繼而連接起小于、鋼渣的生活場景,構建起關系脈絡。又如《天體懸浮》中的洛井派出所,作為基層機構,其處理的案件多為鄰里瑣事,映射著百姓日常生活細節。這種于平淡中見波瀾的敘事方式,讓每個情節都自然地銜接起來。此外,不難發現田耳的小說世界大多鋪設于城鎮與鄉間,不同于大都市的喧囂與繁華,城鄉自帶著質樸與寧靜的氣息,為故事平添幾分輕松與愜意,也讓敘事節奏看起來更加從容。[3]
田耳的懸疑小說中還加入了許多人物的內心感性情感,不以緊張刺激的氛圍和推理占主體,而以人物的內心癥結,抑或是人物的心理落差,作為推進故事發展的勢能。尤其《被猜死的人》更是直接以心理活動推動整個事件的發生。老人們通過下賭注預測下一個將死之人,而獨眼梁順的預測十分靈驗,其他老人為求自保,便向梁順獻上財物,以求延緩死亡。作為“猜者”的梁順“不畏死”,他大膽、激進;而被猜的老人“怕死”,害怕、畏縮,這兩種心理便作為情節發展的雙驅動力。在《夏天糖》中,更是以江標對鈴蘭難以言說的情愛為主線。江標幾次想拯救鈴蘭,都被她拒絕了。當江標讓鈴蘭穿著綠色衣服躺在路中間,試圖重現記憶里的畫面時,他“努力想從她身上找到當年那小女孩的影子,哪怕只是稍縱即逝的一點點痕跡”[2]85,可當江標看到鈴蘭嫵媚的笑的時候,他卻不可控地加速開車軋死了她,毀滅了這一切。這是江標內心近乎變態的極端執念導致的。
在田耳看來,文學創作就是“他們遞交的關于人類生活隱秘狀況的情報”[4]。無論是對小說場景的刻畫還是對人物內心感性情感的描摹,田耳的懸疑小說都展現出了不同于傳統懸疑小說的細膩程度,對人性的剖析是一層層深入,直指內里的。
二、田耳懸疑小說的反類型敘事邏輯
(一)命運的“不湊巧”與宿命感
田耳的懸疑小說常常出現許多陰差陽錯,偶然和巧合,帶有很強的宿命感。例如《一個人張燈結彩》中兇手鋼渣殺死的人恰好是自己心愛女人的哥哥;《衣缽》中李可初涉道門第一天,父親就意外去世了,而后李可也子承父業成了一位有名的道士;《坐搖椅的男人》中小丁終日沉淪于舊時岳父的搖椅,時常打罵妻子,但這是小丁小時候最討厭的模樣;《夏天糖》中則對比了鈴蘭幼時的純真與如今的風塵,江標的幻想遭到破滅,與《衣缽》中的李可的接續父業不同,江標選擇了共同毀滅。根據李敬澤的說法,田耳對巧合和偶然的迷戀是對“人的信念”[5]。《瀟湘晨報》在對田耳的采訪中提到“一個不被待見的孩子,手腳不靈便,成績不優異,壓抑過久過深之后,他將不以約定俗成的方式打量世界”“相信人性本惡,他是從人性本惡出發去看世間”[6],由此我們可以推測,田耳的“人的信念”即為對“人性本惡”的信念,其小說中對命運“不湊巧”的安排是有意為之的,他的童年經歷和成長經歷開辟了他獨特的視野。人性中都有本質的惡,而人之惡能讓“不湊巧”變為“剛剛好”,由偶然變為必然。
同為湘西作家的沈從文,在《邊城》中,一群善良的人卻因為處處“不湊巧”導致了悲劇的發生,然而田耳筆下的人物卻是有著明顯的“惡”的一面。《一個人張燈結彩》中的鋼渣,面對心愛的女人小于,他是浪漫、善良的,他主動學習手語,甚至想著“如果以后和小于生了一個孩子,定要讓他好好學習天天向上”[7]108,然而鋼渣又是一個社會的不安分子,搶劫司機時因被對方看到長相就痛下殺手,卻不曾想司機就是心愛女人的哥哥于心亮。這種反差,不僅蘊含著命運弄人的“不湊巧”,更深刻揭示了宿命的必然邏輯,即前文鋪墊引導后續事件的必然走向。如鋼渣搶劫于心亮之時,正是于心亮開始運貨業務之時;就于心亮而言,他因家庭負擔不得不夜晚工作;就鋼渣而言,他本不打算殺害于心亮,但因為于心亮的反抗使他無法做到全身而退,便將他殺死。這種時間上的“湊巧”與宿命般的交織,看似偶然,實則必然。田耳的小說充滿的就是這樣一種意外或者說旁枝逸出,而也正是這種旁枝逸出使得田耳的小說更有情趣和意趣。
(二)沒有“解疑”的懸疑小說結局
關于懸疑小說的概念,學界已有比較清楚的界定,“以懸念的設置和解除來推進故事情節是懸疑小說最重要的特征”[8]。懸疑小說的一大特征便是懸疑的設置與解除。而在田耳的懸疑小說中,大多采用開放式結局,不僅未完全解開既有的懸疑,反而在結尾巧妙引入新謎團,極大地豐富了文本的層次與解讀空間。例如《一個人張燈結彩》,小說的結尾,老黃本打算信守與鋼渣的約定在年三十一去看望小于,但卻在離小于店面還有百十米遠的地方收了腳,開始了自己的反思。故事結束,劉副局之死的案件還沒有被偵破,老黃是否進入小于的店面也無從得知,小說便以“時間是無限的,時間還將無限下去”[6]144收束全文,又設置了雙重懸念,留下了無限空白。
又有《在看》的結局,在槍響后,“我”看見綁著炸藥的男人試圖將手里的兩股線的頭觸碰一下,隨后“我”便膽小地立刻蹲下,“電線剪斷了嗎?槍打著要打的部位了嗎?”[2]216綁著炸藥的男人被控制住了嗎?現場有人傷亡嗎?這些信息作者并沒有告訴我們,而是又設置了多個懸念,留下開放式的結局。《圍獵》中的小丁,在小說最后還在被人群追趕,最終他的結局如何,又是一個未解之謎。田耳這種不追求傳統“解疑”的結尾方式,不僅進行了大量留白,留足了空位,促使讀者主動填補空位以實現文本的“聯結性運作”[9],更有通過設新懸疑的方式,引導讀者作為偵探,主動參與到故事的再創作過程中去尋找答案,實現了文本與讀者之間深度的互動與共鳴。無論是留白引發的深思,還是以新懸疑激發的探索欲,都極大地提升了小說的藝術魅力與思想深度,讓讀者在閱讀之后仍能沉浸其中,久久回味,常讀常新。
三、田耳懸疑小說的審美意蘊與反思
(一)“雅”與“俗”的藝術合流
懸疑小說歷來被視為通俗文學,以滿足人的欲望和娛樂為主,難以登入文學的“大雅之堂”;然而田耳的創作打破了此種偏見,雖然表面上看起來通俗易懂,但在實際創作實踐中,絲毫未減其寫作的難度與挑戰,其內里蘊含著嚴肅文學的深刻內核,做到了雅俗兼具,實現了從“娛樂文學”到“經典文學”的跨越。
田耳的懸疑小說吸收了網絡文學、影視藝術和純文學的表現手法,小說中有常見的陰謀、愛情和俠義等流行元素,例如《秘要》中的武俠情、《環線車》中的“四角戀描寫”、《被猜死的人》中的“死亡賭博”等,在這些流行元素的外衣之下,田耳以其敏銳的洞察力和深厚的文學功底,實現了“雅”與“俗”的藝術融合,其作品既通俗易懂,又不失高雅韻味。田耳以通俗化的敘述手法和貼近生活的場景描繪,為其小說披上了大眾化的外衣,但其作品的核心深植于文學,值得反復咂摸,仿佛細品一碗回味無窮的“細糠”。新作《秘要》中這一特點尤為突出。小說中,“家家戶戶都有了電視機,最受歡迎的只能是港臺武俠劇,每一部都刀光劍影,光看武打就讓人一個勁兒叫爽”[10],田耳將當時的武俠小說和武俠劇作為故事邏輯和人物心理發展的起點,跳出了固有的武俠小說框架,將故事的寫作重心放在書本的創作、出版與流通上,如此便超越了文本的范疇而走向“寬闊的文化政治與社會歷史視域”[11]。
田耳懸疑小說的“雅”與“俗”的藝術合流集中體現“底層人”上。田耳始終關注的是底層人,其筆下的人物都帶有濃厚的精神創傷。《夏天糖》中江標對鈴蘭的終結,實則源于內心長久以來未曾釋懷的欲望,一段渴望重現并修正的過往;《被猜死的人》中的老朱因恐懼詛咒而先行殺死梁順,這是生存本能,也是人性的反抗;《一個人張燈結彩》中的啞巴小于,身體缺陷使得她對“被愛”的渴望異常強烈,戀人鋼渣的出現成為了她生活的動力,但她卻不知道正是鋼渣殺害了她的兄長,這一設定不僅加深了故事的悲劇色彩,也展現了人性中的盲點與宿命般的糾葛。對各類底層人的深入描寫使得田耳懸疑小說擁有傳統懸疑小說所不具備的深度。
田耳在突破傳統懸疑小說模式的同時,真正做到了懸疑與文學的結合,將懸疑小說這一“俗文學”變成“雅文學”。“俗”包含著通俗化、大眾化的意思,還帶有一定的娛樂性質。田耳巧妙地將這種娛樂性轉化為對人性深度探索的驅動力,使得作品在敘事時還能引起讀者對人性和命運的思索。田耳小說的娛樂是兩重性的:一方面,是一定量的解謎過程,給予讀者滿足與愉悅;另一方面,則通過展現獨有的底層人物的生存狀態與人性特質,以及結局的留白與深刻內涵,引導讀者進行更深層次的反思與共鳴。這種從“俗”到“雅”的升華過程,不僅提升了作品的藝術價值,更賦予了其深厚的精神意蘊與犀利的思想鋒芒。
(二)從反類型到新類型的生成
田耳打破了傳統懸疑小說的部分敘事套路,其小說通過多視角敘事、慢節奏生活化描寫、強調命運的偶然性與宿命感,構建了其獨特的懸疑風格。他的懸疑常以開放式結局留給讀者深思,同時在通俗的敘事中融入嚴肅文學的內核,以此實現了雅俗藝術的結合。這些特征,為田耳在傳統懸疑小說的基礎上新增的獨有元素,即“引入‘變量’,為固定的元素增加新變”[12],形成了反類型的懸疑小說。我們總覽田耳的懸疑小說,短篇如《一個人張燈結彩》《衣缽》,長篇如《天體懸浮》《秘要》,在內容上,均有對命運“不湊巧”的情節設置;在人物關系設定上,均有對男女情愛羈絆的設定;在敘事配置上,均在懸疑敘寫中穿插大量底層人的生活化描寫,形成了一種慢節奏的“懸疑+底層”的小說敘事配置。這些反類型的特征為田耳懸疑小說共同的獨特性,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田耳產生反類型懸疑小說的同時,也形成了一種新類型的懸疑小說。
這種懸疑小說風格,田耳并非個例。比如《漫長的季節》
《回響》和《平原上的摩西》都屬于此類創作。這些類似的“反類型”風格的出現,不禁讓我們思考,這是否也代表著新的類型化的懸疑小說正在生成。賀紹俊在《類型小說的反類型化》中提及“當文學創作過程中有一種新的因素被人們接納并受到人們的歡迎時,這種新的因素就會產生一種吸引力,作者會被這種吸引力所吸引,自然地靠近這種新因素,而讀者則會在閱讀中認同這種新的因素,形成固定的審美經驗”。新類型的出現無疑與“文學消費主義表現”[13]有關。
當下閱讀市場需求不斷提高,教育普及促使越來越多的讀者轉向深度閱讀,在讀物中尋求精神啟迪與共鳴。如今大多傳統懸疑小說的缺點被不斷放大,如膚淺泡沫化,一批剖析現實與人性的懸疑作品則應運而生,其本質也是人們精神境界的提升。懸疑小說經典化,必須要有反類型化的加入,為懸疑小說注入動力。
在這樣的環境下,作為知識分子,作為作家,唯有不斷突破自我,同時有意于與類型文學拉開距離,才能擺脫“從類型化到新類型的生成”這樣的文學循壞圈。薩義德曾用“流亡”來形容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應該具有的狀態,也即“流亡意味著將永遠成為邊緣人,而身為知識分子的所作所為必須是自創的,因為不能跟隨別人規定的路線”[14]56。這對于身為知識分子的作家有著極大的啟發性意義,作家唯有處于一種邊緣的“流亡”狀態,不拘泥于具體的寫作范式,才能有所突破,“流亡有時可以提供的不同的生活安排,以及他們觀看事物的奇異角度”[14]53。作為知識分子的田耳正是借由這種“流亡”的寫作狀態,突破傳統懸疑小說的敘事窠臼,關注到懸疑這一類型小說背后的生長空間,創作了許多反類型的懸疑小說。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流亡”的終結,恰恰相反,這是一個作家寫作的起點,他唯有繼續“流亡”,從“新類型”文學不斷掙脫,才能迎來寫作的不斷突破。
參考文獻:
[1]賀紹俊.類型小說的反類型化寫作[N].深圳特區報,2010-9-20.
[2]田耳.衣缽[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4.
[3]徐勇,伍倩.“去價值化”寫作與日常生活的敞開性——田耳小說論[J].民族文學研究,2017,(03).
[4]田耳.短篇小說家的面容[N].文藝報,2013-4-22.
[5]李敬澤.靈驗的講述:世界重獲魅力——田耳論[J].小說評論,2008,(05).
[6]徐長云.湘西作家田耳“我對底層不敢說是同情”[N].瀟湘晨報,2014-5-12.
[7]田耳.一個人張燈結彩[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8]鴉潔.當代現實懸疑小說的敘事研究[D].蘇州大學,
2019.
[9]沃爾夫岡·伊瑟爾.審美過程研究——閱讀活動:審美反應理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
[10]田耳.秘要[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3.
[11]曾攀.武俠江湖、民間世界與新形式的發生——論田耳長篇小說《秘要》[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3,
(10).
[12]袁勁.網絡小說的反類型化及其問題反思[J].廣東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3,(05).
[13]湯哲聲.論新類型小說和文學消費主義[J].文藝爭鳴,2012,(03).
[14]愛德華·W·薩義德.知識分子論[M].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
作者簡介:
周羽欣,女,漢族,浙江溫州人,紹興文理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