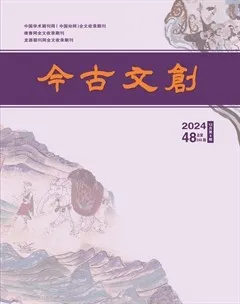主客觀倫理身份沖突與倫理身份附庸
【摘要】歐里庇得斯的作品《特洛亞婦女》運用尖銳的戲劇沖突對人物群像進行描寫,描寫了特洛亞城被攻破后特洛亞婦女的悲慘命運、雙重倫理身份,以及由雙重倫理身份導致的倫理困境、陷入倫理困境后的倫理選擇。目前學界對于《特洛亞婦女》的研究相對較少,且基本集中于問題意識、敘事結構、敘事視角方面。本文將從女性主義與文學倫理學相結合的角度對《特洛亞婦女》的特殊倫理困境及其深層原因、倫理教化意義進行探討。
【關鍵詞】文學倫理學;古希臘悲劇;歐里庇得斯
在國內外學界,歐里庇得斯是文學研究者的重要研究對象。作為古希臘三大悲劇家之一,他的作品具有重要的歷史學和社會學研究價值,目前對他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女性意識、戲劇特色等方面。《特洛亞婦女》是其重要作品,對該作品在文學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敘事上,涉及文本的敘事視角切換與敘事者的轉換、人物設計等方面。
文學倫理學作為當下國內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方面的重要理論,在研究早期西方文學、古希臘戲劇沖突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它旨在在特定的倫理情境下,用倫理視角觀察文學作品及人物形象、人物選擇,詮釋其倫理身份及倫理意義,為文學作品的研究提供新思路、新視角。
《特洛亞婦女》運用尖銳的戲劇沖突,展現(xiàn)了城邦時代戰(zhàn)敗城邦女性的生存狀況,她們在特洛亞城邦賦予的原有倫理身份之上獲得新的倫理身份,但雙重倫理身份產生的主客觀沖突造成了倫理困境,她們在精神上做出了倫理選擇。歐里庇德斯依托社會現(xiàn)狀和發(fā)生過的真實事件,通過描繪特洛亞婦女在倫理困境之下的生存狀況,深入城邦制之下,探究城邦人民的生存狀況和倫理困境產生的根本原因,呈現(xiàn)當時常見的城邦戰(zhàn)爭現(xiàn)象及其結果,對同時代的城邦及其統(tǒng)治者產生了較為巨大的倫理教化作用,發(fā)出了劇作家在城邦時代的人文主義呼聲。
一、倫理困境的展開——二重倫理身份構建
特洛亞婦女的倫理困境始于其二重倫理身份的建構。在文本最開始,特洛亞婦女僅具有一重倫理身份,即特洛伊城邦中的女性——特洛伊城邦男性的妻子、女兒或母親,這一倫理身份依附于特洛伊城邦中男性倫理身份而存在。在城邦制度的倫理情境之下,女性的倫理身份由其依附的男性倫理身份決定,這揭示了特洛亞婦女的第一重倫理身份是帶有不完全個體特性的依附者,特洛亞婦女地位的高低也由其依附男性的地位高低而決定。
以赫卡柏為例,她的第一層倫理身份是特洛伊城的前王后,赫克托爾和帕里斯的母親。同時,由于她依附的男性最為強大,因此她在所有女性中占據至高地位,特洛亞婦女們在無措時都會前來向王后尋找庇護、尋求安慰,歌隊的演繹也始終以其為中心,而赫卡柏的行為、思想也代表了整個特洛亞婦女群體的行為、思想,具有象征意義。再如,安德洛瑪刻是作為赫克托爾妻子的這一層倫理身份出現(xiàn)在讀者和觀眾的視野中。其他特洛亞女性的出現(xiàn)同樣如此,以某位男性的妻子或者其女兒作為主要身份。而她們的話題始終圍繞著男性生活與男性失敗后自身何去何從的惶恐,展現(xiàn)了其生活以男性作為中心的特點。而女祭司卡珊德拉的命運也能夠反映這一點,作為祭司的她仍然難逃被希臘人拉走做阿伽門農的侍妾的命運,可見其命運仍然要依附于男性。
而且,文本開頭已經交代,這些特洛亞婦女的最終命運由抽簽決定,由此可見,特洛亞婦女是具有物化特征、不具備獨立意志的群體,她們更多地像物品一樣被分配,具有附屬的特點,不是城邦中真正的主人。
這種倫理身份決定了婦女對于城邦的附庸,這種倫理身份在戲劇的語言中有極為清晰的描述。例如,在進場歌中,甲半隊提到“我們特洛亞婦女正是膽戰(zhàn)心驚”,以“特洛亞婦女”作為自稱而不以名字自稱,婦女們通過這一稱謂展現(xiàn)了其倫理地位,這也展現(xiàn)女性對于這一倫理身份的認可。
男性作為城邦的主宰和占據主導地位的公民,實際上能夠代表整個城邦的存亡,男性的失敗意味著城邦的滅亡。在城邦被滅亡后,特洛亞婦女整體也被迫成為一個被滅亡城邦的附屬物。相較于婦女們后來被賦予的其他倫理身份,特洛亞城邦附庸這一重倫理身份顯然出現(xiàn)更早,且更為婦女們認可,并始終延續(xù)橫亙整個戲劇發(fā)展過程,構成雙重倫理身份中最為初始的一層。
隨后通過波塞冬和雅典娜的對話,作者交代了當時特洛亞城已經被攻破、男性被屠殺、特洛伊城的女性也將面臨殘酷的命運的現(xiàn)實境遇。借助波塞冬的全知視角將卡珊德拉被迫做妾、波呂克塞娜被殺死在阿喀琉斯墓前的悲慘故事揭示出來,已經為整體特洛伊婦女的悲慘命運奠定了基調。
接下來的進場歌直接通過特洛伊婦女之口揭示了她們將成為女奴的命運。在第一場的劇情中,由傳令官蓋棺定論——大多數女性成為奴隸,就連在原始倫理身份中地位最高的赫卡柏也不例外,她成了俄底修斯的奴隸。兩個重要的女性形象代表安德洛瑪克和卡珊德拉由于美貌與特殊地位被迫嫁給了希臘城邦的男性做妾。這時的特洛亞婦女已經被迫更換她們的依附對象,她們開始成為希臘城邦中的一員,命運由希臘男性掌握。
這決定了特洛亞婦女的新一層倫理身份——希臘城邦中地位較低的妾或者奴隸,并進一步抽象為希臘城邦的附庸。相較于城邦中仍然有一定地位的獨立女性,妾或者奴隸無疑地位更低,因此相較于第一層倫理身份,這是一種降級的附庸。
特洛亞婦女的二重倫理身份在此刻構建成型。一方面是作為特洛伊城邦的女性公民,她們享有一定的城邦權力,依附城邦存在,地位高低由依附者決定;另一方面是作為戰(zhàn)利品的物化形象——奴隸、妾附屬于希臘城。第二層倫理身份在當時的倫理情境下,是第一層倫理身份導致的,但其根本原因在于男性絕對權力的構建,使得兩種倫理身份可以并存,又呈現(xiàn)矛盾沖突的態(tài)勢。
二、倫理困境的深入
——主觀倫理選擇與客觀倫理選擇的矛盾
在城邦制度的倫理情境下,第一層倫理身份為女性自主認可、長期存在,這一層倫理身份也要求女性完全認可當時的城邦制度和自己存在的城邦,并主動維護城邦的存亡、仇視外來者,主動維護自身倫理身份。
以特洛亞城邦的存在為前提的倫理情境中,特洛亞城邦的女性在出嫁前與自己的母親共同依附于自己的父親,在生長環(huán)境中認可自己作為特洛亞城邦女性的身份,并在成長過程中牢固樹立起對特洛亞城邦的認可,對自己父親的認可。在出嫁后,特洛亞城邦的婦女通過感情、制度和長期文化信仰,建立起對丈夫的認同。在女性群體中,特洛亞婦女通過她們附庸的角色建立起地位高低的不同,并對身處于高位的女性建立認同。
以特洛亞城邦的覆滅作為倫理情境,特洛亞城邦男性被屠殺、男性代表的城邦滅亡,特洛亞婦女第一層倫理身份中的附庸物不再存在,它迫使婦女們?yōu)榱苏业叫碌母接刮锖蛡惱砩矸莶坏貌怀姓J一種難以接受的倫理地位。在城邦制之下,則是不得不選擇另一個新的城邦來作為附庸對象。盡管她們在主觀上不認可,但作為敵對城邦的希臘的確是唯一的選擇,而希臘城邦的強制附庸實際上推動了這種進程。第二層倫理身份相對于第一層倫理身份附庸性更強,女性幾乎失去了所有自主權。
在主觀上,受當時城邦至上、對城邦文化認同的理念和維護第一層倫理身份的主觀傾向,特洛亞女性排斥第二層倫理身份,仍有維持原有倫理身份的強烈渴望。
在城邦制的倫理情境之下,女性倫理身份的綁定以血緣和婚姻為基礎,婦女們對于自己原始的倫理身份具有認同感,決定了她們在主觀上更加傾向于選擇自己原有的倫理身份,即延續(xù)自己對于特洛亞城邦的附屬,維持自己既定的地位和倫理環(huán)境。城邦制之下的城邦認同感、歸屬感是城邦制時代的主流價值觀,城邦至上論對特洛亞婦女產生重要影響,因此對于特洛亞城邦她們懷有強烈的主觀情緒,也對于毀滅特洛亞城邦的希臘人懷有深刻的痛恨。正因此,她們對于第二種倫理身份具有本能的排斥。同時,她們對于附庸的男性帶有人類所共通的親情、愛情等情感,而希臘城邦的男性則是她們的仇人,在主觀情感上,附庸于仇人令人難以接受。
在客觀上,特洛亞女性地位降級或被迫改嫁,依附者被屠殺,生存自主權幾乎喪失,原本的倫理身份已經不復存在。
初始倫理身份地位與后續(xù)強行介入倫理身份的對比,作為特洛亞城邦的女性公民的特洛亞婦女盡管已經呈現(xiàn)出物化的特征,但作為女性公民,她們仍然享有一定的公民權,且以赫卡柏為首的貴族階級在女性內部占有優(yōu)越地位,這是后續(xù)身份難以給予她們的。面對第一種和第二種倫理身份的選擇,客觀環(huán)境決定了她們的第二重倫理身份,而主觀上對于第二重倫理身份卻強烈排斥、堅定維護第一種倫理身份,這造成了倫理身份的沖突,進而造成了倫理困境。
面對這一倫理困境,特洛亞女性有兩種選擇——抗爭與順從。抗爭者的抗爭是付出生命的代價、犧牲客觀上的物質實體換取精神上的主動選擇;而順從者則是放棄精神上的自由,以取得客觀上生命的暫存,但順從者在精神上仍然選擇第一層倫理身份而陷入更加深層的主客觀矛盾與掙扎。
主觀上的倫理選擇傾向與客觀上的被動倫理選擇構成了倫理困境的正反兩面,同時也給特洛亞婦女構成了一個走不出的死結,在這種倫理困境下,戲劇的悲劇化意義被擴展到最大。
而面對生與死的問題,女性到底如何選擇自己的命運、做出怎樣的倫理選擇,作者在文中也給出了一定的答案。赫卡柏和安德洛瑪克兩個人爭論,安德洛瑪克認為即便波呂克塞娜被殺死,也比自己的命運好得多,但赫卡柏認為活著仍舊有希望,二人代表了不同的選擇和態(tài)度。但赫卡柏最后的哀歌中對自己死去的丈夫表達了死去也可以不必感受自己這些痛苦的態(tài)度,她在此刻與自己的兒媳婦安德洛瑪克的觀念趨于一致,選擇肉體上的死亡換取精神上的解脫。而赫卡柏作為特洛亞婦女的代表,她的轉變代表了特洛亞婦女的整體態(tài)度和倫理選擇。
三、倫理困境的深度構成原因
——男性絕對權力構建中的女性與其邊緣化
本文的倫理背景是城邦時代,男性占據主導地位,擁有完全公民權,男性代表城邦與城邦至上論作為主流觀點在當時的社會中留存。而女性在當時的社會中地位較低,擁有不完全的公民權。奴隸在當時的社會中幾乎沒有任何的社會地位,完全是城邦的附屬品。希臘城邦處于伯里克利時代,對外擴張戰(zhàn)爭頻繁。作為戰(zhàn)勝國的希臘往往將戰(zhàn)敗國的男性屠殺、城墻摧毀,女性則作為奴隸帶回城邦內。
在《特洛亞婦女》中,這一社會倫理背景也有極為明確的體現(xiàn)。一方面,在特洛伊城邦被攻破后,男性公民都被屠殺殆盡,而為了斬草除根連年幼的赫克托爾之子都沒有被放過,女性公民則基本沒有被屠殺。這種身份待遇的差別已經體現(xiàn)出男女在城邦中地位的不同。
男性作為城邦的主宰,也被視為身份和力量的象征,對于征服者有威脅。赫卡柏也在與安德洛瑪克的對話中提到,赫克托爾的兒子是城邦的希望,希望安德洛瑪克好好撫養(yǎng)赫克托爾的兒子。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都將男性視為城邦的未來與希望,女性不能承擔這樣的使命與義務。由此可見,女性對于城邦的地位顯然沒有男性重要,女性很難憑借自身的力量建立起新的城邦,也很難擁有男性在城邦中的威望、認可度,男性對于城邦的掌控也明顯強于女性。
另一方面,作為參照物的希臘城邦一方,始終是以男性為主宰,女性甚至都不曾參與出征,希臘城邦中的女性在重大的戰(zhàn)爭與社會變遷中沒有話語權和決定權,這反映出早期原始男權社會男性絕對權力已經基本確立,而女性已經基本淪為附庸。
女性這種附庸地位已經演化成一種公共的文化心理與文化認同。作為赫克托爾妻子的安德洛瑪克,赫卡柏勸說她接受命運去做妾的理由是能夠好好撫養(yǎng)大赫克托爾的兒子,以此來復興城邦,體現(xiàn)了母親作為兒子、丈夫附庸乃至于城邦附庸的特征;特洛亞婦女們對于自己丈夫的懷念與特洛亞婦女地位的呈現(xiàn),體現(xiàn)出的是女性地位完全依靠男性的特點,而女性在主觀上也已接受了這一身份。女性們對于赫卡柏地位的認同,也是由于其王后的身份,其附庸的男性地位較高。
早期男權社會的建立過程中,男性通過城邦規(guī)則的制定和絕對力量將女性置于低等地位,通過婚姻、血緣將女性綁定在城邦制中,達成女性地位對于男性的捆綁,從此建立起男性的絕對地位。而在這個過程中,女性被逐漸排除出主流社會,只能獲得部分公民權,并且逐漸邊緣化。從初始的地位低下到話語權、選擇權的喪失,到最終完全淪為城邦附庸。
戲劇中導致女性倫理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女性的附庸地位。正是由于這一地位,女性在城邦被滅后不得不面臨“依附誰”這樣一種倫理選擇,而非獨立自主地選擇自主命運,或在男性被屠殺后接替男性成為城邦的代表,繼續(xù)維系城邦的存在。
女性的附庸地位決定了她對于首先附庸的城邦具有深厚的主客觀連接,在這一城邦覆滅后仍然對于這一城邦保持深厚的感情,在主觀上選擇第一層倫理身份,抗拒第二層倫理身份。正因為女性依附于城邦、但在城邦中又不具有重要地位,也不具備男性復興城邦的權力、代表城邦的獨特身份地位,因此希臘城邦對于被滅亡城邦的女性采取了降檔納為附庸而非和男性一樣趕盡殺絕這一手段,并賦予了婦女們第二層倫理身份,在客觀上造成了女性雙重倫理身份的困境。而這一制度中對女性的要求和女性的特殊地位也女性對于第一重倫理身份的情感依附和對于第二重倫理身份的排斥,并在倫理困境中做出更加順應精神自由而舍棄肉體自由的倫理選擇。
而作為城邦代表的男性往往不會面臨這樣的困境,他們的命運是與城邦共存亡,或者僥幸存活,踏上復興城邦的路途。作為社會附庸的女性在歷史變遷中難以尋找自己真正的歸屬,而承載起了物的特性,擔負起國家、城邦的命運,這正是特洛亞婦女倫理困境產生的根本原因。
四、倫理困境的倫理教化意義
——歐里庇得斯時代的《特洛亞婦女》
歐里庇得斯的《特洛亞婦女》是女性視角下的城邦制度,也是戰(zhàn)敗者視角下的城邦制度,這從根本上決定了其重要的倫理教化意義。
一方面,作者的視角聚焦于戰(zhàn)場上的失敗者而非勝利者,關注失敗者的命運——失敗城邦男性被屠殺,女性淪為奴隸,同時作者用了一定的筆墨直觀或經由他人之口講述戰(zhàn)爭的慘狀,這是對戰(zhàn)爭的控訴和對城邦壓迫者的控訴。
在此基礎上,作者體現(xiàn)出對人的生存狀況深切的人文關懷和對戰(zhàn)爭導致的悲慘結果的反思,表現(xiàn)出作者反對戰(zhàn)爭、希望和平的一面和對戰(zhàn)敗城邦的深切關懷。
在文本寫作的前一年,也就是公元前416年,雅典人攻占了在雅典和斯巴達之中保持中立的墨洛斯島,并殺光島上的男性,把婦女擄走作為奴隸,歐里庇德斯寫作這一劇本,很大程度上是折射墨洛斯島的境遇,表達作者對墨洛斯人的深切同情和對雅典人殘暴行徑的譴責,并反思戰(zhàn)爭給人帶來的不幸后果,希望警醒城邦的統(tǒng)治者。
另一方面,《特洛亞婦女》選擇了一個特殊的聚焦群體——女性,這在當時是極為少見的,而女性群像的描繪在文本的展開中起到了極大的作用。劇中女性的悲慘命運矛頭直指當時的社會對于女性的壓迫,迫使受眾反思城邦制度之下女性的生存狀況,這對于反思女性地位和塑造性別平等意識具有重要作用。
歐里庇得斯的戲劇與當時其他戲劇的顯著區(qū)別之處在于對女性的描寫,無論是描寫女性個體形象的《美狄亞》還是女性群體形象的《特洛亞婦女》,都將目光轉向了社會中并不占主流的群體。
在歐里庇得斯所處的時代,是伯里克利改革的后期,是城邦制度完善乃至發(fā)展到頂峰的時期,也是男性權力逐漸構建的時期。在此后的幾千年時間中,男性的絕對權力不斷得到強化,男性地位逐漸得到提升,女性的地位不斷被貶低、話語權不斷被削弱。在這個進程開始的階段,歐里庇得斯就敏銳地察覺到了這種進程,并開始關注這一進程中被削弱的一方。
《特洛亞婦女》是為女性發(fā)聲、關注女性命運的作品,盡管它一方面將女性置于城邦制的背景下,通過女性的附庸地位來展現(xiàn)整個城邦的命運,是將女性物化的一種手段,體現(xiàn)了鮮明的男權特點;但在另一方面,它將女性納入了人們的視野之中,一改過去始終以男性、城邦作為主人公的創(chuàng)作特點,讓女性的命運帶有自己獨有的性別特點和在男性絕對權力建立中的邊緣化特征,從而被人們認識并得以更進一步地關注這樣一個獨特的群體,是在男性絕對權力過程構建早期的微弱的女性主義呼聲,具有深切的人文關懷意味。
在伯里克利時代的城邦戰(zhàn)爭中,發(fā)動戰(zhàn)爭的雙方城邦秉持城邦至上的理念,勝利方的城邦對失敗方的城邦公民進行殘忍地奴役和屠殺,這在當時極為常見。但《特洛亞婦女》聚焦失敗的一方,通過女性的命運折射整個城邦中人的命運,關注失敗者的命運,促使受眾反思人在其中的悲慘命運,體現(xiàn)人性關懷,這在當時是具有明顯的超前意義的。
在《特洛亞婦女》中,婦女作為城邦的附庸,反映的是一整個城邦的命運,同時在《特洛亞婦女》中,也變相交代了城邦中其他人物的下場——成年男性和未成年的男性均被屠殺,城邦被整體毀滅,這在當時是慣用的做法。而《特洛亞婦女》揭示的就是這樣一種悲劇性的毀滅,它讓觀眾看到了城邦覆滅后的悲慘,從而產生憐憫之心。魯迅曾言:“悲劇就是將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一個城邦中有價值的人被毀滅,有價值的城邦被毀滅,這是人類文明的巨大悲劇。也正因此,《特洛亞婦女》才產生了巨大的悲劇意義,直擊觀眾心靈,產生了巨大的倫理教化作用,呼吁當時的民眾與后來者反對城邦戰(zhàn)爭、保護戰(zhàn)敗城邦中的公民,并關注女性命運,維護了社會的和平與安定。
五、結語
歐里庇得斯是奴隸制早期社會中較為少見的關注女性命運的作家,不同于同時期其他以女性為主題的作品,本文的重要特色在于關注了女性群體命運,刻畫了早期女性群像,揭示城邦制之下女性命運的悲劇,矛頭直指城邦社會與城邦戰(zhàn)爭,展現(xiàn)出深刻的人文關懷與人性反思。
從文學倫理學視角來看,本文的戲劇沖突聚焦于女性二重倫理身份的建構,并在倫理選擇過程中不斷深化沖突、深入闡釋倫理困境,并進一步將主要思考方向引向當時的倫理背景,引發(fā)對于女性命運與城邦制的反思,因而具有深刻的倫理教化意義。
參考文獻:
[1]聶珍釗.文學倫理學批評導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2]歐里庇得斯.埃涅阿斯紀特洛亞婦女[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3]文藝.歐里庇得斯悲劇問題意識研究——以《特洛亞婦女》為例[J].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2015,(8).
[4]申丹.西方敘事學:經典與后經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5]陳瑞華.《特洛亞婦女》中的雅典帝國[J].牡丹江大學學報,201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