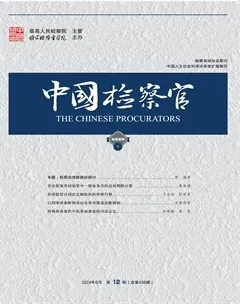相約自殺中的幫助、欺騙行為如何定性
關鍵詞:相約自殺 欺騙自殺 故意殺人罪 間接正犯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何某為尋求觀看他人上吊窒息狀態而產生的畸形快感,在網上找到有自殺意愿,但沒有勇氣選擇自殺的被害人孫某(女,歿年21歲)。何某隱瞞其真實意圖,謊稱自己也要自殺,引導、欺騙孫某確定與其一起采用上吊的方式自殺。兩人在網上確定自殺的具體時間、地點及工具等,由何某預訂客房、購買上吊用的凳子、絲巾等物品,繩子各自攜帶。2022年7月9日晚,何某和孫某在寧波市某區某賓館一房間內,采用將繩子綁在客房樓梯上,再將絲巾綁在繩子上的方式上吊自殺。何某幫助孫某綁了一個死結,而自己在上吊后綁了一個活結,后自行解脫,觀看孫某上吊臨死時的狀態,滿足自己畸形快感。孫某因頸部受力致機械性窒息死亡。案發后,被告人何某打電話報警,并在現場等候處理,但報警時僅稱其與他人相約自殺,后被查實系引導、欺騙孫某自殺。
二、分歧意見
孫某在何某幫助、誘導下自殺,何某是否承擔刑事責任是本案的爭議焦點。首先要厘清自殺是否構成犯罪。自殺是指“在被害人事前知道自己行為結果的前提下,直接或間接地由其自己實施的作為或不作為所引起的死亡”。自殺是自己對自己所為的殺害行為,系自己加害自己、自己實施放棄法益的自暴自棄行為。自殺是當事人自我處分生命的行為,自殺分為違法說、無罪說和法外空間說。近年來,法外空間說成為有力觀點,即“自殺不是法律領域的負價值行為,而僅僅是屬于法律上不考慮違法、有責判斷的法律空白領域之內的放任行為”。本文不糾結學說爭論,筆者認為,目前至少有一點可以達成共識,即自殺行為雖然道德上不提倡,但是刑法評價上不構成犯罪。其次,要厘清自殺相關聯的行為,尤其是相約自殺中幫助、欺騙自殺的行為,在刑法上如何處理。我國刑法對故意殺人罪規定的比較簡單。《刑法》第232條規定,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沒有單獨規定幫助自殺罪、欺騙自殺罪。“利用、控制、操縱被害人使其實施自殺行為,利用者本人就可能是間接正犯,犯罪結果就要歸責于利用者。”幫助、欺騙自殺是否屬于故意殺人罪的射程范圍,需要結合案情,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本案中,存在二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何某不構成犯罪。基于被害人自我答責原則,生命處分權屬于自己決定權的范疇,是人的權利和自由,本案中孫某上吊自殺是基于本人意思所實施的自殺行為,屬于完全自由地處置自己生命的行為。盡管何某存在幫助、欺騙孫某了結自己生命的行為,這屬于取得被害人同意之后對其法益造成一定損害的行為,并不是刑法上的殺人行為。故何某不構成犯罪,孫某對死亡結果自行承擔責任。
第二種意見認為,何某構成故意殺人罪。本案中被害人對死亡的動機存在認識錯誤,沒有何某的偽裝和引導,孫某根本沒有勇氣選擇自殺。在自殺過程中,何某上吊后自行解脫,觀看孫某上吊臨死時狀態,沒有及時救助孫某,導致死亡結果發生。何某是故意殺人罪間接正犯,同時也構成不作為殺人,應當以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此外,何某盡管報警并在現場等待,但未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不成立自首,不能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三、評析意見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主要理由如下:
(一)被害人自殺的承諾必須沒有瑕疵,受欺騙的承諾無效
被害人的有效承諾,必須是被害人意思處于自由的狀態,對承諾的事項能夠獨立作出決定,對相關的行為及后果能夠清楚判斷。自殺者的承諾不能有瑕疵,否則不能成立自殺。司法實踐中,有學者認為,緣于生命法益的高度人身專屬性、不可流轉性的因素考量,基于行為人自主程度和承諾程度的不同,自殺分為自主性自殺和非自主性自殺兩種樣態。筆者認同此種劃分。自主性自殺是個人自我決定權的完整體現,不存在法益損害的空間,自然不應當禁止。比如,被害人主動將自己砍成致命傷、親自服下毒藥、自己跳樓或者投湖等場合中,均是以自己的行為造成了死亡的后果,應當自我擔責。非自主性自殺并非個人真實意思表示,而是在自殺過程中介入了自殺關聯行為,比如欺騙、教唆、幫助他人自殺,類似大量非自主意愿充斥自殺過程,并非個人真實意愿表現,此時認定自殺關聯行為無罪,不合法也難以為人民群眾所接受。我國《刑法》和司法解釋對介入自殺的行為有所規定,在受邪教組織幫助、欺騙自殺的情況下,個人盡管對于結束生命有所認知,但對死亡意義有著明顯錯誤認識,屬于被害人的無效承諾,應當認定邪教的組織人員實施故意殺人行為,以間接正犯(把被害人當成殺害他自己的工具)定罪處理。盡管在其他幫助、欺騙自殺的案件中,行為人對被害人的控制不如邪教組織那么強,但不可否認的是,若他人故意介入會現實地或高度危險地影響自殺者內在意思形成的自由,導致自殺并非完全是自主、自治的結果,應當考慮追究幫助自殺、欺騙自殺行為人的責任。
幫助、欺騙自殺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應當受刑法評價。實施幫助、欺騙的行為人不是在心理影響上增強了他人的自殺意圖,就是于外在物理意義上助力介入,自殺者對于自殺行為完整流程的自主支配受到了干擾,國家法律應當介入并干預這些行為。在本案中,通過孫某就醫記錄顯示,孫某近兩年曾有數十次到醫院就診,其患有抑郁癥,并長期服用藥物治療,性格、情緒波動比較大。何某的供述與辯解可知,“何某先是在跟孫某聊天的過程中偽裝成有同樣自殺想法的人,騙取她的信任,然后慢慢把她誘導到現實中見面,然后配合她的想法讓她心甘情愿去上吊死亡。”從微信聊天記錄等證據可知,孫某原本沒有勇氣自殺,也不愿意自殺。何某為滿足變態的性癖好(觀看他人自殺得到快感),在網絡上撒網式搜索目標,與孫某線上接觸后,非但沒有勸阻開導,反而采取引誘、幫助、欺騙等手段,為孫某提供上吊用的板凳、絲巾等自殺工具并租賃自殺場地,同時在精神上鼓勵孫某自殺,導致孫某產生了何某欲與其一同赴死的錯誤認識,從而做出了在何某幫助下上吊自殺的行為。孫某的承諾系無效承諾,孫某被何某當成了殺害自己的工具,應當以間接正犯追究何某刑事法律責任。因此,第一種意見并不合理。
(二)幫助、欺騙自殺構成故意殺人罪要結合主客觀事實綜合認定
自殺除了主觀方面要求被害人純粹自主自愿,認識并意欲死亡結果發生,客觀方面上還必須完整支配著直接導致死亡的行為,在不可逆轉地造成死亡結果的最后關鍵時刻自己控制著事物的發展。那么,認定幫助、欺騙自殺構成故意殺人罪,主觀方面要考慮行為人影響被害人的程度(前文已述),客觀方面還要考慮行為人是否直接控制著被害人自殺的進程。若行為人控制被害人自殺進程,則應當追究行為人責任;若被害人在通往死亡最后一刻,仍然掌握決定權,卻依然選擇走向死亡,則成立自殺,行為人無需承擔責任。德國有一個案例,行為人與被害人共同自殺,行為人將一根橡皮管連接排氣管并通過車窗接入車廂,然后行為人與被害人共同坐在車里(車門可自由打開),行為人啟動汽車并持續怠速,最終行為人因吸入二氧化碳昏迷不醒,被害人因吸入過量二氧化碳死亡。在這個案件中,被害人完全可以打開車門避免死亡結果的發生,但依然選擇坐在車里吸入二氧化碳,自己跨向了通往死亡的關鍵一步,應當認定為自殺,而行為人不應當承擔責任。這個案例給我們的啟示是,構成自殺的必要條件是自殺者在最后關頭掌握、支配著事態的發展。
本案中,何某控制了孫某的死亡進程,并最終以不作為的方式導致孫某死亡結果的發生。何某為孫某綁了一個死結并幫助孫某上吊,而何某自己綁了一個活結,隨時可以掙脫危險。何某實際上控制著孫某的死亡走向,而非孫某掌握著死亡走向,與上述德國案例存在區別。此外,何某、孫某在相對封閉空間中一同赴死的行為,形成了危險共同體關系。危險共同體義務,是指雖然不屬于法律明文規定,但是當事人之間基于一定事實形成了社會上通常認為的對危險應當予以共同承擔、相互照顧的關系。處于危險共同體關系的成員,在發現其他成員陷入危險后,都有救助、排除危險義務。共同實施合法行為,比如一起爬山,發生雪崩,危險共同體的成員之間有救助義務。共同實施違法行為(共同吸毒)形成的危險共同體關系,當成員陷入危險后,也一樣有救助義務。如前文所述,共同自殺雖不被提倡,但至少不是刑法意義上的違法行為,雙方共同自殺,當何某自行解脫、終止自殺行為后,就產生了救助孫某義務。但是何某的供述與辯解,“我希望能找到女孩,因為在國外色情網站上就有這種上吊自殺的情節,我就希望能按照這樣的情節做來滿足自己的快感,女孩在上吊時掙扎,我在旁邊看著,這樣我心理上能得到最大的滿足”(案發前的想法),“看到女孩子上吊死亡的過程我很興奮,內心再一次得到滿足根本沒有想過要救她,看她死亡的過程也是在我的計劃之內”(案發時的心理活動)。由此看出,何某不僅不幫助孫某脫離危險,反而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選擇袖手旁觀,觀看孫某上吊臨死時的狀態,導致孫某最終死亡。何某既是故意殺人罪的間接正犯,又支配著被害人死亡進程,同時違反了危險共同體關系中的救助義務,以不作為方式產生了被害人死亡后果,應當承擔刑事責任。盡管事后何某撥打電話報警,但隱瞞了幫助、欺騙自殺的事實,不能認定自首,無法從輕、減輕處罰。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人的生命具有極端重要性,一般情況下個人不會放棄自己的生命,對于自殺的認定要嚴格謹慎。自殺者必須清醒認識并且意欲死亡結果發生,意思表示不能有瑕疵,另外自殺者還必須事實上支配死亡進程。只有滿足這兩點,才構成自殺,幫助、欺騙自殺者才可以免責。而當幫助、欺騙自殺者的行為造成了自殺者產生嚴重的認識錯誤,且客觀上又主導自殺者的死亡進程,則應當認定幫助、欺騙自殺者為故意殺人罪的間接正犯,結合案情認定其以作為或者不作為方式產生被害人死亡的后果。
最終,法院判決何某成立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12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賠償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孫某母親經濟損失人民幣20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