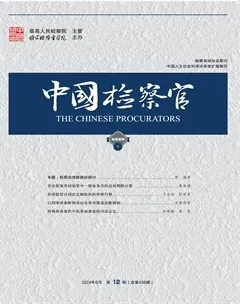非法集資共同犯罪中一般業(yè)務(wù)員的追訴期限計(jì)算
關(guān)鍵詞:共同犯罪 追訴期限 分別評(píng)價(jià) 連帶評(píng)價(jià)
根據(jù)《刑事訴訟法》第16條,犯罪是否超過(guò)追訴期限,關(guān)乎能否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zé)任,是刑事司法的基礎(chǔ)性問(wèn)題。在追訴期限的適用中,追訴期限的起算點(diǎn)、追訴期限的延長(zhǎng)等問(wèn)題,理論與實(shí)務(wù)一直爭(zhēng)議不斷,上述問(wèn)題在共同犯罪中的分歧更大。本文以實(shí)務(wù)中常見(jiàn)的非法集資共同犯罪中一般業(yè)務(wù)員的追訴期限計(jì)算為例,對(duì)上述爭(zhēng)議問(wèn)題進(jìn)行理論探討和實(shí)踐釋疑。
一、非法集資共同犯罪中一般業(yè)務(wù)員追訴期限認(rèn)定的爭(zhēng)議
[基本案情]在陳某等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中,陳某實(shí)際控制的中某公司自2013年2月至2019年4月間以投資股權(quán)融資、眾籌等項(xiàng)目為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金額1億余元。中某公司理財(cái)經(jīng)理張某于2014年3月入職,2018年1月離職,在職期間參與中某公司非法吸收資金數(shù)額200萬(wàn)元。2019年4月,公安機(jī)關(guān)對(duì)中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立案?jìng)刹椋⒆カ@陳某等嫌疑人,但未對(duì)張某采取強(qiáng)制措施。2018年1月,張某離職后回老家工作。2023年2月,公安機(jī)關(guān)將張某抓捕到案。對(duì)于中某公司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犯罪事實(shí),檢察機(jī)關(guān)和法院均認(rèn)為,由于中某公司設(shè)立后,以實(shí)施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為主要活動(dòng),根據(jù)最高法《關(guān)于審理單位犯罪具體應(yīng)用法律有關(guān)問(wèn)題的解釋》第2條規(guī)定,不以單位犯罪論處,陳某等人成立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共同犯罪。檢察機(jī)關(guān)綜合張某的犯罪數(shù)額、退贓退賠、從犯、認(rèn)罪認(rèn)罰等情節(jié),對(duì)張某作出相對(duì)不起訴。
根據(jù)《刑法》第87條、第176條和最高法《關(guān)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yīng)用法律若干問(wèn)題的解釋》的規(guī)定,張某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犯罪數(shù)額200萬(wàn)元,對(duì)應(yīng)的法定刑檔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追訴期限為5年。對(duì)于張某是否已經(jīng)超過(guò)追訴期限,存在兩種觀點(diǎn)。一種觀點(diǎn)認(rèn)為,張某2018年1月從中某公司離職時(shí),其犯罪事實(shí)已經(jīng)終了,應(yīng)當(dāng)自2018年1月起開(kāi)始計(jì)算追訴期限,至2023年1月經(jīng)過(guò)5年,且張某在此期間并無(wú)逃避偵查行為,不能適用追訴期限延長(zhǎng)的規(guī)定,因此,2023年2月公安機(jī)關(guān)將張某抓捕到案時(shí),張某的犯罪已經(jīng)超過(guò)追訴期限。另一種觀點(diǎn)認(rèn)為,張某的犯罪未超過(guò)追訴期限。對(duì)此有兩種論證思路:一種思路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從涉案中某公司犯罪事實(shí)終了之日即2019年4月起開(kāi)始計(jì)算張某的追訴期限,因此,2023年2月公安機(jī)關(guān)將張某抓捕到案時(shí),尚未超過(guò)5年的追訴期限;另一種思路認(rèn)為,即使從張某離開(kāi)中某公司的2018年1月開(kāi)始計(jì)算其追訴期限,2019年4月,公安機(jī)關(guān)對(duì)中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立案后,張某的追訴期限延長(zhǎng),2023年2月公安機(jī)關(guān)將張某抓捕到案時(shí),尚未超過(guò)追訴期限。
以上不同觀點(diǎn),集中體現(xiàn)了共同犯罪中共犯追訴期限的計(jì)算問(wèn)題。為準(zhǔn)確認(rèn)定張某的追訴期限問(wèn)題,需要明確三個(gè)問(wèn)題:共同犯罪中共犯追訴期限應(yīng)當(dāng)連帶評(píng)價(jià)還是分別評(píng)價(jià)、共同犯罪中共犯的追訴期限起算點(diǎn)認(rèn)定和共同犯罪中共犯追訴期限的延長(zhǎng)問(wèn)題。
二、共犯追訴期限應(yīng)當(dāng)分別評(píng)價(jià)
(一)共犯追訴期限應(yīng)當(dāng)連帶評(píng)價(jià)還是分別評(píng)價(jià)的不同觀點(diǎn)
對(duì)于共同犯罪中共犯追訴期限應(yīng)當(dāng)連帶評(píng)價(jià)還是分別評(píng)價(jià)的問(wèn)題,一直存在爭(zhēng)議。一種觀點(diǎn)認(rèn)為,從共同犯罪追訴的一體性以及保證訴訟程序完整性的要求出發(fā),對(duì)于共同犯罪,確定從犯追訴期限所適用的法律條款與確定主犯追訴期限所適用的法律條款應(yīng)當(dāng)同一,不論從犯的參與程度,即使從犯有從輕、減輕情節(jié),其追訴期限與主犯的追訴期限應(yīng)當(dāng)一致。另一種觀點(diǎn)則認(rèn)為,共同犯罪并非適用統(tǒng)一的追訴期限標(biāo)準(zhǔn),而是應(yīng)當(dāng)按照各共犯人應(yīng)當(dāng)適用的法定刑幅度,分別計(jì)算追訴期限。
筆者認(rèn)為,追訴期限是依照法律規(guī)定對(duì)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責(zé)任的期限,是“對(duì)人”的單獨(dú)評(píng)價(jià),共同犯罪的場(chǎng)合,對(duì)共犯人追訴期限的判斷,應(yīng)當(dāng)針對(duì)各共犯具體情況進(jìn)行分別評(píng)價(jià),而不能按照“部分實(shí)行全部責(zé)任”連帶評(píng)價(jià)。因此,共同犯罪中各共犯的追訴期限應(yīng)當(dāng)根據(jù)各共犯所犯罪行對(duì)應(yīng)的法定最高刑分別確定。
(二)共犯追訴期限分別評(píng)價(jià)的主要理由
一般來(lái)說(shuō),由于共同犯罪采取部分實(shí)行全部責(zé)任原則,各共犯所適用的法定量刑幅度是一致的,即法定最高刑相同,適用的追訴期限也應(yīng)當(dāng)是相同的。但也存在共犯法定量刑幅度不同的情形,一是成立共同犯罪但罪名不同的場(chǎng)合,二是成立共同犯罪但適用不同法定刑檔的場(chǎng)合。在共犯法定量刑幅度不同時(shí),應(yīng)當(dāng)根據(jù)各自的法定最高刑分別確定共犯的追訴期限。因此,可能出現(xiàn)部分共犯超過(guò)追訴期限、部分共犯沒(méi)有超過(guò)追訴期限的情形。當(dāng)然,應(yīng)當(dāng)根據(jù)各共犯的法定刑而非宣告刑確定各共犯的追訴期限,例如,共犯可能具有從犯、自首等減輕處罰情節(jié)的,不影響其追訴期限的認(rèn)定。
在非法集資共同犯罪案件中,非法集資整體事實(shí)的犯罪數(shù)額往往特別巨大,雖然普通業(yè)務(wù)員與涉案公司的實(shí)際控制人、高管等人員成立共同犯罪,但普通業(yè)務(wù)員作為從事吸收資金行為的最低層級(jí)人員,僅對(duì)自己實(shí)際參與吸收的全部金額承擔(dān)刑事責(zé)任,而不對(duì)整體非法集資犯罪事實(shí)的全額負(fù)責(zé)。因此,作為共犯的普通業(yè)務(wù)員認(rèn)定的犯罪數(shù)額與主犯不同,適用的法定量刑幅度不同,應(yīng)當(dāng)分別確定各共犯的追訴期限。這一分別評(píng)價(jià)的思路,也符合非法集資案件中分層處理的司法邏輯。本案中,陳某等人可能適用“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而張某的行為屬于“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法定刑檔,應(yīng)當(dāng)按照張某的犯罪數(shù)額所處法定刑檔的法定最高刑確定對(duì)張某涉案犯罪行為的追訴期限,其追訴期限為5年。
三、共犯追訴期限的起算點(diǎn)
根據(jù)《刑法》第89條規(guī)定,追訴期限從犯罪之日起計(jì)算,犯罪行為有連續(xù)或者繼續(xù)狀態(tài)的,從犯罪行為終了之日起計(jì)算。共同犯罪不是各共犯參與行為的“簡(jiǎn)單相加”,而是形成共同故意下的共同行為,因此,共犯的共同犯罪行為終了之日一般應(yīng)當(dāng)是同一的。當(dāng)然,如果部分共犯成立犯罪中止,則從其脫離共同犯罪之日起計(jì)算其犯罪行為終了之日。
(一)非法集資共犯追訴期限起算點(diǎn)爭(zhēng)議
在非法集資案件中,如本案中的張某,在整體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事實(shí)終了之日前離職的,究竟是以其離職時(shí)間還是以整體非法集資犯罪事實(shí)結(jié)束之日起計(jì)算張某的追訴期限,存在一定爭(zhēng)議。
這一爭(zhēng)議實(shí)際源于非法集資案件中對(duì)一般業(yè)務(wù)員犯罪數(shù)額的認(rèn)定規(guī)則。按照共同犯罪的部分實(shí)行全部責(zé)任原則,共犯應(yīng)當(dāng)對(duì)其參與的整體犯罪事實(shí)、犯罪數(shù)額承擔(dān)刑事責(zé)任。但非法集資案件中,一般業(yè)務(wù)員僅對(duì)其任職期間實(shí)際參與吸收的全部金額而非全案犯罪數(shù)額承擔(dān)刑事責(zé)任。從承繼共犯的角度看,一般業(yè)務(wù)員自其參與非法集資犯罪事實(shí)之日參與非法集資共同犯罪較容易解釋,但為何其無(wú)需對(duì)離職后的犯罪數(shù)額承擔(dān)責(zé)任,以及為何對(duì)其任職期間未直接參與的其他共犯非法集資犯罪事實(shí)不承擔(dān)責(zé)任?這其實(shí)是基于一般業(yè)務(wù)員在非法集資共同犯罪中的特殊認(rèn)定思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共同犯罪行為,是不斷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連續(xù)犯罪行為,一般業(yè)務(wù)員作為底層直接參與非法吸收資金的人員,僅對(duì)其直接參與吸收的金額承擔(dān)共同犯罪的責(zé)任。因此,其離職行為切斷了其犯罪行為與整體非法集資犯罪事實(shí)的因果關(guān)系,具有共同犯罪的犯罪中止效果。
(二)區(qū)分不同層級(jí)人員分別認(rèn)定“犯罪行為終了之日”
基于對(duì)各共犯分別確定追訴期限的思路,前述認(rèn)定一般業(yè)務(wù)員刑事責(zé)任的認(rèn)定思路,會(huì)對(duì)一般業(yè)務(wù)員的犯罪事實(shí)終了之日的認(rèn)定產(chǎn)生影響。換言之,認(rèn)定各共犯刑事責(zé)任的邏輯與確定各共犯追訴期限起算點(diǎn)的邏輯應(yīng)當(dāng)統(tǒng)一,即應(yīng)當(dāng)區(qū)分不同層級(jí)人員,分別認(rèn)定犯罪行為終了之日。
對(duì)于主犯,如涉案公司的主要負(fù)責(zé)人員,因?yàn)槠湟话阋獙?duì)整體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犯罪事實(shí)承擔(dān)刑事責(zé)任,即使其提前離職,但不成立犯罪中止的情況下,根據(jù)共同犯罪基本原理,應(yīng)當(dāng)以共同犯罪終了之日即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整體犯罪事實(shí)結(jié)束之日起算其追訴期限。對(duì)于一般業(yè)務(wù)員,因?yàn)樽肪科湫淌仑?zé)任時(shí),是以其任職期間實(shí)際參與吸收資金的共同犯罪事實(shí)部分為基礎(chǔ)的,因此,應(yīng)當(dāng)以其離職之日作為其犯罪行為終了之日,起算其追訴期限。本案中,應(yīng)當(dāng)以2018年1月張某離職之日起計(jì)算其追訴期限。
四、共犯追訴期限的延長(zhǎng)問(wèn)題
根據(jù)《刑法》第88條第1款規(guī)定,人民檢察院、公安機(jī)關(guān)、國(guó)家安全機(jī)關(guān)立案?jìng)刹榛蛘咴谌嗣穹ㄔ菏芾戆讣院螅颖軅刹榛驅(qū)徟械模皇茏吩V期限的限制。共同犯罪中,共犯是否符合追訴期限延長(zhǎng)條件,一是要根據(jù)各共犯的具體情形分別評(píng)價(jià),而不能以主犯連帶評(píng)價(jià)。二是需要對(duì)“已立案或受理案件”和“逃避偵查或者審判”進(jìn)行準(zhǔn)確解讀。
(一)根據(jù)共犯具體情況分別判斷追訴期限是否延長(zhǎng)
共同犯罪中,不同共犯追訴期限的延長(zhǎng)具有相對(duì)獨(dú)立性,各共犯是否符合追訴期限延長(zhǎng)條件,應(yīng)當(dāng)根據(jù)具體情形個(gè)別判斷。關(guān)于是否受追訴期限的限制,無(wú)論是1979年《刑法》第77條規(guī)定的“采取強(qiáng)制措施以后”,還是1997年《刑法》第88條第1款規(guī)定的“立案?jìng)刹榛蛘呷嗣穹ㄔ菏芾戆讣院蟆保夹枰袛喾缸锓肿邮欠瘛疤颖軅刹榛蛘邔徟小保@顯然是對(duì)人的具體評(píng)價(jià)。因此,共同犯罪中,共犯追訴期限是否延長(zhǎng),應(yīng)當(dāng)根據(jù)共犯具體情況分別判斷。例如,在刑事審判參考第1200號(hào)袁某祥、王某恩故意殺人案中,袁某祥、王某恩系共同犯罪,二人作案后,王某恩在被批捕的情況下一直負(fù)案潛逃,袁某祥未逃避偵查,法院認(rèn)為,王某恩符合追訴期限延長(zhǎng)條件,其犯罪不受追訴期限限制,但共犯袁某祥仍然要受追訴期限的限制。
(二)實(shí)質(zhì)判斷是否延長(zhǎng)共犯的追訴期限
共同犯罪中,無(wú)論是“對(duì)事立案”還是對(duì)“對(duì)人(單位)立案”,都需要考慮共犯是否“逃避偵查或者審判”,進(jìn)而實(shí)質(zhì)判斷是否延長(zhǎng)共犯的追訴期限。
第一,在追訴期限制度中理解“立案”,不應(yīng)排除“對(duì)事立案”,但應(yīng)實(shí)質(zhì)判斷偵查機(jī)關(guān)立案后是否指向具體犯罪嫌疑人。例如,最高檢2015年發(fā)布的指導(dǎo)性案例——蔡某星、陳某輝等(搶劫)不核準(zhǔn)追訴案中,明確指出由于案發(fā)后公安機(jī)關(guān)在追訴期限內(nèi)僅發(fā)現(xiàn)了李某忠等3人,沒(méi)有發(fā)現(xiàn)犯罪嫌疑人蔡某星、陳某輝,且2人在案發(fā)后沒(méi)有再犯罪,因此2人已超過(guò)追訴期限。該案系典型的“以事立案”,由于司法機(jī)關(guān)在追訴期限內(nèi)沒(méi)有發(fā)現(xiàn)犯罪嫌疑人蔡某星、陳某輝,2人的追訴期限當(dāng)然要受到限制。但如果在“對(duì)事立案”后,偵查機(jī)關(guān)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指向特定犯罪嫌疑人的,則應(yīng)進(jìn)一步判斷特定犯罪嫌疑人是否逃避偵查。
在經(jīng)濟(jì)犯罪尤其是涉眾型經(jīng)濟(jì)犯罪案件中,公安機(jī)關(guān)接到集資參與人報(bào)案時(shí),既可能對(duì)“事”立案,如XX被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也可能對(duì)“人(單位)”立案,如XX公司、XX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立案時(shí),可能出現(xiàn)部分涉案人員已離職,或者當(dāng)時(shí)的證據(jù)無(wú)法證實(shí)部分人員構(gòu)成犯罪,后期公安機(jī)關(guān)又追捕到案等復(fù)雜情形,需要結(jié)合具體情況綜合、實(shí)質(zhì)判斷。本案中,公安機(jī)關(guān)對(duì)中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立案?jìng)刹椋@屬于對(duì)人(單位)立案,也指向了涉案公司的相關(guān)人員,之后分批、分層次打擊涉案人員,符合此類案件的一般偵查實(shí)踐,在公安機(jī)關(guān)沒(méi)有怠于偵查的情況下,應(yīng)當(dāng)認(rèn)為該立案對(duì)于中某公司涉案人員包括張某等,產(chǎn)生了“立案”效果。需要說(shuō)明,對(duì)單位立案后續(xù)認(rèn)定為共同犯罪的,不影響“立案”的認(rèn)定。
第二,認(rèn)定“立案”后,應(yīng)當(dāng)結(jié)合犯罪嫌疑人“是否逃避偵查與審判”綜合判斷,是否應(yīng)當(dāng)延長(zhǎng)追訴期限。關(guān)于“逃避偵查與審判”存在不同觀點(diǎn),主要分歧在于:是僅限于積極、主動(dòng)的逃避行為,還是也包括如未主動(dòng)投案、未如實(shí)供述等消極行為。筆者認(rèn)為,“逃避”應(yīng)限于積極、主動(dòng)的逃避行為,要看犯罪嫌疑人的逃避行為是否干擾了偵查活動(dòng)的順利進(jìn)行,是否影響了國(guó)家偵查權(quán)的有效行使。因?yàn)閺淖吩V期限制度的立法宗旨而言,如果犯罪嫌疑人長(zhǎng)時(shí)間沒(méi)有再犯罪,也沒(méi)有積極、主動(dòng)逃避司法追究,從改善效果來(lái)看,犯罪嫌疑人特殊預(yù)防的必要性大大降低,應(yīng)受追訴期限限制。反之,如果犯罪嫌疑人積極、主動(dòng)逃避司法追究,證明其特殊預(yù)防必要性沒(méi)有降低,應(yīng)當(dāng)延長(zhǎng)其追訴期限,避免其從逃避行為中獲利。如果行為人沒(méi)有逃避偵查或者審判,但有關(guān)機(jī)關(guān)因自身原因長(zhǎng)期不開(kāi)展偵查、起訴、審判工作,導(dǎo)致案件長(zhǎng)期懸而未決,明顯超過(guò)追訴期限的,不應(yīng)將該怠于偵查效果加諸于犯罪嫌疑人,仍應(yīng)受追訴期限的限制。需要注意,目前公民身份信息實(shí)名制較為普遍,公民的銀行賬戶、出行、住宿等均需要實(shí)名信息,如公安機(jī)關(guān)對(duì)該人采取強(qiáng)制措施(如上網(wǎng)追逃)后,該人長(zhǎng)時(shí)間較為異常地未使用任何可追溯行蹤、聯(lián)系的方式,可以推定其具有逃避偵查的行為。
本案中,公安機(jī)關(guān)對(duì)中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立案后,張某追訴期限是否延長(zhǎng),應(yīng)當(dāng)根據(jù)其具體情況個(gè)別判斷,即需要判斷公安機(jī)關(guān)是否發(fā)現(xiàn)張某涉嫌犯罪,以及張某是否有積極、主動(dòng)的逃避偵查行為,進(jìn)而判斷是否受追訴期限的限制,而不能徑行認(rèn)為張某不受追訴期限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