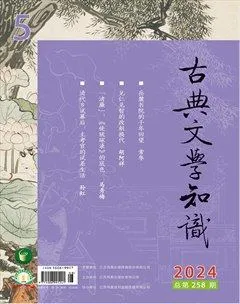《大宗師》2
王景琳 徐匋
莊子說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謨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
今譯
什么樣的人才能稱之為真人?古代的真人,不拒絕少數,不以成功傲人,不使用謀略吸引士子歸于門下。這樣的人,有過失而不懊悔,有成就而不自得。這樣的人,登高不會戰栗恐懼,入水不覺得濕,入火不覺得熱。唯有“知”升華到與“道”為一的人才能有如此的境界。
說莊子
這一段是莊子對真人的總論。文字雖短,信息量卻很大。首先,我們看到莊子心中的真人幾乎囊括了莊子筆下圣人、神人、至人的全部特點。
真人“不逆寡”,是說其胸襟博大,容得下天下各種各樣的人,哪怕是少數派或異見者,也不會去忤逆、去排斥。真人就像《齊物論》中得道的圣人一樣,胸懷“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就是說真人確是有圣人特質的。而所謂“不雄成”,說的是真人有功卻不居功自傲,不以功為功,從不因自己的成就而牛氣哄哄,如同《逍遙游》中的神人一樣。而“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當然不是說真人可以站在懸崖峭壁上“足二分垂在外”,或者縱身躍入水深火熱之中,也毛發無損,刀槍不入。這只是莊子“恣意汪洋”的一種高度夸張寫法,目的在于展示任憑外在世界變化莫測,真人的內心卻絲毫不為所動。真人的這一心理素質,是不是與《齊物論》中所描述的“至人”幾無二致?“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冱而不能寒。”說明真人的心理狀態足以與至人相提并論。
然而,如果真人僅僅是圣人、神人、至人的集合體,那真人就失去了單獨存在的意義。顯然,這不是莊子的本意。那么,在這段話中,對真人的哪些描述是有別于圣人、神人、至人的呢?細究一下,不難發現,真人有著這樣兩個獨具的特點。其一,真人“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是說真人內心十分平靜,不會以人“無定”的“知”去追逐變化著的天地萬物,他們不糾結是非,可以“游心于德之和”,這不正是《德充符》中王駘、伯昏無人等師者所具有的特征?其二,說真人“不謨士”,就是他們不使用任何手段,僅僅憑著自己的人格魅力,天下文人士子便會匯聚其門下,可見真人還真是有老師身份的。
當然,最重要也最能顯示真人身份的還是這一段最后的一句:“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說明真人有“知”,其“知”經過修煉,能升華到與道為一的境地。真人有著師者的身份,這是至人、神人、圣人身上所沒有的。可見真人就是《德充符》中諸如王駘、伯昏無人以及《齊物論》中的南郭子綦一類師者,或者說,他們就是莊子心中的“大宗師”。
那么,真人是否是獨立于至人、神人、圣人之外的另外一類得道之人?據《大宗師》“子祀、子輿、子犁、子來”以下幾段“今之真人”的故事來看,真人具有雙重身份。他們傳道授徒時是“真人”,是大宗師,是老師;平日則如“子祀、子輿、子犁、子來”一般,是生活于現實社會中的至人。這就是為什么《大宗師》中會有“古之真人”與“真人”這兩種說法,而且還說是“先有真人而后有真知”。
有必要補充說明的是,幾乎所有《莊子》注本都將“不謨士”的“士”解做“事”的同音借字,這樣,“不謨士”就成了“不謀事”,不謀略任何事情。這樣的解釋是基于把大宗師看作是“道”而做出的。只有理解了真人才是莊子心目中的大宗師,才可以理解為什么莊子在談論真人時要特別強調“知”的重要。這不全都是因為唯有大宗師才具有這樣的真知?!所以我們把“不謨士”的“士”就當作“士”來解,這樣,不但符合大宗師吸引文人士子投其門下的師者身份,而且也可與《德充符》中的幾位師者還有《大宗師》中的大宗師女偊、許由的身份相呼應了。
莊子說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眾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
今譯
古代的真人,睡覺時不做夢,醒來沒有煩憂之事,飲食不求甘美,呼吸深沉。真人用腳跟呼吸,而普通人用喉嚨呼吸。論辯時被人所屈服的人,話常常噎在喉嚨里說不出來。奢求欲望太多的人,他們得道的機緣就很淺。
說莊子
莊子在這段話中提到了三種人:一是“古之真人”,二是“真人”,三是“眾人”。“古之真人”與“真人”好理解,兩者一脈相承,本質上來說,彼此間并不存在任何區別。所不同的是,“古之真人”的時代,人人都是真人,沒有“眾人”的存在。而在“真人”或者說是“今之真人”的時代,真人與“眾人”同處一個現實世界之中。莊子用了“眾人”一詞,強調在這個時代,相對于真人的“眾人”遠遠多于真人。
真人是一些完全不受現實社會束縛與局限的人。他們旁無雜念,心如止水,因此,覺睡得安穩,呼吸深沉,深沉至腳后跟。這里不要誤以為所謂“用腳跟呼吸”,是說真人都有著特異功能,莊子之所以這么說,只是用夸張的文辭,形容他們的淡定深沉,精神與心態的與眾不同。這樣對照來看,“眾人”的形象就很有些卑微猥瑣了。“眾人”的狀態與“大知小知”們很有幾分相似,也不免終日生活在恐懼陰暗中,常常被“屈服”,結果有話噎在嗓子眼里卻吭吭哧哧說不出來,還要算計著如何去“屈服”別人。這樣的人,怎么可能睡得好覺、沒有煩憂之事呢?在莊子看來,“眾人”之所以會陷入這種可悲又可憐的境地,是由于他們的奢求欲望太多,而“天機”又太淺,自然也就整天活得呼吸不暢,郁悶憋屈了。
看到莊子對“眾人”生活狀況的描述,是不是很有幾分似曾相識之感?今日“眾人”的生活又何嘗不像兩千多年前的“眾人”一樣卑微膚淺?這個由“古之真人”到今之“眾人”的時代大幕,自打拉開,便再也不肯閉幕了。
莊子說
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損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今譯
古代的真人,不知道欣悅生,不知道厭惡死。他們對出生不感到欣喜,對死亡也不抗拒。輕松自如地面對死,輕松自如地面對生,僅此而已。他們不忘自己生命的初始,不尋求最終的歸宿;欣然接受生的事實,忘掉生死,回復自然,這樣就可以稱為不因個人的心智而損害“道”,也不以人為的努力去改變生死。這就是真人。
像這樣的人,用心專一,他們的容貌安閑寧靜,神態端正質樸,嚴肅時像秋天一般,平和時則如同春天;他們的喜怒如四時的變化一樣自然,與萬物自然相處,沒有人知道真人的極限究竟在哪里。
說莊子
這一段談的是真人的生死觀。
相比較而言,在先秦諸子中,莊子是談死生最多的哲學家,沒有之一。仔細翻檢《莊子》內篇,幾乎篇篇都談到了生死。在《齊物論》中,莊子把死比作游子還鄉,還借麗姬出嫁的故事說活著的人雖不曾經歷過死,不知道死去的世界究竟是怎樣,但人完全不必害怕死。麗姬出嫁前哭哭啼啼,以為自己出嫁后的生活會苦不堪言。誰承想其實遠比出嫁前要好。于是麗姬竟后悔自己為什么此前那么畏懼出嫁了。進而莊子又用夢與覺比喻生死這兩種世界,提出人死不是生命的終結,而是新的人生循環的開始。“莊周夢蝶”的故事更是現身說法,說人的生死不過是“物化”的過程,從一物化為另一物而已。在《齊物論》中,也許是為了矯枉過正,莊子甚至對死流露出些許的欣羨之情。
如果說,在《齊物論》中莊子是從哲學層面去探討生死的話,那么,在這一段文字中,莊子則以具體、實際的人生經歷闡發真人的死生觀:“出入”“往來”“始終”,一生中,誰又不經歷無數次呢?特別是生如出門,死如回家,多么稀松平常,這樣的話,人們為什么還要對生與死那么耿耿于懷?莊子談死論生,不像后世的佛教道教要人們此生多行善積德,多給寺廟道觀捐香火錢,以免死后下地獄。莊子希望的是,在這個“眾人”喜生惡死的世界,人們終究可以擺脫對死的恐懼,對生的依戀:活著,就高高興興、無拘無束地活;一旦死亡來臨,就輕輕松松、坦然淡定地去死。焉知死后的世界不比活著的世界更美好?“視死如歸”,在荀子、韓非子那里充滿了保家衛國的英雄氣概,但在莊子這兒,死,被說得那么輕松隨意,就像拉家常一樣。莊子談生論死,其目的完全是為了讓人擺脫長期以來形成的對死的恐懼心理,讓人可以自如坦然地好好活著。
這才是一個沒有被這個世界扭曲的真人對生死的態度!
如果人對死生的問題都可以這樣看得開,想得通脫,人生還會有什么樣的障礙呢?看樣子,在莊子心中,真人并不必像南郭子綦那樣,形如槁木,心同死灰,而更像春夏秋冬四時的變化那樣,當喜則喜,當怒則怒,“喜怒通四時”。只不過,這種“喜怒”是自然的,與人的“成心”、利益等無關,所謂“不以心損道,不以人助天”。如此,便可以真正與自然融為一體,心也就可以走向無限的境地。
極其沉重的話題,讓莊子以極其輕松而又溫暖的話語說了出來。當我們面對生死的挑戰時,是不是也能像真人那樣坦然平靜?
莊子說
故圣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
今譯
所以圣人發動戰爭,滅了別的國家卻不失去民心;讓圣人的恩澤施予千秋萬世,卻不是為了獲取“愛民”的名聲。
說莊子
莊子在上一段談及真人的死生觀時說真人“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意思是真人可與世間一切自然和諧地相處,也就可以自然而然地感化周圍的一切,自然也包括人類社會中各種各樣的人,特別是位高權重的一國之君。從“故圣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所表述的整體意思上看,這里所說的“圣人”只有可能是可以發兵滅他人之國的君主。
莊子雖然很少專門討論政治制度問題,但他并不否定君主制。相反,他說“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人間世》),他是把臣民臣服于君主視為在這個制度下天經地義的責任。但關鍵是應該有一個什么樣的君主。像《德充符》中魯哀公這樣愛民至上的君主,還有衛靈公、齊桓公等等,莊子都統統看不上眼,認為他們都不合格,都達不到道的高度,不具有道的胸懷。而要能使有“圣人之才”的人成為有“圣人之道”的君主,非有“莫知其極”能力的真人不可。從這個角度來看,莊子在這里真正所要表達的是,真人具有的無限潛能,同樣可以影響、感染到君主。倘若君主也能像真人那樣,即便發動了戰爭,也不是為了一己之私利,就不會像衛君那樣造成“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反而可以贏得被滅國人的“人心”,而且“利澤施乎萬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