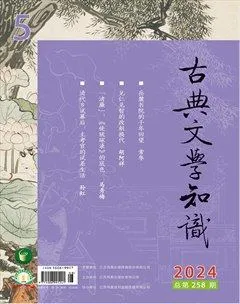岳麓書院的千年回望
常華
世界最悠久的大學在哪里?是始建于1088年的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嗎?是1167年就已聲名鵲起的英國牛津大學嗎?都不是。穿過青翠的竹林,循著小橋流水,我們發現,世界最悠久、保存最完好、如今仍在發揮著教育功能的高等學府,其實就在中國的瀟湘大地上,它,就是岳麓書院。
坐落于岳麓山清風峽口的岳麓書院,始建于北宋開寶九年(976),當時的潭州太守朱洞在唐末僧人筑舍辦學的基礎上,擴大規模,創建了岳麓書院。到了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著名學者周式成為這間隱匿在山林中的書院的首任山長,當時的宋真宗聽說周式在岳麓山腳下開壇講經,將一座書院辦得風生水起,曾特召其入宮,打算任命其為國子監主簿,留在京城講學,但周式卻固辭不受,執意要返回山林。真宗見挽留不住,便賜給了他大量的內府書籍,并手書了“岳麓書院”的金匾送給他。辭別喧囂的京城,重返靜謐的林泉,周式找回的是一份生命的自在與逍遙,在他的主持下,岳麓書院在地方教育體制中的地位開始不斷拔升,《宋史·尹谷傳》載:“初,潭(今長沙)士以居學肆業為重,州學生月試積分高等,升湘西岳麓書院生。又積分高等,升岳麓精舍生,潭人號為三學生。”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當時岳麓書院的地位已相當于今天的大學。
其實,在北宋,書院并不獨岳麓一家,由于朝廷和各級官府的重視,北宋書院呈現出百花齊放的景象,據史料記載,當時的書院已經達到了600余所。在這些星羅棋布的書院中,湖南長沙的岳麓書院和江西九江的白鹿洞書院、河南登封的嵩陽書院、河南商丘的睢陽書院一起,并稱天下“四大書院”。當然,關于四大書院的構成,眾說不一,但有一點卻是不爭的事實,那就是無論哪種說法,岳麓書院始終名列其中,而從辦學規模和辦學水平上,岳麓書院一直處于宋代書院之首。
記得追游故老家。紅蓮幕府在長沙。放船橋口秋隨月,走馬春園夜踏花。
思往昔,謾咨磋。幾番魂夢轉天涯。葵軒老子今何在,岳麓風雩噪暮鴉。
—呂勝己《鷓鴣天》
這首《鷓鴣天》,為南宋孝宗朝官員呂勝己所作。歷經靖康之難的兵燹(xiǎn)火劫,一度詩書鼎盛的岳麓書院也遭受重創,成為一片廢墟。乾道二年(1166),時任湖南安撫使知潭州的劉珙開始重建岳麓書院,身為理學家劉子翚(huī)的侄子和學生,劉珙趕上了孝宗朝對理學政策寬松的好時機,他在平定了郴州爆發的農民起義之后,就將恢復和建立書院作為自己的一項使命。岳麓書院的重建工作進展得很快,不到半年的時間便宣告竣工,為了強化和恢復岳麓書院在南宋教育和學術上的地位,劉珙聘請著名理學家張栻主教岳麓。“記得追游故老家。紅蓮幕府在長沙。放船橋口秋隨月,走馬春園夜踏花”,正是在張栻主教岳麓的這段時期,呂勝己得以成為其門下弟子,當數年后呂勝己在《鷓鴣天》的韻律中,回望自己當年在岳麓書院的求學生活,相信這座掩映于茂林修竹中的學府已經成為他心中永恒的精神家園。
提到張栻,我們必須對這位岳麓書院的第四任山長投去深深的敬意,因為正是他,以其嚴謹的治學態度和開放的治學理念將岳麓書院帶入全盛期。身為南宋初年抗金名相張浚之子,張栻自幼便從父親的言傳身教中汲取到儒學的養分,而他最終能在儒家學脈上闖出自己的一片天地,還是緣于傳承了胡宏之學。紹興三十一年(1161)春,張浚任職湖南路,張栻隨父來到長沙,學術開明的張浚沒有讓自己的兒子只承襲自己的家學,而是讓張栻向湖湘學派的創建者胡宏拜師學藝。胡宏之父胡安國乃北宋末期著名經學家,胡宏作為其少子,“卒傳其父之學”,這位深居衡山的傳道者對于張栻的“涕泣求見”深有好感,在正式收其為徒后,更是對其格外器重,他曾在寫給友人的信中對這位名臣之后不吝其詞地說道:“敬夫(張栻字)特訪陋居,一見真如故交,言氣契合,天下之英也。見其胸中甚正且大,日進不息,不可以淺局量也。河南之門,有人繼起,幸甚!幸甚!”山風浩蕩,云靄四合,一座衡山碧泉書院,就這樣印證下這對理學師徒的背影。當張栻在承繼了父親的蜀學之后,又以自己的勤學篤行盡得胡氏之學,從而成為繼胡宏之后湖湘學派的領袖,我們看到,南宋理學的氣脈之所以形成并得以延宕開來,領軍者的轉益多師、兼容并包,無疑是關鍵一環。
至此,我們可以將視線拉回到岳麓書院了。如果說岳麓書院的復建得益于湖南安撫使劉珙的行政高效,那么,岳麓書院的復興則仰賴于理學大師張栻的治學方略。主教岳麓書院后,張栻并未固守胡氏父子的湖湘之學,而是在此基礎上,博采眾家之長。在辦學理念上,這位湖湘學派的繼承者和開拓者,力主“明理居敬”,倡導“學義、明理、修身、養性”,認為教育不應只為“科舉利祿”服務,應“傳道而濟斯民”,只傳道而不濟民便是虛妄之學,而只濟民不傳道又會無根無本,缺乏依托。更為難得的是,在張栻主教的岳麓書院,學生是可以向老師發出質疑的,而所謂的教與學常常是在一次次論辯中完成,翻開張栻的《南軒集》,我們看到的正是一次次充滿了知識含量的論辯現場,而正是這樣活躍的教學氛圍,讓教與學成為一種雙向的流動,讓看似僵硬的“道”變得更為實用。千年以后,當我們走進岳麓書院,走進這片溢滿書香之地,我們可以想象這樣一幅畫面:在清風竹影中,一位儒雅的學者面對著聚精會神的弟子們,輕搖羽扇,縱橫捭闔,而他的弟子們在其經世致用的教學思想感召下,陸續從這座寧靜的山中院落走出,走向傳道濟民的仕途,走向浴血殺敵的戰場……
張栻能夠讓岳麓書院聲名顯赫,除了其積極用世的辦學思想,還有其海納百川不存門戶之見的辦學胸懷,因為正是他開放的胸襟,讓一代理學宗師朱熹走進了這座“瀟湘洙泗”。南宋乾道三年(1167),這位“百科全書式”的文化大師應張栻之邀,不遠千里專程從福建崇安來到瀟湘大地,來到書聲瑯瑯的岳麓書院。岳麓書院的千年歷史,從此銘刻下這個特別的年份,因為就在這一年,朱熹和張栻兩位大師“聚處同游岳麓”,“晝而燕坐,夜而棲宿”,在岳麓書院共處了兩個多月。事實上,岳麓之會并不是朱張二人的初識,他們的初識是在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當時孝宗在臨安召見張浚張栻父子,恰好朱熹也在臨安等著召見,二人由此結交。時間轉過乾道三年,此時的張栻35歲,朱熹38歲,一位已是湖湘學泰斗,一位已是閩學宗師,當他們攜手走進清風峽口,一起登上赫曦臺看旭日東升,一起品茗百泉軒,聽溪泉錚淙,一座山中書院,便更加厚重,更加豐盈起來。那么,這兩位年齡相仿、學養相近的大師,在這次岳麓之會中,又會交流出哪些更深層次的學術話題呢?
《朱子年譜》載,張朱二人“往復而深相契者,太極之旨也”,錢穆先生則認為,“朱子赴南岳前,于延平遺教仍未能堅定信守,而湖南一派則正與延平相反,故特往求教于南軒”。盡管關于張朱二人在岳麓所論內容學界眾說紛紜,但有一點卻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二人都因此番岳麓之會受益頗深,他們之間沒有學術派別的芥蒂與隔膜,有的只是雙向的交流與包容。
更令人感動的是二人在岳麓書院別開生面的開壇“會講”。伴著山中的鳥鳴,這兩位理學宗師面對絡繹而來的學子,講述奧妙精深的太極、心性、仁愛等諸多哲學命題,他們各自闡述著自己的觀點,講到興處,甚至可以連續三晝夜不休息,而聽講的學生則可以根據二人的會講,隨意轉換自己的陣營,站到自己所支持的大師一方。這樣開放的授課方式著實吸引了當時的眾多學子,他們紛至沓來,生怕錯過了這場發生在岳麓山下的學術激辯,以至于出現了“來學者座不能容,飲馬池水立涸,輿止冠冕塞途”的盛況。一座綠樹環圍的庭院,因為有了自由活躍的空氣和嚴謹務實的學風,而成為萬千學子爭相朝拜的圣地,這不僅是岳麓書院之幸,更是中華文化之幸。
憶昔秋風里,尋盟湘水傍。
勝游朝挽袂,妙語夜連床。
別去多遺恨,歸來識大方。
惟應微密處,猶欲細商量。
—朱熹《有懷南軒老兄呈伯崇擇之二友二首·其一》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在岳麓書院駐留兩個多月后,朱熹最終踏上了歸程。“別去多遺恨,歸來識大方。惟應微密處,猶欲細商量”,兩個多月的相處,朱熹與張栻已然成為心聲互答的至交,他們一起看過岳麓書院的日落月升,一起聆聽岳麓書院的啁啁鳥鳴。當張栻于48歲英年早逝,浸潤過岳麓之風的朱熹并沒有讓這座山中庭院斷了文脈、荒了書聲,紹熙四年(1193),赴任潭州的朱熹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修復歲久傾圮的岳麓書院,“窮日之力治郡事甚勞,夜則與諸生講論,隨問而答,略無倦色”。彼時的朱熹在政務與學術之間往來穿梭,樂而不疲,而我們看到的,則是作為“東南三賢”之“二賢”的張栻、朱熹在學術上的生命接力,是湖湘之學慢慢沁入的朱張傳統,是岳麓書院亢然奏響的高山流水之聲。
此后,盡管岳麓書院曾遭遇多次兵燹火劫,但浩蕩的人文精神始終是這里不息的氣脈。在婆娑的樹影中,我們可以隔著歷史的窗欞,看到思想家王夫之潛心著述的身影;在皎潔的月光下,一張平攤在太湖石上的《海國圖志》大綱,讓我們知道,魏源心中的那片海,其實發端于一片山中的院落;在曾國藩、左宗棠南征北戰的生涯中,我們能于蕭森的鐵器之外,嗅到一股來自書院的墨香;而作為從這座千年學府走出的最優秀的“旁聽生”,毛澤東在中國大地上進行的翻天覆地的偉業,誰又能說不和這座靜謐的書院發生著聯系?在岳麓書院,有一眼清澈見底的泉水,名曰“文泉”,據說,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書院大修,人們在挖地基時,發現了這個泉眼,遂被人們命名為“文泉”,意為文思如泉。如今,歷經240多年的“文泉”依然在汩汩流淌,如果你到岳麓書院,喝上一口“文泉”水,相信會從清冽甘甜的泉水中,品出這座千年書院的悠悠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