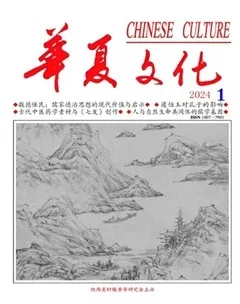蘧伯玉對孔子的影響
代云
蘧伯玉名瑗,春秋晚期衛國賢大夫。衛國與魯國同為姬姓諸侯,又是鄰國,關系密切(《論語·子路》:“魯衛,兄弟之政也”),因此孔子很重視衛國。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周游列國時曾兩次寄居在蘧伯玉家,《孔子家語·困厄》還提到蘧伯玉請孔子相禮,可見他與蘧伯玉的關系比較密切。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載,蘧伯玉是孔子所師事的人之一,綜合考察二人的交往,他對孔子的影響主要包括兩個方面。
一、修身
孔子在衛國時,蘧伯玉派人看望他,孔子問使者蘧伯玉在干什么,使者說他想少犯錯誤,但是做不到,孔子對這位使者大為贊嘆。“欲寡其過”,這是講修身。使者說蘧伯玉“欲寡其過而未能”(《論語·憲問》),“未能”是謙詞,重點在前者即寡過。孔子曾稱贊顏回好學,說他“不遷怒,不貳過”(《論語·雍也》),犯過的錯誤不會再犯,這是修身中重要而難得的事。蘧伯玉善于自我反省,這在當時是被公認的。《莊子·則陽》說他“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淮南子·原道訓》說他“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勤于修身使蘧伯玉成為真正的君子,“外寬而內直,自設于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不悒悒,蘧伯玉之行也”(《韓詩外傳》卷二),《列女傳》借衛靈公夫人之口,說他“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墮行”(《列女傳》卷三《仁智傳》)。在別人看不見的地方依然守禮,不是做給別人看,而是自我要求,這是極高的道德修養。
蘧伯玉的修養工夫受到孔子贊賞,縱觀孔子一生,他在治學修德方面也是勇猛精進,毫不松懈的。他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在人生的每個階段都有進步和突破,這是通過日常積累而發生變化的。不斷反思和改正自己的不足之處,是重要的方法。他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語·述而》)“不善不能改”是在修身上麻木懶惰的表現,隨波逐流,任本能驅使,放棄成為人的責任。孔子對此感到憂慮。他稱贊顏回“不貳過”,還說“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論語·衛靈公》)孔子深入鉆研易學后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述而》)可見他始終認為自己還有不足,念念不忘改過遷善。這與蘧伯玉常欲寡過,日新其德的追求不謀而合。孔子以蘧伯玉為師,可以認為在這方面受到蘧伯玉的影響。
二、處世
蘧伯玉歷事衛獻公、殤公、亡而復人的獻公、襄公、靈公。這一時期圍繞衛獻公被逐與返國,衛國政壇出現動蕩。蘧伯玉被迫卷入卻全身而退,這讓孔子很是感嘆:“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遽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論語·衛靈公》)“卷而懷之”朱熹注:“卷,收也。懷,藏也。”(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2012年,第164頁)卷而懷之即收藏避禍。
據《左傳》記載,衛獻公一再失禮于孫林父、寧殖,激怒他們。孫林父得知衛獻公意圖清除他,為防不測,打算搶先下手。他帶領子弟臣仆到自己的采邑戚,偶然遇見蘧伯玉(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2009年,第1012頁)。孫林父說衛獻公暴虐,衛國社稷有傾覆的危險,問蘧伯玉的打算。蘧伯玉說君臣有別,臣不敢犯君,況且即使廢舊君,立新君,又怎知新君一定勝過舊君?他不愿摻和這種事,就當即決定出逃,為免周折,他選擇最近的國門出國(《左傳·襄公十四年》)。十二年后寧殖之子寧喜迎衛獻公回衛國,又與蘧伯玉商議,他說“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人?”于是又出逃,“從近關出”(《左傳·襄公二十六年》)。
衛獻公復國,孫、寧二氏決裂,在國內接應的太叔儀受到衛獻公責備,在外替衛獻公聯絡的子鮮終身不回衛國,孫林父叛衛附晉,退出衛國政治舞臺,寧氏最后被滅族(“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相比之下,在這場慘烈的內亂中蘧伯玉兩次被拉攏,兩次成功脫身,成為明哲保身的典范。吳公子季札游歷北方諸國時,與蘧伯玉相善,贊衛國有蘧伯玉這樣的君子,可保衛國無患。(“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鰍,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日:‘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莊子·人間世》“顏闔將傅衛靈公大子”一節,蘧伯玉向顏闔講述臣事君時的全身之道,雖然有寓言性質,但也說明他在道家人士那里是具有生存智慧的人物。
孔子對衛國很熟悉,蘧伯玉的經歷他肯定都知道。在保證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從政,這種生存智慧,孔子一早就從老子那里領受了,所以他認可蘧伯玉是很自然的事。
孔子有志于張公室,但魯國自春秋中期以后被三個世襲貴族(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把持政權,孔子這樣的低等貴族沒有參與國政、施展抱負的機會。直到季氏家臣陽虎(《論語》中稱陽貨)叛亂,季氏開始考慮抑制“舊式宗法家臣”(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9頁)的勢力,擢拔非宗法性的才能之士為其所用,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孔子才登上魯國政治舞臺。孟子說孔子的出仕原則有三:“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也。于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于衛靈公,際可之仕也;于衛孝公,公養之仕也”(《孟子·萬章下》)。童書業認為“孔子之仕于魯,實仕于季孫氏也”(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第89頁)。當他張公室的意圖受到季氏的忌憚,再加上齊國插手,孔子被迫離開魯國。他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論語·述而》),用、舍指的都是季氏。也就是說,他能否在魯國從政,取決于季氏的態度。準確判斷和把握國內政治形勢變化,來決定自己的出處,在這方面蘧伯玉的警醒與明智對于孔子而言應該是學習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