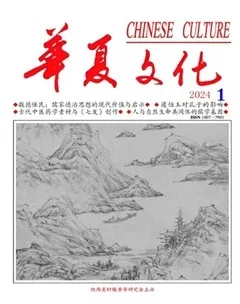敬德保民:儒家德治思想的現代價值與啟示
王家明
“以德治國”是儒家在政治上的第一性訴求,也是首要堅守的原則。“德治”思想源于商周時代對天命的敬畏:天命無常,唯德者為君。在此之中,“德”的最主要內涵是“保民”。在孔子提出“仁”、孟子提出“四端”之后,“德治”便不再是純粹的政治向問題,而是經由“內圣外王”體系的建立,成為了人之為人的本質要求和達成王道的必由之路,己身之道德修養成了一切“德治”行為的起點,對君主的要求也就變成了“圣”和“王”集于一身。這種“德治”思想雖體現出儒家對民生的關注和對立國立君最初緣由的正當性思考,但把“道德”作為治理國家的最高制度,把政治向好的希望全部寄托在統治者一人的道德水平上,顯然也是在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現。與此同時,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努力實現中華傳統美德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涵加以補充、拓展、完善,增強其影響力和感召力,讓舊的文化在新的時代展現出全新的、適應社會發展的意義。儒家“德治”思想正能在當代有所啟示,以期更好地實現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一、儒家德治思想的由來
儒家“德治”思想的形成過程比較漫長,它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商周之際,是在其鼎革之中孕育出來的。商人崇“帝”,以“上帝”為王權所來處,即“君權神授”的道路。“帝”或“上帝”不僅是政治權力的賦予者,更是凡間一切事物的主宰者,凡事都要請命于“帝”。但周代殷以后,小邦競能戰勝大國而成天下共主,這從根本上動搖了“上帝”一直護佑商祚的觀念。同時,為了解釋政權的合法性,周王朝提出了全新的理念:“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尚書·蔡仲之命》)“天”并不護佑一家一姓,而是以德行命人君,有德者為主,失德者則去移其天命。商之敗于周,是因其“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尚書·召誥》)“德”成為了“天命歸否”的唯一標準。并且,“天”以德命君是為了更好地綏安民庶:“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尚書·泰誓》)“天”為護佑下民而立君師以為人主,唯人主“敬德保民”為能克配上帝,如此一來,考察人君“德”與“不德”的標準也就成了民之安與不安,故日“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尚書·泰誓》)“天”之視聽全由民之視聽,人主對民眾如何就是他自己德行的體現,“天畏忱,民情大可見”。(《尚書》.康誥》)且人主在君臨天下的同時也承擔了更多的責任,“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論語·堯日》)。至此,周王朝在部分繼承商人“上帝”崇拜的基礎上,由周公提出“敬德保民”:天命在德、德在安民,故保民即敬德、敬德即敬天。這種“天命無常”、“敬德保民”的思想,直接開啟了儒家“德治”發展的序幕。
孔子繼承了周公“德治”思想,并在此基礎上提出“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在“苛政猛于虎”(《禮記·檀弓下》)的時代,孔子以“德政”為治國之第一綱領,提倡以教化行德政:“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以君子之盛德為偃草之風,小人見君子其德如是,必紛紛效仿以進于德。這實際上已經把“德治”思想由對國家的治理方針收攝到了君主一人的道德修養上,孔子以前的德政主要講如何保民,而孔子則提出以君主本人之德行的提高為“德政”之措施,首開內圣外王之進路。及至孟子又進一步,提出“仁政”,更加細化了“德治”的方法和方向,用“仁”來總括“德”。孟子日:“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孟子·離婁上》)天子統有四海,不仁則失之;諸侯祭有社稷,不仁則失之,以至卿大夫及士庶一是如此,不仁者失其所有,仁者得其所應有。這其實就是對“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尚書·蔡仲之命》)更細致的解釋,并由此而產生了王霸之辯。以仁心施仁政于天下者謂之王,以利心施暴政于天下者謂之霸,由“德治”引申出來并以之為核心的“尊王賤霸”思想自此而有,并在以后成為中國政治上的主流。不過上述“德治”仍然是在效驗上講,是以得天下誘君、以失天下怖君,使之不敢不實行“德治”,而真正從源頭根本上為“德治”立住的則是董仲舒對《尚書》的延伸:“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春秋繁露》)天不以君王為中心,生彼烝民以足奉王者;而是以生民為意,立君王以安四方。主次關系一旦確定,君王在某些角度來看是民眾的“服務者”,那么他的服務態度,亦即其治之德與不德,自然也就成了是否稱職、能否繼續為王的唯一標準。
二、德治的具體內涵
由周繼殷祚而有的“德治”思想,經孔孟發揮成“敬德保民”,有了更為明確的指向和實行措施,以“敬德”和“保民”為王道之方。其中“敬德”又有兩層含義:第一,“德治”是最高政治原則;第二,修德是君主的首要追求。
第一,“德”是最高政治原則。首先,君主應以正德為表率。子日:“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以“正”釋“政”,即以君主之正德為政治之根本,因為“草上之風必偃”,所以“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孟子·離婁上》)君主的德行直接影響整個政治系統的善惡趨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君主好德,則官民莫不效仿,則政無不正;其次,“德治”是所以來遠人、王天下之法。子日:“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論語·季氏》)“遠人”即春秋戰國時期他國的子民。人口是古代國家強盛的基礎,只有更多的子民才能實現社會的發展,所以如何讓更多“遠人”成為本國國民,是君主應當重視的問題。孔子認為以武力征服不可取,以“文德”之修使“遠人”慕仁而來,才是王道之途。孟子更進一步,把“仁”看作天下得失之根本原因:¨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孟子·離婁上》)以“仁政”成“德治”,則生民無不愿往樂土,則天下可得,故日“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孫丑上》)最后,“德治”應該“德主刑輔”。子日:“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以政刑為據,以賞罰為手段,實際上是利誘恐怖。民眾為避免刑罰或者追求賞賜而安分守己,雖能減少犯罪,但只是出于對刑罰的恐懼之心,并非心悅誠服之;若以德以禮為綱教化民眾,則民眾知恥而不為禍亂。故只有把“德治”當作第一政治原則,才能實現王道天下的目標。
第二,“敬德”的另一個維度是君主自身的道德修養,即內圣以成外王。天命靡常,有德者居之,“德治”與否決定了政權的合法性以及能否繼續存在下去,故周公提出“敬德保民”以為“德治”之法。但“這種‘敬德保民首先考慮的還是‘天命靡常,害怕天命的轉移導致政權的喪失,而不是出自于自己的自覺自愿,不是發自人的內在做人的要求與需要。”(李維武:《儒家德治思想的發生、完善及其基本原則》)由對喪失政權的恐懼而行的“德治”,實是不得已而為之者,并非君主之所愿,那么“德治”的內因便不夠充分。直至孔子提出“仁”,孟子對其加以擴充為“仁政”,并且在“仁政”之外提出“四端”:“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梁惠王上》)“四端”為人人本有,時刻呈現于與物相接時,“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孟子·梁惠王上》),這種“不忍之心”即是“四端”之呈現。此“不忍人之心”擴而充之,則能為“不忍人之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即是“仁政”、“德治”。如此,則把“德治”的原因從對天命制裁的恐懼轉移到了人之性善的本然要求上,那么施行“仁政”、“德治”的第一步,也就是君主提高自身的道德修養了,故子日:“修己以敬,修己以安民,修己以安百姓。”(《論語·雍也》)“德治”的模式變成君主以其德行教化萬方、終以成就王道,是內圣——外王的進路,把個人的道德修養和政治的王道達成緊密聯系在了一起。
第三,“保民而王”是實現“德治”最重要的部分。孟子日:“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如果說“修德”是對君主欲成王道德治的個人要求,“保民”則是“德治”最直接的外部政策體現。想做到“保民而王”,首先要意識到“民為邦本”:“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尚書·五子之歌》)“民為邦本”意味著民眾是國家構成的基礎,是君主權力的現實來源,“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荀子·王制》)水之能載舟也就能覆舟,民眾能安于君主之治,也能推翻他:“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孟子·離婁上》)至此,孟子做出了他對民眾地位肯定的偉大宣言:“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民貴君輕”比之“民為邦本”更能體現民眾之重要性,因為“民為邦本”從某種程度來看依然是對君主提出的使其權力更穩固的建議,而“民貴君輕”則直以“保民”為君主天然不得不行之義務;其次,“保民”要求“制民之產”:“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吃飽穿暖,滿足民眾最基本的生存生活需求,不至于饑寒交迫而死,這只是最低標準,如欲稱“德治”并達成“王道”,仍需更進一步:“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衣帛食肉、斑白者不負戴,在孟子所描繪的政治藍圖中,民生的重要性被提升了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果真如此,又怎能不實現王道?最后,民庶既富,則應以德教之。民眾生活上的富裕已經達成,更加以道德教化,至此我們可以看到儒家“德治”思想的終極愿景:君主以修德為本、以富民為要,以禮義教民并輔以刑法,則遠人來服、天下歸心。
三、儒家德治思想的現代價值
儒家“德治”思想雖然具有很大的進步意義,但這其實是把道德社會的結果當作了實現道德社會的方法。在一個以道德為規則和標準的社會中,只能催生出道德作偽,并且在君主獨裁集權的政治中,又因為對道德的解釋有很大的彈性,社會的治亂全部仰賴于君主一人的道德水平,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政治行為。究其內因,在儒者看來,“德治”不僅是實現道德社會的捷徑,更是達成道德社會的唯一途徑,所以懷揣著對道德社會的向往,千百年來直以“敬德保民”之“德治”追求王道。但現在看來,不一定依賴虛無縹緲的“德治”,依法治國同樣可以實現社會道德的建立。并且即便孟子之“民貴君輕”、《尚書》“立王為民”,實際上都仍然屬于對君主的勸諫,欲其自上而下地“以民為本”施行“德治”,其出發點不出“維護政權之穩定”。而中國共產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其宗旨和根本目標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新中國政府也是自下而上建立的、由人民群眾推舉出來的人民政府,人民群眾不再仰統治者鼻息、將美好生活的期待全部托付于統治者的道德水平,脫離了“德治”之“君主以德治國”統治階級的視角,而是真正自己當家做主。
同時我們也要意識到,在社會主義環境下的今天,儒家“德治”思想并非毫無價值。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規范,不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價值”,所以“要認真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精華和道德精髓”,做到古為今用。儒家“德治”思想本身就帶有一定的進步性,它對道德的重視同樣能夠在當下對我們有所啟示:
第一,為政以德。“為政以德”是儒家政治一直以來的要求,政府的設立也是以“先覺覺后覺”為目標,最高統治者不僅是“君”,同時也稱“師”,是統領百官之“君師”,百官則又行教化之事為地方之師。以德治國、以德行政,是儒家政治的根本基調。習近平總書記也強調:“政德是整個社會道德建設的風向標。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德者得也,以德為政,則善施于他人,德得于自身。加強干部德政建設,先讓官員干部做到“有恥且格”,是黨員干部勿忘初心的重要體現。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領導干部加強自律的關鍵是“增強政治定力、紀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終不放縱、不越軌、不逾矩。”其中道德定力更是重中之重,是達成其他方面的基礎,以儒者修身態度提升道德水平并用之于政,也是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的重要途徑。
第二,以人為本。“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儒家政治對當代的重要啟示,雖然在封建王朝中以“保民”為業是為了更好地維護統治,但這也同樣提醒今天的共產黨人要牢記以人民為中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的征程上,我們必須緊緊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站穩人民立場,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尊重人民首創精神,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不僅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鮮明品格,也是中國共產黨不斷奪取勝利的關鍵,更是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實踐要求。
第三,為官務正。“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終不為邪暗小人所惑而易其所守。”(薛瑄:《讀書錄》)以正為官,則其政愈正;以光明之心行事,則其心愈光明。不愧天怍地,養浩然正氣以為人為官,這無關日寸代和學派,而是一以貫之的美德。習近平指出:“每一個領導干部都要拎著‘烏紗帽‘為民干事,而不能捂著‘烏紗帽為己做‘官。”以光明正大之心為官、行光明正大之政,不僅是儒家政治思想中流傳下來的寶貴精神,也是當下從嚴治黨、從嚴治吏的基本要求。
剔除儒家“德治”思想中封建專制和不重視法律效用等落后的部分,對其中合理進步的精髓內容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尋求對當下社會的啟示,以優秀的“德治”精華服務于黨的思想建設,是堅持文化自信的體現,也是新時代的發展要求。提升國家治理效能,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我國進入社會主義新時代的重大課題,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吸收無疑可以更好更快地實現這一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