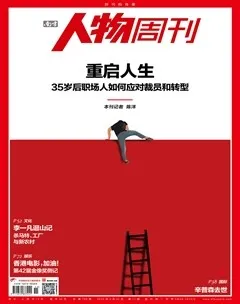《雷普利》 光影交錯(cuò)里的神跡與殺意
楊時(shí)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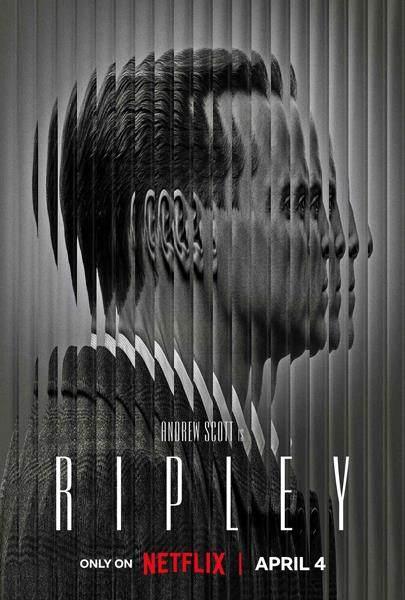
影子,各種影子。投影、背影、倒影、陰影、暗影、剪影……如果說(shuō),有什么元素成就了《雷普利》,那么最重要的或許就是影子。對(duì)影子的運(yùn)用,讓這個(gè)寫(xiě)于數(shù)十年前的故事瞬間變得迥然不同。誰(shuí)能想到呢,在2024年竟然還能看到一部黑白劇集,不是偶爾穿插的、當(dāng)作點(diǎn)綴的黑白片段,而是整整八集全部都是決絕的黑白。只從這形式上來(lái)講,《雷普利》以一種大踏步后退的方式完成了一次極其冒險(xiǎn)又刺激的躍進(jìn),它以保守的面貌成為了先鋒,以極簡(jiǎn)的色調(diào)打造出繁復(fù),像禁欲系背后掩藏著的更魅惑的狂放,欲蓋彌彰。
開(kāi)場(chǎng),一個(gè)男人將一具尸體從一節(jié)節(jié)大理石樓梯上拖拽而下,從他們的龐大身影映射在墻上的時(shí)候,你就知道,一個(gè)古典的犯罪故事開(kāi)始了。它那么希區(qū)柯克,那么拒絕當(dāng)下,那么迷戀舊日細(xì)節(jié),換句話(huà)說(shuō),它那么經(jīng)典,那么永恒。“光永遠(yuǎn)是畫(huà)的靈魂。”這句話(huà)不止一次出現(xiàn)在這部劇中,主角雷普利站在教堂和博物館中凝視著卡拉瓦喬的作品,身后沉默的男人突然開(kāi)口說(shuō)出這句話(huà),像一句讖語(yǔ),像一道寓言,從故事內(nèi)部刺向外部,留下一個(gè)謎面。當(dāng)故事在無(wú)數(shù)影子的交疊之中次第展開(kāi),這句話(huà)顯露出別樣意義,它既指向畫(huà)作本身的技法,也指向這部劇的技法,更隱秘地指向故事之中人性的光亮與灰度。
《雷普利》是個(gè)收束的、冷酷的、啞光質(zhì)感的奇觀(guān)。這部劇集或許會(huì)讓劇迷們想到近處的《白蓮花度假村》以及稍遠(yuǎn)幾年的《新教宗》和《年輕的教宗》,不只是因?yàn)檫@些故事的背景同樣設(shè)置在意大利,更因?yàn)槟撤N對(duì)作者性的共同在意。如果說(shuō)另外三部劇是用無(wú)盡的炫目色彩營(yíng)造出一種內(nèi)心世界的荒蕪倒影,那么《雷普利》則恰恰相反,只用黑白和光暗對(duì)比就塑造出了一朵實(shí)際上多彩到絢爛的惡之花。
為什么一部黑白劇集會(huì)與色彩有關(guān)?那是因?yàn)閷?dǎo)演聰明地使用了一種反向萃取的方法。意大利濃稠的色調(diào)是眾所周知的,導(dǎo)演斯蒂文·澤里安用黑白色調(diào)將其全部遮蔽,反而激發(fā)了觀(guān)眾對(duì)那些色彩的重構(gòu)與想象,把被動(dòng)的觀(guān)看演變成一次主動(dòng)的參與,面對(duì)黑白畫(huà)面,自己在腦中將艷麗填滿(mǎn),這過(guò)程遠(yuǎn)比直接看見(jiàn)色彩更令人悸動(dòng)。這是一種詭異的觀(guān)感,詭異得如同這故事本身。
《雷普利》改編自著名小說(shuō)《天才雷普利》,這個(gè)故事也曾被拍成電影,由馬特·達(dá)蒙主演,對(duì)于喜歡這一類(lèi)型作品的讀者而言,它是這個(gè)圈子里的名著。就是在這樣過(guò)于熟悉的前提下,劇集《雷普利》依靠對(duì)形式的重視,竟然將一個(gè)類(lèi)型故事變成了作者電影。
它是一個(gè)關(guān)于騙子的故事,美國(guó)年輕人雷普利以仿造各種假文書(shū)騙取陌生人的錢(qián)財(cái)為生,處在困頓邊緣。一次意外的機(jī)會(huì)改變了他的命運(yùn),一位富商找上他,希望他能幫自己勸說(shuō)遠(yuǎn)在意大利不務(wù)正業(yè)的兒子迪奇回到家中。在意大利,雷普利開(kāi)始了自己的蛻變,從一個(gè)不知所措的外國(guó)游客一點(diǎn)點(diǎn)變得左右逢源,是迪奇的財(cái)富刺激了他,他將詐騙的能力重新激活,成為迪奇的密友,進(jìn)而取而代之。

在這個(gè)故事中,寄生者吞噬了宿主。它呈現(xiàn)出一種緩慢的、不疾不徐的邪惡,命案的最后一擊當(dāng)然都充滿(mǎn)血腥,也突然而起,但更重要的是之前的整個(gè)過(guò)程,那過(guò)程幽暗、粘稠,雷普利像某種可以釋放麻痹毒素的深海動(dòng)物,不動(dòng)聲色地將對(duì)方俘獲,在某個(gè)不確定的時(shí)刻才完成殺戮。
這個(gè)故事的外殼是社會(huì)性的、關(guān)于法律的,與詐騙和欺瞞相關(guān),但它的內(nèi)核早已隨著故事的展開(kāi)而變成了精神性的,關(guān)于身份的構(gòu)建、認(rèn)同、篡改,關(guān)于對(duì)自我認(rèn)知的錯(cuò)位、重置和可能性,關(guān)于命運(yùn)的流變、詭譎與不可知。是這些微妙的、灰色的、難以言傳的東西讓這個(gè)故事變得高級(jí),從一個(gè)簡(jiǎn)單的詐騙故事的肉身里飛升而出,奔赴那個(gè)帶有終極拷問(wèn)的終點(diǎn)。
劇中設(shè)置了很多雷普利獨(dú)白的場(chǎng)景,有時(shí)是為了篡奪他人身份的排練,有時(shí)是為了應(yīng)對(duì)即將到來(lái)的警察的預(yù)演。這些無(wú)實(shí)物表演成為了故事中最詭異的幾幕,演員安德魯·斯科特演出了一種絕對(duì)的扭曲和邪祟,時(shí)而像個(gè)派對(duì)上的優(yōu)雅藏家,時(shí)而像個(gè)肉鋪里的野蠻屠夫。
雷普利靠近人、觀(guān)察人、戲弄人、操縱人、殺掉人,他是個(gè)反社會(huì)的人,但如此輕易、輕松地融入社會(huì),他的謀生方式是周旋,是耍弄,是在人性與人心的縫隙之間鉆營(yíng)和躲閃,道德因素在他的生命里是不存在的。他有一種因?yàn)槊擅炼械男U力,也有一種因?yàn)槔硇远目b密,他是理性與荒蠻交媾后生產(chǎn)出的怪物。一個(gè)理性的瘋子,一個(gè)瘋癲的智者。
意大利不只是一個(gè)地點(diǎn),也是一種時(shí)間,它用無(wú)數(shù)雕塑、繪畫(huà)以及公共建筑,將古老的時(shí)間封存至今,人類(lèi)在其中新陳更替,但背景亙古不變。鏡頭掠過(guò)寧?kù)o的海面、巨大的穹頂和無(wú)盡的廊柱,一幀一幀一格一格,刻意充滿(mǎn)阻滯,但圖景彼此連綴,最終卻如此流暢。那么多空鏡,那么多凝視,那些恢弘的眾神雕塑皺起的眉頭像萬(wàn)年的驚詫和厭倦,凝視人間的荒誕、苦難與悲歡,看罪惡和愚蠢無(wú)盡重復(fù)押韻,肆無(wú)忌憚。對(duì)于一部劇集來(lái)說(shuō),這鋪張的鏡頭真奢侈啊。
《雷普利》的故事發(fā)生在一個(gè)沒(méi)有攝像頭、沒(méi)有DNA、沒(méi)有人臉識(shí)別的世界,偵探需要走出家門(mén)探尋走訪(fǎng),不停的位移讓這一類(lèi)懸疑故事充滿(mǎn)獨(dú)特的動(dòng)感,那些無(wú)盡的樓梯和臺(tái)階,成為了一種隱喻,那部隨時(shí)會(huì)壞掉的電梯成為另一種隱喻。人在樓梯上攀爬,尸體從樓梯上拖拽,電梯總在急需時(shí)壞掉,這其中都充滿(mǎn)況味,而最終你會(huì)發(fā)現(xiàn),這故事中幾乎每個(gè)細(xì)節(jié)都充滿(mǎn)況味。
讓我們回到影子吧,《雷普利》以影子開(kāi)場(chǎng),也以影子終結(jié)。當(dāng)雷普利不得不以自己原本的身份面對(duì)警探的時(shí)候,他作了一個(gè)大膽的決定,在那幢宮殿般的房子里,他拉下窗簾,戴上假發(fā)和胡須,將自己藏進(jìn)陰影里,完成了一次匪夷所思的終極欺詐。錯(cuò)位、遮擋與隱藏始終是這個(gè)故事的核心,說(shuō)到底這一切都跟光與暗有關(guān)。
故事中不止一次地提到卡拉瓦喬。卡拉瓦喬生活于16世紀(jì)末到17世紀(jì)初的意大利,習(xí)慣隨身攜帶匕首和劍,有命案在身,癲狂詭秘,一生如謎。他的畫(huà)中充滿(mǎn)光線(xiàn)和陰影構(gòu)建出的神跡。他為這個(gè)故事點(diǎn)睛,成為一個(gè)遙遠(yuǎn)的、歷史深處的“雷普利”的倒影。
意大利本身就如同巨大的歌劇院,《雷普利》也被演繹成一場(chǎng)宏大的歌劇,充滿(mǎn)乖張與驚懼、殺戮和鮮血,大幕開(kāi)啟,大幕垂落,令觀(guān)眾唏噓。這故事里有黃雀在后,也有金蟬脫殼,最終所有人都蒙在鼓里,除了死者還有誰(shuí)洞悉真相?有那些巋然不動(dòng)的雕塑,還有那只房東太太的貓,它們看見(jiàn)一切,但就像故事中所言:神明看見(jiàn)一切但沉默不語(y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