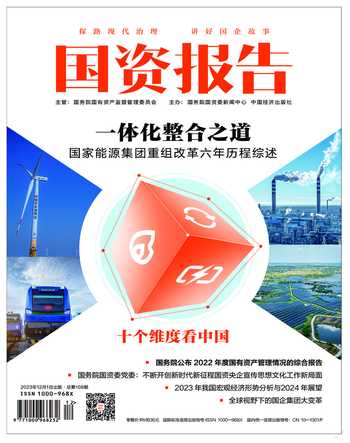大漠驚雷 無問西東
1958年9月,華中工學(xué)院(現(xiàn)華中科技大學(xué))機(jī)械系共有8人被分配到北京工作,魏其勇是其中一個。在前往北京的火車上,這8個風(fēng)華正茂的年輕人很快就親如兄弟,并約定日后務(wù)必要多聯(lián)系。然而誰也沒想到,在北京站道別之后,他們就從此失去了聯(lián)系。不過,那已經(jīng)是后話了。
也就是在那一年,閆五福回到了闊別已久的祖國。他所在的部隊是一支在朝鮮戰(zhàn)場上屢立戰(zhàn)功的英雄部隊——中國人民志愿軍第20兵團(tuán)。他只知道回國后將要執(zhí)行一項光榮又辛苦的任務(wù),卻并不知道大漠深處將成為他們新的“戰(zhàn)場”,也沒料到像魏其勇這樣的知識青年會成為他們新的“戰(zhàn)友”……
一個無法兌現(xiàn)的約定
斗轉(zhuǎn)星移,6年后。
1964年10月16日傍晚,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的第十四場公演結(jié)束后,大家聽到周恩來總理異常興奮地宣布了一個特大喜訊——“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大家可以盡情歡呼!”
然而在這個歡慶的日子里,有些人卻高興不起來。
時任美國國防部長的麥克納馬拉傲慢地說:“中國5年內(nèi)不會有原子彈運載工具,沒有足夠射程的導(dǎo)彈,原子彈無從發(fā)揮作用。”美國媒體也應(yīng)聲嘲笑:“有彈沒槍,一通瞎忙。”
“兩彈結(jié)合”的確不是件容易事,美國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到發(fā)射載有核彈頭的導(dǎo)彈用了13年,蘇聯(lián)用了6年。西方人理所當(dāng)然地認(rèn)為,以當(dāng)時中國的科技實力絕不可能在短時間內(nèi)研制出運載工具來。
其實,這顆原子彈的爆炸對于中國核武器的發(fā)展來說僅僅是第一步。中南海早在幾年前就著手醞釀一個深刻改變世界戰(zhàn)略格局的重大決策。“我國的導(dǎo)彈試驗早在原子彈爆炸之前就已經(jīng)秘密進(jìn)行了。”6年后,已在七機(jī)部一分院總體設(shè)計室擔(dān)任總體組組長的魏其勇回憶,“到了北京,我和另一個同學(xué)被安排坐上了一輛出租車。”車越開景色越荒涼,突然前方一塊大牌子吸引了兩個年輕人的注意——“外國人到此止步”,他們這才意識到自己快到傳說中的“神秘單位”了,卻并不知道他們即將要開啟的一項神秘任務(wù),就是核導(dǎo)彈的研究。因為保密需要,兩人和同行的其他6人從此失去了聯(lián)系,那個“務(wù)必要多聯(lián)系”的約定變得無法兌現(xiàn)。
“我們是在1958年10月出發(fā)的。”當(dāng)年閆五福所在的部隊悄然開進(jìn)大漠深處,則是為了建設(shè)我國第一個綜合性導(dǎo)彈試驗靶場,也就是現(xiàn)在的中國酒泉衛(wèi)星發(fā)射中心。
和魏其勇、閆五福一樣,來自全國高校、科研機(jī)構(gòu)、軍工單位、部隊的數(shù)萬名技術(shù)骨干聚集到一起。他們以赤子之心,無問西東,共同拉開了中國早期導(dǎo)彈事業(yè)的序幕。
1960年,我國仿制的第一枚導(dǎo)彈“東風(fēng)一號”首飛成功。4年后,也就是在第一顆原子彈爆炸之前3個多月,我國已經(jīng)擁有了自己研制的東風(fēng)二號中近程導(dǎo)彈,為解決原子彈的運載工具奠定了基礎(chǔ)。這也是后來我國能快速解決“有彈無槍”大問題的關(guān)鍵所在。
和“嬌小姐”的一樁“婚事”
很多年過去,魏其勇在老家的父母一直以為兒子在北京的“9200信箱”工作。事實上,他已經(jīng)是“東風(fēng)二號”型號總體設(shè)計組組長了。
“我們的工作保密性非常高,不僅不能讓家人知道,即便對同行也要三緘其口。”和魏其勇一樣,一部四室負(fù)責(zé)再入彈頭設(shè)計計算的張宏顯也從不向外界透露自己的工作內(nèi)容,只是他沒想到,日后自己會成為解決一場因保密所致矛盾的關(guān)鍵人物之一。
這件事的起因還要從1963年9月說起。
據(jù)聶榮臻之女聶力回憶,當(dāng)時主管國防尖端武器研制的聶榮臻元帥指出,我國裝備部隊的核武器,應(yīng)該以導(dǎo)彈這種運載工具作為發(fā)展方向,并要求抓緊時間,盡快協(xié)商擬定“兩彈結(jié)合”的方案。
因此,在中央專委的直接領(lǐng)導(dǎo)下,1963年,國防部五院一分院和二機(jī)部九院就開始“兩彈結(jié)合”的接觸。
1964年9月17日,中央專委對“兩彈結(jié)合”的工作作了部署,決定由二機(jī)部和國防部五院(同年年底,國防部五院更名為七機(jī)部)共同組織試驗方案論證小組,由五院的錢學(xué)森抓總。
當(dāng)時,周總理詼諧地說:“從今天起,你們‘二七風(fēng)暴就刮起來了!”
于是,九院幾位主管核裝置總體方案的設(shè)計人員來到一分院進(jìn)一步了解導(dǎo)彈的情況,雙方協(xié)商在彈頭內(nèi)安裝核裝置的要求和基本參數(shù)。一分院也抽調(diào)專人組成了“兩彈結(jié)合”小組,代號140小組。
這場“風(fēng)暴”需要解決4件大事——“小”“槍”“合”“安”。
“‘小是指原子彈的小型化,主要依靠二機(jī)部的人員來完成。”一部四室副主任王國雄對那段歷史依然記憶猶新,“‘槍就是由我們對東風(fēng)二號導(dǎo)彈進(jìn)行改進(jìn)。”
“當(dāng)時,‘東風(fēng)二號的控制系統(tǒng)像一條大尾巴,容易暴露目標(biāo)和受到干擾且移動不方便,不符合實戰(zhàn)要求。所以大家提出了‘割尾巴方案。”原航天工業(yè)總公司總工程師曾慶來說。
“東風(fēng)二號甲”在“東風(fēng)二號”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了方案性的設(shè)計修改,發(fā)動機(jī)的推力由40.5噸提高到了45噸以上,射程從1000千米提高到了1200千米,控制系統(tǒng)也割掉了“大尾巴”改成了全慣性制導(dǎo),提高了導(dǎo)彈的作戰(zhàn)性能。
一年后,“東風(fēng)二號甲”試驗成功。至此,發(fā)射原子彈的“好槍”已準(zhǔn)備妥當(dāng)。
“兩彈結(jié)合”就像一樁“婚事”,想要百年好“合”談何容易。“當(dāng)時,‘兩彈差點因保密問題進(jìn)行不下去。”張宏顯說出了當(dāng)年一件鮮為人知的事情。
“起初,我們只知道原子彈是個‘嬌小姐,具體長什么樣、到底‘嬌在哪里,我們都一無所知。對方只給了一個外形輪廓圖,連設(shè)計圖都沒讓看,具體細(xì)節(jié)更是閉口不談。”張宏顯細(xì)數(shù)起來,“核裝置要放在導(dǎo)彈頭部,它的重心、質(zhì)量、轉(zhuǎn)動慣量怎樣,需要多大空間……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了解。”
原來,“兩彈”雖然都是國家機(jī)密,但原子彈的密級更高,“所以二機(jī)部的同志不敢松口。”張宏顯回憶。
有一段時間,工作幾乎停滯。張宏顯代表七機(jī)部的科研人員將矛盾的來龍去脈寫成文字上報領(lǐng)導(dǎo),錢學(xué)森得知后立刻著手解決溝通問題。
很快,經(jīng)中央批準(zhǔn),兩家單位成立了聯(lián)合工作小組,在一定范圍內(nèi)打破了保密界限,并理順了管理渠道。
“接踵而來的問題也不少。”王國雄說,“這個‘嬌小姐既怕熱又怕冷,還怕潮、怕振動、怕過載、怕沖擊、怕靜電、怕雷電,而導(dǎo)彈卻是個‘粗漢子,搭載環(huán)境可沒那么優(yōu)越。”
為了促成“粗漢子”和“嬌小姐”的結(jié)合,可忙壞了張羅“婚事”的“紅娘們”。聯(lián)姻的兩家人都需要精心調(diào)整自家的“孩子”,以確保“拜堂”時不出任何差池。
“‘東風(fēng)二號甲的彈頭采用玻璃增強(qiáng)塑料材料作為防熱層,使殼體溫度降到100攝氏度以下,解決了‘嬌小姐怕熱的問題。”一部四室總體設(shè)計師于德濱說。
另外,當(dāng)時為了給核裝置提供飛行環(huán)境數(shù)據(jù),研制人員創(chuàng)造性地研制了硬回收裝置;給放置核導(dǎo)彈的密封艙配備了空調(diào),增加了減振和緩沖的措施。
最后一關(guān)就是“安”——“兩彈結(jié)合”的安全問題絕無退路可言。
1965年5月4日,在中央專委召開的第十二次工作會議上,周恩來總理提出了一個極其苛刻的要求:七機(jī)部要做到導(dǎo)彈在飛行中保證不達(dá)目的絕對不掉下來;二機(jī)部要做到導(dǎo)彈萬一掉下,原子彈也不能發(fā)生核爆。
事實上,這個嚴(yán)苛至極的要求是在為上萬條性命做“雙保險”。
一件可以聊幾輩子的大事
甘肅河西走廊最西端有個小鎮(zhèn)——紅柳園,如今只有為數(shù)不多的人還記得,50多年前,那兒差點發(fā)生一場涉及上萬人規(guī)模的集體大遷移。
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國家檔案館,一份編號為1559的檔案揭開了這個秘密——這是一封1966年9月被送往中央軍委的絕密電報。電報的內(nèi)容就是關(guān)于紅柳園地區(qū)的安全問題,而發(fā)出這份電報的機(jī)構(gòu)正是秘密準(zhǔn)備“兩彈結(jié)合”飛行試驗任務(wù)的酒泉導(dǎo)彈發(fā)射基地。
“兩彈結(jié)合”試驗比單純的原子彈試驗更困難和危險,在西方國家有“魔鬼的選擇”之稱。為了減少對本國的損害,美國選擇在太平洋上人煙稀少的海島試驗,蘇聯(lián)則選擇在人跡罕至的北極試驗。
當(dāng)時,由于我國尚沒有強(qiáng)大的海軍力量,所以只能選擇在自己的國土上開展試驗。
“中央要求試驗要萬無一失,出了事也不能傷及一個老百姓。當(dāng)時大家最擔(dān)心的就是彈道下面的紅柳園。這個地方有幾萬居民,我們該如何保證他們的安全?”魏其勇說。
按照理論彈道計算,紅柳園的位置是在導(dǎo)彈飛行96~102秒之間,遭遇風(fēng)險的可能性并不大。然而“兩彈結(jié)合”試驗裝載的是貨真價實的核彈頭,一旦發(fā)射失敗,這里的一切都將不復(fù)存在。
根據(jù)周總理的指示,鐵道部調(diào)集了三列火車在紅柳園待命,彈道下面的數(shù)萬名居民也已被臨時疏散到防空洞,并做好了安全救護(hù)的準(zhǔn)備。“當(dāng)時錢學(xué)森告訴總理,‘導(dǎo)彈掉在紅柳園地區(qū)的概率為十萬分之六,安全程度比坐飛機(jī)還高,大家這才寬心不少。”一部總體設(shè)計室負(fù)責(zé)控制系統(tǒng)的穆元良當(dāng)時在距離發(fā)射平臺只有160米的地下控制室,是留到發(fā)射前最后一刻的科研人員之一。言語間,他始終保持著科研人員特有的自信。
萬事俱備,中國能否擁有用于實戰(zhàn)的核武器,成敗在此一舉。1966年10月27日上午8點,距離預(yù)定發(fā)射時間還有1個小時,發(fā)射場突然狂風(fēng)大作,卷起的黃沙鋪天蓋地,能見度只有50米。
9點,大漠的風(fēng)小了,矗立的發(fā)射托架慢慢打開。突然,從發(fā)射臺下面升騰起灼眼的烈焰,東風(fēng)二號甲導(dǎo)彈托舉著核彈頭呼嘯著拔地而起,直沖云霄。
隨著導(dǎo)彈慢慢遠(yuǎn)去,發(fā)射場的每個人都心弦緊繃。導(dǎo)彈能否飛行正常,又能否按照指令在預(yù)定高度爆炸,牽動著每個人的心。
導(dǎo)彈飛行正常,9分04秒后,羅布泊彈著區(qū)傳來消息——我國首枚導(dǎo)彈核武器在飛行了894千米之后,核彈頭在羅布泊彈著區(qū)靶心上空569米的高度爆炸。
“兩彈結(jié)合”試驗取得圓滿成功!
羅布泊上空升起的巨大蘑菇云,標(biāo)志著中國成為世界上少數(shù)幾個能夠用自己的導(dǎo)彈發(fā)射核武器的國家。
那個美國用了13年、蘇聯(lián)用了6年才完成的“兩彈結(jié)合”試驗,中國僅用了2年。
如今,距離我國“兩彈結(jié)合”飛行試驗已經(jīng)過去了半個多世紀(jì),90多歲高齡的王國雄依然清晰地記得,那個晚上,他拿出此前在中南海向中央領(lǐng)導(dǎo)進(jìn)行匯報后帶回家的那一小包龍井茶,泡了滿滿一大壺茶水,和同事們一起朝圣般地將這壺茶一直喝到天亮。這一晚,他們的臉上都蕩漾著火熱的激情,如同孩子般興奮地回憶著發(fā)射當(dāng)天的每一個細(xì)節(jié)。
(選自中國航天報《共和國航天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