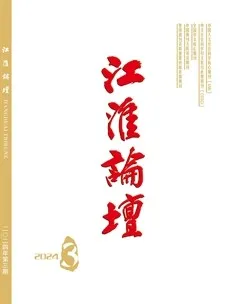柯潤璞論元雜劇的劇場性藝術特征及翻譯策略
摘要:長期以來,由于西方漢學界對中國戲曲缺乏足夠的認知以及譯介方式的問題,致使西方世界對中國戲曲形成了很深的誤解。西方當代漢學界的一些有識之士力圖改變這種誤解,美國學者柯潤璞就是其中一位代表。他在其研究中國戲曲的權威性著作《忽必烈汗時期的中國劇場》中,不僅力圖還原元雜劇的“劇場性”藝術特征,而且特別附上他本人全文翻譯的三部元雜劇《李逵負荊》《魔合羅》和《瀟湘雨》,用以說明元雜劇的“劇場”性質和特點。其中,柯氏尤其看重《瀟湘雨》一劇,認為它是反映元雜劇“劇場性”藝術特征的最佳代表,主要體現為虛擬性的舞臺表演、敘述韻文的靈活運用和“大團圓”結局及其另類處理。同時,他在翻譯時忠于原文的完整翻譯與跨文化轉化的策略,對包括元雜劇在內的中國戲曲在西方世界的傳播,作出了突出貢獻。
關鍵詞:柯潤璞;元雜劇;劇場性;藝術特征;翻譯策略
中圖分類號:J805" " 文獻標志碼:A" " 文章編號:1001-862X(2024)03-0147-008
元雜劇是中國傳統戲曲從上古發展至宋元時期集大成的產物,是“中國之真戲曲”的正式開端[1],西方世界對于中國戲曲的譯介也是從元雜劇開始的。1735年,法國神父杜哈德編輯出版四卷本巨著《中華帝國全志》,書中收錄了法國神父馬若瑟翻譯元代劇作家紀君祥的雜劇《趙氏孤兒》譯本,在西方世界引發了很大的反響。然而,馬若瑟的譯本雖然號稱“忠實”翻譯,但實際上只譯出原劇的賓白部分,而把占一半篇幅的曲詞全部刪去了。其后,西方漢學界對于中國戲曲(元雜劇)的翻譯,也基本上延續馬氏的翻譯路數,由此導致西方世界對于中國戲曲(元雜劇)的劇場性藝術特征或“真面目”的認知偏差與誤解。這一狀況引發西方當代漢學界有識之士的深切憂慮,并對西方世界對于中國戲曲(元雜劇)習以為常的無知和偏見進行質疑與更正。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就有美國當代知名漢學家柯潤璞(James Irving Crump,又譯柯迂儒)。柯潤璞是美國當代漢學界的中國戲曲研究權威和杰出翻譯家,在翻譯方面譯有《戰國策》《竹葉舟》《王九思:中山狼》等作品,在中國戲曲研究方面撰有《元雜劇的要素》《元雜劇的規律及技巧》《忽必烈汗時期的中國劇場》(1)等論文專著。《忽必烈汗時期的中國劇場》被公認是柯潤璞本人乃至美國當代漢學界對中國戲曲(元雜劇)研究的扛鼎之作。柯潤璞指出,元代忽必烈汗時期是中國戲曲發展的一個高潮,包括元雜劇在內的整個傳統中國戲劇一直都是以歌曲演戲,“在戲劇史上大概是最持久不墜的歌劇劇種”[2]177,可是這個事實卻經常被西方國家忽略。而西方對于中國傳統戲劇的根本性誤解,在于沒有認清元雜劇所代表的中國戲劇本質是“雜劇或綜合劇場”[2]178。對于元雜劇的研究,柯潤璞很明確地突出元雜劇的“劇場性”藝術特征,并把元雜劇的劇本視作整體性“劇場”的一個組成部分。為了進一步讓讀者直觀地感受和理解元雜劇的“劇場”性質及藝術特征,柯潤璞精心選譯了在他看來最能代表元雜劇“劇場性”典型特征的三部劇作《李逵負荊》《瀟湘雨》《魔合羅》作為示例。柯潤璞尤其看重《瀟湘雨》,而這一點在學界對于柯潤璞元雜劇翻譯的研究中,并沒有被專門提出和深入討論。(2)本文選取柯潤璞翻譯《瀟湘雨》為研究個案,結合其本人對于元雜劇“劇場”藝術特性的理論分析,說明柯氏選譯《瀟湘雨》的原因和用意,對照分析元雜劇原文與柯氏的英文翻譯,剖析這部作品所代表的元雜劇的“劇場”性質和藝術特征,并且揭示柯氏的翻譯策略和特點,發掘其對于西方世界的中國戲曲傳播與接受方面的獨特價值和貢獻。
一、虛擬性的舞臺表演
《瀟湘雨》由元雜劇作家楊顯之所作,主要演述了翠鸞隨父親張天覺在赴江州歇馬途中因舟覆而不幸與父親失散,被漁翁崔文遠所救并收為義女,后被嫁與其侄崔通。崔通在高中狀元之后,另娶試官之女趙氏。翠鸞千里尋夫,等見到崔通后卻被誣陷為逃婢。崔通對她進行嚴刑拷打,將其發配沙門島,并囑托解差在途中將她害死。翠鸞在發配途中于臨江驛躲雨時遇到了已升任廉訪使的父親張天覺,在父親的幫助下捉拿崔通。因為養父崔文遠的求情,重與崔通結為夫婦,并將試官女兒降為婢女。柯潤璞在《忽必烈汗時期的中國劇場》中多次以《瀟湘雨》為例,作為營造劇場效果的成功典范,說明中國元代戲劇的“劇場”性質。柯潤璞認為元雜劇之所以達到“形式與藝術的巔峰”并受到“空前絕后的歡迎”[2]3,與元代雜劇演員所具備的繁復多樣的表演技藝密不可分。誠如他所指出的“元代雜劇演員不但要會唱,而且還要輔以舞蹈,程式化摹擬動作以及起碼半打以上舞臺技巧為表演注入生命”[2]68。為此,柯潤璞在書中用大量筆墨專門探討元代優伶的技藝。在他看來,元代演員的技藝值得深入探究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元雜劇已經形成了有別于西方戲劇的獨特表演手段——虛擬性的舞臺表演。這種特殊演出技巧的背后,是中西戲劇觀念的分野。柯潤璞指出“西方戲劇在一段時間之內一直努力在舞臺上營造日常生活的幻象”[2]71,最典型的是現實主義戲劇,通過對于“細節的真實”的追求,力圖對現實世界作最忠實的描繪。而“元雜劇的舞臺指示僅僅要求差不多像人世的語氣和動作即可”[2]71。因此,柯潤璞確信“元雜劇的所有舞臺動作已高度程式化”[2]71,元代戲劇虛擬性的舞臺表演形式已經形成了體系。柯潤璞借由《瀟湘雨》論述了三種在元代戲劇中常見的虛擬性舞臺表演形式。
首先是從一地到另一地的虛擬性表演。柯潤璞指出,西方傳統的戲劇理念推崇寫實,因此舞臺布景往往是展現劇情的實景。這種再現具體場景的方式盡管能使劇情更加清晰易懂,卻“由此限制了劇中人物的自由,致使他們只能夠在‘合情合理’的空間里行動”[2]85-86。而元代的演員通過程式化的象征性動作,不需要大量的換景,就能實現從一地到另一地的“空間變換”,甚至可以取得“方寸千里,咫尺江山”的戲劇效果。為論證這一觀點,柯潤璞提醒讀者關注《瀟湘雨》第三折與第四折前段的雨中旅途,這一部分主要演的是翠鸞刺配沙門島的過程。翠鸞被解差押著從衙門出發,在風雨相催、水深泥濘中,被解差呵斥、棒打著趕路,最后在臨江驛避雨時意外與失散的父親張天覺相遇。對于劇本所描述的艱辛旅程,柯潤璞指出“這段旅程表演起來,一定斷斷續續地有各種程式化的臺步,以示路途的遙遠”[2]86。柯潤璞認為這種表演方式十分高明,不但省卻了企圖制造寫實背景的舞臺換景的麻煩,而且在與曲詞的配合下極具舞臺感染力,讓觀眾充分感知到翠鸞在發配途中所經歷的艱難險阻與悲戚無奈。
其次是特殊的虛擬性動作。柯潤璞發現在元雜劇的舞臺說明中,有幾種特殊的虛擬性動作出現頻率極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比如點燈(如《朱砂擔》)、瞎眼(如《燕青搏魚》)、撞階(如《風光好》)。(3)柯潤璞解釋了在元代戲劇中這些動作頻繁出現的原因:“元雜劇是應普通老百姓的需要發展起來的藝術形式,它并不是由富商貴族供養而來。”[2]105因此添加這些戲碼,其主要作用并不是推動情節的發展,而是為了增強戲劇性,換言之,“讓那些熱衷于觀看身段表演的觀眾看得更加滿足”[2]105。在這些高頻出現的動作中,最為觀眾所津津樂道的就是“搖船”。(4)比如在表演幾個人同登小船的情形時,操舟的主人一定要隨著客人登船的重力而搖擺和上下晃動,還得讓人信服。而登船的客人離開堅實的岸邊,登上上下浮動的想象之船的時候,他們也得隨波晃動。如果客人站在扁舟的另一端的話,擺動的韻律還必須正好與主人相反。柯潤璞指出“在傳統的中國戲劇舞臺上,這種表演是非常有看頭的”[2]91。柯潤璞以《瀟湘雨》的開場為例,分析了“搖船”的程式化動作在制造舞臺戲劇效果中的作用:張天覺因被貶謫,需攜其女翠鸞坐船橫渡淮河。他沒有采納排岸司在開船前祭祀河神的建議,觸怒了河神,因此在渡河過程中遭遇了風浪,船翻落水。翠鸞盡管被排岸司打撈上岸,卻與父親失散。在這個渡河的情境中,元代的演員開展了“登船”“船翻落水”“打撈上岸”等一系列虛擬性表演。柯潤璞認為正是由于這些與“搖船”相關的摹擬表演營造了“動人而刺激”[2]194的戲劇場面,在開場就吸引了觀眾的注意力,他相信“觀眾一定會為這種水上的摹擬表演而喝彩”[2]91。
最后是獨特的下場方式——虛下。所有戲劇傳統的上下場無一不是經過精心設計,而柯潤璞指出“元雜劇這樣以形式為主的音樂劇,處理上下場的時候更是會用心對待”[2]77。在梳理了元雜劇諸多充滿變化與想象的上下場方式之后,柯潤璞重點討論了虛下這一特殊的、程式化的下場形式。胡忌對于“虛下”的解釋是“演員背身,表示暫時下場”[3]。周貽白作了更詳盡的解釋,指出“虛下”的發明主要是為了戲劇的連貫性。比如腳色在臺上暫時沒有戲份,可接下來他又需要立即摻入唱白,上、下場會打斷劇情。在這種情況下,演員“向桌子里面的右側一站,以背部對著觀眾”,便與正在演戲的腳色隔離開來,“表示這個腳色當時并未在場上”。[4]在柯潤璞看來,這個動作最初也是最多使用的場景,是“演員從一個房間或某個地方下場而不使用到門”[2]80。隨著舞臺技術的自然演進,“虛下”用以處理更多復雜的情境,比如夢境、指示時光的流逝等。柯潤璞以《瀟湘雨》為例,證明通過“虛下”,元朝劇場已經可以處理兩組人物同時在臺上的兩組交錯的場景。在第四折里,流配途中披枷戴鎖的翠鸞與父親張天覺同宿臨江驛,二人卻都不知道親人就在身旁。老邁、沮喪的父親在驛館里為女兒的失散而憂傷,而走散的女兒在同一家驛館外唱出了她的無望與無助。柯潤璞高度評價這一戲劇場景“不論是營造戲劇幻覺的西方劇場還是中國式的空舞臺,都能營造出很好的戲劇效果”[2]193。他設想如果按照西方劇場的方式,驛館的內、外都要用實景布置,而且當父親、女兒分別表演時,要充分調動舞臺燈光凸顯正在道白或吟唱的人物。柯潤璞說“我確信這樣做會很有效”,但是他話鋒一轉指出“少了一套空場子的表演傳統,就得多出一套轉來轉去的麻煩”。[2]84如果用“虛下”的方式處理,只需要一組人物表演時,另一組人物背過身去即可。柯潤璞對這種簡單有力的表現方式十分贊賞,認為“在空蕩蕩的中國舞臺上”,“虛下”是“非常巧妙的舞臺運用”。[2]79
柯潤璞通過對《瀟湘雨》中三種虛擬性的舞臺表演形式的分析,點明了中國戲曲不同于西方戲劇追求真實的“舞臺幻覺”的藝術特質,強調了元代戲劇“戲是藝術,而非真實”的“劇場”性質,以及虛擬性的舞臺表演在營造劇場效果中的巨大作用。事實上,除了高明的舞臺表演技巧,優美卓越的曲詞在良好的劇場效果上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敘述韻文就是其中一例。
二、敘述韻文的靈活運用
柯潤璞借由《瀟湘雨》說明元代戲劇的“劇場”性質時,高度評價其中的曲文,稱贊它們不僅自身具備極佳的文學性,在表現戲劇效果方面也發揮了極大的功用,其中最讓柯潤璞贊嘆的就是敘述韻文。柯潤璞在閱讀《元曲選》時注意到,里面經常出現的舞臺說明“詞云”中的“詞”并非指宋詞,而是一種松散的“敘述韻文”。它與“用文言文的單音韻律組合而成”的古老韻文形式“唐詩、賦、宋詞”不同,采用的是“各式各樣的多音韻律”,這些多音韻律“由非重讀和輕讀的字群組成”,類似于英語的“抑揚格無韻詩”。[2]129柯潤璞認為,這種敘述韻文“是由金元劇作家發明的”[2]129,發明的初衷是“以娛樂觀眾,掌握觀眾為最主要的著眼點”[5]135。柯潤璞指出,這種彈性的韻文能“充分發揮漢語口語的優勢”[2]129,出之以念誦,更易于使當時的觀眾通曉領會,“歌唱的曲詞便不一定能有此效果”[5]144。柯潤璞將能否熟練地運用韻文作為衡量劇作家能力的重要指標,而《瀟湘雨》的作者在這個方面無疑十分出眾。對此,柯潤璞評價道:“縱觀《瀟湘雨》之后百年的雜劇作品,這樣的成就并不多見。”[5]144《瀟湘雨》對于敘述韻文的成功運用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敘述韻文用在嚴肅的對白當中。敘述韻文在元代戲劇單口的插科打諢中使用頻率較高,而極少用在嚴肅的對白中。柯潤璞強調,在全部的嚴肅對白場景里,所有演員都用敘述韻文的僅見于《瀟湘雨》。[2]130劇中第四折翠鸞刺配途中在臨江驛偶遇父親的情境,不僅是主角翠鸞,其他配角也皆以敘述韻文對話,而且全部押的是同一個韻。在這種嚴肅的情境之下將敘述韻文用到如此地步,無疑十分考驗劇作家的功力。柯潤璞十分欣賞這部分敘述韻文的使用:“詞中始終押魚模韻,長短句相間,劇中板式的變化,以及敘戲劇場面之情而不敘普遍化之情等,均是特出之點。”[5]144
第二,敘述韻文由多人念誦。早期的元雜劇有一個成規,就是“無論哪一折都只有一人主唱”[2]188。柯潤璞指出了這個規定的局限:整折的表現全部集中于一人,“故事既不能有突然的轉折,觀眾的注意力也始終膠著于一處”[5]134。隨著中國戲曲的發展演進,元代之后多人演唱成為主要趨勢。而《瀟湘雨》正是代表了元雜劇從“一人獨唱”走向“多聲合奏”的努力與探索。比如,劇中第二、四折,有兩首加插的曲子[醉太平],其演唱者分別為試官與搽旦,打破了由正旦(唱角)獨唱的限制,顯示了“劇作家在靜態,不具戲劇成分的獨唱曲中引入劇場機趣之流動的努力”[5]144。柯潤璞指出,更引人注目的是“在第四折里舞臺上的所有角色皆以韻文交流”[2]193。廉訪使張天覺夜宿臨江驛時在夢中被哭聲吵醒,于是他教訓了貼身侍衛興兒,興兒教訓了驛丞,驛丞教訓了解差,解差教訓了發出哭聲的翠鸞。在這個情境中,所有層層向下的打壓皆通過敘述韻文生動地呈現出來,反映出“官大一級壓死人”的元代吏制的腐敗。更令柯潤璞贊嘆的是這里敘述韻文的使用:“元雜劇的每一折都是由套曲組成,套曲的其中一個特性就是一折中所有的曲子都是一韻到底。在第四折劇作家創造出一套‘多聲部的’‘敘述的’韻文,它的大部分特征很像‘單獨一人’‘主唱’的套曲。據我所知,《瀟湘雨》是唯一一部把敘述韻文運用得如此極致的元代戲劇,它代表了同時代極其先進的創作技巧。”[2]193-194
第三,敘述韻文強烈的藝術感染力。柯潤璞認為,盡管敘述韻文可用于“單口的插科打諢”“重述重點”“大結局的亮相”[2]129-130等地方,但是從比較高的藝術層面來看,“韻文敘述可以是抒情而動人的”[2]131。比如在《瀟湘雨》中,張天覺思念女兒的情境。張天覺夜宿臨江驛,在夢里與失散的女兒翠鸞重逢。從夢里驚起后,聽著窗外的疾風驟雨,他又不由自主地想念起女兒,不知她是生是死,身處何方,心中泛起凄楚悲涼的情感:
[張天覺云]翠鸞孩兒。只被你痛殺我也。恰才與我那孩兒數說當年淮河渡相別之事。不知是什么人驚覺我這夢來。
[詞云]一者是心中不足。二者是神思恍惚。恰合眼父子相逢。正數說當年間阻。忽然的好夢驚回。是何處凄涼如許。響叮當鐵馬鳴金。只疑是冷颼颼寒砧搗杵。錯猜做空階下蛩絮西窗。遙想道長天外雁歸南浦。我沉吟罷仔細聽來。原來是喚醒人狂風驟雨。我對此景無個情親。怎不教痛心酸轉添凄楚。孩兒也。你如今在世為人。還是他身歸地府。也不知富貴榮華。也不知遭驅被擄。白頭爺孤館里思量。天哪。我那青春女在何方受苦。[6]259
柯潤璞注意到這一段中用了不少襯字,“如‘也不知’‘只疑是’等,大部分出現在句首;‘天哪’則是獨立的感嘆詞”[2]132。這些句首套語和感嘆詞在敘述韻文中的使用,強化了語言的節拍與韻律感,使得張天覺在此處所抒發的孤苦凄涼、對女兒的思念之情更加動人,在劇場表演時能夠充分地調動觀眾情緒,達到更好的戲劇效果。
柯潤璞探究了《瀟湘雨》中在嚴肅對白場景里對敘述韻文的使用,以“多人念誦”敘述韻文來豐富“一人獨唱”的嘗試,以及卓越的敘述韻文本身傳達出的“抒情而動人”的藝術感染力。這些無不說明元代劇作家在“保持元劇結構謹嚴精密特色”的前提下,“在規律的運用上求變化”,以“達到強烈的戲劇效果”的努力。[5]140此外,元代劇作家通過靈活地運用規律技巧以增加戲劇表演的變化與吸引力,不僅體現在敘述韻文的運用上,還體現在結局的另類處理上。
三、“大團圓”的結局及其另類處理
柯潤璞在說明《瀟湘雨》所代表的元雜劇“劇場”性質及特點時,還特意分析了其非同尋常的“大團圓”結局。中國的傳統戲曲往往以大團圓的方式結局,如王國維所說“始于悲者終于歡,始于離者終于合,始于困者終于亨”[7],這是國人樂天精神的反映。《瀟湘雨》從表面上看的確是這種“父子和夫妻兩事兒全”[6]262的“大團圓”結局。最終張翠鸞和崔通重修舊好,與失散的父親張天覺團聚。但是,這種光明結局下的隱痛卻始終讓人無法釋懷:崔通富貴易妻,想致結發妻子于死地,這樣一個陰毒勢利的小人在最后卻未受懲罰,還通過婚姻攀附了更高的權貴;試官之女趙氏,在不了解崔通已婚以及對于翠鸞沒有刁難的情況下卻受到了懲治,成為翠鸞的婢女;翠鸞與崔通重歸于好,并非出于真心,而是出于“一女不嫁二夫”的觀念以及為報答崔文遠救命之恩而不得已進行的妥協。綜上所述,惡人不但未受懲治還有飛黃騰達之勢,無辜之人受到懲罰,被損害者作出妥協。這種結果并沒有傳統的“大團圓”結局“大仇得報,懲惡揚善”的大快人心之感。而且,這部劇的結局在表面上的一團和氣之中,也存在著一些不和諧的聲音,柯潤璞指出了這部劇結局的“不尋常”及其成因。
首先,《瀟湘雨》“直至最后一刻人物之間才倉促草率地和解”,“結局的諷刺以一種蒼白無力的形式呈現出來”。[2]194-195的確,前期崔通冤枉翠鸞偷竊,對她刺字拷打,發配至偏遠地區,要置她于死地。然而,人物之間尖銳的矛盾與戲劇沖突在最后突然以“大團圓”的方式消解了,這種結果并不符合劇情發展的邏輯。事實上,很多學者都對《瀟湘雨》的“大團圓”結局提出過類似批評。比如,日本學者青木正兒認為《瀟湘雨》整部作品是“元劇中杰作之一”,唯獨結尾是敗筆:“但其收場繁瑣,是失敗了。”[8]鄧紹基進行了更為細致的分析:“這種(大團圓)結局投合了一種民間心理,但使被損害者作出妥協,惡人不受懲罰,卻又與長期存在的‘善惡相因’的觀念相悖,因此,這個劇的結局總顯出某種不自然。”[9]概而言之,學者們普遍認為這個結局有不妥之處。盡管從情節發展的角度,柯潤璞也承認這種強行制造“大團圓”的結局尷尬而又勉強,但他從劇場維度對于為什么該劇會安排這種“大團圓”結局作出了解釋:幾乎每一出元劇都要來上這么一個結局,以展現其排場或是制造群像之類的場景。[2]173柯潤璞強調“在成熟定型的元代戲劇中,劇終的全體亮相是所有作品的一個特征”[2]173,不論這個作品是神仙劇、社會劇還是其他哪種類型的戲劇。比如《李逵負荊》的最后場景是大宴群雄,而《摩合羅》則是賞罰眾人。元雜劇通常在第四折最后一景安排劇中人集體亮相,這樣的成規想必跟觀眾愛看大排場的因素息息相關。[2]173因此,從元代戲劇劇場性的角度考慮,《瀟湘雨》結局安排眾人一起上臺舉杯慶夫妻團圓,其目的是營造最后壯觀的戲劇場面。既然觀眾喜歡這種歡樂熱鬧的氛圍,劇作家也樂于投其所好。
其次,在傳統“大團圓”結局一片祥和的氛圍里,存在著不協調的聲音。柯潤璞指出:“在劇中搽旦(被打做梅香,服侍小姐)說的話聽起來令人震驚。”[2]195她說:“我老實說。梅香便做梅香。也須是個通房。要獨占老公。這個不許你的。”[6]261柯潤璞評價道:“我們已經習慣了松糕軟糖式的大團圓結局,卻在此處突然碰到一把尖刀!”[2]195搽旦也就是試官之女趙氏,面對自己所受到的無辜懲罰,并沒有選擇逆來順受,而是大聲宣泄出心中的不滿。除了以上柯潤璞所提到的,她還說:“一般的父親。一般的做官。偏他這等威勢。俺父親一些兒救我不得。”[6]261她所抒發的憤怒,刺破了一團和氣的氛圍,直指元代官場的腐敗與女性婚姻的不易這些黑暗的社會現實。事實上,這種結尾的不平凡歸功于劇中次要角色的另類處理方式。顯然,劇作家對于試官之女趙氏這個次要人物,并沒有處理成一個簡單扁平的形象,相反她被塑造得膽大潑辣,敢于質疑權威,極富魅力。除了搽旦,解差這個角色也引人注目。柯潤璞指出,在元雜劇中多數時候仆人、衙役或下屬不是一味地狡詐粗暴就是全然地不公不義,但是在翠鸞凄苦的旅途上,押她的解差卻具有非比尋常的包容性。他雖然打翠鸞催她快點趕路,但也責怪做官的不公正,害的翠鸞落到如此地步;他對翠鸞固然很惱火,卻把有限的食物分一些給她——事實上,后來他似乎把整個燒餅全給了她。[2]194解差作為一個次要角色,其性格卻充滿復雜矛盾,他雖然粗暴但是卻也有正義心和同情心。正是搽旦、解差這些飽滿立體的次要人物角色的塑造,強化了戲劇的張力,使得演員在劇場詮釋這些角色時更能吸引觀眾的注意力。柯潤璞對此高度評價:“此劇的作者,并不滿僅守著規定做一名出色的工匠;他要的是把成規推展到極限而且讓觀眾接受他的做法。這往往就是天才有別于通才之處。”[2]195
四、忠實于原文的翻譯和跨文化轉化
柯潤璞在向西方譯介元雜劇時,指出過去西方世界在接受中國戲劇時對其本質認識不清,經常存在一些偏見與誤解。在他看來,對于中國戲劇的這些謬見顯然與譯介有直接關聯。西方學者在翻譯中國戲劇時經常進行節譯或者改譯,致使西方世界無法獲知劇本全貌,進而對中國戲劇形成各種誤解。針對這種情況,柯潤璞在充分把握元雜劇的“劇場性”前提下,在對《瀟湘雨》進行譯介時,采取了兩條翻譯策略。
第一,忠實于戲劇原文的完整翻譯。在中國戲曲的海外譯介史上,由于對曲律與規則缺乏足夠的認知與了解,在譯介時經常會出現只譯賓白而不譯曲詞的情況。比如在18世紀,法國傳教士馬若瑟將紀君祥的《趙氏孤兒》譯為法文,但他僅僅是出于輔助研究近代中國口語的目的,翻譯了賓白的部分,唱詞則因極其艱澀,且對這一目的無所幫助,而被完全忽略(或許馬若瑟也并不知道該如何著手翻譯唱詞)。[10]149又如在19世紀,英國的戴維斯爵士(John Francis Davis)是英譯雜劇的第一人。他在翻譯出版馬致遠的《漢宮秋》時,也如同之前的馬若瑟一樣避開曲詞。[10]150柯潤璞認為這種“避開曲詞”的做法忽視了中國戲曲的歌舞性源流,最重要的是脫離了中國戲曲的“劇場性”本質。柯潤璞舉例美國一些劇團在表演中國戲劇時,由于對曲詞的無知,“像演西方話劇一樣,照著他們的舞臺規范一板一眼地搬”[11]167。這樣做的后果,是使演出效果大打折扣,西方觀眾無以真正領會中國戲曲在劇場中的獨特風貌。為了使國外的讀者、觀眾了解中國戲曲的“真面目”,柯潤璞在翻譯《瀟湘雨》時力求譯文的準確與完整,比如第三折在凄風苦雨中翠鸞被解差呵斥、棒打著趕路的情形:
[解子云]快行動些。這雨越下的大了也。[正旦唱]
[喜遷鶯]淋的我走投無路。知他這沙門島是何處酆都。長吁。氣結成云霧。行行裹著車轍把腿陷住。可又早閃了胯骨。怎當這頭直上急簌簌雨打。腳底下滑擦擦泥淤。
[正旦做跌倒科][解子云]你怎么跌倒了來。[6]255
柯潤璞將其翻譯為:
GUARD:
Move along faster,the rain grows worse all the time.
(Hsi Ch’ien-ying 46247344)
TS’UI-LUAN:
(sings)
So great
The rain I’ll never reach a refuge.
(Who knows
Which of Hell’s gates is found on Shamen Island?)
Alas,Alas!
The very air condenses into cloudy brume.
As I walk,
Drowned wheelruts work pitfalls to trap and seize my legs.
And soon will
Wrench a thighbone from its socket.
How will I stand either
The gleaming,streaming rain upon my head
Or the sliding,subsiding mud beneath my feet?
(pantomimes slipping and falling)
GUARD:
Now why did you fall?![2]283
由以上例子可見,柯潤璞的翻譯確實十分完整。不僅將賓白和科介都精當而流暢地翻譯出來,而且其中的曲詞也被翻譯為英文唱詞,被無分軒輊地納入譯文中。在翻譯《李逵負荊》和《摩合羅》時,柯潤璞同樣謹守忠實于原文的全文翻譯原則。以《李逵負荊》首折李逵出場一段為例。原劇腳本有賓白、唱詞以及人物動作提示,柯氏的英文翻譯不僅譯出賓白(云),而且把元雜劇的主體部分諸宮調曲牌翻譯為英文唱詞,甚至演員在臺上表演時應有的動作(科),也完全按照原劇“忠實完整”地譯出,力圖使外國讀者認識到元雜劇作為“雜拼的戲”的綜合性藝術本質。事實上,為了使翻譯更加準確完整,柯潤璞對元曲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比如他在1958年發表的論文《元曲的要素》不僅討論了元曲的結構、內容、來源等方面,而且還介紹了研究元雜劇需要的資源。又如1971年的論文《元雜劇的規律及技巧》研究了元雜劇中曲律的元素、襯字和曲牌的變化。此外,他還將目光拓展到元散曲研究。論文《翻譯“散曲”》(1979)以及專著《上都樂府》(1983)、《上都樂府續集》(1983)中涵蓋了與元散曲有關的豐富的研究主題,其中就包括對曲牌韻律的研究。
第二,跨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在柯潤璞力圖向西方世界介紹說明中國戲曲的“劇場性”特征時,翻譯中所遇到的最大挑戰便是其中的音樂。因為雜劇腳本流傳下來的是文字,而音樂久已失傳,本來已知的規則就十分有限,譯介時如何傳達其中所包含的音樂性韻律,對于西方譯者而言無疑是不小的挑戰。而另一個挑戰涉及文化差異的問題。翻譯是“一種跨文化交流的實踐活動”[12],當在一種文化環境中產生的作品被“移植”到另一種文化環境中時,為了使譯作產生與原作相同的藝術效果,譯者就必須在譯語環境里找到能激發接受者產生相同或相似聯想的手段。因此,翻譯不是原作外形的簡單變易,而是充分把握原作精神的“二度創作”。這無疑十分考驗柯潤璞的母語文化功力,為此,柯潤璞采取了跨文化的創造性轉化的策略。他受到鄭騫對北曲曲律研究的啟發,并吸收了弟子章道犁(Dale Johnson)關于元曲韻律和結構的研究成果,創制了用英語詩歌韻律轉換元曲的獨特翻譯方式,具體的操作是:把元雜劇唱詞中的非韻律詞和基礎詞分開,并將非韻律詞去掉,只剩下基礎詞計數。結果是元雜劇中的同一個唱腔都顯示有同樣數量的基礎詞。比如《瀟湘雨》中第一折正旦翠鸞出場所唱的[仙呂點絳唇]:
舉目生愁。父親別后難根究。這一片悠悠。可也還留得殘生否。[6]248
柯潤璞對這個唱腔進行了翻譯與分析:
(Hsien-lü[mode name], Tien Chiang Ch’un[tune pattern],44345[scansion])[2]186
(sings)
I raise my eyes and worry fills them.
Father, now that you are gone,
Can I trace you?
Oh, the long, long river,
Has it drowned the years you had left to live?[2]255
柯潤璞標示出了這個唱腔由行數和基本音節數組成的公式(44345),這一公式的具體含義是“這一唱腔有5行組成。前2行有4個韻律節拍,第3行有3個,第4行有4個,第5行有5個”。[2]186柯潤璞將這個韻律公式運用到英文翻譯上,就是“每一行的英語重音數量與韻律所要求的音節數量相同”[2]186。他在翻譯《摩合羅》時,采用了同樣的轉譯手法。比如,《摩合羅》的楔子,也就是正末李德昌出場唱的[仙呂賞花時],柯潤璞在英文翻譯中,采用了音節轉換公式,并備注了“77545”[2]313的數字。第一折李德昌挑擔出門,路遇大雨,唱[仙呂點絳唇]和[混江龍],柯潤璞的英文翻譯,同樣對應標出了“44345”和“474477”[2]317的音節數字公式,并且把這一原則貫穿于《摩合羅》全文翻譯的始終。可以說,柯潤璞所嘗試的這種在中西異質文化之間進行跨文化轉化的創造性翻譯策略,不僅反映出原作的創作意圖,而且“讓英文讀者感覺在讀一種地道的語言”[13] 。
柯潤璞的翻譯在西方世界產生了很大的反響。他的英文功底深厚,早年浸淫西洋古典作品,所受影響頗深,使用英文生動活潑、簡潔有力。[11]vi:讀者的感謝漢學家白芝(Cyril Birch)認為他的翻譯具有“完整、準確和無與倫比的誠實的偉大美德”[2]verso。漢學家杜威廉(William Dolby)高度評價他的譯文,認為“他的譯文充滿活力,十分通俗,而且很適合演出。他有時會譯出歌曲的韻腳,并且還是在不扭曲句法的前提下進行巧妙地處理”[14]。當然,柯潤璞翻譯的價值并不止于他對于譯文的處理。而是借由這些劇本,使西方的讀者抑或是觀眾領會到中國戲劇作為一種綜合性劇場藝術的真正魅力。
綜之,柯潤璞十分推崇元雜劇,更是多次援引以論證自己的觀點。他之所以不遺余力地向西方推介《瀟湘雨》等元雜劇,關鍵原因就在于柯潤璞認為它們最能凸顯元雜劇的“劇場”性質和藝術特征。他討論了元雜劇虛擬性的舞臺表演形式,并指出該形式表征著與西方傳統戲劇追求逼真的戲劇幻覺理念的根本分歧。通過對于作品中敘述韻文的靈活運用以及對“大團圓”結局的另類處理的分析,表明了元代的劇作家為了強化戲劇的舞臺效果,增強戲劇的可看性與吸引力,在規律的應用上求新求變的努力。同時,柯潤璞對于《瀟湘雨》等元雜劇準確而完整的翻譯,以及他所采用的創造性轉化翻譯策略,對于扭轉西方的中國戲曲認知有直接幫助。這些對于包括元雜劇在內的中國文化的海外傳播具有示范性作用。
注釋:
(1)柯潤璞的專著Chinese Theater in the Days of Kublai Khan,臺灣學者魏淑珠將書名翻譯為《元雜劇的戲場藝術》,主要基于接受對象是中文讀者,因而采取翻譯中的“歸化”策略。而本文寫作時對該書的書名采用了直譯的方式,譯為《忽必烈汗時期的中國劇場》,認為這樣更加貼近題名原義。
(2)海外漢學界對于柯潤璞的元雜劇翻譯研究,主要集中于對《忽必烈汗時期的中國劇場》這部書的評述。杜威廉、白芝、章道犁、姑蘭(éva Kalmár)、喬治·海登(George A.Hayden)、杰羅姆·西頓(Jerome P.Seaton)等學者都曾對該書進行評點,但是多數書評較為簡略,一般是簡述該書每章的要點,肯定了他對于三部元雜劇的譯介,并指出該書對于中國戲曲研究的里程碑作用。其中喬治·海登的評析最為全面,他細致地評述了柯潤璞在書中提出的重要觀點。比如注意關于元雜劇起源的“飛地說”;肯定了他對于元雜劇劇場性的強調;指出其翻譯應當更凸顯諷刺性,畢竟幽默是元雜劇最有魅力的特征之一。參見George A.Hayden:Review on Chinese Theater in the Days of Kublai Khan.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81(2):663-669.而章道犁則比較中肯地指出了柯潤璞翻譯中的得失,尤其是在韻律方面。參見Dale Johnson:Review on Chinese Theater in the Days of Kublai Khan.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83(2):380-384.但是他們并未點明三部元雜劇的選譯緣由是為了論證元雜劇的“劇場性”,以及在論證該觀點時對于《瀟湘雨》的反復援引與特殊關注。
(3)更多關于元雜劇中出現頻率極高的虛擬性舞臺動作的案例,參見魏淑珠譯:《元雜劇的戲場藝術》,巨流圖書公司2001年版,第91-102頁。
(4)柯潤璞提醒讀者注意,在《元曲選》中許多與搖船相關的場景:《來生債》的第三折全部與《楚昭公》的第三折大部分都是在狂風驟雨的船上發生的。《岳陽樓》中郭馬兒與正末上船,郭推正末入水;《青衫淚》中舞臺說明要一艘船靠近另一艘;《竹葉舟》中漁翁撐船上舞臺,渡一個客人,后來客人墜水;《城南柳》中有艘漁船流下來,凈纜住船,兩人在船上穿脫蓑衣。以上參見魏淑珠譯:《元雜劇的戲場藝術》,巨流圖書公司2001年版,第93頁。
參考文獻:
[1]王國維.宋元戲曲考[M]//姚淦銘,王燕,編.王國維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360.
[2]J.I.Crump.Chinese Theatre in the Days of Kublai Khan[M].Tucson: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80.
[3]胡忌,選注.古代戲曲選注(二)[M].北京:中華書局,1960:34.
[4]周貽白.中國戲曲論集[C].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60:172.
[5][美]柯迂儒,廖朝陽.元雜劇的規律及技巧[J].中外文學,1980(3):126-148.
[6][明]臧晉叔,編.元曲選(第一冊)[M].北京:中華書局,1958.
[7]王國維.《紅樓夢》評論[M]//姚淦銘,王燕,編.王國維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10.
[8][日]青木正兒.元人雜劇概說[M].隋樹森,譯.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7:61.
[9]鄧紹基,主編.元代文學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195.
[10][荷]伊維德.元雜劇——譯本與異本[J].凌筱嶠,譯.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015(2):147-165.
[11][美]柯潤璞.元雜劇的戲場藝術[M].魏淑珠,譯.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1.
[12]謝天振.譯介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1.
[13][美]杰夫·凱勒.柯潤璞與中國口述表演文學研究[J].吳思遠,譯.中華戲曲,2015(1):1-19.
[14]William Dolby.Review on Chinese Theater in the Days of Kublai Khan[J].Theatre Research International,1981(2):146-147.
(責任編輯 黃勝江)
本刊網址·在線雜志:www.jhlt.net.cn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外戲劇經典的跨文化闡釋與傳播研究”(20amp;ZD283)
作者簡介:范方俊(1969—),安徽蚌埠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歐美文學與中西比較戲劇;范寧(1992—),女,河北張家口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歐美文學與中西比較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