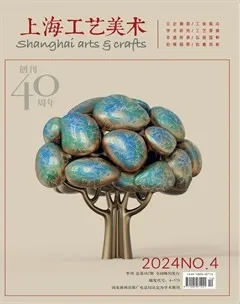島岡達三陶瓷裝飾藝術語言的生成與發展


Tatsuzo Shimaoka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ceramists inthe modern Japanese Folk Art Movement. Jomon mosaicceramic decorative art language, originated by himself, baseson materials and techniques of Mashiko Pottery, and blendsJomon decoration of ancient Japanese pottery with ceramicmosaic decoration techniques of Joseon Dynasty.
島岡達三(Tatsuzo Shimaoka)是近代日本民藝運動中具有代表性的陶藝家之一,其獨創的繩紋鑲嵌陶瓷裝飾藝術語言,基于益子陶藝的材料和工藝技法,融合了日本古代陶器的繩紋紋飾與李氏朝鮮時期的陶瓷鑲嵌裝飾技法。繼濱田莊司(ShojiHamada)之后,島岡達三成為推動民藝陶器發展的關鍵人物,并于1996年被認定為日本重要無形文化遺產(民藝陶器·繩文鑲嵌)的持有者。
島岡達三的繩紋鑲嵌陶瓷裝飾藝術語言充分展現其個人風格,自20世紀50年代誕生直至20世紀80年代,主要以繩紋紋飾和鑲嵌裝飾技法為核心,輔以多樣的釉料、燒成工藝及陶瓷彩繪等工藝技法。隨著其陶藝創作的深入發展,創作使用的工具、材料、釉料、燒成工藝以及作品的表達方式,均展現出多元化的趨勢。島岡達三通過不斷探索與發展繩紋鑲嵌陶瓷裝飾藝術語言,向使用者傳達其陶藝作品所蘊含的樸實無華與健康之美的民藝理念。
一、島岡達三陶瓷裝飾藝術語言的生成
(一)民藝運動的影響
1939年,島岡達三在日本東京工業大學窯業系學習期間,首次接觸到民藝的理論概念。在此期間,他參觀日本民藝博物館,被其間收藏的眾多民藝工藝品和民藝陶器作品打動,并且萌生出在未來進行有關民藝陶器創作的愿景。
縱觀島岡達三創作的所有繩紋鑲嵌陶藝作品,均以民眾日常使用的實用器皿造型作為主體。日本民藝運動以柳宗悅所提出的“民眾性的工藝”概念為理論依據,旨在振興民藝所倡導的“健康之美”,并圍繞民藝工作者展開。然而在實踐過程中,依舊存在諸多矛盾,其中較為明顯的矛盾在于本應該由無名工匠制作的實用器物,實際上卻是由著名的個人作家所實現。這種現象看似與民藝的理念相悖,但不可否認的是,正因為有這些著名個人作家的存在,民藝運動才得以更具說服力和影響力。
柳宗悅在《民藝論》中明確定義了無名工匠和著名個人作家之間的關系:“這一問題跟宗教問題雷同。如果沒有充分理解信徒信心的僧侶們為中介,信徒們將會迷失道路。工匠與作家的關系,跟這種關系沒有什么不同。”著名個人作家依據民藝的理論,指導眾多無名工匠在制作民藝工藝品時把握正確的創作方向。無名工匠的實踐經驗也保障著名個人作家的民藝理論能夠成功轉變為實際的民藝工藝品。因此,可以看出無名工匠與著名個人作家之間實際是相輔相成的關系。
同時,柳宗悅也在《民藝論》中闡述:“作品若要貫徹民藝的美學理念,需要建立起以個人作家為主導的合作關系,并結合當地產區的傳統材料與工藝技法,進行因地制宜的創作。”島岡達三遵循這一指導思想,畢業后扎根益子,學習當地傳統的陶藝知識,積累豐富的實踐經驗,并將民藝的美學理念貫徹于其未來的創作之中。
由此可見,民藝不僅深深觸動了島岡達三的內心,其更深層次的意義在于,憑借民藝的美學理念以及多年對益子傳統材料和工藝技法的執著堅持,為他往后的民藝陶器創作道路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二)濱田莊司與益子陶藝
1946年,島岡達三正式拜入濱田莊司門下。在老師濱田莊司的指導下,島岡達三深刻意識到,學校所學習的陶藝理論與實際創作民藝陶器之間存在顯著的差異。濱田莊司主張在創作過程中,創作者應該跨越已知的理論和工藝技法框架,探索潛意識中所蘊含的“自然之美”。盡管濱田莊司強調創作方式應該源自無意識的表達,實則是提倡將有目的與無意識的創作建立起對立統一的關系。如果創作者拘泥于有目的性的創作,其作品所展現的觀感往往顯得生硬且不自然。這樣的創作違背于民藝向民眾傳遞“自然、健康之美”的理念。創作者通過持續的練習,達到在制陶過程中無需思考即可呼之欲出的肌肉記憶,從而在無意識的狀態下創作出符合民藝“自然、健康之美”的陶藝作品。
島岡達三在老師潛移默化的熏陶下,開始摒棄在大學期間所學的理論知識,轉而依靠反復的陶藝實踐進行創作。由此可見,創作者在民藝陶器的創作中,不應局限于理論指導,更應身體力行地實踐。相較于工藝技法的理論,通過肌肉記憶所引發無意識的“健康之美”才更契合民藝所提倡的主旨。
通過對益子陶藝的深入學習,島岡達三精通了如何運用當地產區特有的制陶材料和工藝技法,在日后為其陶瓷裝飾藝術語言的生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石。無論其陶瓷裝飾藝術語言如何變化與發展,將益子當地用作化妝土的白泥和地釉澆于器皿坯體的表面,再通過傳統的登窯燒制,這一過程始終是島岡達三內心深處對陶藝創作的初衷。
(三)創造繩紋鑲嵌裝飾技法
直至1954年,島岡達三在益子定居,并建立自己的工作室。由于和濱田莊司同居益子的原因,老師常會在出窯時前來審視他的陶藝創作。濱田莊司過于廣泛的創作領域成為島岡達三早期創作中難以逾越的壁壘,因此他的早期陶藝作品都與老師保持高度的一致性。濱田莊司為此不斷督促他在創作中展現個性,探索自己的創作風格。這成為促使島岡達三創造繩紋鑲嵌陶瓷裝飾藝術語言的關鍵因素。
島岡達三開始嘗試運用多種工藝技法進行陶藝創作。1949年,在木縣窯業指導所工作期間,他接受一份委托,與老師濱田莊司共同復刻日本繩紋和彌生時期的古代陶器,用作學校所需的教學樣本。為了深入了解日本古代陶器,濱田莊司和島岡達三拜訪多所大學的研究所,并參觀了眾多的美術館和博物館。在考古學家山內清男的幫助之下收集到大量與日本古代陶器表面繩紋圖案相關的文獻資料。
受到這段經歷的啟發,島岡達三最終將目光聚焦到古代陶器表面的繩紋紋飾和感興趣的李氏朝鮮時期陶瓷鑲嵌裝飾技法上。將這兩種元素融合于自己創作中的關鍵,在于他身為編繩師的父親所制作的編繩。島岡達三采用滾動按壓編繩的方式,在還未干燥的器皿坯體表面壓出凹痕,隨后用益子的白色化妝土填入凹痕并進行打磨。通過與多樣化的釉料、燒成方式和陶瓷彩繪的巧妙結合,島岡達三創造出了具有鮮明個人特色和代表性的繩紋鑲嵌裝飾技法,以及獨特的陶瓷裝飾藝術語言。
二、島岡達三陶瓷裝飾藝術語言的發展
從島岡達三陶瓷裝飾藝術語言的發展歷程中不難發現,其創作始于20世紀50年代。然而,在這個時期未使用繩紋鑲嵌裝飾技法的陶藝作品占據了相當大的比例。經過大量的創作實踐,島岡達三終于在1960年前后成功確立了自己獨特的陶藝風格。至20世紀60年代末期,盡管島岡達三保持了其陶藝作品完整度,但各式各樣繩紋紋飾和鑲嵌裝飾圖案的組合仍展現了一種階段性的嘗試實驗表現。
直至20世紀70年代,島岡達三通過不斷的創作實踐,成功克服了燒成過程中不同化妝土與泥料鑲嵌后收縮率差異的難題,從而使其鑲嵌裝飾技法能夠與繩紋圖案達到完美的結合。隨著創作的不斷深入,島岡達三在制陶材料的選擇和工藝技法的應用上,不再局限于益子當地。他所使用的坯體泥料從益子拓展至日本的其他陶瓷產區,包括備前、信樂等地。鑲嵌在繩紋圖案凹痕內的化妝土,也從單一的白色發展出多種彩色化妝土。
在釉料的選擇上,島岡達三以自行配制的地釉作為基礎,發展出更多樣的選擇。從創作早期與益子褐色色系的顏色釉搭配組合,到后期越來越多鮮艷的顏色釉開始逐漸出現。
在燒成工藝的選擇上,島岡達三從傳統的登窯燒制出發,演變出多種燒成工藝,包括鹽釉燒成和窯變燒成。其中鹽釉燒成以其艷麗的顏色,體現了島岡達三陶瓷裝飾藝術語言對色彩表達的極致追求。窯變的燒成則是因長時間的高溫燒制,使得器皿的造型產生變化。同時,溫度、火痕以及燒制時窯內氣氛不同的微妙差異,共同影響了器皿表面的色彩以及繩紋鑲嵌裝飾圖案的變化。窯變燒成不僅展現了島岡達三對其陶瓷裝飾藝術語言不斷探索和發展。而且正是由于這種多元化的裝飾技法組合,島岡達三的陶瓷藝術語言得以發展并逐步走向成熟,造就了其創作風格的獨特性。
綜上所述,島岡達三的創作發展過程與大多數現代陶藝家存在顯著差異,其創作風格也并非隨著時間的推進而變化。實際上,島岡達三的陶瓷裝飾藝術語言自始至終都展現出豐富的變化,且呈現出一種持續深化的趨勢。隨著不同材料的相互作用和構建,變化的對比關系更加凸顯了其陶藝創作多樣的表現力。盡管島岡達三的陶瓷裝飾藝術語言在發展的過程中始終保持著繁復的變化種類和樣式,所運用的化妝土顏色明度相對較低,但在燒成后的作品造型和色彩上,仍然遵循了當代日本民眾對民藝陶器的審美需求,最大程度詮釋民藝陶器所追求的淳樸、自然之美。
三、總結
島岡達三的創作靈感源自民藝,其創作風格隨著不同時期呈現出多樣性的變化。這樣的發展特點伴隨著其對創作理解的深化,應從變化的維度對其進行深入分析。島岡達三以創造繩紋紋飾和鑲嵌裝飾技法為核心,將傳統紋飾和工藝技法與現代陶藝的創作理念相結合。他的陶瓷裝飾藝術語言和大多數藝術家隨時間線性發展的創作有所不同,其創作初期便在多個維度上同步展開。
島岡達三陶瓷裝飾藝術語言的生成和發展,恰似柳宗悅在《民藝論》中所敘述:“只有藝術的興趣,不是美的源泉。只有運動身體而汗水多的勞動,才格外有約束之美。勤勞的工作和實在的美密不可分。”他利用對自身陶藝創作的思考和理解,既靈活運用了傳統的工藝技法,又將現代陶藝創作的理念與之相結合。
觀察島岡達三所創造的陶藝作品之表象,其本質在于學習傳統的基礎上,借助現代陶藝的材料、工藝技法以及先進的思想理念,發展出其獨特的繩紋鑲嵌陶瓷裝飾藝術語言。由此可見,島岡達三陶瓷裝飾藝術語言的生成與發展,源于其對傳統和現代陶藝的持續學習和深厚積累,這亦是他在陶藝創作中實現量變達成質變至關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