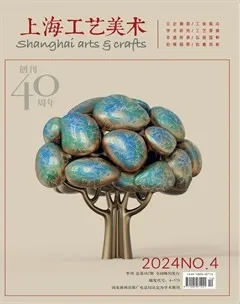溫州發繡在傳承實踐中的文化精神和時代變遷


Hair embroidery was initially carried by Buddha statues andBuddhist sutras, serving religious beliefs. Its spiritual corelies in appeal of respecting Buddha, offering to Buddha andpraying for blessing from Buddha.
在傳承實踐過程中,發繡手工藝代代相傳積累技藝,經過每一代傳承人的手接續手藝,薪火相傳不斷提升,技藝在接受時光的洗禮中被文化豐盈其精神。文化精神是發繡的靈魂根脈,頭發的人文情懷賦予發繡作品創作材料以精神符號標識,在觀念的駕馭下,使得手藝的思想意蘊表達更具情感色彩,為人們所理解。
發繡情感精神在傳遞中獲得時代更新,其一脈相承、內在文化精神指向因時代的變遷而流變。發繡最早的出現是以佛像、佛經為承載,服務于宗教信仰,其精神內核是以虔誠之心敬佛禮佛,向佛奉獻,祈求護佑的訴求。在時代變遷中,發繡社會用途的邊界被突破,不僅僅局限于信仰,而是轉向社會的諸多領域,與現實生活逐漸建立起深刻的內在關聯。頭發是蘊含生命信息的人體物質,從娘胎里帶出來,連結的是血脈基因的傳遞,一根根青絲連起親情族群的凝聚力,在民俗活動中使其具有社會性、精神性和公共文化屬性;發繡在民間文化交流、國家外交活動等特定的文化語境中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生動表現。在這種復雜多維的文化語境中,其內在精神指向究竟如何隨著時代的發展變遷,筆者試圖從發繡的人文情懷、思想意蘊的理解和情感精神表達的時代性等幾個方面進行分析探討。
發繡的人文情懷
發繡是以人的生命物質頭發為媒材,進行藝術創作的民間手工藝。頭發與人的生命情感直接關聯,是人精神和元氣的凝聚體,關乎人的情緒,如有怒發沖冠之說。與其他手工藝相比具有鮮明的自身生命特征,其他手工藝用的材料是與人的生命沒有直接聯系的自然物。如有的工藝是用泥巴為材料進行創作,作品與人本身沒有物質性聯系,不能激起生命情感漣漪,而發繡則不同,在傳統文化里有“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的表述,珍視人的頭發。發繡用具有豐富人文內涵的生命物質關注人自身,表達情懷,給予人親切溫暖的情感體驗。如親情的發繡表達,用母親的頭發繡子女腳印、手印,或肖像,寄予愛的情懷,表達兒行千里母擔憂的親情牽掛,雖有萬般不舍,卻又希望孩子去探索未來的遠方;愛情的發繡傾訴,用新娘的頭發(或者男女雙方的頭發)繡成結婚專屬禮品,以愛與美凝結成愛情的信物,在結婚典禮上由新娘親手送給新郎,有托付終身之寓意,表達白頭偕老的愛情祝福;友情的發繡激發,朋友之間交往也需要禮尚往來,用朋友本人的頭發繡其肖像或其他作品贈之,朋友會感覺到被尊重,被關愛,激發友誼,容易架起溝通的橋梁。
溫州發繡是歌頌人的藝術,定格人生精彩,它關注人的一生,從呱呱墜地到回歸黃土。發繡創作使用人各個時期的頭發,從嬰幼兒時期的胎毛到少女時期的細發,再到中青年時期的粗黑長發及老年時期花白青絲。在不同時期采用頭發的人群也不一樣,在早些時候,溫州發繡所用的頭發基本上是溫州本土的頭發,由于交通不便,與外界交流少,以前的人又比較在乎頭發的人文意義,不輕易送人,搜集頭發很不容易;后來,隨著交通便利起來,附近地區能收集到一些頭發,發繡的影響也隨著頭發的搜集而擴大,了解發繡的人不斷增多,愿意貢獻頭發的人也比較積極;到改革開放后,普通人都能出國文化交流,搜集頭發范圍擴大到全球,得到華僑的幫助,不同人種的各色頭發都能找到,為發繡創作創新提供了豐足的材料來源。
發繡工具人性化設計,按照人體工學原理,充分考慮長時間坐著繡的身體舒適感、操作的順手便利及美觀要求來確定尺寸比例和造型要求,人與工具、空間共同構成創作整體的文化場景。發繡創作進入到新階段,遵循應物施針、法隨心意的創作理念。應物,是指藝術家對客觀對象的感知感應和藝術再現,根據表現對象的表面肌理特征和本質屬性,把客觀肌理轉化為藝術元素,構成針腳語匯,組構成針法語言,達到藝術表達的真實和思想內涵的展現。在遵循造物規律的同時提煉針法的可能性,針法是在客觀存在物中提煉而成,物理與藝理相通,又恰當地表現審美對象。在此過程中,主體認識、體驗得到充分提升,把客觀提供的可能性轉化為藝術符號,傳達主體的精神。所以,發繡針法的運用,不是照搬前人的成果,而是在前人成果的啟迪下,作者的個人感受和智慧創造,有強烈的時代特征和個人辨識度。面對什么樣的審美客體就能在對象感受中提取相應的針法,沒有定規,完全是應物而生,應物施針,物質堅則針腳硬,物質軟則針腳柔,物異針變。在語言的本體追求中,將發繡創作置于整個文化語境中去思考,以客觀物理的本質顯現來確定表現上的針法選擇,針腳是創作者對物象體驗感知的心靈符號。發繡表現生活,生活千變萬化,發繡創作也豐富多樣。對生活的細心觀察和深刻理解,積累經驗,在藝術生活中把握創作技藝的實施。法隨心意,是指創作者的生活經驗、思想觀念、審美意趣、藝術技巧等高度融合的情況下,在實際創作中自覺地控制自己行為,無需主觀刻意努力的自然流露。心靈的能動與物語的默契,主客觀高度一致,在天人合一的思維情景中,藝術法度與審美創造通達,創作進入心靈自由境界,心手相應,施針度線即心靈語言的外化方式,針跡即心跡。藝術家的人生修養和藝術智慧都在沒有約束的狀態下得以自然發揮,不造作、不拘泥,完全體現了人在法度中的主動性,打破了“以法為法”的僵化程式,突出審美主體在對法度的操作過程中由被動轉入主動地位,把發繡語言從傳統的程式中解放出來。這不是不守法度,而是藝術法度已融進藝術家的血液,情之所至,藝之所生,已完全由主體精神掌控法度,即所謂“無法之法”的境界,從心所欲不逾矩,操針弄線即思想表達。
思想意蘊的理解
手工藝創作在時代語境中對作品的思想價值的理解是不可忽視的,發繡一開始就滲透著人類手工的意識觀念,影響個體生命看待世界的視角,蘊含著文化意義和精神寄托,表達發繡誕生之初的神秘情感是甌越這片土地上孕育出來的特有精神文化符號,傳達人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感悟,人對自然和宇宙的敬畏之情。淡定靜守的手藝方式不僅是個體內心的精神修煉,也是對人與自然關系的一種深刻反思和追求,對社會認知的變化,給品讀者以真誠的啟迪和思考。延綿千年的發繡文化在發展過程中,隨時代的更迭和文化的變遷、世俗的牽引等導致其內在文化指向由精神訴求轉向世俗滿足,一部分發繡走向淺表化情感體驗和實用審美。這種變化又恰恰體現了不同時代的文化精神取向,反映了藝術家境遇與心智碰撞的力量和深度。由于發繡的源頭來自精神層面的宗教信仰,其內在文化思想人們是完全能領悟的。社會的普遍心理趨向關注現實生活,思考人的當下福祉。發繡把敬佛的情懷移情轉譯至對人的尊重,對人的尊嚴的維護,如發繡作品《戰爭中的母親》,塑造了一位雙手緊抓木棍,目光驚恐的伊拉克母親,表達在戰爭中失去兒子的痛苦與憤怒,渴望和平,反映深層的社會問題,抨擊反人類的戰爭惡魔奪走了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年輕一代藝術家通過學習傳統技藝,總結前人的工藝手法與特點,在繼承傳統與當下創新的思辨中,獲得多元的藝術表達手段,并與當下的藝術觀念相結合,創作出更具溫州文化特質的發繡新作,在傳承實踐中不斷發現、梳理、創新后形成新的藝術面貌,為我們提供與前人對話的藝術通道。在我的作品里透著前人的信息,繡面的肌理、針法和色彩等視覺語言被幻化為一種富有意蘊的精神空間。如《盼》,綜合裝置與發繡結合,通過材料、結構形態等方式嘗試拓寬發繡藝術表達路徑,藝術家以頭發等材料與繡針的實驗性作為創作的出發點,激發出強烈的創造力,把一個普通的僑鄉留守兒童盼望父母回鄉的情緒展現得痛快淋漓。發繡是具有靈動情感的文化符號,從文化的維度來表達手藝人對人類自身的敬畏和生存處境的深層思考。發繡藝術家為了表達思想情感和審美理想,在藝術創作時,把客觀素材進行藝術加工,在心物相融的美學境界里,轉化為觀念形態上的審美意象,通過發絲、絲綢底料等物質媒介物化為可供人們欣賞的發繡作品。守望著手藝,把自己的思想追求與審美體悟醞釀成一幅幅動人的畫面,在艱辛靜坐中默默地針起針落,拋開一切,孤獨地向前,這是一種什么樣的精神動力?其內質是什么?也許是在等待與之在繡面中猝然相遇的探訪者,各自理解著自己的使命。
發繡情感精神表達的時代性
發繡在不同時代背景下,其內在的精神指向是有變化的。發繡面世之初不是今天看到的模樣,早在1300多年前的唐代,佛教興盛,一些信女用自己的纖發,在絲絹上繡如來佛、觀音菩薩等寶相,放在佛龕里朝夕頂禮膜拜,表達禮佛虔誠情感,發繡在佛教徒之間傳承。溫州發繡可追溯到元代,據《續修四庫全書—戒庵老人漫筆》記載,元代著名界畫家王振鵬,永嘉人(今溫州),于大德九年,繡《端陽競渡圖像》,如白描,甚精妙;其學生夏明遠也用頭發繡成《滕王閣》和《黃鶴樓》,細若蚊睫,侔于鬼工。藝術形式都以線描的方式呈現繡面形象,表現內容從佛像擴展到樓閣和民俗活動等,發繡關注的范圍廣度有所變化。明清時期發繡在民間傳承,據《繡品鑒藏》記載,溫州發繡以佛像為創作內容,如發繡《觀世音像》《達摩渡江圖》等,在本色暗花綾地上以滾針繡成,針跡細密,形象栩栩如生,作品采用白描手法,是對前一代手藝的繼承。
到了20世紀70年代,溫州發繡開始關注政治人物,藝人繡各國元首肖像,在對外文化交流中發揮獨特作用,甚至在國家重要外交活動中作為國家禮品贈送給外國元首。如溫州大學發繡研究院為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夫婦繡像,國家領導人訪問該國時作為國禮贈送給國王本人,發繡獲得國際榮譽,增強手藝人的從業信心,社會對于手藝人群體的期待從漠不關心改向支持。發繡創作拓展到創作社會文化名人,如發繡傳承人為南懷瑾先生繡其母親肖像,感動南先生幫助家鄉人民修建金溫鐵路,手藝的社會認知范圍又得到進一步擴大,媒體開始大力宣傳溫州發繡,政府扶持發繡,認同溫州發繡對溫州經濟社會的發展具有特殊價值。
現在,在非遺保護傳承的熱潮中,手工藝獲得全民認知和好感,不分長幼老少都去關注非遺,體驗也好,收藏也罷,非遺已成為全社會文化工程,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人人都為非遺傳承傳播貢獻力量。青年發繡傳承人繡制英雄人物,弘揚社會正能量,如繡制航天英雄、繡制溫籍27位院士等來禮敬這些英雄人物,把發繡的意義向前發展。在新時代,發繡有新意義,用發繡的方式來觀察世間萬物,細致入微的程度令人嘆為觀止,如發繡《標本盒子》,以思想性表達去發展發繡手藝。社會心理在變化,發繡內在文化精神指向也隨時代變遷,早期以宗教信仰為目的,逐漸轉向對政治人物、社會文化名人的關注,又從英雄人物的表現,到對自然的關注以及對社會問題的漫畫式表達,如發繡《大魚》。當下又重視手工藝的體驗,讓觀眾參與審美創造過程,零距離接觸發繡,與藝術家互動體驗實踐過程。在非遺傳承中以市集、廟會、展演等為平臺,服務大眾,充分展現發繡技藝的多種可能性。
結語
溫州發繡是在傳統文化潤養中發展起來的,其手藝的內在思想精神就是文化浸潤的結果,是文化傳統在現實生活中的手藝展現,受不同時期的社會文化生態波及影響,導致發繡所表現出來的藝術面貌也大相徑庭。在時空的延展中,基于頭發蘊含人文特殊信息,其本身就有精神屬性,作為藝術傳達媒介與作品思想內容契合,反映時代精神。發繡從宗教信仰走向世俗,逐漸延伸融入現實生活,在服務生活中直面時代信息的沖擊,感悟中獲得審美認知轉化,創造發繡當代價值,贏得業界的認可和社會心理的適應而產生認同。時代性表現雖不盡相同,但越來越多地被生活接納并應用于現實中。人們通過發繡藝術作品所體現的思想內容理解其在迭代流變中的手藝追求,更能理解發繡的時代性特點,發繡手工藝的內在文化精神在時代的變遷中得到更新傳遞,以其驚人的情感力量在人們心目中建立起獨特的文化形象,產生藝術魅力,滿足受眾的審美需求,被認為是離人情感最近的藝術。容易觸動人的情感牽掛和精神寄托,能從發繡情感的表達中獲得心靈的舒緩和美好撫慰。正因如此,發繡在時代的文化適應中延伸出新路徑,在受眾欣賞的情懷里確證手藝變遷的緣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