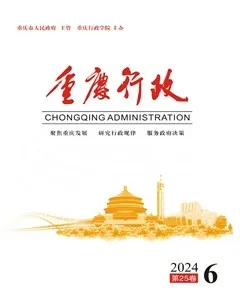應用物質主義價值觀調節自我控制與犯罪程度關系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國家安全是民族復興的根基,社會穩定是國家強盛的前提。必須堅定不移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把維護國家安全貫穿黨和國家工作各方面全過程,確保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這一重要論斷,對于新時代背景下犯罪學研究的開展具有關鍵指導意義,凸顯出犯罪行為原因探究及其有效治理的重要性與緊迫性。犯罪問題嚴重影響社會穩定,而侵財犯罪作為常見犯罪類型,對社會治安和群眾安全感構成顯著威脅。其不僅直接導致個人和社會的財產損失,還在更廣泛的層面上破壞了社會的經濟秩序與公眾安全感。深入研究侵財犯罪服刑人員,剖析犯罪行為與個體因素、社會環境等之間的關系,探尋有效的侵財預防和犯罪矯治措施遏制犯罪態勢,對于維護社會穩定、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具有重要意義。
在改革開放四十多年進程中,侵財犯罪案件歸屬于最為常見的犯罪類型[1],在數量及占比層面展現出相對的穩定性與規律性特征,如2015年侵財犯罪案件占比達83.5%,2018年為78.3%,2021年依然高達70.9%;同時侵犯財產犯罪活動的諸多新型特質,如動態化、組織化、職業化、智能化等特性,也已成為社會治安治理的關鍵難題[2],這進一步凸顯了深入探究侵財犯罪服刑人員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服刑人員作為已經實施犯罪行為并接受法律制裁的群體,為犯罪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人群樣本。他們的犯罪經歷、個人背景、心理狀態以及在服刑過程中的表現等信息,能為犯罪行為的成因、發展過程以及后果探究提供翔實的數據支持。此外,男性在侵財犯罪中所展現出的獨特行為模式,相較于女性具有鮮明的特點:從行為手段來看,男性更偏好采用直接且帶有暴力性質或高風險的方式來實施侵財犯罪,搶劫行為便是典型例證。從心理角度而言,男性往往更具冒險精神和攻擊性傾向。這種心理特質使得他們更傾向于選擇能夠迅速獲取大量財富的方式,即便這種方式伴隨著較高的風險。可見,深入研究男性侵財犯罪行為的影響機制與因素,多維度剖析其侵財行為的本質,能夠更好地解釋和預測犯罪行為,為制定有效的預防和打擊策略提供精準依據,以減少男性侵財犯罪發生,維護社會的和諧與穩定,促進社會的健康發展。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選用整群隨機方法選取某男子監獄侵財犯罪服刑人員,旨在探討男性侵財犯罪服刑人員犯罪嚴重程度與自我控制之間的關系,分析社會紐帶、物質主義價值觀在其關系間的作用,深入理解侵財犯罪的本質和根源,以期為預防和矯治侵財犯罪提供堅實的理論依據和實踐方向。
一、文獻綜述與假設提出
犯罪學領域中的自我控制,是指人抵御犯罪行為所帶來的種種誘惑時所展現出來的自我約束與管控能力[3]。這一能力體現在個體能夠在面對犯罪帶來的潛在利益或滿足感時,憑借內在的意志力和理性思維,克制住自身沖動的欲望,從而避免陷入犯罪的泥潭。社會紐帶是一種能夠對個體潛在的犯罪自然傾向予以有效抑制,進而引導人們摒棄實施犯罪行為的社會聯系,其包含了四個關鍵維度:依戀、投入、參與以及信念。依戀指個體對他人或群體的情感依賴和歸屬感;投入意味著個體在特定活動、關系或目標上投入的時間、精力和資源;參與側重于個體在社會生活中的積極融入程度;信念則涉及個體對社會規范、道德準則和法律的認同與堅守。這四個概念不僅能夠各自獨立地發揮作用,還能夠相互疊加、協同運作,共同對違法和犯罪行為的產生進行精準預測。[4]生物生態模型指出,個體所表現出的暴力、攻擊或者越軌行為,極有可能是個體自身所具備的特質與微觀、中觀以及三類宏觀系統相互交融、彼此作用的最終產物。[5]這里的微觀系統涵蓋了個體直接接觸和經歷的環境,如家庭;中觀系統包含了個體所處的社區、工作場所等;宏觀系統則涉及更廣泛的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背景。對此,在針對某一特定現象或者行為(如犯罪或越軌行為)展開解釋的過程中,需充分考慮個體自身的性格特點、家庭環境的影響,以及社會環境的塑造等多重相互作用。
已有研究表明,侵財犯罪行為的產生與自我控制之間存在著緊密的關聯。朗紹爾等人開展的研究指明,詐騙犯罪行為與低自我控制呈現出顯著的正相關關系。[6]具體來說,自我控制能力越低的個體,實施詐騙犯罪的可能性就越高。國內學者屈佳則基于對貴州省3所監獄服刑人員進行的問卷調查分析,證實了自我控制對于搶劫等暴力犯罪的顯著影響力,也表明自我控制這一概念能夠跨越文化和國別的界限,適用于我國的實際情況。[7]鑒于上述成果,本文提出假設1:自我控制水平與男性侵財服刑人員犯罪程度具有顯著的負向關聯,即自我控制水平越高,男性侵財服刑人員的犯罪程度越低;反之,自我控制水平越低,其犯罪程度則越高。
李敏等人選取了602名搶劫、盜竊犯罪者作為研究對象,證明了自我控制和社會紐帶這兩個因素對于犯罪深度均具備較高的預測效能。[8]陳蕊花通過深入研究證實,在低階層男性服刑人員的財產型犯罪中,低自我控制以及薄弱的社會紐帶與之存在著顯著的影響關系。許博洋等人選取強奸、猥褻犯罪人作為樣本,通過深入探究自我控制、社會紐帶以及性犯罪人所判刑罰之間的內在關系,其研究結果清晰地表明,個體的自我控制和社會紐帶水平越低,那么其實施更為嚴重犯罪行為的傾向就越強烈。[9]然而,在我國本土的相關研究領域中,對于自我控制和社會紐帶之間的整合檢驗工作相對匱乏。自我控制與社會紐帶之間的關系應當為更具發展潛力的整合研究方向讓行,尤其是基于中介機制的理論整合,這一方向更值得未來的本土犯罪學實證研究予以持續且深入的關注。基于前述研究現狀和理論思考,本文提出假設2:社會紐帶在自我控制水平與侵財服刑人員犯罪程度之間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物質主義價值觀指的是一種著重強調金錢和財富的重要性,并以此為基礎來追求主觀幸福感以及彰顯社會地位的價值理念。[10]卡倫等人對來自全球26個國家多達58000多戶家庭的報告進行了深入分析,其分析結果有力地表明,物質主義價值觀對于侵占性犯罪存在著顯著的影響。[11]當個體的物質主義價值觀水平過高時,會極大地增加其實施犯罪行為的犯罪傾向。據此,本文提出假設3:物質主義價值觀在自我控制與男性侵財服刑人員犯罪程度中介路徑后半段上起調節作用。本研究假設路徑效應如圖1所示。

二、對象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運用整群隨機方法,在南方的某所監獄中選取了3個監區的服刑人員作為研究對象。由相關監區的管教民警負責發放問卷,此次共發放問卷322份,回收322份。在經過仔細甄別并刪除無效問卷之后,最終獲得有效問卷202份,有效率達62.7%。被試服刑人員人口統計學情況見表1。
(二)研究工具
1.自我控制問卷(Grasmick服刑人員版)[12]
共18個條目,包括沖動性、尚體性、冒險性、簡單任務、自我中心、脾氣6個維度。采用1(完全同意)~4(完全不同意)4點計分,分數越高自我控制能力越強。本研究該量Cronbach α系數為0.93。
2.物質主義價值觀量表(Material Values Scale, MVS)[13]
共13個條目,包括以財物定義成功、以獲取財物為中心、通過獲取財物追求幸福3個維度。采用1(很不同意)~5非常同意5點計分,其中2、4、5、6、10為反向計分題。分數越高表明物質主義價值觀水平越高。本研究該量表量Cronbach α系數為0.71。

3.社會紐帶量表[14]
共14個題目,包括依戀、投入、參與、信念4個維度。其中,依戀和投入維度每道題,采用1(完全同意)~4(完全不同意)4點計分。參與維度的測量問題為“你在學生時代是每天的學習時間大概是多少”與“本次入獄前,你一周內參加正當工作的平均天數為”,其對應的選項分別為:1 小時以下=1;1~2 小時=2;2~3 小時= 3;3~4 小時=4;4~5 小時=5;5~6 小時=6;6~7 小時=7;7~8 小時=8;8 小時及以上=9。沒有工作=1;1 天= 2;2 天=3;3 天=4;4 天=5;5 天=6;6 天=7;7 天=8。信念維度每道題對應的選項為:從來不會這樣=1;偶爾這樣=2;有時會這樣=3;通常會這樣=4;總是這樣=5。本研究該量表的量Cronbach α系數為0.78。
4.犯罪程度[10]
本研究的樣本全部為被判處有期徒刑的監獄男性服刑人員,并且不存在數罪并罰的情形。本研究以人民法院對服刑人員判處的具體刑期作為衡量其犯罪程度的標準。通過詢問“你被人民法院判處的刑期為?”,答案以“()年()月”的填空形式來獲取具體的刑期數值。在后期錄用數據的時候,將“年”單位統一折算為“月”,例如“3年6月”即輸入為“42月”。
三、研究結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采用Harman單因子檢驗共同方法偏差。結果顯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10個,最大因子解釋變異量為16.16%,遠小于40%的臨界標準,本研究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問題。[15]
(二)相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根據我國刑法對刑期的規定,本研究對被試服刑人員的具體刑期數值進行歸類且本研究被試服刑人員中不存在數罪并罰的情況,即劃分了6個連續數值區間,分別為:6個月~1年;1年~3年;3~5年;5~7年;7~10年;10~15年。可以看出被判處6個月~1年的有期徒刑的刑罰最多,占比達39.6%,被判處10年~15年的有期徒刑的刑罰最少,占比僅有0.4%(見圖2)。

(三)各變量之間的相關性分析
男性侵財服刑人員的自我控制得分與社會紐帶得分呈現正相關關系(r=0.52,P<0.01);自我控制得分與社會紐帶得分均與犯罪程度呈現負相關關系(r=-0.40、-0.41,均P<0.01);自我控制與社會紐帶得分均與物質主義價值觀得分呈現負相關關系(r=-0.39、-0.20,均P<0.01)。
(四)有調節中介模型檢驗
第一步,控制男性侵財服刑人員的年齡、犯罪類型、學歷、負債、處罰經歷、家庭無勞動能力人數等變量,采用PROCESS中的Model 4檢驗社會紐帶在自我控制與犯罪程度之間的中介作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 strap分析結果表明。自我控制得分與社會紐帶得分呈現正相關關系(β=0.50,P<0.01),其中R2=0.27,F=73.1,p<0.01;社會紐帶與犯罪程度呈現負相關關系(β=-0.30,P<0.01),自我控制與犯罪程度呈現負相關關系(β=-0.29,P<0.01),其中R2=0.22,F=27.5,p<0.01,具有統計顯著意義的效應指95%置信區間不包含0。故此,社會紐帶得分在自我控制得分與犯罪程度之間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效應值占總效應的36.8%。第二步,控制男性侵財服刑人員的年齡、犯罪類型、學歷、負債、處罰經歷、家庭無勞動能力人數變量,采用PROCESS中的Model 14驗證物質主義價值觀在自我控制與犯罪程度之間的調節作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分析結果表明(見表2),MVS得分在自我控制與犯罪程度中介路徑的后半段發揮了調節作用。MVS得分×社會紐帶得分與犯罪程度負向關聯,R2=0.27,F=18.5,P<0.01,95%的置信區間不包含0。
最后,通過JN法(Johnson-Neyman)調節效應的可視化分析,展示物質主義價值觀調節社會紐帶與犯罪程度關系的后半段路徑效應圖。如圖3所示,當MVS得分>33.95時,上限置信區間不包含0,表明調節效應具有統計學意義。MVS總分×社會紐帶總分與犯罪程度呈現負向關聯。社會紐帶總分與犯罪程度的負向關聯,隨著MVS總分提高而降低;隨著物質主義價值觀水平的提高,社會紐帶對犯罪程度負向預測程度越弱。

四、總結與討論
研究表明,自我控制與犯罪程度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即自我控制能力越弱,犯罪程度往往越高。假設1成立。依照自我控制理論,那些自我控制能力處于較低水平的個體,往往表現出更強烈的短期獲利傾向。他們在做出犯罪決策時,會選擇性地忽略當前利益帶來的負面后果,這種短視和沖動的行為模式極大地增加了他們實施犯罪的風險;社會紐帶在自我控制與犯罪程度之間發揮著部分中介作用,社會紐帶能夠獨立預測男性侵財服刑人員的犯罪程度。研究假設2成立。根據社會紐帶理論,一旦個體與社會之間的聯系呈現出弱化甚至斷裂的態勢時,盡管個體產生越軌行為的內在動機并未減弱,但實施越軌行為的可能性將會出現大幅度增加。較低的自我控制往往會導致社會紐帶水平的降低,而當社會紐帶水平降低時,個體通常會呈現出一系列反常表現。在上述不利因素的作用下,個體實施犯罪行為的可能性將會顯著增加;研究發現,物質主義價值觀在自我控制與犯罪程度之間的后半段中介路徑發揮調節作用。研究假設3成立。在物質主義價值觀的不同水平調節進程中,呈現出如下態勢:伴隨物質主義價值觀水平的漸次提升,犯罪程度亦相應地展現出上升趨勢。同時,男性侵財服刑人員的社會紐帶和自我控制與物質主義價值觀均呈負相關關系,并且能夠負向預測物質主義價值觀水平。理性選擇理論認為,個體在進行決策時會對行為的成本和收益予以權衡,以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于此,物質主義價值觀會改變個體對于成本和收益的評估,當個體將物質利益置于極高位置時,他們或許會低估犯罪行為的成本,而高估物質財富所帶來的收益,進而選擇實施侵財犯罪以獲取利益。本文以國內的202名男性侵財服刑人員作為調查樣本,旨在探究在具有更為顯著的犯罪傾向的這一特定群體當中,由自我控制因素所導致的其選擇侵財犯罪行為的各類差異要素。除檢驗自我控制所產生的直接效應,以及社會紐帶所發揮的中介效應外,還將物質主義價值觀作為調節變量引入,探究可能產生的作用。細致地衡量男性侵財服刑人員自我控制能力的強弱、社會紐帶水平的高低,以及其物質主義價值觀的偏向,對于其犯罪程度的預測和降低具有重要意義。未來研究可將女性侵財服刑人員、更多男性侵財服刑人員納入研究范圍,運用縱向研究設計,確保結論具有更大的適用性和普遍性。
基金項目:2022年度司法部法治建設與法學理論研究部級青年項目“被害人學視角下電信詐騙全階段預防治理機制研究”(項目編號:22SFB4013)、2023年度中國刑事警察學院研究生創新能力提升重點項目“犯罪傾向性對服刑人員罪錯行為的影響探賾——基于大樣本調查的實證研究”(項目編號:2023YCZD04)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盧建平,王昕宇.十八大以來犯罪形勢的宏觀、中觀與微觀考察——基于司法統計數據的分析[J].犯罪研究,2023(1):32-51.
[2]張萍,肖亞麟.當前多發性侵財犯罪的特點及打防研究[J].武漢公安干部學院學報,2015(3):29-33.
[3]楊學鋒.從社會紐帶到自我控制:兩種控制理論的競爭與調和[J].中國刑警學院學報,2017,(6):64-70.
[4]吳一瀾,佟欣.基于社會紐帶理論的女犯出監教育模式研究[J].河南警察學院學報,2024(3):43-53.
[5]劉杰,孟會敏.關于布郎芬布倫納發展心理學生態系統理論[J].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2009(2):250-252.
[6]Longshore D, Turner S. Self-control and criminal opportunity: cross-sectional test of the general theory of crime[J]. Social Prob? lems, 1998(1):102-113.
[7]屈佳.自我控制水平、差別接觸與暴力犯罪行為的關系研究—基于對貴州省三所監獄服刑人員的問卷調查[J].公安學刊(浙江警察學院學報),2021(2):96-101.
[8]李敏,馬皚.自我控制、社會支持與社會經濟地位對男性搶劫、盜竊犯罪深度的影響研究[C]//中國心理學會.第十二屆全國心理學學術大會論文摘要集,2009:432.
[9]許博洋,周由,張純琍.社會紐帶理論與自我控制理論對性犯罪的實證檢驗——基于我國260名性犯罪人樣本的分析[J].犯罪研究,2021(04):50-64.
[10]Richins M L,Dawson S. A consumer values orientation for materialism and its measurement: Scal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992(3): 303-316.
[11]Martin K D, Cullen J B, Martin M W. What’s yours is now mine: Deviant consumption through acquisitive crime[J].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Marketing, 2013(1): 140-157.
[12]楊學鋒,楊茗美.中文版Grasmick自我控制量表在罪犯群體的跨樣本信效度檢驗[J].心理研究,2023,(01):73-82.
[13]趙靜.物質主義價值觀量表的修訂[J].才智,2017(6):232-233.
[14]Longshore D, Chang E, Hsieh S, Messina N P. Self-Control and Social Bonds: A Combined Control Perspective on Deviance[J]. Crime Delinquency, 2004(50):542-564.
[15]周浩,龍立榮.共同方法偏差的統計檢驗與控制方法[J].心理科學進展,2004(6):942-950.
作 者:彭勃來,中國刑事警察學院碩士研究生
于 龍,遼寧省鞍山市公安局科技創新工作室主任、中共浙江省委黨校(浙江行政學院)平安浙江研究中心研究員
責任編輯:劉小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