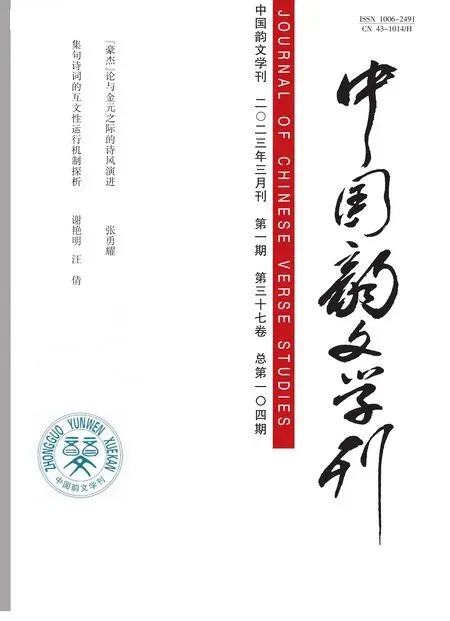“致廣大而盡精微”:肖瑞峰《詩國游弋》略評
李錦旺
(寧波財經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浙江 寧波 315175)
《詩國游弋》是肖瑞峰教授新近出版的一部學術論文自選集,其遴選標準沒有采納學術界通行的“學術獨創性”與“學術影響力”這兩條常規尺度,而是別出心裁,“以反映本人學術全貌及進階”為價值取向,因此頗以原生態的形式呈現出作者學術探索與開墾跋涉的足跡,凝聚著鮮明的學術個性與智慧。對個人而言,這或許不失為一次十分有益的學術總結;而對學術界而言,也足有啟迪后學與金針度人之潛效。如果嘗試用一句簡潔的話語對作者的治學門徑與學術特色加以概括的話,竊以為“致廣大而盡精微”庶可當之。
一 “致廣大”的恢宏格局
1.入門正大
肖瑞峰先生系十年“文革”終結之后中國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重回正軌以來培養出的首批古典文學研究生之一。當時的中華大地唱響了“科學的春天”的這一主旋律,但是“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科學技術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1](P37)。只有奮起直追,才能迎頭趕上,居于我國教育體系金字塔尖之頂端的研究生教育,必然要義不容辭地承擔起向國家輸送高端科研人才的特殊使命。先生的學術起點顯然也深刻地打上了改革開放之初特有的學術印記。他在負笈吉林大學攻讀碩士學位期間,受到了張松如(公木)、郭石山、趙西陸、喻朝綱、王士博等杰出名師組成的導師團隊的悉心面命與卓越指導,經歷了嚴謹、規范而又系統的學術訓練,為他日后在學術之路上行穩致遠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宋代詩論家嚴羽指出,“夫學詩者以識為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2](P1),并強調“論詩以李杜為準,挾天子以令諸侯也”[2](P168)。此論雖系針對學詩者而言,但又何嘗不適用于古典詩學的研究者呢!據肖瑞峰先生回顧,郭石山先生曾有意識地指導弟子們“依次精研細讀李白、杜甫、白居易集,并硬性規定每讀罷一集都要提交一篇作業”[3](P468)。中國古典詩歌發展至唐代,高峰迭起,名家輩出,而李、杜、白等偉大詩人又堪稱高峰中之高峰,由此入手研治古典詩歌,可謂深悉“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之要訣。除此之外,先生還在諸師指導下研讀了中唐杰出詩人劉禹錫與北宋西昆體巨擘楊億的詩和婉約派大家秦觀的詞。在對上述六家詩詞作品充分研讀的基礎上,先生撰寫并陸續發表了十來篇論文,《詩國游弋》前兩輯中的文章差不多過半屬于本階段的研究成果。其中《論劉禹錫的個性特征》與《重評〈西昆酬唱集〉中的楊億詩》刊載于權威期刊《文學評論》與《文學遺產》;《春來花鳥莫深愁——杜甫花鳥詩探微》與《論淮海詞》發表于頗具影響力的學術專刊《草堂》(后更名為《杜甫研究學刊》)與《詞學》;《白居易三題》中的《“樊蠻”考》刊發于多收納大家之隨筆及札記的《學林漫錄》;其他三四篇關于李、杜、白的論文亦分別見載于《北方論叢》《齊魯學刊》等素有良好聲譽的學術期刊。先生在短短兩三年間不僅高水準完成了以劉禹錫詩歌為選題的碩士學位論文——研究劉禹錫的奠基者、南京大學卞孝萱教授“曾主持其論文答辯,以最優評語通過”[4](P1),同時還博涉諸家文集,精心結撰如此多高質量的學術論文,不僅足見其精專與勤勉,亦足彰其深得治學三昧!
吉大張松如、喻朝剛等教授頗以理論見長,受其濡染,先生對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內的中外美學名著進行了廣泛探索與熔裁取鑒,奠定了寬廣而扎實的理論功底。針對古今學者斷章取義指責李白在安史之亂期間醉酒使氣,“竄身南國”,置身事外,遠不如杜甫那樣憂國憂民的苛論與謬見,先生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準繩,征引史料并結合李白大量作品辨真析偽,駁斥謬說,捍衛了太白作為偉大愛國主義詩人的崇高地位。《春來花鳥莫深愁——杜甫花鳥詩探微》不僅萃取郭知達、浦起龍、蕭滌非、王嗣奭、仇兆鰲等古今杜詩學名家之成果,亦博采法國哲學家庫申、蘇聯文學家高爾基以及我國古代詩論家王夫之、施補華、葛立方、葉夢得、劉熙載、劉勰等中外美學名家之觀點,同時還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思維闡明杜詩虛實、動靜、濃淡以及詩畫相結合的藝術特質。先生在學習和運用中西理論與方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思維個性,既反對“食古不化”與“食洋不化”的學究氣,又力倡以拿來主義心態借鑒其觀察問題、分析問題的獨特視角和手段,主張“脫略其形而求其神合”,做到“鹽溶于水”,不著痕跡。
2.格局闊大
先生攻碩期間已經在學術上初辟開闊之局,在后續研究中又進行了縱橫交錯的多向開拓,形成了更為宏闊寬廣的整體格局:一是在劉禹錫既有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深耕精研,往高、精、尖處作全方位的拓展;二是把目光由域內投向海外,開展并引領日本漢詩研究;三是由北宋楊億、秦觀進一步延伸至兩宋時期最偉大的詩人蘇軾與陸游,進行專題探討;四是聚焦中國古典文學的別離主題,借以探討中國文學的歷史流程和古代作家的創作心理。
上述四大領域中,劉禹錫研究最為引人矚目,計發表論文四十余篇,出版專著三部,但采擷入《詩國游弋》的僅有《論劉禹錫的個性特征》與《劉禹錫與洛陽“文酒之會”》兩篇文章。不過二文恰好分屬于作者早期與晚近之力作,而且均立足于“詩豪”這一研究制高點展開論述。前文透入劉詩之骨髓,就其特具的“骨力豪勁”的個性特征作了多層面的細致分梳與深入淺出的論述。后文則截取劉氏晚年創作的一個特殊時段,全面審視與辯證分析了他晚居洛陽時與詩友往還唱和所呈現出的既“歡快其外而悲苦其內”,又“鋒芒雖匿,而氣骨猶在”的獨特創作景觀,深入闡發了劉詩在保持穩定個性特質前提下的流變性與豐富性。兩文對讀,恰有互補與參證之效。
日本漢詩是先生的另一研究重鎮,計發表近二十篇系列論文,出版專著兩部。基于形式格律與歷史、文化內涵和中國古典詩歌的相似性,先生認為日本漢詩既可視為“日本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又可以視為中國文學衍生于海外的一個分支”[3](P229),因為“它總是分娩于中國文學的母體”[5](P212)。因此中國學者從事日本漢詩研究可以“在更廣闊的范圍內對中國古典詩歌進行總體觀照和全面把握,使中國古典詩歌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得以拓展”[3](P229)。收入《詩國游弋》第三輯的五六篇文章,即是踐行上述學術理念的一批力作。
3.視野宏通
《詩國游弋》展現的宏闊治學格局,映現出先生極其宏通的學術視野,二者實有相因相依、相生相成之妙。前者已如上論,后者亦體現出先生在理論方法上兼容并包的開放心態與科研上擺脫茍安一隅,大力拓展新領域的強烈使命。
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思想界迅猛迎來了又一次西學東漸的學術思潮,然而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大多數業內學者依然恪守傳統的考訂箋釋等治學法門,“新方法論在古典文學研究界受到的抵制遠比其他學科為甚”[3](P358)。在中西學術深度交融的特殊學術背景下,先生不僅積極投身于當時思想論爭的急流與漩渦之中,而且試圖因勢利導,以推動古典文學研究跟上時代的浪潮。《關于古典文學研究方法的思考》《宏觀研究與觀念更新》等理論文章即系此時的探索成果。前文呼吁古典文學研究必須進行研究方法的變革,并對傳統研究方法、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和文藝觀以及新方法論在運用實踐過程中的利弊得失進行了全方位的省思,提出移植新方法的可行方案在于“內化”,并就“內化”的多元途徑提出了頗具建設性的思考。后文則力主在古典文學領域開展宏觀研究,認為宏觀研究在學術思想日益系統化與整體化的時代背景下不僅勢在必行,而且堅信“只要不再以抱殘守缺的態度自我禁錮,那就一定會萌生出擺脫舊模式舊窠臼、變茍安一隅為周流寰球的強烈愿望,登上時代的制高點,在更宏闊的背景下,對擴大了的研究對象作時空合一的立體觀照”[3](P353)。總體上看,先生每以上述理念自期自許,亦不吝以此稱許學界同仁,如《評〈唐宋詞通論〉》《評〈唐宋詞史〉》兩篇書評均對著者的哲學意識、歷史意識與宏通視野贊賞有加。
4.目標高遠
先生參與學術界的理論論爭,并非著眼于各家理論本身的是非短長,而是確立了一個更具價值引領性的高遠目標,即“勾通古今中外,促使‘中學’和‘西學’相互融合。在融合和改造的基礎上,建立起新的思維定式和方法體系。不管其中有多少外來的成分,既然經過我們的融合、改造,必定具有中國的‘民族風格’和‘民族氣派’”[3](P348)。當今學術界已在主流話語的強大引領下把“中國風格”與“中國氣派”視為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主導方向,而先生卻在改革開放之初西學盛行的時代倡發此論,體現出難能可貴的前瞻性與戰略性。更重要的是,先生不僅這樣說,而且這樣做了。檢視《詩國游弋》全書,隨處散發著濃郁的“民族風格”和特色鮮明的“民族氣派”。其中研治唐宋詩詞的一系列文章僅透過諸如“花鳥詩”“文酒之會”“酬唱集”“時空藝術”“西湖鏡像”“意象”“別離主題”等琳瑯滿目的主題詞即可略窺我國唐宋時代韻文學特有的中華風韻與文化意涵,核之各文之論述,無不擘肌分理,盡洞其要。其研治日本漢詩的系列論文也一樣打上了中華文化與詩學的烙印。《中國文化的東漸與日本漢詩的發軔》從中日跨文化交流與比較的視角審視中華文化長期流澤日本漢詩的曲折歷程與豐富表現。基于“詩窮而后工”的中華詩學立場,先生不贊成某些日本漢學家所欣賞的菅原道真作為“詩臣”時的風范,而認為恰是遷謫生活“將他造就為‘詩人’后的作品才是彌足珍視的”[3](P317),從而得出了更加科學的結論,也合乎邏輯地將菅原的漢詩創作納入中國詩學框架之內。
如果說入門正大得益于師門的科學培養與積極引導,那么先生超群拔俗的治學格局、博大深邃的學術視野、高瞻遠矚的學術目標則彰顯出個人卓異的先天稟賦、勇于擔當的學術精神、銳意攻堅的堅韌意志以及大力開疆拓土的渾厚學力。
二 “盡精微”的學術品質
先生不僅在治學理念上融微觀研究與宏觀研究于一爐,亦在治學方法上兼采中西學術之長,從而使得《詩國游弋》在“致廣大”的恢宏格局中蘊含著“盡精微”的獨特學術品質。
1.思理精密
先生在理論上早入馬克思主義哲學與美學之堂奧,崇尚實事求是、唯真是求的學術理念,長于運用縝密的辯證思維以破解各種學術難題。針對古今學者對西昆派尤其是楊億詩從內容到形式全面予以否定的學術偏見,先生嚴謹詳實地考察了楊億詩歌創作的整體狀況與有關背景資料,條分縷析地論證了其詩在內容上不僅心系宋室國運,而且融入了憂讒畏譏的身世之感,不乏一定的現實意義;在藝術上則使典無痕,寓實于虛,表現出一定的創造性;在詩史維度上亦對日趨平庸的白體唱和詩具有糾偏之效。在審慎甄辨楊億詩藝術成就之后,先生呼吁“不應以偏概全,一筆抹殺,而應以馬克思主義藝術論為指導,從作品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分析其藝術上的成敗得失”[3](P130)。《蘇詩時空藝術論》亦辟專節從藝術辯證法的角度探討蘇詩在時空藝術處理上的創獲,提煉出微觀時空與宏觀時空的比照、靜態時空與動態時空的轉換、物理時空與心理時空的交融等多種創作模式,給人耳目一新之感。
先生尤擅于對經典作家及其作品進行“時空合一的立體觀照”,以探賾其細膩曲折的情感流程與隱微難察的變化。如論述蘇軾倅杭與守杭期間所作西湖詩的變化,從其身世投影入手由淺入深地鉤稽出蘇軾西湖詩的雙重變化:一是政治詩的銳減,二是心境的變化。前者直接導因于倅杭時期所作政治詩誘發了“烏臺詩案”等慘痛教訓。就后者而言,守杭期間的西湖詩雖然風格如昨,但其情感基調、色調與詠物對象均發生了同步的變化:一方面,人生易老的尋常感嘆嬗變為人生如夢的深刻感喟,同時攝入詩中的西湖景象也常常染上一層清冷甚至清寒的霜色;此外,倅杭時期在詩中所樂詠的蓮花、桂花與牡丹也為守杭時期的梅花所取代,而且摻和著“前度劉郎”式的自憐自傷之感與“怕見梅黃雨細時”之類的政治隱喻。通過層層深入的對比與分析,作者把蘇軾兩度仕杭期間的創作變化作了細致入微的發掘。基于同一研究視角,先生對菅原道真漢詩創作之嬗變作了同樣精妙的闡述,一方面理清了菅原由達入貶時創作上的顯著變化,同時也對他兩為“詩臣”即顯達之際與兩為“謫臣”即困頓之時詩歌情感與基調的細微變化均作了透辟的論析,大大深化了對菅原創作的整體認知。
2.論證精詳
先生治學,堅持科學性與系統性的統一,當代科學常用的歸納法、列舉法、統計法、對比法與作為傳統學術之基石的考據法,先生常常交織運用,各極其妙。《中國文化的東漸與日本漢詩的發軔》即是一篇考論結合的典范之作。作者一方面考訂漢字、漢籍輸入日本之初況與日本漢詩創生之過程,鉤稽日本遣唐使與留學生、僧侶傳播中華文化與詩藝之歷程,同時表彰日本歷代天皇獎掖漢詩之盛況。在諸位天皇中,作者對村上天皇所論尤詳,除舉應和中召詞臣賦“花光水上浮”詩和天德二年(958)舉辦“殿上詩合”之例外,作者還一氣列舉了諸如“內宴”“子日御游”等近二十種詩宴形式,就中對“曲水詩宴”與“重陽詩宴”作了尤為精細的考述,盡顯“中國文化東漸”之魅勢。《〈懷風藻〉:日本漢詩發軔的標志》則兼用數據統計與詩例分析的方法對《懷風藻》的體式(以五言八句居多)、句式(多用對句)、格律(平仄多有未協)與韻式(用韻雷同)作了極其詳盡而精確的分析,無可辯駁地揭示出日本早期漢詩不可避免的“稚拙”特質。
先生還每以平懷審視唐宋諸大家,對其創作之得失作客觀而完整的評述。《論陸游詩的意象》從巨量陸詩中提煉出雄闊、衰颯、清麗等豐富的取象類型與疊加法、比照法、擬喻法、逆反法等多元意象組合模式,對陸詩意與象的水乳交融以及獨創性與豐富性的統一給予了高度的贊賞。但作者不僅無意于拔高陸氏,反而別開生面,系統梳理并且深入探討了陸詩在意象熔鑄與運用方面的兩大突出缺陷:一是意象的因襲與重復,二是意象后綴以蛇足式的議論。最后水到渠成地得出了陸詩熔鑄意象之實踐成敗兼具,值得今人總結與借鑒的結論。
先生亦長于對研究對象作由淺入深、由表及里的全面探究。《浙東唐詩之路與日本平安朝漢詩》前三節逐一論述了日本平安朝詩人向往天臺,吟詠劉阮遇仙與嚴光垂釣以及抒發對剡溪的懷想之情,應該說已經完成了主要使命。但作者卻在四五兩節中以問題為導向繼續把論域往深廣處拓展:其一,日本詩壇何以遲至平安朝而不是在遣唐使頻繁赴唐的奈良朝流行上述題材?其二,平安朝詩人何以唯獨鐘情于“浙東唐詩之路”而對唐代其他地區的風景名勝沒有興趣?作者采用傳播學的視角就此作了深入透辟的論證。前一問題的解答是:日本漢詩的風會變遷晚于中國詩壇,奈良朝詩壇流行的仍是六朝詩,至平安朝以后摹擬對象才轉變為唐詩。后一問題聚焦于“天臺”,一方面認為“浙東唐詩之路”發端于天臺,而天臺恰是平安朝詩人渴望朝拜的佛教圣地;同時又指出無緣親履天臺的平安朝詩人是以留學僧為媒介來認識天臺的,因而有關詩作沒有采用奉佛者的觀察角度與鑒賞眼光。通過引伸研討,不僅得出了更加精審的結論,而且以“天臺”為紐帶與篇首遙相呼應,一氣連貫,別具一種自然渾成之美。
3.解析精妙
先生雖然年近耳順之年方始進行小說創作,但一發不可收,迄今已發表及出版中長篇小說數十篇,自覺地傳承起“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中華文脈,彰顯出詩心史筆的本真面貌。但事實上,先生在漫長的詩學研究生涯中早已洋溢著詩性的氣質,所撰論著無論是商榷古今駁正舊說,還是博綜群籍創立新論,都能直探詩家之心,直接從一手文獻中獲得內證與要證。
先生解詩,多要言不繁,往往通過透視一二人格化的意象即可披露詩人之心曲。如論劉禹錫詩“骨力豪勁”之特征,首先體現為“不畏‘衰節’,唱出意氣豪邁的秋歌”,作者連舉《學阮公體三首》之二與《始聞秋風》《秋聲賦》等詩賦作品,拈出其中兼具個性化與類型化的三組意象——“老驥”與“鷙禽”、“馬”與“雕”、“驥”與“鷹”,要言不繁地闡釋出詩人寄寓其中的昂揚奮發的精神品質與雄風未減的報國壯志,給人豁然開朗之感。在論述楊億詩充滿憂讒畏譏、彷徨失路的危機感時,亦舉《鶴》《禁中庭樹》二詩并分析說:“作者借‘鶴’和‘禁中庭樹’以自況,曲折婉轉地傳達了內心的款曲。孤鶴在漫天大雪中迷離失所、恓惶無依的痛苦情狀豈不正是作者的孤危處境的形象寫照?而‘歲寒徒自許,蜀柳笑孤貞’,一方面不乏傲視衰節的正氣,另一方面又包含著忠而見謗、不為時知的無限惆悵和辛酸。它是自詡、自賞,也是自嘲、自傷。”[3](P126)寥寥百余字,即把詩中寓托的極其復雜的心志與情蘊披示無余。
即使那些純用白描而無所寄興的作品,先生亦每以簡筆揭橥其妙諦。如論秦觀詞的羈旅之愁,曾品鑒其小令《阮郎歸》說:“敘述旅況,無一字道及愁,無一字不含愁:‘風雨’敲窗,一重愁;‘庭院’空虛,二重愁;聞曲感興,三重愁;鄉愁夢斷,四重愁;客中除歲,五重愁;無雁傳書,六重愁。包裹在這么多愁里,不求解脫,也無法解脫,作者真可以算得上是‘天涯斷腸人’了。”[3](P182)同樣寥寥百余字,把詞中潛蘊的“六重愁”層層析出,倘非兼具詩家之才情與學者之筆力,焉能如此舉重若輕!
先生亦精于采用比較視角探析詩人之個性與作品之主題。為了深化闡釋劉禹錫詩中不服老邁之“暮歌”,引入其文友詩敵白居易作為絕佳參照,認為劉詩更辯證地看到了老年人的有利因素與得天獨厚之處,而白詩則大多咀嚼晚境之凄涼。為了突顯劉禹錫的“詩豪”品性,又將李白、杜牧、蘇軾、辛棄疾等同樣以“豪”見稱的文人納入比較視野,認為他們的“豪”分別是“豪邁”“豪爽”“豪曠”“豪雄”,唯獨劉禹錫體現為“骨力豪勁”。當論析陸游詩取象雄闊時,則引入同時代及稍晚的一系列詩人作為反襯:“豪情與壯景契合為既雄且闊、底蘊豐厚的意象,使讀者感受到其內在的力度與熱度。唯其如此,陸游才有別于石湖的‘邊幅太窘’、四靈的‘景象太狹’、后村的‘思致太纖’而獨享‘出奇無窮’之譽。”[3](P194)要之,比較視角既可用于辨同,亦兼用于析異,均有助于闡明作家之個性與作品之風格。
小結 “廣大”與“精微”的有機統一
先生雖然力倡宏觀研究,但對其缺點亦有清晰的認知:“宏觀研究既然是站在某一制高點上對紛紜復雜的研究對象的鳥瞰,那么,它所致力勾勒的必然是整體的輪廓,于局部的顯微則未必在在逼真。”[3](P352)因此主張在具體科研過程中實現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的協調統一:“一方面宏觀研究無法代替微觀研究,另一方面宏觀研究又有賴于微觀研究所提供的堅實基礎。只要我們堅持在宏觀中統率微觀、在微觀中展現宏觀,二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3](P352)對于這一治學理念,先生大約在染翰學術之初即已奉為圭臬,并在數十年學術生涯中始終身體力行之。一方面,論題宏大但絕不流于空疏,必出之以精微的辨析與精詳的論證。如《日本漢詩三論》涉及三個論域寬廣的不同分題,但作者將它們聚焦于探討詩歌本質的復歸,并且建立了以五山詩壇為中心的時空坐標作為日本漢詩衰而復興的共同紐帶,經過有條不紊的論證,不僅揭示出日本漢詩在三個不同維度的同步演變,而且在形散神聚的邏輯框架中的展現出散文式的文風及魅力。另一方面,論題雖然貌似“細小”卻絕不流于瑣碎,往往于小題中寓宏旨,在論證上亦呈尺幅千里之勢。如《論陸游詩的意象》兼論陸詩熔鑄意象之成敗,隱含著以古鑒今的現實考量,折射出作者胸納古今,關懷當下的人文精神。《宋詞中的別離主題》雖然主體部分側重于對宋代別離詞進行藝術與類型分析,但結尾處卻提升到生命意識與文化范型(宋型文化)的高度審視其人文價值。由于作者科學地處理了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之間的辯證關系,使得《詩國游弋》在整體上呈現出廣大格局與精微品質的有機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