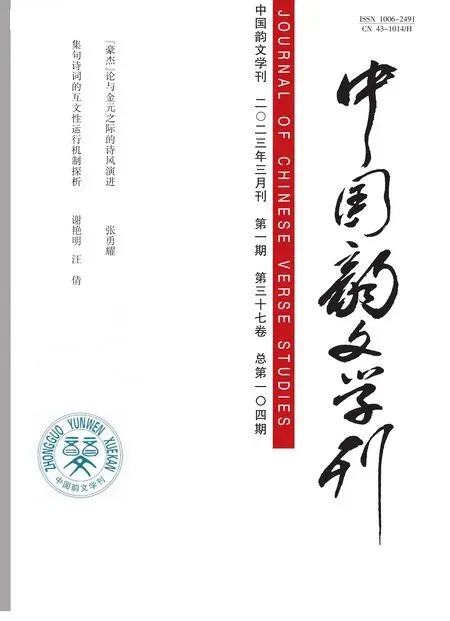晚清淮安“山陽詩群”的生成與質實詩風的建構
叢海霞,杜運威
(1.淮陰工學院 人文學院,江蘇 淮安 223003;2.淮陰師范學院,江蘇 淮安 223300)
宏觀盤點清代文學史,明顯呈現出地域、家族、流派等綜合特質。作為重要組成部分的清代淮安詩歌自然也帶著這類標簽。從地域視角觀之,淮安乃漕運和鹽運的交通樞紐,商業繁榮,經濟發達,私家園林星羅棋布。又因鹽商巨賈、士紳豪門的組織和文人的積極參與,圍繞淮安園林而興起的文學活動成為地域文化的靚麗名片。自家族窗口切入,淮安有不少影響深遠的名門望族,如丁氏、王氏、潘氏等,家學底蘊深厚,在品行塑造、文脈傳承方面承擔重要責任。然若單從詩歌史層面審視,清初之望社與清末之“山陽詩群”,無論是在淮安文學史,還是清詩史上,都是十分耀眼的存在。前者是帶有鮮明政治目的的同聲相應,以一腔悲憤抒發抑郁情懷,譜奏出一曲復雜辛酸的遺民血淚史;后者以變革詩歌歷史地位為使命,對彼時過于獨抒性靈而導致的纖細淫鄙和過于強調學問而造成的生氣桎梏等弊端提出了新的補救措施,即“質實觀”。本文重點討論被人們忽視的晚清淮安山陽詩群的生成及其質實詩風建構等問題,試圖以此重新認知淮安詩壇的歷史地位。
一 晚清淮安“山陽詩群”的生成
如果說清初因為望社的出現,使得淮安成為《清詩史》中著重敘述的存在,那么,為何在更加昌盛的嘉、道、咸、同時期,淮安詩壇卻在各大文學史中銷聲匿跡,陡然消失?盤點嚴迪昌《清詩史》、朱則杰《清詩史》、王小舒《中國詩歌通史·清代卷》等代表性文學史論著,僅僅止步于提點潘德輿、魯一同等名家,都未關注到晚清淮安詩壇整體興盛的現象,更沒有看到“山陽詩群”的存在。
關于該群體,不少學者已經約略談及。如朱德慈《潘德輿年譜考略》載:“四農(潘德輿)別樹一幟,贏得了魯一同、孔繼鑅、葉名灃、吳昆田、黃秩林等眾多追隨者。探花詩人馮煦稱其已獨開一派……”[1](P3)筆者認為潘德輿等人“獨開一派”之說或與事實尚有差距,但命名為“山陽詩群”是綽綽有余的。著名學者孫靜也明確表示,潘德輿“在當時的詩壇上,樹起一面旗幟,力圖推挽一代詩風,使之沿著風雅方向發展”[2](P218)。筆者將順著朱德慈、孫靜等學者提出的設想,進一步揭示“山陽詩群”的內涵及基本特征。
山陽詩群是活躍于清代嘉慶、道光、咸豐時期的淮安地域性詩歌群體。以潘德輿為中心,以《養一齋詩話》提出的“質實”思想為創作綱領,通過地緣、學緣、血緣等關系,逐步發展起來的,有著共同審美傾向的詩人群。其中,以潘氏朋輩之丁晏、高士魁、丁壽祺、丁壽昌、徐登鰲、楊慶之,及弟子之魯一同、吳昆田、孔繼镕、劉湘云、潘亮熙、潘亮彝、潘亮弼、郭斗、鮑搶弼、梁法等為主力,其他山陽地域詩人為積極參與者,后輩之魯蕡、尹耕云、高延第、徐嘉、段朝端、王錫祺等接踵其業,使得山陽一帶火熱的吟詠風尚持續了近半個世紀。
潘德輿倡導的“質實”理念既充分傳承了古典詩歌的優秀傳統,又符合彼時社會動亂、人心思變的社會趨勢,當然在地域上也是勾連起淮安文化融通南北的節點。他說:
吾學詩數十年,近始悟詩境全貴“質實”二字。蓋詩本是文采上事,若不以質實為貴,則文濟以文,文勝則靡矣。吾取虞道園之詩者,以其質也; 取顧亭林之詩者,以其實也。亭林作詩不如道園之富,然字字皆實,此“修辭立誠”之旨也。竹垞、歸愚選明詩,皆及亭林,皆未嘗尊為詩家高境,蓋二公學詩見地猶為文采所囿耳。[3](P45-46)
質實觀內涵有二,一曰質,竊以為主要就藝術審美而言。鐘嶸曾論“班固《詠史》,質木無文”[4](P12),質與文相對,上文亦以“文濟以文,文勝則靡”為反例,都佐證質是一種樸實潔凈的美學風格。然并非排斥文采技法,而是強調潛氣內轉,沉郁頓挫。如其言:“‘質’字之妙,胚胎于漢人,涵泳于老杜,師法最的。”又言:“今人詩無一句不求偉麗峭雋,而怒張之氣,側媚之態,令人不可向邇,此中不足而飾其外之過也。道園詩未嘗廢氣勢詞采,而了無致飾悅人之意,最為今人上藥,惜肯學其詩者希耳。”[3](P41-42)既師法老杜,又特以虞集為典范,都在說明質是一種外表樸實,卻內功深厚的審美特征。二曰實,主要指內容意蘊,即所言之句有真思想、真情懷,特別是對當下正在發生的時事風云的關注,積極表達文人干預社會的責任意識。《養一齋詩話》載:“南宋以語錄議論為詩,故質實而多俚詞;漢、魏以性情時事為詩,故質實而有余味。分辨不精,概以質實為病,則淺者尚詞采,高者講風神,皆詩道之外心,有識者之所笑也。”[3](P46)“以性情時事為詩”清晰表明立場,而反對“以語錄議論為詩”則將矛頭直指乾嘉時期蔓延的“以學為詩”現象。
質實觀的根本目的是試圖恢復詩歌教化人心的作用。潘德輿說:“若事事以質實為的,則人事治矣;若人人之詩以質實為的,則人心治而人事亦漸可治矣。詩所以厚風俗者此也。”[3](P46)丁晏《潘君傳》(潘德輿)更著重點出“君留心當世之務,感時撫事一寄之于詩,悱惻纏綿,出風入雅,藹然忠孝人也”[5](P20)。有忠孝之心,方行忠孝之事,繼言忠孝之詩也。
基于此內核,質實觀在山陽一帶產生了巨大影響。如魯一同曾言:“凡文章之道,貴于外閎而中實。中實出于積理,理充而緯以實事,則光采日新;文無實事,斯為徒作,窮工極麗,猶虛車也。”[6](P422)至于“師事潘養一先生,能傳其業”[7](卷首)(馮煦《吳稼軒先生傳》)的吳昆田更在友朋書信數次談及,如《與申秩亭書》云:“為文則不必求古,但須平實,以切情盡意而止。”[7](卷六)再如丁晏,評論家言其“窮居而能兼善一鄉,有濟于時,有補于物,不以空言為詩,讀者當知有真經術在”[8](P373)。丁氏與王錫祺作淮安詩歌選集時特別關注民瘼時事與氣勢雄渾的詩風取向都與質實觀有內在聯系。因為理真,所以認同。潘氏憑借質實觀及忠孝人品,逐漸成為淮安詩壇執牛耳人物。
一個詩群的成立不僅需要宗主、旗幟及成員,還離不開成規模的文學活動。首先,常規性的雅集唱和是詩群名副其實的前提。我們從各家別集中很容易拈出潘德輿、丁晏、魯一同、吳昆田等淮上文人雅集的記錄,如丁晏別集中就有《季冬二日,盛子履大士廣文招集黃少霞師以炳、潘四農德輿、李少白續香、芷茳、友香兄弟飲澹然居。是日晚,復邀曹介樵若端、周木齋寅至城南僧寮痛飲,醉歸有作》《黃少霞師以炳、潘四農、周木齋、曹介樵若端、倪渥生家駿祇洹精舍小集》《慶成門城樓落成,張介純邑侯重九日招毛秋伯大令、周止安、慶石城大鏞、楊荊門名超、呂星齋偉庚、廣文周木齋登高宴集,即席和止安韻》等多首作品。至潘德輿下世,淮上吟詠非但未減,反而更盛,這在《山陽詩征續編》中有顯著體現。單以編者王錫祺為中心的唱和詩,在《小方壺齋詩存》中就有數十首。需要指出的是,淮上文人唱和并非止步于娛樂消遣,更是創作思想相互交流碰撞的過程。其中不少詩人就受到潘德輿的影響或點撥,如徐嘉《遁庵叢筆》載:“云壑(方其洪)先生早歲登賢書,與四農先生為齊年交。逆旅公車,賡唱疊和,詩境日進。”[8](P444)“輔士(鮑掄弻)先生為四農先生快婿,且入室弟子也。詩篤守師法。”[8](P848)“朱磵南先生纻,字亦僑,與潘四農、黃蔚霞、趙吉人、阮定甫、宋紺佩諸先生皆至契,時相倡和。”[8](P175)丁晏《柘塘脞錄》又載:“芋田(郭瑗)居車橋鎮,貧而工詩,與潘四農明經衡宇相望,亦最契密,刻燭拈題,唱酬無虛日。”[9](P960)以上史料清晰記載了山陽朋輩與潘德輿之間的交游過程,至于潘氏家族、潘門弟子等受到潘德輿的影響就更加直接,也不必再詳細舉例。眾人與潘氏交游學習的過程其實也是“質實觀”逐步擴大影響以及詩群悄然建立的過程。
其次,選集的刊刻是詩群貫徹質實審美標準的重要路徑。與山陽詩群有關的詩歌選集有四,分別是丁晏《山陽詩征》、吳山夫《山陽耆舊詩》、段朝端《山陽詩錄》、王錫祺《山陽詩征續錄》,吳、段二本流傳未廣,影響不大。丁、王二本與山陽詩群有緊密關系,甚至可以說,是該詩群創作的集體亮相。潘德輿《山陽詩征序》云:“若子之所征者,文也,而獻實之,故足貴。然用詩存人,一二篇足矣;三篇外必至精者乃錄之,弗以多貴也。儉卿然余言,余亦與刪擇役。要之,儉卿搜羅出處、行誼、軼事之功為大,后之覽者,必由詩以知人,得其行己之大方,更由此以窺盛衰得失之故,則受范于鄉先輩者遠矣。且以罔羅掌故,庶幾盛衰得失之明鑒法程。鄙拙如予,不克續采文獻竟先世未竟志者,而亦深幸是編之成,借以償吾愿也。”[10](P413)“然予言,予亦與刪擇役”及“償吾愿”等字句已清晰說明潘德輿一定程度參與了《山陽詩征》的編纂。那么該選集勢必帶有潘德輿的編選痕跡,何況丁晏十分欽佩潘氏的詩歌成就及美學風格。因此,《山陽詩征》不僅具有常規選集的基本功能,還具有反映嘉、道時期淮安質實詩風的獨特價值。
再看王錫祺所編的《山陽詩征續編》。王錫祺曾說:“段先生有志續編,輯有《山陽詩錄》,斯役舉以見餉。”[8](P1)換言之,續編充分吸收了段朝端《山陽詩錄》的前期成果,甚至在選錄的審美標準上也與之十分相近,從選錄魯一同、吳昆田詩歌即可管窺。[11](P32-35)王錫祺《山陽詩征續編序》進一步揭示:“士大夫幽憂憤郁,一倡百和,激為變征之聲。迄今十余年間,島寇鴟張,興議變法,間有感時紀事形諸歌詠者,群非笑之,則纟由繹推尋,不亦可識。時局之純漓,趨向之同異耶?”[8](P57)不難看出,續編所執標準與潘德輿推崇社會時事如出一轍。這也是《山陽詩征》及續編大量選刊民生疾苦、針砭時弊作品的根本原因。
綜上所述,潘德輿提出的“質實”思想,在淮安一帶產生了重要影響。以潘德輿朋輩弟子為紐帶,在山陽一帶逐步聚集起一批認同“質實”思想的詩人群體,他們通過常規性的雅集唱和與刊刻選集形式進一步強化了群體屬性。
二 晚清淮安“質實”詩風的建構
若自詩歌史流變看,質實觀的提出實質是對乾嘉學派和性靈詩派后期都出現嚴重弊端的一種反思和再平衡。乾嘉學派在學術研究和作文論理方面也強調樸實簡潔,但由于過度重視考據義理,難免將這種學問化的思維和素材寫入詩中,久之,直接導致以學為詩現象的極度膨脹。翁方綱肌理說縱有合理之處,但難逃此宏觀局限。袁枚率先對此流弊發起詰難,其有諷刺詩曰:“天涯有客號詅癡,誤把抄書當作詩。抄到鐘嶸《詩品》日,該他知道性靈時。”[12](P111)倡導性靈與其說是針對以學為詩,倒不如說是詩歌審美發展過程中的自我轉移。一代文風的轉變有著多種因緣際會,隨著乾隆后期愛新覺羅氏朝政生命力的逐漸流逝,雍容華貴、典雅豐腴的創作風格已經與世人心中訴求形成疏離態勢,整個詩壇正在悄然醞釀新的變革。袁枚領導的性靈詩派的陡然興起正是這種訴求和變革的佐證。然而,性靈詩派未能順著吟詠真性情、真感慨的正道繼續前進,反而陷入纖細狹隘、柔弱鄙俗的另一陋巷中,尤其自袁枚、張問陶、趙翼等核心人員仙逝后,明顯后勁乏力,更無整改雄心。
隨著潘德輿、龔自珍等一批新銳詩人的出現,嘉道詩壇大有洗心革面的勢頭。龔氏以一種更開放激進的姿態,劃破原本壓抑沉悶的天空;潘氏則以理性保守的面目,沉穩堅定地崛起于江淮大地。潘德輿不止一次批判性靈痼疾,如評吳以讠咸《古藤書屋詩存》云:“此集一掃袁、趙之習,誠近今作者。”[7](卷八)《養一齋詩話》又云:“詩積故實,固是一病,矯之者則又曰詩本性情。予究其所謂性情者,最高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耳,其下則嘆老嗟窮,志向齷齪。其尤悖理,則荒淫狎媟之語,皆以入詩,非獨不引為恥,且曰此吾言情之什,古之所不禁也。嗚呼!此豈性情也哉?”[3](P160)基于此,潘氏提出以《詩三百》“柔惠且直”而定義性情,也就是學者總結的溫柔敦厚。從思想史言之,這是一種典型的復古潮流,因而難免遭人譴責,并冠以“倒行逆施”云云。然需要提醒的是,此處所云是針對性靈派毫無節制的性情而發,更強調情之“厚”。所謂“真則厚,率則不厚”,又“詩有一字訣,曰‘厚’。偶詠唐人‘夢里分明見關塞,不知何路向金微’,‘欲寄征鴻問消息,居延城外又移軍’,便覺其深曲有味。今人只說到夢見關塞,托征鴻問消息便了,所以為公共之言,而寡薄不成文也”[3](P16)。他有詩曰:“蔣袁王趙一成家,六義頹然付狹邪。稍喜清容有詩骨,飄然不盡作風花。”因此,性靈派之狹邪需用溫柔敦厚的六義之旨和盛唐諸賢的詩骨來糾正。
潘德輿推進質實的重要舉措有二:
其一,將社會時事納入敘述視野,極大地抬高詩歌反映社會、記錄歷史的價值。這在詩群大將魯一同身上表現得最為強烈,他對鴉片戰爭有著更為深刻的記錄,錢仲聯《夢苕庵詩話》稱贊其“鴉片戰爭時,所為哀時感事之作,尤蒼涼悲壯,足當詩史”[13](P252)。先讀《觀彭城兵赴吳淞防海》:
樓船下洪河,六月大興師。
往問主將誰,南征行備夷。
舟山不復守,乍浦勢尤危。
吳淞控大江,東南纏地維。
守險可百勝 ,嚴師固藩籬。
中樞下火符,副相總戎麾。
海疆八千里,腹背聯絡之。
側聞蛟門軍,半是吳中兒。
此輩市菜傭,臨難心然疑。
楚兵氣精銳,彪彪千熊羆。
百年養汝曹,危急安足辭。
獵獵大斾風,洸洸淮流馳。
彎弓指東溟,不得中顧私。
莫畏統御嚴,中丞有母慈。
行矣謝送徒,報國方在茲。[6](P213-214)
在外敵入侵、國將不國時,整個詩壇涌現出大量引吭高歌的愛國主義詩篇,他們積極抒發一腔怒火的初心是值得稱贊的,然不少作品徒然為了表達的暢快而忽視了技法上的潛氣內轉,難免有直率庸俗,乃至淪為叫囂謾罵的粗制濫造的語句。魯詩澎湃氣勢的形成則很有章法,一方面是情緒張弛控送得很到位,另一方面是視角切入得很巧妙。上文先自主將入,宏論吳淞,次及中樞、副相、士兵,邏輯清晰;繼以“危急、獵獵、洸洸、不得”等急促詞語盤旋氣勢,最終立足點在報效祖國。這樣寫不僅反映出彭城守兵的堅定信心,更因記錄下這段御敵抗辱的光榮歷史,使詩歌成為鼓舞人心的重要載體,承擔起時代賦予的使命。類似作品還有不少,如《讀史雜感五首》《辛丑重有感》《烽戍四十韻》《崖州司戶行》等論及林則徐虎門銷煙及英勇抗敵的壯舉;再如記浙江戰事的《三公篇》,方家評其“最為巨制,筆力堅蒼,敘事簡凈。……三詩不愧為大手筆,并時惟朱伯韓可為抗手”[13](P255-256)。
不唯魯一同,其他詩人對戰事也特別關注。如高延第《石橋莊筑圍記》記載捻軍亂淮甚詳細:“咸豐庚申春,皖寇東擾,鄉民望風遁散,賊踞清江浦十余日,馬隊四出,百里內焚掠殆盡。時天大風雪,流民遭屠掠饑凍死者甚眾。賊退人歸,室廬僅有存者,號哭震原野。既而念無險不可以守,不耕又無可得食也,乃始發憤,集鄉里,筑圍寨,為死守計……”[14](卷四)然更深刻的還是不同詩人筆下立體多維的詩歌,楊慶之有組詩十一首(《堵城》《止帥出》《民吶喊》《防夜火》《糶官米》《闔門節》《轉溝壑》《殺不辜》《兵肆掠》《殲途梟》《杯影蛇》),第一首“我聞淮陰背水陣,死地后生人知奮。大吏此令第一功,二千余戶咸安順。……白發老儒堅不可,牴牾軍令大聲我。行橐返途簜節還,郡城大勢重安妥”,敘述淮安軍民共同御敵場面。至第三首“行者擊柝坐者鉦,五垛一鼓靈鼉鏗。狗嘷雞唱馬長嘯,喧豗口霅霵雷車轟”,聚焦戰斗場面的混亂激烈。中間數首透過糧草、征人思婦、士兵、老翁等不同視角,反復渲染戰爭背景下的殘酷景象。楊慶之的組詩完成了對捻軍亂淮的多方位立體化描摹。其他同類作品還有如陳嘉干《庚申二月朔,袁江紀事二十韻》:“淮水赤復赤,流血飽蛟螭。(婦女投運河死者甚眾)鱗鱗萬瓦屋,一炬靡孑遺。貪狼恣屬饜,邗上來援師。群丑鳥獸散,大府歸遲遲。”丁壽祺《庚申八月紀事》:“風聲鶴唳又經旬,感激居然社稷臣。排難無端招市儈,縱擒能否服南人。將軍跋扈威難犯,宰相模棱意善嗔。日向城頭望烽火,有誰赴闕靖黃巾。”丁晏《庚申守城》、程步榮《庚申春正月逆捻攻淮,孤城困守十日解圍,感而有作》、潘亮熙《丙辰秋夜,述感短歌八章》等,皆是關于捻軍詩歌,堪稱實錄。這類作品的集中出現,固然有生逢亂世的契機,但若無洞察社會之動機和積極表達的創作理念,即便戰爭擺在眼前,依然有大量文人選擇漠視。
其二,拓寬詩言志及針砭時弊的現實作用。將文人目光由知識學問、吟風弄月、個人情懷轉向民生疾苦。如吳昆田《紀旱》詩堪稱詩史:“不雨四十日,中田成焦枯。飛蝗起東海,西與浮云倶。蝝生遂徧野,何計能驅除。大府急民瘼,禱祀丹誠輸。……昔為麥祈實,立見甘霖敷。今已二旬歷,靈應豈忽無。”連續四十日不雨,直接導致禾苗焦枯,蝗蟲四起,民不聊生。面對“蝝生遂遍野”的現狀,詩人心有余而力不足,那種憂國憂民的心緒躍然紙上。天災已經使得民不聊生,然更加令人走投無路的恐怕還是人禍。吳昆田《紀蝗》前數句羅列蝗災慘象后,將矛頭直指當權者的漠視和貪婪:“貪苛誰樂召,饑饉只愁當。冠盜將乘起,干戈未許藏。萑苻雖異類,蟊賊實同方。天意何由測,人謀要貴臧。”不必再贅言解釋詩中所指,犀利的語句已經將殘酷的現實擺在面前。徐嘉《遯庵叢筆》曾指出:“(吳昆田)識議堅卓,能斷大事。聞四方災荒,盜賊竊發,輒憂憤形于言色,所為詩文多關當世之故。”[8](P524)山陽詩群中類似作品還有不少,丁壽征《薊門吟》十首就是典型例證:第一首《盜鑄錢》,憫愚民;第二首《不終制》,誚薄俗;第三首《鈔幣滯》,傷貪吏;第四首《銀價貴》,憂錢法;第五首《貲郎宴》,譏紈绔兒;第六首《麗人游》,諷貴家眷;其他幾首不一一羅列,需要特別強調的是第七首《河堤決》,悲民流也,詩歌如下:
咸豐六年季夏月,永定河頭水漰渤。驚濤駭浪風雨飛,疑是千弩萬弩發。石工堤埽渺難尋,就中似有蛟龍窟。前日喧傳南岸沖,多少田廬付沉沒。監河見險仍疏防,北岸又復驚披猖。怒流決開二十丈,蝄像騰躍天吳狂。亡者誰為主,生者乃更苦。老羸轉徙傷流離,計乏一椽與二鬴。國家歲帑百萬金,未雨綢繆責誰任。斬茭伐竹宜早計,何為坐待長堤沉。帑金既浪擲,民命亦可惜。設官本以衛民生,誰知官多民轉迫。會稽宗子謂御史宗君稷辰古遺愛,執法烏臺冠流輩。上書天子救災黎,請籌撫恤恐不逮。丁壯堵筑借免饑,篤老垂髫資斗概。官私并力全災區,勿使窮民色如菜。[8](P682-683)
詩歌聚焦永定河水災導致良田損毀、生民涂炭的現實悲劇,更悲劇的現象是“設官本以衛民生,誰知官多民轉迫”,類似情形并不稀見,薛炳如《譚雨香邑侯德政頌》:“憶昨湖水漲漫彌,河東河西災祲隨。田禾失收費撐持,目極艱難豈忍窺。”又程步榮《大雪篇壬子臘月十八日紀事之作》:“湖湘一戰萬骨枯,徹骨荒寒更天數。行路難,災民哭,逃亡滿路皆枵腹。攜男挈女走他鄉,一日一夜一餐粥。是刀是雪飛巖谷,茫茫凍路尋骨肉。傷心篷棲與路宿,饑寒逼迫遭殘戮。”魯一同《荒年謠》組詩小序中說:“事皆征實,言通里俗,敢云言之無罪?然所陳者,十之二三而已。”換言之,以上詩人筆下的民生疾苦只是冰山一角,還有大量被遮蔽的社會亂象。此類作品的集體出現絕不是偶然,既是宏觀經世致用思潮對詩歌的重大沖擊,也是微觀山陽詩群在質實觀影響下的集體亮相。
另外,質實詩風的形成還與“詩品之人品”的觀念有密切關系。淮安文人特別注重人品之高尚純潔,哪怕詩歌有瑕疵,或成就不高,若有令人敬佩之人品,則其人其詩皆可傳;反之,即便有八斗之才,亦半字不錄。潘德輿曾云:“人與詩有宜分別觀者,人品小小繆戾,詩固不妨節取耳。若其人犯天下之大惡,則并其詩不得而恕之。”[3](P7)他不止一次地在各種場合申辯人品與詩品之間的主次關系:
杜荀鶴詩品庸下,諂事朱溫,人品更屬可鄙。[3](P68)
(《養一齋詩話》卷四)
典而確,辨而潔,練而質,健而逸,傳世詩文非此不立。……雄、深、雅、健四字,人品、詩文、書法,要皆如此。[10](P973)
(《自題詩稿后》)
靜能隱居樂道,人品甚高,故其詩質而無飾如此,雖未逮道園之渾健,亦元人之特立者。[3](P43)
(《養一齋詩話》卷三)
邱文莊雖稱淹博,而忮刻乖僻,與王端毅公相惡,其人品舛矣,安得與文靖肩隨乎?況文靖嘗教人讀經窮理,殆有繩以貫錢,不得謂之無錢者也。文莊所譏,徒好勝而已矣,何足錄乎?[10](P2133)
(《養一齋札記卷九》)
這種品鑒等第,首重人品,次談詩品,二者相統一的風尚已經不是停留在個人觀點層面,而是貫徹落實為山陽詩群內部的高壓線。丁晏《山陽詩征序》大贊:“其間忠孝節烈、道德文采,彪炳天壤,足為斯集之光。”[5](P170)段朝端《曉漁詩草跋》云:“余幼時聞長老言,先生少失怙,事母極孝,屬歲旱,大病,先生中夜露禱,愿延壽養親,其疾良已。則是集又不以文重,而況芉綿清麗,有如此哉!”[8](P157)不以文重,重在孝道。再如夏涂山《瑚散言序》云:“存赤與予為忘年交,其為人也,靜慤而坦直,卓有道氣。茗底觴次,發一語,輒能以冷雋解人頤。”[8](P3)以上所論都在強調人品的重要性。這種詩論標準一方面彰顯淮上文人淳樸忠孝的高尚品格,另一方面表現在詩歌中則是對節義忠誠題材的重視。如王錫祺盛贊霍克誠《題馬貞女》詩;閻若琛《貞女歌》亦欽佩其中“妾心不可磨”的堅決。至于王德隆之女,嫁后遇賊,寧愿介溝崖投水而死,也不屈從之壯舉,更博得詩人周龍藻的稱贊(《題張橋王貞女墓》)。其他如劉湘云《祭露筋烈女祠樂章》:“白云初起,下映淮水。既潔且清,妾心如此。嫂止田夫,女守其愚。愚能全節,何惜微軀。”曹若曾《吊丁烈女》《哀郝烈女》,丁毓璨《何烈女祠》,劉廣《何烈女》等,都是異口同聲的表達。羅列這些作品,并非宣揚什么觀念,只是為了佐證淮安文人對人品的重視不是停留在口頭層面,而是落實到具體詩歌創作中,且形成了一種倡導忠孝節義的地域特色,這恰恰是質實觀不可輕視的重要一端。
總而言之,山陽詩群的文學價值是被遠遠低估了的。晚清淮安出現的質實詩風既是地域性詩歌的獨特風貌,也是對近世整個詩壇急需變革的現實回應。
結 語
綜上所述,潘德輿倡導的“質實”理念既充分傳承了古典詩歌的優秀傳統,又符合彼時社會動亂、人心思變的社會趨勢,更勾連起了淮安文化融通南北的節點。該理念得到了魯一同、吳昆田、丁晏、王錫祺、高士魁、丁壽祺、徐登鰲、楊慶之、孔繼镕、劉湘云等人的大力支持。由此,以潘德輿為中心,以“質實觀”為創作綱領,以地緣、學緣、血緣等為紐帶,形成了共同追求“質實”詩風的詩人群體——山陽詩群。山陽詩群主要通過兩大途徑建構起質實詩風:一是將社會時事納入敘述視野,極大地抬高詩歌反映社會、記錄歷史的價值;二是將目光聚焦于民生疾苦,拓寬詩言志及針砭時弊的現實作用。此類作品的集體出現既是宏觀經世致用思潮對詩歌的重大沖擊,也是微觀山陽詩群在質實觀影響下的集體亮相。綜合而言,山陽詩群的發現有利于準確定位清代后期淮安文學在整個清代文學史上的坐標,其質實詩風的建構是對乾嘉學派和性靈詩派后期出現嚴重弊端的一種反思和糾正。總之,憑借反映時事、針砭時弊、評鑒人品等特質,山陽詩群已然走出一條打著淮安地域特色旗號的詩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