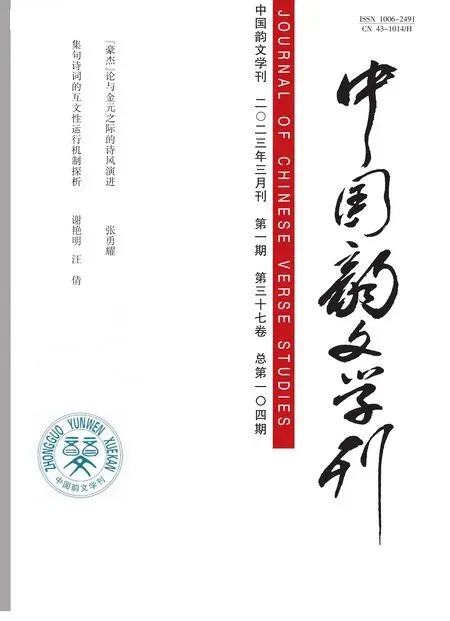論白居易與韋應物詩歌慚愧表現之異同
吳嘉璐
(西華大學 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四川 成都 610039)
緒言
慚愧,是人類常見的情感,但遍尋中國詩,卻發現中國詩人較少在其中表現慚愧的情緒。即使最早如《古詩》中的故夫遇前妻,懺悔自己不該喜新厭舊的詩句,其慚愧也是建立在“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的市儈的、現實利益的比較上的,似乎欠奉真心。因高尚人格被贊許的詩人陶淵明和杜甫,其詩中雖有自省的慚愧、悔恨,但亦較少圍繞道德做文章,比如陶之名句“望云慚高鳥,臨水愧游魚”,不過是對自己既缺乏自由又不在高位而表示遺憾,再如杜甫“共被微官縛,低頭愧野人”“交新徒有喜,禮厚愧無才”,與陶詩出于同一機杼;但陶與杜的詩中已經出現了對他者表達慚愧情緒的端緒,如陶之“顧爾儔列,能不懷愧”,是誠摯的對農人的慚愧,杜之“何日干戈盡,飄飄愧老妻”,是由衷的對妻子的慚愧。
中國詩人中,最集中表現對己對人的慚愧情緒的,當數白居易。白居易詩出現的單音節語匯慚、愧、悔、恨甚至連言慚愧的頻次之高,相當驚人,從數量上看,慚有75首,愧有57首,慚愧連言的有10首;與之相近的悔有33首,恨也有67首。可以說,白居易的一生,不論是在官場或是日常生活中,都伴隨著慚愧的情緒。目前雖然已經有論者注意到他與眾不同的慚愧情緒,如陳家煌(1)陳家煌將白居易的慚愧全部歸于“不自信” 心態,似可以商兌,參考《白居易詩人自覺研究》第三章第五節“盡責的任官態度所產生之‘不自信’心態”,臺灣“中山大學”2007年博士論文。、焦尤杰(2)焦尤杰從理想的崇高和知足心態分析白居易慚愧心理產生的原因,并提出辭官、飲酒和信佛是擺脫慚愧的途徑,而事實上,知足與慚愧的關系并非是單線的,辭官以后白居易也未必不言慚愧,焦之觀點也有所偏,參考《從白居易詩歌看其居官慚愧心理及擺脫途徑》,《欽州學院學報》,2013年第9期。、土谷彰男(3)土谷大體上是從對君的慚愧轉向對民的慚愧這一點來分析韋、白二人慚愧情緒的共性的,參考《白居易青年時期的選良意識——白居易和韋應物的慚愧的比較》,《中國文學研究》,2019年第43期。等,但尚未挖掘他慚愧表現中的矛盾,沒能深入地分析其慚愧情緒與其人生理想、思想觀念的關系。
在唐代詩人中,與白居易表現出相似的慚愧情緒的還有他的前輩詩人韋應物,假如對照韋、白二人的慚愧表現之異同,便能更深刻地分析中國詩人在詩歌中表現慚愧的原因、表現與影響,由此得以揭示緣何在白居易詩中,會展露如此高頻、如此復雜的慚愧情緒。
一 韋應物、白居易詩中慚愧之情的類似表現及其成因
(一)韋、白“進亦慚,退亦慚”的慚愧表現
韋應物、白居易慚愧表現的相似性,最集中地體現在二人不論是在位為官、積極進取,還是暫不在位、急流勇退之時,都以有愧之人自居,對自身的外在境遇和內在心性都多有不滿之處。韋之“踏閣攀林恨不同,楚云滄海思無窮”(《登樓寄王卿》)[1]( P162)一句很好地概括了這種不滿,即不管是隱逸還是做官都有遺憾;白之“但愧煙霄上,鸞鳳為吾徒;又慚云林間,鷗鶴不我疏”(《和朝回與王煉師游南山下》)[2](P1760)以“正言若反”的方式,道出自己既不配在人才濟濟的朝廷為官,又因凡俗之性未退,羞慚于在林間與高人隱士交往的心境。
具體而言,意欲在官場上有所“進”的二人,表現出了因未能盡到為官的責任,同時又違背隱逸的志向而感覺到的慚愧,這種慚愧更多地表現為一種無力感。如,韋應物將其郡守的職責稱為“累”,一方面,他不斷想要擺脫這種世俗的負累,逃離“煩”與“倦”的為官心態:
符竹方為累,形跡一來疏。[1]( P461)
(《游開元精舍》)
常負交親責,且為一官累。[1]( P354)
(《答故人見諭》)
公府適煩倦,開緘瑩新篇。[1]( P343)
(《酬張協律》)
同時提出自己雖然勤苦于政務,卻又因政拙、無術而深感慚愧:
風物殊京國,邑里但荒榛。賦繁屬軍興,政拙愧斯人。[1](P328)
(《答王郎中》)
牧人本無術,命至茍復遷。[1](P328-329)
(《答崔都水》)
政拙勞詳省,淹留未得歸。[1](P199)
(《贈李判官》)
特別是官事暫罷,得以小憩之時,他愈發感覺到自己的片刻逍遙對不起皇帝的恩寵:
自慚居處崇,未睹斯民康。[1](P55)
(《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
即使在大有作為的尚書省、任宰相的協助者左司郎中的職位,韋應物慚愧于自己居然擁有官員身份的情緒,也無法抑制:
顧跡知為忝,束帶愧周行。[1](P499)
(《夜直省中》)
另一方面,與“擺脫負累”的愿望相應和,韋應物還在郡齋暫憩的場合,提到自己存有“退意”,即隱逸的志向:
日夕思自退,出門望故山。[1](P66)
(《高陵書情寄三原盧少府》)
每慮觀省牽,中乖游踐志。[1](P186)
(《因省風俗與從姪成緒游山水中道先歸寄示》)
朝宴方陪廁,山川又乖違。[1](P340)
(《答令狐侍郎》)
韋應物是一個具有強烈的游賞山水、隱逸山林的愿望的詩人;本來在他的心靈圖式中,“既歡懷祿情,復協滄州趣”,仕與隱并非不能調和,但現實卻屢屢事與愿違,正因不能徹底從官場中脫身,便導致了其在短暫的郡齋休憩里,也不能在山水的懷抱中得到愉悅感。上言之“乖志”,正是因無能感所造成的“慚”“愧”的寫照:
宰邑乖所愿,僶俛愧昔人。[1](P527)
(《西澗種柳》)
徒令慚所問,想望東山岑。[1](P314)
(《答馮魯秀才》)
與韋應物類似,白居易時常感覺有愧于自己現時的官位,因為自己沒有才能,甚至是一個“虛薄”“懶慢”之人:
自愧阿連官職慢,只教兄作使君兄。[2](P1917)
(《奉送三兄》)
虛薄至今慚舊職,院名抬舉號為賢。[2](P1515)
(《晚春重到集賢院》)
昔余謬從事,內愧才不足。
連授四命官,坐尸十年祿。[2](P107)
(《納粟》)
回首從前,提到自己能坐穩官位,不過是碰到了好時機:
偶當谷賤歲,適值民安日。
郡縣獄空虛,鄉閭盜奔逸。
其間最幸者,朝客多分秩。[2](P1712)
(《六年春贈分司東都諸公》)
甚至連自己的妻子都不配加封:
我轉官階常自愧,君加邑號有何功。[2](P1532)
(《妻初授邑號告身》)
在公務的閑暇,白居易亦想到自己還處在塵世中的汲汲宦場,未能滿足隱逸的心愿,與韋應物時常流露的情緒一致,且其隱逸的愿望較韋更為強烈,出現的頻次更高:
今年到時夏云白,去年來時秋樹紅。
兩度見山心有愧,皆因王事到山中。[2](P1025)
(《再因公事到駱口驛》)
遙愧峰上云,對此塵中顏。[2](P463)
(《病假中南亭閑望》)
顧我猶俗士,冠帶走塵埃。
未稱為松主,時時一愧懷。[2](P889)
(《庭松》)
悔從白云里,移爾落囂塵。[2](P728)
(《寄題周至廳前雙松》)
見君五老峰,益悔居城市。[2](P619)
(《題元十八溪亭》)
自慚容鬢上,猶帶郡庭塵。[2](P1929)
(《題報恩寺》)
不論是作為隱逸之符號的山,還是山上的云,不論是山下的松,還是清凈的寺廟,都讓白居易自慚形穢。與韋不同的是,白以無法隱逸為愧的詩作中,還突出了由老、病與愁帶來的時間的迫促感,強調為官是出于回報君恩,但志業的實現總是充滿重重阻礙:
病添心寂寞,愁人鬢蹉跎。
晚樹蟬鳴少,秋階日上多。
長閑羨云鶴,久別愧煙蘿。
其奈丹墀上,君恩未報何。[2](P1070)
(《晚秋有懷鄭中舊隱》)
唯慚老病披朝服,莫慮饑寒計俸錢。[2](P1504)
(《早朝思退居》)
與“進”的狀況相對,即使韋、白兩人已經完全處于“退”的狀況,仍然時不時有慚愧的感覺涌現出來,韋應物的名作《晚歸灃川》正說明了這樣的情形:
名秩斯逾分,廉退愧不全。
已想平門路,晨騎復言旋。[1](P389)
平門是長安的城門,還想著平門的路意味著韋應物并非甘心退出官場、離開長安,辭官歸隱本身,是讓韋遺憾甚至慚愧的。由此可見,韋應物的官吏意識已經在心中生了根,即使是歸隱了,也還在慚愧自己過去沒有“當好官”,現在也沒能從官場好好退出。當白居易真正選擇閑職,過上類似隱逸的生活之時,他亦深感“退而有愧”,不過其慚愧之意較韋顯得更復雜:
好住舊林泉,回頭一悵然。
漸知吾潦倒,深愧爾留連。
欲作棲云計,須營種黍錢。
更容求一郡,不得亦歸田。[2](P1996)
(《答林泉》)
衡門蝸舍自慚愧,收得身來已五年。[2](P2241)
(《履道居三首·其二》)
杭老遮車轍,吳童掃路塵。
虛迎復虛送,慚見兩州民。[2](P1873)
(《去歲罷杭州今春領吳郡慚無善政聊寫鄙懷兼寄三相公》)
朝客應煩倦,農夫更苦辛。
始慚當此日,得作自由身。[2](P2198)
(《苦熱》)
由上述詩句可知,首先,令白居易感到慚愧的是,他退居以后,仍然是窮困潦倒的,為了營生,他仍然需要“進”;其次,“退”時回想過往,深感于為官之道有所欠缺,于是,他竟然得出了自己不配為“自由身”的結論,即處“退”仍有所思慮,心靈無法平靜,這與一般觀念所想象的中國詩表達的寧靜致遠的隱逸情調有極大的落差。加之,白居易任州府長官之時,對統管、治理的區域,乃至其中的州民依依不舍,他慚愧于未能將民眾的生活提到更高的水準線上。
(2)韋、白“進亦慚,退亦慚”的成因
對中國歷代文人影響最大的儒家思想,成就了韋應物與白居易二人慚愧意識的表達。孔子雖未明言“慚”,但已稱“吾日三省吾身”,《孟子》中更直接出現了對慚愧意識的具體論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樂也”;更重要的是,孟子把“羞惡之心”納入四端之一的“義”上,提出羞恥感是人類重要的道德情感之一;由此,“恥感意識”作為儒者自省的內在思想傾向,逐漸在古典文人的潛意識層面生根。
韋、白二人之慚愧表現得較他人突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兩者以儒家思想為價值基礎。
首先,二人都積極仕進。韋應物以儒家用世思想為核心人生觀。肅宗乾元二年(759),韋入太學讀書,接受儒家正統思想的教育,此后,他始終沒有遠離仕途的念頭。無論是早年所作的“愧無鴛鷺姿,短翮空飛還。誰當假毛羽,無路相追攀”(《觀早朝》)[1](P440),還是晚年教育子侄的“纻衣豈寒御,蔬食非饑療。雖甘巷北簞,豈塞青紫耀。郡有優賢榻,朝編貢士詔。欲同朱輪載,勿憚移文誚”(《題從侄成緒西林精舍書齋》)[1](P485),皆是渴仕之辭。韋應物一生多次隱居,但每一次隱居之后官位都有所提升。其詩“不能林下去,只戀府廷恩”(《示從子河南尉班》)[1](P70)、“罷官守園廬,豈不懷渴饑”(《洛都游寓》)[1](P445),更表明在隱逸與從宦之間,他會毫不猶豫選擇后者。韋之隱居更多出于策略之隱,比如因為家庭經濟的貧困而暫時居住在寺廟中休養生息,因此不能將他看作一個隱士,反而正是因為他的隱,才顯示出他對仕途不變的追求。與之相似,白居易“世敦儒業”(《舊唐書·白居易傳》)[3](P4340),試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入仕之后,更以“兼濟天下”為志向,以入相為目標,積極進諫,乃至遭貶和遭斥。韋、白二人對仕進有如此強烈的愿望,但現實往往不能完全滿足他們,或是社會的不穩定,或是上位者的阻撓,導致了他們在宦途上或多或少地承受著挫敗。我們可以在兩人訴說慚愧情緒的詩作中體會“進而有難”的狀況:韋應物的“仰恩慚政拙,念勞喜歲收”(《襄武館游眺》)[1](P463)、“逍遙池館華,益愧專城寵”(《春游南亭》)[1](P457),白居易的“我為同州牧,內愧無才術。忝擢恩已多,遭逢幸非一”(《六年春贈分司東都諸公》)[2](P1712)、“身為百口長,官是一州尊……病難施郡政,老未答君恩”(《晚歲》)[2](P1609)所體現出的慚愧情緒,從積極的層面上看,成為二人在為官道路上努力進取的動力;從消極的層面看,是因“政拙”而無法回報“君恩”、略顯迂腐的書生氣的表現。
其次,韋、白二人不僅積極仕進,對儒家提倡的道德亦十分重視。韋、白二人同樣具有剛直的性情,且均更多地表現在因“為國”而“忠君”上,這與儒家之價值觀念是相符的。
韋應物曾自我評價“守直雖多忤,視險方晏如”(《再游西山》)[1](P458),又自言“方鑿不受圓,直木不為輪”;白居易自言“況余方且介,舉動多忤累”,可知,白與韋的自我認識在內在之“直”與外在之“忤”上是高度相似的。史官作為蓋棺定論者,對白居易的道德評價也很高。《新唐書·白居易傳》的“史臣論”作了如此表述:
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為進取計,完節自高。[4](P4305)
性情忠直的詩人,不免以其性情書寫詩作,干預現實政治。可以說,白居易的諷喻詩創作是終生不歇的,雖然后世之人更認同的是他貶謫江州之前所作的諷喻詩,或許功在迎合上峰的時機,又或許功在白本人以編集的形式所進行的“鼓吹”。
值得一提的是,給予白居易諷喻詩創作最大影響的前代詩人,正是韋應物。白《與元九書》中首肯的便是韋“興諷”性質的歌行:“近歲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韋之創作,在諷刺的手法和力度上也的確與白之評價一般別無二致,其《長安道》《貴游行》《夏冰歌》《鼙鼓行》《采玉行》等歌行體的作品也直接給白“新樂府”以形式、內容甚至風格上全方位的借鑒模板。即使脫離“歌行”的形式,白仍將韋《漢武帝雜歌三首》等“以漢喻唐”痛心民隱、痛責權貴的“興諷”詩風放置到《秦中吟》《雜體五首》等作品中,形成具有新的風格的諷喻詩歌。除了以現實故事興諷之外,韋、白二人還共同表現出以“禽鳥寓言”興諷的傾向,比如,韋應物有《烏引雛》《鳶奪巢》《燕銜泥》諷刺現實,白居易的《新樂府·秦吉了》《烏夜啼》《和答詩十首·和大觜烏》《池上寓興》《池鶴八絕句》《禽蟲十二章》《山中五絕句》等亦寄托了詩人的憤慨和憂慮。白《續古詩十首》對韋《擬古詩十二首》的全盤承續,則體現出韋、白二人從儒家思想的角度,對歷史上的士人生存狀態的反思。《古詩十九首》“文溫以麗”,影射現實的傳統,韋不獨“才麗”更融于“興諷”,白則以“復六義”的詩學思考和實踐創作名之為續、實之為復的模擬之作,表達對社會現象、人性內涵的戚戚之感,儒家思想影響下的感傷傳統以諷寫感,以感表諷,從二人對“古詩”這條承繼的線索也可以看出來。
由二位詩人之詩所反映的政治理想來看,他們不但忠于君主、意欲仕進,且意欲為民得利,導致了二人更深層次慚愧意識的展現。在蕓蕓百姓之中,韋、白二人最感愧疚的對象,是農民。戰爭導致的土地喪失與兼并,讓農民流離失所,無法耕種;即使戰爭結束,剛剛恢復耕種的農民又因為繳不起稅,而陷入赤貧。韋應物慨然長嘆“何當四海晏,甘與齊民耕”,亦深刻地揭示了要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就必須先解決國家、戰爭的問題。兩位“不耕者”思考農民問題角度竟然驚人的一致:
微雨眾卉新,一雷驚蟄始。
田家幾日閑,耕種從此起
……
饑劬不自苦,膏澤且為喜。
倉廩無宿儲,徭役猶未已。
方慚不耕者,祿食出閭里。[1](P452)
(韋應物《觀田家》)
田家少閑月,五月人倍忙。
……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
吏祿三百石,歲晏有余糧。
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2](P22)
(白居易《觀刈麥》)
兩詩表現手法雖有所差異,但表現的視角卻驚人的相同:詩題中的“觀”點出了兩位詩人旁觀者的身份,正因為只是旁觀,使得他們無法替農民分憂,甚至還要從農民的勞動所得中分得一杯羹,詩句“方慚不耕者,祿食出閭里”與“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表現了同出一轍的慚愧情緒。即使暫時不在官位上,只要韋、白二人“有閑”,便會用類似的視角,觀農人以觀己,以慚愧表現自省。比如韋應物“公門日多暇,是月農稍忙。高居念田里,苦熱安可當”(《夏至避暑北池》)[1](P484)。在辦公之余,閑暇避暑的時間里,韋應物仍然惦記著在田中辛苦勞作的農人們,擔憂他們抵擋不住暑熱。又如白居易“自慚祿仕者,曾不營農作。飽食無所勞,何殊衛人鶴”(《觀稼》)[2](P547)。在一片閑適與喜悅的氣氛中,白居易與獲得豐收的農人友善地飲酒交談,農人“勤且敬”的勞作讓白自愧弗如,“筋力苦疲勞,衣食常單薄”的生活又不得不引起人的憂心。
韋應物之仕宦歷程中,最為人稱道的是其作為一州刺史有著清廉的官聲與不俗的政績。韋在江州刺史、滁州刺史、蘇州刺史任上,均以勤為吏政的循吏心態為政且有所作為,他的政治作為在他的許多詩作中被保留下來:
到郡方逾月,終朝理亂絲。
賓朋未及宴,簡牘已云疲。
昔賢播高風,得守愧無施。
豈待干戈戢,且愿撫惸嫠。[1](P505)
(《始至郡》)
自嘆乏弘量,終朝親簿書。[1](P458)
(《再游西山》)
同韋應物一樣,白居易既做過江州刺史,又做過蘇州刺史。他雖然不以刺史之職為炫耀的資本,但也不忘竭盡所能做一名良吏:
自顧才能少,何堪寵命頻。
冒榮慚印綬,虛獎負絲綸。
候病須通脈,防流要塞津。
救煩無若靜,補拙莫如勤。
削使科條簡,攤令賦役均。
以茲為報效,安敢不躬親。
襦袴提于手,韋弦佩在紳。
敢辭稱俗吏,且愿活疲民。(4)見《自到郡齋僅經旬日方專公務未及宴游偷閑走筆題二十四韻兼寄常州賈舍人湖州崔郎中仍呈吳中諸客》,該詩自注寫道:“除蘇州制云:‘藏于己為道義,施于物為政能。在公形骨鯁之志,闔境有袴襦之樂。’”見《白居易詩集校注》,第1876—1877頁。[2](P1876-1877)
在這些透露地方官員的小心翼翼與兢兢業業的字字句句中,慚愧自己的吏能不足,或者說前文所言之“政拙”,是良吏心里繞不過去的自省情結。與之相對同時又被韋應物強調的,是對仍然處于生活困境的百姓的惦念與關心,是即使以“游”暫時擺脫俗物困擾,還縈繞在心頭的“未完成使命”的歉疚:
受命恤人隱,茲游久未遑……物累誠可遣,疲甿終未忘。[1](P477)
(《游瑯瑘山寺》)
明人劉須溪曾提到“韋應物居官,自愧閔閔,有恤人之心”[5](P399);清人喬億與劉之觀點暗合——“韋公多恤人之意”[6](P1172),似乎以韋“受命恤人隱”的自述為依據。在這些真誠地表現慚愧情緒的詩句中,真誠度最高、恤人之心最著的是堅持嚴律的酷吏意識和堅持民本的循吏意識兩者所產生矛盾之時,韋應物所表現出的煎熬和無措:
甿稅況重疊,公門極熬煎。
責逋甘首免,歲晏當歸田。[1](P323)
(《答崔都水》)
斯民本樂生,逃逝竟何為。
旱歲屬荒歉,舊逋積如坻。[1](P505)
(《始至郡》)
行政時,官員采用酷吏的手段是無法避免的。傅璇琮曾經提及韋應物任蘇州刺史之時,為了催逼民眾繳納賦稅的一些嚴酷事跡[7](P319):其一是李觀代一位彝姓之人寫信向韋應物道歉;其二是戴察賣琴賣書繳納賦稅;此二事件中韋應物未必直接行使了苛政、對象也不能說是平頭百姓,可見當時的百姓因為稅收的繁重而難以安居更是事實。韋應物意識到了人民的困苦和窘迫,但又不能不完成稅收的任務,這樣的矛盾心理也成為慚愧情緒的要因。
與韋應物一樣,白居易在處理郡務上,亦面臨酷吏意識和循吏意識的矛盾。不過,白居易的酷吏意識相對于韋應物,出現得更早、更為自覺,甚至已經形成了和循吏意識分庭抗禮的趨勢。邵明珍指出,白居易早年的詩作《放鷹》是給唐皇朝的統治階層的、有關如何駕馭臣子的說明書;白居易全體詩作中的“鷹喻”,均以猛禽鷹象征為君之左膀右臂的酷吏的。[8](P130)如果說韋應物“上懷犬馬戀,下有骨肉情”以犬馬戀和骨肉情并言,表現了其對李唐王室的深深依戀乃至親情般的情感寄托,是自降人格的忠君表決的話,那么,白居易的“鷹爪之譬”則是鋒利而高姿態的表忠體現。然而,在蘇州實踐吏治的時候,白居易看到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蕓蕓百姓,不禁因自喻為“鷹爪”的自己而升騰出愧意:
公私頗多事,衰憊殊少歡。
迎送賓客懶,鞭笞黎庶難。[2](P1683)
(《自詠五首·其三》)
浩浩姑蘇民,郁郁長洲城。
來慚荷寵命,去愧無能名。[2](P1691)
(《別蘇州》)
由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這兩位立志為人民辦實事、辦好事的詩人官員身上,所存在的循吏和酷吏意識的矛盾,亦是導致其慚愧情緒產生的主要原因。
當然,做一名良吏并不像想象得那么容易,直接復制某個模板的“紙上談兵”顯然不是良方;更難的是,如何完美地接納可能沒有達到良吏的標準的自我。比如,韋應物時有負氣之論:
方鑿不受圓,直木不為輪。
揆材各有用,反性生苦辛。
折腰非吾事,飲水非吾貧。
休告臥空館,養病絕囂塵。[1](P495)
(《任洛陽丞請告一首》)
此外,韋之郡齋詩中時常提到“宴集”,之所以如此,正是為了調劑為政之苦。韋此詩之句“群公盡詞客,方駕永日游。朝旦氣候佳,逍遙寫煩憂”“遽看蓂葉盡,坐闕芳年賞。賴此林下期,清風滌煩想”“煩疴近消散,嘉賓復滿堂”,看似營造了一種散淡的氣質,但實際是詩人消解內心矛盾,舒緩負累感和愧疚感的方式。
至于白居易,他常常直接感嘆刺史工作的勞苦,言及一郡之長需要平衡各方勢力,十萬戶的郡民和五十口的郡廳工作人員都需要“給養”,天時的寒暖、關系民生的一切問題更需要及時的解決。不過,作為父母官是不能輕易說苦的,身在苦中卻必須甘之如飴,這才符合儒家的觀念與說教:
一家五十口,一郡十萬戶。
出為差科頭,入為衣食主。
水旱合心憂,饑寒須手撫。
何異食蓼蟲,不知苦是苦。[2](P1682)
(《自詠五首·其二》)
韋、白為了能夠在詩中“云淡風輕”地表現良吏的生活,花費了大量的情緒成本,于此,以閑適為審美趣味的郡齋詩字里行間透露出了絲絲點點的苦味。“身處其位,仍覺己苦”的不該是導致慚愧情緒產生的另一要因。二人不能言苦的平淡詩句與嚴苛的良吏標準所帶來的情緒拉扯,營造了詩作內部更為強大的情感張力。
二 韋應物、白居易詩中相異的慚愧表現與成因
(一)詩歌表現慚愧廣度和深度的差異
1.白詩表現慚愧的廣度大于韋詩
白居易同韋應物表現慚愧之最大的不同,在于其詩“事事”“時時”表現慚愧的驚人廣度。如果說韋應物的慚愧投射出一個封建文人乃至官員的君臣意識和社會理想的話,白居易的慚愧則常常表現出接近于平凡人的樣態。
首先,在官位職階不如別人的時候,白居易便流露出羞慚的情緒,其心靈視野全然與凡俗之人等觀齊論:
虛薄至今慚舊職,院名抬舉號為賢。[2](P1515)
(《晚春重到集賢院》)
五侯三相家,眼冷不見君。
問其所與游,獨言韓舍人。
其次即及我,我愧非其倫。[2](P574)
(《酬張十八訪宿見贈》)
流落多年應是命,量移遠郡未成官。
慚君獨不欺憔悴,猶作銀臺舊眼看。[2](P1419)
(《重贈李大夫》)
不論是不配舉號集賢、不配與韓舍人同倫,或是量移貶謫后官位不及銀臺之上的要員,仕進路上的挫折都造成了白居易強烈的愧意,而此等愧意接近于一般人所認知的自卑感。
其次,白居易時常因為過于關注自己的外貌是否老丑,而與他人比較。當他自感老丑或比較以落敗告終便會感到感傷。大多時候,他亦不忘自己為自己設定的“樂天知命”的志趣,即使在無病呻吟式地表現對自己老丑容貌的慚愧時,還要故作灑脫地以調侃的語氣寫出,甚至竭盡全力地表現出對現狀的滿足,像是在一場又一場刻意的演出中,吐露著言不由衷的臺詞:
我慚貌丑老,饒鬢斑斑雪。[2](P795)
(《以鏡贈別》)
我歸應待烏白頭,慚愧元郎誤喜歡。[2](P843)
(《答元郎中楊員外喜烏見寄》)
且喜身無縛,終慚鬢有絲。
回頭語閑伴,閑校十年遲。[2](P2140)
(《游平泉贈晦叔》)
半頭白發慚蕭相,滿面紅塵問遠師。[2](P1555-1556)
(《蕭相公宅遇自遠禪師有感而贈》)
病肺慚杯滿,衰顏忌鏡明。[2](P1342)
(《潯陽歲晚寄元八郎中庾三十二員外》)
每愧尚書情眷眷,自憐居士病綿綿。
不知待得心期否,老校于君六七年。[2](P2769)
(《以詩代書酬慕巢尚書見寄》)
上述詩作中,白因為滿頭白發而自感老丑,覺得自己不配得到別人的喜歡,甚至連照鏡子都會產生自我厭惡感,回過頭來,他又體會到自己已經不再年輕,和別人比年齡不再有任何優勢,剩下的只有濃濃的“慚愧”:不但遺憾自己曾經枉費時光,還自卑于現在老病的自己無法在閑適的生活中獲得真心的愉悅。
再次,白居易在詩中時常表現出對親人,特別是妻兒的愧疚,這在韋詩中也是罕見的。親人和眾人不同,是被儒家文化所特重的角色。白居易對妻兒的愧疚,亦源自儒家思想的差等觀念與自省意識:
藥停有喜閑銷疾,金盡無憂醉忘貧。
補綻衣裳愧妻女,支持酒肉賴交親。[2](P2798)
(《狂吟七言十四韻》)
老去愧妻兒,冬來有勸詞。
暖寒從飲酒,沖冷少吟詩。
戰勝心還壯,齋勤體校羸。
由來世間法,損益合相隨。[2](P2456)
(《老去》)
自己的貧病連累到家人,自己的任性讓家人不安,在白居易看來,都必須去反省一下。不過,白對家人的愧疚,其情感力度顯然是低于對民眾困苦的反思的,他會合理化自己的行為,把對家人的愧疚放在“由來世間法,損益合相隨”的感悟后面。由此可見,愧疚是優先于反省擺出的某種姿態,此種狀態下白居易反省的結果卻是合理化自己“先己后親”的行為。
最后,白居易在享受飽足、溫暖時,常常流露出自己配不上優裕生活的慚愧之意,似出于己身不能滿足儒家“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對士人高標準的道德要求:
省躬念前哲,醉飽多慚忸。
君不聞靖節先生尊長空,廣文先生飯不足。[2](P2314)
(《春寒》)
食飽慚伯夷,酒足愧淵明。
壽倍顏氏子,富百黔婁生。
有一即為樂,況吾四者并。
所以私自慰,雖老有心情。[2](P2257)
(《首夏》)
勞生彼何苦,遂性我何優。
撫心但自愧,孰知其所由。[2](P2720)
(《新沐浴》)
陷入困頓而德行愈發光輝的前哲與困苦無著的羈囚,都能夠引發白居易在道德上的自省,只是他的自省并非都導向對美、善的追求,有時反而是以一種別扭的、試圖消除高尚道德感的自慰來結尾,甚至于他也不曉得“愧”從何而來,“撫心但自愧,孰知其所由”,似乎只是為了愧疚而愧疚,為了反省而反省。
白詩出于道德自省的慚愧表達,呈現出格套化的傾向。他的“慚愧”往往是由人及己的,即從對他人困苦境遇的惻隱之心轉向在自我較優的境遇比較下的“慚愧”,或是他人境遇較佳自己未能與之比肩,無能而“慚”;對比韋應物而言,白之過分提及、強調慚愧情緒,斤斤計較,與凡俗的距離過近,反而造成了文學情感上的“不動人”、思想表達上的“沒厚度”。
2.韋詩表現慚愧的力度強于白詩
白居易以慚愧表現的自省,不若韋應物的自省勇敢、堅決,從二人詩歌中所表現的情緒力度的強弱可以感受出來。韋應物之詩的本身即在真誠改過。懺悔的概念,來自佛教(5)懺悔實際上是梵語和漢語合成詞,“懺”是梵文懺摩的音譯之略,是“容恕我罪”之意,于是,懺悔一詞中,懺指陳露先惡,悔指改往修來,見丁福保《六祖壇經箋注》,齊魯書社2012年版,第138頁。,慚愧與懺悔都因心靈的震顫在情感上表現出強烈的不安,但懺悔具有比慚愧更大的情緒力度,韋詩所表現的接近懺悔:
生長太平日,不知太平歡。
今還洛陽中,感此方苦酸。
飲藥本攻病,毒腸翻自殘。
王師涉河洛,玉石俱不完。
時節屢遷斥,山河長郁盤。
蕭條孤煙絕,日入空城寒。
蹇劣乏高步,緝遺守微官。
西懷咸陽道,躑躅心不安。[1](P424)
(《廣德中洛陽作》)
韋應物的懺悔,是中國古典詩人中少見的、極度真誠的自我反省。上述詩作中,他從少不更事時“不知太平歡”反思起,批評王師的剛愎自用,導致整個時代的潰決,他痛切地找到癥結并想要拔出毒瘤,可以說,他的不安不僅是一種樸素的直覺,還帶著對無力改變現實、自我轉變不夠徹底的慚意。如果說這樣的慚意不夠具體的話,下面的這首詩則巨細靡遺地展露出他荒唐的前半生:
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
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
朝持樗蒲局,暮竊東鄰姬。
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
驪山風雪夜,長楊羽獵時。
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
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
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
兩府始收跡,南宮謬見推。
非才果不容,出守撫惸嫠。
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
坐客何由識,惟有故人知。[1](P361)
(《逢楊開府》)
上述詩中,韋應物所懺悔的不是自己無傷大雅的、道德上的小瑕疵,而是從學識、作風、性情全面地懺悔少年時的胡作非為,“改過”而得“今是”固然沒有被他所忽略,卻不是他所強調的,處于“今是” 狀態下的自己并不是完美無缺,讓人無可挑剔、交口稱贊的,“論舊涕俱垂”的懺悔姿態才是他意欲突出的。
相比于韋應物,白居易的懺悔往往來自人生的某一個截斷面,且頗有“今是昨非”之感,“昨非”是作為“今是”的對照組出現的,“今是”才符合白詩中的真意。白居易《和夢游春》《渭村退居》《東南行》等長韻敘事詩作均以書寫人生剛剛踏上仕途、面對榮光時的心理迷失為主題。此類詩作反映出隨著對佛禪思想理解的加深,白居易開始意識到后悔、懺悔是一種無益的情緒,“必若不能分黑白,卻應無悔復無尤”,把握當下的每一個瞬間,做到是非分明、判斷精準,就不會有后悔和怨恨的情緒。白刻意地避免、克制懺悔情緒,或許只是出于一種逃避的心態。
白詩中還有一種韋作沒有的抵擋慚愧情緒散發的傾向,亦弱化了其詩慚愧表達的力度。白居易體認自己為“性拙”之人,因此不合時宜,不適應官場,而這種“拙”既是生而即來,便不必感覺慚愧:
我性愚且蠢,我命薄且屯。
問我何以知,所知良有因。
亦曾舉兩足,學人蹋紅塵。
從茲知性拙,不解轉如輪。
亦曾奮六翮,高飛到青云。
從茲知命薄,摧落不逡巡……[2](P552)
(《詠拙》)
既登文字科,又忝諫諍員。
拙直不合時,無益同素餐。[2](P561)
(《游悟真寺詩》)
我受狷介性,立為頑拙身。
平生雖寡合,合即無緇磷。[2](P574)
(《酬張十八訪宿見贈》)
晚遇緣才拙,先衰被病牽。
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緋年。
身外名徒爾,人間事偶然。
我朱君紫綬,猶未得差肩。[2](P1526)
(《初著緋戲贈元九》)
自慚拙宦叨清貴,還有癡心怕素餐。
或望君臣相獻替,可圖妻子免饑寒。
性疏豈合承恩久,命薄元知濟事難。
分寸寵光酬未得,不休更擬覓何官。[2](P1581)
(《初罷中書舍人》)
在不同時段充滿“拙”的論調里,白居易強調自己與一般人無異,甚至更劣,是“才拙”之人,所以在宦途上晚得成功,并屢屢遭受跌挫。他又意識到“性拙”才是造成這一切的根本原因,“拙直不合時”“我受狷介性”“我性愚且蠢”,本性蠢鈍無力改變,加之“我命薄且屯”,命是天定的,強求不來,只能選擇認命。勉勵自進并不是順應天命,過分哀傷也是沒有必要的,“窮而樂”才是得以“終吾身”的正確徑路。“拙”與“慚”在白居易大多數詩作中是一對性情互補、正負互嵌的概念。只要以“拙”為前提,強調了自己的“拙”性,就不必有慚愧的情緒,便能實現人生境界的超越。與之相對的,如果宣告了自己處于“慚”的心境中,“拙”的有效性就會大大減弱,因為真正具有“拙”性的人是不會被外在世界,以至內在心靈所煩擾的,所以在表現慚愧情緒的場合,白居易幾不言其“拙”。在“拙”與“慚”的宣言中搖擺的詩人白居易,不但大大降低了他詩中慚愧的力度,還陷入了自我懷疑和自我形象建構破碎的境遇中。對比韋應物詩中的“拙”,雖言及“工拙”“拙直”,但并未與自我命運建立關聯,且韋詩中之“政拙”,較白主觀假想的自我能力不足而言,更多是客觀呈現政務復雜難以處理的情況:“淹留未得歸”(《贈李判官》)[1](P199),“賦繁屬軍興”(《答王郎中》)[1](P328),“念勞喜歲收”(《襄武館游眺》)[1](P463)。這些或喜或憂的情緒是具體可感的,因其真而更具有文學感染力。
(二)造成韋白詩歌相異慚愧表現的原因
1.白詩時時表現慚愧的原因
較韋應物而言,白居易詩在更多的方面表現或深或淺的慚愧,與其個人出身、性格與思想信仰均有關聯。
其一,與韋應物相比,白居易求仕時優先考慮的是經濟因素,雖然韋、白人生中都曾經歷過困頓與貧窮,但韋詩不過是嘆“家貧”,如“家貧無舊業”(《發廣陵留上家兄兼寄上長沙》)[1](P85),“停杯嗟別久,對月言家貧”(《將發楚州經寶應縣訪李二忽于州館相遇月夜書事因簡李寶應》)[1](P357),“家貧無童仆”(《答裴丞說歸京所獻》)[1](P332),“家貧何由往,夢想在京城”(《寓居永定精舍》)[1](P510),且其“家貧”的狀況只短暫地存續在少年時期;而白詩更多地反映其不同時期的經濟狀況,特別是對俸祿及其背后安穩享受生活的在意:
冒寵已三遷,歸期始二年。
囊中貯馀俸,園外買閑田。[2](P1543)
(《新昌新居書事四十韻因寄元郎中張博士》)
三年請祿俸,頗有余衣食。
乃至僮仆間,皆無凍餒色。[2](P703)
(《自余杭歸宿淮口作》)
欲作棲云計,須營種黍錢。
更容求一郡,不得亦歸田。[2](P1996)
(《答林泉》)
白居易在人生各個階段所做的選擇,均出于“求俸”的目的,不論是任中書舍人、一郡之守甚至分司東都,詩中不落余俸、祿俸、種黍錢等字眼;但選擇物質過后,冷靜下來,卻不免產生了道德上的自責,陷入慚愧的情緒。其詩句“慚愧稻粱長不飽,未曾回眼向雞群”(《有雙鶴留在洛中,忽見劉郎中,依然鳴顧,劉因為〈鶴嘆〉二篇寄予,予以二絕句答之》)[2](P1990)正是白借鶴之口,表達高潔之志未能完成的遺憾,通過描繪鶴的睥睨姿態反襯出自己的凡庸。
其二,白居易出身中層階級。與出身貴族的韋應物不同,白一直懷揣著階層躍升的愿望,因此,他的內心時常有一種與周圍的人比較的傾向與欲望。不論是作詩的才華、園林的大小、官位的高低,還是年齡的大小、樣貌的美丑,都會引起他的比較,只要自己落入下風,他類似自卑的慚愧情緒便會滋生。前文曾提及,白居易書寫為官時的慚愧,好談病與愁,正是與他人比較的心態作祟;同時,也因為他的健康過早地被損害,樣貌出現了早衰的現象,身體也跟不上奔放的心靈,他更是陷入自怨自艾的情緒中無法自拔,于是進入惡性循環的狀態。
其三,白居易是一位極度真誠的詩人,他的詩歌,可以說幾乎是他人生的忠實記錄,在詩中書寫“本我”來體現“自我”是他詩歌突出的抒情特色之一。加之白居易自言其詩“理周而辭繁”(《和答詩十首序》)[2](P212),即有“好盡”的特點,故他所展現的“我”,幾乎是全方位的、優缺點盡現的。一個真誠的人,又不可能不是一個會自我反省的人,因此,白居易詩處處都有慚愧,處處都帶著他自我懷疑與自我批判的痕跡。雖然他的部分真誠表達透露出自我懷疑的傾向,導致自我形象的破碎,但人性正是如此,白居易文學形象表達的缺憾反倒凸顯了其為人為文的真與切。
雖然韋應物是白居易在為官與作詩這兩方面所崇拜的偶像,但白對為官與作詩關系的認識卻與韋有迥異之處,這亦導致了白詩所表現慚愧的廣度和內涵都與韋詩不同。韋應物在刺史任上固然也吟詩論句,亦有苦于政拙的慚愧自責,但幾乎未將二者同列考量。白對韋的肯認與接受,建立在其對韋詩酒風流與良政勤績并立同存的想象之基礎上,由此,當白詩中同時出現作為詩人的自滿與無法成為良吏的慚愧情緒的表達時,其中的慚愧情緒便值得玩味了:
三年為刺史,無政在人口。
唯向城郡中,題詩十余首。
慚非甘棠詠,豈有思人不。[2](P700)
(《三年為刺史二首·其一》)
太守三年嘲不盡,郡齋空作百篇詩。[2](P1829)
(《重題別東樓》)
不難發覺,白詩一邊表達著“勤懇為官者不應以空想作詩,作詩無益于行政,甚至應該被嘲笑”的慚愧,一邊又表達著“因為善詠詩所以成為州民心目中的好太守”的自得。他的慚愧并不是嚴肅的,更似以戲謔的語氣表達其對詩人身份的認同,“慚愧”于是成為他彌合官員身份和詩人身份的情感武器。他打卡式地敘己之“慚愧”,更像一個眾人皆知的口癖“慚愧慚愧”,為其詩增添了不少凡俗感。
2.韋詩深刻表現慚愧的原因
學術界并不缺乏對韋詩慚愧意識的研究,這些研究普遍認為,韋應物的懺悔既是在唐王朝面臨的種種憂患的情形下被激發出來的,又是對現時自我的不完善的不滿而導致的,所以,他的懺悔是外在因素和內在因素合力造成的結果。只是,因為缺少新鮮的研究思路,缺乏分析與對照,針對內在因素的分析在已有的論述中顯得很不足夠。筆者以為,與白居易比較,韋詩所表現的慚愧力度更大,原因在于:
其一,韋應物出身長安杜陵韋氏這樣的世家大族,曾祖父韋待價曾為則天朝宰相,祖父韋令儀曾任司門郎中 、宗正少卿,因為和皇室關系密切,所以比一般士人更加忠君、忠主,也有更強烈的社會責任感。韋應物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主要體現在其較一般士人更強的行動力上。本文上述所論韋與白同樣在為官時表現因“政拙”“無術”而感到慚愧的詩作中,韋想要改變為官之“拙”的現狀的行動便更為積極:不論是滁州任上“為郡訪凋瘵,守程難損益”(《郡樓春燕》)[1](P54),或是江州任上“到郡方逾月,終朝理亂絲”(《始至郡》)[1](P505),還是蘇州任上的“于茲省氓俗,一用勸農桑”(《登重玄寺閣》)[1](P439),都是他對政事親歷親為的寫照。相較于白居易晚年社會關懷的消退,韋應物的行為驅動力則保持了更長的時間,這便從側面說明了韋中青年時期之于己身的反省力度和效度都高于白。
其二,韋應物早年經歷與白居易不同。韋因門蔭得補右千牛,成為玄宗的貼身侍衛,過著放蕩不羈的生活,甚至在違法亂紀的邊緣游走,前文所引之《逢楊開府》便全錄了韋應物早年的荒唐生活。與之相反,白居易早年幾乎是在母親的悉心教育下成長起來的,苦讀詩書即為了入仕;同時,因為社會動亂、父親早逝、家庭貧困等原因,白長時間處在顛沛流離之中。因此,之于過去,韋應物需要“反省”的原本就遠遠多于白居易。加之,韋應物是武職出身,其個性氣質中“高歌長安酒,忠憤不可吞”(《送李十四山人東游》)[1](P211)的魄力自然比“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發早衰白;瞀瞀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者,動以萬數”(《與元九書》)[9](P321)的嘆老嗟貧的文弱書生白居易要強得多。韋應物“壯士斷腕”的魄力是他反省、懺悔之“破力”的最大原動力,白則相對缺乏深刻反省的原動力。
其三,韋應物親歷了安史之亂,目睹了安史之亂前的盛世繁華以及安史之亂后的殘破荒涼,因此性情、性格乃至看待事物的方式都發生了巨大的轉變。他原本“少年游太學,負氣蔑諸生”(《贈舊識》)[1](P203),但歷亂失去官職,失去皇帝的榮寵之后,他“憔悴被人欺”,于是他開始發奮讀書,力圖重新回到人生的正軌上。與此同時,國家之“干戈事變”亦讓他反思皇權,反思社會,除了創作一些諷刺詩之外,他亦意欲從改變自身開始改變社會現狀,不但直言“丈夫當為國,破敵如摧山”(《寄暢當》)[1](P164)、“一朝愿投筆,世難激中腸”(《始建射侯》)[1](P542),還在重新踏上為官之路的京兆府功曹任上為民奔忙,《使云陽寄府曹》[1](P98)一詩記錄下了全過程。他冒著炎暑,在大水剛退時跋涉災區,細心巡視災情。洪水退后,“良苗免湮沒”,他由衷地喜悅;但“蔓草生宿昔”“頹墉滿故墟”的現實依然觸目驚心,他直言“賤子甘所役”,即使是“周旋涉涂潦,側峭緣溝脈”亦無可厚非,可見其誓為好官之決心。相比于韋應物,白居易人生中并未經歷如此起伏的、從社會到人生的轉變,因此,二者由自省反思而引發的慚愧情緒的力度有所差異,自不足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