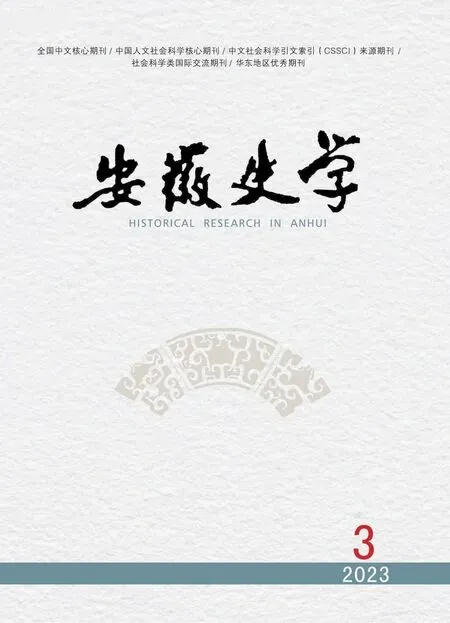灘田開發與界域糾紛
——清至民國時期蘇皖老子山劃界問題案例分析
易山明 陸發春
(安徽大學 歷史學院,安徽 合肥 230039)
行政區劃是中央與地方行政關系的產物,構成行政區劃的要素之一就是“邊界”。(1)周振鶴:《行政區劃史研究的基本概念與學術用語芻議》,《復旦學報》2001年第3期。傳統時期行政區域的劃界,大體遵循“山川形便”“犬牙交錯”(2)周振鶴:《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46頁。兩個相立相悖原則,缺乏有效的管理體系和規范化的爭端處置機制。常見地方志書以“四至八到”表示大致空間方位里程和所至地界,這種“宜粗不宜細”的模糊性表達,加之山川格局的演化變動,為相鄰界域之間可能爆發的邊界沖突埋下了隱患。晚清民國時期因邊界資源引發的爭端尤為多發,反映出人地關系緊張的格局愈發顯現。(3)徐建平:《中國近現代行政區域劃界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1頁。伴隨著人口大幅度增長和對經濟利益的追求,對變動中的邊界資源爭奪和利用,愈來愈成為誘發政區邊界爭議的重要因子。近年來,史學研究重心的下移是國際史學界普遍的趨勢,有關近代內地邊界的研究,無論從成果數量,抑或研究深度,尚有較大的拓展空間。鑒于此,本文將視角聚焦于晚清民國時期盱眙(4)盱眙縣原隸安徽省,1955年為加強洪澤湖管理,劃歸江蘇省。、淮陰(5)原為清河縣,1914年,因與河北省清河縣同名,改為淮陰縣。兩縣邊界問題,通過爬梳諸多關聯史料,結合田野調查,盡可能地“走向歷史現場”,逐步揭橥一場因洪澤湖灘田開發所引起的蘇皖兩省劃界紛爭,分析其多重社會面相和利益糾葛。
一、從山川形便到犬牙交錯:明代以來清河、盱眙間邊界的形成
明代以來,盱眙、清河兩縣之間多以老子山為界,但是老子山界限也經歷了從模糊到清晰的過程。清代民國時期,老子山隸屬清河縣管轄。今老子山鎮地處洪澤湖南岸,屬江蘇省淮安市洪澤區,南與盱眙縣接界,西、北、東三面臨湖,陸地上與洪澤區治所不相連屬。至遲到明代,老子山及其鄰近地域空間格局大抵已經構建成形,由此也萌生一個疑問,老子山一帶在最初劃隸清河縣之時的初始地理環境究竟是怎樣的,是否貼近“山川形便”或“犬牙交錯”的劃界原則呢?
歷史上的老子山并不能算是一個聲名遠播的地方,其地位的彰顯或可追溯至明清兩代清河縣“八景”之一(6)嘉靖《清河縣志》卷1,明嘉靖四十四年刻本,第7頁。,并與治黃、漕運、修建壩閘等工事有著密切聯系,而貫穿其中的正是洪澤湖的形成和演變過程。因此,有關老子山的記載多集中于地方志中。
明清方志對于老子山的敘述多集中于“疆域”“山川”“集鎮”幾目,如正德《淮安府志》載:“腦子山,去治東南一百里,在懷仁鄉。山勢自嵩高山延袤至此,又名老子山。云:老子煉丹于此,頂有紅石。”(7)正德《淮安府志》卷3,明正德十四年刻本,第9—10頁。此處提供的幾處位置信息可以大致廓清老子山所處的地理區位。該志是現存最早的《淮安府志》,其表述為后續史志所繼承,并屢有增補。如天啟《淮安府志》曰:“腦子山,治東南一百里懷仁鄉,山勢自嵩高山延袤至此,又名老子山。傳聞老子煉丹,頂有紅石,境接盱眙諸山,瀕富陵湖。”(8)天啟《淮安府志》卷2,鳳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48頁。由此可見,將老子山作為清河、盱眙二縣之界山,至晚在明代末年已得到官修志書的認可。
清康熙六年安徽建省,蘇皖分治后兩省之省域意識逐漸增強,并內化于各自編纂的地方志中,省級邊界也朝著更加明晰和精確的方向發展。清河、盱眙二縣的邊界記載已經不再滿足于先前的“幅帶狀”,康熙《清河縣志》明確將老子山南之“霍山”作為兩縣界限,“霍山在老子山南,形勢起伏,一峰崒然,跨盱眙、清河之間,上有東岳古廟,為清河南界”(9)康熙《清河縣志》卷1,臺北淮陰同鄉會1990年影印本,第9頁。,這一觀點被更高層面的乾隆《江南通志》(10)乾隆《江南通志》卷1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07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458頁。和國家地理總志康熙《大清一統志》(11)康熙《大清一統志》卷47,清道光九年木活字本,第6頁。所采納,進一步確認了“霍山”的邊界之實。
值得注意的是,蘇皖兩省之于邊界的認識并不同步。盱眙方面的縣志在提及與清河的邊界時,均未明確“霍山”,如乾隆縣志:“老子山在圣人山之東,淮河之涘,盱濱泗境清河之界”;(12)乾隆《盱眙縣志》卷4,清乾隆十二年刻本,第6頁。光緒縣志:“老子山,治東北六十里,接江蘇清河縣界”。(13)光緒《盱眙縣志稿》卷2,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4頁。顯然,安徽方面對于邊界的認知仍然囿于前志之說,固然反映了舊方志的某些弊病,“州郡志乘,體例多因習統志,書法則摸(模)擬經史,抄竊為書,文多雷同”;(14)傅振倫:《中國方志學通論》,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第45頁。當然也存在修志者不認同清河縣之說而有意為之的可能。從后來蘇皖雙方在邊界爭端中列舉的證據,以及戴思哲關于方志功能的研究來看(15)戴思哲認為方志不僅是為偶爾好奇的某位讀者編纂的,更重要的是它能夠成為地方社會中確認合法權利的重要依據,而方志的官修性質則決定了每個縣的方志也都支持對己方民眾有利的立場。參見[美]戴思哲著、向靜譯:《中華帝國方志的書寫、出版與閱讀:1100—17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27—341頁。,刻意為之的嫌疑不能輕易排除。
清季民初,隨著地方自治運動的開展,民眾身份意識有所提升,“此疆彼界”的觀念漸入人心,邊界形態也隨之細化。民國初年,清河方志如此描述老子山鄉的界限:“老子山鄉,其區域東至洪澤湖與山陽、盱眙為界,西至洪澤湖中界,南至六里外與盱眙為界,北至洪澤湖北岸與山陽為界。”(16)民國《續纂清河縣志》卷2,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3頁。
至此,通過對相關史料的梳理分析,自明至清再到民國,清河(淮陰)、盱眙兩縣邊界(具體表現為今老子山鎮南偏西一段與盱眙縣之間的界線)經歷了一個由模糊到清晰的過程(從區塊狀山脈到單個山峰,再到實際里數)。隨著雙方界線的明朗化,此前隱藏于背后或者說根本不能視為問題的矛盾也慢慢浮現出來。
老子山區域劃界看似只是簡單的清河、盱眙兩縣間的畛域之分,其實不然,個中摻雜的主客觀成分隨環境的改變而趨向多元。整體而言,老子山西南方向與盱眙縣接壤處,因山就勢,其邊界的演化與“山川形便”之劃界原則契合度高,實質性的爭議相對較少。老子山東南方向,則隨著洪澤湖的盈縮,地貌發生巨大的變化。自漢末陳登始筑堰御淮以來,高家堰屢被增高加寬,“明初,再修于平江伯陳瑄。至萬歷間,河臣潘季馴復大修之,且砌以石者三千余丈,愈鞏固焉。”(17)靳輔:《治河要論》,《皇朝經世文編》卷98,《魏源全集》第18冊,岳麓書社2004年版,第320頁。淮水被高聳的大壩阻擋,河身日高,潴蓄益深,眾多本來不相連通的湖泊開始匯成一體,形成洪澤湖。這一過程大約完成于清初泗州城沉湖前后,“泗州漸沉水底,自盱眙以東,淮河南岸,盡沒,匯洪澤等三湖,與淮為一,然后統名為洪澤湖”。(18)秦蕙田:《五禮通考》卷20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0冊,第174頁。明代筑高家堰以前,老子山東部一帶尚有大片陸地與清河縣境相連,彼此往來暢通無阻,但隨著洪澤湖水體的擴展,“湖水郁不東注,淹及山下阪田”(19)乾隆《淮安府志》卷5,鳳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441頁。,東部一側低地陷入湖中,使得該區域成為三面環湖之地,與縣治間的交通也由水陸兼備轉向倚重水運,甌脫之勢在所難免,蘇皖兩省高層政區“犬牙交錯”的行政區域格局就此形成。
二、灘田涸出與邊界爭端的初現
清咸豐五年六月,黃河于銅瓦廂(今河南蘭考東壩頭附近)決口,改道大清河由利津入渤海。淮河來水量減少,洪澤湖水位下降,淤出良田為數甚巨。因緊鄰洪澤湖,清河縣亦有大量湖灘涸出,據光緒縣志記載,洪澤湖原尾草灘共田2197頃有余,除撥作他用的72頃余不計入外,實存歸官支配湖灘1949頃有余。清河縣特設“管理湖灘局”,專司涸出灘田的管理。咸豐年間,縣令吳棠根據湖水干涸的時間順序劃分區塊,招引外地大戶前來認領開墾,謂之“招領”(20)胡其偉:《環境變遷與水利糾紛:以民國以來沂沭泗流域為例》,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11頁。,前后共分兩次實施。咸豐五年,招領征租田原灘855頃有余,以人、壽、年、豐四字編號,統稱“上灘”(高田);咸豐九年,續招尾灘暨草田1093頃有余,分別冠以時、和、世、泰四字,名曰“下灘”(低田)。(21)光緒《清河縣志》卷9,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921、921—922頁。因灘田的土壤肥力不同,田租也分不同等次,“租則自上則每畝二百五十文,遞減至草地每畝四十文”,共計歲租錢15000余千文。(22)杜宏春編著:《吳棠行述長編》上冊,黃山書社2016年版,第317頁。此灘田是按照“租則”等第收取租錢而非賦稅,與清代山陜灘案中的征收方式如出一轍(23)參見胡英澤:《清代山陜灘案中的征租問題研究》,《清史研究》2020年第6期。,旨在提示湖灘的所有權屬于官產而非私財。官府的初衷是想通過收租的形式來調節、規范被招領人經營灘田的行為,防止人為因素對洪澤湖灘的過度墾殖或因湖水泛濫而造成的一系列田土紛爭。
淤出田地有高田與低田之分,不僅在于淤出時間的先后,更代表著土壤質量的高低。湖灘之地多為沙質,蓄水能力差,近湖之低田更易遭受湖水漫溢,水旱災害頻繁,即“湖灘地畝,本系黃河浸灌淤墊而成,高田則沙薄居多,低田則湖水易漫,無河渠灌輸之利,無堤圩畔岸之防。春來雨澤偶遲,旱災立見;夏秋湖水盛漲,淹漫尤多。他境雖極豐年,湖租僅得中稔。”(24)光緒《清河縣志》卷9,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921、921—922頁。以致收成也難以保證,“上灘每畝之麥僅收三五斗,下灘麥、豆可各兩石,似下灘勝矣。然上灘秋季亦可收三五斗,無收者少;下灘恒遭秋漲,往往無收。故諺有之曰:‘上灘能養生而不能發財,下灘能發財而不能養生。’”(25)張煦侯:《淮陰風土記》,方志出版社2008年版,第438頁。
光緒初年,為改變這種靠天吃飯的現狀,老子山地區率先施行灘田整治計劃,開鑿溝渠灌溉、排水,如官圩溝“系光緒初年挑筑,西連安徽盱邑,東接湖邊,澇則導水外出,旱則引水灌田,亙延數里,受益農田約有二百余頃。”(26)趙邦彥:《淮陰縣水利報告書》,1917年鉛印本,第5頁。灘田整治和改良工作取得初步成功,為灘田開發邁入新階段奠定了基礎。
此后,老子山東部低地的大片沿湖灘涂陸續被辟為沃壤,但由于涸出時間較短,村落甚少,當地人耕種并不充分,與其交界處的盱眙民人越境墾殖情事屢見不鮮。現存《淮陰縣老子山鄉猶龍書院碑記》便記錄了一件發生在光緒年間因越界開荒所引發的爭訟,而猶龍書院的創辦亦與此事件關聯緊密。該碑記記載,光緒二十年,侯紹瀛任清河縣令,次年冬“勾當本鄉灘地事,渡湖南來,畫井分疆,民皆樂業。”(27)《淮安金石錄》編纂委員會編:《淮安金石錄》,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00頁。此“勾當本鄉灘地事”,指的是老子山鄉灘田被盱眙百姓越界墾占一事,“洪澤湖續涸灘地與盱眙壤相錯,土人視為甌脫,爭墾牧,往往興大獄。”(28)民國《續纂清河縣志》卷9,第1148頁。盡管我們無法獲知更多細節信息,從而還原本案的來龍去脈,然據志書和碑刻內容推斷,像這樣的“大獄”決非孤立的個案。
為了防止類似沖突一再上演,清河縣認為有必要采取措施加大對邊界附近灘田的保護力度。侯知縣有意創辦猶龍書院以興人文,并以湖灘淤田設“學田”以維持書院的日常運行。時人劉庠所作的碑記對此事記載更為詳細,“老子山在洪澤湖之厓,湖涸悉為灘地,則界于清河、盱眙兩縣之間,兩縣之民爭據為業,往往興訟,大府飭官吏履勘丈量,而清厘之其屬于清河者,凡得灘地三百余頃,侯東洲大令爰于老子山之陽創建猶龍書院,為諸生肄業之所。”(29)民國《淮陰志征訪稿》,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99頁。可見猶龍書院是在清理盱眙縣民侵占灘地300頃基礎上創建的,并“撥太安七鄉官荒九十余頃,招佃墾殖”作為學田,以“備書院敦請院長及士子膏火費用”(30)《淮安金石錄》編纂委員會編:《淮安金石錄》,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00頁。,并于適當位置勒石樹立界碑。90余頃官荒劃撥學田,表面上是為地方教育提供物質保障,背后還蘊含著更深層次的考量,清河縣將部分新涸灘田歸入書院名下,實際上是完成土地的確權工作,警告并監督盱眙民眾切勿擅自越界占墾,以防爭端復起,可謂一舉兩得。
民國初年,在“實業救國”思潮影響下,新式農墾公司加大了對洪澤湖灘田的開墾,為改善灘田的水利狀況,趙邦彥治下的淮陰縣也因地制宜提出了大興水利的口號。其在老子山鄉修筑了兩條溝渠,一是疏浚年久淤塞的官圩溝,二是在土橋灘地新開古澗溝,長約300丈。(31)趙邦彥:《淮陰縣水利報告書》,第110、77頁。此外,針對老子山鄉轄下之泰安七鄉一帶灘地濱臨洪澤湖,時有淹漫停滯之虞,亦分委監工人員從事挑浚。(32)趙邦彥:《淮陰縣水利報告書》,第110、77頁。改善和維修水利設施,使得湖灘田地的種植條件較之以前更加優越,不法者視之為有利可圖,1916年盱眙民人鄒驥昌又肆意北占,企圖故伎重演,后因被淮陰縣拘押方才退出侵地。(33)張煦侯:《淮陰風土記》,第422、330、422頁。但是,問題的癥結并未得到徹底解決,這也為兩縣后續爆發更大規模的沖突埋下了伏筆。
三、界域糾紛的加劇和懸案的形成
關于灘地被占墾的原因,冀朝鼎認為“其中一個原因是為了爭奪名義上還屬于國家卻又沒有被任何個人據為己有的土地;另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在從湖床或河床回收這些土地之前的相當一個時期內可以免納地租。由于這些被回收的土地,具有極大的肥沃性,因而就導致了最嚴重的經濟與政治問題。”(34)冀朝鼎著、朱詩鰲譯:《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20—24頁。這一觀點雖然是出于全局視角的宏觀性概括,但也非常符合近代老子山灘田開發之事實。
1928年,江蘇省政府公布《十七年度施政大綱》,以清丈為改良田賦之根本計劃,著重整頓包括淮陰在內的江北荒地。(35)《江蘇省政府十七年度施政大綱》,《江蘇財政公報》第6期,1928年6月,第15頁。各縣很快啟動“清丈”流程,然而因牽涉面廣,阻力紛繁,開局并不順利,其中最為棘手的當屬1929年發生的淮陰、盱眙兩縣關于老子山灘田地界的爭議。此次事件從性質上來說,是光緒二十一年、民國五年沖突的延續和擴大。
1916年盱眙縣民鄒驥昌侵占老子山鄉灘田被逐出,不久又故態復萌,再次侵占灘田達127頃之多,并擅自將原有界碑移至數里之外。而田賦縣稅是淮陰縣財政收入之大宗,約占75%(36)張煦侯:《淮陰風土記》,第422、330、422頁。,盱民此舉激起了淮陰當局的高度警惕。1929年,淮陰縣政府函邀盱眙會勘邊界,“依界碑形勢,丈出廿余頃。界碑之南,仍有地百余頃,尚未丈及”。此次勘界,因盱眙鄒氏民人的抵抗,引發了大規模的械斗,“盱民鄒氏,竟以耽于麥熟,乘我收回地畝時,率眾械斗,砍傷軍警,擄去民夫,而鄒氏之子亦中彈殞命,為禍至慘。”(37)高天:《洪澤湖老子山實錄(下)》,《江蘇研究》第2卷第11期,1936年11月,第6頁。能夠在短時間內召集200余人,并公然對抗軍警,決非一般人所能為(38)張煦侯:《淮陰風土記》,第422、330、422頁。,通過對鄒氏身份的考察發現,其來源于灘田附近屬盱眙管轄的一個叫“鄒家大莊”的村落,該村是一個以鄒姓族人為主體的單姓村莊,占田基本可視為是以某一大戶或幾戶為首、多戶甚至全村參與的集體行為,這也是屢次三番被淮陰縣打擊卻頑疾難除的重要原因。
經歷前次沖突,淮陰縣希望盡快了結此案以便早日重啟二次會勘。1930年4月,江蘇省政府咨請皖省,“派員會勘省界”(39)《會勘淮陰盱眙界址》,《民國日報》1930年4月9日,第5版。,以息淮陰、盱眙兩縣的糾紛。次月,兩省分別委派民政、教育二廳官員會同兩縣地方官一同前往爭執地段查勘。其實,雙方勘界的核心問題仍在灘田產權,淮陰方面準備的證據比較充分,“為灘地總冊及猶龍書院地畝印冊總本兩件。灘地總冊內載放領灘地二百九十余頃,其中有退領之灘地,經官廳劃歸猶龍書院者計九十六頃有余,載在猶龍書院地畝總冊內,冊上蓋有清河縣圖記。”(40)⑥《令知淮陰盱眙兩縣爭界劃定》,《安徽教育行政周刊》第3卷第36期,1930年9月,第8、9頁。筆者曾在淮陰區檔案館中找到一件光緒二十九年洪澤湖洸灘退讓官據和數件民國十七年發給灘戶留存的財政部印單(執照),內容雖不盡相同,但其中都載有詳盡的“灘田四至丈尺畝數”和執業者姓名等關鍵信息,作為收租或征稅之依據。(41)《光緒二十九年王漢光讓洪湖洸灘給石云彩》,淮安市淮陰區檔案館藏淮陰縣清代民國檔案:1002-1937-001-0020;《民國十七年朱敬堂灘田納稅的印單》,淮安市淮陰區檔案館藏淮陰縣清代民國檔案:1002-1937-001-0023;《民國十七年趙絢五承租洪湖灘田的財政部印單》,淮安市淮陰區檔案館藏淮陰縣清代民國檔案:1002-1937-001-0025。淮陰縣所掌握的兩件證物正屬此類,按理說算是證據確鑿。但恰在此時,醞釀已久的《省市縣勘界條例》于1930年5月由內政部呈送行政院,并于6月12日由國民政府核定公布。該《條例》是“泯除界域爭議”(42)《省市縣勘界條例之內容目的在泯除界域爭議》,《民國日報》1930年5月19日,第3版。的重要指導性文件,盱眙縣便以其作為此次勘界的依據,羅列了《條例》中幾條有利于己方的劃界原則——“土地之天然形勢(即文中之邱隴)”和“有永久性之關隘、堤塘、橋梁及其他堅固建筑物(即界碑)可以為界線者”(43)《省市縣勘界條例》,《湖北省政府公報》第102期,1930年7月8日,第43—44頁。,主張以高姓圩與金姓圩所具之邱隴為兩省省界⑥,以達到繼續侵占灘田的目的。此主張自然遭到淮陰縣的強烈反對,如果認可其論,就等于承認了盱民越界墾占老子山土地的合法性,界碑以南的大片灘田也將收回無望。眼看淮陰縣不能接受盱眙縣所提之條件,皖方變換了談判策略,采取回避的態度以期拖延,“嗣省委談話結果,我方主解決省界,皖方則謂先決問題在刑事,劃界當留為第二步。議論不合,終于流產。”(44)張煦侯:《淮陰風土記》,第422頁。由于雙方分歧巨大難以達成共識,此次勘界會談陷入僵局,最終無功而返。
1933年,擱置近三年的皖蘇邊界爭議再次以另一種方式回歸公眾視野。時任安徽盱眙縣長黎在符借口便于“剿匪”,要求將老子山全境劃歸盱眙縣管轄,消息一經傳出,立即引起軒然大波。(45)《清江:淮人力爭老子山》,《新聞報》1933年5月7日,第10版。在江蘇民眾看來,盱方此舉表面上是勘界之爭,根本原因則是涸出灘田背后的經濟利益之爭,“老子山改治屬皖之說,于學地之爭,不無因果關系,蓋盱眙人以太安七鄉學地之誰屬,影響于皖盱之地位,倘能將老子山劃歸盱眙,不但學地糾紛從此勝利,而導淮成功,涸出良田,盱人亦得坐享其利。”(46)高天:《洪澤湖老子山實錄(下)》,《江蘇研究》第2卷第11期,1936年11月,第6頁。淮陰民眾組織保區委員會,推派代表向政府請愿,同時散發近萬字之宣言,痛批老子山改隸盱眙理由之荒謬,指出盱方系“假剿匪之名,行侵占之實”,并將其“陰謀”見諸報端:“老子山系本縣行政第七區地域,所有地丁錢糧,前清咸豐、同治間,被災減削,縣府有案可稽,近年東西各灘出現,約五萬余畝,課租漸次增加,刻已辦理換單改糧,且導淮現已實現,以后租地改糧,將增至六十萬畝以上,將來淮陰財賦,正未可量,該縣(盱眙)以垂涎灘地之故,反謂為并無地丁錢糧,劃歸亦少窒礙,未免欺人太甚。”(47)《淮陰各區長反對老子山劃歸盱眙管轄組織保區委會發表宣言》,《中央日報》1933年5月16日,第6版。
因為導淮的成功,大量良田被涸出,本就膠著的老子山灘田的歸屬問題更加成為雙方爭奪的焦點。為占據主動,1934年5月皖省再一次上呈中央政府,請求在洪澤湖邊地另設一水上縣,歸安徽省統轄,其地北割淮陰之順河集、武家墩,泗陽之新灘,西割泗縣近湖之區,南割盱眙之都管塘、下龜山一帶,東割淮安之高良澗等地,設縣治于老子山。(48)《蘇皖邊境增設水上縣》,《大公報(天津)》1934年9月25日,第9版。后因新縣財政殊難自立,加之淮陰失地過多,該議未能獲準,而歷經多年的老子山灘田爭訴案到此為止已然是一樁懸案。
此后,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中斷了皖蘇兩省關于灘田界域糾紛問題的處理進程。直到新中國成立后,通過土地改革的方式,廣泛開展“土地清丈、劃界定樁”運動,該邊界爭端在國家權力自上而下的強勢介入下才算真正得到解決。
結 語
行政區域邊界按其類型可以分為法定線、習慣線和爭議線三種。近代以降,伴隨人口增長和經濟社會發展,有關資源開發利用的邊界釁端有增無已,于是部分習慣線慢慢演變成爭議線。正是意識到此種模式的潛在危害及不可持續性,政區邊界的法制化在客觀上就成為政府治理現代化必須關注的現實課題。然而,要想將模糊的“界限”落實到精確的“界線”又談何容易。正如學者所言,“邊界不是一個孤立的、靜態的、自然的邊界,它是圍繞生態、國家、社會的相互關系而展開的。”(49)胡英澤:《流動的土地:明清以來黃河小北干流區域社會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377頁。老子山灘田劃界糾紛案存續時間跨度較長,愈到后期矛盾升級、愈演愈烈,問題的核心在于如何分配邊界附近豐富的土地資源,尤其是當這些土地還在不斷增加,且都是未經開墾的新涸灘田時,爭議更趨激烈。先是沖突各方基于自身利益,希望盡可能多地占有灘田并將其變成既成事實,以試圖在劃界事務中取得主動。南京國民政府雖然實現了形式上的全國統一,但并不能有效控制各個省份,很難以權威者的身份主導具體劃界事務,只能暫時居中調和,也是導致民國時期眾多省界糾紛久拖不決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見,行政區劃調整是一個十分復雜、敏感的話題,難以一蹴而就,更不能隨意為之,要從政治原則、社會傳統、地理環境等各方面因素綜合考慮,政區邊界的重新劃定也是一個相互博弈、彼此妥協的過程,應當在積極聽取并回應各方關切的基礎之上,盡量做到經濟社會利益的合理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