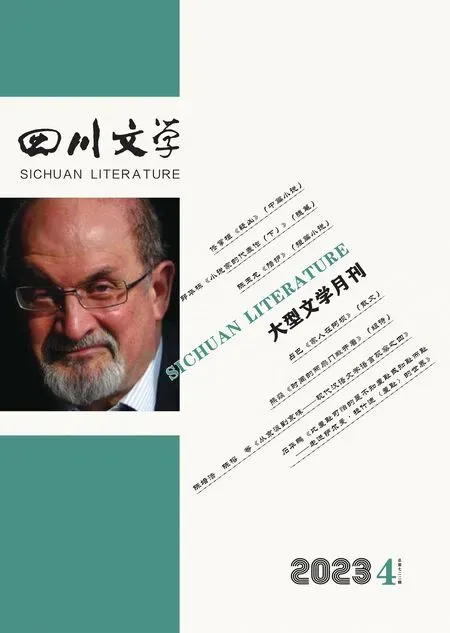梨園與墓園
2023-08-21 07:01:24劉萌萌
四川文學
2023年4期
□文/劉萌萌
我做夢也沒想過,有一天會坐在她面前,看她端出孫二娘的架勢,手上夾著煙卷兒,來來回回挪動沾著泥巴的小腿,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吆五喝六。天剛蒙蒙亮,她坐在馬扎上,蓬著頭發(fā),腳趿俗艷的泡沫拖鞋。刀與案板的撞擊中,碎白菜彈跳著迸濺出來。扶著案板的手時不時遞到唇邊,來上一口。梨樹葉還沾著昨夜的清露。藍色的煙霧,像一條上升的河流,蕩漾在一早的晨光里。
一支煙差不多了,她終于停下來,用手背抹了把汗津津的鬢角。空氣散發(fā)著熱烘烘的青草氣息,像是對剛剛沒走多遠的夏天的補充和追憶。眼前,廢棄的白鐵皮洗衣盆,黃燦燦的玉米面,堆成小山的白菜,隆起半坡參差白綠。她挺著肥沃的肚皮,像傳說中膂力過人的大力士,一手抱盆,一手快速而均勻地攪拌。隔著橫斜的梨樹枝丫,我驚訝地望著幾步之外朝雞柵走去的婦人:穩(wěn)健的步態(tài),粗壯而靈活的腰身,胡蘿卜似的手指靈巧地撥開插銷,群雞跌撞,沸騰而出,帶著一地雞毛的歡騰沖向食盆。
半年前,她打來電話,說從大哥手里租了一塊地,就在一片開闊的梨園里。“找點事做,就不那么悶了。”聽筒里哧哧啦啦交織出一片雜音。這些年,每隔一段時間,就有各種消息,零星地灌入耳朵。那些渠道不同的真假難辨的傳聞,像喋喋不休的小人兒,激烈爭吵,各說各話。輾轉(zhuǎn)于這些言談之間,時間久了,懶得浪費力氣,隨它吧。烏云在父親臉上短暫停留了一會兒,兀自飄走了。……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