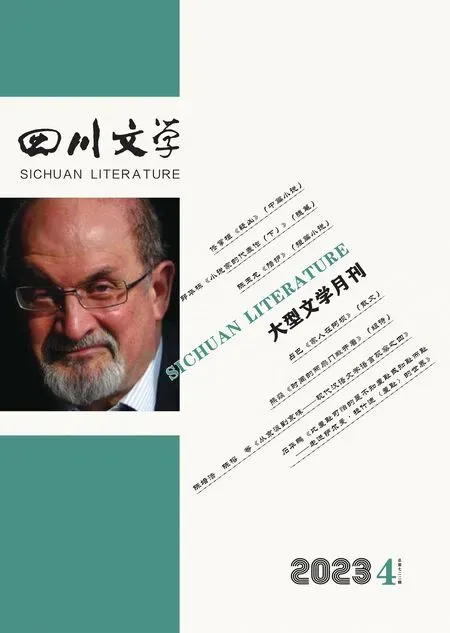隕落黃昏
2023-08-21 07:01:24茍子
四川文學
2023年4期
□文/茍子
一
春天的太陽是溫暖的,一旦偏西,擱置在了西邊那團黑蓊蓊的山頂上,整個安子溝就會黯然失色,陰冷起來。坐在那包青石頭上放牛的老頭兒謝新岳,連連打了兩個噴嚏,一掛鼻涕吊在鼻尖上,他欠身站了起來,一捏鼻子,隨手就把那黏糊糊的臟東西甩在了柏樹丫上,手在地上蹭了兩下,就去牽牛繩子。
肥實的水牛還在埋頭啃草,不想走,故意將頭轉向另一邊,將尾巴甩了過來。謝新岳側身攆了兩步,彎腰就把牛繩撿到了手上。這時,一顆錚亮的隕石,從西邊遙遠的蒼穹劃了一條長長的弧線,不偏不倚直直地掉進了安子溝底。
謝新岳看得真切,一張皺巴巴的臉,異常地驚愕。第一反應就是落禍殃了——整條溝現就他自己和幺女兒謝梅以及何向東三個人,不曉得禍事要發生在哪個身上。
謝新岳牽著牛繩,背著一背篼牛草,幽幽地往家走。偏房的煙囪冒著青煙,謝梅在剁牛皮菜,大黃狗見到他就奔到跟前一個勁地搖尾巴——家里一切都是好好的,只是不見擔糞做秧母田的何向東。謝梅說,向東哥去溝口接他的兒子了。
何向東去年才與已去廣州打工十二年的老婆辦了離婚手續。兒子何理十三歲,初中沒畢業就跟母親去了廣州——離婚時,何向東拼命要兒子,兒子何理卻不愿意跟他,甚至連面都不愿意見。現在突然回來,著實讓謝新岳感到意外,就對謝梅說,你煮一塊臘肉兩節香腸,請他們兩爺子過來吃夜飯。
謝梅說,向東哥打電話來的時候,我就跟他說了今晚一起吃飯。……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