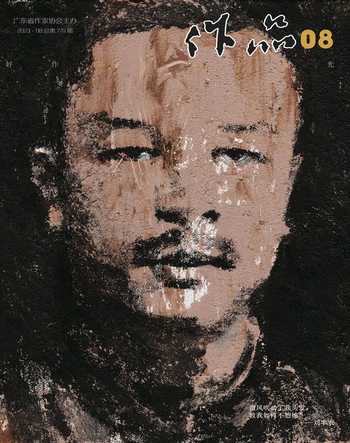白
薛依依
一
旅館坐落在冷清的街道,與周圍所有不起眼的事物融合得剛好,沒有任何突兀之處。一樓是前臺,二樓是客房。電梯門打開,雙腳踩在厚重的織花地毯上,腳步聲瞬間消失在地毯之下。走廊里掛著抽象畫,房間門是啞光黑,一切顯得厚重而內(nèi)斂。打開房門插上房卡,窗簾在音樂聲中自動打開。大床,落地玻璃窗,窗外是一條環(huán)城小河涌。蒂凡尼藍(lán)的床旗、椅子、首飾盒,讓房間擁有藍(lán)色海洋的味道。書桌上方掛著一幅黑白抽象畫、一只鳥的水彩畫,還有一張赫本的黑白照片。
我脫下高跟鞋,換上旅館為客人準(zhǔn)備的棉拖,再到浴室脫光衣服,除下耳環(huán),卸掉臉上的妝。鏡子里的自己,臉上的水珠正滑向胸口,流向腹部,我似乎從未這樣去認(rèn)識自己的身體。凝視久了,感到好像有另外一雙眼睛在看著我。在鏡子后方?在天花板上?還是在抽水馬桶的孔洞里?我晃了晃頭,企圖讓自己思緒回來。
水龍頭的水,是一條飛流的瀑布。我在水中舉高雙手,一只手撫摸另一只手,像兩條洄游的鰻魚,交纏在一起。我喜歡閉著眼睛在水中的感覺,水流經(jīng)全身,仿佛置身于巨大的海洋,海水不停舔舐著身體。
一場洗禮般的儀式結(jié)束后,穿著白色睡袍坐在藍(lán)色圓形靠背椅上,輕盈便跳躍在每一個毛孔。在黑色手提包里拿出巴掌大的檀香木盒,盒面有一朵珍珠母鑲嵌而成的荷花。它是便攜式線香支架,點(diǎn)燃一節(jié)線香,白霧像靈性的舞者,舞動長長白紗,拂向我的臉龐。
我趴在桌子上睡著,醒來時線香已經(jīng)無聲無息燃燒完,只留下它的味道以及慘白的灰燼。面前是旅館放在桌面供客人收納飾品用的藍(lán)色首飾盒,打開第一層,空的;打開第二層,有一個古銅色寬邊闖口手鐲。它與我遺失的手鐲款式一樣,材質(zhì)雖不名貴,但造型卻不常見。它是根據(jù)個人手腕形狀定制而成,恰好,我的手腕與眾不同。
二
我的右手腕長了一塊直徑約10毫米的半圓形骨頭。自我記事起,它就一直伴隨我。
在印度艾哈邁達(dá)巴德旅行時,行至離賈瑪清真寺不遠(yuǎn)的街道,有一個老人,花白胡子垂至鎖骨之處,目光清澈如水。他是定制手鐲的手藝人,比畫著要給我定制手鐲。
他的臉,能看清皮膚上所有的紋路,如云杉木的樹皮。他的手指擦過我的手腕,歲月的粗糙感,在我的皮膚上真實(shí)地走過。手腕上的骨頭,像只烏龜,緊張地?fù)纹鹉屈c(diǎn)薄薄的皮膚。
他測量完手寸后,取出一塊金屬條,用高溫槍來回?zé)藥紫拢旁诜叫未箬F塊上面,用鐵錘敲敲打打。金屬條在錘打下,慢慢變寬變薄,銼刀把兩邊打磨成半弧形。中心用半球形凹槽,打出凹進(jìn)去的形狀,當(dāng)然,從正面看就凸起。老人將金屬條環(huán)繞在一根特制木柱上,讓它變彎,變成手鐲形狀。隨后他細(xì)心調(diào)整手鐲的形狀,打磨它的表面。手藝人的靜氣,在他身上靜靜地流淌。
手鐲做好了,沒有多余的花紋,那樣古樸、靜謐。他拿起手鐲示意要幫我戴上。鐲口從手腕尺側(cè)進(jìn)入,再向外、向下旋轉(zhuǎn),凹槽部分剛好蓋住半圓形骨頭。手鐲上手后,它和我立刻成為一個整體,仿佛是一只大手,握著小手。我把一沓錢像撲克牌那樣在手中展開,最后他拿走1000盧比。
回國后,我一直戴著它,睡覺也不愿摘下來。一天中午,我躺在臥室窗邊藍(lán)色布藝沙發(fā)上,陽光很暖。我伸出右手想讓手鐲曬曬日光浴,陽光下我詫異地發(fā)現(xiàn)手鐲原本凸起的部分變平,摘下手鐲后發(fā)現(xiàn)手腕上的骨頭也已消失。是手鐲里的金屬元素對骨頭有治療作用,還是自身身體吸收的作用?無論我怎么想,好像都無法給手鐲也跟著骨頭變平的現(xiàn)象,做一個合理的解釋。不過終歸是件好事,手腕正常了。我更加喜歡這個手鐲,我視它為幸運(yùn)鐲。可是有一天清晨,我醒來時,發(fā)現(xiàn)手腕上的手鐲不見了。
三
是的,我的手鐲不見了。此刻,在旅館房間出現(xiàn)的是我的手鐲?事情來得太突然、太魔幻。我必須冷靜下來,像福爾摩斯一樣觀察所有事物,推敲所有細(xì)節(jié),甚至一根發(fā)絲都是至關(guān)重要的證據(jù),必要的時候,還要像只獵犬,不能放過任何一種殘存的氣味。
旅館的便箋紙或許留有什么線索,只需要我用鉛筆在表面輕輕涂上一層鉛。倘若曾經(jīng)在上面寫過字,它的痕跡便會顯現(xiàn)出來。電影上不都是這樣演的嗎?可惜便箋紙沒有承擔(dān)像電影中的驚喜,它什么啟示也沒有給我。
我后悔洗完澡后點(diǎn)燃線香,它掩蓋房間里可能殘留的氣味。現(xiàn)在房間里只有線香的味道,真是讓人抓狂。
如果有一種空氣分離抽取機(jī)的話?——我簡單介紹一下我想象中的這種機(jī)器吧,比如不喜歡別人抽煙的味道,開啟機(jī)器就可以抽走香煙的氣味;如果空氣當(dāng)中有其他濃郁的氣味,比如書的霉味,只要你喜歡,就可以悉數(shù)保留下來。如果有這樣的機(jī)器,事情是不是就有挽回的余地?
我還可以從哪兒下手?查旅館房客入住信息?上一任房客是什么人?與我有沒有什么必然聯(lián)系?如果保潔人員并沒有認(rèn)真清點(diǎn)物品,那么手鐲就不一定是上一任房客留下來的。我必須馬上打電話或親自下樓到前臺咨詢這件事情嗎?如果他們以這件物品是客人留下來的,要履行保管義務(wù),要求我上交手鐲,豈不是壞了大事?不不不,再仔細(xì)思考一下,我一定還有疏漏的地方。
最初是什么力量讓手鐲出現(xiàn)在我的身邊,又是什么力量讓它消失?我擁有過它,對不對?這個是事實(shí),對吧?但我曾經(jīng)擁有過什么?我現(xiàn)在擁有什么?我未來又能擁有什么?好像都沒有。
嗯,難道這件物品具有時空穿梭的能力?它借由什么東西穿梭而來?首飾盒嗎?若把手鐲重新放進(jìn)去,一開一合之間,它又會穿梭到什么地方去?先別用手鐲,用其他東西試試。我把客房提供的鉛筆放進(jìn)去,小心關(guān)上盒子并確認(rèn)有沒有關(guān)緊。要多少分鐘才能完成穿梭的過程?10分鐘?5分鐘?啊,我覺得1分鐘都太長。
我在內(nèi)心制定穿梭儀式的規(guī)則,想通過意念與首飾盒產(chǎn)生磁場聯(lián)結(jié)。我從1數(shù)到10。打開的一瞬間,結(jié)果似乎在意料之中,鉛筆并沒有完成穿梭。或許,不是首飾盒而是手鐲才有穿梭時空的能力?干脆用手鐲放進(jìn)去,穿梭儀式再一次結(jié)束后,手鐲依然躺在那里。我暴躁地推開首飾盒。
手鐲不見時我是和誰在一起?對,我是和男人在一起,一個認(rèn)識很久還是剛認(rèn)識的男人?記憶有點(diǎn)模糊,不過,我想起我們一定是度過了一個激情的夜晚,全身的酸痛與昏沉的感覺仿佛現(xiàn)在也能感受到。他究竟是什么人?我努力回想他的容貌、動作,他說過什么話。只記得我躺在床上看見他翻身覆蓋我的那個時刻,他笑起來的樣子真好看,親切、溫柔,有耐心。
我的思想混亂極了。難道我陷入了某種陰謀?一個美術(shù)老師會有什么價值?我是因何事入住這家旅館?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嗎?引我到這里來就是為了還我手鐲,還是最終的目的是想要拿走我身上某件物品,而這件物品與一些不可告人的機(jī)密有關(guān)?搞不好還想直接將我殺人滅口,就像在此刻,其實(shí)我一直在別人的監(jiān)控之中?難怪洗澡的時候就感到有一雙眼睛在盯著我看,女人的第六感很準(zhǔn),不是嗎?
有網(wǎng)絡(luò)存在,封閉的空間會朝宇宙幽微之處無限延伸。我想起一部電影叫《楚門的世界》,里面講述主人公從出生到結(jié)婚、工作,一直都活在被直播里而不自知。我是不是也在楚門的世界里,分不清生活什么是真、什么是假?這個房間不再讓我感到安全,它充滿著我看不見的眼睛在看著我。不管在哪里,都沒有絕對的邊界,絕對的安全之處。
我起身到房門后面,從貓眼看走廊有沒有可疑的人影。走廊沒有人,也沒有任何聲響。我轉(zhuǎn)身把房間里所有燈都關(guān)掉,用手機(jī)打開攝像功能,拍黑暗中的房間,據(jù)說這樣可以檢測到那些隱藏在房間的攝像頭。沒有燈光的房間,空調(diào)的聲響倒是清晰起來,像一只上了年紀(jì)的貓在睡覺。
先從房門口右側(cè)衣柜到小吧臺,再回到左側(cè)浴室。洗手臺上的鏡子、洗漱用品、吹風(fēng)機(jī)的插孔、浴巾、抽水馬桶,淋浴房的玻璃、腳墊、抽拉簾、水龍頭、花灑、洗發(fā)水、沐浴露、天花板,每一個細(xì)微之處都不能放過。如果真的找到攝像頭,那真的太可怕了。還有,我赤身裸體的樣子、我坐在馬桶上痛苦的表情,都被那些人看見了嗎?他們正在某個房間或某個車廂里監(jiān)視著我嗎?
浴室沒有任何發(fā)現(xiàn),我摸黑走出浴室。空調(diào)出風(fēng)口是最容易藏攝像頭的地方,我來回檢查好幾遍也沒有收獲。是電視!電視最容易偽裝,機(jī)頂盒、開關(guān)、插座、路由器、電源最多。我的心跳聲蓋過那只空調(diào)貓的呼嚕聲,小心謹(jǐn)慎檢查著那些線路,還是沒有任何發(fā)現(xiàn)。房間天花板上煙霧感應(yīng)器及消防噴頭都沒有異常。
與我最近發(fā)生的什么事有關(guān)?我必須回憶一下我身邊的人,有些什么人,有些什么異常舉止。我開始翻查電腦上的資料,在MacOS系統(tǒng)中只有圖片與文檔,電腦桌面很干凈。
在“圖片”文件夾中,只有一張相片,我與一個男人的相片。他戴著灰色鴨舌帽,穿著銀色釣魚服,胡子拉碴,鼻孔對著鏡頭,右手在鏡頭之外。我戴著一頂白色鴨舌帽,穿米白的運(yùn)動服,仿佛剛剛哭過,而草地上有一條看起來剛剛上岸的魚。
是那天晚上和我共度春宵的男人,是他拿走了我的手鐲嗎?
我起身打開行李箱,一個20寸的棕色瘋馬皮復(fù)古箱包。里面有一套牛油果色的真絲睡衣、一套休閑服、一件黑色高領(lǐng)打底衣、一條藍(lán)色牛仔褲。這些都很平常,只是有一件黑色絲絨晚禮服,有點(diǎn)奇怪。前面恰到好處的V領(lǐng)、吊帶,后背是全祼款。我是準(zhǔn)備參加什么晚宴嗎?還有一雙用于配晚禮服用的黑色亮片高跟鞋。化妝包里面有小瓶的乳液、卸妝液、防曬霜、隔離霜、定妝粉、眉筆、口紅、眼影、眼線筆、睫毛膏。
我將隨身攜帶的黑色手提包里面的東西全部倒在床單上。除了剛剛用來開房時的身份證,還有一張與身份證大小相同的卡片從里面掉出來。上面有我的照片,照片看起來并不好看,神情憔悴。女人通常都很在意相片,可比相片更讓人驚悚的是上面的文字:
姓名:羅儀
診斷:阿爾茨海默病
緊急聯(lián)系人:飛豬
電話:1312×××××76
就在腦袋里有蜂群飛過之時,微信里顯示“飛豬”的人打視頻電話過來。接通后,居然是那個我和一起照相的男人。
男人說:“羅儀,順利住下了嗎?感覺如何?我很擔(dān)心你,不應(yīng)該答應(yīng)讓你先到酒店。這邊會議一結(jié)束,就馬上過去找你,晚上我們一起參加晚宴。”
我問他:“你是誰?”
他愣了一下說:“是在我給你訂的酒店里,對嗎?別擔(dān)心,我馬上去找你。”
我說:“為什么要來找我,你是誰?”
他說:“我是飛豬啊,羅儀。”
我說:“那你知道這個手鐲嗎?”我對著鏡頭拿給他看。
他說:“知道,你的手鐲。今天出門前,你還特地確定有沒有帶好,老是害怕它不見。”
我說:“你說,這是我自己今天帶過來的嗎?”
他說:“當(dāng)然。”
我說:“那你知道它從什么地方買的嗎?”
他說:“你想不起來?”
我說:“別問我問題,我問什么你答什么。你知道它從哪兒來的嗎?”
他說:“知道,這個手鐲是我和你在印度路邊攤買的。”
我說:“是一個老人為我定制的嗎?”
他說:“不是啊,這種手鐲在那里到處都是。我當(dāng)時想砍價,你拿到手上就不肯再放下,拿一沓錢讓那老頭自己拿,他拿了你1000盧比。事實(shí)上,其他攤位,別人只需用100盧比就可以買下相同的手鐲。你實(shí)在太喜歡了,錢不多,我就由著你。你買回來后,一直很喜歡,很少拿下來。”
我說:“我的右手腕上之前是不是長了一塊骨頭?”
他說:“你一直說你的右手腕上長骨頭。我們?nèi)メt(yī)院拍片,你的手好好的,沒有什么事,沒有長什么骨頭,放心。就是經(jīng)常畫畫,手腕有勞損,常常會酸痛吧。”
我說:“這個手鐲中間以前是平整的嗎?”
他說:“是啊。”
我掛斷電話。是的,我記起了他,我的男朋友飛豬,也記起了阿爾茨海默病。
那一塊并不存在的骨頭,在我身上生長了這么多年。當(dāng)我認(rèn)識到它不存在之后,為什么我又知道它還長在那里?我還記得多少事情?不管現(xiàn)在多么像福爾摩斯,我終將會自己擦去證明自己活著的所有痕跡,包括我的親人、所有生活的技能,還有渴求了一生的愛。
四
我想起一些事,和大多數(shù)孩子一樣,小時候我與父母生活在一起。父親沒有工作,總是外出釣魚,卻從來沒往家里拿回一條魚,哪怕是一條可以放在碗里供我們觀看的小魚。每次出門,少則三天,多則十天半個月。他出門之前,非常謹(jǐn)慎,通常會花上幾個小時仔細(xì)檢查裝備,比如釣箱、竿包、帳篷、鍋具、釣竿、漁線、漁鉤、鉛墜、浮漂、干糧等等。
就在父親準(zhǔn)備外出釣魚的前一天,大伯佝僂著背進(jìn)家門。用菜刀飛快剁著苜蓿草的母親熱情地喊了聲:“他大伯,您來了哈。”父親看見大伯便把頭別過一邊去。大伯“嗯”了一聲算是回應(yīng)了母親,他徑直坐在父親對面。
父親繼續(xù)喝著自己的茶,沒有給大伯倒茶的意思。大伯對父親的態(tài)度司空見慣,并不介意他的無禮。父親輕視所有俗務(wù),包括賺錢養(yǎng)家、打掃房間、清洗衣物,卻總能從家里或其他地方弄來錢滿足自己的需求。就比如這茶葉,也是他從外面帶回來專供自己一個人喝。
大伯開腔了:“我說,你都快四十歲的人了,你把家過成這般光景,你看得下去?如果不是弟妹操持著家里的活計,你這個家,早散了十回八回了。成天游手好閑,釣、釣、釣,你釣個錘子?生下四個娃娃,幾時管過她們的死活?”
父親說:“吃你家的了,還是喝你家的了?你懂得什么叫生活,背就不會彎成這個樣子。你有什么資格在這里指手畫腳?不撒泡尿看看你自己那個鬼樣,活像一只弓著背的蛆蟲,成天在惡臭的生活里拱來拱去,好意思說我?”
大伯被氣得差點(diǎn)倒在地板上。他努力讓自己平靜下來,聲音仍然像篩糠般顫抖:“如果不是弟妹千求萬求,讓我來勸勸你這混賬東西,打死我也不愿再踏入這家門半步。”說罷,大伯便拂袖而去。
母親把頭低下繼續(xù)剁著苜蓿草,肩膀抽動著。
或許大伯的一番話讓父親有些觸動。晚飯后父親把我們四姐妹叫到跟前,要講他的故事給我們聽。平日里父親在家沉默寡言,若是開口,便只有責(zé)罵。他能心平氣和講故事,不知道是多大的恩典了。父親照例泡起他專屬的茶葉,邊喝邊說:“有一年,我獨(dú)自開著一條小船去海里釣魚。白天海面炎熱極了,從早到傍晚,都沒有動靜。就在我準(zhǔn)備放棄的時候,浮漂一下子沉入海中,我知道上魚了。我使勁拉住漁竿,魚在海中東竄西竄,小船被魚拖著走。根據(jù)我的經(jīng)驗(yàn),那是一條相當(dāng)大的魚,說什么我都不會放手。就這樣,我拼命拉著那條大魚。不知過了多久,它終于現(xiàn)身了,是一條大馬林魚,比我的船還要大。大魚拖著船繼續(xù)往大海走,但我依然死拉著不放,即使沒有水,沒有食物,沒有武器,沒有助手,而且左手還抽筋。經(jīng)過兩天兩夜的努力之后,我終于殺死大魚,把它拴在船邊。不巧的是因?yàn)闅⑺来篝~流的血,引來許多鯊魚,它們一窩蜂前來搶奪我的戰(zhàn)利品。大馬林魚最終難逃被鯊魚吃光的命運(yùn),我精疲力竭,最終只是得了一副魚骨頭。”
當(dāng)年姐姐8歲,我6歲,兩個雙胞胎妹妹5歲。我們被父親講述的情節(jié)牽動著,時不時張大嘴巴發(fā)出驚呼,非常同情他的遭遇,非常可惜那條被鯊魚吃掉的大魚。但是,我們還是流露出無比崇拜的神情。那一刻,應(yīng)該是父親這輩子在我們四姐妹心中形象最偉岸的瞬間。
情節(jié)非常熟悉是吧?是的,這個就是海明威寫的《老人與海》的情節(jié),他甚至都懶得做些改動,書里的故事和他所描述的情節(jié)一模一樣。事實(shí)上,他的漁具只能在溪流或湖泊里用用。他從來沒有到過海邊釣魚,更別說還有一條船并釣到大魚。這些都是我長大后才明白的事,當(dāng)年還是太年輕,被他的胡說八道騙得七葷八素。
第二天,父親如期出發(fā)去釣魚。就是這一次,我們四姐妹由高到矮依次排好,目送父親離開家,心中沒有以往對他的恨意,還涌動著激動的心情,仿佛我們在為英雄送行。父親走后,我們四姐妹便迫不及待地找到小伙伴們,由姐姐重述父親的英雄事跡,我和妹妹們不時點(diǎn)頭,以示事情就是那樣子。當(dāng)我們講完,準(zhǔn)備接受眾人的贊嘆時,被一個讀過《老人與海》的大孩子揭發(fā)了。當(dāng)場回家拿來那本書,眾人得知真相后,哄堂大笑。
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父親是個英雄,尤其是一直被鄰居輕看的父親。我們需要用一些高光時刻挽回形象,為他也為我們自己。我們四姐妹和這個大孩子絕交了,直到今天,幾十年過去了,我都還沒有與他和好。
五
半個多月過去,父親依然沒有回來。我們既期盼他回來,能好好問問他那條大魚的事,又從內(nèi)心厭惡吹牛的父親,他讓我們每天受到小朋友們的嘲笑。
一天中午,兩個穿著制服的男人找到我們家,表明自己的警察身份。其中一個問我:“你家大人在哪?”我非常害怕,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們這樣的人家,從來沒有和警察扯上過什么關(guān)系。最后還是妹妹們?nèi)グ褘寢尳羞^來。
警察:“他什么時候離開家的?”
母親:“大約20天前。”
警察:“離開前,有沒有發(fā)生什么事,或者他有什么異常?”
母親:“我叫孩子的大伯來勸一下他別出去釣魚,他們吵了一架。”
警察:“那孩子大伯在哪?能把他叫過來嗎?”
母親:“在他家。我讓孩子去叫。”母親便叫姐姐去叫大伯。
母親:“是怎么了,他犯什么事了嗎?”
警察:“有人在離這里20公里的未名湖邊,發(fā)現(xiàn)了有人居住過的帳篷、釣具及生活用品,還有一張寫有遺言的紙條,便報了警。我們?nèi)ガF(xiàn)場查探,鎖定是你家的男人,便尋著找來了解一下情況。你需要和我們一起去湖邊看看是不是你們的家什,再決定下一步怎樣做。”
聽到湖邊發(fā)現(xiàn)疑似父親的遺物,母親號啕大哭,仿佛是愛到深處,又仿佛是為她過往艱難的人生,更有可能是為了避免某些嫌疑。總之,她需要一場痛哭。兩位警察耐心等她哭完,直至大伯過來后,她才止住哭聲。警察詢問大伯最近都在哪兒,有沒有離開村子之類的話,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便讓嚇得渾身發(fā)抖的大伯走了。
母親要和警察一起去現(xiàn)場,她安排姐姐在家照顧兩個妹妹,帶著我一起出發(fā),因?yàn)樗X得平常不愛說話的我最值得信賴,尤其是這樣的時刻。
到了未名湖邊,看到那些物品,母親非常肯定地告訴警察,就是父親平日里用來釣魚的家什。警察給了一張并不完整的牛皮紙,上面用燒過的木炭筆寫了一行字:“我走了,與任何人無關(guān),不用找我,讓我安心地走。”
此時湖面波光粼粼,湖心島的蘆葦叢中時不時竄出幾只白鷺,微風(fēng)吹拂著每個人的臉龐。遠(yuǎn)山像灰色的大色塊連接著天與地,樹木在湖的四周爬向山坡,沒有被修剪過的草地顯得蒼翠又狂野。未名湖雖小,但湖光山色,草木掩映,相較我們生活的小村莊,風(fēng)景確實(shí)美太多。
警察分析父親應(yīng)該是投了湖,叫人過來打撈。三個小時過去,在太陽即將下山的時候,他們打撈出一具骸骨,衣服相對完整,但人的肉身卻喂養(yǎng)了一湖的魚。母親看到衣服后,便知道是父親無疑,哭暈了過去。一個男人掐她的人中,母親醒過來,癱倒在一旁繼續(xù)哭。
我第一次看見人骨,對死亡產(chǎn)生了恐懼,這種恐懼甚至比失去父親帶來的恐懼還要強(qiáng)烈。可是此時,沒有誰會關(guān)注到我。他們發(fā)現(xiàn)一條鳊魚在父親的胸腔里撲騰,一個男人說:“把這條魚放回湖里去吧,可能是死者的靈魂變的,要不怎么會這么巧,打撈時這么大動靜都不游走?肯定是想再看家人最后一眼。”聽著大人紛紛為父親生前一些荒唐的行為開脫,我也感受到了人性善良的一面。死者為大,即便他生前是惡棍,死后還是需要拔高他的形象,生者的眼淚能為死者送行。
那些就是他最愛的魚兒們,他一輩子沒有釣到一條魚,他就愿意這樣在湖底,看著魚兒穿過他的胸膛。那么熱愛釣魚的人,最終將自己的肉身,奉獻(xiàn)給他從來沒有釣上來過的魚。
我一直抗拒去釣魚,我不想重復(fù)父親的失敗,也不想因?yàn)獒烎~想起父親。可是,飛豬卻帶我來到離學(xué)校不遠(yuǎn)處的魚塘。我拒絕握住那漁竿,他掰開我緊握的手掌,先用我的手指去觸摸漁竿,繼而手掌,再到整雙手去觸摸它。
最后我決心試試,幾分鐘后,水面的浮漂沉下去。他喊“拉”,我便用力拉著。第一次感受到魚在釣線的另一端和自己博弈。我本能地拼命握住漁竿,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會。魚的力氣非常大,東竄西竄。我想起父親那天講故事的神情,也想起那個故事,眼淚不停地流下來。
飛豬見我淚流滿面,也不過來幫我,直到我無聲的哭泣變成蹲在地上號啕大哭,他才急忙過來,從后背環(huán)抱著我,兩只大手覆蓋在我那還緊緊握著漁竿的手上,在我耳邊說:“別怕,別怕,有我在這兒,肩膀放松,沒事的。”我感受到從他手掌傳來的力量,慢慢我停止哭泣。他與我共握一條漁竿,感受魚的力量慢慢由強(qiáng)變?nèi)酢W詈篝~浮出水面,他用撈網(wǎng)網(wǎng)住它,是一條七八斤重的鯉魚。我仿佛用一場哭泣替父親和自己完成了某種儀式。就是這次,我們拍了那張存在電腦上的相片。
飛豬住在隔壁,我和他之間的關(guān)系,是從我搬進(jìn)翠瓏郡23樓開始。他教我開通天然氣,使用銀行卡代扣物業(yè)費(fèi)、水電及停車費(fèi)還包攬各種小家電的安裝。他的出現(xiàn),讓我的生活變得簡單起來。
六
父親去世后,我們家變得更艱難。雙胞胎妹妹常常一跑便滿臉紫黑,呼吸不過來,醫(yī)生診斷為“先天性心臟病”,醫(yī)生說可以去大城市通過手術(shù)治療。為了湊手術(shù)費(fèi),母親過上了比以前更苦的生活。8歲那年,與我同年紀(jì)的小朋友都去讀書,我還在家里幫忙打草喂豬,飼養(yǎng)兔子,直到10歲我才開始上學(xué)。
姐姐因?yàn)槭懿涣思依锏呢毟F,更受不了貧窮還沒有個盡頭,15歲就和一個肩膀上站了一只鷹的流浪藝人去浪跡天涯。母親因此大病一場,更多的活落在我的身上。
我怨恨很多的人,比如沒責(zé)任感的爸爸、生下我們的媽媽、逃跑的姐姐還有患病的妹妹。我想去一個沒有疾病,不用為錢而煩惱的世界。在我還沒有去成的時候,兩個雙胞胎妹妹先行去了,前后相隔一天,那時她們倆14歲。媽媽說:“她們?nèi)チ藳]有疾病也不用為錢而煩惱的世界。”
媽媽用那些還不夠給妹妹們做手術(shù)的錢,開了一間很小的百貨店,賺錢供我讀書。她希望我學(xué)醫(yī),覺得家里能有個醫(yī)生就不至于那么害怕疾病,何況當(dāng)醫(yī)生是個好工作,還能賺到很多錢,以后一輩子衣食無憂。可我偏偏不愿成為上帝的化身,不愿面對那些渾身病痛的人,我還是世間最多傷痛的那一個呢。我報考了美術(shù)學(xué)院,母親對我哭過、罵過、打過、威脅過,我還是不改志愿。事實(shí)上,我并不熱愛美術(shù),只是為了逃脫母親安排的人生。
一晃又過去好多年。我從美院畢業(yè)后因?yàn)槔L畫天賦并不高,不能夠成為職業(yè)的藝術(shù)家,便回到本地高中教美術(shù)。母親憑借勤勞與聰明,將百貨店經(jīng)營得有聲有色,規(guī)模比之前大幾倍,請了兩個收銀員、三個雜工。上天沒有辜負(fù)勤勞肯干的人,母親依靠自己的努力過上了好日子。她沒有和我住在一起,而是住在店鋪的閣樓。她說不習(xí)慣住在23層高的大樓里,太高讓她害怕,也不方便每天來店里看店。我們的生活真正好起來了,真好,只是依然沒有姐姐的消息。
飛豬是個不婚主義者,母親說他不愿意結(jié)婚就不值得和他耗在一起,女人的青春太有限。與填寫志愿那次一樣,我再一次違背了母親的意愿。
在我28歲的最后一天,母親為我的婚姻問題焦躁不已。那時我正在開車,母親喋喋不休重復(fù)那些讓人煩心的事,讓我不要因?yàn)楦赣H的不良示范而不再相信男人。我在恍惚間把車開向兩個亮光的地方,希望從光中穿過去,之后便得光明。可那是一輛大卡車的車燈。
在醫(yī)院醒來,我右腿骨折,腦袋受到嚴(yán)重撞擊,固定在床上不能動彈。母親當(dāng)時因?yàn)闆]有系安全帶,撞出車外當(dāng)場死亡。我似乎再也感受不到疼痛,淚水無聲潤濕了纏在臉上的紗布。
母親走后,我不擅長百貨店經(jīng)營,飛豬幫忙將百貨店轉(zhuǎn)讓出去。結(jié)余幾十萬元現(xiàn)金,存在銀行。我除了到學(xué)校上課外,幾乎沒有其他活動,沒有結(jié)交任何新朋友,一是我不能從與其他成年人的交往中找到快樂;二是社交讓我感到無限的壓力;活著就是為了感受痛苦。
母親走后,我的生活變得一團(tuán)糟,常常失眠,或從夢中驚醒。直到有一天,我開著車,前一刻我還知道在哪條街,后一刻我便不知道身在何處,甚至不記得家在哪兒。飛豬這才意識到,我的精神狀況出了問題。次日他帶我去醫(yī)院檢查,半個月內(nèi)做完多項(xiàng)檢查后,我得到可怕的結(jié)果:阿爾茨海默病。俗稱:老年癡呆。
七
一個年僅30歲的阿爾茨海默病患者,引起了醫(yī)院的重視。醫(yī)生綜合非常多檢查與會診,包括家族疾病譜、既往史等等,得出我罹患這個病的誘因,極有可能是28歲那年的車禍,頭部受到重創(chuàng)有關(guān),這種情況比其他慢性因素誘發(fā)的病情要來得更迅猛。旅館那次驚心動魄的暫時性失憶并不是第一次,我的記憶早就在和我捉迷藏。
我意識到這個疾病是白云形狀的橡皮擦,它總是在變幻各種形狀,目的是逃過記憶的反擊,以便出其不意偷襲我的記憶、擦掉我的記憶,直到它們把我置于永恒的白色世界,才會善罷甘休。有人總是害怕黑,將一切恐懼之事形容成黑,但我感到白遠(yuǎn)比黑更讓人無望,它們是卑鄙的小人、可惡的小偷、無恥的強(qiáng)盜,你感受到它們在掠奪你所有的一切,卻無可奈何。憤怒是最無力的反抗,并且對于這件事一點(diǎn)作用也沒有,等同于你已經(jīng)承認(rèn)無牌可打。我相信,如果我不是第一次發(fā)病,在此之前,我肯定憤怒過、恐懼過、祈求過。
不知道在記憶中遺忘的事,會不會在世界其他地方重現(xiàn)?要知道,這個宇宙不是空白的,它存在許許多多事物,但它們不會被平庸的心靈所發(fā)現(xiàn)。而我將成為那個平庸的人,精神最貧瘠的人,實(shí)在讓人感到悲傷。會有人撿到我遺失的記憶嗎?它呆在別人的記憶中會比呆在我的記憶里更快樂嗎?如果我積極去思考新事物,或許它能比舊事物更保鮮,就像身體里新鮮細(xì)胞替代老細(xì)胞那樣?
飛豬和我在候診室等了將近一個小時后,我坐到了醫(yī)生的跟前。他體形肥胖,態(tài)度和藹。
醫(yī)生說:“早上好,羅儀。”
我說:“早上好,醫(yī)生。”
醫(yī)生說:“有感到哪兒不舒服嗎?”
我說:“如果消化不太好也算的話,嗯,沒有什么胃口,能給點(diǎn)助消化的藥嗎?”我想或許這樣講,大家會輕松一點(diǎn)。
醫(yī)生說:“嗯,可以的,這消化不良也是個問題,可以多喝點(diǎn)牛奶、酸奶或水,食物要選擇容易消化的東西,保持適當(dāng)運(yùn)動。最近有交到新朋友嗎?”
我說:“沒有,我不喜歡和別人交往。”
醫(yī)生說:“睡眠怎么樣?每天大約睡幾個小時?”
我說:“入睡比較困難,每天大約五六個小時,容易醒。”
醫(yī)生說:“我會再給你開點(diǎn)幫助睡眠的藥,你平常還是要做有氧運(yùn)動、力量訓(xùn)練30~60分種,一周五六次。運(yùn)動有助于睡眠以及能保護(hù)你的心臟和肌肉。可以加一些冥想、音樂、腹式呼吸,這些有助于讓你放松。”
醫(yī)生說:“平常生氣的時候多嗎?”
我說:“還好,有時候可能因?yàn)閷W(xué)生比較容易生氣。”
醫(yī)生說:“嗯,你的職業(yè)比較特殊。如果我建議你和學(xué)校說明情況,換個工作,你感覺怎么樣?”
我說:“不,除了教孩子們畫畫,我不會做其他事。讓我好好想想。”
醫(yī)生說:“羅儀,我明白,你暫時還能勝任,但是隨著病情的改變,有可能會影響教學(xué)質(zhì)量。如果你不能出色完成本職工作,那么對孩子們來說是不公平的。當(dāng)然,這些建議不是我的本職工作,你可以自己考慮。”
我說:“醫(yī)生,你就告訴我,我多久后會變成傻子,然后死去?”
醫(yī)生說:“目前沒有特別好的辦法徹底治好這個病,但是配合治療,得到改善的概率是非常大的。這個時間沒有個定數(shù),一切結(jié)果與你是否積極治療有著直接的關(guān)聯(lián)。”
聽到這兒,我非常難過,等同于他承認(rèn)這個病的不可治愈性。醫(yī)生讓我躺在檢查床上,用一些陌生的儀器,在我身上從頭部到腹部仔細(xì)檢查著。我對這些儀器很排斥,儀器粗糙,沒有溫度,甚至太過冰冷。它隨意游走在我炙熱的身體上,像上帝一樣任意翻看我的內(nèi)部。我還是得忍受著,那些我看不見的內(nèi)部,有著與我勢不兩立的敵人。
審判官停下來,坐回電腦桌前開始寫處方,每寫一個字都要確認(rèn)很久,把醫(yī)生的謹(jǐn)慎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最后,他跟飛豬說到二樓收銀臺付費(fèi),然后分別到收銀臺對面的中藥房、西藥房取藥,最后還對飛豬說:“照顧比治療重要,陪伴比藥物重要。”飛豬點(diǎn)了點(diǎn)頭。我沒有再說一句話。或許,當(dāng)初我真的應(yīng)該聽母親的話,學(xué)醫(yī)。
在回家的路上,我和飛豬說:“醫(yī)生建議我不要再工作,你怎么看?”飛豬說:“我們先不辭職,本來你的課也不多,我們再慢慢想辦法。你別把自己得這個病的事跟別人說,免得別人說三道四。以后課表給我一份,有課的時候我都會幫你設(shè)置好鬧種提醒你。”“嗯,好。”說完我便看著放在雙膝上的藥,中藥類的有紅花、丹參、三七、石斛等等,西藥有蘇糖酸鎂、奧拉西坦等等,名字聽起來都很美。然而,它們是戰(zhàn)士,要代替我和體內(nèi)的某些細(xì)胞奮戰(zhàn)。有時候感到,死亡是一件好事,當(dāng)你慢慢知道,你不自覺地在記憶中擦去自己的痕跡。
八
飛豬把中藥放在廚房,轉(zhuǎn)身便過來抱著我。他用力嗅我脖子上的味道說:“羅儀,你身上有一種莫名的香味,讓我著迷。”隨后他在包包里拿出拍立得相機(jī),說:“從現(xiàn)在起,我的寶貝要成為最美的攝影師,你可以用拍立得將身邊的人、做過的事都拍下來。如果拍的是人,那就在相片的背后寫上這個人叫什么、住在哪、電話、與你的關(guān)系、做什么工作,盡可能詳盡。如果是做菜,就寫下這個菜叫什么名,應(yīng)該怎么做,甚至你可以拍下這個電熱水壺,然后注明它的功用。”他邊說邊對著自己拍了一張,待相片出來后,他晃動幾下,找來筆,在上面?zhèn)渥ⅲ骸褒堬w,綽號飛豬,職業(yè)規(guī)劃師,住在羅儀的隔壁,2-2301房,電話:1312XXXXX76。特征是:帥,最愛羅儀。”寫完后他將那照片給我。
我問飛豬,為什么會和我在一起?他說:“在你搬進(jìn)23樓的第一天,我就注意到你。當(dāng)時你穿著藍(lán)色緊身的牛仔褲,黑色的T恤,粗跟黑色馬丁靴,還有及腰的黑色長發(fā),打扮雖然樸素但青春靚麗,我被你迷住了。”“我們不打算結(jié)婚嗎?”“我是不婚主義者,你一開始就知道。但這并不妨礙我們相愛,所有情侶會做的事,我們都在一起經(jīng)歷著,難道不是嗎?”是啊,換作任何人,誰也沒有勇氣去面對一個患有阿爾茨海默病的女友,這個責(zé)任沉重到愛情也不能承受,但是有他陪伴的這些歲月本身就已經(jīng)是恩賜了。
飛豬讓我隨身攜帶一本日記本,記錄下我身邊發(fā)生的任何事,說對以后有很好的醫(yī)學(xué)參考價值,又或者對我的生活也有備忘作用,這樣我不至于沒有途徑認(rèn)清事情的真相。
于是,我隨身攜帶的日記本上多了類似以下的記錄:
*今天我和英語老師陳熙在學(xué)校打了羽毛球。她的球技真好。
*今天我好像沒有按時吃藥?
*今天上午這一節(jié)課,我突然不知道講什么,腦袋里完全空白。
我試圖對某些情況置之不理,但壞消息是它們變壞的頻率在加劇。這種瞞著學(xué)校的日子沒有持續(xù)太長時間,原因是即使在飛豬的定時提醒下,我也能忘了上課的時間,有時還在課堂示范時突然畫不下去。總之在校長辦公室,我對校長承認(rèn)了病情。學(xué)校給我辦理停薪留職,讓我好好配合醫(yī)生的治療,好了之后再回來上班。當(dāng)然,我知道這些都是安慰的話。
我徹底宅在家里了,飛豬每天都會過來我這邊幫忙收拾房子。他將散落在房間的衣服,還帶著湯水的方便面盒子,以及一些不明來由的塑料薄膜等清理出房間。自從不上班后,我變得沒有力氣收拾屋子,有時還覺得雜物也不是非收拾不可,對臟亂的承受力越來越強(qiáng),我對飛豬的依賴也越來越強(qiáng)。我的精神與肉體都在開始松散,世界正在收攏它的口袋,給予我的可能性越來越少。
九
門外有人不停按門鈴,我沒有起來開門。直至門外安靜下來,屋內(nèi)才重獲寧靜。這里沒有電視、沒有網(wǎng)絡(luò),手機(jī)處于關(guān)機(jī)狀態(tài)。門窗緊閉,但房間里沒有完全暗下來,光從沒拉嚴(yán)實(shí)的窗簾縫隙透進(jìn)來。我感到自己身處密林,只有一束光亮從葉片的縫隙跳下。我穿著白色的衣服,躺在光下,光滲入我的身體,直至與白色融為一體。迷糊中,我看見肩膀上站著一只鷹的男人牽著姐姐的手從密林中走向我。我睡了又醒,醒了又睡。在半睡半醒之間,我聽到父親在那里說話:“羅儀,羅儀,你聽得見我說話嗎?你生這個病,是你潛意識里很早就啟動的自殺程序,甚至比你把車開向卡車時更早。你比我更希望去死。這個家沒有給過你一點(diǎn)溫暖與愛,我很抱歉,我不配做你的爸爸。但是羅儀,這個世界值得你用心去看看。”當(dāng)我喊著“爸爸”撲向他懷中時,就從夢中哭醒了。
人的身體是極其復(fù)雜的系統(tǒng),尤其是人的大腦。如果不能再記憶事物,就會讓人稱為“呆子、傻子”。我不愿意像其他失能、失智的阿爾茨海默病患者那樣住進(jìn)養(yǎng)老院,被護(hù)工投喂食物而不能感受到它的味道,又或是穿著病號服由護(hù)工決定是否幫你淋浴、是否需要推你去曬太陽。當(dāng)對發(fā)生在自己身上的任何事都不能感知時,也就意味著失去生活的價值和意義。我能想象到的這些護(hù)理,已經(jīng)是阿爾茨海默病患者得到最好照顧的理想化情景了。我是否能得到這樣周全的照顧,這本身就是未知數(shù)。
這個病將讓我陷入很長一段時間的毫無尊嚴(yán)的茍延殘喘,它是深不見底的泥潭。我必須振作起來,去嘗試各種自救的方法,不能拖累飛豬。
在我還沒有徹底變成傻瓜之前,我想在世界之間去認(rèn)識我自己。我對世界沒有什么認(rèn)識,就像對自己的身體、對自己的思想那樣,一切模糊、不確定。每一片瓦礫都與世界有著千絲萬縷的關(guān)系,我也一定有的,不是嗎?
我起身去浴室里,用剪刀把自己及腰的長發(fā)剪成齊肩的短發(fā)。用雙手撫摸自己中間略高于兩側(cè)的額頭,還有眉骨、眼窩、鼻子、嘴唇、耳朵。這些形狀就是我在別人眼中的五官嗎?我看到的與他們看到的會有所不同嗎?人的心智,它又藏在哪里?
沒讓任何人發(fā)現(xiàn),我離開了家,踏向了未知的旅途。日記本上開始記下許多不完整的故事,字?jǐn)?shù)一次比一次多,不再像以前,只能寫一兩句話。我用耳朵分辨聲音的種類,用眼睛去分辨色彩的層次,追尋人們面部的五官、神情、話語,并且嘗試寫下我能想得起來的所有故事。寫作比畫畫更適合我,我之前沒有發(fā)現(xiàn)。我在沖破一些邊界,雖然沒辦法證實(shí)是否能最終打破一些禁忌,但我已經(jīng)能捕捉到某種精靈的身影。
在旅途中,我的生活能力總是表現(xiàn)得不盡如意,我決心不把阿爾茨海默病當(dāng)一回事,無論它以什么形態(tài)出現(xiàn)。我也會像剛學(xué)走路的孩子,跌倒后爬起來再走,經(jīng)驗(yàn)對我來說失去意義就讓它失去好了。我的記憶是有瑕疵的,甚至破裂的,反而多一些非常態(tài)的歡樂。我開始不再恐懼它。
十
一年后,我途經(jīng)一個村莊,看見山坳處有一所低矮房子,周圍彌漫著白煙。那里有裹著籬笆的菜園,四處晃蕩的雞鴨,宛若人間仙境。我看見一個婦女在地里干活,她將一些曬得半干的雜草點(diǎn)燃,正是這些燃燒的火堆升起了濃濃的白煙。她的眉眼之間有一種讓我感到非常熟悉的神態(tài)。我問她:“大姐,我從外地來,能否在您家吃個晚餐?我會付錢。”大姐說:“什么錢不錢的,留下來吧,多雙筷子而已。”
我走進(jìn)她的家,一幢木質(zhì)結(jié)構(gòu)的老房子,屋頂采光窗將屋內(nèi)照得亮堂,沒有什么霉味。屋子里物品雖多,但不顯凌亂。有個男人正在做竹籃子,看見我便立刻放下手中的活和我招呼,大姐介紹這是她家的男人。
大姐問起了我老家是哪里的,待我說完,她一拍手掌,說:“哎喲,巧得很咧,我也是從哪里來的,不過我十幾歲就從那里離開了。”
我說:“您從來沒有回去過嗎?”
大姐說:“回去個什么鬼嘛,大老遠(yuǎn),我早忘了具體在哪個地方啰。”
我說:“您在老家還有家人嗎?”
大姐說:“有的,有媽媽和妹妹。”
我心里一緊,大概我猜的是不會錯了,我問她:“您姓什么叫什么?”
大姐說:“我姓羅,叫羅玲。”
天下的巧合都讓我碰上了嗎?我壓制住內(nèi)心翻滾的波濤,繼續(xù)問她:“您從家里出來后就到了這里的嗎?”
大姐說:“不是的,我是跟著一個流浪藝人離開家的,我們家太窮太苦了。離開后,我跟著他走了很多的地方,后來他把我賣到這里。不過現(xiàn)在這個男人對我還算好,我也就安心留在這里了。”聽到這兒,那個男人,也就是我的姐夫,不好意思地?fù)蠐项^。
我說:“那你就一次都沒有想過回去尋親嗎?”
姐說:“想過,但是也沒有個臉回去啊。你想嘛,自己要走還有啥子臉回去嘛?”
我說:“那你有沒有想過,家人的定義就是會相互包容,不會計較什么臉面啊,能在一起最重要?”
姐說:“唉,說得也是啊,找個機(jī)會回去看下。”
快到晚餐時,有兩個孩子背著書包跑回了家,一個男孩一個女孩。姐說這是二娃和三娃,還有一個大娃兒在縣里讀高中,一個月才回來一次。我看著她忙里忙外,日子過得平淡又真實(shí)。晚餐,姐姐做了干竹筍炒臘肉、雞蛋炒韭菜,還有一種風(fēng)味特別的魚干,和一瓶刺梨酒。姐說都是她家的平常菜,我卻吃出了人間美味。酒到酣處,我告訴了姐姐我的身份。姐姐和姐夫難以相信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但我說出父親吹牛皮講《老人與海》的故事時,姐姐失聲痛哭了起來。
我在姐姐家住下了,每天和她一起干農(nóng)活。干完后,我覺得精神特別好。寫作也有新的進(jìn)展。
后記
我叫羅玲,是羅儀的姐姐。我沒有辦法像羅儀一樣把文章寫好,我只能簡單交代一下羅儀的情況。在我們相認(rèn)后的半年,我們夫婦倆和羅儀一起來到她生活的地方,也見到了飛豬。飛豬幫我們把房子賣了個好價錢。他希望能照顧羅儀,羅儀拒絕了。我們夫婦倆也覺得由我們照顧羅儀更加合適,在我們農(nóng)村不用花什么錢。她每天很開心,像孩子。
另:五年后,飛豬再次來到我們家時,帶來了署名為羅儀的詩集與一本關(guān)于阿爾茨海默病患者旅行的散文集。飛豬說不管是詩集還是散文,都收到了非常好的反響。不幸的是,羅儀現(xiàn)在已經(jīng)聽不懂這其中的意義,也已經(jīng)認(rèn)不出飛豬。我們這里山好水好,雞蛋青菜也都充足,請相信我們能照顧好羅儀。再次感謝所有關(guān)心羅儀的讀者。
羅玲
2021-12-23
責(zé)編:胡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