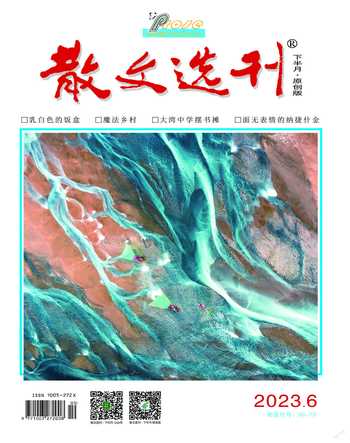散文背后的故事
我是沒有創(chuàng)作理論,也不相信創(chuàng)作理論的,我就想把散文寫好。我現(xiàn)在出了56部書,大概有90%都是寫西藏的、寫青藏高原生活的:汽車兵生活、邊站生活、醫(yī)院生活、西藏地區(qū)的藏族生活,都是這些。
幾十年當中,我就是愿意啃硬骨頭。可能當兵一輩子的性格就是這樣,難解決的事、難弄的題材,我非得把它弄下來不行,最后基本上都弄下來了。我只給你們舉幾個例子。
我有一篇文章是《情斷無人區(qū)》。西藏有一片無人區(qū),我們50 年代過去的時候,無人區(qū)是真的無人。現(xiàn)在說是無人區(qū),其實早就有人了。平叛部隊有一個戰(zhàn)士,在追一個叛匪的過程中,被遺忘在無人區(qū),最后變成一個完全藏化了的人。
我知道這個事以后,從北京坐車過去。那時候還沒有高鐵到拉薩,連到格爾木的火車都沒有。我坐到蘭州以后倒車坐到西寧,然后就坐汽車。我后來寫出了《情斷無人區(qū)》,寫完以后也沒人給發(fā)。一個解放軍戰(zhàn)士在平叛的時候,被遺忘在無人區(qū),變成一個野人一樣沒有下落的人了,誰敢發(fā)?他每年7 月份從無人區(qū)里出來買些東西,頭發(fā)也不理——沒法理,穿的衣服破破爛爛的。我第一年進去沒看到他,第二年去也沒看到。那時候我在北京就坐車去了,因為我是汽車部隊的。那里有5 個汽車團,我去的時候他們就派個小車,還配一個醫(yī)生,這樣比較保險。那時候我已經(jīng)寫了好多高原題材的文章。我后來終于碰到了他,他說不了多少話,也不愿意說。
我得魯迅文學獎的那本《藏地兵書》上有《情斷無人區(qū)》。出版社在出版我的集子之前,要給我拿掉,我說你們不要拿這篇文章。后來這篇文章發(fā)在《解放軍文藝》和《電影電視文學》。發(fā)表以后,他們把它改成電影,叫作《一只藏靴》,因為那里面貫穿的就是一只藏靴。他們把農(nóng)奴主的女兒改成了農(nóng)奴的女兒,這下子就沒意思了。原本的故事是說,農(nóng)奴主的女兒在平叛的時候,用她的一只藏靴救了一個解放軍戰(zhàn)士,后來這個戰(zhàn)士成為野人被遺落在了無人區(qū)。
有一篇文章,我覺得也可以給大家說一說。現(xiàn)在的人可能都不知道當年首鋼的改革。首鋼是一個企業(yè),原來叫石景山鋼鐵廠,已經(jīng)快爛掉了,每年賠得一塌糊涂。一個人一拍板子,說我把首鋼承包了,這個人叫周冠五。他把那時候年年賠的首鋼承包了以后,和國家有合同了,上繳利潤百分之幾,最后首鋼成為一個很富有的企業(yè),在中國買了好多企業(yè),把美國的鋼鐵公司都買了,把鋼鐵礦都買過來了。現(xiàn)在的首鋼就這么起來的。
我當時寫周冠五的時候,他正在做這些事情,當中有些已經(jīng)做了。有些人說你膽子好大,你怎么還敢寫首鋼?他們那時小頭交給國家,大頭留給企業(yè)。那時的人就是這樣的,他們說,我們是有協(xié)議在的。那時的人覺得,這樣有利可圖。我原來的題目叫《首鋼十年改革實錄》,主管根本不理我,看不起我,就那么一個當兵的怎么還來?而且新華社一個很大的記者來采訪,稿子都沒寫出來,寫了個報道也報道不出去,我一個當兵的卻來寫,還寫了一本書。我是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的書,這個書出了以后,開了個研討會,好多人來就想看看我這個當兵的。抗日戰(zhàn)爭中的盧溝橋事變是我啃下的又一個硬骨頭,那本書也30來萬字。盧溝橋事變就寫國民黨抗戰(zhàn),抗日戰(zhàn)爭的第一槍是國民黨打響的,不是我們打游擊的八路軍。日本投降是給國民黨投降的,我就說我要寫盧溝橋。我那時候就是這股勁兒,骨頭越硬我越要去啃它,有的能啃下來,有的啃不下,但是大部分最后還是啃下了。
我在首鋼住了大概一年多,首鋼開始不理我,后來讓我轉(zhuǎn)業(yè)到首鋼,我倒不轉(zhuǎn)了。他們在首鋼給我搞了個房子,讓我住在那里,把書寫出來。我寫《槍響盧溝橋》,為了采訪國民黨打響抗日戰(zhàn)爭第一槍的營長金振中,還有韋縣長——叫什么記不清了——我到處找他。他是四類分子,在河南他是國民黨旅長,給弄回去以后被管制起來了。但是他們那個村書記很好,他寫了個交代材料,把這個過程都說了。那時候還沒有復印,我就抄。金振中就是打響盧溝橋抗日戰(zhàn)爭第一槍的營長,后來當了國民黨旅長。后來我把交代材料弄回去后,形勢好一點兒了,我就找他談了幾次,寫了這本書。
我主張作品要源于生活,還要高于生活。書里那種升華出來的東西,是作家認識它的結(jié)果,不光光是就事論事。所以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工作座談會上說,人民群眾喜歡來自大眾的作品,但是他們還不滿足,還要高于生活的,比生活更集中、更改革、更有普遍意義的。一共6 個“更”,這是毛主席講的。其實毛主席在延安就把這話講清楚了。作家的責任就是要高于生活。高于生活就要看作家的功力、本事,只就事論事是不行的。
比如我寫了個小稿子,也就是幾千字,叫《嫂鏡》。一個排長的愛人,到邊防站去度假,看她的愛人。她去了以后,發(fā)現(xiàn)邊防站沒有一個女的,看到的都是男的,有時候跑過一只狐貍也是公的。就這么一句話,這個東西我想象出來的,后來有人還看笑了。這個嫂子在這里一年零一個月以后要回去,她是浙江杭州人,是個演員。她在這休假一個月,教戰(zhàn)士們唱歌、洗衣服、開展文藝體育活動,戰(zhàn)士們堅決不讓她走。“嫂子,你再住一段時間。因為邊防站從來不來一個女的。”嫂子說,我要回去上班,我明年再來。戰(zhàn)士們說,那也不行。嫂子光笑不吭聲。排長說,人家來不了了,她有小孩了,要生小孩。那怎么辦呢?戰(zhàn)士們讓她把照片留下。邊防線上沒有照相館,沒法照相,她就從唐古拉山邊防站跑到格爾木去照了一張照片,把這個照片留下。嫂子是流著眼淚去的,回到杭州以后,她心里怎么也安靜不下來。看來邊防上沒有女人真是不行的。她當時就說,我回去以后,給你們寄一個最好的標準照。她說到做到,回家以后找了一個照相館,照了很好的照片寄給大家。照片寄到后掛了起來,結(jié)果戰(zhàn)士們還不解渴,都想要一張。排長說,這個照片我們到格爾木去給你們加印,一人一張。嫂子也來信說了,你們就把嫂子的照片貼到你們床頭上。排長買了些鏡框,把嫂子照片鑲在里面,貼在戰(zhàn)士床頭。
后來我就把這個稿子直接遞給《文匯報》。《文匯報》當時已經(jīng)登過我?guī)灼遄恿恕!段膮R報》編輯叫桂國強,我現(xiàn)在還記得桂國強給我寫的信:“宗仁老師,這篇稿子我們要在八一的時候登,要做‘龍頭。”這篇文章發(fā)出來后,轉(zhuǎn)載也太多了。就是說,作家要敢于寫別人認為你不敢寫的,或者是寫不好的題材。
生活當中美的東西到處都有,作家要發(fā)現(xiàn)美,提煉美。美的東西它存在于生活當中,但是它不是現(xiàn)成的,要經(jīng)過作家頭腦勞動、升華以后,才變成美。
我有一次想和藏族姑娘照個相,我是突然生發(fā)了這么一個想法。以前在拉薩河里,我看到了一個藏族姑娘打水,她還拿著藏族背桶。背上以后我就跑上去喊她,要和她照個相,但人家不理我。她看了我一眼,背著水就走了。但是我發(fā)現(xiàn)她抬頭看了一下,說明她聽見了我說什么。我相信她聽見了總還是會回來的,而且她要打水。第二天我就還在這個地方等,其實我有把握又沒把握。這姑娘又來了,來了以后她還背那個桶,又到這里打水來了。這時候她就用很不熟練的漢語問我,昨天你找我干什么?我說,昨天找你你不理我,現(xiàn)在你問我找你干啥,我倒不自在了。因為人家一個姑娘,穿的衣服很漂亮,要不然我也不愿意跟她照相。
我就跟她說了,我說咱們兩個合影,她當時就答應了。我說,咱們以布達拉宮為背景,前面是拉薩河,后面是布達拉宮。但是我們兩個合影,沒人給拍怎么辦?這時來個人,他也自作多情,來給我們拍照,我也大大方方地和姑娘照了一張照片。他照了以后夸說,這張照片很美,我就幫你起名叫“唐柳姑娘”。
當年,文成公主從長安帶去一棵柳樹,栽在布達拉宮前面,被稱為公主柳。后來她死了以后,拉薩的人就給柳樹澆水。我那個散文名字就叫《唐柳姑娘》。有些人以為這肯定是寫小說瞎編的,但我在這篇文章后面有一句話,說姑娘來自西藏林芝歌舞團。這句話一下子就告訴你,這不是編的故事,這是真實的故事。后來這篇文章在《解放軍報》上——2001 年還是2002 年我記不得了——被推出來了。《解放軍報》,你想想,哪能把這樣的文章登出來?編輯那個水平你可想而知了,還加上個按語:“老作家王宗仁已經(jīng)把春天的信息帶來了,這是一次美的震撼。”
我們把生活變成文學就行了,你把它寫好就行。
我還寫過一個很不好掌握的、很不好寫的題材。歌舞團的一個演員,1954 年跟著陳毅到西藏慰問演出的時候,到達可可西里。文工團員穿的衣服很漂亮,他們穿的衣服和別的部隊都不一樣。戰(zhàn)士們?yōu)榱丝次墓F員——他們第一次見文工團員——晚上去把人家住的帳篷圍了,讓人家唱歌,沒完沒了地唱,唱了一個還要一個。有文工團員最后唱得不行了,因為高原反應死在那里了。就是這么個事兒。他們后來都很難過,不該讓人家這么沒完沒了地唱歌。但是在那個地方,見到女的,特別是見到一個女的文工團員,難得很啊!
我后來寫了《歌的高度》,這個歌永遠在高原上飄揚。
我今天給大家說這些東西,更多的我也不一定能說得清楚。咱們都是搞創(chuàng)作的,你要下功夫,光下功夫還不行,你要向上、向下。向上那是高于生活,向下那是深入生活,這兩個哪個都少不了。
(本文系作者在“2022 年度中國散文年會”上的即興演講,標題為編者所擬,劉筱雪錄音整理。)
責任編輯:張若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