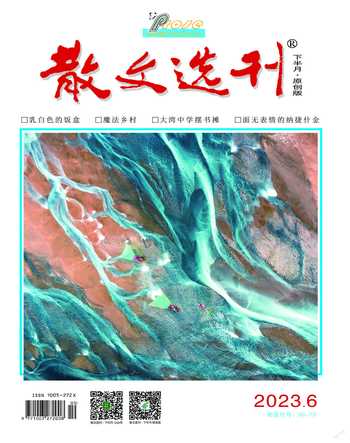愛恨都會隨風(fēng)而逝
朱敏
外公走了,享年92 歲。其實(shí),他是可以安詳?shù)刈咄晁娜松詈笠欢温返摹5赣H說,外公走得很痛苦,因為要搶救,于是進(jìn)行了插管。外公不停掙扎,終于無望。當(dāng)醫(yī)生將病人生與死的選擇權(quán)交給他的兒女之后,兒女們總要選擇不至于讓自己余生不安的方式。“萬一救回來了呢?”僥幸總是大于等死的焦慮。但最后,外公終于沒能搶救回來,幾根管子和幾滴血跡是他與這個世界作出分別的標(biāo)志。
最后的時刻,外公沒有忘記遠(yuǎn)在幾百公里外的唯一的兒子,他艱難地蠕動著嘴唇,呼喚著舅舅的名字,說,還沒回來嗎?當(dāng)我母親連聲說著“來了來了”的時候,外公終于閉上了他的眼睛,而舅舅在門前的重重一跪,也將作為兒子的最后一絲遺憾墜入無邊的黑洞。
其實(shí),在舅舅之前,外公最想見的便是外婆——那個讓他包容了一輩子、愛了一輩子的女人。外公對我母親說:“你娘呢?去哪里了呢?”而我外婆,卻很不情愿地、絮絮叨叨地走下樓。外公與外婆是被時代的紅絲線牽錯的怨偶。外婆是地主家的小女兒,從小嬌生慣養(yǎng),讀書讀到了初中。外公是外婆家的長工,雖然長得濃眉大眼,卻一字不識。隨著時代變了,大批地主被鎮(zhèn)壓,外公翻身當(dāng)了主人,興高采烈地娶了地主家的女兒,外婆也委委屈屈地做了長工老婆。當(dāng)然,這種埋在心底的委屈,不斷長出八腳爪,化成戾氣和各種語言暴力,不斷向生活的四壁沖撞。當(dāng)生存成為人生的目標(biāo)與重心,這種委屈與暴力尚能暫時服軟。當(dāng)人生不再為生存絞盡腦汁,當(dāng)兒女們?nèi)找骈L大直至各自成家,很多形而上的東西便變成了巨大的鴻溝。二十多年前,外婆與外公不再像別的老年夫妻一樣,攜手看夕陽,而是各自開伙,各吃各的飯。一幢空蕩蕩的老房子,兩個暮年老人,像鄰居,又像是互為租客。年逾古稀的外公,重新學(xué)起了做飯、炒菜。他經(jīng)常得意地對去看望他的女兒、我的母親說:“我會燒紅燒肉了”“我會燒紅燒帶魚了”……而外婆,則在她的神佛世界里,整日念經(jīng),并且由此衍生了她的職業(yè)……兩個世界里的人,終于徹底地不再有交集。
記憶里的外公,土地是他的根。他早出晚歸,風(fēng)雨無阻。一把鋤、一架犁,就是他與世界相處的方式。他春播秋收,像一只燕子一樣,壘窩銜泥,以自己的堅毅,一點(diǎn)點(diǎn)地拱出屬于自己的天地人生。他把外婆的責(zé)罵、暴戾,甚至羞辱統(tǒng)統(tǒng)收下,以自己泥土般的淳樸與憨厚,展示了他對外婆深沉的愛。他曾經(jīng)對我說:“你外婆很不容易,夏天穿那么厚的衣服念經(jīng),每一塊錢,都是辛苦來的……”而外婆,漸漸地,以她的戾氣表明了她的存在。也許是缺乏安全感吧,外婆拼命地存錢,似乎銀行卡上逐漸增大的數(shù)字才能填補(bǔ)她一生的空白……
外婆89 歲了。那天早晨,我坐在她的床上,看她低垂著頭落寞的樣子,心里忽然泛起了無比的酸楚。外婆竟然有一剎間認(rèn)不出我,問我是誰,我忽然掉下淚來:我的外婆,那個要強(qiáng)了一輩子的女人,終有一天,會與她的不甘一起,永遠(yuǎn)隨風(fēng)而去。
不管你是不是遇上了對的人,其實(shí),所有的恩怨,都會隨風(fēng)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