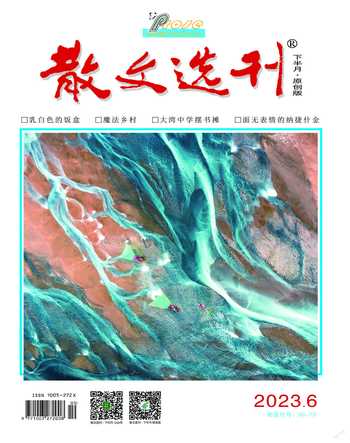山里美食
藍宇

到了九月,我們孩子跟著大人從地里割了豆梗挑回家里,在房頂上暴曬。烈日下的屋頂上,我們貓著腰兒,翻翻這兒,又翻翻那兒,去尋找在水泥板上被燙得打滾的黃豆蟲。
黃豆蟲的身子只有半顆黃豆大小,圓鼓鼓的,兩頭稍尖,顏色白中偏黃。這是一種隨著黃豆收成而來的美味,也是我們小孩子幫大人收黃豆、曬黃豆最大的動力。黃豆蟲原本躲在豆莢子里,經過暴曬的豆莢子爆裂開來,它們也便隨黃豆滾落而出。黃豆自然不怕太陽暴曬,可它們不行。滾燙的水泥板燙得它們到處蠕動,這便使它們無處藏身。圓胖胖的黃豆蟲撿了一天,黃豆便也暴曬了一天。太陽落下西山時,我們將撿了一大碗的黃豆蟲放到一邊,然后興致勃勃地將曬了一天的黃豆梗堆在一起,抄起竹竿便是一頓亂打。曬干了的豆莢子,在竹竿的瘋狂打擊下裂開,一顆顆黃豆也就脫落出來,當然,還有一只只美味的黃豆蟲。
架鍋下油,待鍋頭滾燙,便可以倒入黃豆蟲翻炒,這時候火候要大,因為黃豆蟲太小,經不起長時間的炒弄,需要大火速戰速決。從下鍋到起鍋,不超過個把分鐘,一碗清香四溢的炒黃豆蟲便炒好了。黃豆蟲的口感,和竹蟲的口感差不多,竹蟲有一股竹筍的香味,而黃豆蟲則自帶一股黃豆的香氣。黃豆蟲除了可以吃,還可以用來治療息肉增生。我小時候手上和腿上長了很多息肉,據母親說,是因為我小時候喜歡去看大人殺魚,我手上和腿上的息肉就是被魚血沾上后長出來的。按照母親的說法,人體沾上魚血便會長息肉。這個說法對不對我不知道,反正我小時候確實愛看大人殺魚。
我的手上腿上確實有許多息肉,特別是我的大腿上,有一塊手指粗長的息肉,像一只大肥蟲趴著一樣。這種息肉非常頑固,無論你切掉它多少次,四五天后,它又重新長了起來,和原來的沒什么區別了。
但黃豆蟲可以治好這種頑固的息肉。你必須先用刀將息肉貼肉切掉,把黃豆蟲搗碎,用碎汁兒涂抹在切口上,息肉便不會再長出來了。
所以,我一年級時九月的某個下午,已經謀劃多時的母親和哥哥將我綁在床上,母親用磨了三個早上的鋒利菜刀將我手上的息肉一塊塊切掉。起初在切手上的小息肉時,一點兒感覺也沒有。直到鋒利的菜刀往我腿上那塊蠶一樣的息肉切去時,一股鉆心的疼痛才從大腿外側傳來。我想掙扎,可大哥用力壓著我,我也只能在驚呼的惶恐中被母親操刀割肉。割手上的息肉時我沒有感覺也沒有流血,可割大腿上的息肉時不僅鉆心的痛,還流了一攤血水。
母親不顧我的哭鬧,找來一塊干凈衣布擦凈了血水,便將搗碎的黃豆蟲汁澆在我的傷口上。
那時我心里想,如果這黃豆蟲滅不掉我的息肉,那不僅是害我白白遭了這份罪,還白白浪費了小半碗的黃豆蟲啊!還好,黃豆蟲確實見效了,我手上和腿上的息肉真的沒有再長起來。
開年后的二月,成了最難熬的一個月份。不止我們難熬,山林間的萬物皆是如此。這時候,稍大一些的孩子便趁著周末帶我們去山上獵山鼠。山鼠是生活在山上專吃草根野果的老鼠,一般能長到兩三斤,有白色和灰色兩種。灰色常見,白色的偶爾會獵得一兩只。
獵山鼠是個技術活,我們小孩子弄不來。之所以跟大孩子去,是因為大孩子需要我們幫他們壯膽。因為山鼠所藏匿的地方都比較偏僻,要么是深山老林,要么是石縫山洞里。找到山鼠經常出沒的地方后,就地找一塊二十幾斤重的平坦石塊,用木棍將石塊呈45°角立起,在木棍下橫著放一根木條,一頭用草藤綁上一塊紅薯或是油桐籽,一個簡單的部署裝置便做好了。等饑餓的山鼠經過,咬食了機關上的紅薯或是油桐籽,橫木彈開,支撐石塊的頂木受力不平衡倒壓下來,便將肥碩的山鼠壓在石頭下。有時候運氣好時,一塊石板就能壓住兩只山鼠。
這樣的捕獵山鼠的簡單裝置我們漫山遍野去放,第二天一大早便去查看。那時候山鼠很多,一個晚上便能捕到十幾二十只大山鼠,足有十幾二十斤的鼠肉。
我們很少會直接煮食山鼠肉,須是臘干了,成了鼠肉干了,而且是家里來了貴客了,才會從灶上的橫木上拿下來招待客人。
山鼠捕回來后,一只只丟進灶里燒去皮毛,然后開膛破肚,將內臟都扔了,便將一只只空了腹腔的山鼠用竹簽串起來掛在灶臺上。因為灶臺經常生火做飯,在火烤煙熏之下,鼠肉不會變質。臘干后的山鼠肉從灶上拿下來,需要先在火上燒軟了老皮,再放到鍋里用水煮,之后用刀輕輕刮去被煙熏出的煙灰。如此清洗三四遍之后,便可以切塊用黃豆燜。
黃豆燜山鼠肉絕對是我們山屯一道極具特色的地道菜肴,配上山姜和土韭菜燜熟后,臘鼠肉特有的香味便被引了出來。往往是一小碟黃豆燜山鼠肉,便可以醉倒一桌壯漢。
據說現在山鼠很難見到了,有人到山里收購山鼠肉,一斤一百五十塊,卻依舊是個有價無貨的局面。
吃了黃豆燜山鼠肉,醉了一夜酒,第二天就需要一道田螺酸筍湯來解酒。
田螺須是我們山屯特有的田螺,那種一煮就會散發獨特清香的田螺,在別處絕對是沒有的。酸筍也是別處沒有的,這種酸筍是我們屯子里特制的,用刺竹剛長出來的鮮嫩枝條切成片,用一個瓷缸盛著,密封放置一年后才能開封。這種由刺竹嫩枝條制成的酸筍,一旦開封,那香氣便四溢開來,讓人聞之神清氣爽,胃口大開。
我們小孩子自然不會讓大人獨食,各自捧了碗也喝上一兩碗后,這才打著飽嗝兒,搖著一肚子酸水出門玩去。不過,在我們山屯可還有一件更為奇怪的吃食。我們曾經見過大人從山外的水渠里撈回一顆顆黃豆大小的白鵝卵石,然后將鵝卵石放到鍋中用豬油翻炒,加點鹽,然后就吸著那些翻炒過的鵝卵石喝酒。
想著想著,我的饑餓感又蔓延開來了。我暗自吞咽著口水,夜也不禁由深轉薄,薄得窗外已望得見黎明的到來。
責任編輯:蔣建偉
美術插圖:曲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