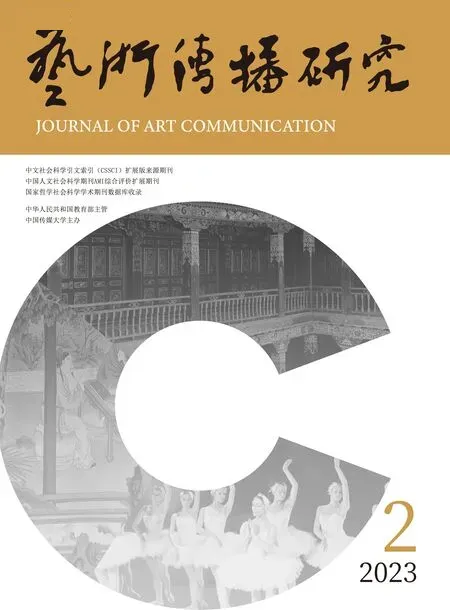“沉浸技術”對藝術接受的影響
——基于“沉浸藝術展”受眾訪談的定性研究
■ 吳恩楠 毛妮莎
進入21世紀以來,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使人類的生活迅速地數字化、數據化,甚至可以說,整個世界都在變成一串串代碼,而這也深刻影響著藝術品的呈現與傳播方式。(1)陳思函:《從鮑德里亞的藝術思想看沉浸式藝術展》,《藝苑》2021年第5期。一方面,技術的發展加快了藝術品的復制速度,將大眾帶入一個“數字復制時代”,網絡上和集市上都充斥著藝術復制品;另一方面,科技與藝術的融合也正在改寫藝術品及其復制品的呈現方式,使之越來越多地由單一感官的表現轉化為多感官聯動的展現,而且作品本身也可以成為一個參與和感知的過程。
在這樣的背景下,以“喚醒五官、深度體驗”為“賣點”的“沉浸藝術展”逐漸興起,策展方試圖通過360度環繞式場景的建造,讓受眾實現從觀看者到參與者的蛻變。“在(這種)展覽中,光影取代了油彩,空間置換了畫布,全身心體驗取代了單一的視覺觀看。”(2)徐天博:《沉浸式藝術展的藝術特征及價值研究》,碩士學位論文,深圳大學,2020年。策展方亦希望通過這種體驗,讓受眾與作為“他者”的作品共歷幻境,從而使二者建立情感聯結,以此促成受眾的藝術接受。但是,也有學者認為,新技術所打造的光影效果只是被復制的藝術品的一種展示手段,“沉浸展覽”也只是文化消費主義的一種產物。(3)參見楊紅、隗家興、張烈:《“網紅展”的流行成因分析及其內在特征》,《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2021年第4期。這種觀念同本雅明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一書中關于藝術品“光暈”(也作“光韻”,aura)消逝的論述息息相關:在技術的影響下,藝術品的“展示價值”(exhibition value,德文ausstellungswert)已遠遠超越以往藝術所致力創造與傳承的“膜拜價值”(cultic value,德文kultwert),從而使傳統藝術的“光暈”逐漸消逝。如果說,“沉浸藝術展”的目的是吸引受眾消費,那么被加注了技術因素的展覽也只不過是一件“符號商品”,按法國哲學家鮑德里亞的觀點來闡釋即屬于“擬像與仿真的文化”范疇。由此說來,根據鮑德里亞《消費社會》中的觀點,受眾只會對商品的符號價值趨之若鶩,而不會再在意商品本身的使用價值。(4)吳恩楠:《社會化媒體中眼見為虛的影像符號審視》,《青年記者》2022年第8期。在這里,如果將本雅明與鮑德里亞的觀點相互嵌合起來,可以發現,藝術作品的展示價值對應其符號價值,其膜拜價值則對應其使用價值。因此,受眾若不在意藝術品本身的膜拜價值,便只能淪入消費符號的境地,藝術接受亦無從談起。
“沉浸技術”對藝術作品的影響,究竟是利多還是弊多?對此的觀點割裂,無疑反映出數字復制時代沉浸藝術研究的強大學術魅力,而對“沉浸藝術展的內容特征與傳播邏輯”“展覽空間中技術之于受眾的影響”等議題的探討,也由此變得越發重要。
一、數字復制時代藝術接受范式的轉變
“審美的自律性”將藝術審美的對象束之高閣,為少數特權階層所有,這導致藝術接受的主體長久以來只能是“藝術精英”,或者說具有一定藝術專業素養的人士。(5)參見郭書、李書春:《機械復制時代中國微觀造型藝術的“大眾化”走向》,《藝術傳播研究》2022年第2期。但數字復制時代的到來,催生了以數字技術為核心的“沉浸藝術”,藝術作品的無損復制和數字化呈現,以及社交媒體的廣泛傳播,無疑加速了藝術作品的大眾化進程,也讓藝術接受的主體開始由“精英”向大眾偏移。簡單來說,在數字復制時代,藝術接受范式的轉變主要包含兩方面內容:一是藝術審美對象向“沉浸藝術”轉變;二是藝術接受主體向“普羅大眾”轉變。
(一)沉浸藝術:數字光暈的締造
“沉浸”(immersion)一詞在《新華字典》中的釋義為“浸入水中,常比喻處于某種境界或思想活動中”,其英文同樣是指被水環繞的狀態,亦可引申為“專注”。關于為何“沉浸”都發生在水中而不是陸地上,黃鳴奮曾經解釋道:“人作為陸地生物進入水中才會有異樣的感覺,因此‘沉浸’二字就詞源而言本就和異質世界相關聯。”(6)黃鳴奮:《新媒體與西方數碼藝術理論》,學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394頁。這意味著,受眾要想進入沉浸狀態,就必須先將注意力集中到一個不同于真實世界的虛擬世界中,以達到“神游太虛”的效果。美國心理學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提出的“沉浸理論”(也作“心流理論”,flow theory)解釋過人們在某些日常活動中如何“全情投入”,過濾掉不相關的知覺,從而達到沉浸的狀態。(7)Mihaly Csikszentmihalyi,Finding Flow:The Psycho-logy of Engagement with Everyday Life(New York:Basic Books,1997),p.22.沉浸狀態給人們帶來的便是沉浸體驗,即人們對某件事情感興趣時忘卻周圍環境,繼而忘記時間的存在的一種心理狀態。
由此,讓受眾以沉浸技術為橋梁,進入藝術作品所構建的幻想世界的藝術形式,即可被稱為沉浸藝術。沉浸技術的運行邏輯,是通過感官為受眾提供具身性的體驗,從而為他們打開通往藝術世界的大門。這里的“具身性”(embodiment)是指人類的生理體驗與心理認知狀態之間具備的強烈聯系。(8)Krishna Aradhna,Norbert Schwarz,“Sensory Marke-ting,Embodiment,and Grounded Cognition:A Review and Introduction,”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no.2(2014):159-168.國內亦有學者指出,人類的認知行為與身體的體驗活動緊密相連,人類認知是根植在現實世界同身體經驗的交互之中的。(9)文旭:《語言的認知基礎》,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08頁。可見,相對于傳統藝術而言,沉浸藝術的主要優勢便在于豐富了藝術作品的呈現維度,依靠音樂、燈光、裝飾等元素對藝術作品中的場景進行還原,讓人們能夠更加具象化地感受作品并與之互動,從而將受眾從拉康式的實在界拉入他者的想象界,實現維度的升華。從這個層面上說,數字科技不僅在根本上變革了藝術形式,也能夠幫助人們在身臨其境的體驗中實現對自我、對作品、對世界的深刻反思。(10)王紅、劉怡琳:《交互之美——teamLab新媒體藝術數字化沉浸體驗研究》,《藝術教育》2018年第17期。這也正好印證了麥克盧漢“媒介即是人的延伸”的著名論斷,因為若將組成沉浸藝術的各種元素視為媒介物,則它們顯然延伸了人的感官,并將人們引入一種超脫于現實的“異質空間”,從而實現沉浸。
但是,同傳統藝術相比,沉浸藝術也面臨著一個最大的爭論,即其是否具有光暈。本雅明曾浪漫地指出,藝術的光暈是指“在一定距離之外但感覺上如此貼近之物的獨一無二的顯現”,它源自“原真性”(authenticity,德文echtheit)。如果說藝術起源于巫術禮儀,最初是祭祀祈福用的洞穴壁畫,進而演變為在世俗禮儀中對美的向往和憧憬之心,那么那時的藝術品都是藝術家的手工原作,是凝結著人們美好想象的“原真的物”。但現在,“手工原作的獨一無二性被機械復制的摹本眾多性所取代”了,這導致傳統美學的秩序受到挑戰,原真性開始消解,光暈漸漸凋零。(11)于悠悠:《數字復制時代藝術作品的光暈再造》,《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2022年第1期。作為復制產品的沉浸藝術之所以被眾多學者質疑沒有光暈,也是由于其作品能夠忽略時空因素而不斷復現,不符合獨一無二的原真性邏輯。不過,在光暈的消逝讓藝術從獨一無二的“神壇”跌落的同時,技術也為藝術帶來了更多的建構性與可能性——這里的“跌落”是一種世俗化的表征,普羅大眾的“藝術神學”由此興起。(12)賀婧:《對“靈暈”的呼應:數字復制技術時代的藝術——從本雅明到斯蒂格勒》,《新美術》2020年第10期。另外亦有學者認為,沉浸技術賦予藝術原作以新的復制方法,讓原作實現了“數字永生”,這一獨特的存在方式會倒逼受眾回過頭去敬仰原作,反而提升了原作的地位,因此也可以說沉浸藝術具有一種“數字光暈”(digital aura)。(13)[英]約翰·伯格:《觀看之道》,戴行鉞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頁。按照拉圖爾(Bruno Latour)的說法,實物的數字化過程會伴隨著本雅明意義上的“光暈遷移”(the migration of the aura),而且“一個糟糕的復制會使原件有消失的風險,而一個良好的復制的原件可能會增強其本真性并繼續引發新的復制”(14)Bruno Latour,Adam Lowe,“The Migration of the Aura,or How to Explore the Original through Its Facisimiles,”in Switching Codes:Thinking through Digital Tehcnology in the Humanities and the Arts,eds.Bartscherer,Thomas and Roderick Coover(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1),pp.275-298.。因此,識別藝術復制品的“好”的與“壞”的光暈,將為藝術接受活動提供重要的導向。
(二)藝術接受:受眾本位的范式轉變
藝術接受是指接受主體在傳播學的意義上對藝術作品開展的各類品鑒活動,也是藝術創作和藝術作品實現自身價值從而構建完整藝術世界的途徑。(15)張偉、宋偉主編《藝術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14-215頁。所以說,藝術接受作為藝術傳播活動的一個環節,其主要價值在于探尋作品的意義。藝術接受的主體即指受眾,根據王宏建主編的《藝術概論》的分類,這里的受眾主要包括普通的社會大眾與具備更強“鑒賞力”的人士兩類,他們在面對同樣的藝術作品時,觀感和接受程度通常全然不同。另外,美國學者艾布拉姆斯(M.H.Abrams)曾在其著作《鏡與燈》中提出了文藝活動的四要素,即世界、藝術品(作品)、藝術家(作家)與受眾(讀者),(16)[美]M.H.艾布拉姆斯:《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酈稚牛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頁。后來傳播學者阿瑟·阿薩·伯格(Arthur Asa Berger)又在這個基礎上添加了第五要素,即媒介(或可稱之為技術要素),其中所有要素均與其他要素相連,共同構成了作品的內在價值。
因此,對本文而言,作為藝術接受主體的受眾勢必受到來自世界、藝術作品、藝術家與沉浸技術的影響。然而,伴隨著20世紀以來的“作者之死”與“作品之死”,受眾成了“上帝”,藝術接受的范式也逐漸變成了“以讀者為中心的自由閱讀”:作者的重要性被沖淡,導致讀者的閱讀行為成為關鍵,這種范式上的改變轉移了讀者對作者的興趣,改寫了揣測作者本身想法的重要性。(17)方維規:《文學解釋學是一門復雜的藝術——接受美學原理及其來龍去脈》,《社會科學研究》2012年第2期。于是,受眾的主體性得以凸顯,這也意味著他們在藝術接受之前,會提前代入自己的文化經驗,預先在腦海中構造作品的內容,成為伊瑟爾口中的“隱含的讀者”。因此,在觀看沉浸藝術展之前,受眾對展覽具有先決的審美期待,展覽中的具身性體驗則是判斷實際感受是否符合期待的關鍵因素,同時也是促成藝術接受的重要元素。另外,具身性體驗又源自沉浸技術——作為一種媒介,它勾連起受眾與藝術作品,以一種保羅·萊文森式的“人性化”演變趨勢,將藝術接受的范式由間接的感知體驗轉變為直接的沉浸體驗,由單一感官的經驗轉變為全身感官的聯動。(18)孫玉明、馬碩鍵:《從感性接觸到沉浸體驗:媒介進化視域下藝術接受范式的演變》,《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4期。

圖1 沉浸展覽受眾的藝術接受產生模式
此外,回到數字復制的消費時代中來看,技術的進步讓藝術逐漸大眾化、商品化,也讓藝術接受活動成為一種“藝術接受對象—媒介—藝術接受主體”的雙向互動。藝術接受主體在社交網絡上的一個簡單的“@”(表示呼喚其他特定用戶前來閱覽)就能發展為一股強大的輿論力量,影響藝術創作乃至策展活動,這便是藝術接受的效應。(19)劉俊:《技術視野下網絡視聽發展的進路與規律——基于接受與創作的互動》,《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9期。同時,科技令藝術作品可以被批量復制:一件著名的傳統藝術作品可以通過批量復制進入大眾的視野,再以沉浸展覽的形式變得可消費、可體驗,不再那么高高在上。從這個層面上說,藝術的大眾化、商品化,以及“曝光率”的增加,無疑能夠提高藝術接受的程度。但也如前所述,數字復制時代的“數字光暈”能否真正喚起受眾的藝術接受,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驗證。
綜上所述,以受眾為中心的藝術接受主要涵蓋“受眾的審美期待”“受眾的體驗”“受眾的接受效應”三個環節,其中的受眾群體又主要分為“普羅大眾”與“藝術精英”(藝術專業人士)兩類。本文將沿著以上的藝術接受發生脈絡,逐一探討沉浸技術之于沉浸藝術展受眾群體的影響。為此,筆者曾采用半結構化訪談的方法,在2022年3—6月考察過15名親身體驗過沉浸式藝術展覽的人士,并根據受眾群體的不同,將他們分為“普通大眾”和“藝術專業人士”兩類,其中前者10位、后者5位。這些受訪者的基本信息統計于下頁表格。

本研究訪談對象基本信息統計表
二、審美期待:情感與價值的凸顯
審美期待是藝術接受活動的起點,代表著受眾渴望得到滿足的需求。康士坦茨學派的姚斯(H.R.Jauss)將其稱為“期待視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s),他認為作品與受眾密不可分,作品需要為受眾的審美活動創造可能,也只有滿足受眾的希冀才能實現價值。(20)[德]H.R.姚斯:《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周寧、金元浦譯,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8頁。數字復制時代的沉浸展覽同樣如此,作為一件要“購票”才能享用的“商品”,它需要策展方確立各種主題來創造期待空間,它本身的展示價值亦會因此凸顯,并以票面價格的形式體現。而對受眾來說,既然帶著各種情感目的走入展覽,那么票價就是他們衡量展覽體驗最直觀的指標,“值或不值”都是他們情感的宣泄。本文中受訪的15位受眾的觀展期待主要表現為“尋奇”“敬仰”與“療愈”三種情感需求模式,兩類受眾之間沒有明顯的差異。
(一)尋奇:沉浸技術的魅惑
英國人類學家蓋爾(Alfred Gell)曾在《魅惑的技術與技術的魅惑》一文中將藝術稱為“魅惑的技術”。他指出,藝術是一種技術體系,歸因于社會的生產制造,而技術如手工工藝,作為構成藝術的關鍵要素,本身就具有魅力。(21)[英]阿爾弗雷德·蓋爾:《魅惑的技術與技術的魅惑》,關祎譯,《民族藝術》2013年第5期。因此可以說,沉浸技術本身即具有“魅惑”,具體表現為前文所述的“數字光暈”,而魅惑的結果就是受眾的好奇心被激發。15位受訪者中有7位均使用了“好奇”這一表述,其中3位普通大眾式受訪者表示自己從未體驗過沉浸展覽,因此“很想來看一看”(S6)。具體的表述如:
朋友送票,然后沒看過,想嘗試,而且那個展比較有名,聽說有很多“高大上”的東西。(S3)
好奇,一方面是喜歡印象派作品,另一方面是好奇沉浸式展覽是什么體驗。(S7)
對藝術專業人士而言,“尋奇”則主要表現為追求不同于傳統藝術展覽或現實景觀的新奇體驗,例如受訪者S12觀展的誘因是“對那些有名望的作品的新的呈現方式有一種期待”以及“厭倦了‘三次元’當中的一些景色,想追求光怪陸離的感覺”,她參加“敦煌光影藝術展”是希望看到科技賦能之下“有名望的作品”的呈現有何不同。
此外,部分受訪者的“尋奇”還表現出一種從眾心態,他們所期待的是他人評價中大紅大熱的“網紅展”。有部分受訪者表示去觀展只是因為“聽說”(S3)。在這種情形下,以符號學的觀點來看,“人云亦云”的結果實質上是對此類特定“網紅展”的符號消費,此時沉浸展覽本身的所指意義已被摧毀,他們的參觀行為也僅是一次“情感沖動”的結果。
(二)敬仰:膜拜價值的留存
沉浸藝術展覽作為數字復制技術的產物,是通過“交互設計、情景再現或場景模擬”的方式復刻藝術原作的,因此它所呈現的是數字復制技術帶來的“展示價值”。(22)李絢麗、李晨:《博物館體驗式展覽初探》,《中國博物館》2017年第1期。這一現象加劇了本雅明所說的藝術品“膜拜價值”的消逝;過分強調“展示”,只會將沉浸展覽拖入消費主義的深淵。“膜拜價值”所強調的,是受眾與藝術品之間的一種“無法逾越且無法克服的距離”,這種距離就是凝結了藝術家心血與奇思妙想的光暈。(23)王懷春、袁亞婷:《從本雅明“光韻”理論看手工技藝類非遺的價值與傳承》,《石河子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因此,若置換到本文的語境,應該說“膜拜價值”所強調的是受眾在數字光暈下對原作近在眼前卻又“遙不可及”的敬仰之情。
筆者通過對受訪者的調研發現,15人中僅有2人是因對特定藝術流派或藝術原作的敬仰而去觀展的,比如前述的受訪者S7就是因為“喜愛印象畫派的作品”才到場,而并非全然因為數字技術。同時,這種“敬仰”也表現在受眾對藝術展覽主題的審美期待上,他們會把對原作的喜愛延展到對展覽主題的喜愛。比如某位受訪者表示,他去觀看《莫奈與他的朋友們》沉浸展,是專門為了這個主題與相關人物。
我個人很喜歡(梵高的)《向日葵》,所以去看了。展前我是知道這位藝術家的,(這次)也是特地為了去看他的作品。(S14)
這一發現值得警醒。數字光暈或許能令原作實現“永生”,也能倒逼受眾敬仰唯一的原作,但數字技術的泛濫確實正在令作品漸漸失去原有的膜拜價值,沉淪在“技術的魅惑”中卻忽視了“魅惑的技術”,這也正是當代藝術傳播所面臨的一種危機。
(三)療愈:日常生活與社交儀式
藝術療愈應該說是一個橫亙古今的話題。自遠古起,人類就利用壁畫和原始歌舞來抒發自身的情感。亦有研究表明,只要參與藝術活動,無論是藝術創造者還是藝術接受者,都會牽動自身的情感,并伴有生理參數的波動。(24)高萍:《體驗式藝術展覽研究》,碩士學位論文,中央美術學院,2021年。本文所說的療愈,是指通過外界技術裝置誘發感官體驗,以此紓解參與者的精神壓力或傳達其難以言表的隱匿情感,從而實現心理層面的治療與治愈。共有6位受訪者表示自己參觀展覽是為了自我療愈,其中3位希望能緩解現實生活中的壓力,探尋心靈的慰藉。比如:
生活需要。平時工作太累了,需要一些娛樂。(S8)
沉浸式也是釋放壓力的一種方式,它可以讓你安靜下來,即便一個人也不會孤單。(S13)
同時,有3位受訪者表示,自己去參觀是為了“陪伴”具有社交關系的另一方,以滿足對方的心理需求。從這個層面上說,受訪者本身是情感療愈者,期待通過陪伴去深入對方的內心,了解對方的審美需求,從而鞏固社會關系。在這種情況下,“看展”成了一種儀式,其意義在于增強與發展社交關系。例如:
自己都是和好友約好一同觀看的,算是和朋友的一種小聚,又或是一種交流。(S9)
我是為了陪女朋友。(S10)
因為有學藝術的女兒吧,不停地被拉去看展,這漸漸成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S4)
正如約翰·杜威(John Dewey)所言,“藝術增強了當下生活的感覺,并強調了享樂中有價值的東西”。通過調查亦可見,欣賞沉浸藝術已被一部分受眾視為可以進行藝術療愈的體驗,而沉浸藝術展也可以成為他們抒發個人情感的意義空間。
三、多感官體驗:身體與場景的勾連
體驗,關系到藝術接受的產生。吉布森(James J.Gibson)曾在《視知覺的生態進路》中指出:人可以經由身體知覺,直接構建與外在環境的聯系,而并不需要相關背景基礎。(25)谷曉丹:《數字空間藝術具身交互美學與審美趨向——基于可供性具身認知視角》,《渤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1期。這一觀點被稱為“技術可供性”,指技術所能提供給人的東西。在沉浸展覽中,技術為受眾營造了一個可供體驗的場景,而受眾在其間身心一體的經歷便是具身體驗。筆者訪談的15位受眾的此類具身體驗主要可以被描述為“五感聯動”和“符號內爆”兩種,而且普通大眾和藝術專業人士之間的體驗明顯不同。
(一)五感聯動
實現前文所述的身、心與周遭環境一體的具身性沉浸狀態,主要依靠的便是沉浸技術的“可供性”:由技術所構建的場景會成為一個不同于現實世界的異質空間,它同受眾的知覺直接關聯,受眾在接收其信息的同時也在感知自身的信息,進而有可能迸發出與空間的共鳴。這種知覺又是五感嵌合的,身體由此會逐漸與場景融合為一個信息交互系統,受眾哪怕此前對展覽內容不甚了解,也能夠獲得具身體驗。在筆者的訪談中,共有9位普通大眾和2位藝術專業人士體驗到了這種“交互”,其內容也涵蓋視、聽、觸、嗅、味各個方面,比如:
第一次去這種沉浸式藝術展,不同于室內很安靜的擺件展覽,這個展覽更有互動性,我不會糾結于自己有沒有看懂或者“get”(接收、領會)到藝術家的想法,不需要假裝欣賞、不懂裝懂,而是更關注自己的體驗感了。(S1)
有點類似于小故事的表述方式。有音樂、有光、有背景板那種,然后走在里面就像走在畫集里。(S8)
沉浸展覽中,受眾之于場景也并非全然被動參與,而是能夠發揮主體性,主動調動知覺和情感,實現身臨其境的效果。比如:
整體的藝術沉浸感非常強,很多裝置可以人為參與。參與到空間中才能感受氛圍。(S5)
海洋生物系列,讓你感到仿佛在漆黑的背景下聆聽自己內心的聲音。這也是一種沉浸的體驗和給予自我的空間。(S13)
同時,一些展覽也打破了固有的五官邏輯,讓受眾用聲音去“看”,用觸覺去“聽”,實現了自身物理行動能力與場景空間的深層次互動。比如,受訪者S12表示自己曾體驗過一個“霧氣沉浸展”,展場的能見度很低,但是“觀眾用腳探索走廊,手觸摸墻壁,這些感受也是另一種模式的‘看見’”。

圖2 霧氣沉浸展概念圖
(二)符號內爆
“內爆”(implosion)是真實與擬像之間的一種鮑德里亞式的失衡,其結果是媒介塑造的景象代替了現實,原本的真實因而失去了意義。沉浸技術的可供性,一方面為受眾提供了無與倫比的體驗,使“精英藝術”降低了“門檻”,另一方面也使作品成了可被復制的消費符號,讓“藝術精英”們因此而擔憂作品之于他們自身的意義被削弱了。可以說,“內爆”讓大眾坍縮為吸收一切的“黑洞”,所有的意義看起來都將消亡。有受訪者表示:
我個人覺得這種技術帶來的經歷對藝術專業人士來說是削弱了體驗的,因為我會比較關注原作的創作語境,它是為什么被創作出來的……但是這些高科技的東西并不能給我提供這樣的感受,策劃這些東西的甚至也是一些根本不懂原作的人,所以展會就變得沒有意義了。(S11)
關于如何解決“內爆”問題,有藝術專業人士呼吁沉浸藝術展應反過來關注現實,而不是一味地追求“超真實”的具身體驗。受訪者表示,展覽的重點在于凸顯原作的意義,而不是強調技術的力量:
當沉浸展覽運用冰冷的數字系統時,其吸引力和接受度會逐漸下降……大家需要的是可以觸及并且有熟悉感的物質材料,用以闡釋原作,不至于(讓人)迷失在虛擬的符號中。(S14)
所以說,沉浸技術和其場景內的物質材料之間的平衡,關系到受眾對真實的感知,且材料的使用要能幫助受眾理解原作,而不是成為技術的附庸。
四、接受效應:虛擬與現實的碰撞
藝術接受效應,是指藝術接受活動在受眾親身體驗后所達到的效果,它是審美期待中的受眾需求是否得到滿足的體現。而受眾的評價,則是衡量藝術接受效應的最直觀的指標。(26)楊慧:《消費文化視域中的藝術接受研究》,博士學位論文,遼寧大學,2016年。按照關于審美效應的觀點,促成藝術接受的條件是受眾與藝術品產生共鳴,因此筆者也按照“能否與藝術品產生情感聯結”這一標準對受訪者進行了調研,最終發現沉浸藝術展的藝術接受效應主要呈現出“超真實符號的批判”“娛樂抑或娛樂至死”與“人與物的情感勾連”三種樣態,且兩類受眾的接受效果有明顯的不同。
(一)超真實符號的批判
海德格爾曾預言“一個世界圖像的時代即將到來”。技術的發展將整個世界編碼成了可以被展示與解讀的仿真圖像,而數字復制技術在延展了圖像的傳播的同時也加劇了真實的消逝。沉浸展覽運用復刻藝術品的圖像,輔以聲光電環境、煙霧和文字說明等感官因素,讓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個場景,這個場景在展覽期間不斷被復制、被展示,最終成為一個“超真實”的擬像符號。但是,藝術專業人士由于深諳符號背后的超真實邏輯,對沉浸技術所建構的場景也會有高度的警覺。具體來說,他們在此的態度至少有三個方面:
首先,他們更關注原作藝術品的創作方法與創作語境。顯然,數字技術復刻下的作品已經失去原作的筆觸、刻畫、原生態顏色的細節等“技法”,所以他們在已然脫離歷史語境的狀況下,會認為自己所感受的一切都是被建構的“真實”,因此難以和作品產生情感連接。相關的闡述如:
我覺得看實物的好處在于(可以)理解藝術家是怎么去刻畫作品的。你從近處看,會想到他是怎么去進行他的創作,用了什么樣的技法,通過什么樣的方式把這個作品做出來的。實際上我覺得現代藝術的根本的點就是它無法和大眾產生連接,因為它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藝術理解是需要“門檻”的。但看實物好在你能看到他是怎么做的,而這種(沉浸展)就完全不行。(S15)
其次,他們對沉浸展覽接受效果的一個重要評價指標是策展人的專業水平。策展直接影響展覽的質量,是區分展覽“身臨其境”與“空洞虛假”的關鍵要素。對于質量不高的沉浸展覽,他們會一針見血地批判。比如:
如果這個策展人的水平比較高,應該是可以讓更多的人去走進他想展示的這位藝術家或這個藝術作品的。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我衡量一個沉浸式藝術展的標準吧,就是去觀察策展人的思路是什么。一切的聲光電、一切的新媒介、一切的文字,實際上都是幫助策展人去闡釋他看法的工具。(S11)
最后,他們也更在意藝術作品的“光暈”問題,認為在沉浸技術“加持”下的原作再現只是一種“炫技”行為,甚至有時候讓技術之于藝術品成了喧賓奪主的存在,這種本末倒置會讓人無法進入藝術家的具體語境之中。同時,他們也認為超真實的技術符號嚴重削弱了受眾的思考能力,這是由于當過分強調技術而忽視了本源時,人會深陷在對沉浸展覽的膚淺觀感中而無法思考。參看這段意見:
好的沉浸藝術展應當做到技術“隱形”,也就是說更多地注重以技術襯托藝術作品,而不是單單炫技。(它)還應該滿足觀眾的感官需求,而不是單調乏味。(它)也要注重審美,很多展覽粗制濫造,缺乏審美細節考量。比如說梵高的沉浸展覽,很多時候一張畫中間有斷層,然后“沉浸”下來就感覺很突兀。中間斷了一整塊,還不如傳統的畫作讓人身心愉悅,這樣的沉浸展覽就缺乏思考……現在沉浸藝術大多被資本操縱,觀眾沉迷在其中,失去了主觀能動性。(我)就是“打卡”吧,虛擬場景體驗更重要,藝術本身的意義和對內涵的批判性思考就顯得沒那么重要了。(S12)
在包含科技元素的沉浸展覽中,受眾通過藝術接受活動所獲得的認知,并不是關于現實原作的真實認知,而是由各種圖像與感官元素建構的超真實符號的認知;受眾所了解到的關于原作的“事實”也不過是被策展人加工過的、非真實的擬像。普通大眾對此可能更難分辨,但藝術專業人士能精準地把握展覽背后的傳播邏輯并開展批評活動。
(二)娛樂抑或娛樂至死
藝術接受活動自古以來就具有娛樂功能,人們通過藝術獲得精神上的紓解,“原始欲望的升華與宣泄產生了消除心理壓力的愉悅感”(27)楊春時、俞兆平、黃鳴奮:《文學概論》,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94頁。。與參加沉浸展覽的“療愈”動機相對應,沉浸展覽具有的娛樂效果也能幫受眾緩解日常的壓力。但是,伴隨著藝術接受活動“門檻”的逐漸下沉,原本需要專業素養才能品鑒的藝術品已經幻化成一張張門票式的消費符號。這導致受眾對沉浸展覽的消費變成了一種充斥著泛娛樂化性質的消費,“拍照打卡”成為看展過程中的一個固定環節,甚至一些質量不高的展覽已經沒有真正的藝術作品駐扎,只有五顏六色的“打卡”幕布在“吸睛”。(28)蔣肖斌:《拍照還是看展?沉浸式展覽讓你沉浸了嗎》,《中國青年報》2021年8月24日第9版。
對于沉浸展覽的泛娛樂化傾向,藝術專業人士和普通大眾中均有人注意到了,但二者的表現不盡相同。對前者而言,因為具有較高的鑒賞水平,因此很容易發覺這一“娛樂至死”的現象,從而批判泛娛樂化效應;而對后者來說,由于熱衷于“打卡拍照”,在展覽中尋求心理滿足,所以很容易沉淪于此。當“打卡”的意義超越“觀展”本身的意義時,就呼應了那句“我們將毀于我們熱愛的東西”(29)[美]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章艷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第2頁。。筆者訪談中的相關記錄如下:
很多不太用心的沉浸藝術展如同一個噱頭,背離了藝術的嚴肅性。比如說“網紅展”,雖然多有互動性和絢麗的場景布置,但是缺乏內涵,也就“打打卡”罷了,很容易淪為消費符號,背離藝術的初心。而且的確挺貴的,和內涵不成正比,就比如說梵高的沉浸展吧,因為是視聽投影藝術,所以沒有一個真跡,(但)還要130塊的門票。(S14)
我還挺喜歡的,因為沉浸式確實就是感受比較好,投入感會比較強,然后就是拍照,哈哈哈,美美地發“朋友圈”。(S8)
由此看來,我們既應當警惕沉浸藝術展的過度娛樂化趨勢,又有理由對其固有的娛樂功能給予支持。有受訪者表示:“在展覽中看到很多親子、情侶(組合),(它)非常適合大眾參與,愉悅身心”(S1);“比畫震撼的是,投影把作品放大很多倍!你可以觸摸它,感受它的色彩,(感到它)強烈傳達著梵高的(藝術)思想”(S4)。
(三)人與物的情感勾連
藝術品是作者的弗洛伊德式的夢境,本就有一定的理解“門檻”。但數字的賦能,使“精英”的藝術大眾化,讓更多的人能夠在沉浸中體驗作品內容,形成理解原作的情感紐帶。這種效果主要歸功于場景中各式的物(如裝置、造型、煙霧)與人的聯動。在這個層面,藝術專業人士與普通大眾基本達成了一個共識:只有在物的因素足夠令受眾“具身”的情況下,受眾才更有可能同作品產生情感聯結。這不僅是沉浸展質量高低的判別標準,也是受眾能否真正完成藝術接受的重要指標。
盡管受訪的藝術專業人士均對沉浸展覽進行了批評,但他們仍然肯定了質量上乘的沉浸展中那些積極的物的因素,并認為與場景的聯動能夠幫助他們實現藝術接受。例如:
空曠透明的玻璃幕墻和像花朵一樣的玻璃藝術結合在一起,讓你感覺萬物皆可生,不是只有花朵和陽光的結合才是最美的,玻璃好似也有了生命一般。(S13)
對普通大眾而言,他們能在足夠“沉浸”的場景中短暫地忘卻自身的社會角色,也有機會感同身受地理解作者的表達,進而實現高品質的藝術接受。例如:
在觀展的時候,也許其中一幅畫或一段背景音樂就會(讓我)產生共鳴。盡管開展的藝術家們國籍不同,但藝術帶來的美是相通的。我會忘記自己的社會角色,去體會作者想要表達出的情感,去感同身受。(S9)
“物”成為展覽中的積極因素之后,“人”的因素反而成了相對消極的部分。這主要體現在沉浸展覽的限流規定上,因為過多的觀眾會導致會場嘈雜,從而降低受眾的體驗質量。有受訪者表示:
房間里人多的時候也很影響體驗,小孩子也很多,吵吵鬧鬧的。(S7)
不能產生情感聯結,主要是人多導致了觀感很差。(S6)
由此可見,人與物共同構成了沉浸展覽的體驗效果空間。其中,物的因素是構成沉浸場景的基石,是能否觸發藝術接受的關鍵。但我們同樣要關注人的因素,如果客流問題解決得不好,展覽就更有可能淪為消費符號從而失去其內涵。
結 語
羅伯特·哈桑(Robert Hassan)曾說,“我們創造了工具,工具又反過來塑造我們”(30)[澳]羅伯特·哈桑:《注意力分散時代:高速網絡經濟中的閱讀、書寫與政治》,張寧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161頁。轉見曹璞、方惠:《“專注的養成”:量化自我與時間的媒介化管理實踐》,《國際新聞界》2022年第3期,第71-93頁。。在數字復制大行其道的消費社會時代,作為工具的沉浸技術形塑了沉浸展覽中藝術品的呈現方式。從以具身體驗為基本邏輯構造的沉浸場景中迸發的數字“光暈”,為受眾提供了與藝術品發生深度情感聯結的可能,提升了普通大眾式受眾的藝術接受水準。但另一方面,沉浸技術帶來的超真實表征與過度娛樂傾向,又會讓沉浸展覽落入“只能拍照打卡”的消費符號的窠臼。這一點已經被眾多藝術專業人士所警惕,因而沉浸技術并不一定能提升他們的藝術接受質量。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失衡,不僅會讓人跌入消費主義的陷阱,還會讓藝術陷入“內爆”的境地,徹底失去“光暈”。在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我們不妨以沉浸式的藝術展覽作為窗口,正視其影響,并對其可能產生的反面效果有所預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