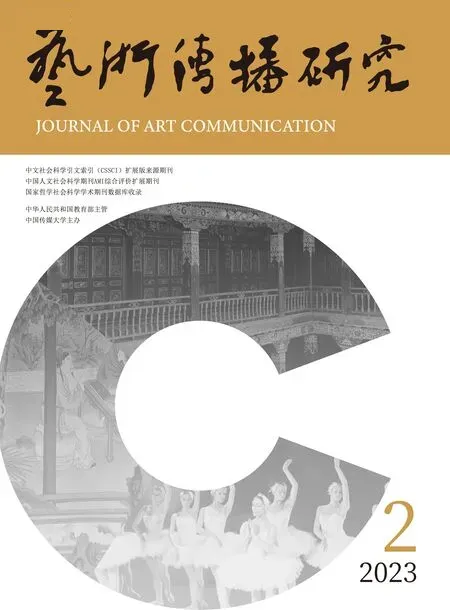早期中國現(xiàn)代性視野下的濮舜卿生平創(chuàng)作再考察
■ 張彩虹
濮舜卿在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的顯影,主要以其在戲劇界和電影界的創(chuàng)作實踐為勝。2013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創(chuàng)立“女性電影先驅(qū)者研究工程”(The Women Film Pioneers Project,WFPP),濮舜卿以編劇身份入選。(1)參見https://wfpp.columbia.edu/pioneer/pu-shunqing/。有關她的生平資料和研究論文,大抵反映了國內(nèi)外電影學界對這位中國電影的女性先驅(qū)的研究現(xiàn)狀。不過,這些成果數(shù)量不多,且鮮見從社會史、文化史角度展開的對其生平、創(chuàng)作演進軌跡的整體觀照。(2)國內(nèi)現(xiàn)有關于濮舜卿的研究為數(shù)不多,有代表性的是舒平的《第一個電影女編劇:濮舜卿》(《電影新作》1994年第5期)、左懷建的《女性視角與夏娃形象的改寫——讀濮舜卿劇作〈人間的樂園〉》(《名作欣賞》2008年第23期)、許航的《女性社會先鋒的影像表達——濮舜卿電影劇作中的社會性別意識》(《南開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2期),等等。縱觀濮舜卿1949年之前的生平與創(chuàng)作,不難發(fā)現(xiàn)其與早期中國現(xiàn)代性的“復合”與“多元”狀態(tài)的“同頻共振”。如果說“現(xiàn)代性一詞是一個內(nèi)涵繁復、聚訟不已的西方概念”(3)汪暉:《韋伯與中國的現(xiàn)代性問題》,載《汪暉自選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頁。,那么早期中國現(xiàn)代性更是一個寓意豐富并正在不斷衍生發(fā)展的復雜課題。有別于西方現(xiàn)代性在啟蒙現(xiàn)代性和審美現(xiàn)代性之間構(gòu)成的自反性張力,早期中國現(xiàn)代性以啟蒙現(xiàn)代性為主調(diào),以反帝反封建、追求個性解放和民族獨立為旨歸,呈現(xiàn)出“復合現(xiàn)代性”和“多元現(xiàn)代性”的“混沌”狀態(tài)。(4)早期中國現(xiàn)代性的“復合”性與“多元”性研究,參見張振波、金太軍:《復合現(xiàn)代性:中國現(xiàn)代性范式及其政治秩序圖景》,《文史哲》2020年第3期;馮平、汪行福、王金林、孫向晨、徐洪興、鄧安慶:《“復雜現(xiàn)代性”框架下的核心價值建構(gòu)》,《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7期;汪行福:《復雜現(xiàn)代性與思想再解放》,《學術界》2015年第10期;汪行福:《復雜現(xiàn)代性與現(xiàn)代社會秩序重構(gòu)》,《探索與爭鳴》2014年第6期;方朝暉:《多元現(xiàn)代性研究及其意義》,《馬克思主義與現(xiàn)實》2009年第5期;等等。其總體狀態(tài)表現(xiàn)為:“在共時性結(jié)構(gòu)上始終存在著前現(xiàn)代性、啟蒙現(xiàn)代性與審美現(xiàn)代性的多元對抗。在歷時性結(jié)構(gòu)上,現(xiàn)代文學思潮之嬗變也似乎呈現(xiàn)為非線性的‘流動的現(xiàn)代性’(齊格蒙特·鮑曼語)。但這種對抗與流動卻是非邏輯的混雜,沒有一種要素能夠根深葉茂,取得真正的優(yōu)勢。”(5)張光芒:《混沌的現(xiàn)代性——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思潮總體特征的一種解讀》,《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2004年第3期。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共中央加強對文化運動的領導,引發(fā)革命文藝、普羅文藝熱潮,直接推動了30年代左翼文化運動的崛起。與此同時,抵抗日本侵略、民族救亡圖存的時代背景也使“革命”現(xiàn)代性取代“啟蒙”現(xiàn)代性,成為30至40年代中國現(xiàn)代性的主流話語。在此背景下,濮舜卿的思想及創(chuàng)作與早期中國社會現(xiàn)代化過程相對應——從“教育啟蒙”“戲劇、電影啟蒙”到“法政啟蒙”的“娜拉三態(tài)”觀照了有關現(xiàn)代性的思辨在不同階段的主題轉(zhuǎn)化,呈現(xiàn)出“混沌”狀態(tài)的鏡像式存在。
一、始于現(xiàn)代教育的啟蒙現(xiàn)代性之路

1924年,《婦女雜志》第10卷第3號刊發(fā)了中國共產(chǎn)黨早期女革命家向警予的《中等以上女學生的讀書問題》一文,呼吁為拓展女子職業(yè)發(fā)展,應開辦女子高等教育。而濮舜卿在1923年即已考入東南大學的預科,1927年3月畢業(yè)于該校的政治經(jīng)濟系。該校和1919年創(chuàng)辦的燕京大學同是國內(nèi)最早實現(xiàn)男女同招的大學,其教員隊伍中既有畢業(yè)于日本早稻田大學和美國哈佛大學的政治經(jīng)濟系主任王伯秋,也有詞曲學大家吳梅等國學大師,可謂學風開放、兼容并蓄。(10)東南大學編印《國立東南大學一覽》,1923年,第75-78頁。在這樣的校園氛圍里,濮舜卿雖主修政法專業(yè),卻對詩詞、戲劇情有獨鐘,是吳梅主持的該校學生社團——“潛社”的主要成員之一。(11)王季思:《憶潛社》,載王為民編《吳梅和他的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3頁。“潛社”成立于1924年春,寄寓吳梅“希望遠離政治漩渦,潛心學習之意”(12)徐燕婷:《吳梅詞學教育新范式與潛社女詞人的詞學活動》,《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2期。。然而,就濮舜卿而言,以法政護航、以藝術熏陶性靈并開啟民智才是興趣所在。在校園戲劇活動中,她和教育專修科的侯曜相識、相戀,一起創(chuàng)辦了東南劇社,聯(lián)袂出演了侯曜的劇本《山河淚》(1925),成為繼留日女作家白薇、北平女子高等師范附小教員吳瑞燕之后又一位接受過高等教育并登臺表演的知識女性。侯曜對由教育轉(zhuǎn)向戲劇的初衷的剖白,也代表了她的心聲:“我……喜歡研究戲劇,以為戲劇教育民眾,感化民眾的力量比任何事業(yè)來得大。”(13)侯曜:《悲歡離合的生活》,《和平之神特刊》,1926年。早期中國社會的現(xiàn)代化進程亟待以啟蒙理性革除封建積弊,喚起大眾的個體解放意識,推動民族國家走向新生。這是激發(fā)濮舜卿以詩詞、戲劇為媒介,拓展啟蒙現(xiàn)代性對現(xiàn)實的影響力的外在動因。
濮舜卿的現(xiàn)代教育和戲劇啟蒙之路,也是挪威戲劇家易卜生(Henrik Ibsen)的社會問題劇《玩偶之家》進入中國后引發(fā)的“出走的娜拉”社會寓言的時代鏡像。該劇于1907年進入中國,劇中追求人格獨立的新女性“娜拉”的形象對早期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1918年《新青年》雜志出版的“易卜生專號”,引出了胡適、田漢、丁西林、歐陽予倩、郭沫若等新文化運動中的代表性作家一系列反對封建包辦婚姻、倡導戀愛自由的劇作。然而,囿于性別差異,男性作家對封建倫理壓制下的女性痛苦很難有切近的“具身”體驗,所以難免或多或少地呈現(xiàn)出一種居高臨下的“啟蒙”或“救贖”姿態(tài)。因此,“盡管胡、陸、田、丁等男性作家重構(gòu)了易卜生的戲劇模式,倡導女性解放,但他們關于性別和女性身份的觀點卻受到一種自我參照的立場限制,即男性和女性都作為公民肩負著國家改革的共同責任。這種往往以男性為導向的‘改革婦女’的話語并沒有充分考慮婦女自身的作用,以回應她們的社會和歷史使命”(14)Li Guo,“Rethinking Theatrical Images of the New Woman in China’s Republican Era”,CLCWeb: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15,no.2(2013).。1926年《婦女雜志》第11卷第6號上刊發(fā)的宋淑貞的文章《期望女文學家的崛起》表示,“文學是以情感為主的,而女子心思幽靜,富于感情,自然與文學最為相宜”;與男子讀書多為博取功名不同,“女子是多數(shù)賦性純潔,不易沾染社會的惡習,發(fā)露其天賦之靈思美感,研究文學,比較很易成功”。(15)宋淑貞:《期望女文學家的崛起》,《婦女雜志(上海)》1926年第12卷第6期。當然,女性寫作能力的提升有賴于現(xiàn)代教育的普及。有統(tǒng)計稱,截至1930年,全國受過初等教育的女性為1653016人,其中受過中等教育的女性有90386人,受過大學和專修學校等高等教育的只有3283人,占同期男性的10.81%,而出國留學者更是格外稀少,截至1931年僅為227人,不到留學總?cè)藬?shù)的1/8。(16)嘯云:《現(xiàn)階段女子教育的問題檢討》,《婦女生活》1936年第2卷第5期。即便是有幸接受現(xiàn)代教育的女性,在封建意識濃厚的家庭和社會環(huán)境中,其走向獨立自主之路依然困難重重。不過,濮舜卿在性格志趣上的爽朗瀟灑,決定了她的戲劇、電影創(chuàng)作不會拘泥于同時代女作家作品中常見的那種猶豫、彷徨、感傷的自敘色彩,而是更富有積極樂觀的理想主義傾向。1927年,她在《婦女雜志》上發(fā)表《易卜生與史德林堡之婦女觀》一文,指出《玩偶之家》敲響了“婦女解放的警鐘”,相較于“莎翁的婦女是能支配一切,造福一切的幸運之神”,易卜生對婦女的“同情的態(tài)度和鼓勵的態(tài)度”才是最可取的。(17)濮舜卿:《易卜生與史德林堡之婦女觀》,《婦女雜志(上海)》1927年第13卷第9期。因此,濮舜卿的戲劇創(chuàng)作也多著眼于以“智慧”(知識)開啟女性心智,鼓舞女性自強、自立的反抗精神,她也由此自覺踐行了以現(xiàn)代教育喚起民族意識更新的啟蒙之路。
二、影、戲雙棲:啟蒙現(xiàn)代性的媒介先行者
“現(xiàn)代性的歷史就是社會存在與其文化之間緊張的歷史。現(xiàn)代存在迫使它的文化站在自己的對立面。這種不和諧恰恰正是現(xiàn)代性所需要的和諧。”(18)周憲:《現(xiàn)代性的張力——現(xiàn)代主義的一種解讀》,載金元浦編《多元對話時代的文藝學建設》,軍事誼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頁。有別于西方現(xiàn)代性在啟蒙現(xiàn)代性和審美現(xiàn)代性之間的自反結(jié)構(gòu),源于“五四”和新文化運動的早期中國現(xiàn)代性主要以啟蒙現(xiàn)代性為核心,將小說、戲劇的改良視為在社會上推廣和普及啟蒙現(xiàn)代性的一種媒介工具。濮舜卿的戲劇和電影生涯集中在1924—1929年。相對于具有傳統(tǒng)優(yōu)勢的戲劇,當時的精英知識分子對電影這種新興娛樂媒介的接納程度并不高,電影從業(yè)者的社會地位也比較低下,不被傳統(tǒng)文化界認可和接納。對此,從美國學習戲劇歸來并于1925年創(chuàng)作了中國電影史上第一部標準化電影劇本《申屠氏》的洪深感慨道:“我有兩個觀念,第一,我以為做影戲,是正當職業(yè),在電影界勞心勞力混口飯吃,也同人力車夫。跑了一身大汗,賺兩角小洋車錢一般,不是什么可恥的事。第二,凡是道德人格的名譽,乃是個人的事,與職業(yè)沒有多大關系的,……不過不幸社會對于電影界,格外的苛求,格外的注意罷了。”(19)洪深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戲劇集(影印本)》,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87-88頁。同一時期,美國電影界倒是已經(jīng)出現(xiàn)大量寫作電影腳本的“腳本女孩”(script girls)。她們多為白人中產(chǎn)家庭主婦,還不乏曾為雜志撰稿的女作者。她們在公開投稿或?qū)懽鞅荣愔袆俪?為默片撰寫幾行、一段或一頁的情節(jié)大綱,賺取稿酬以提升在家庭和社會生活中的身份與地位。(20)See William K.Everson,American Silent Film(New York:DaCapo Press,1998),p.32;and Tom Stempel,Framework:A History of Screenwriting in American Film(New York:Continuum,1988),pp.10-14.這種類似兼職的工作深受女性喜愛,因為它既不妨礙女性承擔家庭義務,又能“追求更多創(chuàng)造性體驗”(21)Martin F.Norden,“Women in the Early Film Industry”,Wide Angle 6,no.3(1984):64.See Anne Morey,Hollywood Outsiders:The Adaptation of the Film Industry,1913-1934(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3):48-49.,并且較容易獲得,畢竟“很少有人認真對待這個新行業(yè),所以大門向女性敞開”(22)Cari Beauchamp,“Frances Marion:‘Writing on the Sand With the Wind Blowing’,”Creative Screenwriting 1,no.3(Fall,1994):56.。美國最早的有記錄可考的電影女編劇是卡萊姆制作公司的演員兼作家吉恩·岡蒂耶(Gene Gauntier),她從1907年就開始寫“粗糙的”劇本——“一首詩、一幅畫、一個短篇故事、當前戲劇中的一個場景、報紙上的一個標題”(23)Gene Gauntier,“Blazing the Trail,” Woman’s Home Companion LV,10 (Oct,1928):183.。到了20世紀20年代,大約50%的好萊塢電影劇本是由女編劇撰寫的。(24)Wendy Holliday,“Hollywood’s Modern Women:Screenwriting,Work Culture,and Feminism,1910-1940”(PhD.diss.,New York University,1995),p.100,114,140(note 49),144(note 82).然而,同樣因為性別歧視,大部分女編劇都只能以匿名形式發(fā)表她們的作品,電影文學的概念也是遲至40年代才在好萊塢確立。(25)邵牧君:《電影、文學和電影文學》,《文學評論》1984年第1期。相較而言,中國電影文學的地位確立要更晚一些,像1935年趙家璧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就收錄有小說、詩歌、散文和戲劇,卻未包含電影劇本。因此,對濮舜卿來說,與大洋彼岸的女性先驅(qū)者一樣,投身電影業(yè)著實需要一番對抗流俗、跨越媒介、挑戰(zhàn)自我的見識與勇氣。
1924年,濮舜卿隨侯曜加入由留美學生梅雪儔等人創(chuàng)辦的長城畫片公司,該公司前期出品的多為侯曜編導的“移風易俗、針砭社會”的社會問題劇。1925年,該公司拍攝了根據(jù)濮舜卿劇本改編的同名電影《愛神的玩偶》,并在《申報》上連續(xù)刊登推廣消息,稱這部影片“為東南大學女學生濮舜卿所編,劇旨高尚,劇情曲折,對于現(xiàn)在的婚姻問題多所討論”(26)《游藝消息》,《申報》1925年9月28日第14版;《長城新片〈愛神的玩偶〉告成》,《申報》1925年10月19日第3版;《游藝消息》,《申報》1925年10月22日第20版。。該片的主人公是小學教員明國英和“醒華大學”學生羅人俊,兩人的自由戀愛被封建家庭阻撓,所以熱切向往著“到新社會去找新生活”。濮舜卿在該片的“本事”中寫道:“他們是有志的青年,終歸是不肯做愛神的玩偶的。”(27)濮舜卿:《愛神的玩偶》,載鄭培為、劉桂清編選《中國無聲電影劇本》(上),中國電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271頁。這份對沖破封建家庭阻力的自信,充滿了青年人特有的天真與浪漫。與同期的好萊塢女編劇熱衷描寫女主人公在兩性關系中的主動性與掌控力,以及對刺激的冒險生活的向往等審美現(xiàn)代性表達不同,濮舜卿以啟蒙主義為出發(fā)點,著力于對封建意識的批判。當然,《愛神的玩偶》在寫作格式上與《申屠氏》相比也顯稚拙,作為中國電影史上第一部由女性寫作的劇本,其歷史意義主要體現(xiàn)在對電影文學的性別突破上。
除了編劇創(chuàng)作,濮舜卿還勇于嘗試表演工作,她在侯曜執(zhí)導的電影《棄婦》中飾演了追求婦女解放的侍女采蘭。1926年,長城公司因經(jīng)營不善,轉(zhuǎn)向當時流行的古裝片路線。因旨趣相悖,婚后的濮舜卿和丈夫侯曜轉(zhuǎn)入新成立的民新影片公司,她也成為該公司主創(chuàng)人員中唯一的女性。濮舜卿全程參與了侯曜導演的反對封建壓迫、提倡戀愛自由的《西廂記》,還與侯曜聯(lián)合導演了《木蘭從軍》,(28)《劇場消息》,《申報》1927年6月6日第2版。跟隨攝制隊在沙漠中經(jīng)受了“席地而臥”“腹饑如鼓”的惡劣條件,順利完成了“黑山”外景戲的拍攝任務。(29)濮舜卿:《在沙漠過年之民新攝影隊》,《電影月報》1928年第1期。濮舜卿的電影小說也被改編為反戰(zhàn)題材影片《戰(zhàn)地情天》,于1928年拍竣。(30)濮舜卿:《戰(zhàn)地情天》,《電影月報》1928年第5期。濮舜卿在民新影片公司身兼數(shù)職,既擔任編劇部主任,(31)《劇場消息·民新影片公司攝制蔡公時影片》,《申報》1928年6月30日第6版。又擔任導演、剪輯、制片工作,當時的同業(yè)女性中無出其右者。1927年,上海電影界成立攝片助餉會,下設執(zhí)行、導演、編劇等7個分委員會,濮舜卿是其中唯一的女性成員。(32)《上海電影界攝片助餉會成立大會》,《申報》1927年7月7日第15版。20世紀20年代,即使是好萊塢的女編劇們,也必須在社會空間和私人生活之間保持脆弱平衡:一方面,她們筆下的女性人物越來越具有現(xiàn)代感和掌控欲;另一方面,她們自己卻要在媒介中刻意打造具有“女人味”的、“沒有女性主義的野心”的、“在寫作的同時安于做一個賢妻良母”的傳統(tǒng)女性形象。與此同時,她們還不得不忍受性別歧視導致的同工不同酬。(33)Aline Carter,“The Muse of the Reel,”Motion Picture Magazine XXI,no.2(March,1921):62,105.因此,可以料想,身處當時封建意識濃厚的中國社會的濮舜卿,也必須付出更多的勇氣和努力,才能在早期中國電影業(yè)參與多種職業(yè)身份的實踐,并獲得上海電影界對她能力和地位的肯定。
隨著閱歷的增加,濮舜卿對社會事務的關注不斷加深,創(chuàng)作選材也隨之在女性解放、婚姻自主類的議題之上加入了更為寬泛的社會時政問題。早在1926年,她創(chuàng)作的劇本《芙蓉淚》就已獲得“中華國民拒毒會”電影劇本征文比賽的甲項獎。(34)《拒毒會電影征求昨日揭曉》,《申報》1926年7月18日第15版。1927年,她的文章《她的新生命》獲得該年“全國女青年協(xié)會編劇部”舉辦的評獎征文活動第二名。(35)《女青年協(xié)會懸獎征文揭曉》,《申報》1927年9月7日第15版。同時,她還保持著戲劇創(chuàng)作的熱情。1927年,在獨幕話劇《黎明》中,她以象征主義手法講述了一個反對社會壓迫的寓言故事:生活于平靜鄉(xiāng)村的夫婦在城市中遭遇了“金錢”“道德”和“輿論”等一眾惡魔的誘惑。這些惡魔象征著城市生活中的各種欲望,而劇中的妻子在“智慧”女神的鼓勵下,產(chǎn)生了強大的反抗力量。1931年,該劇在天津公演,濮舜卿親自出演了“智慧”女神一角。(36)參見《天津商報畫刊》1931年第3卷第8期。1928年,濮舜卿又以“濟南慘案”為原型撰寫了激發(fā)民眾抗日愛國熱情的電影劇本《蔡公時》。(37)《劇場消息·民新影片公司攝制蔡公時影片》,《申報》1928年6月30日第6版。遺憾的是,上述戲劇和電影劇本大都沒有獲得巡回演出或投拍的機會,這主要與彼時商業(yè)電影公司追拍粗制濫造、逃避現(xiàn)實的古裝片和武俠神怪片,商業(yè)戲劇界也比較浮躁有關。濮舜卿把戲劇、電影當作啟蒙現(xiàn)代性的媒介利器,喚起民眾關注日益深重的民族生存危機的初衷由此也并未充分實現(xiàn)。
1933年,濮舜卿的劇本集《人間的樂園》作為“文學研究會通俗戲劇叢書”第七種,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書中收錄了她的四幕劇本《人間的樂園》(年份不詳)、三幕劇本《愛神的玩偶》(1925)和獨幕劇《黎明》。1935年,《人間的樂園》又被收入洪深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戲劇集》中,是該卷18個劇本中唯一的女性作品。1936年,該劇再度被收入由俊生主編,由商務印書館和上海仿古出版社出版發(fā)行的《現(xiàn)代女作家戲劇選》。一系列的收錄,說明濮舜卿以劇作家的身份獲得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界的認可。《人間的樂園》作為濮舜卿的戲劇代表作,繼續(xù)以象征主義手法聚焦女性解放的主題。“智慧”女神激勵“亞當”和“夏娃”把“天國”的美麗花園建設到人間:“你們是人,要去做人所應做的事,過人所應過的生活,何必定要讬(托)庇神力呢?”(38)濮舜卿:《人間的樂園》,洪深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戲劇集(影印本)》,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285頁。她稱贊夏娃為“最有膽氣的女子”“將要被推為女權運動的始祖”,(39)同上書,第286頁。并敬告女性說:“你們不要怕自己能力薄弱,只要有決心,有毅力,什么偉大的事業(yè),都可以成就!”她同時也不忘勉勵男子們,要盡自己的責任,“和女子合作”(40)濮舜卿:《人間的樂園》,洪深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戲劇集(影印本)》,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292頁。。對控制人類思想的“上帝”,“智慧”說:“若是你們不信有上帝,上帝就會消滅的。”(41)同上書,第294頁。關于濮舜卿以象征主義手法行理想主義之實的戲劇風格,洪深批評說,“可以代表那時期的學生劇——就是學生們寫了在學校里演的戲劇”,其特點“就是說教的意味太重,而事實太近于空想了”(42)同上書,第70頁。。確實,因為“實地的觀察和生活的經(jīng)驗”(43)同上書,第11頁。的不足,濮舜卿的劇本多采用《圣經(jīng)》元素,童話、寓言的痕跡明顯,內(nèi)容略顯清淺稚拙,而這也是“五四”之后一批女性劇作家作品的共性,這些作品在西方現(xiàn)代戲劇流派的影響下,“尚未深化為對其深層的戲劇審美意識的共鳴”,更多是一種“探索、模仿、嘗試”。(44)陳方:《中國早期女作家戲劇創(chuàng)作論》,《戲劇藝術》1994年第3期。然而瑕不掩瑜,濮舜卿1925—1929年間的戲劇、電影創(chuàng)作,在戲劇和電影文學領域確立和推進了女性話語權,在全球電影先驅(qū)者群體中為東方女性實現(xiàn)了“顯影”,為處于“五四”啟蒙現(xiàn)代性中的媒介革命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三、“法政”啟蒙:對“革命”現(xiàn)代性的探索及其局限
1930年之后,濮舜卿逐漸淡出電影圈,開始執(zhí)業(yè)律師生涯。這一由藝術啟蒙到法政啟蒙的路徑轉(zhuǎn)換,可以看作中國現(xiàn)代性于20世紀30年代早期轉(zhuǎn)向的一種反映。彼時,中國社會的內(nèi)外危機日益加深,各種保守、復古思潮沉渣泛起,繼續(xù)革命則成為左翼思潮的旗幟,“成為一種代表歷史發(fā)展方向的普遍意識,成為推動歷史發(fā)展的‘火車頭’”(45)陳建華:《“革命”的現(xiàn)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165頁。值得指出的是,自20世紀20年代起,媒介中高頻出現(xiàn)的“革命”,其內(nèi)涵同樣存在著“多元”指向。夏中義認為,現(xiàn)代中國革命觀起源于戊戌變法失敗后,具有“三維二元”特征:“三維”指“革命”一詞既是對中國語境的古義翻新,又是借助日文中介,對英文單詞revolution的對應性意譯;“二元”則指“革命”在上古漢語中就有維新改良的“堯舜革命”和暴力顛覆的“湯武革命”的雙重意涵。只不過近代以來,受法國大革命影響,中國語境中“革命”的二元指向漸漸朝向革舊鼎新的一元面向發(fā)展。(夏中義:《“革命”探源啟示錄——評陳建華的〈“革命”的現(xiàn)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文藝研究》2003年第6期。)。1930年3月2日,“左聯(lián)”在上海成立,魯迅在演講《對于左翼作家聯(lián)盟的意見》中指出,“對于舊社會和舊勢力的斗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同時他也認為“戰(zhàn)線應擴大”,“應當造出大群的新的戰(zhàn)士”。(46)魯迅:《對于左翼作家聯(lián)盟的意見》,《萌芽月刊》1930年第1卷第4期。“左聯(lián)”的成立拉開了激進的左翼文化運動的序幕。與此同時,提倡以漸進方式推動制度改良的右翼“革命”理念也在滋生。濮舜卿顯然更傾向于后者。早在1928年,她就在《革命軍海陸空大戰(zhàn)記》一文中對北伐戰(zhàn)爭的勝利表達了欣喜之情,并誤將民族國家振興的希望寄托其中。(47)濮舜卿:《革命軍海陸空大戰(zhàn)記》,《電影月報》1928年第8期。1929年,以羅明佑、黎民偉為代表的民族資本家創(chuàng)辦聯(lián)華影業(yè)公司,發(fā)起“復興國片、改造國片”運動,力圖以“聯(lián)華新片”打破商業(yè)電影粗制濫造、無序競爭的混亂局面。濮舜卿和侯曜也參與創(chuàng)辦了“聯(lián)華”在北平的“電影人才養(yǎng)成所”,并拍攝了《故宮新怨》一片。然而,在動蕩的時局和混亂的思潮中,以戲劇和電影為媒介貫徹啟蒙理性的現(xiàn)代性追求,不可避免地要遭遇挫折。基于上述背景,濮舜卿選擇回歸法政專業(yè),謀求以法政啟蒙和制度改良繼續(xù)推動婦女解放與社會進步。
1931年,濮舜卿加入天津律師公會,開始在平津兩地執(zhí)業(yè)。(48)《律師公會改選結(jié)果》,《益世報》1931年9月21日第6版。回顧20世紀初葉,中國女性的法律從業(yè)自然也有一個曲折的歷程。1912年,上海女子法政學堂成立,然而同年北洋政府卻仿照日本公布實施了《律師暫行章程》,不允許女性從事律師職業(yè)。1920年,宋美齡在南京創(chuàng)辦女子法政講習所。(49)銅雀:《宋美齡創(chuàng)辦女子法政講習所》,《福爾摩斯》1929年5月14日。同年,上海出現(xiàn)了第一位女律師——美國人海倫·麥考利夫人(Helen Leary)。1926年,出身廣東政商世家、留學法國獲法學博士學位的鄭毓秀女士,以法國律師牌照在上海的租界區(qū)掛牌執(zhí)業(yè)。1927年7月23日,《律師章程》修訂版終于發(fā)布,女性獲得了和男子同等的法律執(zhí)業(yè)資格,然而女律師依然鳳毛麟角。1939年,上海律師公會會員名錄中共有1204人,其中女律師53人,僅占4.4%。至1948年,女律師緩慢增加至70人,在1178人的總數(shù)中占6%。(50)陳同:《近代社會變遷中的上海律師》,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頁。作為一種新生事物,女律師很容易引發(fā)社會關注,比如1927年,天一公司就推出了由胡蝶主演、以莎士比亞名劇《威尼斯商人》為藍本大幅改編的電影《女律師》。同時,真實的女律師也很容易成為與電影女明星一樣的話題人物,被各種娛樂小報作為談資。
濮舜卿的執(zhí)業(yè)足跡遍及津滬之間,“平津一帶一人而已,委辦案件婦女為多,是法律家也是文學家”(51)心冷:《女律師濮舜卿訪問記》,《大公報(天津)》1932年4月30日第7版。。此時的她驚覺道:“以前理想,覺得現(xiàn)代中國的婦女,多半處在黑暗悲慘的境地。誰知執(zhí)行律務以后,承辦不少痛苦婦女受人欺壓虐待的案件,才知以前的理想,只是百分之一的比例,以后愿以法律的能力保障女權……”(52)同上。她代理的陳旭芙訴寧夏軍閥馬鴻逵解除婚約案,在《大公報(天津)》連續(xù)五天刊載啟事。(53)《律師濮舜卿女士代表陳旭芙女士聲明否認婚約并與家庭脫離關系》,《大公報(天津)》1932年2月17-21日第1版。1933—1934年,她又在天津《益世報》上以18期連載的《婦女應有的法律常識》,進行系列普法宣傳。1934年,她將自己的律師事務所由天津遷往上海,次年加入上海律師公會。(54)《最近遷滬執(zhí)業(yè)之女律師濮舜卿女士在其津辦公室留影》,《天津商報畫刊》1934年第11卷第29期。隨后,她在《申報》副刊《婦女園地》設專欄答復讀者的法律問題,并擔任進步女性雜志《婦女生活》的法律顧問。《婦女生活》雜志創(chuàng)辦于1935年7月,其主編沈茲九后來于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這本雜志多刊發(fā)鼓勵婦女解放并積極參與抗戰(zhàn)救國的文章。例如,其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了著名報人金仲華的文章《給現(xiàn)階段的中國婦女》,指出五四新文化運動已經(jīng)過去十幾年了,婦女解放運動進入停滯狀態(tài),上層社會婦女滿足于“班克赫斯脫”(55)埃米琳·班克赫斯脫(Emmeline Pankhurst,1858—1928),又譯埃米琳·潘克赫斯特,英國婦女參政權運動的奠基者之一。她出生于曼徹斯特具有激進主義傳統(tǒng)的中產(chǎn)家庭,與律師出身的丈夫理查德·潘克赫斯特(Richard Pankhurst,1838—1898)同為社會主義者。1903年,她建立了“婦女社會與政治聯(lián)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主張以暴力手段推動男女政治平權,該組織的口號是“給我們死,或者讓我們獲得所要求的”。但一戰(zhàn)爆發(fā)后,她開始與政府合作,號召女性廣泛參與生產(chǎn)勞動,彌補因男性參戰(zhàn)而導致的勞工不足。1918年,英國議會通過《全民代表法案》,規(guī)定年滿30歲的女性擁有投票權。1928年,在她去世前一個月,英國女性獲得選舉權年齡下降到21歲,與男子相同。式的、脫離現(xiàn)實的政治點綴作用,因此“現(xiàn)階段的中國婦女運動才是最最值得注意的”(56)金仲華:《給現(xiàn)階段的中國婦女》,《婦女生活》1935年創(chuàng)刊號。。該刊第2期登載的《法律與我們》一文,更談到雜志聘用法律顧問的初衷,在于喚起女性運用法律保護自己的權益,并指出:“人與人之間真正得到了平等的國家,自然他們制造出來的法律,才是真正平等的。”(57)《法律與我們》,《婦女生活》1935年第1卷第2期。
濮舜卿在當執(zhí)業(yè)律師的同時,還熱心于社會政治活動,比如積極參與由李璜組織的地下活動,從天津的租界購買彈藥,秘密運抵東北抗日前線。李璜回憶道:“……幸得一個廣東同志侯東明(即侯曜),他的國語說得很好,而他是電影導演,常往來平津,攝取鏡頭,無人不知他是戲劇界中人,他的太太濮舜卿也是同志,同他一道活動。我與他夫婦商量運輸?shù)氖?難得他倆對這危險工作,一口承認(即答應)……”(58)李璜:《學鈍室回憶錄》,(中國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第182頁。由此可見,濮舜卿有著一般知識女性所不能及的才略和膽識。然而,時局弄人,這對世人眼中志同道合、家庭美滿的賢伉儷卻因動蕩時局而分離。(59)有關侯曜與濮舜卿幸福家庭生活的報道,見《侯曜先生與濮舜卿女士伉儷合影》,《天津商報畫刊》1931年第2卷第38期;《在他爸爸導演下之姿態(tài)(名導演家侯曜君之愛女)》,《天津商報畫刊》1931年第3卷第44期;慕維通:《侯曜妻,濮舜卿業(yè)律師:夫唱婦隨,藝術家生活羨煞天下人》,《開麥拉》1932年第84期。1933年,華北局勢日益緊張,侯曜不得不南下香港避難。1938年左右,侯曜與身兼入室弟子和秘書的編劇、導演尹海靈結(jié)成伴侶,直至1942年被日軍殺害于新加坡。(60)羅卡:《侯曜:傳奇的審視和重構(gòu)》,載香港電影資料館編《香港早期電影游蹤第二冊·電影先驅(qū)侯曜》,香港電影資料館2014年版,第21-39頁。這段情況在抗戰(zhàn)勝利后被發(fā)表在上海《東南風》雜志的《女律師濮舜卿》一文中,此文還將侯的遭遇描述為他拋棄故鄉(xiāng)妻室的“報應”。(61)友孫:《女律師濮舜卿》,《東南風》1946年第4期。文章認為濮舜卿與侯曜在東南大學相識時,侯曜在廣東老家已有妻室。1924年,侯曜加入長城公司編劇(導)《棄婦》乃是因為“侯濮相愛以后,侯曜便把鄉(xiāng)間的妻子遺棄了”。1933年,兩人因“家庭細故”仳離,侯曜只身南下,與尹海靈結(jié)成伴侶,“又表演其棄婦事實,將濮舜卿遺棄于天津”。迷信固不足取,人物可待全面評價。
家國離亂下的個人生活變故,使濮舜卿以法律意識喚起女性群體自我保護能力的意愿更為迫切。1935年,她在《女青年月刊》上發(fā)表《婦女與法律知識》一文,指出在“兩性”和“金錢”問題上,法律可以“保護個人的生存,比較積極而有力量”,還指出當時坊間熱議的電影明星阮玲玉“殉訟”悲劇就是阮玲玉缺少法律知識造成的。(62)濮舜卿:《婦女與法律知識》,《女青年月刊》1935年第14卷第6期。
抗戰(zhàn)勝利后,國家面臨著從戰(zhàn)爭泥淖中重建的契機,濮舜卿開始為男女平權謀求法律和制度保障而奔走呼號,并參選南京市參議員。(63)李忠峰:《濮舜卿:一位南京市參議員競選人,誰知她是一位女話劇作家》,《婦女月刊》1946年第5卷第2期。同時,她還主編了《上海婦女》雜志,一如既往地關注婦女問題。1947年,她針對日本侵略導致的家庭離散、女性慘遭離棄的社會問題,尖銳地指出婦女以法律為武器保護自身權益的重要性,并認為“五四運動之后,易卜生《娜拉》(即《玩偶之家》)一劇介紹到中國來之后,不但騷動了整個的文壇,也震蕩了中國法律界的心靈”(64)濮舜卿:《戰(zhàn)后離婚問題的面面觀》,《婦女文化》1947年第2卷第3期。。她的觀點呼應了昆侖影業(yè)公司同年拍攝的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的批判現(xiàn)實主義主題,然而“出走的娜拉”的社會問題,經(jīng)過30多年的時光流逝,并沒有得到真正解決。這一年,濮舜卿以婦女組織候選人身份參選南京市國民代表大會代表,止步于“婦女團體”候補人選。(65)《南京國代選舉選票結(jié)果公布》,《申報》1947年12月3日第2版。民國時期,女性參政不免被人譏諷為政治點綴品;戰(zhàn)后國民黨政權的深度腐朽與信用崩塌,更使偏向理想主義的濮舜卿很難實現(xiàn)抱負。這同時也說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沒有得到根本改造的前提下,寄希望于以法律啟蒙推動社會制度局部改良的右翼的“革命”現(xiàn)代性道路是走不通的。
濮舜卿在20世紀10—40年代的“娜拉三態(tài)”,對應著齊美爾關于現(xiàn)代社會中“人是天生的越境者”的論斷,充分體現(xiàn)了“五四”知識女性的內(nèi)在生命力對超越固化時空限制、不斷突破邊界束縛的渴望,以及探索民族國家現(xiàn)代化之路的各種努力與嘗試。本文對濮舜卿的再考察,涉及她以現(xiàn)代教育啟蒙激發(fā)女性關于獨立自強的初步認知,以戲劇和電影等媒介啟蒙大眾并改造社會風尚,以理想主義的法政啟蒙改良社會制度的經(jīng)歷,力圖還原她相對完整的個體精神譜系以及她與早期中國現(xiàn)代性的那種“復合”與“多元”的“混沌”狀態(tài)之間的對應關系。希望通過對這位先鋒女性的個體生命的解讀,能夠進一步幫助我們回顧和反思早期中國社會現(xiàn)代化進程中有關現(xiàn)代性的思辨、論爭及其文化癥候,以鉤沉歷史去燭照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