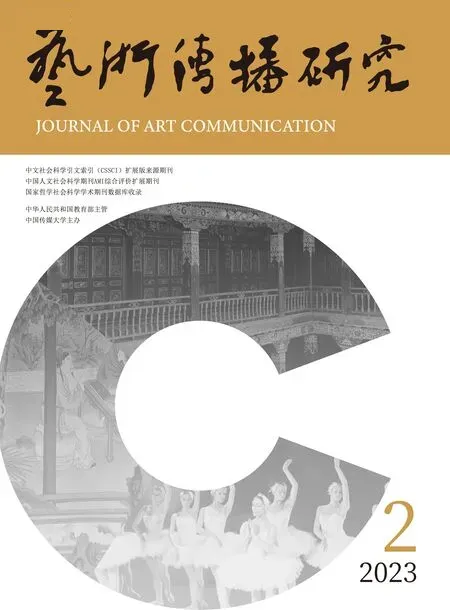心性現(xiàn)實主義的主體間性構型
——以近十年中國電視劇人物性格塑造為例
■ 王一川
歷史的實踐經(jīng)驗和理論認知告訴我們,中國文藝(或藝術)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策略之一,在于繼續(xù)堅持和深入拓展現(xiàn)實主義精神傳統(tǒng)。現(xiàn)實主義(或?qū)憣嵵髁x),是陳獨秀于1915年在創(chuàng)辦于上海的《青年雜志》中發(fā)表的文章《今日之教育方針》(載第一卷第二號)和《現(xiàn)代歐洲文藝史譚》(載第一卷第三、四號)中先后提出和倡導的。從那時以來,現(xiàn)實主義在中國文藝界已經(jīng)持續(xù)生長一百多年,有過豐富而又復雜的演變歷程,特別是與中國古典心性論傳統(tǒng)之間產(chǎn)生過一番曲折的交集。(1)關于此觀點,詳見筆者《中國現(xiàn)實主義文藝中的心性論傳統(tǒng)》,《當代文壇》2023年第3期。一個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是,近十年來陸續(xù)出現(xiàn)了一批既展現(xiàn)經(jīng)典現(xiàn)實主義精神,又凸顯中國式心性論傳統(tǒng)在當代社會生活中的回歸的電視劇作品。這批電視劇作品的出現(xiàn)表明,移植到中國長達百余年的現(xiàn)實主義種子,終于找到了與中國古典心性論傳統(tǒng)相嫁接的合理方式,其果實之一就是心性現(xiàn)實主義美學范式的定型和成熟(2)該概念為筆者于2022年初評論長篇小說和電視劇《人世間》時首次提出,詳見:《〈人世間〉:心性現(xiàn)實主義范式的成熟之作》,《文匯報》2022年3月4日第10版;《藝術公賞力的一座里程碑》,《文藝報》2022年3月2日第4版;《中國式心性現(xiàn)實主義范式的成熟道路——兼以〈人世間〉為個案》,《中國文藝評論》2022年第4期。。這意味著我國文藝界成功地將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華文化傳統(tǒng)相結(jié)合,具體來說,也就是中國電視劇領域內(nèi)出現(xiàn)了一大批將馬克思主義推崇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與中國古典心性論傳統(tǒng)相結(jié)合的、體現(xiàn)心性現(xiàn)實主義范式的電視劇作品。
一、現(xiàn)實主義與心性論傳統(tǒng)
首先我們需要看到的是,外來現(xiàn)實主義與中國古典心性論傳統(tǒng)正在相互融合的進程中不斷地成長。現(xiàn)實主義和心性論,一個偏重客觀實體及其真實性,一個講究主體心性,是中外迥然不同的兩種話語體系。人們對現(xiàn)實主義文藝的基本精神并不陌生,即追求藝術審美的客觀性或真實性,把現(xiàn)實生活中的假的、丑的揭露出來并加以批判,同時讓人們領略真善美的積極價值,并且激勵人們向往光明的未來。而心性論傳統(tǒng)則注重主體的“心”以及本性的重要性,要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3)提煉自《大學》“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即個體首先是“誠意正心修身”,進而承擔“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責任。由此可見個體德行修為在中國傳統(tǒng)人格構型中具有優(yōu)先性和基本作用。但是,在經(jīng)歷現(xiàn)代中國百余年的曲折演變后,現(xiàn)實主義精神與中國古典心性論傳統(tǒng)在近十年間逐漸實現(xiàn)融合生長,即客觀真實性與主體心性智慧之間緊密交融起來,直到產(chǎn)生心性現(xiàn)實主義文藝美學范式,并逐步走向定型和成熟。心性現(xiàn)實主義意味著既堅持現(xiàn)實主義特有的客觀理性精神和科學態(tài)度,又同時滲透進心性論傳統(tǒng)所持守的主體心性態(tài)度,并且將這兩者高度統(tǒng)一地融合起來。這標志著外來的現(xiàn)實主義文化種子在中國大地結(jié)出了只屬于這片東方土地的獨有成果。
實際上,導致心性現(xiàn)實主義文藝在這十年間走向定型和成熟的動因有不少,可以列出的方面頗多,這里暫且指出以下三個最有代表性的方面:一是中國學術界早就對心性論傳統(tǒng)的地位和作用開始了重新反思和評價。在改革開放初期的1978年,龐樸就撰文《孔子思想的再評價》(載《歷史研究》1978年第8期),提出應當辯證地評價孔子這一新主張,開始扭轉(zhuǎn)過去一段歷史時期內(nèi)一邊倒地全盤否定孔子的潮流。李澤厚在《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一書中將孔子視為中國文化的象征予以推崇。與此同時,張岱年、梁漱溟、湯一介等哲學家也曾提出彼此有所不同但也相通的肯定性見解。二是民間社會層面一直在流行古典式心性論傳統(tǒng),如仁義精神、俠肝義膽、憂患意識等,其間一直有著心性論傳統(tǒng)在當代社會中復蘇的強烈愿望——盡管過去曾在國家和社會層面受到抑制。三是國家層面在意識到精神文明建設嚴重滯后于物質(zhì)文明建設后,急切地倡導復蘇本土古典文化傳統(tǒng),因而古代心性論傳統(tǒng)在近十年中獲得重新興盛的機遇,具有一種必然性和重要性。恰如《白虎通》指出的那樣:“教者,何謂也?教者,效也,上為之,下效之。民有質(zhì)樸,不教而成。故《孝經(jīng)》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論語》曰:‘不教民戰(zhàn),是謂棄之。’《尚書》曰:‘以教祗德。’《詩》云:‘爾之教矣,欲民斯效。’”(4)〔清〕陳立:《白虎通疏證》,吳則虞點校,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371頁。可以說,正是來自學術界、民間社會和國家層面的心性論傳統(tǒng)復蘇愿望的相互滲透和協(xié)同運作,有力地匯聚成了心性現(xiàn)實主義文藝的定型和成熟之動因。
二、心性現(xiàn)實主義的主體間性構型
鑒于心性現(xiàn)實主義在文藝創(chuàng)作與作品中的呈現(xiàn)方式多種多樣,這里選擇考察文藝作品中主要人物形象在主體間性方面的構型方式。主體間性,也譯作交互主體,由德國現(xiàn)象學創(chuàng)始人胡塞爾提出,他借此概念強調(diào)每個個體都是由他與周圍他者之間的交互關系構成的。如果想認識和理解一個人,就需要認識和理解他與周圍他者的關系怎樣,而他周圍的他者又同另一批他者構成聯(lián)系,另一批他者自身還有其他更加復雜的他者。法國哲學家勒維納斯索性提出“人質(zhì)”概念來闡釋個人與其周圍他人之間的緊密關系狀況。這就是說,必須把個體的存在命運交給“他人的人質(zhì)”——“人類本質(zhì)首先并不是沖動,而是人質(zhì),他人的人質(zhì)”(5)[法]艾瑪紐埃爾·勒維納斯:《上帝·死亡和時間》,余中先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7年版,第19頁。。每個人來到世上,絕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始終同他人纏繞在一起的共同存在。因為不得不同他人打交道,相處、共生、相互纏繞在一起,這就相當于充當了“他人的人質(zhì)”。“人是這樣一種存在,對他來說,在他的生存中,關系到他的存在本身,他必須要抓住他的存在。”(6)同上書,第23頁。具體地說,“人的生存(或此在)由三個結(jié)構描繪在它的此(存在于世)中:這三個結(jié)構就是先于自身存在(計劃)、已然在于世(真實狀態(tài))、作為共存(與萬物共存,與在世界內(nèi)部所遇見者共存)的存在于世”(7)同上書,第29頁。。人生在世的存在往往由三個結(jié)構組成:你的生命不是你自己給的,而是由父母給的,而父母的生命也是由其父母給的,這顯然都是先于自身的存在;你來到世上,既要同父母相處,還要同讓你獲得衣食住行等必需生活資料的其他所有他人相處,以及同教導你文化修養(yǎng)的更多他人相處,這便是已然在于世的存在;個人在成長的過程中,需要同更多的他人、更豐富的關系也即萬物產(chǎn)生關聯(lián),例如同班級同學、老師、同事、上級、下級、客戶、乘客、旅客、患者、醫(yī)生、護士、交警、快遞員、司機等彼此共在,這就是作為共存的存在于世。這三個結(jié)構其實是相互纏繞和共同發(fā)生作用的,特別是讓其中的他人成為自我的不得不始終小心翼翼地應對的對象。“因為他人占據(jù)了我的心,以至于我的自為、我的自在都成了問題,以至于它都把我當成了人質(zhì)。”(8)同上書,第159頁。人生在世的主要任務,說到底就是學會與他人相處、相互共在,所以好比自我被當成他人的“人質(zhì)”一樣。“當我說到我,我就不是一個自我之概念的特殊情況:說到‘我’,就是擺脫了這一概念。在這一第一人稱中,我是人質(zhì),承擔著所有其他人的主觀性,但又是唯一的,不可能被替代,或者說,體現(xiàn)著在責任心面前躲避的一種不可能性,比擺脫死亡的不可能性還更嚴重。”(9)[法]艾瑪紐埃爾·勒維納斯:《上帝·死亡和時間》,余中先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7年版,第163頁。勒維納斯在闡釋“人質(zhì)”的概念時認為:由此,自我來到世上就立即被賦予了“人質(zhì)”的角色,承擔起所有他人的生存在世的守護者責任,必須時時處處帶著神圣的責任感去認真關懷和顧念他人,替他們著想。
這樣的主體間性觀念并不神秘難懂。如果從中國古代儒家倫理傳統(tǒng)看,即意味著看一個人不能只看他本人怎樣,而需要考察他與周圍他人之間的關系狀況——這簡化起來就是重視“二人”關系,即他本人與他周圍的他人之間的關系。世上萬事萬物,無論有多復雜,都可以被簡化為這種“二人”關系,都可以從處理“二人”關系的角度去考慮。儒家標舉“仁者愛人”,以及制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一系列“二人”關系規(guī)范等,正是出于這個道理。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唐君毅在現(xiàn)代標舉“人與人互為真實存在”的“倫理社會”之說,目標在于“促進人與人之價值感之彼此共喻,而逐漸形成一中國之人與人互為真實存在之中國社會”(10)唐君毅:《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上),載《唐君毅全集》第13卷,九州出版社2016年版,第91頁。。在這種傳統(tǒng)型“倫理社會”中,真正重要的不是個人與集體、集體與集體、個人與自我等關系,而是“每一個人對其他個人之關系”。這就是說,“每一個人,可以同時普遍地內(nèi)在于諸倫理關系中之諸其他個人之精神之中,而諸倫理關系中之諸個人,亦可內(nèi)在于此個人之精神中。則每個人自身與其精神,即對諸倫理關系中諸其他個人為一普遍者。而其為普遍者,乃一真實存在之具體的普遍者。……人類要由抽象的存在而成為具體的存在,兼不泯失其特殊性與普遍性,則舍將人與人之關系,化為互為真實存在之倫理關系,亦無道路”(11)同上書,第91-92頁。。這種現(xiàn)代新儒學意義上的真君子,應當自覺地將個人真實存在與他人真實存在相互交融地予以體驗,同時將他人真實存在轉(zhuǎn)化為個人真實存在去體驗。而假如人人都能夠這樣做,那么“人與人互為真實存在”的“倫理社會”的建立,就是可以期待的。
由此可見,“主體間性”這一現(xiàn)代概念與中國古典儒學的“二人”關系觀念有著相通之處。兩者同樣是指一個人的存在狀況不僅取決于他個人,而且往往同時受制于他與周圍若干他人的關系的情形,從而個人的存在實際上是由他與眾多他者之間的諸多復雜關系構成的。這些都表明,人類主體的存在往往不是孤立無援或孤獨無涉的,而是交互的或間性的,是由若干有形和無形的人際關系共同構造起來的。這種來自中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二人關系”和“主體間性”觀念共同告訴人們,人生在世,無論個體是否愿意,都不得不同周圍他者(包括他人和他物)打交道,受到其影響,也給予其影響。
其實,馬克思主義已經(jīng)辯證地和歷史地回答了這個問題:人的本質(zhì)不在于抽象的個人,而在于“現(xiàn)實的個體的人”(12)[德]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神圣家族,或?qū)ε械呐兴龅呐小?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3頁。。馬克思強調(diào)“人的本質(zhì)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xiàn)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3)同上書,第501頁。,這意味著把“現(xiàn)實的個人”置身于“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之中去作完整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強調(diào)這樣的個人的現(xiàn)實性:“這是一些現(xiàn)實的個人,是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zhì)生活條件,包括他們已有的和由他們自己的活動創(chuàng)造出來的物質(zhì)生活條件。”(14)同上書,第519頁。這種“現(xiàn)實的個人”不是首先由其社會意識決定的,而是由其社會存在決定的。“這里所說的個人不是他們自己或別人想象中的那種個人,而是現(xiàn)實中的個人,也就是說,這些個人是從事活動的,進行物質(zhì)生產(chǎn)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質(zhì)的、不受他們?nèi)我庵涞慕缦蕖⑶疤岷蜅l件下活動著的。”(15)同上書,第524頁。可見這里的“現(xiàn)實的個人”是有鮮活生命的個人,他們通過自己的勞作活動而同環(huán)境發(fā)生聯(lián)系,所以具有超越動物的靈性。同時,這種“現(xiàn)實的個人”更是始終與周圍他人相交往的人、彼此共在的人。總之,“人們自己創(chuàng)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chuàng)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chuàng)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chuàng)造”(16)[德]卡·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0-471頁。。人們總是在既定的歷史條件下去創(chuàng)造自身的新歷史,從而既是史詩的主角,同時又是史詩的行吟者。由此看來,“二人”關系和主體間性或交互主體,實際上都可以被理解為現(xiàn)實的個人角色構造,也就是指向了現(xiàn)實個人的主體間性的構型狀況。
主體間性構型,在這里是指個人作為主體總是存在于他與周圍他者的相互關聯(lián)狀況中,并且也由于這種相互共存關聯(lián)而排列組合成為一種相對穩(wěn)定而又處在變異中的人格構造。這樣的主體間性構型,就不只是指向一種靜態(tài)的主體人格構造,而是指向一種始終與周圍他者共存和相互發(fā)生矛盾,以及尋求相互調(diào)和的、動態(tài)的和變異的人格構造形態(tài)。
而就心性現(xiàn)實主義文藝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來看,其主體間性構型的分析方式可以有若干。下文擬從個人與周圍他人的相互關聯(lián)狀況去考慮,也就是著眼于個人與他人打交道、共存以及在社會關系網(wǎng)絡中發(fā)揮自身的社會作用的角度去考察,以求更加清晰地體現(xiàn)心性現(xiàn)實主義作品中主體間性構型的表征和作用。
三、心性現(xiàn)實主義的主體間性構型方式
為了具體分析心性現(xiàn)實主義電視劇作品中人物形象的主體間性構型,不妨參照《尚書》的如下論述:“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17)李民、王健:《尚書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頁。這里有關“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的論述,體現(xiàn)出帝舜時代對為人正直而又溫和、處事寬厚而又明辨是非曲直、性情剛毅而不粗暴、待人態(tài)度簡明而不傲慢的人格構型的欣賞和倡導態(tài)度。孔子在回答子張所提如何從政時說,君子應該做到“尊五美”。這里的“五美”指“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18)楊伯峻譯注《論語譯注》,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236頁。。由此可見這里對“君子”的人格構成要求在于:給民眾實惠而自己沒有耗費,能讓民眾勞動而他們并不怨恨,自己行使仁義之事就不叫作貪,個人安泰矜持卻不驕傲,威嚴卻不兇猛。(19)同上書,第237頁。描述“五美”的構詞方式的特點在于,可以充分考慮和兼顧個人在主體間性構型上的既異質(zhì)、易變而又可以相互化合等辯證組合情形,體現(xiàn)出儒家式“中庸”或“中和”原則在人格構型上既規(guī)范而又靈活多樣的運用。這里沿用這種古典式構詞方式,以有利于看出人物形象中個人與周圍他人之間,或者主體與其他主體之間的多樣而又復雜的間性關聯(lián)狀況。由此可以看到心性現(xiàn)實主義在當前電視劇作品中的幾種主體間性構型模式:愚而智式主體、散而聚式主體、識而行式主體、異而同式主體、創(chuàng)而讓式主體、變而安式主體、過而改式主體和融通式主體。限于個人的閱歷和本文篇幅,下面只能簡要地列舉,不尋求全面和完整。
其一是愚而智式主體。心性現(xiàn)實主義將客觀現(xiàn)實狀況同個人的主觀性相互融合,呈現(xiàn)出一種憨而慧或大智若愚的主體間性構型方式,也就是既憨厚、直率而又聰慧、明智的人格狀態(tài)。這種主體間性構型主要針對家庭或家族關系,以及鄰里關系,其較早的突出實例是《傻春》(2011)中的老大素春。該作品的主角為老趙家的九口人,父親趙宇初性格耿直而又自以為是,母親許敏容有著“大小姐”脾氣和男尊女卑的舊思想,七個兒女各有其性格。長女素春因?qū)W習成績不好、遇事反應遲鈍,被父母分別叫做“傻春”和“傻老大”,并且常受弟妹們欺負和父母打罵,但始終親切善良,忠厚隨和,總是以一張笑臉面對家人和周圍鄰居,甚至成為全家的頂梁柱式人物。該劇先后通過“蘋果事件”“小楚不消化事件”“找回小楚事件”等情節(jié),反映出傻春看似愚笨而實則聰慧的品格,強調(diào)正是她給家里帶來了凝聚力。她誠然沒有多少文化,更不會知道多少儒家學說,但憑借其先天和后天習得的對儒家式忠厚和友善持家原則的領悟力和實行力,完成了愚而智式主體的構型。又如《情滿四合院》(2015)中鋼廠食堂廚師何雨柱,為人憨直、善良、仗義、機敏,人稱“傻柱”。他熱心幫助同院鋼廠工人秦淮茹,后者年輕守寡且?guī)е粌簝膳?還要贍養(yǎng)婆婆,日子過得艱難,但講孝道、善良、能干。他們兩人歷經(jīng)曲折而結(jié)成知心伴侶。放映員許大茂自私且貪圖便宜,同傻柱成為對頭。他不斷挑撥離間,從而時常引來傻柱的報復。而同一胡同的三位老工人,人稱“三位大爺”,善于調(diào)解鄰里糾紛。傻柱在與鄰里相處中一路磕磕絆絆,終于逐漸成熟,敢于擔責,把四合院改建成了養(yǎng)老院,還在秦淮茹的支持下與許大茂實現(xiàn)和解,從而讓這座四合院的鄰居們和睦地生活在了一起。除此之外,長篇小說和電視劇《裝臺》(2020)中的西安“城中村”裝臺隊隊長刁順子,也有著一副憨愣性格和樸實外表,但內(nèi)心明白事理,為人仁厚仗義,總是替他人著想。以他為首組建的劇院舞臺裝臺隊匯攏了一群鄉(xiāng)下壯漢,一道在西安為劇院演出做裝臺工作。正是在多年的裝臺生活中,他諳熟秦腔藝術,其人生言行都受到濡染,并在日常生活中自然流露出來。這樣一套愚而智的言行準則,讓他成為周圍人信賴和依靠的對象,只是小說和電視劇的結(jié)局有所不同:在小說里,他終究無法駕馭刁蠻任性的女兒刁菊花,任憑其氣走蔡素芬,落得人走而家破的結(jié)局;而在電視劇中,刁菊花終于發(fā)生轉(zhuǎn)變,使得蔡素芬留下,家變得完整了。這種差異并不改變刁順子的愚而智式主體間性構型。這種主體間性構型的特點在于人的外表與內(nèi)里德行之間往往構成反差性組合,突出了內(nèi)在美質(zhì)的重要性。
其二是散而聚式主體,意即分散而又聚合的主體間性構型。這種主體間性構型同樣是針對家庭或家族關系以及鄰里關系來說的,涉及中國社會的基層主體間性構型方式。《下海》(2011)講述了20世紀90年代初北方小城中陳氏家族父母雙亡后的動蕩生活故事。長輩去世后,大哥陳志平當家;志平的大妹志芳在丈夫趙永明的鼓動下南下廣州行醫(yī);志平的妻子周蕓為人善良、工作勤奮但意外下崗,也不得不去廣東開辟新路,與志平的關系愈益疏遠;小妹志華的丈夫李林因業(yè)余時間偷辦拳擊班而與校方?jīng)_突導致入獄,出獄后與小妹辭職南下求生計;志平因為陳家的破碎也被迫南下,試圖挽回家族的分離頹勢,重建完整的陳家。經(jīng)過志平和其他家庭成員的共同努力,遭遇親情與無情、仁義與金錢、本分與發(fā)跡等種種沖突和調(diào)和,歷經(jīng)分離、離婚、復婚等陣痛的陳家,意識到了完整的家的重要性,最終重聚并發(fā)表飽含親情喜悅的“廣東宣言”。與此相似的作品還有《溫州一家人》(2012),該作講述了溫州農(nóng)民周萬順一家在80年代初離家奔赴各地(包括外國)艱苦創(chuàng)業(yè)的故事,描寫了周萬順、其妻趙銀花、兒子麥狗和女兒阿雨賣掉祖屋,借錢闖蕩,經(jīng)歷坎坷而最終建成現(xiàn)代企業(yè)的風雨歷程,展現(xiàn)了當代中國商人的奮斗史。與此相關的還有《雞毛飛上天》(2017),該劇以陳江河和妻子駱玉珠的感情和創(chuàng)業(yè)故事為線索,講述了義烏改革發(fā)展三十多年的曲折而輝煌的歷程。劇中陳江河和駱玉珠本是青梅竹馬,卻被棒打鴛鴦,各自闖出一條商路,歷經(jīng)坎坷后重逢,相約不再分離,夫妻聯(lián)手同戰(zhàn)商海,扶持下一代王旭和邱巖將產(chǎn)業(yè)傳承和壯大。這種主體間性構型一面承認現(xiàn)實生活中家庭成員分離和分散的不可逆轉(zhuǎn)性,一面伸張家庭成員團聚的重要性。
其三是識而行式主體,屬于一種敏銳識別生活趨向并及時付諸行動的主體間性構型。此類代表作之一《歲月》(2010)改編自小說《滄浪之水》,其中主人公梁致遠堪稱后知后覺的代表,他從校門踏入社會后感到社會人事關系復雜,雖然同善于交往的許小曼之間性格可以互補,但天生的書呆子氣讓他與她分了手。他重新面對復雜的社會關系,逐漸適應其生存規(guī)則而順利晉升,但結(jié)果發(fā)現(xiàn)與當初青蔥時代的理想愿景越來越遠,為時已晚,只能陷入悔恨和反思中——這種悔恨及反思性成為其主要的人格構型特點。《正陽門下》(2013)中返城知青韓春明善于知而行,勇于開拓,乘改革開放東風艱苦創(chuàng)業(yè),雖然不斷遭到暗算、被騙,讓真誠愛情和婚姻也出現(xiàn)危機,但由于有眾人幫扶,幾經(jīng)磨難、堅韌持守,最終建立了收藏和保護流失海外或瀕臨毀滅的古代藝術品的私人博物館,成為一名成功的京城文化企業(yè)家。《大江大河》(2018)改編自小說《大江東去》,講述了三位男主人公在改革開放時代的開創(chuàng)性業(yè)績。這三人是國企技術員宋運輝、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老板雷東寶和個體戶楊巡。他們分別再現(xiàn)了國有經(jīng)濟、集體經(jīng)濟和個體經(jīng)濟的運行狀況,傳達出對歷史興衰的感慨。他們?nèi)耸侵械姆独5胁⒉槐厝粠砣松腋?這三位主人公就不得不遭遇歷史的“大浪淘沙”般的無情洗刷,有著不同的命運歸宿。《超越》(2022)講述了輪滑少女陳冕以短道速滑為事業(yè)目標,最終成長為國家隊主力而出征冬奧賽場的故事,重點在于刻畫三代運動員/教練員之間并非單純爭勝好強而是為國爭光的精神傳承關系和彼此之間的深厚情誼,從而為奧林匹克精神提供了一種中國式新闡釋。《春風又綠江南岸》(2022)講述了臨危受命的江南縣委書記嚴東雷帶領班子成員推進環(huán)保工作、發(fā)展綠色產(chǎn)業(yè)的故事。嚴東雷為人不張揚、不說大話但心中有數(shù),認準了就堅決做,最終影響并激勵了班子成員,他們齊心協(xié)力推進工作,并且滿懷仁義幫扶企業(yè)家走出困境迎來新生,從而通過環(huán)境整治、精準扶貧、效能革命、掃黑除惡等過程,使得江南縣走上綠色發(fā)展的正確軌道。《大山的女兒》(2022)講述了黃文秀在研究生畢業(yè)后毅然回鄉(xiāng)投入扶貧工作,到百坭村任第一書記的故事。她回鄉(xiāng)不是僅僅出于報恩意識,而是渴望以開創(chuàng)精神為改變鄉(xiāng)村面貌而建功立業(yè)。她總是以仁厚態(tài)度對待村民,幫助他們脫貧致富,屬于新一代中的知而行典范。這種主體間性構型主要考慮個人在社會中的作為方式,突出仁厚、仁義、容讓等品質(zhì)的重要性。
其四是異而同式主體。展現(xiàn)這一類型主體的代表作《父母愛情》(2014)講述了海軍軍官江德福與“資本家”家庭出身的安杰歷經(jīng)五十年風云卻堅如磐石的感情故事。這對夫妻克服了各自在出身、文化程度、興趣等方面的性格差異,歷經(jīng)磨合、磨礪和摩擦等,共同撫養(yǎng)五個孩子長大,一道牽手到老,體現(xiàn)出身份和性情不同者卻可以形成高度同一性的格局。《歡樂頌》(2016)敘述了從外地到上海打拼、同住“歡樂頌”小區(qū)的“五美”的生活故事。她們中有大齡職場女性樊勝美、實習生關雎爾、工資低廉的邱瑩瑩、海歸金領安迪和富家女曲筱綃。她們性格各異,命運有別,但經(jīng)過若干次磨合,逐漸結(jié)下姐妹情誼,共同應對變化中的上海職場生活。這種主體間性構型偏重于不同個人在家庭和社會關系整體中的彼此共在的狀況,傳達異質(zhì)性中的共通性原理。
其五是創(chuàng)而讓式主體,意即既創(chuàng)業(yè)又敢于容讓,關鍵時候能夠做出容讓性舉動。比如作品《正陽門下小女人》(2018)講述了徐慧真和她的小酒館的幾十年變遷,傳達了這位女性創(chuàng)業(yè)者的正直、仁愛、仗義、嫉惡如仇等性格,同時又凸顯出容讓、包容、慈悲等善良品格。《都挺好》(2019)也講述了職場成功女性蘇明玉創(chuàng)而讓的品格。她從小受家人排斥,憤而離家出走在外獨自打拼,當母親突然離世、老父精神狀態(tài)失常、長兄遠在國外而次兄只會“啃老”時,不得不回家料理母親的后事、照顧精神崩潰的父親、調(diào)解兄長矛盾,直到疏解家庭糾紛,讓全家重新凝聚為整體。這種主體間性構型揭示了創(chuàng)業(yè)或創(chuàng)造過程中面對名與利、進與退、得到與給予等矛盾時所做的選擇。
其六是變而安式主體,試圖表達一種通過改變心態(tài)而達成自我及他人心安、心安是福的道理,也就是強調(diào)生存于變化不息的生活中的個人,通過改變自我心態(tài),也可以實現(xiàn)心安。比如作品《山海情》(2021)講述了六盤山麓涌泉村村民在福建援建干部幫扶下整體搬遷至戈壁新家園吊莊的故事。村民在村干部馬得福動員下入住吊莊,但無法忍受沙塵暴肆虐等異常艱苦的條件而又搬遷回山上,幾經(jīng)反復,終于應最年輕村民群體的要求而完成整體搬遷。《我在他鄉(xiāng)挺好的》(2021)講述了四位女性在北京異鄉(xiāng)拼搏的故事。胡晶晶的突然離世打破了喬夕辰、許言、紀南嘉三人的平靜,使得她們緊急行動起來,重新思考人生的意義,尋找更合適的生活方式,最終明白了“心安是吾鄉(xiāng)”的道理。
其七是過而改式主體。這是一種發(fā)現(xiàn)自身過錯并主動糾錯或改過的主體間性構型,是現(xiàn)實主義精神與中國心性論傳統(tǒng)相融合的一種重要呈現(xiàn)。比如作品《風吹半夏》(2022)講述了許半夏在鋼鐵行業(yè)白手起家、艱苦創(chuàng)業(yè)的過程,展現(xiàn)了民營企業(yè)從最初“野蠻生長”到后來呈現(xiàn)智慧型發(fā)展的鮮明轉(zhuǎn)變和扎實提升。該劇的一個敘述重心在于,民營企業(yè)家許半夏在其鋼廠實業(yè)由小到大、從逆境轉(zhuǎn)向順境并接近騰飛的重要時刻,主動反思早年過錯,向當年灘涂污染事件受害者及其家屬做出真誠懺悔,并且自覺地向他們賠罪,體現(xiàn)了中國企業(yè)家的群體人格覺醒。這種企業(yè)家主體性格獲得轉(zhuǎn)變和升華的背景,顯然與2012年以來新時代中國社會興起的古典心性論傳統(tǒng)復歸熱潮緊密相關,特別是在這種熱潮中,中國社會各行各業(yè)領袖型人物越來越有著基于古典心性論傳統(tǒng)的君子式人格復蘇、轉(zhuǎn)型或升華上的自覺,并且務實地轉(zhuǎn)化為生活中的實際行動。許半夏正是他們中更具理想主義精神的突出代表。
其八是融通式主體,屬于上述幾種主體間性構型方式的融通形態(tài)。《人世間》(2022)由同名小說改編而成,講述了工人周志剛及其家族20世紀60年代以來近半個世紀的人生經(jīng)歷。周志剛和三個子女周秉義、周蓉、周秉昆都體現(xiàn)出了各自的主體間性品格。周志剛是中國產(chǎn)業(yè)工人的一個典型,有著耿直善良的性格,服從國家需要而長年離家到南方工作,偏愛小兒子秉昆并對他的一生發(fā)展(如考大學、成家、生子等)寄予厚望,到頭來卻飽嘗失望,多次生氣訓斥、責罵但都無濟于事。歲月滄桑磨礪了他的性格,促使他逐漸認可秉昆對鄭娟及其帶來的兒子的接納,以及包容秉昆和他的“六小君子”的底層生活情狀,并在臨終時回望一生,對經(jīng)歷的往事和陪伴在身邊的親人都感到滿足。不止周志剛,其長子周秉義也有著正直有為的性格,無論是當插隊知青,還是在軍工企業(yè)做廠長,抑或在地方任職,都秉持家教,做純正、正直、務實的普通人,在擔任干部時更是主動為百姓辦實事,甘于清廉,是有作為的好官。次女周蓉秉持一種孤高雅致的性格,相信詩意和遠方,在其教學和文學創(chuàng)作中自覺追求遠離底層人群的高雅人生,盡管時常遭受挫折,也愿意以文學理想去指導實際生活中的人和事。周秉昆的性格可以用憨直仗義去概括,他自幼生活在底層,同光字片街道中的“六小君子”投緣,雖然沒有考上大學,但始終在向往理想的生活,孝敬父母,關愛友朋,以生存的韌性直面生活的艱辛和苦楚,并對落難的鄭娟投寄真情實意,不離不棄、相親相愛地持守一生。這幾位主要人物都展現(xiàn)出了心性論傳統(tǒng)在中國社會倫理制度中的長期涵濡之功。
實際上,電視劇作品及其主體間性構型現(xiàn)象遠不止上述這些,但這些應當是其中較為重要的。這些人物的主體間性構型的出現(xiàn),是當前社會中心性論傳統(tǒng)復蘇并與現(xiàn)實主義精神相交融而反映在電視劇藝術中的一種特定寫照,具有必然性。
四、反思心性現(xiàn)實主義電視劇的主體間性構型
以上就心性現(xiàn)實主義電視劇作品中人物的主體間性構型狀況作了簡略分析,盡管這種分析還有待細化和深入,但畢竟已經(jīng)可以幫助我們看到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了。我們首先應看到,愚而智式主體、散而聚式主體、識而行式主體、異而同式主體、創(chuàng)而讓式主體、變而安式主體、過而改式主體、融通式主體等主體間性構型的出現(xiàn),具有重要的審美認識價值:這些電視劇人物的主體間性構型真實生動地展現(xiàn)了中國社會在當代已經(jīng)和正在發(fā)生的巨大變革和取得的飛速進步,而這些巨大變革和飛速進步恰恰伴隨著當代中國人及其家族的生存方式的劇烈變動。改革開放進程伴隨著越來越頻繁的城鄉(xiāng)人口流動和人們生存方式的變遷,使得中國城鄉(xiāng)經(jīng)濟和社會逐步發(fā)生巨變,也使得中國個體生存?zhèn)惱砟酥良易迳鎮(zhèn)惱矶急煌度氲絼×易儎又小.攤鹘y(tǒng)生存方式和家族倫理都遭遇人口流動帶來的各種強力沖刷時,主體間性構型方式發(fā)生變化就是必然的。以《下海》《溫州一家人》《雞毛飛上天》等作品人物的散而聚式主體間性構型堪為其中的代表,此時古典心性論傳統(tǒng)重新登場亮相,無疑出于必然。正如《下海》結(jié)尾的“廣東宣言”所呈現(xiàn)的那樣,當代中國個體和家族亟需援引古典心性論智慧來在現(xiàn)實生活中產(chǎn)生重新穩(wěn)固家族倫理關系的凝聚力。這表明,電視劇是擅長及時反映時代社會變遷景觀的藝術門類之一(與它不同而又可以媲美的應當就是電影),可以形塑出新時代社會變遷的美學鏡像。
其次,我們還應當看到,這八種主體間性構型方式各有特點:愚而智式主體、散而聚式主體和創(chuàng)而讓式主體比較適合協(xié)調(diào)社會關系范圍較近的家庭、家族、鄰里關系;識而行式主體更貼近于改革開放時代個體的行動和創(chuàng)造姿態(tài);異而同式主體和變而安式主體便于概括流動型社會中城市陌生人之間的關系;過而改式主體是當前社會尤其需要但帶有更強理想化色調(diào)的主體間性構型;融通式主體則在上述構型范式中具有更強的互動、貫通和概括性。這種多樣性和差異性正可以用來應對當前流動型社會中主體生存方式的豐富性和復雜性,由此得見中國電視劇創(chuàng)作在反映現(xiàn)實生活的豐富性和復雜性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還需要指出的是,這里呈現(xiàn)的八種人物性格大多有著強烈的理想主義色調(diào),而其現(xiàn)實性和反思性偏弱。以弘揚理想主義為主調(diào)當然有其合理性,但冷峻地揭示現(xiàn)實狀況并加以深入反思也具有同樣重要的價值。《情滿四合院》里的何雨柱、《正陽門下小女人》中的徐慧真以及《風吹半夏》里的許半夏,在劇集結(jié)尾處都表現(xiàn)出了顯著的理想化色彩,即更多地透露出當代中國社會中還存在理想或幻想層面的主體性成分。這雖然值得標舉和追求,但同樣需要做的是真正揭示這種理想主義精神生存于現(xiàn)實中的困難性。在這方面,《我在他鄉(xiāng)挺好的》敢于在一開頭就揭示胡晶晶之死帶來的深重陰影,《大江大河》終究沒有給三位男主人公設計出“大團圓”或理想化結(jié)局,《山海情》反復表達山民們整體搬遷下山后在戈壁灘上的生活的艱難面——這些不加掩飾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都值得鼓勵和進一步發(fā)揚。比較而言,當前和未來中國電視劇創(chuàng)作亟需增強的,正是“良史之材”所應具備的“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zhì)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20)〔漢〕班固:《漢書》(第九冊),〔唐〕顏師古注,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738頁。的中國式現(xiàn)實主義精神。
最后值得關注的是,這幾種人物主體間性構型范式的共存表明了一點,即當代中國人的主體理念和倫理理想已經(jīng)產(chǎn)生一種普遍而深刻的變化:不僅繼續(xù)傳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一直倡導的“共產(chǎn)主義美德”這一現(xiàn)代革命傳統(tǒng),而且也讓以“中華傳統(tǒng)美德”為標志的中國古典心性論傳統(tǒng)得以強勢復蘇,并且同外來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形成新的相互滲透和交融。正是這種互滲和互融反映出:具有世界普遍性的外來現(xiàn)實主義同中國本土心性論傳統(tǒng)之間,是可以形成跨文化交融態(tài)勢的。這或許可以被視為中國當代電視劇創(chuàng)作對世界現(xiàn)實主義文藝的一種獨特建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