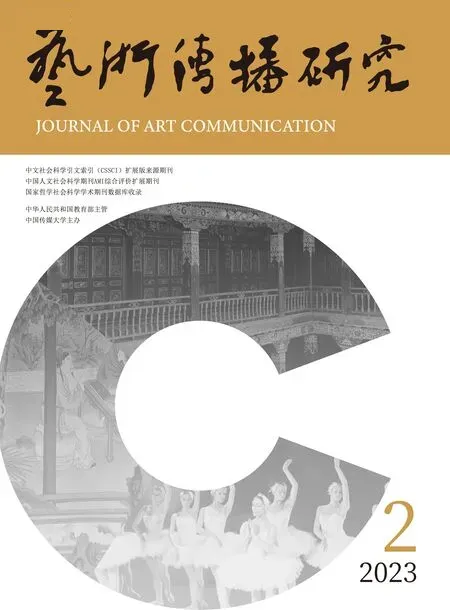后人類視域下的數字藝術與三種虛擬身體觀念
■ 劉書亮
“后人類”(post-human)是一個復雜的“理論—實踐”領域,藝術生產在這里與科技應用、哲學思辨交織共生,呈現出鮮明的跨學科特征。近年來,關于身體的研究逐漸在后人類視域中占據了重要位置,相關藝術實踐也開始促使我們重新思考人的身體。而在數字藝術研究的領域里,下述問題亟待我們深入探討:后人類語境下,身體觀念究竟如何影響著數字藝術的媒介形態及其大眾傳播過程?
許多學者認為,后人類想象在讓信息不斷走向離身。凱瑟琳·海勒(N.Katherine Hayles)曾篤定地判斷,將心智從身體中分離、將信息從物質中分離的傾向是當前文化的關鍵性特征,也是后人類研究的常見論調。(1)[美]凱瑟琳·海勒:《我們何以成為后人類:文學、信息科學和控制論中的虛擬身體》,劉宇清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3頁。然而本研究將指出,事實并非完全如此。我們看到,在各類數字藝術中,身體不僅并未缺席,有時反而越發具有根本性的地位,只不過身體的內涵發生了某些難以避免的變化。假如我們在后人類視域中已無法把“身體”一詞跟傳統意義上的(狹義的)肉身畫上等號,那么就應該找到更合理的界定身體概念的新方式。
本研究中的“數字藝術”,主要指各類在數字技術語境下創作生產出來的作品,包括但不限于當今的影視、動畫、數字視頻、CG繪畫、三維建模、數字游戲、虛擬現實等。本文將至少在兩個維度上建立“后人類視域下的身體”與“數字藝術生產與傳播”的學理性聯結:第一,諸數字藝術的媒介形態和傳播規律都直接關乎身體;第二,許多科幻藝術作品也在借助敘事來想象虛擬身體(海勒曾論及許多科幻小說,而本文將重點補充科幻電影與動畫的案例)。下面,本文將首先對兩個常被科幻作品借鑒與致敬的著名思想實驗進行重訪、延展與分析,并提出當前人們對數字化虛擬身體的三種理解范式——代碼身體、隱喻身體與肉身仿擬,由此嘗試闡述數字游戲、虛擬現實等數字藝術形態,乃至虛擬數字人、元宇宙等概念與這三種范式之間的復雜關系。
一、“莫拉維克構想”與機械身體的“賽博格”
不少學者共享著一種觀點:信息可以在不同媒介之間傳遞且自身不被改變。在今天,這確實是一個頗為明顯的事實。在藝術領域,藝術作品曾經終究要落實到一些物質介質上——它“在某個東西上”。那時候,我們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據媒介材料來劃分藝術門類的:雕塑對應于大理石、木頭或銅,電影對應于膠片,繪畫則對應于畫布和顏料。而在數字時代,創作結果是數據化的。(2)劉書亮:《數字時代的藝術創作》,《文藝報》2022年7月13日第8版。藝術家們通過功能各異的軟件,在數字化的工作環境中生產繪畫、雕塑、視頻、音樂等。而且,雖然創作發生在某個屏幕上,但作品可以方便地在其他屏幕上被展示,并可以被傳輸和復制,數據本身在這個過程中理論上沒有損耗。因此,數據化的藝術作品并沒有最終的、獨屬于它的承載介質,而在互聯網的迅速發展之下更是如此。約翰·彼得斯(John D.Peters)指出,互聯網在哈羅德·英尼斯(Harold A.Innis)的角度上是具有“空間偏向”的典型媒介(3)[美]約翰·杜海姆·彼得斯:《奇云:媒介即存有》,鄧建國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387頁。:信息通過數字化的方式脫離了沉重的物質,從而變得輕盈和敏捷,能以極快的速度跨越空間傳播。
而在這批學者眼中,人本身同樣不是附著于媒介/身體之上的,而是一種能夠脫離媒介的信息樣式。控制論之父諾伯特·維納(Norbert Wiener)認為,我們可以把有機體的模式看作一類消息,去傳輸人體的整套模式,跟傳輸電報沒有絕對的區別,只是難度不同。(4)[美]維納:《人有人的用處:控制論與社會》,陳步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89-90頁。
對此,最著名的技術展望之一來自漢斯·莫拉維克(Hans Moravec)描述過的思想實驗(下文簡稱為“莫氏構想”):在腦外科醫生的操作下,某人的腦子被一層層地掃描和建立模型,同時,醫生身旁電腦里的程序會完整復刻這個腦子,由此逐漸挖空它。最終,此人的心智就會整個從身體中移到那臺電腦中繼續“運行”——這臺電腦于是成了此人的等價物。(5)Hans Moravec,Mind Children:The Future of Robot and Human Intelligen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pp.109-110.
人的心智可以拋棄身體嗎?按照海勒等人的看法,莫拉維克給出的答案當然是肯定的。但是,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莫拉維克接下去的論述。“莫氏構想”的手術完成后,緊接著要解決的是給這個“數字大腦”賦予身體的問題——莫拉維克的解決方案是一具機械假肢之身,也就是說,“數字大腦”被安裝在替換過的新機械身體里,作為一個典型的“賽博格”(Cyborg)繼續生活。莫拉維克也提及,我們就算是能把自己的數字化心智傳送到另一個星球上,也需要在目標星球上有一個機器人,以便我們把心智傳導到里面。(6)Ibid.,pp.110-114.因此,“莫式構想”只是讓實驗對象換上了代理身體,而不是真的取消身體。同樣,維納“用電報傳輸人”之假想,也多次提及“在別的地方用別的材料把它再造出來”(7)[美]維納:《人有人的用處:控制論與社會》,陳步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90頁。,所以并沒有從實質上拋棄身體的觀念。
二、“缸中之腦”的另一端:“缸外之電腦”與虛擬身體
數字化的虛擬身體是與“莫氏構想”不太相同的一種思路。它以思想實驗“缸中之腦”(Brain in a Vat,一譯“缽中之腦”,后文也簡稱“缸腦”)為典型代表(當然,學界通常認為相似的哲學思考至少可以追溯到笛卡爾)。該思想實驗的提出比“莫氏構想”更早,它來自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在《理性、真理與歷史》一書中,普特南假想某人的大腦被單獨取出,放入營養缸中使其得以存活,并有一臺計算機連接著這個大腦的神經末梢。對這個人(盡管物質上似乎僅剩下這具大腦)來說,人群、物體、天空等似乎都存在,但實際上他所經驗到的一切都是由從計算機傳輸到神經末梢的電子脈沖所喚起的幻覺。(8)[美]希拉里·普特南:《理性、真理與歷史》,童世駿、李光程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6頁。雖然普特南想利用“缸腦”討論的重點是指稱、表征、概念的問題,并且他的部分論述實在令人難以接受(后來也有很多學者對他的結論的落腳點表示質疑,但這并非本文要討論的,故在此不做展開),可這并不妨礙“缸腦”本身作為經典思想實驗被后人不斷討論。
普特南至少有一件事情做得與莫拉維克很像:他所描述的這個實驗框架,充分強調了“缸腦”對代理身體的感知——對“缸腦”來說,“此人若要抬起手來,計算機發出的反饋就會是他‘看到’并‘感到’手正被抬起……甚至還會以為他正坐著讀書”,普特南稱之為“感官的饋飼”。(9)同上書,第6、13頁。而抬手、坐著,都是直接關乎身體的行為。
然而,“缸腦”的原有肉身已經被移除。實際上,對于這項思想實驗,有一個被很多人忽略的尤為重要的議題:“缸中之腦”必然需要搭配一臺“缸外之電腦”,方能將人的身體感知(盡管是虛擬的)落實下來——既要用信息搭建虛擬的肉身,又要讓信息“流經”這個虛擬肉身并能引發它的反應。“缸外之電腦”為“缸腦”提供了一個現象學意義上的被“意向”到的身體。
從腦與身各自的構造來說,“缸腦”與“莫氏構想”恰好遙相呼應、形成對照:“莫氏構想”是數字化的腦加上機械實體的身體;“缸腦”則是真實的人腦加上數字饋飼的身體感知。如果把二者結合起來,甚至也可以想象一個完全沒有傳統肉身的、完全數字化的生命——就像科幻動畫《萬神殿》(Pantheon,2022)里所描繪的,人腦被完整地(盡管在這個故事中不是“完美地”)掃描、存儲并上傳到云端,成為“上傳智能”(UI,uploaded intelligence)。但無論怎樣,身體概念都被生命表征與生命活動所需要。也正是出于這個原因,在《萬神殿》的故事中,女主角麥迪(Maddie)直到在游戲中看到了父親的虛擬化身形象,才終于從情感上確證了父親歸來的事實。恰如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所指出的那樣,人并不是一個精神加上一個與之分立的身體,而是一個合同于(avec)身體的精神。(10)[法]莫里斯·梅洛-龐蒂:《知覺的世界:論哲學、文學與藝術》,王士盛、周子悅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5頁。身體是人格心智的必要組分,而不是某個獨立外在于心智之物。誠然,我們在此已經將數字媒介搭設的虛擬身體視作肉身的某種替代之物,后人類觀念也確實意味著傳統肉身局部甚或全體的失效與替換,意味著對其進行改造、增添或重建,但心智跟身體性或者說跟虛擬身體并不分離。
當然,數字環境下的虛擬身體形態多樣且頗為駁雜,呈現了一種“復數的”身體性。而在數字藝術領域,通過各藝術門類的媒介特性與豐富的藝術傳播現象,去把握虛擬身體的觀念,還是比較容易的。下面,筆者將分別論述“代碼身體”“隱喻身體”與“肉身仿擬”這三種建構數字化身體的范式,并著重對比它們在藝術中的差異。
三、代碼身體:數字游戲、虛擬現實以及作為身體景觀的人工智能
“代碼身體”是有限模式下的身體塑造,是在特定維度上建立數據化、編碼化的身體模型,而不是要完美地復刻人類的肉身形式(下文對“肉身仿擬”的論述將指出,完美復刻是尚不能實現的)。代碼身體的一個典型應用領域是數字游戲。作為“第九藝術”之名的重要爭奪者之一,數字游戲對我們的經驗的影響不僅僅在于因利用手柄、鍵盤與鼠標等而造成的交互認同,還在于當玩家緊張而興奮地享受賽車、動作、第一人稱射擊等類型的游戲時,常常會不由自主地跟隨屏幕里的游戲角色(或說玩家的化身,即avatar)扭動自己的身體,如同在和角色一起冒險,由此產生身體層面的密切聯結。因此,有些人反對唐·艾迪(Don Ihde,一譯唐·伊德)將數字游戲視作一種準具身但非具身狀態的立場(11)參見劉錚:《虛擬現實不具身嗎?——以唐·伊德〈技術中的身體〉為例》,《科學技術哲學研究》2019年第1期。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數字游戲里的身體,是從相對抽象的圖形顯示開始出現的。早期數字游戲之一《乓》(PONG,1972)屏幕上的一條線就代表了玩家,我們可以將其闡釋為角色(化身)的球拍、手甚或全身。隨著計算機圖形學的不斷發展,游戲作品逐漸將身體復雜化、具象化、精美化,目前可以說已經在編碼的復雜程度上找到了特定的平衡。虛擬現實游戲進一步增強了傳統數字游戲的沉浸感,增加了交互維度,但它塑造虛擬身體的范式并未發生根本的改變,所蘊含的仍是一種代碼身體。
代碼身體以建立模型時的損耗為直接代價,簡化卻也異化了生命表征(可稱為“簡異化”)。例如游戲的數據系統就常常把虛擬生命體的屬性簡化為一些數值,像“生命值”“魔法值”“攻擊力”“攻擊范圍值”“防御力”等。此時,玩家在游戲作品中的各類互動及其對敘事的參與均有賴于這個數值系統。它非常類似于被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所批判的科學分析方法,即被用科學符號化約成了跟其他事物共通的要素,(12)參見[美]撒穆爾·伊諾克·斯通普夫、[美]詹姆斯·菲澤:《西方哲學史》,鄧曉芒、匡宏等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9年版,第434-435頁。可以說失去了生命綿延之本質,但它也正是我們的技術現實。當今的技術還有能力將游戲角色的身體與面孔參數化,甚至可以一鍵隨機生成身體和面孔。這也體現了代碼身體的一項重要特征——循著海勒的說法,就是在身體層面以“模式/隨機”替代了“在場/缺席”:當生命以虛擬的身體存在于網絡空間時,模式才是根本現實,而舊有意義上的在場只是視錯覺。(13)[美]凱瑟琳·海勒:《我們何以成為后人類:文學、信息科學和控制論中的虛擬身體》,劉宇清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48頁。為了進一步說明這一點,海勒還給出了“閃爍的能指”這一表述——它意欲表達的是,計算機中的能指不再是物質化的痕跡、標記(譬如紙面上的墨水印跡),而是由編碼所構造的模式系統,這導致能指具有“貫穿可變性”。海勒以電子文本的字體修改為例:要改變字體,只要給系統一個簡單的指令即可,無須像活字印刷術那樣重新安置每一行、每一顆活字。僅從這點看來,比起她反復提及的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閃爍的能指”其實跟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一譯波德里亞)所論述的仿真(simulation)秩序相似性更高——從海勒的行文看,她幾乎只是希望從對拉康的闡述中提取出“能指”這個詞。在鮑德里亞筆下,仿真秩序對應著價值的結構規律,他用模式生成(generation through models)、差異調制(differential modulation)、調節(regulation)、代碼(code,本文將此種虛擬身體命名為“代碼身體”正是緣于該詞)等來描述仿真秩序的特征,并反復以基因/DNA作為類比去說明這種符號內爆的秩序。基因能夠轉譯出生命,而仿真秩序意味著我們可以通過調制局部的基因編碼來改變生命的性狀(14)[法]讓·波德里亞:《象征交換與死亡》,車槿山譯,譯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73-79頁。,正如我們通過簡單的操作就能快速改變電子文本的字體或迅速生成游戲作品中的一張面孔、一副身體那樣。
除了數字游戲與虛擬現實,代碼身體也在人工智能領域發揮著作用。過去有許多人認為,我們對人工智能的想象與實踐路徑是“無身體”的,即它們雖然可能具有極強的能力,卻也是極度單調的、單向度的信號輸入輸出系統——圍棋人工智能AlphaGo、僅能以機器的方式與人交流對話的ChatGPT以及Midjourney、NovelAI等人工智能繪畫產品都是例子。然而實際上,人們在打磨人工智能產品或服務時,常常期望它表現出一定的身體性。譬如語音智能客服等非常簡單的虛擬人格應用,當它能“聽”與“說”時,它的輸入輸出模型就可以被看成作為交流“器官”的“耳”和“口”,盡管其功能已經通過編碼與算法被大幅簡化。這里很重要的是,當今的技術強烈地渴望為它賦予虛擬身體表征(甚至也可能是類似于機器人那樣帶有實際物理形態的機械假體),譬如我們會為它添加盡可能自然的吐字能力。這會讓人聯想到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論述聲樂藝術時所闡釋的“人聲的顆粒”(the grain of the voice)之身體性。巴特的說法頗為浪漫:我們在帶有“顆粒感”的人聲中能聽見舌頭、嗓子、牙齒,“身體的物質性在訴說著它的母語”(15)Roland Barthes,“The Grain of the Voice,” in Image,Music,Text,ed.and trans.Stephen Heath(Fontana Press,1977),pp.182-183.。這種微妙的身體性,正是人工智能技術所追求的:人們想要的不是回復或誦讀的機器,而是能以假亂真的語氣、停頓和情緒。有人甚至要為人工智能客服賦予姣好的外貌、流暢的肢體動作與口型動畫,使之成為功能型的“虛擬數字人”。當人工智能成為身體景觀之后,這種角色塑造也便成為某種特殊的藝術實踐——而這些都是通過代碼身體來完成的(這些塑造代碼身體的相關技術倘若能在未來臻于完美,也就成了后文的“肉身仿擬”范式),哪怕身體對功能的實現不起決定性作用。此類情景在行業里已經頗為常見:人工智能歌手“小堂妹”(來自“微軟小冰”)展現自我的短視頻作品需要將虛擬的臉合成到另一副身體上;清華大學的虛擬學生“華智冰”(同樣基于“微軟小冰”的框架)作為人工智能卻有一段“親身”走入校園的視頻宣傳片(當然,這個案例中起作用的是辨認不清面孔的替身演員)……總之,被人們“意向”到的生命,在技術賦權下亟待被具體化、可視化、身體化。
四、作為隱喻身體的互聯網及在其影響下的數字藝術傳播規則
在學界對后人類的討論中,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是一個不斷被提起的人。他的著名洞見“媒介是人的延伸”涉及的媒介范圍頗廣:電視、貨幣、住宅、汽車、時鐘……不一而足。可以說他秉持著人類感知層面上的某種泛媒介觀,而這些媒介重塑著人的感知。故對他來說,泛媒介正意味著泛身體,“任何發明或技術都是人體的延伸或自我截除”。以他所舉出的典型例子來說,車輪就是人身體的一部分。當腿腳延伸為能快速轉動的輪子,產生了以腳行走所沒有的速度時,也就從人身上“截除”了腳的原有功能。(16)[加拿大]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何道寬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59-61頁。
麥克盧漢意義上的身體是一種隱喻化的身體。必須說明,這里的“隱喻”取自認知語言學,尤其是喬治·萊考夫(George Lakoff)對隱喻的經典闡釋,是指源域(source domain)與目標域(target domain)兩個概念域之間的跨域關聯,而不是基于相似性。(17)[美]喬治·萊考夫、[美]馬科·約翰遜:《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何文忠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12-213、219頁。值得說明的是,兩位作者1980年在該書初版正文里并沒有明確提及“源域”和“目標域”,在2003年版的后記里才提到這兩個詞。盡管如此,學界仍常常將這兩個詞與此書、與萊考夫一起討論。因此,上文論述過的代碼身體不應被稱作隱喻化的。麥克盧漢式隱喻身體與代碼身體的區別在于,隱喻身體無須以肉身的形式為藍本,而只要反過來改變人的感知結構與比例就可以了——這也是麥克盧漢的常見思考路數。所以,我們有理由將數字技術場域中的隱喻身體定義為一種相對穩定的、帶有歸屬與占有性的“技術—感官”連接:該隱喻身體被我擁有,故我能享用它給我帶來的特定可供性(affordance)。
互聯網便是一種非常典型的隱喻化的數字虛擬身體。通過互聯網,我們延伸了視覺和聽覺,并得以訪問視頻、圖片、文字以及它們組合成的個人主頁等林林總總的“數碼物”(digital objects),即成形于屏幕上或隱藏于程序后端的物體,它們由受結構或方案(schema)管理的數據與元數據組成。(18)許煜:《論數碼物的存在》,李婉楠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頁。網民的生存狀態接近盧西亞諾·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提出的“信博格”(inforg,一譯“信息人”),即連接在網絡中的信息生物(19)Luciano Floridi,“Web 2.0 vs.the Semantic Web:A Philosophical Assessment,” Episteme 6,no.1(2009):25-37.——這可以區別于傳統意義上的“賽博格”概念。
海勒對身體概念的理解與使用也常常具有一些隱喻的性質。基于后人類研究的標準立場,她甚至寫道:物與人都擁有身體。不過有趣的是,她為人對身體的占有補充了一個前提:她將市場關系作為后人類世界中更具決定性的關系,并對自由人本主義做出了直截了當的批評。自由人本主義認為,人類的本質是“不受他人意志影響的自由”,“自由是一種占有功能”,而個人對自我的所有權也在時間上早于市場關系。但海勒援引麥克弗森(Crawford B.Macpherson)并指出,這種想象化的自然狀態僅僅是市場化社會的一種回顧性的創造。海勒提出,“六百萬美元先生”——該稱呼來自科幻劇《六百萬美元先生》(TheSixMillionDollarMan,又譯名《無敵金剛》,1973年起)——之所以擁有賽博格身體的各部分,是因為他購買了它們,是市場關系決定了這種所謂的自然條件。(20)[美]凱瑟琳·海勒:《我們何以成為后人類:文學、信息科學和控制論中的虛擬身體》,劉宇清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4-5頁。市場關系先于自然關系,這對整個互聯網環境來說不可謂不貼切:我們“擁有”互聯網并能夠使用它作為虛擬身體,是因為我們購買了相關的硬件,使用了操作系統、網絡瀏覽器等軟件,注冊了特定網絡平臺的賬號,并默認同意了平臺提供的用戶服務協議。所以,更具體、更明確地說,作為我們隱喻身體的互聯網,其實是由賽博環境搭建起的一種對互聯網內容的“可訪問性”。
這在當今以Web 2.0為主流的網絡時代尤其值得玩味,因為它塑造了讓數字藝術得以實現大眾傳播的總體結構。這是一個普遍聲稱人人皆可創作、作品發布便利的時代,是一個似乎真的實現了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曾主張的“每個人都能出名15分鐘”(21)有很多線索表明這句話可能不是安迪·沃霍爾說的,但這句話目前確實已經被和他牢牢綁定,同時也確實能夠代表他的藝術觀念。的時代,但也是因Web 2.0模式而讓網絡平臺成為霸權的時代。既然用戶的個人身份與平臺賬號及其技術和可訪問性相綁定(身份證號、手機號等信息的錄入都保證了這一點),平臺賬號就是用戶的一種隱喻身體,用戶也就由此具備了以市場關系為前提的身份歸屬。而基于此,用戶們創作并上傳的各類作品,最終都成了平臺才是其真正占有者的“內容”(content);用戶即使面對自己的作品也只是訪問者。當下,甚至數字游戲的發行往往也要依賴“蒸汽”(Steam)等游戲平臺對玩家賬號的管理。同時,我們以自身的能力通常也無法更改這種身份綁定關系,除非在必要時專門向平臺方申請,讓有專業技術且(更主要的是)有權力的主體來操作一臺“手術”,才能卸除/解綁這部分虛擬身體。這更說明了市場關系在此對自然關系所起的決定性作用。
Web 3.0重新定義了數碼物的歸屬——它用區塊鏈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構造了互聯網的規則。不過,目前Web 3.0的發展前景還不夠明朗,我們甚至也完全可以質疑它是不是Web 2.0平臺權力過度問題的唯一解(22)劉書亮:《Web 3.0之后的網絡時代:一場假想的虛擬閑聊》,《文藝報》2023年3月10日第8版。——毋寧說我們正處于“準Web 3.0”的技術語境下。但無論如何,“非同質化通證”(NFT,Non-Fungible Token)一度成為藝術界的新寵,數字藝術家與設計師們紛紛入局這個基于區塊鏈的嶄新的藝術交易市場。其間一個頗為有趣的現象是,數字藏品作為NFT藝術的特殊形態,因在區塊鏈上具備唯一性,卻又缺乏充分的交易性,成了一種“賽博紋身”:只要我購入并擁有了一件數字藏品,它就真正被記錄和印刻在我的互聯網隱喻身體上了。這一例子充分說明了一個事實:當作為隱喻身體的互聯網發生改變時,數字藝術的展示、傳播、交易規則也隨之改變。
五、肉身仿擬:數字藝術領域的終極神話與科幻理想
根據上文的論述,普特南借助“缸腦”思想實驗描述了一種“完美的”(用他自己的話說也是“邪惡的”)技術理想:為那個被剝奪了身體的頭腦完整重制了數字信息化的肉身感官,還可以消除腦手術的痕跡,該受害者將覺得自己“一切如常”,完全無法察覺自己已然成了“缸腦先生”。倘若真要實現這個目標,負責這場手術的醫師/科學家就必須用一整套應用程序去復原受害者的身體感知特征。
但要做到這件事何其困難!在此,我們可以對“缸腦”思想實驗進行一些延展想象。譬如,假設“缸腦”所屬之人原本是近視的,那么術后的“缸腦先生”仍應是近視的,程序可能要為他配一副與他原有生活中相同的眼鏡,被他“意向感知”。按照物理現實中的邏輯,那副眼鏡的鏡片隨著時間的推移可能會磨損,甚至在他被絆倒時會掉落損壞。而且他是否容易視疲勞也應該被設計在程序中……此外,這臺計算機還要完整地仿擬出他身體的其他各類特征,如果做不到,我們便有理由相信,“缸腦先生”過不了多久就會開始思考他自己的身體和所在的世界是否已經被篡改,他將對一切的真實性產生懷疑,猶如電影《楚門的世界》(TheTrumanShow,1998)的某個賽博版本。
拋開“缸腦”思想實驗的具體情境,搭建這種“肉身仿擬”式的虛擬身體,是希望讓虛擬身體盡可能全面、完善地復刻傳統肉身的運作,以至于讓生命體最終無法區分自己是在現實中還是被虛擬的。這不僅要求構造出肉身的知覺狀態,還要構造出一套包含其他假想生命體在內的、指向整個世界的關聯系統。這種情況下,人們甚至能夠實踐“虛擬身體-世界的圖靈測試”:為受試者提供一個完全虛擬的身體感知及其環境,看受試者能否覺察到異樣并判別其為“虛假的”非物理環境。鑒于任何與人們傳統肉身感知經驗之間的差異都會被無情地指認成瑕疵,這種搭建目前仍是無法實現的技術神話,哪怕僅僅是在視覺這一個層面上。日本機器人專家森政弘1970年發表論文提出的“恐怖谷”(uncanny valley)理論所反映的迄今仍是擺在計算機視覺藝術與計算機圖形學面前的重大難題:當仿人類的造型與人類在外表上雖然足夠相像但又做不到完全相同時,其間微小的差異都會格外明顯,使造型失去親和力,讓人類產生反感、恐懼、厭惡等情緒,(23)參見劉書亮:《什么是“恐怖谷理論”》,《文藝報》2019年3月22日第8版。從而也易于被分辨出是假人。即使單從這個角度來看,科技界距離“虛擬身體-世界的圖靈測試”的成功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因為在數字化的感官世界中,我們甚至還幾乎沒有能力在視覺上實時塑造一個能跨越“恐怖谷”、欺騙我們的眼睛從而被完全視為真人的形象。總之,肉身仿擬范式對虛擬身體和虛擬世界的塑造,要求不可謂不苛刻。
盡管如此,肉身仿擬仍是人類長期的夢想——既是技術夢想,也是藝術夢想。人們一直在用《黑客帝國》系列(TheMatrix,1999年起)、《頭號玩家》(ReadyPlayerOne,2018)這樣的科幻作品來描繪和想象達到技術奇點(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后的賽博身體、世界與藝術。這跟電影批評家安德烈·巴贊(André Bazin)提出的“完整電影”(24)[法]安德烈·巴贊:《電影是什么》,崔君衍譯,中國電影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頁。概念關系密切,卻比它更加長遠。如果說虛擬身體是一種虛擬現實,那么肉身仿擬就是這種虛擬現實從代碼身體出發所邁向的某種終極形態。
不過,非常值得指出的是,肉身仿擬嚴格說來并不是當今標準意義上的后人類立場,因為它歸根結底是人類中心主義的:它確立了一個終極目標,將人自身視作最完滿的形式;技術的進步無非是要逼近這個目標,數字藝術事業的發展也仿佛被坍縮為一個在感官真實性上趨近于無懈可擊的宏大敘事。然而,對藝術來說,這恰恰是需要警惕和反思的事情,因為無盡地追求感知真實可能代表了一種工具理性的、現代性的癥候。
假設我們在賽博世界不是要復刻人的感知模式,而是去改造這個模式,難度反而可能會低許多,因為身體的運行邏輯被簡化了——這也就是“代碼身體”范式。例如,人工智能語音客服的“嘴”不會累,“嗓子”也不會變啞,因為從經濟的(economical)原則來看,程序完全不必提供這樣的復雜性。當然,人工智能的“嗓子”變啞完全可以是科幻電影或喜劇性表演的理想情節——肉身仿擬范式正是滋養科幻藝術的主要范式。
以《攻殼機動隊》(GhostintheShell,漫畫1989年起,動畫1995年起)作品序列中的“番外”系列動畫短片《塔奇克馬的日常》(TachikomaDays,2002年起)為例,人工智能戰車塔奇克馬(Tachikoma)就是對肉身仿擬范式的著名想象[準確地說,它仿擬的是機器人的身體,但后人類視域中人與機器人是同理的,唐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是該立場最重要的代言人(25)可參見Donna Haraway,“A Cyborg Manifesto: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in Manifestly Haraway(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6),pp.5-68.]。《塔奇克馬的日常》專門展現了塔奇克馬們在完全以數字媒介搭建的賽博世界里的生活,調性輕松可愛,創意卻頗為瘋狂,令人忍俊不禁:它們在這里不僅會恐高,還會打噴嚏以及打盹兒,甚至會出現“左撇子”與“右撇子”之分。(26)劉書亮:《塔奇克馬平時思考些什么?——人工智能的日常生活與哲思》,《文藝報》2023年1月6日第8版。
這一系列短片展現出肉身仿擬低效率的一面:大家一起看電視時,一架塔奇克馬竟然會擋住其他塔奇克馬的視線——身體遮擋身體,這倒是非常符合物理空間的運行邏輯,是對肉身仿擬范式的絕佳想象,然而在賽博世界里設計出視線遮擋顯然是“舍近求遠”,嚴重降低了信息的傳播效率,讓賽博空間本該具備的信息傳遞優勢蕩然無存。更甚的例子是,這些塔奇克馬雖然明知數字生命體可以通過傳輸信息(即“拋棄身體”的信息)來直接、高效地溝通,卻仍對自然語言抱有極大興趣,想要“說人話”。不過,它們后來經過討論,終于想明白了一件事:人類自然語言(與身體密切相關)在信息傳遞的準確性方面有較大的局限和損耗。麥克盧漢曾在《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的“口語詞:邪惡之花?”一節中為該論題提供了洞見,指出語言是人的延伸(盡管語言也讓人的官能割裂,這是延伸引發的截除效應,此處他提及了亨利·柏格森來說明這一點);而計算機則超越、繞開了人類的自然語言,通過代碼實現了一種普遍的寰宇意識。(27)[加拿大]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何道寬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00-101頁。如果硬要選擇不繞開自然語言,幾乎可以被視為技術返祖現象。當然,《塔奇克馬的日常》不過是一出科幻喜劇,是一種戲仿與嘲弄,但我們確實可以說,在數字空間里完滿再現肉身的視覺邏輯或語言邏輯的實際價值是存疑的,盡管它已然成為人類藝術想象的重要側面。
電影《流浪地球2》(2023)是另一個值得玩味的例子。該片中,圖恒宇用已故的女兒丫丫生前的數據構造了一個有思考能力與人格的數字生命,雖然僅能通過一塊屏幕跟這個“丫丫”交流對話,但故事中的量子計算機已經有足夠的算力用肉身仿擬范式來展現“她”,所以“她”又顯得無比真實。圖恒宇的肉身即將犧牲時,他把自己的數字分身也接入了量子計算機,由此終于可以給“丫丫”一個擁抱(虛擬身體之間的互動)。而此時,面對圖恒宇生前尚未完成的任務——傳輸密碼并重啟根服務器,數字化了的兩人選擇以“丫丫”口頭逐個背誦數字、“圖恒宇”手動逐個錄入的方式來完成。這一選擇不可謂不低效,但該片正是借助這種低效、笨拙的方式,才令典型的“最后一分鐘營救”式的交叉剪輯得以成立:在千鈞一發之際,“圖恒宇”完成了發動機器的壯舉,同時也“贖了罪”。質言之,這種更加接近我們肉身經驗的身體仿擬范式,雖然實際應用可能會有諸多不便,但在敘事上卻具備得天獨厚的優勢。肉身仿擬并非必要,但人們對其無比迷戀。
六、結語與必要的補充
論述至此,我們有必要對三種虛擬身體的觀念與整個數字藝術生態的關系進行一些總結。第一,互聯網身體以隱喻性的方式體現,它雖不具備傳統肉身的形式,卻塑造著我們的生活與感官,并對數字藝術作品的傳播生態起了關鍵作用。第二,若是追求生命體在賽博空間內的表達方式與人類肉身的一致性,必然要消耗大量的存儲力與算力,今天的創作條件尚不足以實現這種完滿的肉身仿擬。這種范式并不經濟,有時甚至呈現出舍近求遠的笨拙,但它仍然受到科幻藝術作品的格外青睞。第三,“簡異化”的代碼身體在隱喻身體與肉身仿擬之間取得了某種平衡。數字游戲、虛擬現實,還有被塑造為身體景觀的人工智能等,均是其目前最具代表性的藝術應用形態。
值得注意的是,“元宇宙”(metaverse)作為人們對下一代互聯網的典型想象,或許將是數字身體未來的重要應用場所。從身體的維度看,互聯網行業對元宇宙的核心話語實際上正是:我們不滿足于互聯網僅僅以隱喻身體的方式出現;我們希望它全面進化為代碼身體,攜帶人的身體形式,甚至要讓相關技術朝肉身仿擬去努力,讓人無法分清現實和虛擬(這恐怕是最為極端的元宇宙觀)。
而人們在“元宇宙”這個廣袤的賽博世界里的發展,不僅是對其“空間”的“開墾”(如虛擬房產買賣、虛擬辦公室的搭建等,它們與建筑和室內設計有關),同時也是對“生產虛擬身體”這一行為的迷戀:數字人、人工智能等都可能被這個概念包納其中。應該看到,虛擬身體的不斷生產,與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筆下的“空間修復”過程同理,目前是資本對自身危機的一種轉移,(28)參見孫舒悅:《大衛·哈維“時間-空間修復”理論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吉林大學,2022年,第25頁。體現了對價值進行無限攫取的意愿。而同時,數字藝術中那些用于表征身體的技術,也正在引領對未來媒介生活的想象。在傳媒科技不斷發展、人類共同命運也面臨重大選擇的當前,如果說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講的自我技術(technologies of the self)、互聯網上的個人配置(29)參見[法]讓-保羅·富爾芒托等:《數字身份認同》,武亦文、李洪峰譯,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第46頁。或曰自我整飭型勞動都能在(甚至有必要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代碼身體來完成,而交互的過程也會更多地伴有一種游戲化(gamification)的體驗,那么如何更好地在這種環境中實現價值理性的傳遞與引領,讓商業利益更充分地服務于社會利益,讓藝術思維和藝術財富通過計算機美術、動畫、游戲等體裁的敘事與互動造福于現實的人文生態,就無疑都是值得持續開展學術探討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