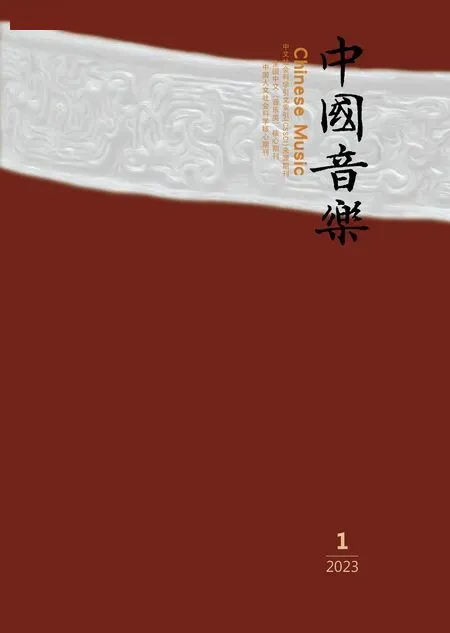實錄型音樂影像文本寫作
○劉桂騰
影視人類學界曾有這樣的觀點:影像志中的“影像不是唯一的手段,寫作也同樣是一個手段”①這里的“寫作”,是與“影像手段”相對的“文字書寫”手段。郭凈:《去做影像志,而不只是紀錄片》,微信公眾號“影音檔案”,https://mp.weixin.qq.com/s/iXLrG68Lo7row3imMAXKBQ,2021年12月3日。。對此,卡爾·海德(Karl G·Heider)持有更為鮮明的學術立場:“影視民族學不能單獨存在。”②這個“影視民族學”實際是指影視人類學的“影視文本”。卡爾·海德指出:“影視民族學不能單獨存在的觀點也許是傳統的電影攝制者所不能接受的,但對于影視民族學家來說,卻是理所當然的… …人們需要了解民族研究和電影拍攝時的具體環境,以及體現在行為之中的文化內容,其中包括許多一般的事實和抽象的概念。通常它們都是文獻性的,而非形象性的。”〔美〕卡爾·海德著:《影視民族學》,田廣、王紅譯,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年,第191頁。乍一看,這個論斷太過直白。不過,如果人們明白這是就民族學(人類學)研究中的影像文本寫作而提出的主張,大概就不會莫名驚詫了。正因為如此,譯者沒有將原著Ethnographic Film直譯為“民族學電影”或“民族志電影”而改譯為“影視民族學”,以突出其“民族學”而非電影技術理論的特點。③李德君:《急待開拓的新興學科—中譯本序》,載〔美〕卡爾·海德著:《影視民族學》,田廣、王紅譯,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年,第3頁。對于民族音樂學/音樂人類學學科框架中的音樂影像志來說,這個主張是適用的—音樂影像志是運用“兩支筆”書寫的多模態“志式”描述性研究。
在音樂影像志的文本類型中,實錄型音樂影像文本以其鮮明的學術性和紀實美學特色而獨居一席。與著眼于公共文化平臺民族志知識傳播的影像創作不同,實錄型音樂影像文本是以調查人為主導、以“保存”(文獻典藏、活態傳承)和“利用”(學術研究、文藝創作)為旨歸、具有文獻遺產價值的音樂民族志寫作。
一、音樂影像文本的“文獻遺產”價值
音樂影像志學科對象的特殊性在于:“音樂建構并利用生產音響的器物,使用身體去生產及拌合聲音。”④〔美〕安東尼·西格爾:《蘇亞人為什么歌唱:亞馬孫河流域印第安人音樂的人類學研究》,趙雪萍、陳銘道譯,陳銘道校訂,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2年,第Ⅴ頁。記錄“使用身體生產”的音樂現象,無疑是視聽影像描述方法最為擅長的領域。然而,“音樂”自身結構形態(旋律、曲體結構、調式調性、節奏節拍等)的特殊性,決定了實錄型音樂影像文本的寫作不能排除文字書寫手段。它需要以影像符號與文字符號組合形式,通過多模態文本的互文⑤劉桂騰:《多模態表演話語分析方法》,《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22年,第3期,第53-59頁。實現其“文獻遺產”價值。所以,實錄型音樂影像文本,是由鏡頭語言與文字符號共同構成的多模態音樂文本類型。它是一種文字與影像組合互文的多模態“志式”文本結構:影像模態提供了視覺形象與聲音數據,據此轉譯出來的文字符號則提供了可視化的文字/譜式文本。二者通過“互文”方式,共同完成實錄型音樂影像文本的建構。
二、作為“文獻遺產”的音樂影像文本
實錄型音樂影像文本的“文獻遺產”特征,集中體現在注重音樂事件描寫的完整性。即使是后期用于學術交流與分享的實錄型音樂影像文本,在縮剪的過程中也要保持其音樂(舞蹈)敘事的相對完整。如果剪輯者不具“音樂”專業背景,就可能在非編過程中偏重畫面“內容”而犧牲音樂描寫的完整性。在音樂影像志實錄型文本的寫作中,這是個十分突出的問題。日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旅游部、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網、國家圖書館中國記憶項目中心等單位主辦的“非遺影片展映”活動,展映了115部《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記錄工程》“綜述片”。根據承辦方對該項目的宗旨和意義的闡釋,對非遺的影像記錄的目的是“用影音多媒體記錄的方法保存下來,變成國家文獻系統中重要的文化文獻遺產,并讓這些文獻服務于非遺的研究與傳播,反哺、反饋于非遺的活態傳承”⑥在《影音邂逅非遺 煥發全新活力》一文中,國家圖書館中國記憶項目中心副主任田苗認為:“對這些非遺代表性傳承人的記錄工作,是非遺保護的一個重要基礎性工作。把他們身上承載的文化記憶、文化觀念、文化技能和傳承教學手段,用影音多媒體記錄的方法保存下來,變成國家文獻系統中重要的文化文獻遺產,并讓這些文獻服務于非遺的研究與傳播,反哺、反饋于非遺的活態傳承,才能夠讓非遺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中不被丟下并煥發出全新生命力。”牛夢笛:《影音邂逅非遺 煥發全新活力》,轉載于文化和旅游部官方政務新媒體平臺“文旅之聲”,https://mp.weixin.qq.com/s/RgAc06W4ncVPhdFZ6kJubA,2022年7月14日,原載《光明日報》。。由此可見,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基礎,實錄型音樂影像文本具有作為文獻遺產“存證”的價值。遺憾的是,已經掛網展映的許多非遺“綜述片”(“樂舞”單元)似乎并未達到這個學術要求。盡管“綜述片”因篇幅所限需要大量縮剪,但作為針對“樂舞”的一種實錄,其音樂、舞蹈語言表達的相對完整理應得到保障。雖然在30分鐘篇幅內不可能囊括采訪的全部內容,但是,如同人物的語言表達,一句話的意思表達必須完整。這一點,似乎從來沒人出錯。大概是因為漢語口語的表達(包括字幕)幾乎人人都能夠辨識其正誤。音樂、舞蹈語言的表達同樣如此。雖然不必一定要把一首樂曲或舞段完整呈現出來,但是,一個樂句或舞匯的完整意義不可肢解。語言表達需要符合語法,樂舞的呈現同樣要遵守音樂、舞蹈的敘事邏輯。這樣一來,縮剪過程中剪切點的選擇就必須考慮旋律、曲體結構和節奏節拍等元素,應該在符合音樂舞蹈語法規則的前提下進行裁切和轉場。否則,這種實錄型音樂影像文本就喪失了文獻遺產價值。即使是面對公眾的綜述性“非遺宣傳片”,也應堅持音樂民族志知識的基本規律。或許,從“宣傳”的角度來看這些綜述片已經達到了目的;但若從音樂民族志知識“傳播”與“活態傳承”的要求來看,這些專業的技術性問題就不能忽略不計了。這是由實錄型音樂影像文本作為“文獻遺產”的屬性所決定的,即使是經過“二次開發”用于文化傳播、交流場景的影像文本也不應例外。
實錄型紀錄片拍攝團隊的專業知識結構,是音樂影像文本學術性的重要保障。20世紀50年代開始組織攝制的“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科學紀錄電影”,多在攝制團隊中設置“民俗顧問”“學術指導”職位;“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記錄工程”項目,也專門設置了“學術專員”一職。顯然,這些職位的設置都是出于保障實錄型影像文本學術價值的措施。
實錄型音樂影像的攝錄往往不采取擺拍方式,而是在音樂事件的動態過程中進行拍攝。所以,現場對表演者音樂行為記錄的準確性就顯得格外重要。若不能掌握各種樂器的器型、音色特征,就很難迅速、準確抓取到表演者的鏡頭,以致出現手忙腳亂或張冠李戴的問題。若要做到這一點,攝錄者就須有相應的音樂專業訓練。但在大量的非遺保護項目的實錄中,團隊組成人員—拍攝、錄音、剪輯等生產要素的專業結構問題似乎仍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只有具備相應專業背景和技術能力的音樂影像志生產機制,才能使實錄型影像文本的“文獻遺產”價值真正得到保障。
三、以“調查人”為主導的生產機制
如果將民族志紀錄片的生產方式從宏觀上分為虛構的創作型影片和非虛構的實錄型影片,虛構與非虛構紀錄片的產生各有其相應的生產機制。創作型紀錄片是以“導演”為責任人、以文學腳本為藍本而形成的影像文本;而非虛構的實錄片“是在田野數據采集、整理過程中形成的影像文本:田野先行,無腳本,以‘調查人’為核心組成團隊。實錄型影像文本并非由拍攝主體的‘劇情’設計而成。倘若有什么‘劇情’的話,那也是出自客觀對象自身的文化形態本身而非由電影導演‘編導’出來,譬如某些地方戲曲、曲藝的實錄,非遺項目的錄制尤其如此”⑦劉桂騰:《鏡頭是學者的眼睛—音樂影像志范疇與方法探索》,《中國音樂》,2020年,第2期,第20頁。。雖然影像創作也需田野作業,但那是為寫腳本而做的“體驗生活”,與實錄型影像文本相比還是融入了更多的主觀意圖和審美訴求。
由此可見,“‘調查人/導演’不是一個簡單的稱謂問題,它反映了當下人們對紀錄片‘真實性’問題的不同認識;是民族志影片的兩種責任機制和不同的學術理念”⑧劉桂騰:《鏡頭是學者的眼睛—音樂影像志范疇與方法探索》,《中國音樂》,2020年,第2期,第20頁。。作為兩種民族志知識的生產責任機制,田野實錄實行“調查人制”而不是“導演制”。主持現場工作的“調查人”無需對事件進程進行調度,更不能“導演”文化持有人的行為,而是指揮拍攝團隊、協調各工種間的配合,通常還要親自承擔其中一項工作(攝影或攝像)。調查人對整個作業項目負責,把握現場機位布局以及音樂影像數據的采錄重點和主要內容選擇的方向,掌控現場的總體工作量和工作進度,還包括人員分工、經費使用、協調與當地人的關系,等等。
四、同期聲與長鏡頭“連續拍攝”的原則
在以調查人為主導的實錄型音樂影像攝制中,走同期聲與長鏡頭“連續拍攝”的技術路線是個行之有效的路徑。
音樂影像文本同期聲的主要內容,包括音樂(演唱、演奏、吟誦)、言語(神喻、咒語、誦讀、對話、解說)、環境(鞭炮、交通工具、雞鳴狗叫、風雨雷鳴及人群的嘈雜聲)等。在田野錄音中,同期聲是主要的錄音方式。同期聲是實錄型音樂影像文本“文獻遺產”價值的重要因素,因而對錄音設備和錄音師都有較高的專業要求。在實錄型音樂影像文本的拍攝團隊中,專設錄音師職位是必要的,也是由音樂影像志的學科屬性所決定的。許多人不以為然,以為攝像機上的同步錄音設備就能夠滿足需要了。但專門以“音樂”為對象的音樂影像志作業,不重視影像數據采集的錄音環節是令人費解的。讓我們聽聽讓·魯什對錄音問題的看法:“我們必須正確評價真正起作用的音樂,無論它是褻瀆的還是宗教儀式的,也無論它是工作的節奏還是舞蹈的旋律。我還必須提醒各位注意的是同聲電影的手法應該屬于民族音樂學。”⑨〔法〕讓·魯什:《攝影機和人》,載〔美〕保羅·霍金斯主編:《影視人類學原理》,王筑生、楊慧、蔡家麟等譯,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89頁。顯然,讓·魯什認為同期聲錄音并不僅僅是個技術活,錄音師還該受過民族音樂學的專業訓練,應該具備專業音樂知識。同理,音樂影像志的錄音者也應掌握相應的專業錄音技術。音樂院校音樂學的學生都會有音樂理論與表演的專業背景,以他們對聲音的理解力和專業知識,受過一定技術訓練便可勝任錄音工作。但在田野錄音環節中容易出現的問題是,受任者往往因為自己“懂音樂”而輕視了錄音的重要性。例如,在一場儀式音樂數據采集中,尤其是在一個固定位置工作就會感覺非常乏味。如果不注意觀察電池的續航狀態,就可能發生在錄音過程中斷電的事故,嚴重影響錄音質量甚至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再如,錄音者如果不了解話筒的指向性就不會進行適當的設置,或者在現場無法掌握正確的拾音方向,最終導致錄音質量和效果大大降低。另外,與攝像配合的同期聲錄音,既要明確錄音與攝像的“主從”工作關系,也要有自己的主動性,按照攝像的意圖,主動尋找合適而又不與攝像相脫節的音源位置。這樣,雙方才能配合默契達到理想的合作效果。盡管在音樂影像志田野作業中錄音不是一個獨立工作環節,但需要錄音者具有極強的責任心和協作精神。
在田野后期的影像數據處理中,一些剪輯師為了“好聽”——出于個人審美偏好而破壞了音畫之間的時序關系,是實錄型音樂影像文本寫作中常見的問題。我們并非全然排斥非編中聲音蒙太奇手法的使用,而是強調剪輯者要堅持實錄型影像文本的學術性,保持其“文獻遺產”價值。再“好聽”的聲音也替代不了同期聲本身的學術價值,何況,好不好聽的審美標準并不該由局外人來決定。為增強影像文本的聽覺效果,實錄型音樂影像文本除了同期聲外,有時也會加入“音效”(鐘鈴、流水、腳步、交通工具的聲音等),以增強影像文本的感染力,但要慎用。在音樂影像志文本中,為避免破壞同期聲的真實性,一般不在音樂事件進程中使用音效,通常是片頭或片尾中適當插入音效。
與蒙太奇一樣,長鏡頭也是基礎性的影像思維方法。長鏡頭流派的電影理論家認為:“長鏡頭能保證電影時間與電影空間的統一性和完整性,表達人物動作和事件發展的連續性和完整性,因而能更真實地反映現實,符合紀實美學的特征。”⑩許南明、富瀾、崔君衍:《電影藝術詞典》(修訂版),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18年,第155頁。不難看出,“連續拍攝”原則與作為文獻遺產的實錄型影像文本的攝制要求十分契合。但是,從音樂影像志田野作業的角度來看,是把“連續拍攝”原則作為方法論的內核而非視為一個具體的拍攝手法。具體講,所謂“連續拍攝”是指音樂事件整體進程的連續性而不是某一事件片段拍攝的“一鏡到底”。亦即,在音樂行為和事件過程的實錄中,要保持聲音本體描述(器與器聲、同期聲與環境聲音等)和行為主體描述(表演與肢體動作等)以及事件進程描述(儀式與表演的時序等)的完整性。為實現現場記錄的完整性,拍攝者在田野拍攝中要遵守長鏡頭“連續拍攝”原則,在事件進程中進行不間斷的拍攝。這與由導演設計、演員表演和各工種聯動而實現的“長鏡頭”不是一回事。調查人的主要工作,只是根據拍攝內容和地點的現場條件進行合理的機位配置和布局。如果是單機位作業,可能需要移動機位。雖然攝像師的移動過程可能會產生一段廢片,但錄音部分仍會保持時間的連續性。
田野作業的影像記錄工作從來就不會有一種萬全之策,只能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但,無論如何也要堅持“連續拍攝”原則。當然,文如看山不喜平,強調完整描述并不意味著平鋪直敘,實錄型音樂影像文本也不是一本簡單的田野“流水賬”。
五、影像數據的轉譯與音樂學分析
雖然實錄型音樂影像文本的價值并不局限于“文獻遺產”,但它的應用場景主要還是在學術領域,如教學、科研、講座、展映活動和學術研討會等。其中,用于音樂學分析的實錄型影像文本,因其自身的特殊性—需要將影像文本中的“音樂”信息轉譯為對象化的文字或譜式。由于影像方法的局限性所致,有些田野作業信息無法通過影像手段來描述。因此,需要將把影像文本無法以書面符號形式傳達的音/視頻信息轉譯為譜式文本或文字文本。
(一)轉譯為譜式文本
譜式符號模態的轉譯,是將影像中的音樂數據對象化為可識讀的譜式符號形式,譬如,以音樂符號描寫形成的靜態化樂譜、以波形圖曲線描寫形成的動態化頻譜等,本文將其統稱為“譜式文本”。限于篇幅,我們只討論影像模態轉譯為樂譜的方法。
記譜是音樂學分析的基本功。作為音樂形態分析對象,將田野采錄的歌曲、樂曲的音頻記錄轉譯為樂譜,是田野影像數據后期處理的必備工序。譜例除了用于音樂形態分析,還可用于學術著述的發表和出版中。把影像文本中的音樂內容轉譯為樂譜是個專業性很強的操作,需要受過音樂理論和記譜訓練的專業研究者來做。當然,任何轉譯都不可能替代影像文本中原始聲音記錄。記譜只是為了將相關的音頻數據轉譯為可視化的譜式文本,以為音樂形態分析之用。將影像文本與譜式文本結合起來進行音樂形態分析,是通過感官體驗的對象化實現對聲音意義分析與闡釋的學術研究過程。因此,將影像記錄的音樂行為轉譯為符號化譜式文本具有方法論意義。
在記譜實踐中,記譜者常常陷入“牛角里的兩難”境地:究竟是以詳細記譜還是簡明記譜方式為好?用一個語言學的類比,或可將譜式文本的繁簡之別視為國際音標標音法中的“嚴式”與“寬式”之分;前者以嚴格的“音素”(音腔)區別來標音,而后者則以能辨義的“音位”來標音—將聲音的變化穩定在記譜者的樂感判斷位置(骨干音)上。這樣一來,記譜者本己文化熏陶、訓練出的聲音判斷就會與異己文化的慣習產生差異,即所謂的“雙重樂感”。記譜者應該盡量取局內人的視角,提高自己的雙重樂感能力。
查爾斯·西格(Chares Seeger)曾將記譜法分為“規定性記譜”與“描述性記譜”兩種:“用規定性記譜法的記譜者通常只記下了解該風格的當地人需要知道的東西。… …描述性記譜法則試圖對一部作品的某次表演做出徹底而客觀的記錄。”?〔美〕布魯諾·內特爾:《民族音樂學研究:31個論題和概念》,聞涵卿、王輝、劉勇譯,湯亞汀校訂,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2年,第69頁。譬如,一位古琴演奏家根據“規定性”的琴譜演奏,因其掌握古琴的演奏技法并熟諳其風格特征,所以能夠在譜面音樂符號“梗概”的提示下理解并進行演奏。這是用于表演的“規定性”樂譜。而對于一位研究者來說,則需要對琴家的某一場演奏進行詳細而完整的記錄。這是以譜式文本記錄聲音實況并用于學術分析的“描述性”樂譜。我們在此不是專門研究記譜法,只是試圖尋找一個具有實踐意義并具可操作性的影像模態轉譯方法。規定性記譜和描述性記譜方法問題的核心,是“繁和簡”如何才好這個令人兩難的問題。如果取一個中庸、平衡的辦法,就是將二者結合起來,采取先簡后繁、繁簡結合的記譜方法。以節奏型記譜的步驟作為例:首先,由“拍”到“節”:先記分值(拍子),然后劃小節(單位);繼而,由“粗”到“細”:橫向進行—先憑樂感粗記(節奏型);縱向進行—再記細節(聲部)。
對于一些僅憑聽覺難以判斷的節奏,可以通過多模態話語分析方法進行綜合判斷,并以聚合型的譜式文本呈現。譬如,使用Adobe Audition等能夠可視化處理音頻的工具,在頻譜圖界面中同時檢視視頻和轉換為頻譜形式的音頻文件,通過計量化的波形圖與視頻中的表演動作,再結合聽覺的樂感來記譜。最后,將影像、樂譜、頻譜聚合為一種多模態聚合型的文本形式(見圖1)。這種描寫方法在一些可視化音樂分析中并不鮮見。但由于學術分析目的不同,我們格外強調影像元素的必要性。雖然目前在紙質媒介(期刊、著述)中還無法實現動態影像呈現(只能以照片形式替代),但在電子演示文稿之類的數字化熒屏媒介中,音視頻與頻譜和樂譜的同步呈現已無任何技術障礙了。所以,將影像元素作為譜式文本的必備要件具有現實的可行性。

圖1 熱貢魯若(六月會)—《喂哈》,黃南藏族自治州同仁縣四合吉村,2017年
利用這種聚合態的譜式文本進行音樂民族志的田野描寫,可以立體、多維地呈現田野現場的觀察結果。就實錄型音樂影像文本寫作而言,將影像中的音樂數據對象化—轉譯為可識讀的譜式符號形式,比單一的影像或文字符號更易于識讀和進行音樂分析。
(二)轉譯為文字文本
就音樂影像志研究而言,通常都要將實錄型音樂影像文本中的口述或對話的內容轉譯為文字文本。譬如人物采訪記錄,一般都是通過轉譯為“逐字稿”來做學術分析。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與奧地利國家音響檔案館聯合考察項目“蒙古族民歌”的轉譯,可作為音頻轉譯的范例。?蕭梅:《音響的記憶—田野錄音與民間音樂檔案》,載《田野的回聲—音樂人類學筆記》,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15頁。這種影像文本的整理,不僅把音頻信息保留在原始記錄中,還將聲音以文字形式“轉譯”為可視化的文字模態文本。將田野訪談的影像記錄轉譯為文字并不是個簡單的事,既枯燥又有相當的難度,有時還需要熟悉民族語言。有些方言較重的民族語言,可能還需要回訪被訪談者才能正確記錄下來。
影像數據轉譯的內容,主要包括音樂事件中的人物、器物、聲音和人文、地理等信息:
器:響器名稱、材料、尺寸及功用等
聲:器聲與人聲名稱、聲音形態特征等
身:表演行為名稱及基本特征等
禮:信仰、儀式名稱及基本特征等
史:歷史沿革、傳承譜系等
地:地名、山川風物概述等
人:人名、親屬關系等
影像數據的轉譯并非簡單的“翻譯”,而是對影像文本相關內容的解釋和補充。對這些通過訪談記錄下來的影像數據進行轉譯,是要將影像模態無法清晰傳達給觀眾的內容(時間、地點、人名、族屬、年齡、器名和樂種名稱、親屬關系、宗教信仰等)做出必要的“注釋”,通過字幕、畫外音的形式將視覺內容與特定的時空關系“錨定”?法國符號學家R.Barthes曾經歸納了圖文并用結構關系的三種模式:“錨定(anchorage),文本支持圖像;說明(illustration),圖像支持文本;接遞(relay),圖文互補。”轉引自曾方本:《多模態符號整合后語篇意義的嬗變與調控》,田海龍、潘艷艷主編:《多模態話語分析:理論探索與應用研究》,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83頁。下來。同時,從音樂影像志的學術指向來看,文字與譜式模態數據,既可作為音樂影像志檔案文獻的有機組成部分,也可為音樂學的研究提供可識讀的分析對象。
六、多模態的實錄型影像文本
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第二屆華語音樂影像志展映”的獲獎作品中無一例實錄型影像文本入列,這個結果是完滿中的遺憾。其原因,一方面,大多實錄型音樂影像文本的確缺乏影像技術含量與視覺表達技巧;另方面,是否還存在忽視影像文本作為“文獻遺產”價值的傾向?音樂影像志的發展是否需要一個多元、平衡的學術評價體系?
(一)“學術的”抑或“藝術的”
如果將音樂影像文本類型的失衡問題引申到關于民族志紀錄片是“學術的”還是“藝術的”長期爭鳴中,也許能夠從宏觀上找到問題的癥結。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格里高利·貝特森(Gregory Bateson)曾經圍繞是否使用“三腳架”展開了激烈的爭辯,集中反映了影視人類學界的不同學術傾向。貝特森認為影像記錄應當是一門藝術,而米德則批評“藝術論”者“往往在追求藝術制作時忽略了對情節的忠實。這種過分的要求一直占據著電影界。而與此同時,很多文化沒有得到記錄便消亡了。”?〔美〕瑪格麗特·米德:《文字訓練中的影視人類學》,載〔美〕保羅·霍金斯主編:《影視人類學原理》,王筑生、楊慧、蔡家麟等譯,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5頁。今天看來,她將民族志紀錄片僅僅視為“客觀記錄”的確有所偏頗,影像志也不該被絕對的“真實”綁架而止步于“客觀記錄”。但她對影像文本“文獻遺產”價值的認識仍具現實意義。對于實錄型音樂影像文本的寫作來說,尤其如此。
卡爾·海德持堅定的民族學(人類學)立場。他針對影像文本“失真”問題所開出的藥方是:“如果這些影片是專為民族學研究制作的,那么就必須以輔助性文字材料對影片中的失真問題進行解釋,并就失真的程度進行說明。”?〔美〕卡爾·海德著:《影視民族學》,田廣、王紅譯,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年,第121頁。雖然他所給出的解決辦法有些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味道,卻也老老實實道出了影像文本在某些方面力乏難竟的實情。如今,已經沒人天真地相信民族志的絕對真實,但是,民族志的相對客觀性是存在的。最大限度逼近事實真相,依然是民族志的學術追求。其實,“即使那些致力于超越‘科學證據’功能的情感體驗的優秀影像文本,也是建立在‘客觀記錄’的基礎之上,具有鮮明的紀錄美學風格特征”?劉桂騰:《摹寫·建構·復原—音樂影像文本的生產方式與真實性》,《中國音樂》,2022年,第2期,第104頁。。無論“學術/藝術”的爭鳴抑或“失真”問題的討論,說到底就是對民族志紀錄片“真實”問題的認識分歧。民族志紀錄片的事實必須是真實的,否則,就不能稱其為紀錄片。這一點,應該是業界的通識;然而,對于究竟什么是民族志的“真實”,可就有不同的理解和主張了。從弗拉哈迪的紀錄片奠基之作《北方的納努克》問世以降,關于民族志電影的“真實”問題就成了學科史的一個永恒主題。后現代新銳們對經典民族志的反思與批判,將分歧和爭鳴推上了高峰。
民族志紀錄片的“真實”不存在嗎?
我們不妨將紀錄片的“真實”視為拍攝主體與文化持有者達成的一份民族志“婚約”—由“生活的”和“學術的”事實所構成的默契。即,這份“真實”是拍攝主體與其對象共同建構的一種事實:“生活的”事實,是在文化持有者現實生活中真實存在的事件。其對象、地點及時序是非虛構的事實并具可驗證性。一些所謂的“非遺項目”之所以被詬病,就是因為它們不是現實生活中的一部分。而“學術的”事實,則是由調查人(拍攝主體)書寫的民族志敘事。“學術的”事實要符合“生活的”事實要件,但“由于‘學術的事實’里也會帶入研究者的主觀因素,所以,田野人應該具備相應的學科訓練和符合田野倫理的職業操守,不能任意擺布田野對象,不能以‘共謀’之名編造事實;尤其是田野作業拍攝的環節中,不能預設、操控田野事件發展的進程”?同注?,第102頁。。亦即,“生活的”事實是由現實社會層面的客觀存在而定,而“學術的”事實則由道德層面的學術倫理所限。二者相互制約,共同建構了民族志紀錄片的真實性。進而,形成了民族志的紀實力量。舍此,也就失去了民族志之所以為“志”的基本屬性和特質。對了,用“真實性”這個詞來表述我們對于“真實”的訴求,或許更顯寬容且易于理解。就此而言,真實性也是音樂影像志寫作必須堅守的學術底線。
(二)“兩支筆”的多模態話語寫作
在影像志的文本建構中,出于“客觀記錄”需要的學術性文本類型依然具有現實意義。只是,創作型與實錄型影像文本應置于不同音樂影像志知識生產機制中來建構。如是,人們就不必糾結諸如“三腳架”“失真”的問題,而應當承認所有民族志書寫形式都有其難以克服的短板,從而以多模態話語方法進行實錄型音樂影像文本的寫作。
從學科史的角度來看,影像描寫從“客觀記錄”到“學術表達”并非顛覆性的范式轉型,而是因應時代發展之需的代際擴容。亦即,民族志的“客觀記錄”功能依然沒有過時,而是將影像數據信息由文字模態語篇的“附件”升級為具有獨立表達能力的實錄型影像文本。海德的“影視民族學”研究,就曾運用文字與影像模態兩種文本形式呈現田野調查成果:“由加德納和我本人寫的與《死鳥》一片相配套的民族學著作,就是沿著這個方向邁出的一步”?同注?。。但,我并不認同其出于“以輔助性文字材料對影片中的失真問題進行解釋”的動機。不同模態文本間并非誰依附于誰,而是形成不同模態文本之間互文的關系。以本人科爾沁蒙古薩滿祭祀儀式田野調查為例,最終完成的田野作業成果,除了影像模態文本《絕響:色仁欽的塔拉亨格日各》,還有文字模態文本《搭巴達雅拉—科爾沁蒙古族薩滿“過關”儀式音樂考察》。?劉桂騰:《搭巴達雅拉—科爾沁蒙古族薩滿“過關”儀式音樂考察》,《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06年,第1期,第43-57頁。這是針對同一田野作業對象,以多模態話語方法完成的音樂影像志寫作,而不是將文字文本僅僅作為影像文本的“輔助性文字材料”;反之亦然。就音樂學的研究而言,音樂影像志該是“兩支筆”的多模態話語寫作。而當下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是:實錄型音樂影像文本的寫作,如何能夠在保持“文獻遺產”價值的同時提升其影像技術含量,使之能夠以豐富、專業的視覺表達形式為音樂學的研究以及知識生產、傳播及傳統音樂的活態傳承服務。解決這個問題,尚需音樂學同仁虛心向影視人類學、電影學等相關學科請益,進行更多、更深入的理論探索與田野實踐。
在我看來,民族音樂學/音樂人類學理論框架中的音樂影像志,應堅持以實錄型影像文本為基礎,借鑒跨學科的有益經驗,構筑文本類型多元、平衡發展的格局,從而形成一個具有自身特色的音樂學新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