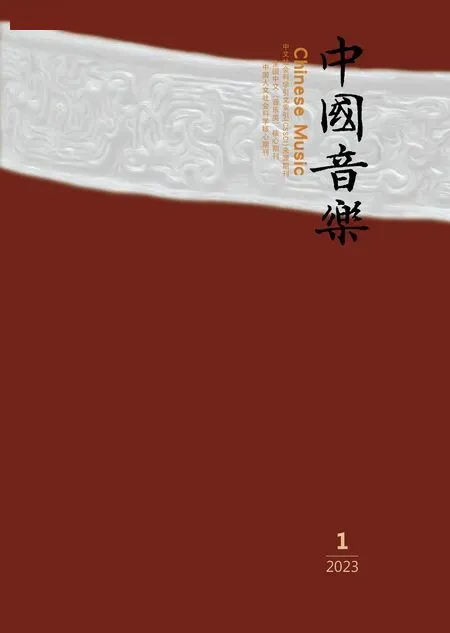音像志學基礎理論①
○鮑 江
你認識哪個伊洛魁聯盟的人嗎?不認識
你認識哪個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嗎?不認識
你認識哪個開弦弓村的人嗎?不認識
你認識哪個努爾人嗎?不認識
你認識哪個憂郁的熱帶的人嗎?不認識
你認識哪個巴厘島的人嗎?不認識
… …
我們做音像志吧,一個一個地去認識他們
去認識他們各自的生活世界
—題記
前 言
音像志是音像與志相結合構成的一個學術領域,它包含兩個部分,即音像為本體的片子制作和文字為本體的片子制作研究文本寫作。音像志是影視人類學的普遍化擴張形式,是民族志電影作為方法和目的從人類學擴張至人文社會科學全域的具體表現。
影視人類學是人類學與電影交叉形成的學術領域,20世紀50年代以來逐漸在各國興起,70年代拓展到電視領域,90年代以來再拓展到數字音頻視頻領域。②鮑江:《多點起源到交流互鑒:影視人類學70年的一個視角》,《民間文化論壇》,2021年,第6期,第33-37頁。影視人類學遵循音像學術的一般規律,包括片子制作和片子制作研究文本寫作兩部分,人類學片子又稱作民族志電影、影像民族志、音像民族志等,他們能指不一,所指則是一致的,即長期田野工作的片子制作成果。
按成果指向,現代文科學術可分作兩類:片子制作類和文本制作類,前者以音像作為本體用鏡頭制作片子表達自身,后者以文字作為本體用文字寫作文本表達自身。片子制作類學術是新興領域,始于1895年。第一個制作民族志電影的人是費利克斯·路易斯·勒尼奧(Félix-Louis Regnault),他是一位專門研究病理解剖學的醫生,1888年左右對人類學產生興趣,那年,“計時攝影術”的發明者朱爾斯·蒂安·馬利(Jules étienne Mare)向法國科學院展示他使用賽璐珞膠片的新攝影機。1895年春天,勒尼奧在馬利的助手查爾斯·孔德(Charles Comte)的協助下,拍攝一位沃洛夫婦女在西非博覽會上制作陶器的鏡頭。這部片子展示沃洛夫制陶方法,一只手轉動淺槽底座,另一只手塑形。勒尼奧稱,他是第一個注意到這種方法的人,這種方法說明不使用輪子制陶到古埃及、印度和希臘使用原始水平輪子制陶之間的過渡。他寫了他的實驗,包括從影片中摘取的幾幅線描圖,于1895年12月出版;就在同一個月,盧米埃爾兄弟首次公映“電影”(cinématographe)片子,那是一次成功的商業實驗,開創了電影工業。③Emilie De Brigard.The History of Ethnographic Film.Principles of Visual Anthropology.Second edition.Paul Hockings ed.,Berlin:Walter de Gruyter &Co.,1995,p.15.
片子制作類學術百余年歷史里,先后出現三種模態:影院電影、電視片和網絡視頻。在影院電影獨尊的時代,片子制作歸屬于藝術。電視興起后,片子制作的歸屬變得模糊。影院電影片子制作繼續歸屬于藝術,電視片子制作涉及廣闊的社會生活面,藝術的框子似乎容不下,于是另立傳媒類別,把電視片子制作和電視片子制作研究文本寫作放在它里面。網絡視頻于21世紀初伴隨社交媒體興起,打破片子制作的專業壟斷,片子制作和分享變得前所未有的普及。
影視人類學自其興起就一直在文本制作類文科學術部門里,相關學者在文字學術的海洋里如同遠帆孤影,在邊緣潛心打磨人類學與音像交叉創新的可能性。按21世紀網絡視頻催生人文社會科學與音像交叉創新的廣闊視角,影視人類學即彰顯其獨一無二的先鋒價值。這一點是音像志學科建構以影視人類學為基礎的邏輯所在。長期田野工作是人類學方法利器,從中發展出來民族志文本和民族志電影兩種成果。“長期田野工作+民族志文本”實際已跨出人類學成為一種普遍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長期田野工作+民族志電影”作為研究方法,也指向在人文社會科學中的普遍適用性。按民族志文本和民族志電影跨出人類學與民族學場域、成為人文社會科學普遍方法的語境,“民族”這個前綴顯得累贅,不如取消,迭代為“文本志”和“音像志”這兩個名副其實的術語。④我曾撰文提出音像志的初步構思。鮑江:《音像志初探—兼評三個相關課題》,《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期,第62-69頁。
一、20世紀的影視人類學理論建構
音像志接續并發展影視人類學在學術史上積淀的理論探索成就。音像志的研究范圍,與影視人類學一脈相承,聚焦片子制作及其研究文本寫作。音像志的研究取向,超越影視人類學早期主流的作為文字人類學輔助工具的監控攝像頭式無剪輯客觀記錄影像的學術定位,一脈相承影視人類學早期居于邊緣后來逐漸確立其主導地位的不是復制現實而是創作“真實電影”(Cinéma Vérité)的獨立學術定位。
19世紀末自電影誕生即作為田野記錄工具應用于人類學研究,人類學家要求電影制作者保存所有素材,而不是將其“剪輯”成“片子”。⑤Colin Young.Observational Cinema.Paul Hockings ed.,Principle of Visual Anthropology.Second edition.Berlin:Walter de Gruyter &Co.,1995,p.100.直到20世紀50年代,民族志電影才成為一個制度化的科學領域,擁有公認的專家和評論圈。⑥Brigard 1995,p.14.真實電影是讓·魯什(Jean Rouch)與埃德加·莫蘭(Edgar Morin)合作片子《夏日紀事》(1961年)提出的一個民族志電影術語,指表現攝影機介入條件下拍攝者與非演員影片主體真實相處的片子。《夏日紀事》是民族志電影的一道分水嶺。在它以后,一切都不可能再是老樣子。影片中,電影制作者與他的影片主體之間那堵看不見的墻倒塌了。⑦Young 1995,p.112.導演讓·魯什與埃德加·莫蘭出鏡出聲,與影片主體一道在鏡頭前展示他們的生活世界。受真實電影啟發,觀察電影開創旁觀記錄并表達拍攝對象為主旨但在片中略微提示拍攝者在場的片子模式,譬如片中剪入片中人與鏡頭后的拍攝者對話的幾個鏡頭。觀察電影由科林·楊(Colin Young)、保羅·霍金斯(Paul Hockings)等發軔于20世紀60年代末,后來逐漸發展成為民族志電影主流。
1975年《影視人類學原理》⑧Paul Hockings ed.,Principles of Visual Anthropology.Second edition.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Co.,1995.(下文簡稱為《原理》)問世,它后來證明影響巨大。它匯集1973年在芝加哥舉行的第九屆人類學與民族學大會的多篇論文。這本書標志著民族志電影迭代為影視人類學,后來成為影視人類學這一分支學科的奠基石。它的銷量很大,1995年,它的主編保羅·霍金斯出版了經過大量修訂和擴充的第二版。⑨David MacDougall.New Principles of Visual Anthropology.The Corporeal Image: Film,Ethnography,and The Sense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p.265.《原理》英文原名Principles of Visual Anthropology。此前另有一本首版于1967年的專著同樣以Visual Anthropology這個術語作為主標題,即約翰·柯里爾(John Collier)和馬爾科姆·柯里爾(Malcolm Collier)合著的《視覺人類學:照相作為研究方法》(Visual Anthropology:Photography as a Research Method)。⑩John Collier,Jr.and Malcolm Collier.Visual Anthropology:Photography as a Research Method.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Albuquerque: Th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86,p.160.Previously published by 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67.據保羅·霍金斯,柯里爾那本書是第一次使用Visual Anthropology這個術語作為書名。?據保羅·霍金斯2021年7月5日給鮑江的電子郵件。特別感謝保羅·霍金斯。《原理》的問世重新定義Visual Anthropology這個術語,把它的核心所指從照相轉向民族志電影。1988年有學者把Visual Anthropology這個術語翻譯為影視人類學引介到中文學界。?于曉剛、王清華、郝躍駿:《影視人類學的歷史、現狀及其理論框架》,《云南社會科學》,1988年,第4期,第71-81頁。
在許多方面,《原理》是對當時影視人類學的混亂與確定兩方面狀態最好的總結。它站在十字路口上,一條路是繼續尋求自然科學精確性的人類學,另一條新路是正在努力通過寫作也通過諸如攝影和電影的新方法浮出水面的關于社會經驗的人類學。?David MacDougall.New Principles of Visual Anthropology.The Corporeal Image: Film,Ethnography,and The Sense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p.265.《原理》可辨析出一些普遍原理或者說假設。一是當時影視人類學這個新興領域幾乎完全是從民族志電影的角度來構思的。影視人類學家應該自己使用電影,或者研究其他人制作的電影。除了個別例外,影視人類學也沒有被構思為人類學的一種獨特的視覺形式,影視人類學僅僅被構思為影視技術嫁接到既有的人類學實踐上。《原理》中電影概念基本上被認為是現實主義的和工具性的。如果人類學家著手制作電影,他們被認為是在為日后分析做記錄,或者試圖用影片給尚未入門的學生教授人類學。電影制作要么被認為是一種收集數據的方式,要么被認為是一種生產精確的現實復本的方式。在第一種情況下,人類學主體工作將在以后進行,屆時電影素材將提交分析。在第二種情況下,著手拍攝時人類學主體工作業已完成,電影的目的僅僅是展示既有的知識體系。闡述上述方法的作者包括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讓·多米尼克·拉茹(Jean-Dominique Lajoux)和蒂莫西·阿什(Timothy Asch.)。個別像讓·魯什(Jean Rouch)和馬克·麥卡蒂(Mark McCarty)那樣對人類學電影抱有別樣目的的奇人,在《原理》中也被給予一席之地,但《原理》占主導地位的觀點是,電影制作是一種人類學筆記,或者是一種教學課。?MacDougall 2006,pp.264-265.
《原理》問世30年后,大衛·麥克杜格作《影視人類學新原理》(下文簡稱為《新原理》)一文,收入他的專著《有形的影像:電影、民族志與感覺》于2006年出版。?MacDougall 2006,pp.264-274.《新原理》在學術史反思基礎上提出一個新的影視人類學理論框架。《新原理》的學術史反思聚焦《原理》主流理論觀點,并選取卡爾·海德(Karl Heider)1976年首版專著《民族志電影》和杰·茹比(Jay Ruby)1975年發表論文《民族志電影是電影民族志嗎?》作為擴張語境,展開對影視人類學成立早期主流理論建構的述評。
海德《民族志電影》從文字人類學里拈出民族志性質的幾項特征,假設它們與民族志電影制作最相關。第一,民族志是基于長時段定點研究對人類行為進行細致描述和分析的方法;第二,民族志把具體觀察到的行為與文化規范聯系在一起;第三,民族志第三條基本原理是整體觀,在某種程度上,對事物和事件的理解必須置于社會和文化語境中;第四,民族志以真理為目標。?Karl G.Heider.Ethnographic Film.Rev.ed.,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2006,pp.4-7.這些原理充分體現民族志文本學術史成就,言之鑿鑿,條理清晰;但很遺憾,海德忽視電影的本體特征,沒有在這些原理與民族志電影實踐之間建立起有效的聯系。譬如,第一條原理以長時段定點研究、人類行為、細致描述、分析等關鍵詞比較充分地定義民族志文本的方法特征,但它們與民族志電影的相關性如何?指向民族志電影的長時段定點研究的內涵是什么?人類行為是否構成民族志電影的基本對象?文字描述與鏡頭描述有什么聯系與區別?鏡頭可能成為分析工具嗎?第二、第三條原理里的關鍵詞“文化”,它本身是文字人類學史上的觀念建構產物,它與民族志文本的聯系不言而喻,但它與民族志電影是否構成聯系?如果可能構成聯系,那是怎樣的聯系?第三條原理基于“文本”(text)寫作理路故而強調“語境”(context),該邏輯應用于民族志電影是否適當?第四條民族志文本以真理為目標,真理目標對于民族志電影是否同樣有效?諸如此類的問題在海德《民族志電影》中并未提出來展開探討。總而言之,海德《民族志電影》的最大問題是把民族志文本和民族志電影想當然混為一談。
按麥克杜格,海德民族志電影理論的背后是對中立方法論優點的信念。在海德看來,一部成功的民族志電影應該不被過于具體的理論興趣所污染。事實上,一部電影應該追求所認識事物的純凈。因此,他堅持整體主義,盡可能多地包含周圍的語境。海德的比喻是人體,它應該保持完整,而不是以碎片或缺胳膊或缺腿的形式展示。?MacDougall 2006,pp.265-266.
海德含蓄而明確地對比民族志者對真理的承諾的純潔與藝術家被假設的對審美愉悅的首要承諾。對于理性觀察者來說,從這個角度來看,真理在世界上是顯而易見的。介于觀察者和被觀察者之間的系統必然有污染。因此,海德說:“為了判斷一部影片的民族志性,我們需要知道現實被扭曲了多少和被扭曲到何等程度。”?MacDougall 2006,pp.265-266.
杰·茹比最著名的發展民族志電影理論的努力,發表于1975年,與《原理》首版同年,它的標題是《民族志電影是電影民族志嗎?》。它明確提出原理,一共4條。與海德不同的是,茹比宣稱電影要成為民族志,必須以某種文化理論為依據,他呼吁徹底改革電影的慣例,制作結構符合人類學的電影,而不僅僅是關于人類學主題的電影。茹比受索爾·沃思(Sol Worth)教學的啟發,在影視人類學的討論中納入對視覺交流人類學的興趣。然而,盡管茹比對人類知識的建構性做出姿態,與海德的邏輯實證主義形成鮮明對比,但長遠地看,他揭示自己是一個失敗的實證主義者。他的第三條原理宣稱“民族志作品必須包含揭示作者方法論的陳述”。它必須“包括某人在制作電影的過程中做出眾多決定的科學理由—每個鏡頭的取景和長度、主題的選擇、技術決定(例如電影膠片、鏡頭等的選擇)、收集的現場聲音類型、工作室聲音的使用、剪輯決定等”。簡而言之,要做到真正科學,民族志電影應該詳盡地揭示可能影響精確的現實再現的電影制作者的所有偏見。后來,茹比將這些想法發展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自我反思咒語。?MacDougall 2006,p.266.
除了所涉及的實際障礙,以及學者傾向于對自己的盲點視而不見的事實,這種方法,在它對科學方法的尊重中,最終回到海德對視角純凈的追求這里。似乎一旦所有方法的和知識的扭曲都剝離干凈之后,人們可以最終抵達科學真理的某種最佳形式。但是,這種柏拉圖式的理想已經與當前的人類學知識概念越來越抵牾,即人類學知識被認為取決于觀察者與被觀察者的關系,實際上,不可避免地,取決于那種關系的產物。?MacDougall 2006,p.266.
麥克杜格用海德和茹比的例子說明影視人類學在20世紀70年代與人類學主流分道揚鑣時備受困擾的幾個知識問題。因為正是那個時候,影視人類學開始發展制度性的基礎設施,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學術認可,這尤其要歸功于霍金斯主編《原理》的出版。我們在這里看到的是一門漸漸浮出水面的新興學科,它正努力擺脫由另一種媒介即文字媒介構成其知識目標的人類學家強加給它的期望。海德和茹比竭盡全力構思而成的影視人類學原理實際上不過是文字人類學原理的變異罷了。盡管用意是好的,但這些處方往好處說是令人困惑的,往壞處說是對這門新學科的發展構成某種阻礙。?MacDougall 2006,pp.266-267.
按貫穿海德《民族志電影》《原理》主流和茹比《民族志電影是電影民族志嗎?》的理論觀點,民族志電影制作通常被期待關注耳熟能詳的民族志論著的類別:社會組織、經濟、宗教、儀式、政治等。總的來說,影視人類學并沒有被認為給人類學增加了一個重要的新維度,而是被認為是溝通人類學寫作已經規劃好的關切點的一種不一樣的方式。因此,影視人類學只不過是一個將這些關切點翻譯為視覺說明形式的附屬品。?MacDougall 2006,pp.267-268.
民族志電影在1975年首版《原理》迭代為影視人類學。民族志電影的興起可回溯到20世紀50年代,在世界范圍內有幾個獨立起源,在中國是國家影像文化工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科學紀錄電影”(下文簡稱為民紀片),在法國是巴黎人類博物館民族志電影委員會專職影視人類學家讓·魯什的工作,在美國是哈佛大學電影研究中心專職影視人類學家羅伯特 ·高德納(Robert Gardner)的工作。?同注②,第33-34頁。
民紀片工程由國家財政專項資助,采取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為甲方、電影廠為乙方的合作模式,民族研究者和專業電影人合作開拓這個前所未有的以片子制作為導向的學術領域。民紀片工程始于1957年,1966年“文革”開始后中斷,其間一共完成15部膠片電影拍攝。“文革”結束后,民族研究所詹承緒等著手恢復民紀片工作。1976年拍攝彩色膠片電影《僜人》,1978年完成。參加過多部民紀片拍攝的楊光海從電影廠調入民族研究所,創建電影攝制組并任組長。1978年楊光海按民紀片模式拍攝5部苗族系列片,1980年完成。最終形成21部民紀片格局。?鮑江:《你我田野:傾聽電影人類學在中國的開創》,北京:民族出版社,2017年,第15-18頁。
進入20世紀80年代,不同起源的影視人類學進入交流與融合的歷史進程。?同注②。1988年中文學界開始有影視人類學這個術語。1990年民族研究所在電影攝制組基礎上成立影視人類學研究室,該研究室一直存續至今。?轉引自龐濤、鄧衛榮:《“中國社科院民族學與人類學所影視人類學研究室”簡介》,鮑江:《影視人類學季春》,王一惠主編:《影視人類學論壇》(電子期刊),2013年,第3期,第47-50頁。2000年該研究室成員張江華、陳景源、楊光海、龐濤、李德君、李桐組成的課題組合著我國第一本公開出版的影視人類學專著《影視人類學概論》(下文簡稱為《概論》),比較全面地綜述了20世紀影視人類學理論建構成就。《概論》由十章組成,包括影視人類學的研究對象和任務、人類學片的特征和拍攝原則、人類學片的多元功能及分類、國外影視人類學的形成和發展(上)、國外影視人類學的形成和發展(下)、中國影視人類學的發展、新中國早期人類學片拍攝方法和部分影片拍攝情況、人類學片的拍攝與制作、現代視聽科技在影視人類學中的應有、照相與影視人類學等。?張江華、李德君、陳景源、楊光海、龐濤、李桐:《影視人類學概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1-3頁。
《概論》的理論視閾未超出《原理》主流、海德《民族志電影》及茹比《民族志電影是電影民族志嗎?》的理論視閾。它把文字人類學歷史成就、乃至影視學歷史成就當作不言而喻的前提,定位它們為“母體學科”?張江華等:《影視人類學概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1-24;9頁。,但又不切斷影視人類學與它們結為一體的“臍帶”,于是,影視人類學成為從業者有生產欲望但難以生產的一個難產兒。譬如《概論》給出的一個影視人類學定義:“影視人類學是以人類學研究中影視手段的應用方式及其表現形式為研究對象,探討影視手段在人類文化研究中的功能、性質、應用規律,以及人類學片的特征、分類和制作方法的人類學分支學科。”?張江華等:《影視人類學概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1-24;9頁。定義者試圖建立影視人類學獨特的研究對象,但又離不開母體學科文字人類學及其研究對象“文化”,于是發出這樣一種模糊不清的聲音,如同嬰兒在母親子宮里喃喃自語。
二、21世紀初大衛·麥克杜格的影視人類學理論建構
影視人類學的理論建構囿于文字人類學的學術史成就,也就關閉了自己發展成一門獨立學科的大門。換言之,影視人類學要獲得獨立,首先必須建立自己獨特的研究對象。
大衛·麥克杜格正確地指出,我們的工作較之于更大的社會抽象,應該更專注于物體、個人、時間和地點的相互關系。?MacDougall 2006,p.270.最廣義地講,看電影的許多特征也是我們社會現實經驗的組成成分。這些成分包括我們的三維空間意識,對世界上的物體及其性質的意識,對物質性的和社會性的相遇的意識,對人類的意識,以及對在時間里展開的事件序列的意識。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加入我們對電影所建構的諸多世界的認同這項更鄰近的影響:我們對不同環境的感覺,對我們自己的身體之外的身體的感覺,以及我們對人作為獨特個體擁有他們自己的情感、思想和言談舉止風格的洞察。正如在生活中一樣,我們對電影中他者個人的經驗,既是物質的也是心理的。如果我們在尋找一種新的更適當的通向影視人類學的方法,我們最好去尋找這類交匯點。在此交匯點上,《新原理》為重新概念化的影視人類學假設三條原理:
1.使用視覺媒體獨特的表達結構,不使用那些說明文衍生出來的表達結構。確認片子與文本的表達結構差異。它與茹比的電影呼吁有聯系,即呼吁電影在形式上成為人類學的,而不是蜷縮于“教育”電影電視節目說教式陳規舊習。它承認,視覺媒體,特別是電影,在過去的一百年里已經發展出自己的表達常規,涉及影像和聲音的時間安排,類似音樂在比較長的一個時段內設計組織音高、節奏和音色的方法。當然,這些常規也在不斷演變。?MacDougall 2006,p.271.
2.發展不依賴科學方法有效性原理的人類學知識形式。確認片子與文本的知識標準差異。它是更根本的一步,呼吁接受(和創造)不一定符合源于自然科學的邏輯和證明模式的人類學知識形式。此主張表達對人類學努力定義其真理主張并奠定本學科時最常信奉的那些原則的挑戰。尋求在那些合法性領域之外構建知識的方法,這樣的一步也意味著此類知識內容的某種轉變。?MacDougall 2006,p.271.
3.探索視覺媒體證明有表現親和力的社會經驗領域,特別是這些領域:地志領域(the topographic)?topography一詞,15世紀早期意為“一地之描述”,來自晚期拉丁語topographia,來自希臘語topographia,意為“一地之描述”,來自“地”(topos)+“志”(graphia)。自1847年,意為“一域之集體特征”。相關詞有topographic;topographical;topographically。趣詞網(https://www.quword.com/etym/s/topographic),2022年7月21日。這里我們把the topographic翻譯為“地志領域”。、時間性領域(the temporal)、有形領域(the corporeal)?corporeal一詞,15世紀早期形容詞后綴al+拉丁語corporeus,意為“身體性質的”,來自corpus,意為“身體”(活的或死的),來自PIE*kwrpes,來自詞根*kwrep,意為“身體、形式、外觀”,可能來自動詞詞根,意為“出現”(同源詞:梵文krp,意為“形式、身體”,阿維斯坦文kerefsh,意為“形式、身體”,古英語hrif,意為“肚子”,古德語href,意為“子宮、肚子、腹部”)。趣詞網(https://www.quword.com/etym/s/corporeal),2022年7月22日。這里我們把the corporeal翻譯為“有形領域”。和個人領域(the personal)。?MacDougall 2006,pp.270-271.確認片子獨特的對象領域。它識別特別適合影視人類學的概念領域。這不意味著將研究局限于這些領域或建立一個排他的區域。相反,它呼吁人類學家在影視人類學中繪制新路線,不必擔心他們正在偏離研究不同社會中生命如何被模式化和被經驗化的這個人類學任務。它呼吁在人類學寫作經常遇到困難的領域充分發揮視覺媒體的潛力。?MacDougall 2006,p.271.
《新原理》是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推倒重來的影視人類學新理論建構之舉。它在表達形式和知識標準兩個維度劃清片子與文本的界線,揚棄體現于《原理》主流、海德《民族志電影》、茹比《民族志電影是電影民族志嗎?》和《概論》的依附于文字人類學歷史成就的影視人類學理論建構,明確提出影視人類學獨特的學術取向—視覺媒體證明有表現親和力的社會經驗領域。
當然,我們也察覺到,《新原理》的四大領域建構離“探索視覺媒體證明有表現親和力的社會經驗領域”目標還有一定的距離。《新原理》未提出并處理電影本體與四大領域的關系問題。相反,南轅北轍,列舉完四大領域的標題,隨即話鋒一轉,提示四大領域與文字人類學諸多領域的聯系。這樣的一種論證方式,悖逆文中提出的建構影視人類學新原理的策略:如果我們從頭開始重新發明影視人類學,不那么關注人類學的歷史發展,我們應該有可能提出一套非常不一樣的探索社會的參數。最實質性的分離,無論如何,應該源自被音像打開的非常不一樣的知識領域。?MacDougall 2006,p.270.按此策略,在這篇高度凝練地提出影視人類學新原理的文章里,蜻蜓點水似的指點四大領域與文字人類學關切點之間聯系的努力,既累贅又攪混水。實際上,提出四大領域主題之后,進一步努力的方向應該是基于影視人類學本身已取得的成就積累,辨析具體實踐道路,探索地志領域、時間性領域、有形領域和個人領域在影視人類學內部如何展開。大衛·麥克杜格是學術史上罕見的片子制作和片子制作研究文本寫作并駕齊驅的影視人類學家,他的片子和文本體現一以貫之的主觀性,構成其生活世界的具體內容。譬如他2014年發布的片子《宮墻下》(Under the Palace Wall),呈現他集拍攝、錄音和剪輯于一身以觀察電影模式與德瓦拉村(the village of Delwara)的交流交融。德瓦拉村位于印度拉賈斯坦邦南部,坐落在一個昔日之宮殿、今日之豪華酒店的下方。該片可以視為他在《新原理》里提出的地志領域的一部代表作。
按音像本體視角審視《新原理》,我們看到在文字人類學之外建構影視人類學理論的決絕的轉向努力,隱約看到影視人類學新原理大廈可能的地上建筑物之局部,并且也發現這座影視人類學理論大廈缺失地基。本文的著力點即在此—為影視人類學和音像志理論大廈打造地基,確立影視人類學和音像志的基本對象——具體人生活世界。如是提出音像志原理:1.音像志以音像為本體,包括片子制作及其研究文本寫作。原理強調音像志以音像為本體。按知識本體論角度,人類學一分為二,分為兩種人類學:一為文字為本體的文字人類學,一為音像為本體的影視人類學。前者以文本表達自身,追求普遍性概念;后者以片子表達自身,追求具體性世界。影視人類學作為后起、新興的人類學分支之一,它延續文字人類學的傳統研究對象,即人在遠方田野,但它懸擱文字人類學術語庫,以音像為本體探索自身獨立的學術可能性。?鮑江:《本體論分杈:影視人類學與文字人類學》,《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第13-20頁。音像志作為影視人類學的普遍化擴張形式,它以音像為本體,以片子表達自身,追求具體性世界。2.音像志主要用鏡頭制作片子表達自身。強調音像志主要用鏡頭制作片子表達自身,有別于主要用文字制作文本表達自己的文本志。3.音像志以具體人生活世界為基本研究對象。明確音像志的基本研究對象是具體人生活世界。
以建筑打比方,具體人生活世界音像志如地基,地上建筑物則預留給未來人文社會科學與音像志交叉創新的專科音像志實踐和理論建構,以期一個以豐厚的由世界各地音像志者制作的關于世界各地具體人生活世界的音像志作為經驗基礎的關于人的音像人文社會科學世界。
三、音像志的基本研究對象
音像志以具體人生活世界作為基本研究對象。音像志者以音像工具為媒,與志主相處,用鏡頭創作關于志主生活世界的真實電影。?生活世界作為影視人類學基本對象的論證。鮑江:《生活世界影視人類學理論》,《電影藝術》,2020年,第1期,第56-60頁。
音像志開山之作羅伯特·弗拉哈迪(Robert Flaherty)《北方的納努克》,以納努克為主角,開創以具體人作為對象的音像志道路。海德在《民族志電影》中正確地指出,弗拉哈迪深知電影的具體性,與此對照的是文字的一般性。他通過跟隨具體個體的具體行動,使影片獲得概括。他把影片聚焦在納努克這個因紐特男人上;聚焦在莫阿納這個薩摩亞青年人上;聚焦在阿蘭島人上。他試圖做得更多,而不僅僅是給我們看面目不清、身份不明的因紐特人或薩摩亞人抑或愛爾蘭人。他把影片推至電影具體性的極限,讓觀眾享受認識一個盡管異國情調但是真實的個體。這一點可能是弗拉哈迪對民族志電影最重要的貢獻,它顯然影響到《獵人》和《死鳥》。可以肯定地說,沒有民族志電影因為過于聚焦個體而變得糟糕,相反,有許多片子因為沒有這么做而導致諸多缺陷。?Heider 2006,p.22.
科林·楊在《觀察電影》一文中引用他的同事大衛·漢考克(David Hancock)的拍攝筆記,強調觀察電影非常擅長具體,但根本不擅長做概括:“我們用長鏡頭處理具體個體,而不是處理文化模式或文化分析。我們試圖在一個鏡頭里完成一個動作,而不是將其碎片化。我們的工作是基于作為人(不僅作為電影制作人)的我們與被拍攝的人,即人與人之間的開放式互動。他們的觀點和關切塑造并結構影片,而不是由我們對他們文化的特定主題或分析的強調,那可能扭曲或過分強調該主題對于那些人和那文化的重要性。”?David Hancock.See Colin Young.Observational Cinema.Paul Hockings ed.,Principle of Visual Anthropology.Second edition.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Co.,1995,p.108.
麥克杜格在《新原理》中也正確地指出,重新審視一下在過往影視人類學中我們最看重的東西是有益的。當然,它肯定不是圖表更擅長展示的社會結構描述,也不是論文更擅長研討的經濟和宗教調查。或許,它也不是儀式或技術過程的冗長記錄,它們的沉悶并未因解釋而得到緩減,盡管它們顯然有其信徒。相反,它是我們遇到的個人,他們生活在其中的房間、街道和院落,他們經歷的旅行,他們解決的困境,他們制造和使用的物品,他們聽到的聲音,他們的面孔和交談,他們的恐懼和喜悅,簡而言之,它是個人與具體社會親密相處得來的這種知識的暗示。?MacDougall 2006,p.273.
“具體性”是人類學電影的基石。某種意義上,人類學電影(音像民族志)是倒立的民族志。在文字民族志中,具體田野是手段,普遍理論是目的;在人類學電影中,普遍理論是手段,具體田野是目的。具體的人、物、事件和人物話語構成再現本體,人類學概念思辨僅是隱匿在作品背后的背景及可資引申闡發的余緒。與普遍性概念保持距離是人類學電影確立自身的邏輯要求,在此要求下,人類學文本慣用的從具體過渡到普遍的創作手法失去意義,人類學電影研究對象落實于作為文化載體與創造者的具體人物。懷抱認識異質文化、文化自覺、跨文化的職志,直面具體田野,角逐具體性,是人類學電影確立自身獨立學術場域的必由之路。?鮑江:《“具體性”是人類學電影的基石》,《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9月12日。
具體人作為音像志主有什么講究?它涉及兩個基本概念:生活世界與整體性。視聽媒介的使用帶來了人類學著力點的一個重要轉變,主要涉及內容方面。它帶來對個體社會生活世界、更不用說個體社會經驗的一種新的人類學理解。?MacDougall 2006,p.269.具體人生活世界整體性,是影視人類學和音像志最根本、最具體的研究對象。此確認姍姍來遲,但終究已經到來。研究具體人生活世界整體性,坦白地說,文字人類學難得做好,僅為阿堵傳神寫照這一項?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睛)。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于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巧藝》。,鏡頭描寫流光溢彩,訴諸寫作,罕有學者有那樣的文筆。
生活世界是哲學家胡塞爾提出的一個概念,英文作life-world,即以生命為前提的世界。按胡塞爾現象學,我們不討論我們身外是否有一個客觀的世界,但是我們可以探討你的生活世界、探討我的生活世界。按胡塞爾現象學,生命是第一位的,生命是最可貴的東西。可以說,這種思想遙遙呼應于中國文化的精神,如《論語》講述的道德,聽到馬圈失火的消息時,應該先問照顧馬的人傷著了沒有;如《史記》的敘事體例,以人物為中心。?同注?,第59頁。
“觀自在者·自省·生活世界”(transcendental ego as spectator of ego's life-world)三位一體理論視閾,是胡塞爾現象學對西方哲學的開拓性貢獻。它在現代西方哲學史上突破“自我·我思”(ego cogito)視閾,提出以“觀自在者”(transcendental ego,也譯作“超越論的自我”)為主體、以“生活世界”為“自省”對象的三位一體理論視閾。
生活世界有二重空間結構,即“自我生活世界”(ego's life-world)和“觀自在者生活世界”(transcendental ego's life-world)。自我生活世界指相對于自我的生活世界,它是一個相對于自我主觀絕對有效的世界。觀自在者生活世界指相對于觀自在者的生活世界,它是諸多可能的生活世界之一。是為胡塞爾生活世界的二重空間結構。它們在時間上非此即彼,前者體現為不斷擴張充實的生命歷程,后者體現為生命的自省時間。?鮑江:《斷網時間:生活世界中的自省片刻》,《中國社會科學報(社會學版)》,2022年6月22日。
音像志的整體性體現為生活世界的整體性。音像志者用鏡頭創作關于志主生活世界的真實電影,涉及志者與志主基于默契或者協商選擇記錄并呈現的志主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音像志者如同影視人類學家,在他們這里,人是具體的,有他或她自己的名字,有自己的身份,有自己的生活世界,其中包含思想、行為、欲求、情緒等可以概括的和其他不可以概括的一切。他們一旦選定拍攝對象,就意味著要設法盡可能全面、有序、清楚地記錄并呈現他或她的生活世界。?鮑江:《天生良知鑄夢人》,載王海飛主編:《微行集—影視人類學的道路》(第一輯)“序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并且,跳出音像志內部視角,站在外部旁觀者視角,我們發現,音像志實際體現攝影機介入條件下志者與志主相處,體現他們生活世界視閾融合的成果。
特別需要指出,胡塞爾是在其現象學脈絡里提出的生活世界概念;具體地說,生活世界概念的提出以懸置實證科學的客觀世界為前提。我們將音像志的基本對象定位于在胡塞爾現象學意義上的具體人生活世界,這意味著我們已經把實證科學的客觀世界放入括號存而不論,把學術史上層出不窮的用來描述客觀世界的普遍概念放入括號存而不論。僅就實證人類學而言,描述客觀世界特征的經典專業術語諸如“文化”“社會”“民族”“儀式”“親屬制度”“神話”“宇宙觀”“族性”“結構”“象征”“認同”等我們放入括號存而不論,新近流行的專業術語如“感官轉向”“本體論轉向”“人與非人”“人類紀”等我們放入括號存而不論。甚至胡塞爾后學在實證科學意義上使用的“生活世界”這個術語,我們也放入括號存而不論。換個角度說,當我們接收到有人使用實證科學術語時,我們僅僅把它們當作他或她主觀生活世界里的東西,僅此而已。
具體人生活世界的音像志研究,生活世界以具體人為前提,世界以生命為前提。打個比方,假設某個名叫張三的志者制作某個名叫李四的志主的音像志,意味著志者張三以志主李四的生活世界為研究對象范圍,以鏡頭為媒,與志主李四相處,通過交流、觀察、傾聽、選材、拍攝、整理素材、提煉主題、剪輯等環節制作形成片子。生活世界是活的,志者與志主相處過程中彼此的生活世界視閾逐漸發生交匯交融,共同凝固一段生命時間、沉淀一份永恒的音像記憶,是為音像志的本質。其他條件不變,換人不管換志者還是換志主,或者不換人換志者和志主的年齡,意味著生活世界發生變化,音像志的內容會隨之發生變化。
四、音像志的倫理
音像志以具體人生活世界為基本對象,因此對音像志者提出特殊的倫理要求:1.音像志場域以具體人為基礎,志者和志主皆為主體,要求既尊重對方又不失自我,體現“四海之內皆兄弟”的人與人相處之道。2.音像志場域屬學術性質,要求志者和志主以公益心參與其事,志者和志主有角色署名權。3.音像志者以導演角色為音像志作品負責。
當音像志者將鏡頭對準具體人,他們的研究對象就不再是手段,而是主體,他們的研究實踐的本質不再是探索客觀他者,而是探索主體之間相處及相處之道。影視人類學正是在這里,與基于匿名操作技術和抽象“報告人”的文字人類學分道揚鑣,與追求客觀他者的文字人類學分道揚鑣。音像志者與志主相處及相處之道應當如何?在普遍意義上,我們從孔子《論語》中獲得啟發:“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里的人我相處之道是兄弟相處之道—尊重有度,即我對人秉持恭敬心態,并且保持彼此之間適當的禮節距離。其中的度,即禮節距離,是個動態概念,它在相處中發生變化。一般說來,陌生的時候禮節距離比較遠,熟悉了禮節距離比較近;在放松的場域,譬如酒酣之際,禮節距離比較近;在嚴肅的場域,譬如儀式、學術答辯、法庭審判等,禮節距離比較遠。
在特殊意義上,隨著音像志開工制作,參與者生活世界中即生發出一重攝錄機介入條件下的主體相處場域,鏡頭兩端的主體分別為志者和志主。鏡頭所到之處“落子無悔”,客觀記錄下志者與志主相處,如其所是,不增不減。真實生活世界與真實電影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纏繞發展。前文提到的法國影視人類學奠基人讓·魯什與莫蘭合作提出真實電影概念的《夏日紀事》,魯什與他的非洲伙伴們長達60年的學術實踐?Paul Henley.The adventure of the real: Jean Rouch and the craft of ethnographic cinema.ix·Prefac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9.,尤其是他與達姆亨·齊卡(Damouré Zika)、朗姆·伊布蘭伊瑪·迪奧(Lam Ibrahima Dia)、滕魯·姆茹瓦奈(Tallou Mouzouran)組成的“達朗魯滕”幫(Da-La-Rou-Ta)的電影實踐,給志者和志主相處及相處之道樹立了先行者典范。?Henley 2009.
按觀自在者視角,音像志是志者和志主在攝錄機介入條件下敞開、展示并擴張自我生活世界的特殊生命歷程。“真實歷險”是保羅·亨利(Paul Henley)給他撰寫的讓·魯什傳記取的名字。51Henley 2009.據讓·魯什,電影是歷險,困難則在于你必須不斷努力駕馭它。52Jean Rouch.In Paul Henley.The Adventure of the Real: Jean Rouch and the Craft of Ethnographic Cinema.ix·Preface.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9.音像志參與者在真實生活世界基礎上建構作為真實電影的音像志,音像志作為真實電影又構成參與者真實生活世界的組成部分;從真實生活世界到真實電影、再從真實電影到真實生活世界,攝影機如同魔法般參與到志者和志主的生命歷程,對他們的生活世界產生不可逆的影響。音像志給志者和志主提供一種無與倫比的“看見自己”的契機,促成自我反思和自我完善。譬如讓·魯什曾經這樣談及《夏日紀事》的發現:“看到銀幕上的自己之后,一個個瞠目結舌!從那一刻起,他們開始脫胎換骨!”53張同道:《冒險是我的職業—讓·魯什訪談》,《電影藝術》,2007年,第1期,第143頁。在此意義上,音像志有真實歷險特征,它持續挑戰志者和志主的駕馭能力。志者和志主應以尊重有度的兄弟相處之道作為倫理原則,如是規避音像志歷險之旅的系統性風險。從相反角度說,不尊重人挖掘本人不愿公開的生活世界方面是音像志的倫理禁令。
五、音像志的研究方法
音像志的研究方法,我們用七個關鍵詞定位:攝影機、錄音機、剪輯機、志者、志主、生活世界、長時段田野工作。攝影機、錄音機和剪輯機是音像志工作的必要工具,按現在的數字音像技術,一部智能手機即兼有這三種功能。志者是拍攝主體,他可能是一人或一團隊,最好是一人,一身兼多任:導演、攝像、錄音、剪輯等;若是團隊,成員越少越好。志主是拍攝對象、片子主角。音像志內容錨定于志主生活世界,體現志者與志者相處及相處之道。田野工作與書齋工作相對,指研究者直接從研究對象那里獲取知識的方式。音像志知識來源于長時段田野工作,來源于志者與志主長期相處;生活世界的廣闊、人與人相知需要時間打磨,這兩方面要求音像志的田野工作周期是長時段的。
音像志錨定具體人生活世界為基本研究對象,關乎音像本體。片子的基本技術單位是鏡頭,即按下攝錄一體機錄制按鍵開始紀錄具體時空中的所見所聞,再次按下攝錄一體機錄制按鍵終止紀錄,這樣形成的一段音像素材我們稱作鏡頭。在技術層面,片子是由一個又一個鏡頭組成的。片子的基本內容單位是場(或稱作場景),它是用分鏡頭組合或長鏡頭清楚地表達具體人在具體時空中做具體事的一段音像。在內容層面,片子是由一個又一個場組成的。如何在鏡頭層面和場層面實現多樣性的統一,是做片子最根本的挑戰。意識不到或應對不好這個挑戰,對于片子后期剪輯是個災難,大概率得依賴配樂或畫外音解說或字幕來發揮組織功能,把缺乏內在統一性的素材生硬地串聯在一起。我們設定具體人生活世界作為基本研究對象,實現了音像本體要求與音像對象的契合,一勞永逸地徹底解決了這個挑戰。
場建構,即制作用分鏡頭組合或長鏡頭清楚地表達具體人在具體時空中做具體事的一段音像,是做片子的基本功。場建構關乎視聽(音像)規律,必須在片子制作實踐中自己感悟。感悟不到、感悟不透這項基本功,就不入片子門,看再多片子、評論再多片子甚至制作再多片子也是外行。
“上午,晴,微風,張同學在圖書館自習一本某專業書”,這是我常給修民族志電影制作課的同學布置的一個練習題,要求同學把文字表達轉換為鏡頭表達,目的是鍛煉場建構的基本功,涉及分鏡頭組合描述具體事件、場的空間建構和場的時間建構;合格的習作,應該能讓觀眾如臨張同學之境并觸及此際他或她的精神世界。掌握場建構方法是個反復練習熟而生巧的過程,好比學說話,先模仿前人經驗,再形成自己特色。
六、音像志的實踐理性原理
做音像志的根本目的是充實和擴張世人生活世界。第一層,志者和志主通過做音像志獲得生活世界的充實和擴張;第二層,公眾通過觀看音像志作品獲得生活世界的充實和擴張。
音像志是活生生的人與人相處的場域。志者將鏡頭指向志主生活世界,從志主生活世界中選擇拍攝內容、拍攝和剪輯,創建一個又一個表達志主生活世界片段的場,日積月累形成音像志的場儲備。相處日久,相知漸深,志者在某一刻會頓悟到一個主題,此時志者即有可能在剪輯機時間線上通過篩選和組合場儲備來創建敘事完成片子,如果發現場儲備不充分,則補拍。
迄今的現代學術經過學術史反復渲染創建了牢固的自我與他者二元對立統一體,其代價是你我之維幾乎被遮蔽為無,因此現代人在完整的人意義上變得殘缺,我們滿腹經綸,但往往目中無具體人,不知道如何與具體人相處。借助音像的獨特魅力,音像志打開參與者生活世界的自我封閉,給與參與者探索與具體人相處的機緣,使每個參與者的生活世界都獲得充實和擴張。這里的音像志參與者包括志者、志主和觀眾。
音像志屬學術志業。音像志片子有別于其他非學術的片子類型,諸如藝術片子、商業片子、宣傳片子等,各自恪守各自疆域,井水不犯河水。音像志追求真實電影,追求永恒的學術價值;今日之志,明日之史。對于志者、志主以及他們同時代人而言,音像志是志,對于后人而言,音像志是史。音像志作為史的意義,從讓·魯什2000年在紐約大學“非洲現代性編年:讓·魯什電影回顧展”《美洲豹》(1957—1967年)映后交流發言中可見一斑:
這是關于一個已經永遠消失了的時代的一份編年史。不過,它既已永遠消失,但又沒有消失,因為有這部影片存在。對我來說,這就是電影的力量和電影的情感。如此奇怪的一種保留記憶的方式。你可以年復一年地與新的公眾分享它。我想,對我來說,這是非常令人感動和鼓舞人心的。54Chronicles of African Modernities: A Retrospective of Jean Rouch's Films(NYU,2000).Transcribed and introduced by Jamie Berthe.
七、音像志的專科化
具體人生活世界為基本對象內容的音像志,是最樸素、最貼近生活本身的學術,因此它能自下而上地與人文社會科學既有分科異花傳粉形成專科音像志。
主題化是文字本體的人文社會科學的基本運作方式,學者按思辨標準劃分學科、界定領域,形成樹型科目結構整體。理論上,文字本體的人文社會科學所有學科都可能與音像志交叉并在本學科底部分杈培育形成本專科音像志。譬如,人類學民族學與音像志交叉形成民族志電影(民族音像志);社會學與音像志交叉在特定范疇內形成專科音像志,諸如社區音像志、宗族音像志、家音像志、群體音像志、行業音像志、鄉土音像志、城市音像志,等等;民俗學與音像志交叉形成民俗音像志;音樂學與音像志交叉形成音樂影像志;舞蹈學與音像志交叉形成舞蹈音像志;地方志與音像志交叉形成地方音像志;口述史與音像志交叉形成口述音像志;宗教學與音像志交叉形成宗教音像志;國別研究與音像志交叉形成國別音像志;區域研究與音像志交叉形成區域音像志;體育學與音像志交叉形成體育音像志;等等。
專科音像志為專科領域奠定最貼近生活本身的經驗基礎,結構性地完善專科領域的知識結構。以音樂影像志為例。音樂學原本是一門從生活中抽離出來的特殊學科,它以音樂為研究對象。按學科建構邏輯,音樂學從生活中來,它應該也回到生活中去,以豐富生活。但迄今學術史的走勢并非如此,跟其他現代學科一樣音樂學內部專業領域越分越細,反方向的學科整合以及學科實踐與生活本身交流互惠的運動則趨向淡薄。近年音樂學者蕭梅、劉桂騰等聯手影視人類學者創辦“華語音樂影像志暨國際音樂影像志展映”。筆者2021年應邀擔任第二屆評委,近距離接觸學者用鏡頭把音樂拉回到田野現場、拉回到具體人生活世界的努力,感覺音樂學似乎因此有了一種打通專業內外讓人親切的體溫,變得不再那么高冷,這里蘊藏學術重大增長的契機,彌足珍貴。
結 語
以上嘗試提出一種音像志學基礎理論建構,探討了音像志的理論源流、音像志的基本研究對象、音像志的倫理、音像志的研究方法、音像志的實踐理性原理、音像志的專科化等問題。建構音像志領域,在工具方面是數字音像技術普及使然,在知識方面是現代學術自我完善內在要求使然,把現代學術迄今單向度膨脹的術語世界拉回具體人生活世界,彌補現代學術但見層出不窮的概念術語創新不見活生生的人的缺陷,指向現代學術內部文字與音像、先驗與經驗、普遍性與特殊性等諸多二元對立統一體內部張力的歷史性飛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