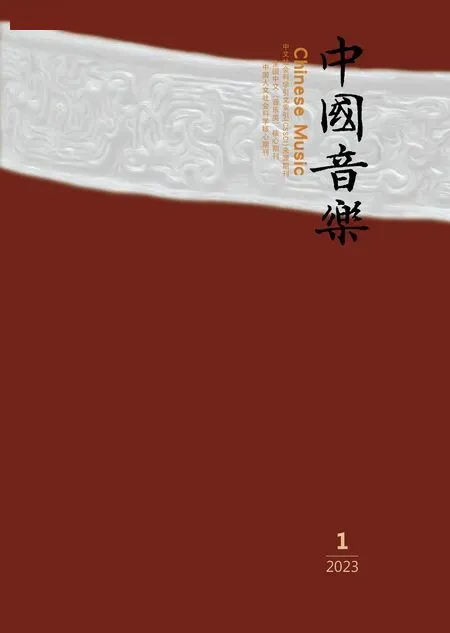賦象于聲
——論白云山節日影像志實踐中的音樂議題
○梁君健
在影像人類學領域,音樂不僅發揮著一般性的敘事表達功能,而且還是一種重要的文化要素,關涉到田野工作和文化闡釋等一系列更加核心的議題。早在經典好萊塢時期,電影創作者就穩定地將音樂用于情感表達、敘事激發和場景解釋。①Claudia Gorbman.Film music.In The Oxford Guide to Film Studies.Edited by John Hill and Pamela Church Gibson,Oxford: OUP,1998,pp.43-50.在電影的視聽語言中,音樂主要發揮三方面的作用:一是整合不同的事件和場景,形成流暢敘事;二是能夠讓觀看者更自然地進入由音樂引發的敘事過程和情感狀態;三是賦予視覺呈現以個人化的視角。②Holly Rogers.Introduction: Music,Sound and the Nonfiction Aesthetic.Music and Sound in Documentary Film.Edited by Holly Rogers,New York: Routledge,2015,pp.1-19.對于紀錄片來說,音樂具有更為特殊的意義。在很長時間內紀錄電影一直是以教育、告知和宣傳的功能為主,因此,音樂和解說也往往比畫面具有更強的優先性;而對沒有畫外音和解說的紀錄電影來說,音樂扮演著故事引導者的角色,帶領觀眾從一個場景到另一個場景,并定義出敘事和意義的段落。③Paul Animbom Ngong.Music and sound in documentary film communication: An exploration of Une Affaire de Negres and Chef! CINEJ Cinema Journal,2020,8(1),pp.156-184.然而,相比于主題、敘事、風格、作者等研究熱門,音樂較少得到注意。本文將首先綜述民族音樂學和影像人類學領域關于聲音的相關文獻,進而以白云山影像民族志的田野與制作實踐為例,探討節日影像志中的音樂議題。本文認為,對于音樂進行人類學式的視聽呈現這一“賦象于聲”的任務在田野工作和后期剪輯兩個層面中有不同的方法論,二者共同構成了對于音樂事項的文化闡釋。
一、文獻綜述:影像人類學中的音樂
在人類學領域內,音樂是一類獨特的文化要素,對其進行的豐富研究推動了民族音樂學這一學科的出現與成熟。民族音樂學的核心任務是探討音樂是如何被文化規則和社會結構影響,又是如何反過來影響社會的。在田野工作中,學者致力于展現和分析音樂與社會的關系,將音樂表演和音樂創作視為一種超越了單純的藝術活動之外的社會行動;這時,音樂體現出文化實踐的獨特價值,是人類展開意義創造與傳播的重要手段。④Timothy Rice.Ethnomusicolog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對于音樂展開研究,既能夠幫助人類學家理解特定的文化世界,也能夠揭示出音樂制作者是如何通過音樂來表達文化持有者群體自身的文化身份。⑤Georgia Curran and Mahesh Radhakrishnan.The Value of Ethnographic Research on Music: An Introduction.Th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Anthropology,2021,22(2-3),pp.101-118.除了民族音樂學之外,人類學的其他領域也發展出對音樂的類似觀點,如民族生物學也重視探究歌曲的文化作用,將音樂視作一種儲存了地方性的知識并規定著特定的文化實踐的文化資源。⑥álvaro Fernández-Llamazares and Dana Lepofsky.Ethnobiology through Song.Journal of Ethnobiology,2019,39(3),pp.337-353.
影像人類學領域對于聲音的研究最初和電影與紀錄片領域類似,大多采取視聽表達的分析視角,探討音樂的敘事功能。很多學者集中于田野錄制的環境音和同期聲對于意義建構的價值,⑦Irina Z.Leimbacher.Beyond the visual: Sound and image in ethnographic and documentary film,Visual Studies,2013,28(2),p.192.也有學者考察了詩意紀錄片(Poetic documentaries)將音樂和環境音響用作敘事手段的各種方法,包括現實主義層面和觀念層面的。⑧Kerstin Stutterheim.Music as an Element of Narration in Poetic Documentaries.The New Soundtrack,2018,8(2),pp.103-117.在創作領域,早期具有人類學特點的紀錄片偏好使用地方性的音樂,來營造環境氣氛和異文化語境。例如,展現東南亞傳統文化的紀錄片《錫蘭之歌》(The Song of Ceylon,Basil Wright,1934年)在出片名字幕和片頭的解釋性字幕時,以當地的清唱歌曲為配樂,為觀眾營造出即將步入陌生文化的進入感和異域情調。20世紀上半葉重要的紀錄片導演弗拉哈迪的《亞蘭島人》(Man of Aran,1934)的音樂由富有經驗的故事片作曲約翰·格林伍德譜寫,編曲借鑒了亞蘭島的愛爾蘭本地音樂。弗拉哈迪希望通過原創但富有本地特點的音樂增加電影的可信度和人類學紀錄片所期待的本真。⑨K.J.Donnelly.Irish Sea Power: A New Version of Man of Aran (2009/1934).Music and Sound in Documentary Film.Edited by Holly Rogers,New York: Routledge,2015,pp.137-150.
不過,隨著影像人類學這一學科走向成熟,關于音樂的思考也得到深化。保羅·霍金斯認為,視覺人類學家更多關注人類如何表達和傳播他們的文化傳統,這主要由可觀察到的形態構成,如語言、音樂、藝術、舞蹈,對空間的使用等。⑩Paul Hockings.Historical Foreword.Viewpoints: Visual Anthropologists at Work.Edited by Mary Strong and Laena Wilder,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2009,p.2.隨著人類學從行為科學到闡釋科學的轉向,影像人類學也不再滿足于僅僅記錄可觀察到的文化現象,而且進一步地希望將這些文化現象轉化為文化理解。這引發了人類學紀錄片的一個重要的實踐問題:當拍攝的東西無法自證的時候,如何通過各種視聽方式對其進行闡釋。?Peter Loizos.Innovation in ethnographic film: from innocence to self-consciousness,1955-1985.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p10.符號、象征和超現實,都是應對上述問題的有效探索。超現實主義將文化視為一個有爭議的現實,《無糧的土地》(Las Hurdes,路易斯·布努埃爾,1933)被視作超現實主義人類學的早期代表,它反思了我們熟悉的影像和聲音的配合方式會如何讓我們變得盲目相信。?Jeffrey Ruoff.An Ethnographic Surrealist Film: Luis Bu?uel's Land Without Bread.Visual Anthropology Review,1998,14(1),pp.45-57.在影像人類學的領域,讓·魯什質疑既有的模仿生活的電影模式,認為單純的經驗性的記錄并不能帶來對于他者的成功理解。他提出了“電影通靈”的觀念,希望通過電影拍攝讓處于文化邊界兩端的拍攝者和拍攝對象在影像所建構出的特定場域中實現文化分享。?梁君健:《人類學視野下的“電影通靈”觀念考》,《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第49-56頁。加德納也同樣質疑了觀察式風格、或者經驗性的表象真實。他從電影藝術本身,尤其是蒙太奇流派中尋找超越經驗性的表象真實的方法。在具體的創作中,加德納展現出對于暗示和模糊曖昧的特殊愛好,以及對于隱喻和轉喻的越來越多的使用。?Ilisa Barbash and Lucien Taylor.Introduction:resounding images.The Cinema of Robert Gardner.Edited by Ilisa Barbash and Lucien Taylor,New York: Berg Publishing,2007,pp.1-13.
從上述文獻可以看出,在影像民族志中,音樂大致發揮了邁克爾·雷諾夫(Michael Renov)所提出的四類功能:記錄與保存,說服與倡導,分析與質詢,傳遞與表達。?Michael Renov.Toward a Poetics of Documentary.Theorizing Documentary.Edited by Michael Renov,New York:Routledge,1993,pp.12-36.具體到實踐層面,音樂主要涉及兩個層面。其一,是將音樂視作田野工作的對象和來自于田野記錄的視聽素材,其二,是將音樂視作表達主題與傳遞情感的視聽語言和影像詩學的要素與手段。本文接下來將以白云山影像民族志實踐為例,進一步探究“賦象于聲”的理論與實踐議題。
二、田野拍攝中的音樂事件
筆者自2017年2月起,以陜西省佳縣白云山道觀為核心,展開針對當地道教民俗和鄉土社會的田野調查與影像拍攝,其中一個重要考察對象是當地道觀保存的道教音樂。此地的道教音樂于2008年被增選為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歸屬于編號為Ⅱ-139的“道教音樂”大項中。根據“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博物館”網站介紹和田野材料,白云山的道教音樂有三個主要來源。其一,明萬歷三十六年(1608)北京白云觀道士來白云山總理教務時,就將當時北京白云觀的道教音樂帶入陜西,成為白云山道教音樂的主要構成。其二,來源出自一則被廣泛記錄的傳說,據說清代龍門派第九代傳人白云山道士苗太稔曾云游江南,受南方正一道的科儀的影響,學習并帶回了南方道教音樂。?《白云山道教音樂》,《音樂天地》,2018年,第9期,第44頁。其三,從曲牌和曲調來看,當代的白云山道教音樂還明顯地受到陜北地區的佛教音樂和民間音樂的影響,在長期的民間共存與競爭過程中充分吸收融合。
筆者針對道教音樂的田野考察,基本遵循了民族音樂學的既有框架。Alan Merriam在《音樂人類學》(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中綜述了該領域的研究議題,其中的一部分議題來自這一領域中傳統的跨文化比較研究和非田野的音樂文本研究,而與特定文化社群中的音樂實踐相關的議題則包括了:音樂與身體和語言行為之間的關系,音樂家群體的社會屬性,音樂的學習與傳承,作為符號行為的音樂,音樂與文化史。?Alan P.Merriam.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4.
在田野工作中,筆者首先考察和記錄了制度性的宗教音樂,系統地考察了以四月八廟會為代表的音樂使用情況。每年在三月初三、四月初八和九月初九,白云觀都會舉行廟會,成為黃河兩岸黃土高原及整個西北地區的重要民俗節日。其中,四月初八的廟會從初一開始,持續八天,是歷時最長、規模最大的廟會。在廟會過程中,既有道士團體在熏壇、起經、上表、醮紙等清醮科儀中的奏樂,也有信眾組織聘請的山西吹手班子伴隨著迎香紙、迎錢糧和上供等過程的奏樂。上述音樂都與特定的宗教儀式和信仰實踐密切咬合。此外,廟會期間還有道教管理協會邀請的戲曲表演,以及自行前來表演的三弦說書藝人。晉劇、說書、吹手等演奏的音樂,與制度性的宗教音樂一并構成了廟會的文化表演的聲音景觀。例如,在2017年秋季九月初九的廟會中,舉行主要宗教儀式的真武大殿對面的戲臺上,同時進行還愿戲的演出。這時,真武大殿內部整個道教科儀的過程中一直伴有戲臺上唱戲的聲音,是在科儀前半段念經時,戲曲音樂甚至蓋過了誦經聲音,直到科儀后半部分開始吹打演奏后,道教音樂在大殿中才成為聲音的主流。
在田野工作中,筆者還針對核心的傳承群體,即白云觀掌握科儀音樂演奏的道士群體,展開了人生史的深度訪談,以了解音樂的學習與傳承方式。按照當地傳統,白云山周圍陜北地區的民間道士主要承擔著清醮和白事等民俗功能,需要掌握多項技能,其中最主要的即為“一寫、二念、三吹打”。書寫民俗儀式中用到的榜文和表文是首要的,其次是誦經,最后才是與音樂相關的技能。包括音樂在內的技能主要是師徒相傳,弟子在和師父出門“辦事”的過程中學習,同時配以道士們之間相互抄寫的科儀和樂譜的手抄本。對于音樂學習來說,大多數的道士都是在沒有樂譜的情況下通過聽和練而完成。近些年來,在宗教活動不斷正規化和全國范圍內跨地域交流增加的情況下,一些本地道士有機會前往北京白云觀、武當山道教學院等地修習道教高功課程,學習標準化的“全真正韻”并帶回統一印制的樂譜等資料。不過,目前這些學習成果還沒有投入實用。靖邊縣的一位劉姓道士就曾在武當山學習過全真正韻,也希望能夠在本地廟會和民俗活動時嘗試。但實際上,完整的全真正韻需要更多的音樂和儀式參與者,他感覺,陜北的老百姓恐怕既請不起這么大的班子,也無法欣賞這樣的繁瑣儀節。
最后,筆者還記錄了白云山道教音樂中獨特樂器“管子”的制作過程,展現了與音樂相關的其他技藝傳承。白云山道團使用的管子原本為木質,與北方其他地區相同;但20世紀40年代起白云山道士改用自制的錫管,因其發音明亮,用作領奏樂器,也成為了白云山道教音樂的代表性樂器。?張明貴,康至恭講說,申飛雪收集整理:《白云山道教音樂》,西安:陜西旅游出版社,2010年,第18-19頁。在田野工作中拍攝到的錫管和哨片分別由張姓和劉姓白云山工作人員制作完成。前者擔任真武大殿保安,后者負責東岳廟值守,二人并非在冊剃度道士,而是白云觀中道士的俗家弟子。他們根據道觀中既有的舊物件、結合著幾位懂音樂的道士的指導,在閑暇時間里通過不斷摸索,學會了樂器的制作,并成為行家里手。同時,筆者還跟隨他們前往神泉堡附近山溝里的一片蘆葦地采集制作哨片的原料。這片山溝因為土質和小氣候的原因,生長的蘆葦尤其適合制作哨片。而這些知識最早是劉姓工作人員從民間吹手朋友那里得知的,這同樣是和音樂相關的地方性的知識。
在對音樂表演、儀式過程和訪談展開影像記錄的過程中,主要借鑒和發展了“音樂事件”(musical events)這一觀念。音樂事件最初用來強調音樂表演的社會屬性,將音樂表演視作在特定時間和空間中所發生的一次性事件和表演者與觀眾之間的積極對話,因而相比于樂譜和“純粹”的音樂現象具備了社會和歷史語境。?Robert Edgar,Kirsty Fairclough-Isaacs,and Benjamin Halligan.Music Seen: The Formats and Functions of the Music Documentary.The Music Documentary: Acid Rock to Electropop.Edited by Robert Edgar,Benjamin Halligan,and Kirsty Fairclough-Isaacs,London: Routledge,2013,pp.1-22.本文認為,在影像民族志工作過程中,音樂事件既是社會事件,也是拍攝事件,在田野中針對音樂而展開的每一次拍攝都同時具備上述兩個屬性。其中,社會事件是指可以與拍攝行為和攝像機相分離的、屬于文化社群自身的與音樂有關的行動和闡釋。這包括了在具體的情境中所發生的人通過儀式性的音樂與神靈之間產生連接,也包括了音樂的操演者和受眾處于特定的表演現場而產生的知覺體驗。拍攝事件是指由田野工作和攝像機參與而引發的原本不會發生的事件。在影像人類學領域,最著名的拍攝事件當數讓·魯什1967年制作的10分鐘單本影片《圖魯和比蒂》(Tourou et Bitti)。當時,讓·魯什正在拍攝一場原本應當由音樂演奏而觸發的附體儀式。在這次拍攝之前,附體一直沒有成功;拍攝時,讓·魯什將鏡頭對準音樂的演奏者,演奏者原本準備停下來,發現魯什正在拍攝,于是繼續進行音樂演奏,而正是接下來的演奏成功地引發了附體。讓·魯什認為,這次附體是田野拍攝所引發的原本不會出現的現象。筆者的田野拍攝并未完全遵從“不干涉”的原則,相反,筆者主動地向當地人訂制了管子這一樂器,并對很多拍攝對象進行了訪談拍攝。這些都構成了拍攝事件,一些原本不會發生的場景激發出存儲于當地人精神世界中的地方性知識和技術經驗,提供了對于音樂的文化理解。在拍攝過程中,筆者還注意充分發揮視聽語言的場景構筑優勢,以確保拍攝出來的素材符合敘事性紀錄片對于“人物—行動”鏈條的敘事需求。
三、賦象于聲的創作挑戰
筆者在白云山田野工作期間遵循“不浪費的人類學”的拍攝理念,盡可能地將田野拍攝延伸到道教民俗和白云山周邊農村社會中,并計劃制作多部紀錄片作品呈現田野研究的不同發現。莊孔韶自1995年起提出“不浪費的人類學”的觀點,?稚桐:《“不浪費的人類學”思想與實踐》,《云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4期,第63-69頁。認為人類學家除了傳統的文字民族志之外,還應當“借助多種形式,如小說、隨筆、散文和詩,及現代影視影像手段創作,以求從該族群社區獲得多元信息和有益于文化理解與綜觀”?莊孔韶、王劍利:《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人類學電影攝制》,《贛南師范學院學報》,2013年,第4期,第17-19頁。。在影像人類學的創作領域,劉湘晨、陳學禮、顧桃等一批影視人類學者和紀錄片工作者都圍繞特定群體和地域進行長期拍攝,并剪輯成不同風格和題材的紀錄片,以更加完整地展現文化特質。目前,筆者已經根據田野素材完成了首部紀錄片的制作,即,作為“中國節日志”項目核心成果的影像人類學文本《眾神降臨—陜西省佳縣白云山四月八廟會》(86分鐘)。本文的這一部分將以這部作品為例,探討在剪輯處理田野素材時所面臨的“賦象于聲”的議題。
按照《“中國節日志”項目實施規范》,節日影像志應完整反映節日的現狀,要關注“節日中”“節日前”“節日后”三部分結構,并注意兼顧歷史源流。在視聽創作層面,將傳統節日變成以影像媒介為載體的“志”,需要在人類學田野工作的基礎上,“經由口述、呈現、敘事及風格形成所構成的層級性創作思路”才能得以最終呈現。?劉廣宇、焦虎三:《口述與呈現,敘事與風格—爾蘇藏族“環山雞節”影像志創作后記》,《民族藝術研究》,2014年,第6期,第98-103頁。以紀實性的線性影像文本為最終目標,對于素材的剪裁和組合不可避免地會遇到如何對待節日事項的復雜性、如何平衡儀式與日常、如何揭示文化的深層結構等問題。?劉廣宇:《〈中國節日影像志〉:實踐困境與反思起點》,《貴州民族研究》,2020年,第10期,第62-67頁。按照節日志項目的上述要求與特征,筆者和兩位剪輯師在嘗試了圍繞不同群體和主題的章節式結構后,發現這種方式不利于展現節日本身的基本樣貌,最終決定仍然按照四月八廟會本身的時間順序為結構,將紀實性的場景—事件與解釋性的對白與訪談相互配合、作為影片的主體內容。由于四月八廟會本身周期較長,參與的人物眾多,影片中不設貫穿全片的線索人物和敘事主角,而是將道士、信眾、樂手等不同角色按照他們參與廟會的不同階段串聯進影片中。
在影片中,前期拍攝的音樂事件主要通過兩種方式得以表達。首先是在道教儀式的紀實段落中以同期聲的方式展現代表性的道教音樂,并以說明性字幕的方式介紹音樂的曲牌及其對應的經文名稱。為了確保準確性,字幕內容在粗剪完成后專門與精通音樂和科儀的道士進行核對。其次,影片還包括了兩個音樂表演者的訪談段落。其中,對道教高功曹致平的訪談是在真武大殿的道教科儀之后,他對科儀用樂進行了解釋,并回憶了自己學習寫榜文和音樂的經歷。第二段相關的訪談對象是來自山西的宮姓吹手,這段訪談與白云山黃河渡口的紀實畫面相互配合,回憶的是他少年期間第一次從山西乘船過河來陜西這一側的白云山提供吹打服務時所遭遇的風浪,隨后跟隨的是他們吹奏祈雨曲牌的紀實段落。
在視聽語言層面,“賦象于聲”的問題主要體現在音樂與畫面之間的關系上,這時,“象”主要是指微觀場景中的視覺圖像。隨著有聲電影和同期聲錄制技術的出現,音樂從默片時代的現場伴隨演奏轉變為與動態影像同步的視聽語言要素。在人類學紀錄片中,音樂與畫面主要依靠兩種視聽語言手段發展出不同的關系,進而服務于影像民族志的不同目標。音樂與畫面的第一類關系是同期聲,暗示觀眾這是來自田野現場的原本的音樂。這時,視聽語言層面主要采取的是連續性剪輯的技法,在確保現場感的同時,借助音樂的連續性將不同的畫面整合成為一個完整場景。節日影像志的大部分道教科儀的剪輯采取的就是這一方案,通過代表性曲牌中的連續音樂段落,將原本長達一兩個小時的科儀濃縮為幾分鐘的電影時間。音樂與畫面的第二類關系是配樂,這時,聲音并非來自影片所展現的拍攝現場,具有獨立性。不過,人類學紀錄片領域通常反對沒有任何文化意義的單純承擔剪輯功能的音樂使用,非同期的音樂在影片中應當得到進一步的解釋。這一問題典型地體現在讓·魯什在博士學習期間拍攝的展現非洲土著獵殺河馬的紀錄短片Les Magiciens de Wanzerbé(38分鐘,1948年)中。據推測,讓·魯什當時并沒有進行同期聲錄制,在剪輯獵殺河馬場景時使用了在其他場景中錄制的當地鼓點音樂和咒語的聲音。?Paul Henley.The adventure of the real: Jean Rouch and the craft of ethnographic cinema.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p.46.1954年,魯什回到拍攝地,將這部影片放給當地人看。當地人認為影片音樂是不對的,因為捕殺河馬的時候需要安靜,音樂只會驚擾獵物。?Paul Stoller.The cinematic griot: the ethnography of Jean Rouch.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p.43.
音樂的非同期使用脫離了寫實功能后,人類學紀錄片需要對這類具有獨立性的音樂展開文化闡釋。這時,“賦象于聲”的議題體現在音樂與社會的關系上,“象”主要是指宏觀的社會文化景象。在剪輯《眾神降臨》的過程中,筆者和剪輯師主要試圖通過訪談和解釋性字幕,發展寫實段落中的音樂的非寫實的闡釋功能。例如,在宮姓吹手訪談后所接的祈雨曲牌演奏,就同時具備了寫實與闡釋的功能。廟會期間,山西吹手的主要工作是為信眾集體上供進行伴奏,這主要集中在早晨和上午,白天大部分時間里,他們都會在五龍宮院落休息,遇到信眾較多的時候就隨機地演奏一曲。因此,影片中的演奏段落可以看作是一個常規的紀實段落。但是,剪入片中的曲牌是筆者在田野拍攝時專門挑選拍攝的一支祈雨調,這是五龍宮前眾多演奏內容中的一小段,對這個具體的民俗活動場景來說并不具備典型性。但是,祈雨儀式及其音樂在陜北總體的民俗信仰活動中有很強的代表性,能夠體現區域文化特征。筆者的剪輯目標,是通過這段現場的音樂表演,用此時此地的紀實性的音樂去指涉陜北地區抽象的社會文化景觀。
但是,發揮文化闡釋功能的“賦象于聲”在節日影像志的制作中遇到了兩個層面的挑戰。首先,四月八廟會本身包括的文化事項繁多,行動主體多元,且時間跨度也較大。這種復雜節日客觀上很難用線性結構的影像志表達清楚。影像民族志畢竟是具有固定時間長度的文本,這也壓縮了對于音樂等具體文化事項的闡釋空間。其次,對于如何進行音樂闡釋,本片原本希望主要依靠對表演者的深度訪談,但訪談在影片中的篇幅需要控制,以免影響事件的流暢性和節奏;更重要的是,訪談本身也是一種依靠文字語言系統進行的闡釋,這對于音樂這種聽覺形態在文化實踐中的意義來說并非最合適的影像闡釋手段。道教科儀的音樂具有情緒調控和情景演示功能。?劉仲宇:《簡論道教法術科儀的表演特征》,《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2期,第114;117-119頁。道教儀式的表演和一般的舞臺表演具有不同的假定性,神職人員和信眾都相信借助音樂而產生的人神關系是真實存在的。因而,道教儀式中的音樂表演能夠起到對于信仰的喚起和傳播的功能,引發信眾的情感呼應,達到慰藉效果和心理滿足。?劉仲宇:《簡論道教法術科儀的表演特征》,《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2期,第114;117-119頁。這種主體和具身層面的音樂闡釋,在白云山節日影像志的制作過程中雖幾經嘗試,但最終受制于拍攝素材和剪輯結構的考量,仍然缺失。
四、總結與反思
在影像人類學領域,音樂不僅是一種視聽表達元素,而且也是一個需要闡釋的文化事項。在民族音樂學的田野工作框架和音樂事件的田野拍攝觀念的基礎上,影像民族志中涉及兩類“賦象于聲”的議題。其一,是視聽語言層面對于同期聲音樂的使用,它帶來了田野現場音樂事件的現實主義還原,同時也通過連續性剪輯的視聽方式以音樂為基礎整合與濃縮了紀實畫面,營造出完整連貫的音樂事件場景。其二,是在文化闡釋層面對于音樂的使用,通過音樂在影片中實現更為廣泛的社會文化指涉,呈現音樂與社會的復雜關聯。但是,由于對視聽語言和敘事結構的考量,音樂的闡釋在深度和主體性方面都遇到了挑戰。
在白云山影像民族志這一案例中,道教音樂展現出民間音樂和規定性音樂之間的融合特征,在長時間的歷史和廣闊的文化場域中形成了復雜的音樂發展狀態。在完整呈現節日面貌為首要任務的節日影像志之外,如何進行更加有效的“賦象于聲”的音樂闡釋,筆者認為有兩個視聽策略可以嘗試。第一個策略是仍然遵循傳統的敘事紀錄片的形態,但將音樂作為首要的素材組織原則和敘事結構,圍繞這一主題切入和理解白云山民間信仰。這時,音樂和節日被看作是同等重要的、理解總體文化的切入點。影片與文字相互補充,傳遞更加多元的田野經驗。第二個策略是借助較新的網頁互動和超鏈接技術,將此前嘗試過的章節體敘事結構發展為“數據庫電影”的形態。這時,不同文化要素之間的網狀關聯能夠得到更充分的呈現,觀眾在互動式的觀看中主動地發掘音樂在社會文化結構中的位置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