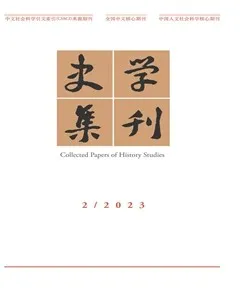西南邊疆環境史上官民互補環保機制研究
主持人語(南炳文):本專欄本期刊發環境史專家周瓊教授的大作《西南邊疆環境史上官民互補環保機制研究——以清代云南二元環保模式為例》。本文以環保碑刻較多、極富代表性的清代云南施行的環保二元機制形成的原因(清代云南生態破壞及環境災害)、實踐及案例為研究對象,探討了制度的維度和彈性對保持與推動生態環境良性發展的積極作用。作者指出:官方及民間環保法制的相互認可及支持是良好環境管理制度的基礎,民間環保法制的補充與彌縫功能是提升官方環保法制公信力的潤滑劑;二元環保機制是鄉土生態環境恢復及重建的制度保障。此文的價值,除了對有關歷史經驗做了很好的總結之外,更應重視其對于以后做好現實生活中的有關事宜具有指導意義。特予推薦。(廊坊師范學院特聘教授、南開大學資深教授)
摘 要: 明清時期,邊疆民族地區環境災害的發生隨著開發的深入日趨頻繁,地方的環境保護逐漸形成了官方法制及民間法制共存互補的二元環保機制。官方推行的植樹禁伐令等措施得到了各民族的認可,民族地區從自然崇拜及鄉規民約、習慣法層面推行的生態聯保措施也得到了官方支持,形成了官方與民間兩種環保法制并存共進、相輔相成的模式,并在具體的生態管理實踐中高度契合。官方認可并支持民間環保法制及其實施,民間環保法制依賴并彌補了官方法制的不足,從而使云南民族區域的生態環境長期保持了良性發展態勢,彰顯出邊疆民族地區二元環保機制的現實資鑒價值。
關鍵詞: 邊疆環境史;清代;云南;二元環保機制;官方及民間并行模式;制度維度
明清時期中國的環境保護機制有兩種模式,一是專制集權統治下官方制度自上而下推行的模式,二是官方制度與民間制度并行互補的模式。因官方及民間的環境保護法制有兩種不同的形態及模式構成,并在特定的時空場域內二者共存,故稱“二元”,這種二元環保法制是中國古代二元法制的代表。明清時期,因農業、礦冶業開發后生態破壞嚴重,故二元環保機制存在于大部分省區,山西、陜西、四川、湖南、云南、貴州、廣西等地留存了大量關于明清環保法制的碑刻史料,①
但從生態環境保護的具體實踐,尤其是從生態環境的保護效應來看,以邊疆民族地區的二元環保法制實踐成效較為明顯,其中又以清代云南的實踐成效最具代表性。云南少數民族養林護水、資源取用有度的制度,與官府植樹育林的制度共行互輔,體現了中國傳統集權體制下民族環境管理中的生態民主制模式。這種二元環保機制實踐的史料大量留存于地方志及碑刻中,是中國傳統的集權統治制度在邊疆民族地區以包容本土制度的方式得以順利推行的典型個案。學界對云南民族生態文化、生態倫理、習慣法等進行了研究,(參見姜愛:《近10年中國少數民族傳統生態文化研究述評》,《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李技文、龍運榮:《近20年來我國民族文化生態研究綜述》,《大連民族學院學報》,2010年第2期;楊平:《近十年來中國少數民族習慣法研究綜述》,《蘭州交通大學學報》,2013年第2期;巫洪才:《中國少數民族習慣法10年研究之述評與反思》,《黑龍江民族叢刊》,2013年第3期。)總結邊疆民族生態觀及其環境保護、生態思想的成果不斷涌現,(解魯云:《云南生物多樣性保護與少數民族生態觀研究綜述》,《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5期。)但多側重于生態思想及環保措施的挖掘,從理論及法制層面探討民族地區環保機制、環保模式的成果尚不多見。本文以環保碑刻較多、極富代表性的清代云南施行的環保二元機制形成的原因、實踐及案例為研究對象,(“云南107塊林業碑文有明、清和民國3個時期,分別占8.4%、69.16%和22.43%,歷經13朝。最多的清時期74塊,其次是民國時期24塊,最少的是明代9塊”。參見李榮高:《云南明清和民國時期林業碑刻探述》,《林業考古》,2002年第1期,第252頁。)探討制度的維度及彈性對保持及推動生態環境良性發展的積極作用。
一、二元環保機制誕生的原因——清代云南生態破壞及環境災害
清代云南各民族在環境保護實踐中形成并傳承了官方、民間環保法制并行的二元機制及實踐模式,與其特殊的歷史進程、民族傳統文化及自然生態變遷、環境災害歷程密切相關。這種二元機制的形成,既是清代集權統治與民族傳統治理方式交融及環境災害凸顯的結果,也是地方統治者及各民族管理者為維護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所采取的環境應對措施。
(一)古代中央王朝在云南的農業墾殖及礦業資源開發對生態環境的破壞
古代不同歷史時期的殖邊拓展及經營都使云南的生態環境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壞,云南的生態環境呈現出極強的時代性和區域性特點。秦漢時期云南除人口聚居較多的滇池、洱海區域得到初步開發外,其余大部分地區都處于原始狀態,物種多樣性特征顯著,瘴氣濃重,( 周瓊:《清代云南瘴氣與生態變遷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嚴重困擾了云南各民族的生產生活及中央王朝的經略。唐宋時期,云南仍是“三春邊地風光少,五月瀘州瘴癘多”( (唐)駱賓王《軍中行路難》云:“去去指哀牢,行行入不毛……川原繞毒霧,溪谷多淫雨……滄江綠水東流駛,炎洲丹徼南中地……三春邊地風光少,五月瀘中瘴癘多……灞城隅,滇池水,天涯望轉積,地際行無已。”參見《駱賓王集》卷三,清嘉慶道光間秦氏石研齋校刻本,第6頁a。)的化外之地,范圍廣大的山區半山區或濕熱的河谷地區依然保持原始狀態。平坦肥沃且水熱條件較好的滇池、洱海區域得到了普遍開發,壩區生態環境開始遭到破壞,河流及水利工程因水土流失而淤塞,農業水旱災害開始增多。但鄰近壩區的半山區的開發力度還不大,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的程度較小,“西道出邛僰,百里彌箐林。俯行不見日,刺木郁蕭森。伏莽有夷僚,巢枝無越禽”( (明)周季鳳纂修:正德《云南志》卷二三《文章一》, 明嘉靖三十二年刻本,第9頁b。)的狀況比比皆是。雖然元代云南土著民族人口稀少、移民也較少,但仍是外來移民少數民族化的“夷化”( 廖國強:《清代云南少數民族之“漢化”與漢族之“夷化”》,《思想戰線》,2015年第2期。)期,人們過著定居及區域游牧相結合(亦耕亦牧)的生活,生態環境長期保持原始狀態。
明清時期,中央王朝加大了對西南民族地區銅、鐵、金、銀、錫、鉛等礦產資源及楠木、杉木、柏木、楸木等珍貴植被資源的開采力度,云南生態環境呈現出了開發—破壞、恢復—破壞、局部恢復—大范圍破壞、再恢復—某些區域徹底及不可逆破壞等曲折的變遷歷程。
明代是中央集權專制統治在邊疆民族地區深入推進的時期,云南人口急劇增加,三百余萬漢族移民涌入民族聚居區進行屯墾,( 林超民:《漢族移民與云南統一》,《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期。)漢族人口數量逐漸超過土著居民,云南少數民族開始出現“漢化”現象,民族分布格局及生產生活方式發生了巨大變遷,經濟開發向半山區和山區拓展,自然地理面貌由此發生了重大改變,區域環境變遷進程由此轉向。隨著農業墾殖及礦業開發范圍的擴大,生態環境的自然恢復能力被人為破壞,原始森林的面積及數量開始減少,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的區域沿著壩區—半山區—山區的開發方向順勢擴展,“蒙樂山中多上古不死之木,大徑數尺,高六七丈不等,山夷不知愛惜,經年累月入山砍伐……十年八年后,土薄力微,又舍而棄之,另行砍伐,惜哉惜哉”。((清)羅含章纂:嘉慶《景東直隸廳志》卷二八《雜錄》,道光九年增訂嘉慶二十五年刻本,第57頁a。)滇池、洱海等成熟農墾區的水災、旱災、泥沙淤塞等頻發,半山區、河谷地區也成為水旱、滑坡、水土流失、泥石流等環境災害的頻發區,“自明開采淘金……歷二百余年,兼以沖沒民屯田地,廠雖封閉,害尤未息……水在中行,田列兩旁,沙填河底,沖沒田地……河溝淤阻,田地盡成沙洲,垅畝盡為荒壤……又恐霖雨泛漲,淹沒闔州,害深禍大”。( 段金錄、張錫祿主編:《大理歷代名碑·種松碑》,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437頁。)深山區因交通不便、生存條件惡劣,很少有人居住,生態環境仍保持原始狀態,如金沙江流域的元謀就是森林茂密、瘴氣橫生之地,“山川多瘴疬,仕宦少生回”,((明)楊慎:《元謀縣歌》,(清)鄂爾泰修、靖道謨纂:雍正《云南通志》卷二九《藝文九》,清乾隆元年刻本,第6頁b。)“達元謀縣,歷黑箐哨,陰翳多淖,出箐至蟲八蠟哨、干海子,林杉森密,猴猱扳援,不畏人……樹多木綿,其高干云。有金剛纂樹,碧干猬刺,漿殺人”。( (明)劉文征撰,古永繼點校:天啟《滇志》卷四《旅途志第二·陸路·建昌路考》,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6-167頁。)
明代的墾殖對云南生態的破壞尚未威脅到當地民族的生存,但清代范圍更廣、力度更強的礦冶及山地墾殖對云南生態環境的破壞,對當地民族的生存發展構成了威脅。康雍以后,隨著移民源源不斷地進入,云南因戰亂災荒損耗的人口數量逐步恢復并開始大幅增長,山多田少(山地面積94%)的云南農墾逐步向山區和森林地帶推進。植被生存空間遭到擠壓,丘陵山地普遍種上了玉米、馬鈴薯等高產作物,山區民族傳統的蕎麥、燕麥、高粱等作物也在坡地廣泛種植,因田頭地角“零星”土地享有按下則田地收稅或永免升科等優惠政策,水濱河尾、山洼坡角的畸零土地被廣泛墾殖,(《清高宗實錄》卷一六五,乾隆七年四月丁巳條,《清實錄》第11 冊,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89頁。)丘陵山地的開發超出了環境的承載度,生態災難逐步顯現。如水利工程因日益嚴重的水土流失及壅堵而不得不每年耗資疏浚修護,( 參見周瓊:《清代云南內地化后果初探——以水利工程為中心的考察》,《江漢論壇》,2008年第3期。)“郡有南北二河……久為沙磧所苦,橫流四溢,貽田廬害,遂發民夫修浚,動以萬計,群力竭矣,迄無成功……積雨之際,涌洪澎湃”。((清)陳廷焴:《種樹碑記》,(清)劉毓珂等纂修:光緒《永昌府志》卷六五《藝文志·記》,云南省圖書館傳抄清道光六年刻本,第25 頁a。)隨著坡地水土流失的面積及流失量增加,很多山腳或河濱田地在雨季或水患被“水沖”“沙壓”“沙埋”后,成為無法墾復的永荒地。如乾隆八年(1743)永善縣“山水泛漲,夾雜砂石,沖壓田地房屋”,(《清高宗實錄》卷二○五,乾隆八年癸亥十一月己酉條,《清實錄》第11冊,第648頁。)滇池“號為膏腴者無慮數百萬頃,每五六月雨水暴漲,海不能容……兩岸群山諸箐沙石齊下,沖入海中,填塞壅淤,宣泄不及,則沿海田禾半遭淹沒”。( (清)鄂爾泰修,(清)靖道謨纂:《修浚海口六河疏》,雍正《云南通志》卷二九《藝文五》,清乾隆元年刻本,第44頁a。)很多膏腴之地因水土流失、土壤肥力下降變成永荒田或暫荒田而被棄耕,“又查出永荒應暫免征條丁公耗官莊等銀……此項田地多因水沖石壓,人力難施,或因水無去路,匯為巨澤……現在可種之地尚且廢棄,此等永荒,斷難遽求墾復”。( (清)岑毓英修,(清)陳燦纂:光緒《云南通志》卷五八《食貨志二》,清光緒二十年(1894)刻本,第25頁b。)
雍正、乾隆朝對云南銅、鐵、金、銀、錫、鹽等礦產資源的集中開采,嚴重破壞了礦區生態環境。礦產采冶煉鑄、鹽井的熬煮都需要大量木炭,致使礦區成百上千年的森林在百余年內耗損殆盡,清人王太岳《論銅政利弊狀》記載:“硐路已深,近山林木已盡,夫工炭價數倍于前”,大部分礦山因山林砍伐及礦產開發殆盡而“硐老山荒”;群居的礦丁也是山地生態破壞的推手,大廠礦丁多至數萬人,礦山林地被耕地居所取代,數量龐大的樵采導致植被的持續性破壞,“從前定價之時,或因彼地糧食豐裕,薪炭饒多……近來各廠商民湊集,食物騰貴,柴炭價昂”。( (清)莫庭芝、(清)黎汝謙采詩,(清)陳田傳證,張明、王堯禮點校:《黔詩紀略后編》卷五《包御史祚永一首》,貴州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25頁。)繁盛一時的銅、鹽生產是清代云南生態遭到破壞的重要動因,“民間薪炭,幾同于桂”的記載常見于史籍,礦山、鹽井周圍十余里甚至四五十里范圍內,青山盡禿,硐荒礦絕,“山多田少,曠野蕭條,加以承平日久,森林砍伐殆盡而童山濯濯”。( 云南省大關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整編:《民國大關縣志稿》卷三《氣候》,大關縣黨史縣志辦2003年版,第53頁。)
19世紀以后,云南生態破壞的災害累積性后果開始呈現。生態基礎脆弱區的水土流失較為普遍,如曾經瘴氣密布的東川、昭通等地因銅礦的大規模開采導致地表覆蓋植被在幾十年內消失殆盡,泥石流、滑坡、塌陷等地質災害日益嚴重,蔣家溝近三百年的泥石流發育史與東川銅礦的開采及植被破壞相同步,小江也成為泥石流多發區(泥石流溝多達107條)。同治三年(1864)小江流域發生的泥石流導致耕地荒蕪,“沖淤田土,不能開墾,奉文永免碧谷壩官莊租米三百一十五石零,小江官莊租米三十四石零”。( (清)馮譽聰續修:光緒《東川府續志》卷一,清光緒二十三年刻本,第12頁a。)連生態環境較好的新平縣水利工程也開始出現淤塞,“水龍……灌溉城南一帶田畝……年久失修,泥沙壅塞”。( 符廷銓修,魏鏞纂:民國《續修新平縣志》卷一一《農政·水利(塘堰·溝洫)》,1919年石印本,第42頁a。)
(二)明清云南各民族傳統生存方式的改變及小冰期氣候巨變引發頻繁的環境災害
制度往往對歷史進程、社會發展及其變遷軌跡產生重要的乃至決定性的影響,也對生態環境及其要素變遷和發展方向產生直接影響。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區域及不同類型的社會制度,對各生態要素、生態系統、生態環境及其發展軌跡都產生了不同的影響。在特定歷史時期,傳統政治統治集團在利益的驅動下,往往將制度作為破壞環境的合法外衣無限制地擴大其影響力。元明清中央王朝在西南大部分地理位置僻遠、生態環境原始的民族地區長期實施土司制度,較大程度地保持了西南邊疆、民族地區的文化傳統及生存生活方式,延緩了對這些地區的開發,使得其生態環境長期保持在原始狀態,土司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當時西南民族地區生態環境穩定、持續發展的保障。( 周瓊:《土司制度與民族生態環境之研究》,《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2012年第4期。)
隨著明清專制統治的深入,很多礦產等資源豐富、戰略位置重要,且長期處于羈縻或臣屬狀態的西南民族土司控制區,相繼被以武力或和平的方式改土歸流,西南民族地區原有的生態保護的政治屏障消失,流官官員迅速進駐,在短期內建立起了有效的專制集權統治秩序,廣泛推行內地實施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措施,把內地礦冶業、農業的開發模式移植到了云南,并以“溥育”“涵化”等方式改變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和生活方式。少數民族對森林、礦產、水等資源的有限利用方式及“夠用即止”的使用心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對生態環境造成了極大沖擊。中央王朝的統治模式及對資源的集中開采方式,改變了西南民族地區生態環境的自然演變趨勢。很多瘴氣叢生的地區逐漸成為生態破壞最嚴重的濯濯童山區,水災、旱災、霜凍和泥石流等環境災害頻發。
同時,明清小冰期的寒冷氣候對云南小區域立體氣候產生了極大沖擊,區域氣候極其不穩定,雨季開始時間及降雨量的年份、月份差異極大,降雨時間及總量受到嚴重影響,從而加快了云南氣象災害發生的頻次,植被及其生態系統的自然恢復速度隨之減慢,生態環境的自然恢復能力及其對極端氣候變化的適應力與抵御力也大大降低,“幾種氣候因子的不利組合大大加大了天氣災害發生的概率和破壞性……云南社會存在著雨季開始早晚、雨季降水的強弱和時空分布以及夏季溫度變化這幾個氣候變化應對的脆弱點,歷史上一些重大的天氣災害常常就發生在這種脆弱點上”。( 楊煜達:《清代云南季風氣候與同期災害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63-164、170-171頁。)明清以來對邊疆經濟開發導致地理、地質結構及生態系統的改變,加劇了寒冷氣候對區域生態環境的沖擊及影響力度。
氣候變遷導致了區域環境的極大變遷,本土物種開始減少或滅絕。因野生動物生存環境遭到破壞,食物鏈斷絕,內地時常出現的虎患、狼災、豹災等動物災害,也開始不時地在云南礦冶區、農墾區及其周邊環境變遷劇烈的地區發生,災年尤甚,“萬歷三十一年,大饑,虎至近郊傷人”,( (清)屠述濂編纂,張志芳主編:《騰越州志:點校本》卷一一《災祥》,云南美術出版社2007年版,第244頁。)“嘉靖十年,虎入州境噬人”,( (明)劉文征撰,古永繼點校,王云、尤中審訂:《滇志》卷三一《雜志·災祥》,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1頁。) “康熙十四年,有虎出姚之西界觀音箐、大苴村食人”,( 由云龍編纂:民國《姚安縣志·災祥》,楊成彪主編:《楚雄彝族自治州舊方志全書·姚安卷上》,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64頁。)“康熙二十四、二十五年,虎復出入于東南界,傷人幾至百數”,( (清)管棆纂修,陳九彬校注:康熙《姚州志》,楊成彪主編:《楚雄彝族自治州舊方志全書·姚安卷上》,第196頁。)宣威州 “康熙五十九年多虎患,噬人數百,守備朱廷貴同土司安于蕃率兵捕之,連殺九虎,患乃平”。((清)劉沛霖修,(清)朱光鼎纂:道光《宣威州志》卷五《祥異》,清道光二十四年抄本,第34頁a。)
18世紀以后,云南干旱、洪澇、風雹等氣象災害的發生頻次增快。嘉慶九年(1804)夏秋間,云南府大雨成災,“富民縣地方于本年七月十七八兩日,大雨如注,晝夜不絕,各處山水匯集,城外之螳螂江一時宣泄不及,十九日子刻,水勢加增,灌入城內,縣城內外民房及衙署、鹽倉、祠廟多有坍塌,近城田禾,間有被淹”。( 水利電力部水管司、科技司、水利水電科學院編:《清代長江流域西南國際河流洪澇檔案資料》,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1804頁。)類似記錄在地方志及官員奏章中不絕如縷,云南有了“氣候王國和自然災害王國,除海嘯、沙塵暴和臺風的正面侵襲外,幾乎什么自然災害都有……往往多災并發、交替疊加、災情重,有‘無災不成年之說”( 解明恩:《云南氣象災害的時空分布規律》,《自然災害學報》,2004年第5期。)的災害記憶。
寒冷氣候導致降雨量和河流來水量減少,部分支流干涸甚至斷流,再加上植被生態系統的退化,從而加速了河谷地區土壤的風化及貧瘠化。風化土在雨季極易流失,引發了河谷生態系統的逆向演替。如森林茂密、環境原始的金沙江、紅河、瀾滄江流域的生態環境開始退化,19世紀以后,這些區域的水土流失日益嚴重,逐漸演變為干熱河谷。山地生態系統的逆向演替導致生態環境的自然恢復能力日漸喪失,動植物生存環境日漸惡化,數量和種類不斷減少,( 楊彪:《瀾滄江流域云南段水土流失及其防治措施》,《林業調查規劃》,1999年第4期。)生態脆弱性日趨增強。
(三)官方與民間的環境災害反思與環保愿望
明清時期,云南因大規模的農墾、礦冶開發及建筑、柴薪等的過度消耗,生態環境逐漸惡化,環境災害增多,地方統治者及士人鄉紳開始思考其發生原因及應對策略,官方及民間的生態憂患及環保意識逐漸覺醒。
首先,統治者意識到了培植樹木對堅固堤岸、保持水源的重要意義,倡導植樹,雍正五年(1727)二月初七日諭:“修舉水利、種植樹木等事,原為利濟民生,必須詳諭勸導,令其鼓舞從事……飭教職各官,切加曉諭,不時勸課,使小民踴躍興作。”(《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五三《史部·詔令奏議類》,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本,1986年,第414冊第541頁。)很多地方官認為植樹護林可以保護水源和河渠堤岸,“山多林木,根盤土固,得以為谷為岸,藉資捍御,今則斧斤之余,山之木濯濯然矣。而石工漁利窮五丁之技于山根,堤潰沙崩,所由致也。然則為固本計……種樹其可緩哉!”((清)陳廷焴:《種樹碑記》,(清)劉毓珂纂修:光緒《永昌府志》卷六五《藝文志記》,清光緒十一年刊本,第25頁a。)
其次,民眾對森林涵養水源功能認識頗深,“森林與水利亦極有關系……山有樹則林深,林深則蔭濃,蔭濃則土潤,土潤則泉流,理固然也。天氣下降,必有樹木以承之,而后可與地氣合;地氣上升,必有樹木以通之,而后可以天氣交,天地交則陰陽合,陰陽合則云雨施,故童山之上或無云,深樹之間或多雨,理又然也。蒙化四面皆山,樹木砍伐殆盡,近十年來或三年一旱,或間年一旱,推原其故……無樹木之所致也”,( 李春曦等修,梁友檍編纂:《蒙化志稿》卷九《地利部·水利志》,1920年鉛印本,第3頁a。)他們擔心若繼續采伐,生態破壞將更加嚴重,“此地龍潭響水,樹木茂盛……今被居民砍伐,漸次稀少……倘再行樵采,數年之后,即為童山”,(《南華“神明永庇”封山碑》,曹善壽主編,李榮高編著:《云南林業文化碑刻》,第113-114頁。)建議種植樹木、制定森林保護規程,以恢復地方生態環境,“排植桑柘數萬株……則蠶桑之利開,旱乾之患可免,而材木亦不可勝用矣”。( 李春曦等修,梁友檍編纂:《蒙化志稿》卷九《地利部·水利志》,第3頁b。)
因此,云南地方官員及民間士人在檢討生態惡化狀況及后果時,幾乎都認識到森林破壞、缺乏管理,以及共同遵守具有約束力法令的失效,是環境惡化的根本原因。于是,制定保護森林及水源等制度,以及對林木樵采、栽種時間進行管制等,就成為官方及民間上層人士的共識,很多官員還以勸民植樹為己任,“久所縈念,思有挽回,雖遞年捐廉購種,以為之倡,奈事無專責……致棄前功……妥定章程,遞年播種”。((清)文源:《稟籌款種松以恤灶艱事》,(清)羅其澤等纂:光緒《續修白鹽井志》卷八上《藝文志·詳議》,光緒三十三年刻本,第41頁a-42頁b。)有的官員開始倡導培植林木以恢復地方生態環境。
二、清代云南官方與民間二元環境保護機制及其實踐
生態意識的覺醒促使云南地方政府、官員及各民族都采取了成效不一的植樹護林等生態治理及恢復措施,促成了不同層域的環保制度的制定,官方倡導實施的環保法制逐漸得到少數民族的認可及實施,各少數民族尊奉的環保傳統和習慣法也得到官府的認可和接受,從而形成了官方環保法制與民間環保法制并行、地方官及民眾共同參與和遵守的二元環保模式。
(一)清代云南官方及民間的二元環境保護法治的建立
云南官方及民間的二元環保機制,是區域環保歷史上一種共存并行、互補互輔的制度模式,創建于清初,成熟于清末至民國年間,衰微于20世紀60—90年代。21世紀以后,民族生態思想、環保法制及其成效才重新受到重視。
第一,清前期官方環保法制在云南民族地區推行,其合法性及權威性得到少數民族的認可。隨著明清專制統治在云南的深入,官方法制開始嵌入傳統民族社會中,如推行皇帝諭旨:“雍正五年十二月初四日……工部等衙門議覆遴選道員采辦木植,奉上諭:各省采辦木植等項,具著該督撫遴選賢員辦理,照民間價值給發,不許絲毫扣克……俾屬員敬謹尊奉,倘稍有不尊諭旨之處,朕必訪聞,將督撫等一并從重治罪。”(《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六四《史部·詔令奏議類》,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414冊第744頁。)在官山官澤、風水重地實施嚴格的封禁令,“刑部奏:酌議風水重地、青樁外官山界內盜伐樹株……應仿照白樁青樁舊制、立定界限……嗣后如在青樁以外官山界內,有盜砍官樹……放火燒山者,均照青樁內于犯滿徒罪上減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從犯再減一等,計贓重于徒罪者加一等”。(《清宣宗實錄》卷三五,道光二年五月丁亥條,《清實錄》第33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630頁。)通過科舉選拔充任邊疆府州縣的官員是執行官方封山禁采育林等環保制度的中堅力量,“勒石釘界,禁止樵采……撥派兵役巡查,并嚴飭地方官隨時稽察”。(《清宣宗實錄》卷二三,道光元年九月丙子條,《清實錄》第33冊,第426頁。)清代云南地方官員推行內地成熟的山林川澤管理制度,故當時的“官方環保”有兩層內涵,一是官府的環保制度及措施,被作為國家權威的象征;二是官員個人的環保行動,被作為代表國家法制且頗具號召力的具體實踐。其權威性及正統性是少數民族認同及擁護官府的基礎,在二元環保法制中發揮著核心及主導作用,具體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
首先,云南地方官府制定了植樹禁伐制度——積極倡導植樹,禁止砍伐森林,違者嚴懲。植樹護堤、禁伐堤樹等保障農業生產的根本性制度在云南得到首倡及推廣,產生了較好的法制效果。
云南的江河渠流岸畔及山坡谷地往往是耕地的集中區,泥沙淤塞比較嚴重,地方政府常常撥專款,并委派專人負責閘壩河堤的維護浚修,“除出示曉諭,并分諭允當、實力興辦外,所有卑職籌款種樹,擬訂章程,諭飭尊辦”。( (清)文源:《稟籌款種松以恤灶艱事》,(清)羅其澤等纂:光緒《續修白鹽井志》卷八上《藝文志·詳議》,第42頁a。)地方官員也積極提倡和鼓勵植樹。“擬請籌提款費百余金,購備松子數石,排植桑柘數萬株,諭飭各約鄉保甲,按照地面戶口發給,山地則種松樹,平地則種桑秧,每戶分種十株,責成保甲巡視,半年之后,官莊清查,有虛文搪塞者罰之,有實心辦理者賞之”。( 李春曦等修,梁友檍編纂:《蒙化志稿》卷九《地利部·水利志》,第3頁b。)督修水利工程的基層官員在筑好堤壩后,立即在兩岸栽種柳樹,既可以起到護衛堤壩和涵養水源的作用,也可以防止水土流失。大理浪穹縣縣城東南九里的三江口河渠泥沙淤塞嚴重,土壩坍塌,知縣陳煒于嘉慶八年(1803)、嘉慶十一年(1806)、嘉慶十二年(1807)筑旱壩種柳樹,“以舊河西岸接旱壩筑堤埂數千丈,種柳數千株以遏河泥”;浪穹蒲陀崆因沙壅浪入經常潰決,多次疏浚修埂后,地方官在堤岸上種植柳樹護堤,“廣植楊柳,禁人斫伐”。( (清)岑毓英修,(清)陳燦纂:光緒《云南通志》卷五三《建置志七》,清光緒二十年(1894)刻本,第10頁a。)鄧川渳苴河泥沙壅塞,水患嚴重,官府在兩岸種植柳樹以固堤岸,“堤皆沙埂,水漲多沖塌……里甲沿堤植柳……以固堤根,用奠安流”。( (清)王師周:《治渳苴河議》,王文成輯,江燕等點校:《〈滇系〉云南經濟史料輯校》,中國書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07頁。)為了保障植樹的順利實施,官方設立了培育樹苗的苗圃。宣統三年(1911),牟定縣建立了鈴陽公園苗圃,( 云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總纂,云南省林業廳編撰:《云南省志》卷三六《林業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8頁。)培育樹苗,供植樹造林使用。
云南楚雄鎮南州龍潭森林被破壞后水源受到影響,“龍潭向來樹木茂盛,擁護靈泉……倘再行樵采,數年之后即為童山”。乾隆四年(1739)二月二十八日鎮南知州“親往踏勘”,他發現“近城居民紛紛樵采”,故聽從民眾建議,頒布禁伐令:“矧此龍潭,澤及蒸黎,周圍樹木,神所棲依……準據輿情,勒石永禁,凡近龍潭前后左右五十五丈之內,概不得樵采。”(《響水河龍潭護林碑》,張方玉主編:《楚雄歷代碑刻》,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325頁。注:五十五丈之“十”,整理者將碑刻“十”誤為“千”,今正之 。)但毀林行為及環境災害依舊頻繁發生,因此鎮南州正堂又發布了不得樵采的禁令,對破壞森林、違反砍伐禁令者予以制裁,并將其作為定制推行:“如敢違禁,斯攜斧行入山者,即行扭稟。”(《南華“神明永庇”封山碑》,曹善壽主編,李榮高編著:《云南林業文化碑刻》,第113-114頁。)乾隆六十年(1795)繼任的鎮南州正堂再次頒布植樹禁伐令:“為圣恩嚴禁砍伐事……仰州屬地方人民漢夷人等知悉,嗣后見性山寺周圍及仙龍壩前后四至之內……栽植樹木,擁護叢林,以滋龍潭。該地諸色人等,不得混行砍伐。倘有不法之徒,仍敢任意砍伐,許爾等指名稟報,以嚴拿重究。”(《南華仙龍壩外封山碑》,曹善壽主編,李榮高編著:《云南林業文化碑刻》,第114-115頁。)嘉慶四年(1799),針對當地放火燒山、毀林開荒導致“山崩水涸”的狀況,臨安府石屏州候補知州發布禁伐樹木的禁令,“毋得再赴山場放火燒林,挖取樹根……砍伐所禁諸樹。倘敢故違……從重究治”。(《石屏縣秀山寺〈封山護林碑記〉》,曹善壽主編,李榮高編著:《云南林業文化碑刻》,第217頁。)
官府的禁伐令對敬服官府統治權威的云南各少數民族而言,具有極大的威懾性及約束力,官方禁伐令逐步在民族地區樹立起了權威性,產生了極好的法治效率。如道光三十年(1805)三月,鄂嘉分州正堂接士民稟告有人私砍老柴窩的樹林后,迅速提訊罪犯,重加罰責;十月,查明士民王億兆等燒山縱火,立即提訊究治,“重加罰責外,出具甘結,日后不得妄伐一草一木”。(《鄂嘉州封山護林永定章程碑》,張方玉主編:《楚雄歷代碑刻》,第370-371頁。)官府對違反禁伐令者一一法辦,對民眾的言行產生了較好的規范作用,建構起了官方法制對民眾行為約束的有效性,對地方生態環境的保護發揮了積極作用。
其次,官員個人率先示范,并親自倡導、執行植樹禁伐令,在云南民族地區環境保護中發揮了極強的示范作用,促進了官方法制的構建進程。
為促使官府倡導的植樹號召更快地被實施,地方官員以勸民種樹為己任,積極在植樹區推進禁伐令。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大理知府在下關東鋪村勸民種松,“合村眾志一舉”,“奮然種松”,當地生態環境迅速得到恢復,“青蔥蔚秀,紫現于主山”,官民心安,“良材之產于此,即廟宇傾朽,修建不慮其無資”。為了更好地保護所植之樹,官員在植樹區推行禁伐令,將種松之山劃為公山,不準隨意進入,禁止破壞或盜伐木材,禁止在松林里“采伐扦葬”,“倘有無知之徒,希圖永利,竊為刊損者,干罰必不免”。(《大理下關市東舊鋪村本主廟護松碑》,段金錄、張錫祿主編:《大理歷代名碑》,第498頁。)
一些官員還率先捐資購買樹種,育苗植樹,對勸導民眾植樹起到了較好的示范及激勵作用。如道光二年(1822)大理巡道宋湘買松子三石,“科民種于三塔寺后”,六年后即見成效,“松已尋丈,其勢郁然成林”。(《大理種松碑》,曹善壽主編,李榮高編著:《云南林業文化碑刻》,第272頁。)道光四年(1824),永昌知府陳廷焴“率民夫挑挖(沙河),復捐買松種數十石,遍種于山根箐腳,以固其源”,((清)劉毓珂等纂修:光緒《永昌府志》卷六《地理志·山川·保山縣》,清光緒十一年刻本,第5頁a。)他植樹的先導行為被村民勒碑記載,成為官方環保法治獲得少數民族認可的感化劑——官員身體力行的示范效應推動了官方法制在民族地區的實施。光緒年間,白鹽井提舉文源籌款種松,“公局每逢年節,有送署水禮,卑職到任時即經裁免,用為種松……通計各節水禮共減的款銀四百七十余兩,按年提出,專作種松常款,選派井紳六人,以一人為總辦,以五人為五井分辦……薪近及遠,使無間斷,培蓄數載,樵采以時……將見林木不可勝用也”。( (清)文源:《稟籌款種松以恤灶艱事》,(清)羅其澤等纂:光緒《續修白鹽井志》卷八上《藝文志·詳議》,第41頁b-42頁a。)
第二,云南民間環境保護法制的實施,得到官府的認可及支持,確立了民族區域環保法制的合法性。云南民族眾多,地理、交通及自然條件復雜,各民族呈大雜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長期延續了樵采、耕作、建筑等與森林密切相關的生產生活方式,官府的環保制度無法深入這些區域。地方士紳采用族人長老商議并決定村寨大事的慣例,召集山林水源林區域的村寨長老商議規程,以勒石立據的方式,制定各村寨、家庭都必須遵守的植樹、禁止放火燒山、保護森林等規約,或將約定俗成且共同遵守的習慣法頒行各村寨,長期遵守。這些更接地氣的環保制度與官方環保法制的目標無疑是一致的,地方官府便因地制宜,認可并支持民間環保法制的實施,促使各民族村寨形式多樣的護林護水等傳統環保規制成為民間具有較強約束力的合法法制。
首先,云南地方官府支持民族地區的鄉約及習慣法。各民族地區類型豐富的護林護水等鄉規民約和習慣法,是各民族在長期的生產生活中形成、發展起來的,以兩種方式存在及傳承,一是以文字、文本形態存在,是村民共同商量及討論后制定的,以鄉規、寨規、合約、規約、禁約、公約、村規為主,刻于石碑上,或以契約、文書等形式存在,這些鄉規民約是基層法制的核心及基礎。因為有確切的文字記錄,所以這些鄉規民約具有極強的正規性和權威性,受到族長及村民的尊奉。二是無文字(非文本)、以口頭傳承等方式存在,以各民族約定俗成、各村寨共同尊奉的習慣為主,作為區域性民間法律長期被沿用,代代相傳,這是在民族傳統思想意識及行為習慣的基礎上形成的鄉村約束機制,被稱為“習慣法”。
清代云南民族地區普遍存在的鄉規民約和習慣法,以保護森林、水源林及水源、水利等護林禁伐、違者嚴懲的法令為主。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立于陸良縣馬街鎮如意龍潭的《禁樹碑記》記載:“合村會議,將糧田近于龍潭左右者盡種松子……其成功宜同心以嚴禁斧斤……不可怠于栽培……倘不遵公義,違者稟官究治。”(《陸良縣馬街鎮如意龍潭〈禁樹碑記〉》,曹善壽主編,李榮高編著:《云南林業文化碑刻》,第161頁。)乾隆四十六年(1781)立于楚雄紫溪山的《鹿城西紫溪封山護持龍泉碑》記載了村民對樹木涵養水源功能的認識及保護樹木的鄉規:“大龍箐水所從出,屬在田畝,無不有資于灌溉。是所需者在水,而所以保水之興旺而不竭者,則在林木之陰翳,樹木之茂盛,然后龍脈旺相,泉水汪洋。近因砍伐不時,挖掘罔恤,以致樹木殘傷,龍水細涸矣……益加栽培……如有違犯砍伐者,眾(重)處銀五兩,米一石,罰入公。”(《楚雄市〈鹿城西紫溪封山護持龍泉碑〉序》,曹善壽主編,李榮高編著:《云南林業文化碑刻》,第157-158頁。)類似的民間環保法制在民族村寨普遍存在,官府對其持認可及支持態度,只要村寨將違犯鄉規民約者報官,官府就按各民族的處罰規則進行制裁,如嘉慶十三年(1808)立于祿豐縣川街阿納村土主廟的《封山育林鄉規民約碑》記載:“請立樹長、山甲,須日日上山巡查……建造木頭……未報而私砍者,罰錢三百文……松栗枝葉,不容采取堆燒田地,犯者每把罰錢五十文。”(楊泰撰:《祿豐縣川街阿納村土主廟封山育林鄉規民約碑》,曹善壽主編,李榮高編著:《云南林業文化碑刻》,第241-242頁。)這就為民間環保法制持續發揮環保效用提供了根本性保障,也為各民族在更大程度上接受官方法制奠定了基礎,表現了地方官府對民間環保法制的包容態度。
其次,云南各民族出于培植風水等原因,制定的保護村寨林木及水源的寨規村令,是官方認可的民間環保法制的重要內容。云南各民族長期以來與大自然相依相存,十分敬畏大自然及其相關神靈,他們認為森林植被與風水、地脈、生存及災害密切相關,能保護村寨生生不息、繁榮昌盛,將土地、山林、河流視作生命的根基和源泉,一些與山林、水源和動物有關的禁忌和習俗逐漸成為約束人們行為的規范被自覺遵循。明清時期,隨著漢族移民不斷移入山區,云南各民族生存空間變小,在生存及經濟利益的驅動下,保護環境的原始宗教崇拜和習俗受到極大沖擊,各族人們的生態保護思想及觀念逐漸淡薄,隨意砍伐森林的現象突出,區域性環境災害隨之增加。因此,各民族重新重視傳統的護林保水法規,并將其勒石立碑,作為永久遵循的規章制度。
傣、彝、壯、白、苗等民族對良好生態環境與民族生存發展,以及對農業經濟及水源利用的關系有深刻的認識,他們認為森林與地方風水密切相關,對生態破壞造成的水源枯竭等后果深有體會。乾隆五十一年(1786)楚雄蒼嶺區西營鄉所立《擺拉十三灣封山碑記》記載:“名山大川,實賴樹木以培植風水。”(《楚雄市〈擺拉十三灣封山碑記〉》,云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總纂,云南省林業廳編撰:《云南省志》卷三六《林業志》,第286頁。)趨利避害的傳統風水觀使云南各民族保護森林、不得隨意砍伐的生態意識逐漸凸顯,并制定了禁伐幼小林、有計劃伐林的規章制度。如道光四年(1824)廣南縣舊莫鄉底基村《護林告白碑》記載:“嘗聞育人材者,莫先于培風水;培風水者亦莫先于禁山林。夫山林關系風水,而風水亦關乎人材也。”(《廣南縣舊莫鄉底基村湯盆寨護林告白碑》,曹善壽主編,李榮高編著:《云南林業文化碑刻》,第284頁。)并要求全體村民“仍照古規,培根固木,將寨中前后左右山場樹木盡封”。江川縣《萬古如新護林碑》記載植樹有關“村中之風水”。(《江川縣〈萬古如新〉護林碑》,曹善壽主編,李榮高編著:《云南林業文化碑刻》,第409頁。)安化鄉柏甸村民宣統三年(1911)重申林木保護傳統,認為森林茂密會使風水隆盛、衣食自裕,給地方帶來富貴吉昌的好運,若無森林樹木,“則殺氣顯露,災害自生”,各村公議后,規定保護公私山場林木,禁伐林木尤其是禁伐幼小樹木,否則予以處罰;遇紅白事、起蓋房屋等,應有計劃采伐,公私山場所產樹株不準私賣他鄉。(《江川縣安化鄉香柏甸村〈保護山林碑〉》,曹善壽主編,李榮高編著:《云南林業文化碑刻》,第506-507頁。)乾隆二十九年(1764)武定縣護林碑就認為,森林是柴薪、風水之源,“生木以供薪,故永不可少”,種植松林“一以供薪,二則培植水源”,對隨意砍伐踐踏森林者處以重罰。(《九廠鄉姚銘護林碑》,曹善壽主編,李榮高編著:《云南林業文化碑刻》,第124頁。)
光緒十八年(1892)丘北縣立的護林碑記載,森林豐茂與否與風水及水源枯竭有密切關系,“風水所系,土民養命之物,向以封禁”,樵采過甚會導致水源枯竭,“昔之年,山深木茂而水源不竭;今之日,山窮水盡而水源不出”,鼓勵植樹,不準砍伐,甚至也禁伐樹枝樹葉,“以培風水”。(《錦屏鎮上寨村永入碑記》,曹善壽主編,李榮高編著:《云南林業文化碑刻》,第436-437頁。)光緒十八年(1892)祥云恩多摩乍村彝族立的護林碑也強調森林乃風水所攸關、水源之所系、民生之攸賴,規定龍潭附近樹木不得隨意砍伐,制定了護林巡防的鄉規。(《東山彝族鄉恩多摩乍村護林碑》,曹善壽主編,李榮高編著:《云南林業文化碑刻》,第439頁。)道光四年(1824)廣南縣舊莫鄉湯盆寨的護林碑記載,林木茂密有助于保護風水,有助于人才輩出,“育人才者莫先于培風水,培風水者亦莫先于禁山林。夫山林關系風水,而風水亦關乎人材也……林木掩映,山水深密,而人才于是乎振焉……仍照古規,培根固木,將寨中前后左右山場樹木盡封……若有不遵……送官處置”。(《廣南縣舊莫鄉底基村湯盆寨老人廳護林告白碑》,曹善壽主編,李榮高編著:《云南林業文化碑刻》,第285頁。)
類似的民間護林條規在云南民族地區比比皆是,相關碑刻及例證不勝枚舉。這種出于培植風水、保障水源林目的的村規,受到云南各族尊奉;官府出于保護森林的目的,也支持此類法規的實施。官方環保法制與民間環保法制并行,成為云南各民族聚居區良好生態環境保持的重要保障。
再次,云南各民族原始宗教信仰及禁忌中神圣動植物及其場域的保護習俗及法規等,也是得到官方認可的民間環保法制。云南山高谷深、江河險峻的地理狀況及原始險惡的自然環境,制約著各民族的生存及發展,“萬物有靈”是各民族普遍存在的觀念,山川河湖、溪潭飛瀑、花草樹木、飛禽走獸、日月星辰、風雨雷電、森林樹木、獸龜龍蛇、祖先神靈等均成了不同民族的圖騰崇拜對象,對自然神靈的崇奉思想及言行成為引導各村寨生產生活的行為準則。因此,各民族村寨都有一個或多個得到人們共同敬奉的神林(神樹)神山(崖)、圣湖(潭)神泉(井),村民不得隨意進出這些區域,也不得隨意褻瀆、毀壞崇拜物。如不許砍伐神林神山中的樹木草木、不射殺動物飛禽、不掃葉積肥、不扔污物、不置葬;不在圣湖、神泉等水源區洗滌、捕魚或喧嘩,不讓牲口踐踏,不丟棄臟物、不吐痰等。因此,壯族和傣族的村寨及水邊的古樹(保命樹、靈樹)、獨龍族村寨及家族“難郎地”的樹木,都作為祭祀崇拜對象存在了成百上千年。迪慶藏族不砍神山上的一草一木、不獵殺一鳥一獸。( 楊士杰:《論云南少數民族的生產方式與生態保護》,《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5期。)這些崇拜行為促成的各民族愛護森林及水源的良好習慣和行為美德,成為云南民族生態思想和精神文化的核心內容,并成為各族人民嚴格遵奉的習慣法律。
總之,很多這種植根于自然崇拜等基礎之上,并在客觀上起到保護神林(樹)、神井、神泉、神湖作用的習慣及傳統,與官府環保法制的目標高度一致,并得到官方的認可,從而使村寨習慣法的合法性得到確認,對各民族地區生存環境的保持和發展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民族聚居區長期保持了森林茂密、物種繁多、水源豐沛的優美景觀,“夫塘愈多則蓄水愈廣,蓄水廣則分溉者自眾。故雖旱魃為災,厄于天者,或可補救于人也”。( 李春曦等修,梁友檍纂:民國《蒙化志稿》卷九《地利部·水利志》,第1頁b。)
(二)清代云南官方及民間二元環保法制共存并行的實踐
專制統治及法令的一統性是清代集權政治的特點,官方的環保法制具有毋庸置疑的權威性,在云南推行時如得到少數民族的認同,就會更加順利施行,雍正十一年(1733)六月二十一日,“著傳諭該督撫等轉飭有司……其應行補種柳樹之處,按時補種,并令文武官弁禁約兵民,不得任意戕伐,倘有不遵行,將官弁題參議處,兵民從重治罪”。(《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三二《史部·詔令奏議類》,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415冊第669頁。)而云南各民族的基層法制只有獲取官方的認可及支持后,才能確立自身的合法性及權威性。因雙方目標一致,故云南逐步構建起官方、民間二元并存互補的環保機制,凸顯了官府對民間環保法制的包容認可,以及少數民族對官方法制的認同和依賴,體現了傳統專制體制下特殊的區域民主環保模式,這是中央王朝對邊疆民族地區羈縻統治模式在另一種意義上的延伸。
清代云南民族地區的環保法制內容多以碑刻的形式得以留存,其間留存的生動案例,反映了官方環保法制與民間環保法制共存互補的史實。這既是云南各民族借助官府的正統性和權威性制裁不法者以達到保護環境之目的,也是官府確立官方法制在民族地區合法性的實踐,雙方為共同目的達成共識,維持了生態保護模式的長效性,體現了官民二元環保模式的民主特色和良好的環保成效。
最典型的案例是楚雄府鄂嘉州護林碑記載的官方環保法制與民間環保法制并行的實踐。道光三十年(1850)二月十三日,鄂嘉州州判接到村民黃金鎧、王豐泰報案,有人私自砍伐老柴窩山樹木,燒炭爭地,筑窯洞燒石灰,致泥沙壅塞、水源枯竭,“闔里糧田無水灌溉”,州府立即將私自砍伐者拘拿提訊,重加責罰。村民擔心再發生類似事件,懇請州官“永定章程,保護泉源,俾世無乏水之患”,州官訪查后認為“老柴窩所發之泉,歷代灌田食水……豈容卑鄙小人妄行刊伐,開挖燒炭,使泉源無所庇所,致有干涸之患?”官府便發布了“示仰漢夷人等知悉”的告示:“不惟不準開挖燒炭,即使取薪者亦不準登山剪伐,倘敢不遵,許該約扭稟來署,按照絕人飲食以致死罪者律訐辦,絕不寬容。”同時規定官府“隨時稽察”,違者治罪法辦,并制定了五條曉諭各村的保護水源林禁令:不得放火燒山打獵、不得筑窯燒炭燒石灰、不得開挖種地、不得采取柴薪、不得放牧牲畜,并委托鄉約執行者監管,“以上各條,俱系有關水源來脈,仰大村里鄉約遞年稽察”,這是官方環保法制明確規定支持民間環保法制的案例。此章程頒布僅半年,“士民王億兆等擾官藐法,縱火燒山”,且老柴窩山附近邦糧山、核桃山、老鐵廠村民不斷伐樹,水土流失嚴重,“幾至樹株伐罄,沙泥壅塞,殊于水道大有窒礙”,官府即令村民沿山“撒種松秧,培植樹木,至于炭窯,概行拆毀”,并令合邑漢夷共同遵守,違犯者嚴懲,包庇者同罪,“倘有再赴老柴窩山箐刊發一草一木,以及開挖種地筑窯燒炭者,許該鄉保等指名俱稟,以憑鎖拿到案,不特治以應得之罪,且必從重罰銀……若隱不報,并及是案嚴懲,本分州言出法隨,絕不稍寬”。(《鄂嘉州封山護林永定章程碑》,張方玉主編:《楚雄歷代碑刻》,第370、371頁。)該禁令落款除“道光三十年十月三日”官府“示”字以外,還有“合邑士民同立”字樣,反映了該禁令是官府、村民共同頒布實施的。這是一則反映官、民法制共存并行、相互認可的具有法制效力的環保禁令,是雙方利用對方在基層社會中的權力優勢共同執法的典型個案。道光朝鄂嘉州官府不僅認可民間鄉規民約,還依仗鄉約在民間的約束效力執行官方禁令;鄂嘉州的民間鄉約也存在與官方法制結合的明確意圖,借助官方權威使鄉約在更大程度上得到民眾認可、遵守及傳承。
大理彌渡縣彌祉山的護林法規也是一則官民二元環保法制并行的典型案例。該地生態環境長期以來保持良好,“彌祉太極山老樹參天,泉水四出……千家萬戶性命,千萬畝良田,其利溥矣”,(《彌祉八士村告示碑》,曹善壽主編,李榮高編著:《云南林業文化碑刻》,第515頁。)但后來森林被村民破壞,水源及農業生產受到威脅,“近者無知頑民砍大樹付之一炬……深林化為荒山,龍潭變為焦土。水汽因此漸少,栽插倍覺艱難,所以數年來雨澤愆期,泉水枯竭,莊稼歉收”。(《彌祉八士村告示碑》,曹善壽主編,李榮高編著:《云南林業文化碑刻》,第515頁。)光緒二十二年(1896)牛街瓦臘底村村規禁止伐樹,違者罰銀十兩;(《彌祉八士村告示碑》,曹善壽主編,李榮高編著:《云南林業文化碑刻》,第518頁。)光緒二十九年(1903)大三村《封山育林告示碑》規定,盜伐松樹者“準鄉約、伙頭、管事、老民將……送官究治”。(《彌渡縣紅星鄉大三村〈封山育林告示碑〉》,曹善壽主編,李榮高編著:《云南林業文化碑刻》,第473頁。)這種官方環保法制與民間環保法制共存并行的模式,一直持續到民國年間。民國二年(1913)八士村村民稟縣知事陳禎,有“頑民”亂伐致龍潭干涸,陳禎出示通告,規定不準濫砍亂挖森林,“永遠勒石”,同時,村民也制定了懲罰規制,“藉資灌溉而重森林……亂砍濫挖者,即由該村董、百長五十長等集眾罰議,以示懲儆”。(《彌祉八士村告示碑》,曹善壽主編,李榮高編著:《云南林業文化碑刻》,第515-518頁。)
嘉慶四年二月,通海縣秀山的森林保護制度也是官方及民間環保并行模式的典型案例。該森林保護制度實施時間較長,表明了二元環保法制不是臨時的,而是一種長效性的法制模式。此制度是通海縣秀山“闔郡老幼”匯集于隍祠商量“妥議”后制定的,“令鄉保同小的稟明天臺,懇恩出示,將寶秀壩前面周圍山勢,禁止放火燒林”。(《秀山封山護林碑》,黃珺主編:《云南鄉規民約大觀》上冊,云南美術出版社2010年版,第103頁。)光緒二十七年(1898)八月,開遠白棕棚村民確定的鄉規民約條例也是請地方官員“給示勒石,以正鄉規,永遠遵守”,(《開遠白棕棚一同碑》,黃珺主編:《云南鄉規民約大觀》上冊,第110頁。)以官方、民間環保法制并行方式推行。宣統二年(1910)江川縣林木保護碑,也是官民二元環保機制的典型案例,“蓋聞條例不經官示,雖眾論至公,亦屬徇私制事,不順人情,即當面服從,實難終理固然也”。(《江川縣永遠遵守護林碑》,曹善壽主編,李榮高編著:《云南林業文化碑刻》,第503頁。)
可見,云南民族地區這種普遍存在于官方環保法制圈之外的、松散的民間環保法制得到了官方的認可及支持,成為官方禁伐令的重要補充,在官方法制不能覆蓋及深入的村寨起到了較大的約束及規范作用,使民族區域環保法制在最大范圍內發揮了最好的環保功效,這是官、民環保模式并存的基礎。二元環保機制是邊疆民族環保法制史上的極佳范式,雖然“禮失而求諸于野”不一定是絕對現象,但中國傳統生態法制的很多原生內涵,無疑在邊疆民族聚居區得以流傳和保留。少數民族崇拜尊奉神靈、敬拜并祈求神靈護佑,保證生存資源長期供養族人的意愿,不自覺地把自己看作自然界一個與其他生物處于同等地位的生物個體,這種與自然環境共存共榮的意識,以及其用口耳(或文字)傳承的習慣法或鄉規民約等民間環保法制,客觀上保護了生態環境,踐行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在中央王朝統治深入后,官方環保法制與民間環保法制相互認可、相互支持,民族地區的生態環境得以按自然演變規律演進,從而保存了云南生物多樣性的典型特征,云南民族地區的生態環境得以長期保持良好狀態,如“天柱峰在鎮西山前……四圍虬松老樹,蒼翠欲滴,時有珍禽翔止”,((清)何愚、(清)李熙齡纂修:道光《廣南府志》卷二《山川》,清光緒三十一年重抄本,第4頁b。) “圭山在州治東,其山樹木蔭翳,禽鳥喧集,鹿豕潛游,山巔有池,盛旱不涸”,( (清)金廷獻修,(清)李汝相等纂:康熙《路南州志》卷一《山川》,清康熙五十一年刻本,第25頁a。)“月濤山在治西六十里……山勢險峻,林木茂密,古樹頗多,高八九丈,直徑約三四尺,禽獸孳生甚繁。半個山在治西四十里馬路沖村……諸峰矗立……上多山禽猛獸,林木蓊翠挺拔”,( 朱偉修,羅鳳章纂:民國《羅平縣志》卷一《地輿志·山川》,1933年石印本,第51頁a。)凸顯了適應區域環境特點的二元環保法制的獨特魅力,在保持水源、涵養水土、避免洪旱與泥石流等自然災害、維護區域生態平衡及生物多樣性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清代云南民間環保法制對官方法制的補充與彌縫效應
清代云南二元環保法制最為突出、最值得肯定的效應,是在一些生態破壞嚴重且官方法制未能覆蓋或發揮作用的地區,民間環保法制發揮了不可或缺的補充與彌縫作用。官方環保法制一般偏于宏觀及理性,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以鄉規民約和習慣法為主體的民間環保法制則偏于微觀層面,適于具體問題的解決,尤其是在各民族鄉規民約及習慣法中有官方法制沒有明確規定、無法發揮約束效能的內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彌補官方環保法制的缺陷,二者形成了較好的共存互補模式。具體有三方面的表現:
一是各民族的公山禁伐令彌補了官方法制在公山植被保護方面的缺失。云南傣、彝、白、納西、傈僳等民族都是定居山區半山區的尚水尚火民族,對森林的依賴及需求很強,一般經各族村老寨長商約后,除在各族神山、神樹、神泉區選定特定區域外,劃定一定面積的公山,供薪爨及建筑之用,但因產權、責權不明,公山成為集中采伐地,植被損減,水源枯竭,水土流失嚴重,水利工程淤塞,田地被水沖沙埋。道光初年永昌知府陳廷焴《種樹碑記》記載:“先是,山多材木,根盤土固,得以為谷為岸,籍資捍衛;今則斧斤之余,山之木濯濯然矣。而石工漁利,窮五丁之技于山根,堤潰沙崩所由致也。”( (清)陳廷焴:《種樹碑記》,(清)劉毓珂纂修:光緒《永昌府志》卷六五《藝文志記》,清光緒十一年刊本,第25頁a。)官方法制沒有對民族村寨公山的管理條款,但各村寨的鄉規民約有相應的公山植樹和保護森林的法規,雖然其形式及內容各異,卻形成了對官方環保法制的第一重補充。
各地方志及碑文詳細記載了各村寨公山環保法制形成的原因及內容。如大理老君山下的公山林地被村霸顏仁率、李萬常盤踞砍伐燒空,墾為耕地,不久后水源枯竭、栽種維艱,乾隆四十八年(1783)十月十二日,村寨鄉老族長合議,認為老君山乃合州之龍脈,農業水源所攸關,應保全山上森林,制定了保全水源林鄉約:嚴禁在水源區伐樹、嚴禁放火燒山,禁止砍挖樹根、販賣木料,“務尊律紀條規,保全公山,如敢私占公山及任意砍伐、過界侵踏等弊,許勘山人等扭稟,以便究治,絕不姑寬”。(《大理劍川縣金華山麓保護公山碑記》,段金錄、張錫祿主編:《大理歷代名碑》,第501-502頁。)嘉慶四年云南石屏縣秀山寺碑文記載:“原寶秀一壩,周圍皆崇山峻嶺……在昔,樹木深,叢山浸水,栽插甚易。今時山光水小,苦于栽種。弊因各處無知之徒,放火山林,連挖樹根,接踵種地,以致山崩水涸。及雨水發時,沙石沖滯田畝,所得者小,所失者大,數年來受害莫甚于此。”( 《石屏縣秀山寺封山護林碑記》,曹善壽主編,李榮高編著:《云南林業文化碑刻》,第216頁。)當地民族制定了護林禁伐、保護水源林的村寨法令,“禁止放火燒林、挖樹根種地,并禁砍伐松柏、沙松和株木等樹”。( 《石屏縣秀山寺封山護林碑記》,曹善壽主編,李榮高編著:《云南林業文化碑刻》,第217頁。)
云南各族鄉規民約規定禁伐公山樹木,違者嚴懲。大理洱源右所鄉蓮曲村后的紅山原是樹木蔭翳之地,道光年間公山管理不嚴,“斧斤伐之之后日,每不見其濯濯乎?”光緒八年(1882)六月村中父老商定:按戶出夫栽種松樹,以供薪柴建筑之用,為杜絕無良之徒假公濟私、擅自伐樹的后患,制定了不能毀伐松林,違者嚴懲的法規,“欲以公辦也”。(《洱源右所鄉蓮曲村栽種松樹碑》,段金錄、張錫祿主編:《大理歷代名碑》,第604頁。)光緒三十三年(1904)昆明官渡區禁伐公山碑曰:公山植樹,“歸由公處照管保護……不準私家砍伐,若公處動用樹木,亦必須修寺蓋廟,大公至正之事,方能砍伐……自示之后,無論何人,不準私砍公山樹木”。(《官渡禁止砍伐公山樹木碑》,曹善壽主編,李榮高編著:《云南林業文化碑刻》,第484-485頁。)
公山禁伐鄉約是云南各族村寨通行的、約束力極強的民間法制。在少數民族的傳統認知里,習慣法是其日常生活中世代遵守、不能違反的禁令,因此,習慣法的生態保護功能更強,對官方法制的補充效應也更為突出。如鶴慶縣大水渼合村護林碑規定:“從來公山之木嘗美……因世道猖狂,將松樹盡皆燒毀,兼之砍伐殆盡……茲合村會集公同酌議,定下章程……再有執斧斤而砍伐松樹者,罰銀一兩入公……南山坡地一半之松樹,亦古遺之公山,凡偷松之規程,亦似此之辦也。”(《鶴慶大水渼護林石碑》,曹善壽主編,李榮高編著:《云南林業文化碑刻》,第475-482頁。)民族村寨通行的鄉規民約和習慣法的有效性甚至超過了官方法制,是二元環保法制推行的基礎。
二是民間環保法制對森林火災的嚴格防范,補充了官方森林防火法制的缺失。云南冬春干旱,在農林牧交錯區和生產生活混雜區,森林火災最為常見,是森林大面積損毀的隱形殺手。但清代云南地方官府很少有防火效果較好的森林防火法令。民族村寨的環保法制卻制定了較好的防范林火的規定及措施,體現了民間環保法制在山林防火方面的強烈意識及實際行動,這是民間環保法制對官方環保法制的第二重補充。
云南森林火災有自然及人為原因,如開墾燒荒、狩獵燒炭、取暖做飯、上墳祭祀等都是引發森林火災的誘因。部分刀耕火種的民族為燒一小片荒地或獵獲一只野獸就會引發林火,燒掉成百上千畝森林,對各民族生產生活造成嚴重影響。為減少森林火災,許多村寨自發訂立禁止縱火燒山等相互監督、共同遵守的鄉規民約。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景東縣者后鄉制定了種松樹蓄養水源、培植棟梁之材、禁火封山的鄉規,取得了良好的生態效果,“不數年林木森然,薈蔚可觀”,但因管理不善,樹木被采伐殆盡,經石巖村公議,決定照舊封山育林,禁止縱火焚山、砍伐樹木,禁止毀樹種地,違者重罰,其中罰銀33兩的規定使很多人不敢冒險違犯。(《景東縣者后鄉石巖村封山碑》,曹善壽主編,李榮高編著:《云南林業文化碑刻》,第355-357頁。)同年昆明西山團結鄉多依樹等五村立的鄉規民約碑第一條就是“放火延燒山林者罰銀五兩入公”,第二條規定“盜竊松包在山燒剝者,每包罰銀一錢”,( 《昆明市禁止砍伐公山松樹碑》,曹善壽主編,李榮高編著:《云南林業文化碑刻》,第486頁。)體現了民間環保法制對山林防火的重視。
類似法規在云南生態良好的民族地區普遍存在。如嘉慶四年通海秀山護林碑記載:“將寶秀壩前面周圍山勢禁止放火燒林……仰附近居民漢彝人等知悉示后,毋得再赴山場放火燒林……倘敢故違,許爾鄉保投入扭稟赴州以憑,從重究治,決不姑貸。”(《秀山封山護林碑》,黃珺主編:《云南鄉規民約大觀》上冊,第103頁。)道光八年(1828)鎮沅州“為給示嚴禁盜伐樹木燒山場事”立碑,要求民人李澍等在種樹木之處立界址,不讓牲畜踐踏,若有混行砍伐、縱火盜伐不遵禁令者,罰銀十兩充公;(《鎮沅直隸州永垂不朽碑》,曹善壽主編,李榮高編著:《云南林業文化碑刻》,第307頁。)道光三十年(1850)雙柏縣鄂嘉鄉護林碑規定“不得放火燒山、打獵”;(《鄂嘉鄉護林碑》,黃珺主編:《云南鄉規民約大觀》上冊,第91頁。)宣統年間墨江哈尼族立的護林防火碑認為林木是山之“皮毛”,山林火災會傷害昆蟲,“嚴禁放火燒山事。自來山以草為毛……地方相連,草木見缺,不能禁止,后來出草必更艱辛。況放火燒山,傷害昆蟲較多,非唯有害地方,亦共大損陰德,自今之后,若有人放火燒山,拿獲罰銀三兩三錢”。(《墨江團結鄉護林防火石刻碑》,曹善壽主編,李榮高編著:《云南林業文化碑刻》,第510、511頁。)墨江團田、新撫、壩溜等鄉都發現了清末民初制定的禁止野火燒山、砍伐樹株的石刻。
云南民族地區防范森林火災的鄉規民約,雖然是各民族在生產生活中自發形成的,但其根本目的和宗旨與官方法制高度一致,促進了地方性的官方法制的發展。清末,部分地方官員開始在區域治理中重視森林火災的防范,如光緒年間白鹽井提舉文源奏請設員巡查、撲滅森林火災,“每罹野火,致棄前功,乃復集紳灶籌維……培蓄數載,樵采以時……諭飭村莊頭人,認真稽查,如見野火,刻集村人,立往撲滅,赴井照章領賞,倘見火不管,準由卑職就近差提就賠,用昭懲勸……立案飭尊在案”。((清)文源:《稟籌款種松以恤灶艱事》,(清)羅其澤等纂:光緒《續修白鹽井志》卷八上《藝文志·詳議》,第41頁a-42頁a。)官府對當地生態環境的保護顯示出了更多的積極性,得到了村民的認可及遵守,這是民間環保法制彌補、推進了官方法制的積極效應。
三是云南少數民族對生存資源適度利用的機制,彌縫了明清時期官方法制的不足。對資源適度、有計劃利用的思想及原則得到了各少數民族的認同及遵從,并作為約定俗成的、共同遵守的制度確立下來,從而彌補了官方法制在資源限制開發方面的缺失,這是民間環保法制對官方環保法制的第三重補充。
少數民族的環保法制較好協調了人類生存需求與森林及資源保護的關系,制定了培植森林供用材及柴薪適度采伐的鄉約。如宣統二年(1910)江川縣護林碑記載,因“人心不古”及亂砍亂牧,“沿山樹木若彼濯濯可慨”,經官方曉示、民間公議后決定,各戶同心協力廣種松秧、培植雜樹,派人看管,待成材后按山林歸屬地有計劃地采伐;(《江川縣永遠遵守護林碑》,曹善壽主編,李榮高編著:《云南林業文化碑刻》,第503-504頁。)對已成材的樹木只許采枝葉作柴薪,禁止伐樹及挖取樹根,以保持森林的自育能力。一些鄉約還對適度采伐柴薪做出規定,如咸豐七年(1857)鶴慶州護林碑規定:“所有迎邑村人培植松樹,只準照前規采枝割葉以供炊爨,不得肆行殘害。至于成材樹木,毋許動用斧斤混行砍伐。示后倘有故犯,定即提案重究。”(《永遠告示碑》,張了、張錫祿編:《鶴慶碑刻輯錄·環境保護》,大理白族自治州南詔史研究學會2001年版,第230頁。)牟定官村護林碑記載:“婦女入山抓拾落地松毛、墊背枝,不準砍扭松、櫟樹枝……入山挖疙瘩,只準取干枝,不準挖活樹疙瘩,過年不得采摘青松毛鋪墊。”(《官村封山護林山規碑》,曹善壽主編,李榮高編著:《云南林業文化碑刻》,第568頁。)因此,對生存資源適度、有計劃利用的原則,是鄉規的重要內容。如光緒三年(1877)江川縣規定“種植樹株……以濟后人之柴薪”,制定了公私樹林保護及林材有計劃使用的規則:不能砍樹,只能修撿枯枝,公私樹林各自管理,不得相互侵占,“私不得與公爭論樹株,公亦不得估騙私家之山”。(《江川萬古如新護林碑》,曹善壽主編,李榮高編著:《云南林業文化碑刻》,第409-410頁。)光緒二十九年(1903)大理彌渡縣紅星鄉育林碑規定有選擇、有計劃地采伐山林:“凡川中牧樵上山,只準砍伐雜木樹,不準砍伐果木、松樹及盜修松枝。”(《大三村封山育林告示碑》,曹善壽主編,李榮高編著:《云南林業文化碑刻》,第472-473頁。)這使民族地區儲集了豐富的林材資源,“夷人以畜牧為利,其木多松,以備棟宇,他邑取資焉”。( (清)李毓蘭修,(清)甘孟賢纂:光緒《鎮南州志略》卷二《地理略·疆域》,清光緒十八年刻本,第6頁b。)
保護幼林使之成材、以持續使用森林資源,是少數民族鄉規民約中不可缺少的內容。如大理劍川沙溪西北半山區石龍村白族民眾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勒于本主廟殿廡主山墻上的鄉規碑,制定了禁止亂砍樹木尤其不準亂砍“童松”的鄉規,若亂砍山場古樹和水源樹,一棵罰錢一千;砍童松者處重罰,拿獲砍童松一棵者罰銀五錢。(《蕨市坪鄉規碑》,曹善壽主編,李榮高編著:《云南林業文化碑刻》,第352-354頁。)江川香柏甸村護林碑規定不準砍賣小樹,“拿著每挑罰谷一斗,凡打樁者,每棵定銀壹分”。( 《江川安化香柏甸村保護山林碑》,曹善壽主編,李榮高編著:《云南林業文化碑刻》,第507頁。)
少數民族有限度地使用自然資源的法制更有利于資源的節約使用及環境的保護,“統而言之,補山為上,取材次之,不言利而利在其中矣”,(《(大理下關市東)舊鋪村本主廟護松碑》,段金錄、張錫祿主編:《大理歷代名碑》,第498頁。)達到了維護人與環境和諧穩定及長效發展的目的,這種樸素的生態理念及法制實踐彌補了官方法制的缺失及不足。不同民族的環保法制及內容雖有差異,卻是大同小異,在交融互鑒中促成代代相傳的人—林、人—山、人—水、人—生物共存共生的共性理念,在官方法制未能深入及覆蓋的區域,發揮了維護本土生態良性發展的功效,從而奠定了很多民族地區保持良好生態環境的基礎。云南民族地區較高的植被覆蓋率及原始的生態環境常見于各類史籍記載,“七村龍潭在七村河上,廣袤可百畝,深不可測,水中無荇藻,潭旁古木參天,樛枝蔽日,木葉下墜,鳥輒銜去,故潭水極清,時能興云作霧”。((清)李毓蘭修,(清)甘孟賢纂:光緒《鎮南州志略》卷二《地理略·山川》,第24頁a。)“文廟公山,距城西北二十五里……面積約二十五方里,森林茂密,產松子,量極多,為縣屬公共林場,邑中以樵蘇謀生活者多取給是山”。(楊必先等纂修,王金鐘重抄:民國《江川縣志》卷五《地下·山川》,1934年稿本重抄影印本,第133頁。)“馬臺鄉、邦東鄉、平村鄉林區……如珍貴之椿樹、香樟、象牙木、杉松、黃心藍、柏木、紫柚木均廣,他如青木、紅木、樗櫟、檞抃、楷構亦繁,青松則觸目皆是,不勝計其數;泰山鎮、興文鄉均居縣城西南,所轄各保均松蔭夾道,綠樹交蔭,極目千杉,悉松杉柏木及毛栗青木、紅木、黃心藍楷木等木類,不勝枚舉”。( 丘廷和纂修:民國《緬寧縣志稿》卷一一《農政》,云南省圖書館藏1948年抄本,第13頁a-14頁b。)
三、清代云南官方及民間環保二元機制的當代啟示
清代云南民族地區在實踐中建立起來的官方、民間環保法制相互認可、共存并行的二元模式及其成效,對當代生態恢復、環境治理及生態文明制度建設,有極大的現實資鑒作用。
(一)官方及民間環保法制的相互認可及支持是良好環境管理機制的基礎
清代云南二元環保法制能長期并行互補,有歷史的原因,也有民間環保法制本身的原因,二者共存互輔的模式,在現當代環境保護及生態恢復中,依然有存在與延伸的適應空間。
第一,官方法制對民間法制的認可,是民族地區的基層法制認同并支持官方法制的前提。元明清三朝對云南民族地區長期實施羈縻制及土司制度,專制統治長期未能深入,官方法制的作用及效能較為有限,民間法制在各民族的社會生活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隨著清代專制統治的深入,官方法制開始嵌入云南傳統民族社會中,而官方環保法制順利推行的前提,是需要得到各民族的認同及支持。對官方法制而言,民間法制的認同也具有統治合法性被認可、統治措施得以順利推行的特殊意義。因此,官方對云南各民族環保法制的存在及施行給予的包容、認可及支持態度,贏得了各民族的認同。少數民族的認同、支持及配合,對官方法制的順利推進發揮了較為重要的作用。
同時,云南的氣候、生態環境、地形地貌、民族情況及其歷史文化發展情況比較特殊,官方法制不可能面面俱到,也不可能在每個民族聚居區都能順利推行,因此,在官方法制缺失的地區,民間法制的補充、彌縫功效就顯得尤為重要,這是清代維持官府在民族地區統治長治久安的基礎。
第二,云南少數民族及其法制所具有的包容性、融合性和對官方的依賴性,是民族區域社會穩定、官方法制得以施行的基礎。云南各民族在長期的生產生活中形成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共存共生的思想觀念,認為人是自然界的組成部分,自然崇拜行為極為普遍。自秦漢以來,云南就是地廣人稀之地,自然資源豐富,不同類型的移民源源進入,民族認同感較強,對外來民族具有較強的包容性,也有較強的主動融合與被動交融的特點。這種歷史發展慣性及文化傳統,在清代各民族環保機制的建立及實施中表現較為突出,由此賦予了民間法較強的包容性特點。清代云南各民族的習慣法及鄉規民約的具體內容彰顯出的對自然界生命的尊重、愛護的態度及行為,不自覺地延伸到官方環保法制中;官方環保禁伐法制對民間環保法制的類似內容及措施起到了較強的強化作用,成為官方及民間環保法制的并行模式存在的人文基礎,也是這種模式長期存在的前提。
清代云南的民間法制對官方法制認可的另一原因,與云南各少數民族長期以來形成的對中央王朝及其權威的依賴傳統有密切關系。漢晉至元明清以來在云南推行的羈縻政策及土司制度,使各民族在不違反中央集權統治的前提下,保持或基本傳承了原有的社會組織形式和管理機構,保留了各自的歷史文化傳統,民族頭人也借官府鞏固自己在民族地區的統治,逐漸形成了較強的民族向心力、歸屬感及依賴感。因此,民間環保制度推行時不僅需要各民族的認同,也需要得到在政治、經濟及文化、軍事上更強大的官方的認可及支持,才能更好地存在及發展,這種自源性的依賴需求,正是官方所需要的。而改善及保護環境以保障地方農業經濟發展,也是官方的目標及需求,于是,官方環保法制及民間環保法制很快達成一致,民間法制認同、執行官方的環保法制,官方環保法制也包容、承認、支持民間環保法制的有效性,二者在共存互補的基礎上形成了良好的、極具現實資鑒價值的二元模式,使各民族的鄉規民約代代傳承,實踐并傳承了中華民族多元傳統生態文化的內涵。
第三,官方環保法規及民族習慣法、鄉規民約的共存并行模式,在環保實踐中成效良好。清代以降,在農業、礦業開發高潮過后,得益于亞熱帶濕熱溫暖的氣候及降雨優勢,云南一些環境自我恢復和更新完善能力較好的區域,生態有所恢復。很多民族聚居區或民族文化傳統保持較好地區的生態環境,經過短暫破壞后也得到修復,不僅因為這些區域具有良好的自然地理條件及氣候,而且也得益于二元環保模式及其卓有成效的生態管理實踐。換言之,清代云南官方環保法制對民間環保法制的兼容與認可、各民族(民間)對官方法制的依賴及認同,促生了中國環保史上官方環保法制與民間環保法制共存并行、相輔相成的二元環保模式,從而使民族地區的生態環境長期保持在良好狀態。這是云南保有“植物王國”“動物王國”“生物多樣性基因庫”等美名的原因之一。
一項完善有效的環保機制的誕生、實施及持續發展,不僅與官方的主持及倡導密切相關,也與不同區域、民族的文化傳統密切相關。清代云南地方官府根據具體情況,有效利用民間法制尋求依靠的契機,使民間法制成為官方法制順利貫徹的基礎及保障,官方法制借此潛移默化地深入民族地區,“同治十三年,禁止砍伐森林,城北土官箐樹借以培養水源,兵燹后無恥之徒任意入山砍伐……知縣左維奇特示禁止”。( 符廷銓修,魏鏞纂:民國《續修新平縣志》卷二《政典志·法禁》,第33頁。)這在中國古代環境法制史及中國法制一體化歷程中,都具有較強的典型性,在現當代環保法制構建中具有資鑒價值。
總之,明清云南民族地區實施的二元環保法制,是以官方法制為核心、以民族民間立法及信仰為基礎的高度契合的機制,構建起了一張官民尊奉的環保法制網,對民族區域環境的保護起到了積極作用,緩解了生態危機,穩定了區域生態系統,對當代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具有借鑒作用。
(二)民間環保法制的補充與彌縫功能是提升官方環保法制公信力的潤滑劑
在清代云南民族地區實施的二元環保機制中,民間環保法制最突出的功能是彌縫、補充了官方法制在具體問題及微觀措施層面的缺失,提高了官方法制的公信力,對當代生態治理及環境保護制度建設,有資鑒意義。
第一,官方制度與民間制度在生態管理及治理中的高度契合,使官方法制的合法性及執行力大大提高。顯而易見,少數民族生態環境管理制度雖然比較切合實際,但也存在較大的局限性,即只在封閉、傳統、同質性強的區域社會中有較好成效,但隨著清代內地化進程的加快及農業礦冶業的迅速發展,云南各民族地區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環境災害頻發,本土生態承載力及其資源的有限性、生態管理機制的局限性日漸凸顯,民間環保法制的合法性及權威性受到質疑,急需官方法制的支持。官方法制雖具備民間法制缺失的權威性和穩定性,卻存在覆蓋不周、長于宏觀失于具體之弊,在具體案件處理中不得不倚靠具體性、針對性較強的民間法制,或與民間法制配合執法,使民間法制發揮了補充輔助作用,呈現出雙方無法替代且高度契合的互補性特點。
官方環保法制在民族地區推行時,很多官員采取的植樹護林、捐資買樹的措施,以及對民間環保法制的支持,達到了垂范民眾、緩解生態危機的效果,為官方環保法制的實施奠定了社會基礎,增強了官方環保法制的合法性及公信力,達到了補充及鞏固官方環保法制的作用;民間環保法制是各民族在長期生產生活實踐中形成的傳統生態維護機制,由村民集體會議討論制定,依靠本民族的文化傳統和信仰體系進行傳承,有深厚的群眾基礎及實施空間,具有高度的地方認同性,能在更大層域上彌補官方環保法制在區域生態恢復及保護中的缺失,雙方并行互補、共進共贏,進一步提升了官方環保法制的有效性,取得了較好成效,這是區域生態恢復及治理中值得借鑒及推廣的模式。
第二,二元環保機制有助于推進環境保護法治的民主化建設。清代云南官方及民間環保法制在植樹護林方面的趨同性,使雙方在具體案例的判定實踐中采取了相互認同、包容及支持的做法,在區域生態恢復、生態系統穩定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為現當代環保立法的多維共存開創了成功先例。少數民族民間通行的環保措施及法制能發揮良好作用,與官方注意到民間法制的積極作用并持包容、認可態度密切相關,村民對鄉規民約、民族宗教信仰、習慣法等的遵守及參與慣性,使其對官方法制持有較大的信任度和接受度,從而使官方制度在實踐中能潛移默化地體現其優勢,展現了清代集權體制下基層生態民主法制的特點及其實踐的成功優勢。
在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宏觀視域下,推行國家法制的同時發揮鄉規民約在基層社會中的規范作用,化導其積極主動的生態保護理念與行動,是當前生態管理的主要任務,“通過發展少數民族習慣法提升制度認同、公眾參與和自律秩序的形成,著力公民角色、文化兼容和一體格局的建設和拓展,從而形成多元治理秩序,推進民主環保法治建設”。( 苗澤一:《法治中國語境下的少數民族習慣法的發展》,《貴州民族研究》,2016年第4期。)在這種民主環保法制的屬性下,官府無疑也包容了邊疆少數民族把自己視為自然界的生物個體、適度使用資源以保障生存資源持續再生的理念,雖然有的生態觀是以原始宗教崇拜及禁忌的方式體現,主觀上存在尊奉神靈以求護佑、保證生存資源長效使用等目的,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客觀上卻達到了保護生態、延緩環境危機的效果,在增強基層環保法制高效執行力的同時,豐富、更新了中國傳統的法制體系。
(三)二元環保機制是鄉土生態環境恢復及重建的制度保障
制度是環境管理及恢復的前提及保障。在環境變遷的諸多驅動因素中,制度是最根本、最能動的人為動因,影響并決定著環境變遷的方向及結果,調控著生態系統的演替及服務功能格局。恢復及重建本土生態環境、讓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系統永續發展,是當代生態治理的重要目標。
第一,鄉土生態環境的良性發展需要復合的、有維度的環保制度的保障。清代云南各民族的法制多保留于碑刻及民間文獻中,以鄉規民約及習慣法的形式被世代尊奉,在中央王朝統治深入后,在官方法制尋求支持及認可之時,民間法制以認同、支持官方法制的方式,得到了官方法制的支持及認可,從而形成了包容互補、共存并行的復合性的二元環保機制,這是最適合民族地區鄉土生態環境良性發展的制度,對各民族地區本土生態環境及原生生態系統的保持發揮了巨大作用。清代云南地方官府對民間法制的認同,在另一種層面上給予了適合本土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特點的民間法制以適當的存在空間,用有效的、持續的制度保障了鄉土生態系統的演替及發展,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有了存在及實施的前提。如果官方環保法制給民間環保法制留有空間,民間環保法制也遵奉官方環保法制,二元環保法制存在及實施中的維度優勢就能較好展現,區域生態環境的保護及恢復重任就能實現,生態屏障的建設及保護才能成為可能。
在二元環保法制的約束及教化下,各民族形成了共同尊奉官方及民間法制的傳統,其保留至今的生態觀、生存理念及其對植被的保護措施,在區域生態系統的良性發展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延緩了生態惡化的進程。因此,秉持、遵守國家生態環境的基本制度,充分挖掘各民族傳統生態文化及民間環保機制,弘揚資源適度利用的原則,將一些曾發揮功效但即將失傳的民族傳統生態習慣法或鄉規民約,通過制度、法律及文化教育等方式確定下來,并賦予當代環境和資源保護的內涵,與現當代環保理念及具體措施相結合,就成為當代生態環境管理的重要任務。
第二,二元復合的環保制度的存在及實踐不是單一、孤立存在的,其實施及運營需要一整套完善的社會體系及制度的支撐。制度的產生及建設往往基于現實的需要及促動,以持續規范某種行動或行為模式;制度模式的建立及傳承不僅需要社會及人文環境的督促、維護,而且也需要人文思想及文化傳統的塑造。云南各少數民族傳統的生態法制,以及文化中尊重與保護自然生態系統穩定的鄉土生態觀,取得了良好的鄉土生態環境保護成效。但這種成效的取得,絕對不是只單純依靠法制的約束力,而是在各民族的傳統生態思想、生態信仰、生存理念、生態禁忌習俗和環保行為等文化及社會基礎的規范、涵育下取得的。
隨著現當代社會的發展,傳統的環保機制及模式也需要進行調適,二元或多元環保機制的良好成效也需要環境教育的普及,以及公眾環保意識的建立、科學技術及社會經濟實力的提高、官員及相關人員以身作則的示范、公眾參與及跨地區跨國的合作交流等多層面的協調及配合。挖掘并促使各民族優秀生態文化在生態文明建設中成功實現轉型,是當前基層生態文明建設不可忽視的環節。
第三,生態韌性的強化及生態系統的地方性、本土性特點的保持是生態文明建設及區域環境保護機制建設中需要重視的問題。歷史上二元環保機制的內在邏輯及本土生態系統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是本土生態韌性建立及存在的基礎,而區域的生態韌性及其不斷增強的動力則是當前西南邊疆的生態安全及生態形象建設的前提與保障。借鑒歷史時期邊疆民族地區官方與民間共存互補的二元環保機制,實踐國家立法與民族區域立法、官方法制與民間法制相結合的模式,尤其各民族全民參與并奉行環保法制的經驗,將環境保護融入生產生活的實踐中,堅守人與自然、人與生命或非生命共存共進的生態整體觀,不僅可以對現當代區域生態恢復及生態安全、生態屏障的建設,乃至對生物多樣性的保護、恢復等工作,都能發揮極大的支撐及資鑒作用,而且也可以對人類自身的可持續發展起到積極的保障作用,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愿景目標才能實現,生態文明時代也才能真正來臨。
生態系統的本土性是生態治理、生態恢復等機制建設中必須堅持、不可喪失的基本理念及原則。生物入侵、生物災害及生態系統的崩潰,在當前的生態危機及生態屏障建設中早已不是陌生的話題,要順利實現生態命運同體的愿景,必須重建、恢復本土生態系統并保持其健康、良性的更替發展態勢。要達成此目標,只有充分發揮官方制度與民間制度的彈性優勢,循序漸進,以某些生態恢復、更新能力較強的區域為核心區,持續恢復、培植符合各地生態特征的生態系統,使本土生態圈的范圍不斷擴大,再以官方法制為核心,調動并發揮民間法制全民參與環保的優勢與能動作用,制定出與之相配套的、符合區域立地條件的生態恢復與治理的措施及政策法規,由點及面地恢復區域自然環境,才能構建起一個個生物類型及生態系統各具特點、穩定并持續發展的生態圈,建立起兼容并包、因地制宜、互補并行的二元或多元生態機制,達到保障本土生態系統的平衡及持續發展的目的,最終建立起“千地千面、各具特色”的生態命運共同體,展現多樣性及鄉土性生態系統充滿韌性及持續性的特點和優勢。
責任編輯:孫久龍
A Study of the Complementar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Civilians in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Southwest Frontier:A Case Study of the Du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odel in Yunnan in the Qing Dynasty
ZHOU Qio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nvironmental disasters in the border areas inhabited by ethnic minorities became more and more frequent with the deepening of development. In the lo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dual protection mechanism of coexistence and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the official legal system and the folk legal system was gradually formed. Official measures such as tree planting and logging ban had been recognized by all ethnic groups, while ecological protection measures carried out in ethnic areas from the aspects of nature worship, village regulations and customary laws had been officially supported, forming a mode of coexistence and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official and non-government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s, which was highly compatible in specific ecological management practices. The government recognized and supported the folk legal system and its implementation, the folk legal system relied on and made up for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official legal system, which enable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Yunnan ethnic areas to maintain a long-term sound development trend, highlighting the practical value of the du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chanism in border ethnic areas.
Key words:history of frontier environment; the Qing Dynasty; Yunnan; du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chanism; official and civilian parallel mode; institutional dimension
收稿日期:2022-02-12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災害文化數據庫建設”(17ZDA158)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周瓊,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環境史、災害史、災害文化史、生態文明史。
① 碑刻史料的環境史及生態價值研究成果豐富,如倪根金:《中國傳統護林碑刻的演進及在環境史研究上的價值》,《農業考古》,2006年第4期;曹善壽主編,李榮高編著:《云南林業文化碑刻》,德宏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李鵬飛:《從碑刻看清水江流域民間生態行為》,《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2016年第3期;周飛:《清代民族地區的環境保護——以楚雄碑刻為中心》,《農業考古》,2015年第3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