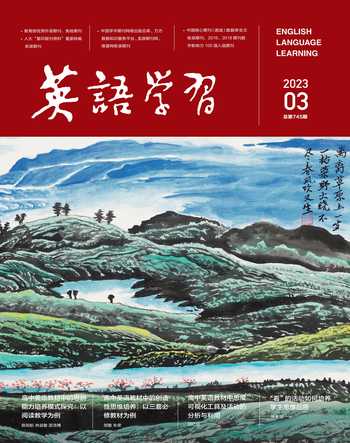他者的社會化:哈克貝利·芬的成長
摘? ?要:《哈克貝利·芬歷險記》通過一個未成年人的旅途成長經歷探討成長的社會性和建構性本質。哈克因“非人”的芬老爹,成了小鎮社會中的“病人”—— 一個有自殺沖動、沉默的他者。哈克在旅途中通過角色操演參與岸上生活,在反復實踐中成長為兼具社會審美認同和道德認同的書寫者。但哈克未抵達旅程的終點就重新啟程,他的成長是一種持續的建構。
關鍵詞:《哈克貝利·芬歷險記》; 他者;成長;社會化
引言
《哈克貝利·芬歷險記》(以下簡稱《哈克》)是一部經典的成長小說,講述了小流浪漢哈克在密西西比河上順流冒險的成長故事。旅途中,哈克時而在河上,時而在岸上,“上岸—離岸”構成小說情節的主要單元,為哈克的成長勾勒出時間和空間的軌跡。哈克每次上岸,幾乎無一例外地要喬裝打扮一番,使用虛構的身份融入岸上生活。一路走來,哈克虛構身份的變化直接體現在他的偽名上——莎拉·威廉姆斯、瑪麗·威廉姆斯、莎拉·瑪麗·威廉姆斯、喬治·彼得斯、喬治·杰克遜、湯姆·索亞等。無論扮演誰,他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在岸上暫得棲居。那么,為什么哈克只能以虛構的身份在岸上暫得棲居呢?
《哈克》中,馬克·吐溫把一個成長因子置于“岸上—河上”二元對立的結構中,如同在一個培養基中投入一粒種子,一邊培育,一邊觀察,看看它到底如何成長。小說中“成長”的內涵向來受到評論家的關注。張德明(1999)結合人類學和心理學理論探究小說中的成人儀式原型結構和哈克成長的關聯,他肯定“岸上—河上”二元對立的存在,借用榮格心理學術語闡述“河上的世界代表了哈克的‘自性,而岸上的世界代表了‘他性”,而哈克的成長是不斷返現“自性”與“他性”,最終“達成個人與社會、內心與環境的平衡”。顯然,此處的“自性”與“他性”之說關照的是哈克的內部經驗,而未充分關注哈克的社會身份。郭晶晶(2017)提到吐溫多部小說中的易裝情節,認為哈克的易裝策略體現對二元對立的消解。但其筆墨之少讓人意猶未盡。要探究哈克成長的本質就必須同時關注“種子”與“培養基”。小說的“岸上—河上”二分世界中,岸上是小鎮的棲息地,是社會主體之所在;而河上是哈克的避難所,是他者的棲居所。芮渝萍(2004)認為,“成長……意味著一個人從他者和邊緣的地位走向主流文化的中心,實現了他者的主體化和邊緣的中心化”。孫勝忠(2020)指出,“成長小說中,社會化的實現往往被視為主人公‘成熟的標志之一”。可見,成長小說中往往存在成長的社會化維度,成長對象的社會化過程常構成作品重要的敘述內容,而現有研究對這一點的關注不夠。從個人與社會關系的角度來看,《哈克》通過哈克這個未成年“他者”的成長經歷來探討成長的社會性和建構性本質。
小說中存在他者與社會的二元對立,他者哈克在社會中的成長是逐漸社會化的過程。囿于原生家庭,哈克生而為他者,在社會中陷入存在的困境。但是,通過他者的角色扮演,他者與社會之間的張力得到釋放,他者以虛構身份在社會中暫得棲居,哈克在這一過程中逐漸被社會接納。小說中,哈克被社會的接納并不意味著旅程的終點;他的重新啟程,意味著他的成長是一種持續的建構。
他者在社會中: “非人”“病人”“自殺”“沉默”
小說開篇,哈克講述了在寡婦道格拉斯家的生活:一天的教養和訓誡結束后,哈克回到房間,靜坐窗邊,本想刻意想些讓自己快意的事情,卻徒勞無果,他難掩內心真實的聲音:“真悶得慌,我想死掉算了。”(吐溫,2000)“死”字從哈克嘴里脫口而出,顯示了哈克潛意識中的自殺沖動。涂爾干認為,自殺是“集體疾患”的表象(轉引自趙立瑋,2014),也就是說,自殺的根本原因要去社會中尋找。哈克在文明的訓誡中流露出向死之心,不得不使我們關注他的社會處境。《湯姆·索亞歷險記》中寫道,“鎮上所有的母親都實實在在討厭哈克貝利,也害怕他,因為他不務正業、不守規矩、舉止粗俗、行為惡劣,還因為所有孩子都羨慕他,喜愛私下跟他交往,希望自己敢于像他那樣自由放任”(吐溫,2004)。顯然,哈克是小鎮上的問題少年,是小鎮生活的他者。哈克之于小鎮社會即是邊緣他者之于主體現實。
“他者”是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和生態批評中常提及的術語。“他者”存在于不平等的二元對立關系中,比如,女性是男性的他者,東方是西方的他者,自然是人類文明的他者。一面是主體、中心、權利、話語,而另一面是客體、邊緣、義務、沉默。小說中,密西西比河造成的地理分割恰恰象征一個二分的世界,岸上是群體小鎮的所在,而河上是邊緣人的避難所。細讀小說不難發現,小說中存在諸多邊緣人物,他們在岸上難以棲身,無不與密西西比河聯系密切。哈克和吉姆是陸地逃亡者,只能在密西西比河上漂流生活。騙子“國王”和“公爵”也是陸地逃亡者,他們與哈克在河上相遇。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哈克的父親芬老爹(Pap Finn),他仿佛只是一個河邊暫住者 ,但是他的尸體浸泡在密西西比河中。而岸上世界則是要“文明化”哈克,要制裁吉姆、騙子和芬老爹的地方。王楠(2015)認為,權力把個體塑造成知識的主體,規訓身體,使其臣服和吸納社會規范,而欲望的主體為了存在只能選擇服從, 并在對權力/律法或社會規范反復吸納和引用的過程中,被生產出一個屈從的主體。小說中的岸上小鎮是主體與權力的容器,也是規訓個體并生產主體的社會性空間。作為不完全屈從的越軌個體,那些邊緣人在岸上世界勢必會遭遇坎坷。借用伯格和盧克曼(2019)的比喻,“如果把日常生活至尊現實比作生活的‘白日,邊緣情境就構成了生活的‘黑夜,它在日常意識的四周不懷好意地埋伏著”。社會的至尊現實對他者“不懷好意”的埋伏不會置之不理,他者要么被治療,要么被虛無(認為它不存在)。換言之,社會的越軌者在日常生活中要么是需要治愈的“病人”,要么是根本沒有資格接受治療的“非人”。“病人”和“非人”均體現他者在社會中的存在困境。
伯格和盧克曼(2019)說:“一切個體都出生在某個客觀的社會結構中,在這里他遇到了負責自己社會化過程中的重要他人……重要他人將世界中轉給他,并在中轉過程中對這個世界進行修改。”哈克的他者身份之因要追溯至他生命之初的重要他人——芬老爹。芬老爹與小鎮之間的矛盾從出場就已昭然若揭。他無視小鎮的律法與規范,欺凌法官、詆毀學校、偷走哈克,并公然向小鎮宣戰,最終是他管住哈克。芬老爹是社會里的“撒旦”,而哈克是“撒旦”的繼承人;或者說,芬老爹是第一代他者,哈克是第二代他者。
第一代他者芬老爹是小鎮中的“非人”。王楠(2015)將巴特勒作品中“less than human”的表達譯作“非人”,指“一類被變成主權/法的例外但又被包含在國家之中的主體”(王楠,2016)。小說第五章,新上任的審判官想教芬老爹重新做人,吐溫小說原文的表達是“…he was a-going to make a man of him”(吐溫,2008)。言外之意,“he is not yet a man”;或者說,“he is less than a man”,他是“非人”。審判官煞費苦心地把芬老爹帶回家,準備耐心教育他,芬老爹也積極表現,誠心坦白,承諾戒酒。這不僅感動了審判官,更感動了芬老爹自己,二人相擁而泣。可是,一天不到芬老爹就原形畢露,酩酊大醉時還險些丟了性命。審判官幡然醒悟:能讓芬老爹改變的恐怕只有火槍了——這一結論恐怕是鎮上其他人早已認同的了。火槍能做到的無非就是斷了芬老爹的氣,讓他從人變成尸體。顯然,真給芬老爹一槍是行不通的,但這結論已然給他判了死刑,芬老爹在小鎮人看來只是一具行尸走肉。
“非人”的判決不只來自小鎮,芬老爹在潛意識中與小鎮共謀,也非人化自己。芬老爹是嗜酒如命的酒鬼,如哈克所見,“每次他拿到錢就喝個爛醉,每次醉了就到鎮上到處惹事,每次惹了事就被關起來。這對他正合適,這種事情他最拿手了”(吐溫,2000)。芬老爹酗酒是一種自我麻醉,酒醉下的芬老爹是譫妄的精神錯亂者,他的不安和恐懼常常在酒后爆發。在恐懼的鬼影前,芬老爹感覺自己遭到追殺,只能無奈大喊“讓一個可憐的家伙自己待會吧!”。芬老爹在被幻覺干擾時,把流著自己血液的兒子看成了死亡天使的化身,一心要消滅他。芬老爹的弒子行為是一種自殺表現。精神錯亂的芬老爹既被追殺又在自殺,芬老爹也是手持火槍的人,芬老爹的自殺實則表明他其實內化了岸上世界的觀念,潛意識之中對自己進行非人化,他實則是岸上世界的同謀者。
在共謀的他者和小鎮社會之間的第二代他者哈克也表現出種種病癥,他則是有待被治療的“病人”。這些病癥其一便是語言的失效或沉默。哈克在寡婦家時,時常發生語言的誤解。比如,道格拉斯說他是“一只可憐的迷途羔羊”(吐溫,2000), 他卻以為人家在罵他是牲口。哈克索性放棄了語言溝通,所以當華森小姐教訓他時,雖然他內心有想法,卻不會說出來。當哈克在寡婦家中感到焦慮時,湯姆·索亞的出現立刻讓他擺脫了絕望和死亡的氣氛。湯姆和其他孩子是小鎮的正常孩子,他們的世界并不像成年人那樣封閉,他們為哈克與社群之間搭起了一座溝通的橋梁。但值得注意的是,起初哈克在和鎮上孩子們玩耍時,基本上是個沉默的角色。孩子們與大人不同,他們在一起時會有更多的肢體交流,仿佛身體是無意識領域,比語言領域更公平。即便如此,哈克和湯姆之間仍存在裂縫。小說第三章,當哈克試圖與湯姆交流想法時,出現了這樣一段:
“我說,我們為什么看不見呢?他說如果我不那么無知,只要看過一本《堂·吉訶德》的書,不用問就會明白了。他說那都是魔法變的。他說那里有好幾百名士兵,還有大象和財寶等,有魔法師和我們為敵,他們把那些東西都變成了一所兒童主日學校,完全是出于惡意。我說好吧,那我們要做的事兒就是去找那些魔法師了。湯姆·索亞說我是個笨蛋。” (吐溫,2000)
哈克繼續與湯姆爭論了一番,但最終湯姆制止了爭論并罵哈克是“一個標準的大笨蛋” (吐溫,2000)。 湯姆表現得像華森小姐一樣,當他和哈克意見不合時,便勒令其閉嘴并辱罵他;而哈克對湯姆也像對華森小姐一樣,即便心里不能認同,卻也緘口不語。“語言構成了社會化最重要的內容,也是社會化最重要的工具”(伯格、盧克曼,2019)。哈克身在小鎮社會之內,實則在小鎮社會之外,語言的失效和沉默恰是他游離在小鎮社會系統之外的表現。此外,同芬老爹相似,哈克也被某種不可名狀的自殺沖動誘惑著。他在寡婦道格拉斯家不時感到窒息般的孤獨感,順口說“死掉算了”。他更是在逃離小鎮之際,布置了自己被謀殺的血腥現場,完成了“自殺”,而這場儀式上的“自殺”恰是哈克自救之旅的開始。
他者在成長中:“操演”“審美”“道德”“書寫”
正如伯格和盧克曼(2019)指出,原生家庭使個體經歷初級社會化,而個體進入社會時會經歷次級社會化和再社會化,最終得以在社會中安身立命。社會化使哈克從他者轉向主體。哈克在小鎮生活中的存在方式是不停地表演。哈克在陸地上通過喬裝打扮、改名換姓的“角色扮演”參與小鎮生活。如毛亮(2015)所言,在現實建構過程中,個體意識會對所感知到的內容進行“賦形”與“賦意”。哈克的角色扮演正是其“賦形”與“賦意”的實踐。這種實踐用巴特勒的話語來說,即是“操演”。操演指向的是建構性,如巴特勒所言,性別角色之所以被認為理所當然就是因為它一再被重復,最后被自然化了(Butler,1999)。可見,操演是參與和實踐,其結果是吸納、接受、融入,是社會化。
哈克的旅途成長經驗伴隨“賦名”和“賦形”,是重復性操演的實踐,目的是用“替身”隱藏“真身”。隨著旅途的深入,重復性操演的實踐使哈克的隱藏能力得到發展。在旅途伊始,哈克造訪朱迪思·洛夫圖斯夫人家。由于演技拙劣,他進行了三次更名,從莎拉·威廉姆斯到瑪麗·威廉姆斯到莎拉·瑪麗·威廉姆斯又到喬治·彼得斯,最后被洛夫圖斯夫人戲稱為莎拉·瑪麗·威廉姆斯·喬治·亞歷山大·彼得斯。流落到格蘭杰福德家時,哈克變身為喬治·杰克遜,這次哈克要比之前謹慎得多,為了防止露出破綻,他巧妙地從巴克口中學會名字的拼寫,并反復練習、爛熟于心。隨著哈克角色扮演經驗的累積,他虛構身份的能力越來越強。伯格和盧克曼(2019)認為,“‘隱藏能力的發展,是成年過程的一個重要方面”。經歷漸長的哈克在社會中逐漸由不適變得舒適,成長為兼具審美認同和道德認同并且不再沉默的準社會青年。
當哈克誤打誤撞進入格蘭杰福德的地盤時,他扮成一個迷路的男孩,輕而易舉地被格蘭杰福德家所接納。格蘭杰福德家如同圣彼得斯堡一樣,但待哈克進入格蘭杰福德家時,他已不似早先在寡婦家那般感到百般難受了。當然,格蘭杰福德家與寡婦家不同,但此時的哈克相較于之前也發生了改變。在格蘭杰福德家,哈克寫道:“這是很可愛的一家人,他們住的房子也可愛至極。我從前在鄉下,從來沒有見過一所這么精致、這么有派頭的房子。” (吐溫,2000) 哈克竟然贊美起房屋的氣派來,他如同一個參觀藝術展的青年,仔細欣賞著房屋裝飾的細節:擺件、桌布、書目、圖畫。特別是這家已故女兒的畫作和詩作,讓哈克著魔一般地被吸引。他仔細研究過許多次,對所有細節了然于心。他坦言:“有好多回被她的圖畫弄得悶悶不樂,我無法理解她的心情,我就無精打采地來到她原來住過的那間屋里,拿出她那本老剪貼簿來,認真地看了一遍。我很喜歡那一家人,連死的都包括在內,我不希望我們之間有任何隔閡。”(吐溫,2000)此時的哈克儼然一個憂郁的藝術青年,與格蘭杰福德家達成審美認同。“審美認同就其根本語義而言,指的是人們在對于什么是 ‘美以及如何接近、表達和通達此‘美等方面所達到的觀念和行為方面的相似性和一致性”(向麗,2014)。可見,審美認同指向觀念和行為方面的相似性和一致性。不僅如此,哈克想到這女孩生前給別人作詩,死后卻沒有人給她作詩,于是他絞盡腦汁嘗試為她創作幾首詩。雖然創作以失敗告終,但哈克的表達沖動被刺激和喚醒,而這背后的動力是滿足公平性的道德訴求。
如果說審美認同是哈克成長表現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則是哈克的道德認同。李萍(2019)認為,道德認同包含兩方面意義:“其一是指道德主體與通行的社會理想道德要求的一致性或相同性,這可以視為道德社會認同;其二是表明道德主體(道德行為者或當事人)與道德自身的關系水平,這揭示了道德主體自覺自愿地與道德不離不棄、始終如一的狀態,這一層面的道德認同其實就是當事人的道德自我認同。”道德是社會的觀念力和情感力之所在(楊修業,2021),無論是道德社會認同還是道德自我認同,都意味著個體的社會化。
《哈克》第十九章到第三十三章大約占全書三分之一,其中“國王”和“公爵”兩個人物操縱著哈克的旅程。“國王”和“公爵”對岸上比對河上更感興趣,但他們因敗壞的道德與失范的行為受到岸上世界的驅逐。哈克離開格蘭杰福德家后,決心過木筏漂流生活,但“國王”和“公爵”的闖入使哈克被動上岸,并被賦形為無名的隨從或幫手。哈克早就輕松識破兩個人的騙子身份,且對兩個騙子的欺詐惡行和敗壞的道德嗤之以鼻。但正如他所言:“假如我從爸爸那兒沒學到別的什么的話,至少我是學會了這么一手:對付這種人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他們隨心所欲。”(吐溫,2000)顯然,哈克在道德上鄙視騙子,行為上卻對其放任不管。他對騙子的否定說明他具有道德社會認同;但他做騙子的幫兇,說明他還不是與道德不離不棄、具有道德自我認同的人。善良的姑娘瑪麗·貞是讓哈克從幫兇到揭兇的關鍵人物。哈克在受到瑪麗禮待后,反復三次自責:“這位姑娘多么好啊,她的錢眼看著就要叫那個老壞蛋搶走,我卻袖手旁觀!”(吐溫,2000)最后他終于良心發現,罵自己不作為是“下賤、缺德、不是人”(吐溫,2000),決定幫瑪麗把這筆錢拿回來。哈克在作出決定之際,反復感嘆“這位姑娘多么好啊”。“好”在哪里呢?這個模糊的“好”字飽含著青澀的初戀般的含蓄,含蓄到哈克自己都不自知。哈克回想起瑪麗時說:“自從那一回我看著她走出房門以后,我再也沒有見到她。盡管如此,我總是時時刻刻地想念她,想了不知多少遍,我永遠記著她說要替我禱告的那句話。”(吐溫,2000) 或許很難說清這個曖昧的“好”具體指什么,但它一定不是騙子的那一類,而是與之對抗的力量。在對瑪麗“好”的肯定下,哈克在道德認同上又進一步,而這種牽念的情愫和延續的沖動往往昭示著成熟的到來。
小說最后一章,哈克抵達菲爾普斯農場時,被誤認為圣彼得斯堡的湯姆·索亞。菲爾普斯農場是一個與圣彼得斯堡有親緣關系的小鎮。經過漫長的旅程,哈克仿佛回到起點,扮演起了湯姆——“他是一個很體面的孩子,教養又好,又有身份,家里的人的身份也都好;而且他人很聰明,并非傻頭傻腦的;懂得是非,絕不稀里糊涂;既不卑鄙,又有好心……”(吐溫,2000)。就是這樣的湯姆·索亞,哈克演起來并不費心,甚至可以說他順利被菲爾普斯接納。哈克或許把順利的融入歸因于菲爾普斯夫婦的熱情和輕信;但從另一面看,又何嘗不是因為他對這場表演駕輕就熟呢?與在圣彼得斯堡不同,哈克在菲爾普斯不再抱怨文明化的生活了,他已經適應了。
正如伯格和盧克曼(2019)所言,“語言構成了社會化最重要的內容,也是社會化最重要的工具”。那么,成長到小說結尾部分的哈克已然是掌握語言工具的人。如果說在圣彼得斯堡時,哈克在湯姆面前常常是沉默或被斥責的被動狀態,到菲爾普斯農場時,哈克顯然不再被動,而且已成長為一個比湯姆更有知識的人。當哈克與湯姆交流時,他自信滿滿:“我一句話不說,因為這正和我預料的一樣,不過我非常清楚,一旦他的主意拿定,那就不會有任何異議”。(吐溫,2000) 他不僅教湯姆如何不給薩莉姨媽惹麻煩,更開始向湯姆提出建議,甚至說服湯姆接受其中一部分,而湯姆也開始時不時詢問哈克的意見。更重要的是,哈克已成長為一個作者。在小說“就此停筆”(吐溫,2000)之前,哈克寫道:“湯姆現在已經快痊愈了……所以我也沒有什么可寫的了,可是我還是感到很開心,因為如果我早知道寫一本書這么麻煩,我就不會動筆,以后也不會再寫了。”(吐溫,2000)小說之初,哈克在圣彼得斯堡學習閱讀文字;在格蘭杰福德家,他受到藝術的啟蒙,開始有書寫的沖動;而在菲爾普斯農場,哈克終于完成了書寫。
持續的建構
小說結尾,哈克說:“可是我想,我得在湯姆和吉姆出發前先到印金地區去走走,因為薩利姨媽想要收我做干兒子,好教我做人學好,那種事我真是受不了。我早就嘗過那種滋味了。”(吐溫,2000)哈克的旅程尚未結束。哈克作出放棄定居生活而選擇河上旅居的決定在小說第十八章已出現。哈克在離開格蘭杰福德家時感嘆:“歸根結底,在筏子上比哪都好。別的地方實在太別扭、太悶氣了,可是木筏就不一樣。坐在木筏上,你會感覺到又輕松、又自由、又舒服。”(吐溫,2000)在此,我們有必要再考究一下哈克在格蘭杰福德家的經歷。在格蘭杰福德家,小男孩巴克(Buck)不僅名字拼寫與哈克(Huck)只有一字之差,性情也與哈克相似,他與哈克仿佛孿生兄弟。從很多方面來看,巴克就是哈克。如果不是家族世仇和血腥屠殺摧毀了格蘭杰福德家和巴克,哈克或許會定居于此。這里,巴克的“被殺”照應哈克在旅途之初的“自殺”。哈克在小鎮社會的煎熬,讓他以“自殺”開啟逃避之旅;而當到了旅程后半部分,哈克可以安于一地的時候,他卻遭遇“被殺”。巴克是哈克在小鎮里的“真身”,他不用改名換姓,不用佯裝表演,可是他卻被世仇傳統所殺。馬克·吐溫不甘心讓哈克的社會化變成“從此過上幸福生活”的童話。“真身”是徹底的社會化、是終點,終點的覆滅當然是揭示性的。哈克并未抵達成長的終點,他還要繼續在探險的旅途中尋找自己。哈克的現實建構是能指延展的鏈條,不可抵達“超驗的所指”。操演的虛構是“替身”,是敘事,是身體實踐,是社會主體與社會他者之間的中介,是二元對立之間的中間之地。
伯格和盧克曼(2019)認為,雖然“個人······出生在一個客觀的社會世界中”,但“主觀生命并不完全是社會的。個人既把自己看成社會之內的,也把自己看成社會之外的”;在伯格和盧克曼看來,“主觀現實中總是存在一些并非源自社會化的因素,比如那些先于任何社會理解的過程,并且與之脫離的個體對個體身體的感知”。哈克的旅程始終與吉姆相伴,關于吉姆是否為人,哈克的感知與社會的告知并不是統一的,相信自己還是相信社會正是哈克旅途中要不斷自我追問的。“客觀現實與主觀現實之間的對稱永遠不是靜態的,不是一旦達成便一勞永逸的事情,而必須總是實際地被生產和再生產出來。換句話說,個人與客觀社會世界之間的關系就像一個持續尋求平衡的行為。”(伯格、盧克曼,2019)在這個意義上,《哈克》這部小說的經典之處就在于它回應了人(而且是每個人)在社會中如何存在的問題。
參考文獻
Butler, J. 1999. Gender trouble[M]. New York, NY: Routledge.
彼得·L. 伯格,托馬斯·盧克曼. 2019. 現實的社會建構:知識社會學論綱[M]. 吳肅然,譯.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郭晶晶. 2017. 馬克·吐溫作品中的身份轉換策略研究[D]. 武漢: 華中師范大學.
馬克·吐溫. 2000. 哈克貝利·芬歷險記[M]. 刁克利, 譯.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
馬克·吐溫. 2004. 湯姆·索亞歷險記[M]. 潘明元, 譯. 北京: 中國致公出版社.
馬克·吐溫. 2008. 湯姆·索亞歷險記&哈克貝利·芬歷險記[M]. 北京: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毛亮. 2015. 自我、自由與倫理生活:亨利·詹姆斯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李萍. 2019. 論道德認同的實質及其意義[J]. 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1): 57—63
芮渝萍. 2004. 美國成長小說研究[M].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孫勝忠. 2020. 西方成長小說史[M]. 北京: 商務印書館.
王楠. 2015. 從性別表演到文化批判:論朱迪斯·巴特勒的政治倫理批評[J]. 婦女研究論叢, (2): 81—89
王楠. 2016. “非—人”的倫理難題:巴特勒與卡夫卡[J]. 國外文學, (4): 44—51
向麗. 2014. 他者視域下的審美認同問題研究——兼論審美人類學的研究理念[J].思想戰線, (6): 66—71
楊修業. 2021. 涂爾干思想中的情感力面相——論《自殺論》中現代社會的心態危機[J]. 社會學評論, (2): 241—256
張德明. 1999.《哈克貝利·芬歷險記》與成人儀式[J]. 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4): 91—97
趙立瑋. 2014. 自殺與現代人的境況 涂爾干的“自殺類型學”及其人性基礎[J]. 社會, (6): 114—139
趙靜
南開大學外國語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