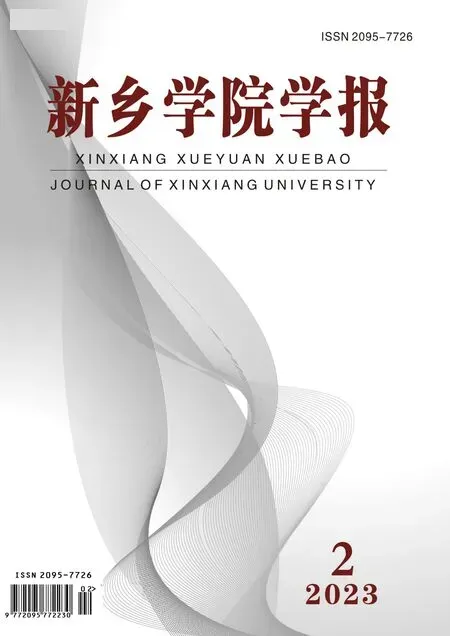論劉震云創作的“形式”冒險與審美意蘊
趙薇
(中南大學 本科生院,湖南 長沙 410083)
“形式”是作品的符號系統,也是文藝創新的一個生長點。劉震云是一位有自覺形式追求的作者,在創作之路上一次次華麗轉身,不斷創新,不斷超越,成為極少數既能保持旺盛生命力,又能登上作家富豪榜的純文學作家,其眾多作品已成為純文學與商業模式相得益彰的經典案例。在一個機械復制的時代,與商業文化市場、主流文學體制均保持冷峻疏離狀態的劉震云,卻輕松駕馭著大眾傳媒和網絡資源,既成功堅守了精英作家的立場,又巧妙抓住了審美主動權。“劉震云現象”內蘊著文藝諸多層面的思考價值,“形式”即是其中之一。
一、轉軸循環的敘事結構
敘事結構是文本形式的重要方面,與敘事視角、敘事時間共同構成文本的敘事模式。敘事結構關系著故事的呈現方式和敘事風格,是文本創新的重要切入點。傳統的經典敘事結構對文本的展示,已經難以構成審美驚異。而劉震云個性化的敘事結構,是其文本形式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成為自身獨特的敘事風格標簽。
劉震云熱衷于敘事結構的形式實驗,他說:“《故鄉相處流傳》對我的創作歷程意義非常大,是戰略性的轉移。 ”[1]早期的“單位系列”,敘事庸常、瑣屑,備受爭議也令人耳目一新。如果說這尚易于被模仿,甚至被超越,那么,“繞”“擰巴”[2],卻是不可復制的“劉式”敘事結構。“繞”表述的是一種不通暢、不正常、背離常理的社會生活與生命狀態,而這一目標正是通過“劉式”轉軸循環敘事達成的。
劉震云是“講故事”的高手。其作品敘事結構龐雜、語言繁復,鮮少直指故事本身,而是撿起一個線頭,慢慢“繞”。如劉震云甚為看重的《一句頂一萬句》,上部命名為“出延津記”,下部命名為“回延津記”,組成一個大循環:敘事從“老楊”到“老馬”,再到“老李”“老段”……一大串人物,無名但個性鮮明,精彩紛呈然而錯綜復雜,受眾在眩暈中會猛然發現,故事早已被妥當地安置在一個個順手布就的或大或小的場景和境域中,而主要形象也在不經意中一次次走到作為故事軸心的前臺。
文本語言的“繞”,指向事情背后的生活邏輯與思維方式的“繞”,最終指向所描述的“繞”的人生狀態的深層原因,即生存倫理與語言邏輯的雙重錯位——從“老裴和老蔡打架因為幾張餅,但娘家哥放下餅,一竿子支出去幾十年,先從老裴的爹娘說起”,到感嘆“原來世上的事情都繞”[3]20。
“繞”是理性思維與審美判斷力的行走、回環、阻礙、釋放,展示出思維過程中想象力的線性迂回之態;“繞”表征著蕓蕓眾生思維的糾纏狀態和邏輯推進方式。劉震云敏銳地捕捉到這種思維的奧秘,并以夸張的方式放大了這個過程。因此,劉震云自覺呈現的“繞”,具有了一種形式美,展現出辨識度極高的“劉式”風格,創造了文本獨特的韻律與節奏。
劉震云對敘事結構的試驗,甚至達到“肆無忌憚”的程度。如《吃瓜時代的兒女們》,第一部分非常隆重,前言、正文、附錄齊齊整整,第二部分卻出人意料,除了前言一句話,不分章節,且正文也就一句話:“一年過去了。”[4]第三部分單刀直入,故事極為簡潔利落。當然,這種“創新”也引來了爭議。形式上對常規范式的變形和扭曲,未必助益了內容的獨特傳達,但確實是對固化了的心理形式的喚醒,由此激發出接受過程中的新異感、鮮活感,從而達到一種奇特的審美效果。
二、奇譎多變的語言風格
敘事結構之外,劉震云同時有著鮮明的語言個性化自覺。作為文本基本構成因素的“語言”,成為這個創新者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打造獨特形式的材料,被肆意捶打、任意收放,語言試驗頻頻發生且極具形式感。
一是語言之“收”。雖然劉震云筆下的生活混沌凝滯、人物語言絮叨纏繞、故事情節復沓回環,但其行文的具體語言,卻拒斥蕪雜,純凈、干脆、利索,從不追求表層的華美,大多采用白描手法,盡顯干練氣息:“老裴就在黃河邊上支起剃頭挑子,給老曾圍上剃頭布,用熱水給老曾洗頭。待洗泛了,比劃一下,就下了刀子。 ”[3]13寥落幾句話,卻境域宏闊,不乏細節,猶如一幀大氣的速寫。對修飾語詞的棄用甚至杜絕,使劉震云的故事,猶如一棵棵挺拔、疏朗、遒勁的大樹,斫枝棄葉,剛毅果斷,直指高空,打造出鮮明的個性風格。語言的純凈,同時導致另一個美學效果:節奏明快。對蕪雜的拋棄,既突出了句式的主干,也使劉震云的敘事得以快步如飛、急速推進,但即使以這種語言方式推進的結果,仍是敘事與人物的轉軸循環。在《我不是潘金蓮》中,這種從不拖泥帶水的語言,尤其使作品敘事清晰、節奏明快,排斥想象力的耗費甚至分歧,直指文本的意旨傳達,生成獨特的審美效果。
二是語言之“放”。雖然“冷峻”是劉震云語言風格的一個特點,但奇特的是,劉震云的某些文本,又被公認為一場場語言的狂歡。現實生活中沉默寡言的劉震云,在二百二十萬字的《故鄉面和花朵》、二十二萬字的《一腔廢話》中,極盡鋪排之能事,“語言”的洪流甚至淹沒了故事情節和意義本身,行云流水、胡言亂語卻一本正經,讓人目不暇接、不知所云。這種汪洋恣肆的語言爆發,顯然是一種與后期文本形成對照的語言試驗,想象力在語詞符號的雜多中自由組合,生成一組組表象,造就思維過程的形式狂歡。《手機》之后,劉震云嘗試新的語言試驗,風格漸趨收斂和沉靜。
三是首句之凝練。文本的開頭,是作品與受眾審美關系的起點。劉震云對語言形式的自覺追求,也體現于對文本開頭的凝練設計:“二樓的廁所壞了”“小林家一斤豆腐變餿了”“縣委書記到省城開會,就像生產小隊長進了縣城,沒人管沒人問”……這種客觀、中性、日常的陳述短句,看似波瀾不驚,卻醞釀著千頭萬緒。“在工地,大家都知道,劉躍進是個賊”“楊百順他爹是個賣豆腐的”“鎮上看電話的老牛,1968年和嚴守一他爹一塊賣過蔥”……這種表述讓人深感時光流轉,寥落的幾筆盡顯生命輪轉的悠長。這些看似平淡無奇的開頭,其實暗藏著人物命運的洶涌波濤,也讓行文具有了凝練、厚重的氣息。
三、多樣化的母題敘事
母題敘述的審美個性化,是優秀文藝作品形式價值的重要表現。對“母題”的創新表達,是劉震云形式追求的一個重要動力。劉震云的敘事,鋪排瑣細,卻不至于變成原始混沌的生活之流,母題巧妙地隱現其中。在其多變的藝術世界中,充滿了繁復的技巧,諸如反諷、復調、語言狂歡、新寫實主義、新歷史主義、存在主義等等,這些斑駁陸離的色調,使其文本成功躍出同類母題敘事的汪洋大海,極具審美個性和表現力。
“劉震云是一位保持創作主題連續性和具有自覺的哲理之思的作家,在他的小說中有一種揮之不去的表達荒誕、揭示荒誕、對抗荒誕的主題”[5]。這個一以貫之的母題,即人生的“西西弗斯”悖謬,或是“事兒本身很荒誕”,或是“事兒的理兒擰巴”,又或是“悲劇之中,一地喜劇”[6]。劉震云一直在以不同方式切入關于存在的無奈與荒誕的母題。
劉震云關注小人物的生存悖謬。劉震云有著濃重的草根氣質,從底層的新兵,到機關的小職員,再到《溫故一九四二》中的卑微者,到延津和某某省形形色色的百姓,這些一代又一代混跡于各行各業的小人物,徒勞地生成理想,頑強地堅持信念,又在不知不覺、順理成章中走向失敗,絕望卻又不放棄。劉震云溫和地接受悖論化的現實,又極力突顯小人物們荒誕中的隱忍與執著、小奸小惡中的真誠與善良,在現實的夾縫中,爭出各自的一條存在之路。
劉震云也寫了“大人物”的表里悖謬。那些掌握著話語權的“大人物”,有履職時的兢兢業業,選人用人時的眼光與講究,也有為人處世的謹小慎微、遇事時內心的惴惴不安。“李安邦”因妻子貪圖小利而嘆恨,“楊開拓”為侄子將五分之三工程款理直氣壯裝進私人腰包而義憤填膺,“馬忠誠”淡看名利置身事外不爭搶副局長之職,他們看起來清正、有操守,但在劉震云敘事中,這些“大人物”在小利面前的節操都是表象,在商人“趙平凡”開出的“安全”的兩千萬面前,在限量款名表面前,在“犒勞自己”的欲望面前,他們才展現貪婪、腐化的最真實一面:“安邦”無德安邦、“開拓”無能開拓、“忠誠”毫不忠誠,極有可能在軍隊中冉冉升起的“李棟梁”,也必然成不了棟梁。正如《我不是潘金蓮》中的司法人員“董憲法”“王公道”“史為民”,這些“表”與“里”的悖謬,展示著表象世界的荒誕性。
劉震云還重視“一句話”的悖謬。《鄉村變奏》中,小水因為戀人說“我看李發也比你強”,憤而從事運輸行業出了車禍;《被水卷去的酒簾》中,鄭四因被質問“你會干什么”,搏命掙錢買縫紉機和自行車,卻仍沒有贏得青子的心;《手機》講述民國期間的一個口信、1968年的一通電話、手機時代的一條短信,對嚴家祖孫幾代人生活與命運的撥弄;《我不是潘金蓮》中,李雪蓮因為一句話,掙扎半生、徒勞無功,反而誤了整個人生。在劉震云筆下,“西西弗斯”式的荒誕無處不在。
四、冷峻嚴肅的哲學向度
在一個技術日益發達并瘋狂碾壓日常領域的時代,借助情節、臺詞、角色、環境甚至主題、思想、意象等重復性因素的隨機選取,文藝作品的機械復制,已易如反掌。隨著數據庫與樣本量的增加,借助人工智能,類型化的文藝“產品”數量可按需呈幾何級數增長。但為什么是劉震云的作品,而不是唐家三少、天蠶土豆、葉非夜等寫手的玄幻、仙俠、宮斗類作品,引發著關聯真金白銀的電影業持續的改編熱情?答案是哲學。劉震云以對形而上的終極追求,回應與引領著電影觀眾精神超越的向度。
劉震云現象,奠基于其文本對現實人生、人性、人情的深層追問,也有賴于形式因素對這一追問的強力支撐。他筆下總是有兩種生活:話語呈現出來的生活與實際的生活。語言是人的存在方式,然而語言有時詞不達意、有時易于被偽裝,這就使語言無法真正呈現生活,或者語言所呈現出來的生活極不可靠。
在《一句頂一萬句》中,所有的語言都無法真正表達自己,人物的精神荒漠揭示著中國人的千年孤獨。無論語言的多寡和言說方式如何,都缺乏對“孤獨”的形而上破解,無法抵達真相。文本中,各色以“老”命名的、具體而又虛幻的人物,錯雜登場、自說自話、各成體系,所有嘗試構建純粹的交流共域與話語中心的努力,均宣告失敗。話語的所指相互替代、無限循環,言語的滑稽邏輯以真理的假面出現,有效溝通遙遙無期,絕對孤獨就在這樣的語言游戲中被彰顯出來。
在《吃瓜時代的兒女們》中,宋彩霞、朱菊花、齊亞芬、蘇爽……究竟是正直實誠的老實人,還是狡詐可恥的騙子?一個個語言的陷阱,讓精明能干如牛小麗這樣一個不失為“大女人”的人,也無從辨識。而恰恰是牛小麗這個自強不息、眼中不揉沙子的 “勵志姐”,最后成為被吃瓜群眾不齒與唾罵的妓女。令人深感荒誕、悲涼的是,她確實墮落成一個妓女。在機緣巧合與命運的捉弄下,她無可奈何地走向了這樣一個身份反轉的結局。劉震云對這種悖謬命運的關切,正是對人的存在的嚴肅的哲學追問。
劉震云的獨特地位,既在于切中了時代脈搏,又在于多變且個性化的形式追求。正是憑借這雙峰并峙,劉震云將自我與追逐商業利潤、缺乏形式創新的各級“寫手”區分開來,也超越于孤高自詡、無視市場的某些純粹精英創作,借助與影視的深度互動,大力拓展了純文學的領域。有著高度寫作自覺的劉震云,以其對人類認知與審美各環節的深度了解,走出了一條獨屬于自己的,既尊重商業現實又堅守文藝理想的光明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