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美德的育化:亞里士多德音樂(lè)教育思想的價(jià)值向度
周亦斌,張忺寒
(湖南第一師范學(xué)院a.音樂(lè)舞蹈學(xué)院,b.黨政辦公室;湖南 長(zhǎng)沙 410205)
音樂(lè)作為文明創(chuàng)新、文化創(chuàng)生的見(jiàn)證,從對(duì)大自然聲響的模仿,到形成有規(guī)律的樂(lè)音組合,始終伴隨著人類的生產(chǎn)與生活。音樂(lè)教育從最初的耳聞口傳到多元跨域發(fā)展,始終浸潤(rùn)在各類育人實(shí)踐探索中,呈現(xiàn)出鮮明的時(shí)代特性。古希臘城邦時(shí)期,新興有閑階層意識(shí)到高尚的道德情操、豐富的知識(shí)儲(chǔ)備和完美的德性靈魂,是通向至美至善的必由之路。因此,一種關(guān)乎城邦與公民恒久發(fā)展的理想教育雛形,在向往善美生活的激勵(lì)下開(kāi)始顯現(xiàn)。音樂(lè)的育化與倫理功效是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反復(fù)提及、討論的主題,他從人性和正義的角度出發(fā)考察教育問(wèn)題,強(qiáng)調(diào)音樂(lè)在構(gòu)建理想城邦、規(guī)范政治生活、培育德性靈魂時(shí)的功能特性及價(jià)值歸屬,以追尋音樂(lè)教育的本真奧義,厘清音樂(lè)之于城邦生活的德性張力。
一、遵循古典邏輯:音樂(lè)本源的闡析
古希臘時(shí)期的“音樂(lè)”(mousikē)是一個(gè)多元概念,有別于現(xiàn)代意義上的具象理解。它的話語(yǔ)解釋范式嚴(yán)格遵循著既有的古典邏輯,一方面在哲學(xué)闡釋時(shí)關(guān)聯(lián)神話意象與自然科學(xué),普遍認(rèn)為最初的音樂(lè)幾乎涵蓋所有的“美育”和“智育”,且與分別掌管音樂(lè)、歷史、史詩(shī)、情詩(shī)、悲劇、喜劇、舞蹈、頌歌、天文的九位藝術(shù)女神有關(guān);另一方面在育化實(shí)踐中發(fā)掘和諧特性與療愈功效,不僅將音樂(lè)基本理論、演奏技藝、詩(shī)歌閱讀、禱文吟唱、修辭學(xué)等涵蓋在內(nèi),也把對(duì)美好事物、知識(shí)的追求及療愈心靈的活動(dòng)納入其中,亞里士多德亦在說(shuō)明音樂(lè)性質(zhì)時(shí),將其稱作某事物的知識(shí)。因而,古希臘人常利用音樂(lè)本質(zhì)上的趨神性,將音樂(lè)與“真”“美”關(guān)聯(lián),使其“軀體”(指音樂(lè)本體)在由不同要素構(gòu)成的同時(shí),維持著微妙的和諧,并以此為媒介,展開(kāi)人神間的無(wú)界交流、訴說(shuō)和取悅。“正如在一支合唱隊(duì)中,當(dāng)指揮示意開(kāi)始時(shí),整個(gè)男人的合唱隊(duì)(有時(shí)也可以是女人的)便一齊高歌,有些音高,有些音低,由這些不同的音調(diào)混合成和諧悅耳的樂(lè)曲。統(tǒng)轄整個(gè)宇宙的神也是如此:音調(diào)由可以恰當(dāng)?shù)乇环Q為合唱隊(duì)指揮的神從高處發(fā)出。”[1]624
古希臘人對(duì)和諧秩序的不懈追求及對(duì)古典哲學(xué)的美學(xué)解構(gòu),同樣在別的音樂(lè)闡釋中得以窺見(jiàn)。畢達(dá)哥拉斯(Pythagoras)學(xué)派站在純粹理性思辨的視角認(rèn)為,數(shù)是萬(wàn)物的本源,音樂(lè)是其中一個(gè)由聲音和節(jié)奏組成的系統(tǒng),受數(shù)學(xué)規(guī)律的支配,是在整個(gè)有形和無(wú)形的創(chuàng)設(shè)中運(yùn)作的“微觀世界”[2]21。音樂(lè)和數(shù)密不可分,且數(shù)是開(kāi)啟、連接精神和物質(zhì)世界的鑰匙,音樂(lè)和節(jié)奏既然按照數(shù)的規(guī)則排列,那么在某種程度上就必然顯現(xiàn)著與宇宙相和的天地至理,“純粹的數(shù)學(xué)家就像音樂(lè)家那般,是它那井然有序美麗世界的自由創(chuàng)造者”[3]52。亞里士多德認(rèn)為,和聲在本性上是由音調(diào)和與之相應(yīng)的數(shù)構(gòu)成,且一切音調(diào)在本性上都是數(shù)之本源的聲響化。赫拉克里特(Heraclitus)在揚(yáng)棄畢達(dá)哥拉斯學(xué)派和諧思想的基礎(chǔ)上,接納感性和變化的客觀存在,提出了對(duì)立統(tǒng)一的觀點(diǎn)。在他看來(lái),相互排斥和迥異的音調(diào)結(jié)合在一起才能造就最美的和諧。赫拉克里特不僅認(rèn)識(shí)到事物對(duì)立統(tǒng)一的特性,而且認(rèn)為斗爭(zhēng)是事物生發(fā)的源力,只有差異化的音調(diào)才能在給人以沖擊的同時(shí),達(dá)到矛盾的和諧統(tǒng)一。這即類似弦樂(lè)器的調(diào)律,通過(guò)協(xié)調(diào)、組織琴弦音調(diào),將不同音調(diào)的琴弦和諧地糅合在一起,產(chǎn)生所需要的曲式,從而表達(dá)出不一樣的聲音沖擊和感情色彩[4]196。亞里士多德同樣認(rèn)可音樂(lè)和諧論,認(rèn)為其實(shí)質(zhì)即高音和低音的比率。可見(jiàn),古希臘關(guān)于音樂(lè)本源的闡析是立足古典邏輯視域的合理推演,乃古代人生觀、宇宙觀演繹的必然結(jié)果。
二、構(gòu)建理想政體:音樂(lè)教化的澄清
古希臘時(shí)期音樂(lè)被廣泛地用于各種場(chǎng)合,尤其是其政治表達(dá)功能,被廣大哲學(xué)家、政治家奉為構(gòu)建城邦優(yōu)良政體的特殊途徑。它以形式、風(fēng)格多樣的方式承載著塑造政體、價(jià)值觀和文化內(nèi)涵的重任,對(duì)于培養(yǎng)公民對(duì)政體的認(rèn)同感、責(zé)任感,推動(dòng)城邦朝著理想方向發(fā)展至關(guān)重要。
自城邦建立開(kāi)始,教育即開(kāi)始承擔(dān)具有廣博意義的政治功能,而音樂(lè)作為古希臘宗教、教育和公民儀式的必要環(huán)節(jié),始終在城邦生活,政治活動(dòng)中保持著鮮活的生命力,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shuō):“要確定音樂(lè)的本質(zhì)或?yàn)槭裁疵總€(gè)人都應(yīng)該了解音樂(lè)的知識(shí)并不容易。”[5]306音樂(lè)本身從曲式與調(diào)性上不僅錯(cuò)綜復(fù)雜,且當(dāng)它被視為與人類及其生活相關(guān)時(shí),復(fù)雜程度更甚。因此,古希臘人將音樂(lè)納入教育是基于不同音樂(lè)對(duì)聽(tīng)眾所產(chǎn)生的不同影響這一前提,以培養(yǎng)服從、勇敢、自律、理智、聰慧、公正的品格,即身心的和諧發(fā)展。亞里士多德關(guān)于音樂(lè)教化的觀點(diǎn)主要集中在《政治學(xué)》一書,他指出音樂(lè)在施行美育教化的同時(shí),還承擔(dān)著智育的職能,且是公民德性教育實(shí)踐和男孩教育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內(nèi)容[6]90。不論是為了娛樂(lè)、美德,抑或智力享受,“他發(fā)現(xiàn)沒(méi)有證據(jù)能夠表明兒童天性能夠產(chǎn)生美德。相反,美德是習(xí)得的習(xí)慣”[7]111。由此,亞里士多德聚焦于兒童(年輕人)的教育,以培養(yǎng)身心健康和諧發(fā)展的公民。
(一)夯實(shí)德性根基的需要
城邦政體的良性構(gòu)建不僅需要公民的積極參與,更需要使他們學(xué)會(huì)正確地表達(dá)、傳揚(yáng)各種城邦政治生活的價(jià)值觀與理念,如此才能在公民間形成一種普遍的共筑理想政體的價(jià)值歸一,達(dá)到城邦建設(shè)的“德”之歸位。其中,公民的自覺(jué)是基礎(chǔ),與之相適的強(qiáng)化“德性”自覺(jué)的音樂(lè)教育則是進(jìn)一步夯實(shí)德性根基的關(guān)鍵角色。
亞里士多德認(rèn)為,公民的理想教育是一種自由、理性、完美和至善的教育。故施行音樂(lè)教育既是理智的享受,又是靈魂的凈化,目的在于通過(guò)培育理性、習(xí)慣和自然和諧相處而使人變得善良。它從人最本原的部分開(kāi)始,初始便觸及靈魂,然后發(fā)展到理性的形成,繼而彌補(bǔ)人與生俱來(lái)的缺陷,使人靈魂充盈,獲得生命整全。亞里士多德以一種現(xiàn)代人難以理解的方式描述了先賢們研究音樂(lè)的動(dòng)機(jī),他將人的活動(dòng)分成工作、消遣、閑暇三大類。其中,閑暇既非完全與工作脫離的狀態(tài),也不是純粹的娛樂(lè)活動(dòng),它是一種處于中間地帶的能夠使人內(nèi)心充實(shí)、靈魂升華的活動(dòng)。而音樂(lè)正是亞里士多德認(rèn)可與閑暇類似的一種具有非凡價(jià)值的理性實(shí)踐,這種“閑暇”對(duì)于追求卓越而言,是十分必要的德性行為。操持“閑暇”作為一個(gè)人追求的最高目標(biāo),直接關(guān)涉美善幸福生活的獲取,對(duì)政治美德和統(tǒng)治亦不可或缺。因此,亞里士多德認(rèn)為應(yīng)該使教育以這樣一種方式接近——讓他們?yōu)橐簧姆此蓟蛴兴枷氲纳钭龊脺?zhǔn)備,而這種接近和準(zhǔn)備應(yīng)包含音樂(lè)教育[8]121。
城邦推行的奴隸制民主政體,要求公民具有強(qiáng)健的體魄和趨神般完美的心靈,這與亞里士多德提出的“一個(gè)人生來(lái)就是人,而不是其他動(dòng)物,并且其身心必定具有某種特性”[9]277的觀點(diǎn)不謀而合。亞里士多德批判地共享了柏拉圖(Plato)關(guān)于音樂(lè)的部分觀點(diǎn),認(rèn)為在兒童時(shí)期就應(yīng)使身體和心靈的教育并行,用體育強(qiáng)健體魄,以音樂(lè)滌蕩心靈。那些經(jīng)過(guò)篩選的節(jié)奏、旋律,能夠模仿和部分再現(xiàn)真實(shí)生活環(huán)境中的各種因素,激蕩心神、引發(fā)共鳴,從而達(dá)到錘煉心志的目的。從功能上說(shuō),音樂(lè)雖少文字表達(dá),也無(wú)圖像顯現(xiàn),但其獨(dú)特品性所鑄就的陶冶情操、淬煉心智的育化實(shí)效不失為一種圣潔美好之物,教育者必須依據(jù)每個(gè)人各異的身心發(fā)展特點(diǎn)來(lái)規(guī)劃與制定教育目標(biāo),那些最好的東西在本源上都合乎自然。
亞里士多德開(kāi)創(chuàng)性地提出了教育必須適應(yīng)人自然發(fā)展的原則,即按照人的身體、情感、理性的順序依次發(fā)展。最基礎(chǔ)的階段是身體訓(xùn)練,緊接著通過(guò)德育與美育的導(dǎo)向作用,將各種情感與欲望引入良好的運(yùn)行軌道;最后是理性的培育,使靈魂中判斷和理解的能力得到發(fā)展。他首次提出按年齡差異劃分教育階段的具體措施,兒童普遍年紀(jì)偏幼、心智尚淺,且對(duì)那些缺少快樂(lè)的事物懷有一種本能的抗拒,因此適時(shí)地將音樂(lè)天然屬性上的快樂(lè),融入7—14 歲這個(gè)兒童最想且最易接受的階段,符合少年的天性,故對(duì)兒童實(shí)施包括音樂(lè)教育在內(nèi)的德智體美和諧發(fā)展的教育至關(guān)重要。這種暗含既定模式的發(fā)展軌跡,實(shí)際上正是亞里士多德本人認(rèn)可的培育理想城邦公民、合格政治生活參與者及優(yōu)秀政體建設(shè)者的標(biāo)準(zhǔn)育化范式。
(二)施行道德教化的訴求
音樂(lè)在古希臘社會(huì)被認(rèn)為是一種能夠影響人性格、情感、道德、行為的藝術(shù)語(yǔ)匯,有助于增強(qiáng)道德教化的倫理效果,提升公民品格中的道德規(guī)范。音樂(lè)在推動(dòng)城邦生活朝向有序發(fā)展方面發(fā)揮著難以替代的作用,它與教育結(jié)合,涵養(yǎng)公民秩序等構(gòu)成優(yōu)良城邦的美德基礎(chǔ),培育青年審美能力;它與宗教相契合,為公民找尋個(gè)體精神、靈魂歸屬,助力人神對(duì)話、表達(dá)虔敬;它與政治社會(huì)生活共進(jìn),營(yíng)造良好道德氛圍,引導(dǎo)公眾傳達(dá)政治意圖。
作為古希臘哲學(xué)語(yǔ)匯中的一種樸素表達(dá),音樂(lè)不僅是“聽(tīng)”的音樂(lè),更是“思”的音樂(lè),音樂(lè)中的和諧使人感受美好,進(jìn)而提升道德中的理性成分,有助于培育公民的美德(arete)精神,造就十全十美的人。古希臘人認(rèn)為善良的人就是有德之人,而美德是正直、勇敢、虔誠(chéng)和適可而止(即“中庸”)的綜合表現(xiàn),因而非常重視音樂(lè)的道德教化功用。他們認(rèn)為,音樂(lè)教育必須與治國(guó)方略并行,公民教育也必須包括有監(jiān)督的音樂(lè)教育,如誦詩(shī)或奏樂(lè)都必須在有權(quán)威的長(zhǎng)老監(jiān)督之下進(jìn)行,才能切實(shí)保障陶冶情操的效度,“任何人,不論性別、年齡或階層,都不準(zhǔn)免除這個(gè)教育,每個(gè)人都必須為改進(jìn)國(guó)家的道德、社會(huì)和政治盡責(zé)”[10]4。亞里士多德也通過(guò)模仿說(shuō)解釋了音樂(lè)的教化作用和對(duì)道德意志的影響。他認(rèn)為,人們通過(guò)聆聽(tīng)蘊(yùn)含某種情感的音樂(lè)會(huì)獲得同樣的感情,如果長(zhǎng)期聽(tīng)誘發(fā)卑鄙情感的音樂(lè),容易被塑造出卑鄙的性格,反之長(zhǎng)期聆聽(tīng)和諧高尚的音樂(lè),則有助于身心和諧健康地發(fā)展。通過(guò)一系列以體操和音樂(lè)為要素的公眾教育,可以保障筋骨與心智的鍛造同向同行,造就“正經(jīng)”的人。這種公民切實(shí)需要且真正有用的科目即是好的教育[8]122。
亞里士多德認(rèn)為,用音樂(lè)來(lái)行使教化職責(zé),本身就是形成人性格的一種神秘力量,那么音樂(lè)的力量到底是什么?為了游戲、休憩還是美德?如果是美德的話,那么音樂(lè)是否和體操一樣都影響性格呢?亞里士多德拋出了這樣的疑問(wèn)。他肯定了音樂(lè)對(duì)年輕人性格的塑造作用,即音樂(lè)有助于美德的形成。同時(shí),試圖證明這個(gè)假設(shè)的正確性:“我們大家一致同意,音樂(lè),無(wú)論發(fā)于管弦或諧以歌喉,總是世間最大的怡悅。我們可引詩(shī)人繆色奧的詩(shī)為證:‘令人怡悅,莫如歌詠’。由此我們可以知道,為什么對(duì)于社會(huì)交際以及閑居遣興,世人往往以音樂(lè)取樂(lè)——音樂(lè)確能歆動(dòng)人心,使之歡快。這里,我們可以把音樂(lè)的怡悅作用作為一個(gè)理由,從而主張兒童應(yīng)該學(xué)習(xí)音樂(lè)這門功課了。”[11]425在回答這個(gè)問(wèn)題的時(shí)候,他認(rèn)為音樂(lè)似乎具有了娛樂(lè)的力量,也能提高人的心智和性格。“娛樂(lè)是為了舒暢,而舒暢當(dāng)然是甜美的,因?yàn)樗怯捎趧谧鞫碌目嗤吹囊环N解脫。”[12]568故提高心智應(yīng)該包括那些高貴、令人愉悅的因素,恰好音樂(lè)皆具。正如古希臘神話中教士穆塞歐斯所感嘆的那樣,在凡間一切事情之中最甜美的便是愉悅的歌唱。
(三)通向和諧發(fā)展的必要
古希臘城邦中,音樂(lè)教化被當(dāng)作規(guī)約行為準(zhǔn)則、建立文化認(rèn)同、塑造共同價(jià)值、統(tǒng)一道德標(biāo)準(zhǔn)的重要文化手段,對(duì)于推動(dòng)公民、城邦走向和諧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它在彰顯神性的同時(shí)激發(fā)人類趨和與向善,以一種靈性的藝術(shù)表達(dá),時(shí)刻提醒著人們努力達(dá)成“和諧”的共同理想,這從古希臘人將道德與心靈的教育擺在首位即可得見(jiàn)。
對(duì)和諧的追求和節(jié)奏的掌控,使音樂(lè)對(duì)所有人都具有普遍吸引力,雖然亞里士多德的和諧思想中對(duì)音樂(lè)節(jié)奏、調(diào)式的論述不如柏拉圖那般苛刻,甚至允許音樂(lè)用作娛樂(lè)和欣賞,但他認(rèn)為所有為教育青年人使用的音樂(lè)必須合乎“法”(即適度與和諧),反對(duì)音樂(lè)教育過(guò)分職業(yè)化。如避免演奏吉特拉琴這類需要高超技巧且容易造成德性失調(diào)的樂(lè)器,應(yīng)選擇那些對(duì)學(xué)生理解音樂(lè)和學(xué)術(shù)有幫助,能促進(jìn)他們心智發(fā)展的樂(lè)器。同時(shí),不應(yīng)過(guò)分鼓動(dòng)兒童去操練音樂(lè),而應(yīng)學(xué)會(huì)鑒別和欣賞,且一旦培養(yǎng)了這種鑒賞力,如辨別高貴與狂熱曲調(diào)的能力,那就意味著為政治美德奠定了基礎(chǔ)。這時(shí)年輕人就可以停止接受音樂(lè)教育,因?yàn)閿U(kuò)大化的音樂(lè)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會(huì)危及一個(gè)人從事其他活動(dòng)的能力。因此,“音樂(lè)課程的進(jìn)度要遵守這樣的規(guī)則:其一,不要教學(xué)生們學(xué)習(xí)在職業(yè)性競(jìng)賽中所演奏的那些節(jié)目;其二,更不要教學(xué)生嘗試近世競(jìng)賽中以怪異相炫耀的種種表演,這類表演竟被引入現(xiàn)行的教育課程,實(shí)屬失當(dāng)”[11]432。這里的“失當(dāng)”,是指這種行為有損良好性格及道德靈魂的培養(yǎng),比如為了投人所好,不惜做一些做作、夸張的動(dòng)作,長(zhǎng)此以往就會(huì)失去作為自由人的閑暇。此外,這一時(shí)期不論是家庭教育還是學(xué)校教育,歌頌的是知識(shí)及一切的美好事物,其中音樂(lè)學(xué)校是作為傳播廣義上的音樂(lè)教育而存在,不僅要擁有智慧與道德,且其根本宗旨是調(diào)節(jié)身、心、靈魂的和諧發(fā)展。
三、通達(dá)至美至善:音樂(lè)功能的導(dǎo)正
早期古希臘慶典中的主要節(jié)目不僅有賽馬、競(jìng)走等體育展示,還包含合唱與音樂(lè)比賽等藝術(shù)活動(dòng),其中和聲、旋律和節(jié)奏是評(píng)判音樂(lè)藝術(shù)作品優(yōu)劣的重要元素。人們普遍認(rèn)為,節(jié)奏可能在樂(lè)音之前就出現(xiàn)了,如勞動(dòng)中不經(jīng)意間的工具敲擊,生活中器具的碰撞等。這種敲擊和碰撞從無(wú)意識(shí)的接觸到有規(guī)律的組織,便形成了最早的節(jié)奏。當(dāng)時(shí)公眾篤信這種旋律、節(jié)奏的組合與宇宙現(xiàn)象相關(guān),像日月星辰、潮起潮落、興亡往復(fù)、陰陽(yáng)交替、轉(zhuǎn)世再生等,它們存在相互觀照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且人類性情也與這些觀照間存在著一種神秘聯(lián)系[13]15。
(一)鍛造靈魂
古希臘時(shí)期的音樂(lè)被認(rèn)為可以用來(lái)療愈身體、心靈和靈魂,音樂(lè)的節(jié)奏和曲調(diào)真切地反映了人類性格,憤怒、溫和、放浪、節(jié)制,這些情感都能在音樂(lè)中如實(shí)地體現(xiàn)。亞里士多德繼承并發(fā)展了柏拉圖的靈魂說(shuō),肯定感性的地位和作用,且確信人的最高本質(zhì)即每個(gè)人靈魂中占據(jù)支配地位的那部分——理智。因此,他把“人的靈魂區(qū)分為植物的、動(dòng)物的和理性的三個(gè)部分”[14]21。
音樂(lè)對(duì)人的鼓舞作用,是育化時(shí)鍛造靈魂的重要切入點(diǎn)。亞里士多德指出,通過(guò)影響性格或靈魂,音樂(lè)具有影響判斷的力量,節(jié)奏和曲調(diào)能喚起情緒或心境,如憤怒、平靜、勇氣和節(jié)制。這些心境或許一定程度上會(huì)促進(jìn)、妨礙我們對(duì)可敬人物和高尚行為的認(rèn)知,但這種認(rèn)同感的獲取實(shí)際上會(huì)使我們變得可敬和高貴[8]124。因而,有智慧的靈魂是一個(gè)人幸福的源泉,這即需要我們不僅要對(duì)善良和美好有所甄別,更要對(duì)自身行為是否合乎德行形成理智判斷,對(duì)于這些問(wèn)題若能作出正確決斷,則會(huì)進(jìn)一步夯實(shí)靈魂。亞里士多德認(rèn)為音樂(lè)可以模仿人類的七情六欲,其“陶冶理論”便是希望教育通過(guò)音樂(lè)這種媒介適當(dāng)?shù)乇Wo(hù)兒童,在抵御邪惡、消除負(fù)面情緒的影響的同時(shí),強(qiáng)化靈魂中的美德要素,逐步適應(yīng)善的要求。因此,當(dāng)人們模仿音樂(lè)中的形象進(jìn)行演唱或演奏時(shí),不僅是外在地欣賞、感受藝術(shù)形象的情感,同時(shí)也在對(duì)其中的感性體驗(yàn)進(jìn)行二次加工和創(chuàng)作,本質(zhì)上即一次自我完善、主動(dòng)向善的體悟。
(二)磨礪情感
亞里士多德認(rèn)為情感不只是靈魂的運(yùn)動(dòng),更是有靈魂的人的運(yùn)動(dòng)。音樂(lè)對(duì)人情緒的模仿作用,使其成為錘煉情感的最佳手段。對(duì)亞里士多德來(lái)說(shuō),音樂(lè)的情感力量是一種跡象,表明我們可以在旋律中找到性格的模仿和相似性,對(duì)一段音樂(lè)的不同情感反應(yīng)是其和聲或節(jié)奏性質(zhì)不同而牽引出的結(jié)果[15]413。因此,他在探討音樂(lè)教育過(guò)程中提出了長(zhǎng)笛為什么會(huì)讓人產(chǎn)生快樂(lè)和悲傷兩種相悖的情緒,為什么將朗誦穿插進(jìn)歌唱中會(huì)帶有悲劇色彩等有意義的問(wèn)題。
音樂(lè)的本體運(yùn)動(dòng)非常接近人的情感運(yùn)動(dòng)。音樂(lè)樂(lè)調(diào)色彩繽紛、音色迥異的天生屬性,正如人的性格一般,這也就解答了不同的人聆聽(tīng)不同樂(lè)調(diào)時(shí)產(chǎn)生不同情感體驗(yàn)的原因。同時(shí),在這一過(guò)程中音樂(lè)與聽(tīng)者間建立起了一條通道,使聲音和聽(tīng)者的靈魂間產(chǎn)生了和諧。因而接受過(guò)這類正確音樂(lè)教育的人幾乎能夠復(fù)制大部分情緒,使它可以被聽(tīng)眾感覺(jué)和識(shí)別,它既能使人溫柔融化,也能使人怒火中燒,即使是最鐵石心腸的人,只要撥動(dòng)正確的琴弦,也會(huì)產(chǎn)生共鳴[16]268。音樂(lè)在情感上觸動(dòng)我們,使我們了解和習(xí)慣真正的愉悅,這也就不難理解亞里士多德關(guān)于樂(lè)調(diào)對(duì)性格、情感影響的分析。
正如混合利底亞調(diào)更適合表達(dá)壓抑、沉郁的情感,而多利亞調(diào)所特有的厚重感往往使人心舒意緩,中正平和。至于催發(fā)人心、激蕩心神則非活潑的弗里吉亞調(diào)莫屬,其律調(diào)極高,律格威武雄壯,有利于鼓舞精神和激發(fā)強(qiáng)烈的愛(ài)國(guó)情懷。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稱贊弗里吉亞這一調(diào)式,主要是因?yàn)橛纱俗V寫的出征音樂(lè)、祭神音樂(lè)等,可以激發(fā)人們非凡的戰(zhàn)斗熱情和虔敬的宗教情感,滿足精神需要[17]179。希臘人為了達(dá)到藝術(shù)教育的目的,希冀詩(shī)文、歌曲、繪畫甚至雕塑,都能起到情感熏陶的作用,現(xiàn)今雅典古城遺址仍可清晰地感受到造型藝術(shù)上所蘊(yùn)含的濃重多利亞和愛(ài)奧尼亞風(fēng)格的結(jié)合,表現(xiàn)在建筑和雕塑上的意象似乎也在彰顯著某種教化意蘊(yùn)。從亞里士多德對(duì)情感的描述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音樂(lè)教育的好壞取決于它是否以一種有序或無(wú)序的方式打動(dòng)我們。通過(guò)音樂(lè)在不同類型的情感運(yùn)動(dòng)中給聽(tīng)者帶來(lái)愉悅,能夠使人享受有序或無(wú)序的情感。如果通過(guò)音樂(lè)教育能使聽(tīng)者熟悉或習(xí)慣平衡這一類情感運(yùn)動(dòng),就能最終達(dá)到培養(yǎng)美德的目的。
(三)導(dǎo)正德性
亞里士多德指出,音樂(lè)本身具有相對(duì)穩(wěn)定的秩序和無(wú)窮的變化,宜在教育中使用。遵循恰當(dāng)理性的原則是判斷某一行為道德價(jià)值最根本的標(biāo)準(zhǔn),只有適度才能培育德性[18]296。關(guān)于適度的討論體現(xiàn)在他“把旋律區(qū)別為培養(yǎng)品德、鼓勵(lì)行動(dòng)和激發(fā)熱忱的三種基本音節(jié)”[11]436。他認(rèn)為,當(dāng)人們?cè)谘堇[、欣賞一首具有高尚情操的樂(lè)曲時(shí),音樂(lè)作用于人的潛在素質(zhì)教育功能便悄然發(fā)生,美妙的音樂(lè)潤(rùn)物無(wú)聲,在不知無(wú)覺(jué)中品格就獲得了錘煉,需要說(shuō)明的是在特定環(huán)境中所允許的音樂(lè)愉悅的類型是由是否追求更高的境界,即美德來(lái)衡量。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快樂(lè)最終朝向美德。那么,是否所有的聲音、曲調(diào)都適合用作德性的育化?由于在聲音中不僅有高音和低音,還有強(qiáng)音、澀音等,如果人們對(duì)感覺(jué)對(duì)象的情感太過(guò)強(qiáng)烈,則會(huì)破壞感覺(jué)器官;而一旦刺激太強(qiáng),那么協(xié)調(diào)的比例(這種比例就是感覺(jué))也會(huì)被破壞。極端的感官刺激不僅會(huì)破壞我們的感覺(jué)器官和感知能力,甚至對(duì)靈魂的生長(zhǎng)都會(huì)產(chǎn)生影響,更別說(shuō)對(duì)德性的導(dǎo)正,“強(qiáng)烈撞擊聽(tīng)覺(jué)器官的聲音是刺耳的;因此,令人尤為痛苦”[19]29。
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觀點(diǎn),在選擇樂(lè)調(diào)時(shí)最好是以培養(yǎng)品德為主,保證音樂(lè)教育符合中庸、可能和適度三項(xiàng)標(biāo)準(zhǔn)。我們應(yīng)該選取中庸,既不過(guò)度,也非不及。而德性是中庸之道的一種,同時(shí)“德性和善是一切事物的尺度”[20]224,是一種具有選擇能力的品質(zhì)。在這一點(diǎn)上,他與柏拉圖達(dá)成共識(shí),皆強(qiáng)調(diào)理性的節(jié)制,在面對(duì)音樂(lè)的感官刺激時(shí),應(yīng)講究節(jié)制且理性的享受,因?yàn)橘|(zhì)樸的音樂(lè)文藝教育才能凈化心靈、塑造優(yōu)良城邦公民。他在考察音樂(lè)本體特質(zhì)時(shí)發(fā)現(xiàn),低音天性中的高貴品格,常孕育著美好的事物,但太過(guò)高亢或過(guò)于低沉的曲調(diào)會(huì)打破美好的界限,故不適合教育之用。高亢嘹亮的曲調(diào)短時(shí)間內(nèi)激勵(lì)人心的作用非常顯著,但長(zhǎng)期的持續(xù)會(huì)讓人處于一種緊張焦灼甚至焦慮狂躁的狀態(tài),不利于身心滌蕩和德性情感的引導(dǎo),反之亦然。例如笛這種聲音高亢且在吹奏時(shí)可能會(huì)讓人身體不協(xié)調(diào)的樂(lè)器,雖然它對(duì)人心有鼓動(dòng)、激勵(lì)效果,但在表現(xiàn)道德品質(zhì)方面稍欠,可選擇更為緩和的里拉琴。從曲調(diào)調(diào)式特征來(lái)看,不同年齡段的人適合采用不同曲調(diào)進(jìn)行德性培育,老年人氣勢(shì)衰微,最好只唱一些低吟淺唱的曲調(diào);年輕人情感活躍,更適合高低相和、百轉(zhuǎn)千回的利底亞調(diào);而多利亞調(diào)基本遵循了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天人合一,對(duì)于最大化發(fā)揮音樂(lè)的德性效力頗有助益。因此,我們有理由認(rèn)為,正確且恰當(dāng)?shù)囊魳?lè)教育至少能對(duì)德性的導(dǎo)正做出積極貢獻(xiàn)。
此外,亞里士多德強(qiáng)調(diào)在用音樂(lè)對(duì)兒童進(jìn)行德性培養(yǎng)時(shí),務(wù)必謹(jǐn)慎對(duì)待且遵循音樂(lè)的最佳原則。不管多么微不足道的環(huán)節(jié),都必須正視音樂(lè)在兒童德性生成過(guò)程中的強(qiáng)大塑造力和影響力,防止德性導(dǎo)正過(guò)程中因監(jiān)管不力而導(dǎo)致的“序”的混亂、“和”的失衡。因而,用于教育的優(yōu)美旋律最好有序且保持在一個(gè)單一和弦或單一模式的音程范圍內(nèi),不至于產(chǎn)生過(guò)于強(qiáng)烈的刺激。亞里士多德他不否定其他曲調(diào)帶來(lái)的影響,但建議我們遵循那些對(duì)音樂(lè)教育素有研究的人的先進(jìn)意見(jiàn)[21]264。
四、結(jié)語(yǔ)
古希臘作為西方教育思想的策源地,塑造了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等社會(huì)要素的原始形態(tài),亞里士多德對(duì)音樂(lè)育化美德的論述亦產(chǎn)生于這一思想活躍、各家爭(zhēng)鳴的時(shí)期,它既不是對(duì)一種共同信仰不假思索的接受,也不是一種漫無(wú)目的的情感傳遞的結(jié)果,而是對(duì)教育問(wèn)題的清醒認(rèn)識(shí),是全方位和諧發(fā)展教育理念的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在他看來(lái),自然界中的事物存在著普遍聯(lián)系,音樂(lè)則能通過(guò)描述這種普遍聯(lián)系而再現(xiàn)真實(shí),讓人在受到感染和陶冶后,獲得享受,進(jìn)而提升道德水平和靈魂境界。
從亞里士多德對(duì)旋律和節(jié)奏的關(guān)注開(kāi)始,其音樂(lè)教育理論便擁有了堅(jiān)實(shí)的哲學(xué)基礎(chǔ),他認(rèn)為音樂(lè)教育并不依賴于情感的盲目傳遞,而是一種有意識(shí)的感性訓(xùn)練,旨在突顯音樂(lè)的育化力量。因而,這些關(guān)于音樂(lè)教育的言論不僅是亞里士多德個(gè)人審美的興趣所在,更是當(dāng)時(shí)關(guān)乎古希臘社會(huì)存亡的重大問(wèn)題。不僅因?yàn)橐魳?lè)的特質(zhì),而且還有它們作為維護(hù)城邦統(tǒng)治的倫理、道德、教化功用[22]10。對(duì)生命的尊重和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享樂(lè),無(wú)疑讓音樂(lè)的神性、人性、德性和諧地統(tǒng)一起來(lái),影響了整個(gè)古希臘教育。但古希臘的政治、道德危機(jī)使得教育中原本被遮蔽的矛盾凸顯,還是不可避免地走入了衰落期,音樂(lè)和繪畫不再被看作是教育的必要部分。亞里士多德所闡釋的保守教育措施,其用意更多的是想通過(guò)音樂(lè)的育化力量重尋荷馬時(shí)代那般質(zhì)樸的美德,從而阻止古希臘傳統(tǒng)價(jià)值觀的凋零。
新時(shí)期的教育發(fā)展亦不再局限于知識(shí)技能的簡(jiǎn)單傳授,而是應(yīng)立足于馬克思主義美學(xué)思想和文藝觀,從古典傳統(tǒng)中為當(dāng)下音樂(lè)藝術(shù)美育發(fā)展找尋參照對(duì)象、汲取養(yǎng)分,觀照教育德性,更多地轉(zhuǎn)向如何提升教育品格、關(guān)注個(gè)體成長(zhǎng)和促成身心圓融,最終通達(dá)個(gè)體生命的完整性發(fā)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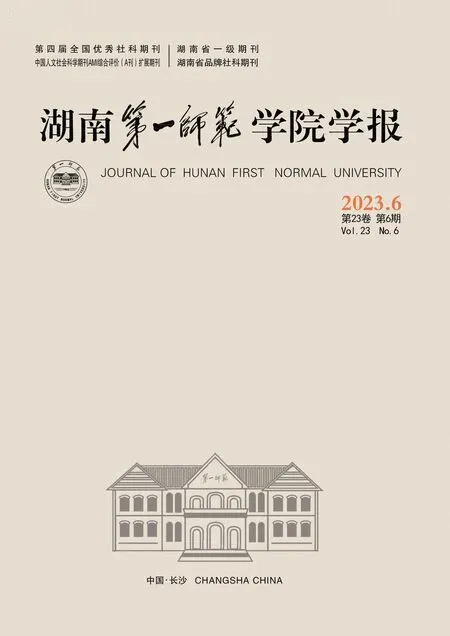 湖南第一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23年6期
湖南第一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23年6期
- 湖南第一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的其它文章
- 湖南第一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23 年總目次
- 接受與流播:韓國(guó)瀟湘八景詩(shī)中的“恨別思?xì)w”
- 中國(guó)共產(chǎn)黨人精神譜系融入高校“大思政課”建設(shè)的多維論析
- 新時(shí)代實(shí)現(xiàn)高職學(xué)院思政課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探究
- 新時(shí)代大學(xué)生生命教育的實(shí)踐困境與路徑優(yōu)化
——基于人體形態(tài)學(xué)科技館沉浸式生命教育的探索 - 當(dāng)代中國(guó)女性主義思潮的演進(jìn)、效應(yīng)與引領(lǐ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