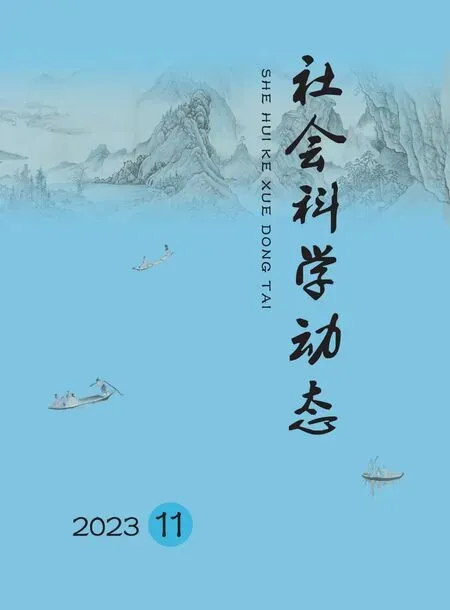重塑墨子:梁啟超《子墨子學說》的撰寫及其影響
李佳煌
墨學復興是近代學術轉型中的重要事件。1904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發表《子墨子學說》,開啟了墨學的近代研究。梁啟超雖自稱此文在框架上多取日人高瀨武次郎的《墨子哲學》一書,但在學說闡釋上,其為塑造墨子形象而對墨子學說進行的一系列分析仍具有不少獨立見解,尤其是將墨子重塑為以宗教形式倡行實利主義、兼愛主義的實行家,奠定了墨學近代化闡釋的基本規模,從而在中國近代諸子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過往學界對此文已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或在近代墨學研究史中涉及該文的學術史地位,或在對比梁啟超前后期墨學研究中分析《子墨子學說》。①其中,對《子墨子學說》做出專題研究的有黃克武與日本學者末岡宏。②但以往研究仍存在可以進一步追問的余地。如《子墨子學說》的寫作緣起、本土學術淵源、學術反響及其在中國近代諸子學史上的學術意義等基本問題,尚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基于此,本文將從學術史的角度對梁啟超《子墨子學說》予以進一步分析與考察。
一、《子墨子學說》的寫作緣起
梁啟超是中國學術向近代轉型中的關鍵性學者,他憑借著對傳統學術的深刻理解,與對西方近代學說的了解,為溝通中西學術作出重要貢獻。
晚清以來,諸子地位發生顯著變化,最突出的是墨子地位的提升。③而梁啟超對晚清墨學復興的各個環節都非常熟悉,并參與其中。其一,孫詒讓贈《墨子間詁》于梁啟超。晚清仍有不少學者沿著乾嘉考據傳統,對《墨子》進行訓詁、校注,孫詒讓的《墨子間詁》被認為是集大成之作。梁啟超曾自稱孫詒讓贈書是其對墨子及周秦諸子產生濃厚興趣的重要因素。④其二,梁啟超從其業師康有為學說中了解到墨學與西學相通的觀點。康有為曾明確說道:“墨子之學,與泰西之學相似,所以鄒特夫先生云:墨子之教流于泰西,其中多言‘尊天’‘明鬼’之說。”⑤可以說,康有為認為西學與墨學的相似是全方位的,以自然科學而言,康氏認為“墨子專言物理”⑥,就社會宗教而言,康氏認為西方宗教是墨子天志、明鬼說的翻版,因此他反復強調“墨子正開西學派”“歐洲盛行墨學”。⑦此外,康有為還對比了墨子與耶穌之異同,認為墨子與耶穌都“能死,能救人,能儉”,且“傳教最勇悍”,有不少弟子“死于傳教”。⑧康有為對墨子的闡釋在《萬木草堂口說》的“學術源流”一節中,都可以尋見,而古今學術源流正是當時梁啟超等人聽課中感到最“興奮”的內容。其三,與梁啟超同為維新人士且關系甚密的唐才常、譚嗣同等人“為治新學者”而多談墨學。梁啟超本人也好談墨學,且被夏曾佑稱為“兼士”。⑨唐才常在《治新學先讀古子書》中肯定墨學的社會價值,即“欲救今日士、農、工、商各懷私心之病,則必治之以墨學”⑩。譚嗣同在《仁學》的“自敘”中開篇便提出“能調燮聯融于孔與耶之間,則曰墨”,其認為墨有兩派,即“任俠”與“格致”,這兩派“近合孔、耶,遠探佛法,亦云汰矣”,肯定了墨學在溝通中西學術方面的價值。?
從梁氏接觸的墨學來看,大多為西學與墨學在天志、明鬼、兼愛及自然科學有相通之處,并肯定墨學具有重要的社會價值。受此影響,梁氏在1902 年發表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指出:“墨子生于宋,宋,南北要沖也,故其學于南北各有所采,而自成一家言。其務實際、貴力行也,實原本于北派之真精神,而其刻苦也過之;但其多言天鬼,頗及他界,肇創論法,漸闡哲理,力主兼愛,首倡平等,蓋亦被南學之影響也。”?然而,此文僅在“孔北老南”的說法下簡單提及墨子學說,其在第一章第三節“論諸家學說之根據及其長短得失”的“闕”,使胡適認為《子墨子學說》是《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的補作?,但從兩文思想內容來看,二者并無繼承關系。因為梁啟超在《子墨子學說》時已將兼采南北的宋人墨子重新定義為曾受孔學,之后為抗衡老孔學說而采用宗教形式立說的魯人墨子,并將墨子時代定于孔子與孟荀之間,稱墨子為“從儒學一轉手者”。?
除本土墨學復興對梁啟超關注墨學形成誘導之外,梁啟超在日本接觸到的中國哲學研究也是其在1904 年闡釋墨子學說的重要誘因。
梁啟超在20 世紀的最初幾年中,對日本中國哲學研究關注較多的是陽明學。有研究者指出,梁啟超曾多次直接引用日本學者井上哲次郎的陽明學觀點。?梁氏之所以重視日本陽明學研究,是因為其對于日本學者提倡陽明學中的知行合一、實行主義以及對利己主義的批判、對國民道德的培養等思想是非常認可的。?值得注意的是,高瀨武次郎也是日本陽明學研究的代表人物,他在1898 年出版了《日本之陽明學》,又在1904 年出版了《王陽明詳傳》。高瀨武次郎的陽明學研究主旨直接繼承其師井上哲次郎。而日本近代墨學的發展與以井上哲次郎為代表的學者群體又密切相關。據日本學者研究指出,日本近代墨學的代表學者服部宇之吉、藤田豐八、木村鷹太郎、西脅玉峰及高瀨武次郎都是井上哲次郎的學生,在其論述中,“處處可見與西方哲學家或哲學概念之比較”。?他們認為陽明學中提倡的若干理念,與墨學中的某些觀點是能夠相通的,如墨子的力行與陽明學的知行合一。同時,他們認為墨學與西學也有相通之處。其中,高瀨武次郎就關注到墨子兼愛與耶穌博愛理念的相近。這無疑吸引梁啟超關注到墨學的社會價值。故此,梁啟超應是通過日本陽明學接觸到高瀨武次郎等人的墨學研究。此外,日本學者常常從“倫理學”視野闡釋墨子學說,如木村鷹太郎所著的《東洋西洋倫理學史》一書,就借助西學中的實利主義學說資源闡發墨學思想。?梁啟超曾在《東籍月旦》首列書目類別為“倫理學”,其中明確提到了《東洋西洋倫理學史》。?
不過,梁啟超之所以接受上述思想資源,與其此一階段從培養“私德”的角度肯定宗教形式的思想傾向有關。1902 年10 月,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發表《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一文,以宗教家對未來犧牲之精神肯定了宗教對進化的積極意義,并引斯賓塞“國界應當盡破,世界必為大同”,透露出對康有為學說的重新肯定。?同月,他還在《新民叢報》發表《宗教家與哲學家之長短得失》一文,特別強調應該重視宗教之道德,康有為、譚嗣同都有得于佛學,以宗教思想之力對社會風潮發生巨大作用。?這一思想傾向對梁啟超塑造具宗教色彩且注重力行的墨子形象產生重要影響。
綜上所述,晚清墨學研究與日本近代墨學發展為梁啟超重新認識墨子學說提供了思想誘導,促使其在闡發提升國民道德、發揚宗教中的道德精神的思想主張時注意到墨子學說,從而開始塑造墨子具有宗教形式、持“利他主義”的“實行家”形象。
二、《子墨子學說》的思想來源
關于梁啟超《子墨子學說》的思想來源,可分為兩方面。一方面是日本學說的影響。這主要是高瀨武次郎的《楊墨哲學》。梁啟超在文中明確指出其文“間采高瀨武次郎所著《楊墨哲學》,其案語則全出自鄙見”?。實際上,不只在按語,在行文內容上,梁啟超也多有自己的發揮。末岡宏在研究中對比二者異同后,進一步補充到梁啟超對加藤弘之的利己主義觀點的接受。?需要指出的是,末岡宏的研究尚忽視了梁啟超更為關鍵的本土思想來源。
首先,《子墨子學說》最直接的思想資源來自康有為。其一,關于墨子的時代背景與孔墨關系。就墨子學說時代背景而言,梁氏在《子墨子之時代》概括為“然交通既繁,詐械日出,奢靡相尚,故倡學救世者,咸懷復古思想。如孔子之言堯、舜、文王。老子之言黃帝,許行之言神農,墨子之言大禹,凡以救此敝也”?。此論顯系承自康有為“諸子托古創教改制”?的觀點。就孔墨關系而言,梁氏將墨子視為“實從儒學一轉手者也”與康有為認定墨子本孔子后學的身份歸屬是一致的。?其二,在分析墨子天志思想時,梁啟超在“天”的案語中認為“耶、墨兩圣之教義,本無一不為孔子所涵,而以耶、墨與孔教同視不得也”,又說“儒家謂道之大原出于天”。?“諸子之始皆由于天”“墨子近于耶穌”的觀點多次被康有為強調。?其三,在墨子節葬問題上,康有為認為孔子提倡的“三年喪”是“以父子天性,動以至仁”,孔子傳教得力于“三年喪”,而反對三年喪的墨教則因此短于傳教。?梁啟超認為墨子提倡節葬,是“搗儒家之中堅”的觀點,但也指出墨學此舉是過分忽視“消極的欲望”,從而“不能大行于后者,未始不坐是”。梁啟超多次指出墨子學說只言“物質之實利”,而不知“精神上之實利”,如果“得此條發明之”,即吸納孔子學說中的“義”,然后“知墨子之言利,圓滿無憾也”。?梁啟超能夠指出墨學之不足與儒家之優長,正與康有為學說影響有關。這從梁啟超于1904 年所作《近世之學術》為康有為的孔教及諸子學說有所回護可以看出。?
其次,梁啟超還吸收了章太炎在《儒術真論》一文中比較儒墨異同的見解。1899 年8 月,章太炎于《清議報》發表《儒術真論》,認為儒家原本主張“天為無明”和“無鬼神”,并以此反對康有為孔子受命于天及將儒學宗教化神秘化的觀點。?章太炎據公孟子與墨子的對話分析認為,公孟子所說的“有義不義,無祥不祥”是反映儒家觀點的,儒家的“命”并不具有能夠決定“治亂安危”的作用,所謂的“天”也是在自然之中,即“天為無明”。?梁啟超同樣在文中引《墨子·公孟》篇,不過其重在指出墨子所說的“古圣王皆以鬼神為神明,而為禍福,執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國安也。自桀、紂以下,皆以鬼神為不神明,不能為禍福,執無祥不祥,是以政亂而國危也”?。梁啟超認為章太炎特標《公孟》三義為儒、墨異同之關鍵“可謂特識”?,“有義不義,無祥不祥”確實是儒家的立腳點。儒家重視“義不義”與墨家重視“祥不祥”顯然為梁啟超在文章開篇提到的墨子以宗教形式抗衡“趨于哲學與社會”的孔老,以及反復申言的墨子以天志為中心學說,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
此外,梁啟超還受到了夏曾佑的影響,尤其是在評價墨子宗教思想與孔墨優劣上。其一,在論述墨子“明鬼”時,梁啟超受夏曾佑影響。夏曾佑認為孔墨相反之始端在于墨子節葬,節葬必明鬼,“有鬼神則生死輕,而游俠犯難之風起,異乎儒者之尊生;有鬼神則生之時暫,不生之時長,肉體不足計,五倫非所重,而平等、兼愛之義伸,異乎儒者之明倫”?。而梁啟超在認識墨子學說中的“明鬼”時,雖起初認為“明鬼”贅疣而無謂,但在第五章中,其又從“精神”上認為“有鬼無鬼之論辯,與民德之強弱升降,有大關系焉”。尤其是在分析墨子輕生死精神時,認為“蓋有鬼神則有靈魂,有靈魂則身死而有其不死者存,有靈魂則生之時暫而不生之時長,生之時幻而不生之時真。夫然后視生命不甚足愛惜,而游俠犯難之風乃盛”?。此論顯然受夏曾佑書中觀點的影響。其二,在孔墨學說的評價上,梁更受夏曾佑影響。夏曾佑在《三家總論》中提到:
孔子留術數而去鬼神,較老子為近人矣,然仍與下流社會不合,故其教只行于上等人,而下等人不及焉。墨子留鬼神而去術數,似較孔子更近,然有天志而無天堂之福,有明鬼而無地獄之罪,是人之從墨子者,苦身焦思而無報;違墨子者,放辟邪侈而無罰也。故上下之人,均不樂之,而其教遂亡。至佛教西來,兼老、墨之長,而去其短,遂大行于中國,至今西人皆以中國為佛教國也。?
夏曾佑在此處主要表達了兩層意思:一是孔子留術數而去鬼神但遠離下流社會,墨子留鬼神而去術數但報施之說缺乏以致教亡;二是佛教能夠兼其之長、去其之短,而盛行于中國,至今未衰。梁啟超同樣認為墨子在報施說上有所欠缺,墨子缺失了宗教家最重要的原質之一即“靈魂”,如果有此義,“然后禍福賞罰之說,乃圓滿而無憾。”墨子在這方面的不足導致其教不倡。梁在論墨子非命時認為可以將佛之因果說作為其奧援。此外,梁還提到“孔教之不能逮下,皆坐是”,進而認為如果“使孔子而如佛之權實并用,兼取墨子祥不祥之義而調和之”,那么,中國“二千年來社會之現象,其或有異于今日乎”。?二人觀點基本一致。
綜上所述,梁啟超的《子墨子學說》不僅借助了高瀨武次郎等日本學者的研究,還接受了康有為、章太炎、夏曾佑等國內學者的相關論述。
三、墨子學說體系的塑造
大體來說,《子墨子學說》最大的特點是“憑借新知以商量舊學”?。梁氏在文中引用大量西方社會思想學說,并以西方社會科學的概念將墨子義理分門別類。但值得注意的是,其還指出了墨子學說中存在的“循環論證”:墨子根據周末的社會情形倡行節用、節葬、非樂、尚同、尚賢、兼愛、非攻的學說主張,而為與孔老抗衡,又借以宗教為形式的“天志”作為立說基礎,并使“天志”本身在內容上又含實利、兼愛諸義。墨子言“明鬼”不過是為改良社會提供一方便法門,言“非命”也是“天志”的題中之義。因此,梁啟超突出“天志”在墨子學說中的關鍵地位,認為墨子學說中代表道德的兼愛主義與代表幸福的實利主義都要靠“天志”來“調和”,并專章闡釋其學說與“實行”的關系如何,最終的落腳點都是為了突出墨子救世而起的“實行家”形象。
首先,梁啟超論述了墨子學說產生的時代背景,強調墨子學說為救時而起,并指出“天志”在墨子學說體系中起關鍵作用的思想背景。梁啟超認為墨子的時代在孔子稍后、孟荀之前,墨子因“周末文勝之極弊”而有節用、節葬、非樂諸義,又因“社會不統一”而有尚同、尚賢諸義,因“內競最烈”而有兼愛、非攻諸義。梁啟超使用“救此弊”“而人道或幾乎息,是當世睿哲之所最憂,而汲汲欲救之者也”等詞句,突出墨子學說提出的救時之義。然后,梁氏又指出初民時代的社會為“迷信之狀態”,到了“孔老倡學”,才全趨于“哲學與社會之實際”,且“其宗派雖殊,然其為迷信之敵則一也”,而后出的墨子為與孔老抗衡,則“據宗教之基礎以立一哲學也”。這就為突出墨子學說中的“天志”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背景。?
其次,梁啟超詳細論述墨子學說如何圍繞“天志”而成立。
第一,梁啟超分析了墨子學說中“天”的內涵,并指出墨子的宗教思想、實利主義與兼愛主義是墨學之總綱,但后兩者都要靠“天志”來調和。具體而言,梁啟超認為在追求道德與追求幸福中間有一“矛盾”,而墨子追求的是“必要的欲望”,反對“奢侈的欲望”,故節用是墨子“實利主義之目的”,節葬、非樂也是如此。同時,墨子追求的利固然重視利己,但也重視“最大多數者”之利與使“良心泰然滿足者”之利。由此,墨子要求追求利與道德相統一起來。而墨子學說中的“天”本身有“天欲義而惡不義”“天欲使人相愛相利,不欲使人相惡相賊”的含義,這就使“天志”處處透漏“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的理念。換言之,“天志”本身就要求對人“兼而愛之”、愛人利己。于是,“天志”便能夠調和道德與幸福。?
第二,梁啟超認為墨子雖然既言“天志”又言“明鬼”有些贅疣,但這是出于為改良社會提供一“方便法門”。梁氏對墨子言明鬼的緣由,一方面指出是墨子重視宗教思想而未脫上古野蠻信仰之遺習所致,另一方面又強調墨子并非絕對的迷信。因此,墨子辨鬼神之有無,不是從學理上求答案,而是“于實際上求答案”。
第三,梁啟超重點分析了墨子學說中看似矛盾的“既言天志又言非命”之說。梁啟超認為非命是“墨學與儒學反對之一要點”,儒家可為命定說的代表,而墨子則是反對命定說的力行說。在《非命》中,梁啟超首先闡釋了儒學對命的基本看法:“孔子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命是儒教中“普通信條”之一,命有消極(有制限的,盡人力之所得與不得歸諸命、修身以俟之)和積極(無制限的,以命自暴或以命自棄)兩種。康有為在解釋墨子以“無命”之說攻擊孔子時說道:“《論語》則首以學而后知命,孔子立名之后,命即隨之。蓋命所以視其有一定之理,不可強求,即孟子所云孔子得不得之義也。名則興起撥亂之治矣。夫有行,而后有命;無行,是無命也。翟獨昧于此,而力爭之。”?梁啟超在解釋儒家“命”義時顯然受到康有為影響,將儒家的命與“義得不得”相聯系,但對于墨子“非命”說評價卻有不同。他肯定墨子非命說的依據是與命相反的“力”符合優勝劣敗的天演公例。康有為看到墨子在攻孔子“立命”說時“引《書》為證”,但《書》中多言天命,康將此解釋為“墨子之《書》亦墨子刪改而成,其言皆托古墨子之《書》”?。梁啟超則認為“墨子固言,天也者,隨人之順其欲惡與否而禍福之”,如此一來,“天志”與“非命”便達到了統一。梁啟超肯定了墨家“既言天志而又非命”的觀念,并感慨道“安得起墨子于九原化一一身……而為之廓清辟邪之”?。
隨后,梁啟超在論及墨子實利主義中的“本天說”時,對墨子“既言天志又言非命”這一命題在補儒家思想不足上的價值做進一步引申。梁啟超并不否認孔教命定說中的“義”,并認為孔教提倡的“義”確實是“道學正鵠”,但是“奈其所謂義不義之目的,又卑下淺薄無以導人向上之途,此實中國德育墮落之一重要原因”。這就是說,只言道德之大義律使孔教雖高尚卻不普及。梁啟超指出孔子如果像佛教“權實并用”,又采取墨子“祥不祥”之義,那么,今日中國社會就不是這樣。所謂“祥不祥”之義就是梁啟超概括的墨學之綱領——利之大原出于天,而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最后,梁啟超重點分析了墨子學說的“實行”。他重視儒墨學說的比較,并表現出較為明顯的“揚墨抑儒”傾向,從而突出了墨子的“實行家”形象。對于“尚賢”,梁認為儒家與墨子都有“尚賢”之義,但是儒家在“尚賢”之外,又有“親親貴貴”諸義,而墨子“舍賢外他無所尚”。故墨子尚賢主義是“實取舊社會階級之習,翻根本而摧破之”。對于“非命”,梁啟超認為非命力行正與厭世主義相對,人人則可有“自由競爭之銳氣”,所以墨子的“實行力所以至強而莫能御也”。對于“明鬼”,梁啟超指出“明鬼”體現了墨者輕生死的精神,而這種精神可以“起中國之衰”。總之,梁啟超通過分析墨子學說各要義與“實行”之關系,肯定了墨子的“實行家”精神。?
綜上所述,《子墨子學說》首先指出墨子學說產出的時代背景及其據宗教形式立一哲學的思想背景,而后分析了墨子如何圍繞“天志”建立自身學說體系,以及墨子學說與“實行”之關系,從而塑造了墨子的“實行家”形象。
四、《子墨子學說》的學術反響與意義
在清末的墨學研究中,孫詒讓的《墨子間詁》與梁啟超的《子墨子學說》對當時學界影響最大。方授楚曾指出前者“著作精審”,后者則“文辭暢達,使新學小生,能知有所謂墨子與所謂墨學者”?。當時學界受到梁啟超影響的學者有錢玄同、胡適、王桐齡等人。錢玄同于1910 年讀梁啟超《子墨子學說》時,批評其“強與歐西附會”,但是亦有可取之處。他認為言教育者,“重實行不重理論”,孔子這樣的“哲學家言不能供教育之用”,不過孔子畢竟“立教以六藝為本,固與玄言有異”,最好的方法就是“兼取孔、墨”。顯然,錢玄同重視墨子實行的精神與梁啟超一致。?
胡適也受到梁啟超影響,他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有關墨子的見解多與梁啟超相同。胡適同樣認為墨子為魯人,受到儒家學說影響,而后又從明鬼、節葬、非樂、非命四端攻擊儒家的壞處。胡適認為“墨子的天,是有意志的。天的‘志’就是要人兼愛。凡事都應該以‘天志’為標準”。其中,他對墨子既言天志又非命的解釋與梁啟超的論證幾乎一致。梁啟超稱墨子為據宗教形式立一哲學的實行家,而胡適徑稱墨子為實行的宗教家,故二人所論又有一定差異。?
王桐齡在1922 年出版的《儒墨之異同》一書中認為孔子、墨子都是實行家而非宗教家,該書從宗教、道德觀念、政治理想、實行等方面對比儒墨異同,于內容上多有直接承襲梁啟超之處。如其論墨子天志、兼愛為“墨子所以言天志者,凡以為兼愛說之前提云爾。所謂天志者,極簡單而獨一無二者也。曰,愛人利人而已”;又如其論墨子非命為“墨子劃分天與命為二物。天也者,隨人之順其欲惡與否而禍福之,是天有無限之權也。命定而不移,則是天之權殺也。故不有非命之論,則天志之論終不得成立也”。
平理而論,梁啟超固然重視墨子的宗教思想,但其將宗教視為墨子為立一哲學而借助的形式,這就產生了墨子所欲立哲學的根本觀念是否為“天志”的問題。張爾田在《史微》的《原墨》篇中認為天志為墨子學說之本,兼愛、非攻諸義皆由“天志之義推而見諸行事”,與梁啟超觀點相近。張煊則提出反駁,稱墨子學說以兼愛為本,“以實用為主”,“于人實無利者,墨所不取”。張爾田對此反詰道:“豈一主張實用,即當決口不涉天耶?”梁啟超后期將墨子的根本觀念視為兼愛,或受此爭論影響。但就總體而言,《子墨子學說》已能夠較為融洽地處理天志與兼愛的關系問題,其論述雖較為粗疏,但還是有的放矢。
由上可知,《子墨子學說》在學界產生了重要的學術反響。而更值得關注的是,該文還在推動諸子學研究的近代轉型上具有重要的學術史意義。
第一,在研究方法上,該文吸納日本學術資源,突破傳統漢學主導下的墨學校注,開啟墨子義理闡釋的近代化先河。嚴靈峰就曾指出其學術史意義在于“突破了歷來考證工作的藩籬,采用新的方式,并以之與西方思想比較,來研究整個的墨子思想;蹊徑獨辟,在墨學的研究中,創新天地,開新境界,梁氏真是昭代異人!”。梁啟超承續晚清墨學復興以來的學術脈絡,又受日本近代墨學研究影響,運用西方概念與分析方式對墨子義理加以闡釋,可以說是將中國本土學術傳統與西方現代性進行一次接軌的大膽嘗試。不可否認的是,晚清以來不少學者在諸子學研究上進行牽強的中西比附,梁文部分也存在這一弊端,但正如有論者指出近代學者會通諸子與西學的努力確實促進了“文化革新”。梁啟超為墨子義理闡釋近代化發揮的作用仍值得肯定。
第二,促進諸子進一步平等。清代中葉,汪中在《墨子序》及《墨子后序》中表現推崇墨學之意,對傳統的儒墨關系提出了新的認識,表現出明顯的孔墨平等傾向。盡管汪中已萌發孔墨平等的意識,但其于經學統治時代發此論,學術影響有限。梁啟超將進化的歷史觀與諸子學說結合在一起,在文章開篇便將孔老墨學說與“宗教哲學”的思想邏輯加以結合論述,客觀上平視墨子與孔老諸子。而后梁氏又對墨子義理進行詳細闡釋,采取孔墨對比的方式,并提出可使墨學與孔學相結合的思考,無疑提高了墨子在諸子中的地位。這種孔墨比較的闡釋方式被胡適、王桐齡等學者遵循。同時,梁文在論述墨子實行家精神時,有一定的“揚儒抑墨”傾向。將此放置于近代學術轉型中來看,這事實上充當了突破康有為“揚儒抑墨”的有力“推手”,從而在客觀上促進了諸子平等。
第三,初步構建起以宗教哲學為核心概念的孔老墨敘事。清末,康有為構建了“周末諸子并起創教,托古改制,爭教互攻”為核心的諸子敘事。梁啟超此文雖然繼承康有為諸多觀點,但其通過引入哲學概念進一步突破康有為的敘事體系,而這事實上成為清末民國諸子敘事的主要體系之一。1906 年,章太炎在《論諸子學》中明確指出:“墨家者,古宗教家,與孔、老絕殊者也。”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儒家公孟言無鬼神”“道家老子言以道蒞天下”,如此說來儒、道便“皆無宗教”。至民國時期,以宗教哲學為核心概念的諸子敘事體系得到進一步深化。胡適、呂思勉是持這一敘事的代表學者。1919 年,胡適出版《中國哲學史大綱》,從“老子”講起,認為老子是一個“極端的破壞派”,孔子是“積極的救世派”,墨子則受儒家的影響,但其“反對儒家,自創一種新學派”,后又輸入天志、明鬼,為實行的宗教家。呂思勉認為“人群淺演之時,宗教哲學,必渾然不分,其后智識日進,哲學乃自宗教中蛻化而出。”其中,老、孔便是將哲學從宗教蛻化的代表,不過,“諸家之言,皆似無神論、泛神論,而墨家之言‘天志’‘明鬼’,則所謂‘天’所謂‘鬼’者,皆有喜怒欲惡如人。故諸家之說,皆近機械論,而墨子乃獨非命”。呂思勉與梁啟超的論述極為接近。從學術史的眼光來看,以宗教哲學為核心概念構建的諸子敘事,本質上是將諸子同社會歷史演進結合起來,進而闡發諸子的學說理念。這無疑極大地推動了諸子學研究的近代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