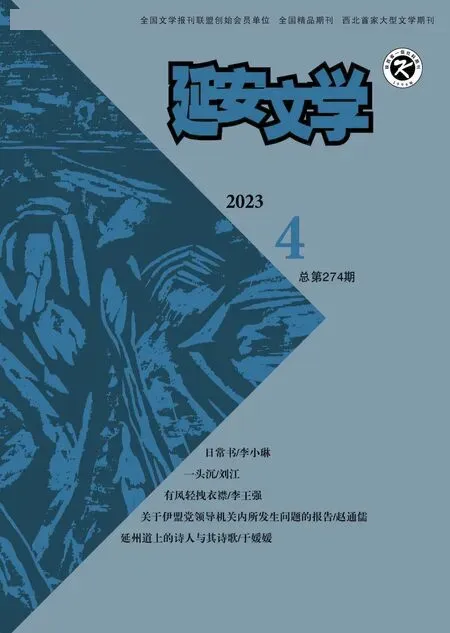西地平線上的落日和星空(外一篇)
孟澄海
太陽還沒有落山。
或者說,這里本來沒有山,黑戈壁上只隆起著饕餮般的沙丘。太陽就懸浮在一層青灰的煙塵之上,光線呈現(xiàn)出暗紅或蒼黃顏色,沉落之前,猶若祭壇上渾圓的銅鼓,喑啞、悲涼、凝重……
那時候,我已來到居延海邊。
風吹過來,我感到身上已沒了祁連山雪花的冰涼,而是一種令人心煩的干燥與悶熱。能看見風的背影,卷著沙塵在遠方奔跑,鬼魅般飄起又落下。幾十只駱駝站在風中一動不動,恍若褐色山崖。居延海就在風的背景下展開,湛藍或澄碧,雪浪漣漪,一圈一圈由里向外蕩漾。火星一樣荒涼的巴丹吉林沙漠,卻環(huán)抱著這么一個水泊,令人想起審美的悲壯和崇高。《圣經》上說,神靈無處不在。神有意造海,水就來了。其實,在時光遠方,神就是自然造化,掌握著秩序規(guī)律。人類足跡尚未抵達這里的歲月,神給這里安排了天堂般的環(huán)境:澤鄉(xiāng)水國,芳草野花,錦鯉銀鷗……
很靜,我站在岸上,彎腰掬起一捧水,輕輕靠近嘴唇,清涼,甘洌,依然有黑河源頭的氣息和味道。水湄邊,是干凈柔軟的黃沙,被水浸潤過,泛出鹽堿的斑漬,淚痕一般。周圍長滿蘆葦,瓔珞般的穗子在風里搖擺,葦花四散飄揚。夕陽余暉,牽著細密的光線,穿過蘆葦蕩,將金箔一樣的光點灑向水面,與粼粼水融合在一起,如夢似幻。天鵝飛起,白鷺落下,歸家的路已被暮色占領,但羽毛和翅膀依然明亮,暈染著落霞的色彩。
我的四周黃沙漫漫,死亡般的孤獨無處不在,而這一刻,突然感到居延海就像一顆碩大的冰藍露珠,懸掛在靈魂深處,濕婉,細膩,深情脈脈。
落日下,萬靈歸于闃寂,海水漸趨深沉。從我站立的角度望過去,波心里還有云朵的倒影,緩緩游弋著,若隱若現(xiàn),似真似幻,以默言的夢境告白天空。我腳下長著零星的荒草,草間是螞蟻的家園,洞穴密布,營壘森嚴。我發(fā)現(xiàn)一群蟻正抬著蟻王的尸骸,整齊有序地向它們的墓地走去。生靈都有人類不可知曉的秘密,也許在居延海尚未出現(xiàn)的年代,螞蟻就在此地創(chuàng)建了王國,它們加冕與喪葬的禮儀持續(xù)了億萬斯年。也許,在它們的記憶中,這浩渺遼闊的水域,只不過是前塵往事里的一滴淚水。
書上說,居延海是黑河的閭尾湖。閭尾一詞出自《莊子》,意思是水的歸宿。那個洞悉天地宇宙奧秘的哲人,認為萬物運動的最高境界為自由自在,逍遙快樂。黑河古稱弱水,發(fā)源于祁連山,流經青海、張掖、酒泉,最后穿過茫茫戈壁荒原,魂歸漠野,最后匯聚成波光瀲滟的巨大海子。《山海經》記載,昆侖山由弱水之淵環(huán)繞,山上有昆侖懸圃,西王母就住在那里。中國許多神話傳說都與此水有關。最叫人產生聯(lián)想的還是《紅樓夢》中,賈寶玉對林黛玉的那句愛情表白:任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一條滄桑孤獨的內陸河與愛情扯上瓜葛,至少也增添了幾分婉約柔美的色調。
這是我第二次沿著黑河西行,乘車旅游,走走停停,或拜訪古跡,或體驗風光,時間安排寬裕,心情自然閑適輕松。記得第一次去額濟納看金秋胡楊,行色匆匆,一路上似乎見到除了戈壁荒漠,就是黃沙白草,所有的風景都籠罩著蠻荒蒼涼的色彩。那時候,正是青春在身,滿腦子都浮現(xiàn)著邊塞詩的意象:大漠,孤煙,長河,落日,西風里的流云,流云下的古堡和驛站。跟幾個寫詩的朋友坐在黑河岸邊的古渡上,看著太陽穿過胡楊林,慢慢接近西地平線。紛紛揚揚的胡楊葉片,從樹冠飄落,帶著橙黃或暗紅的夢幻,覆蓋了我們的惆悵和憂傷……
三十年過去,詩化的激情逐漸淡化,人間煙火堆積于心,有了一種滄桑厚重。向西遠去的頭一個夜晚,我伏案讀帕斯的太陽石。帕斯自稱這是時間之詩。他受阿茲特克太陽歷史影響,認為有兩種不同的時間,一種是線性的,即充滿暴力的人類歷史;另一種是非線性的,恰似宗教的神圣節(jié)日,已被人類丟失。古代墨西哥人的金星歷讓帕斯著迷:金星既是啟明星,又是長庚星,具有死亡和復活雙重品格;它每隔584 天在同一位置與太陽重合。帕斯想探尋像金星那樣切入宇宙時空的永恒瞬間,《太陽石》因而采用584 行,首尾6行重復,構成環(huán)形結構。讀完帕斯的長詩,我感到那些玄奧的意象背后還有看不見的東西,旋轉的時空隱含神秘的內聚力。
2019 年秋日的某個傍晚,我從金塔縣城出來,走進了黑河東岸的一片荒原。這里方圓幾十里沒有村莊,不見人煙。視野里除了石頭和蓬蒿,只有空空蕩蕩的黃昏暗影。黑河無聲無息,仿佛應了某個神靈的召喚,流向地老天荒的遠方。我斜躺在岸邊的一個沙丘上,抽煙或小憩,讓身體像沙蜴一樣舒展開,盡情享受漠風的吹拂。也就在那個時刻,我看見了帕斯詩中的金星。她懸浮在祁連山偏西的天空上,飽滿燦爛,在山嵐的映襯下,周圍氤氳了一個淡藍的光圈,現(xiàn)出幾分孤絕的神秘。如果按照帕斯的說法,沿著金星閃亮的光線前行,就可抵達時光永恒的彼岸。我的猜想是,也許金星能讓時間倒流,使消逝的歷史現(xiàn)場重新回到當下,周秦漢唐,宋元明清紛紛復活,穿過我們好奇的眼瞳……大地之上,天穹之下,大漠戈壁空空蕩蕩,死寂如夐古的夢魘。
事實上,我在金星微光斜照的地方,只發(fā)現(xiàn)了一處烽燧。當?shù)嘏笥迅嬖V我,那個烽燧就是漢代的肩水金關遺址。漢武帝時代,設置河西四郡,為了鞏固邊陲,連通西域,在黑河沿岸修筑了許多關城驛站,而肩水金關便是其中之一。闕樓早已坍塌,甕城不見蹤影,歌榭舞臺被雨打風吹落去,就連烽燧上的黃土也年復一年剝蝕消減,成為光陰的記憶。曾經滯留于此的戍邊將士、商賈駝隊、詩朋詞侶、墨客高僧……都凋零于無邊的曠野之中,葬于風,埋于雪,然后消弭、飄散于虛空。
在戈壁,死亡是焦黑的,更悠久的死亡是白熾的,茫茫白砂,是時間風化的尸骨。許多世代過去了,許多地質年代已經迷茫。烽火依舊。死亡能夠禁止一切,已知,未知,歷史以及未來,記憶或者猜想,禁止鳥群從上空飛過,禁止月色暗示潮水……烽火臺獨立西風,但不僅僅指向天空。它傷痕累累,一年里總要將身上的灰塵放棄一次,如同一棵樹,根系向下,令枝蔓擁有向上的力與渴望。而那最后一片葉子,最后一朵花,在飄落之前正努力寫下對時間的告白。
而在時間幽深寒涼的黑夜里,有一種神秘的物質深埋地下,它們是書寫著漢字的簡易木牘,宛若燦爛的星斗在另一個遙遠的時空里靜悄悄旋轉,等待著與人類相遇。
1930 年,由中國、瑞典的科學家組成的西北科學考察團,在肩水金關的烽燧周圍出土漢簡近1 千枚。1973 年甘肅省居延考古隊又掘漢簡1 萬多枚。內蒙古居延地區(qū)一次性發(fā)掘出土如此多漢簡,這在當時轟動了整個世界,人們把居延漢簡與殷墟甲骨、敦煌遺書、故宮內閣大庫檔案并稱為20 世紀中國文化史上的四大發(fā)現(xiàn)。居延漢簡,內容均為兩漢張掖郡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轄區(qū)內的屯戍文字,它出自當時中下屬士吏之手,非為藝術而書,是一種本色的呈現(xiàn)。試想在戎馬倥傯的年代里,駐邊扎寨的將士們顯然不可能像書齋里的文人雅士,悠閑地推敲著一筆一畫,一切皆隨意瀟灑。于是我們看到居延漢簡的輕松自如,恣意率真,信手寫來,其飛動的線條和縱橫開張的間架造型都是毫不掩飾的赤裸裸的感情流露。當然,軍卒書寫時也許還不知書法是何物,更談不上士大夫階層濃郁的文化氣息。但他們無心拈來的書跡卻正是書家日夜追求的童年純真。漢之拙樸自然,漢之雄渾狂野,都蘊含在文字書寫的點橫撇捺之中,凸顯了那個時代的精神氣象。
河漢橫亙天穹,星月的光輝默默映照人間。從酒泉到額濟納,我發(fā)現(xiàn)黑河兩岸的秦關漢城或沉沒,或傾圯,只剩下孤獨死寂的廢墟。廢墟和古渡的傍晚,羊群正穿過碎石的河道,塵土飛揚,去向不明。玄奘渡河西行,鳩摩羅什去往中土,都要穿越此地的西風流云、星光月色,如今一切都成煙云,空留黑河浩大的水勢,如誦經聲。居延海邊的黑水城已成千年遺址。岸邊的佛塔依舊守護著神靈漸弱的呼吸。我不知從祁連山黑河源頭到居延海,從此岸到彼岸,已有多少故事像河水遠遠流逝。今夜,在這遠離城市的荒涼地方,在這西地平線上的一個叫居延海的藍色水泊岸上,我抬起頭來眺望星空:河漢無聲,鳥翼稀薄,云朵向群星瘋狂地生長,風吹著空曠的夜也吹著我,風吹著未來也吹著過去。我成為某個人,某間點著油燈的陋室,而這陋室冰涼的屋頂被群星的億萬只腳踩成祭壇,我像一個領取圣餐的孩子放大了膽子,住進了星光的呼吸里……
天馬飛過山河大地
過敦煌,朋友們都去了莫高窟。
二千多年的朝圣路,依舊人來車往,懸壁上的佛端坐西風流云之間,吸引著凡塵目光。但人心已經不古,物質至上的時代,站立仰望或伏身跪拜,靈魂再也無法抵達三危山頂?shù)默摤摪籽?/p>
我踽踽獨行,來到了一處水洼地。
當?shù)厝税堰@里稱作壽昌水庫,其實它就是一個海子,古稱渥洼池,水淺,瀾靜,魚翔,鳥飛,幽藍純凈得像一個夢境。幾千年來,那個夢境里泊著天光云影,還有蘆花與紅葉,還有上古時遺留的星月呼吸……
岸上長滿了草,野花斟滿霜花,搖一下滴落露珠,再搖一下便招來白翅黑斑的蝴蝶,它們和周圍的童山禿嶺構成強烈對比。秋天里,生與死,繁盛與衰敗,在此地都有另類的美學意義。
坐在一棵胡楊樹下面,頭頂上罩著金黃的樹冠,身邊翻飛著金黃的落葉,腳下跳躍著金黃的夕暉光斑,我恍惚置身于一座金黃的神殿之中,心緒頃刻平靜了下來。對胡楊而言,時間即是虛空,她不在乎生老病死,與沙漠戈壁對晤千年,一旦衰朽,依然獨立西風,將錚錚鐵骨指向蒼穹,向人世傳達神的隱語。
暮色降臨。有牧人趕著幾匹駱駝走過渥洼池,弦月下,霧嵐與月色交融,掩映著駱駝高大的身軀,剪影般若隱若現(xiàn)。遠處的鳴沙山與月牙泉已陷入暮靄,更遠處的祁連雪峰只剩下鋼藍的輪廓,頭顱深埋星空,孤獨如我。
突然想起暴利長,那個活在歷史傳說中的河南人。
地方史志上說,漢武帝元狩三年,生活在河南新野縣的小吏暴利長,因犯罪罹刑,被當?shù)毓俑滠姲l(fā)配至西北邊陲敦煌,到渥洼池畔開荒屯田。那些日子,暴利長時常去水邊放馬,他發(fā)現(xiàn)來自祁連山上的一群野馬,每天黃昏都飛奔到渥洼池邊飲水。一天,他在野馬群中看見了一匹與眾不同的駿馬。這匹馬鬃毛披拂,骨骼挺拔,棗紅毛色,跑起來四蹄颯踏生風,周身閃耀著光芒,宛如一團燃燒的火焰。
暴利長為了捕獲這匹野馬,就用泥土捏塑了一個假人,讓它手持馬籠頭和韁繩立在水旁。時間久了,野馬對假人習以為常,失去了警惕,暴利長便代替假人,親自手持套索立于水旁,趁馬不備時將其套住。他聞知漢武帝酷愛良驥,便把此馬說得神乎其神,并詭稱它是從渥洼池水中躍出的馬,后來托人將馬獻給了武帝。漢武帝本是個十分愛馬的人,之前,曾通過祭司占卜,在卦辭中得到了“天馬當從西北來”的神諭,于是派人到西域烏孫國去探尋天馬。這次,當聽說眼前的這匹馬從池水中躍出,且能騰云駕霧,日行千里,自然喜出望外,認定此馬便是太一天神所賜,立刻命眾臣齊聚皇宮,稽首拜賀,并展開木簡,親筆寫下了《天馬歌》,歌曰:
太一貢兮天馬下。
沾赤汗兮沫流赭。
騁容與兮跇萬里。
今安匹兮龍為友。
讀《漢書·武帝紀》,有這樣的記載,“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班固是嚴謹?shù)氖穼W家,他生活在東漢,彼時,武帝的茂陵早長出白草黃花,他只根據前人的說法,小心翼翼寫下了一句話,記下了馬出渥洼池的具體時間。至于那個暴利長以后去了何方,落腳哪里,我翻遍所有史書,均語焉不詳,找不到任何蛛絲馬跡。史書闕如,倒是民間故事一直沒有泯滅,傳說武帝自得到天馬后,龍顏大悅,降旨赦免了暴利長的罪過,并賜給他養(yǎng)老的俸祿,不久,他便騎著一匹白駱駝離開敦煌,東歸洛陽。
暴利長做夢也沒料到,由自己編織的一個美麗謊言會改變后半生命運,使他重回桑梓,安度晚年。更不會料到,他墾荒牧馬的地方,那個幽藍清澈的渥洼池,會走進煌煌史冊,千百年來被文人騷客反復敘述、詠唱,成為充滿神秘色彩的天馬故鄉(xiāng)。
沒有風,渥洼池的四周一片闃寂。黃昏的月牙如藍菊花瓣,漂浮在水面上。歷史的天空下,時間就是一個水滴,一片水泊,從不同角度折射著時空歲月,如夢似幻,迷離渺茫。我恍惚走進了博爾赫斯筆下的交叉小徑的花園,于時間迷宮里盤桓、逗留,眼前忽而是明月青天、霜冷長河,忽而是西風殘照、漢家陵闕;乍見烽火狼煙、鳴鏑啾啾的戰(zhàn)場,又聞絲綢之路上幽怨的琵琶羌笛……
我相信,在狂野拙樸、胸襟浩蕩的漢朝,那一匹凌空翱翔的天馬,就是一個時代的隱喻。
事實上,馬出渥洼的故事流傳開來之時,漢朝與匈奴的戰(zhàn)爭已經結束,那個逐水而居、彎弓射雕的游牧民族,在留下一曲“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繁息”的一曲悲歌后,便消失在茫茫朔漠,從此音訊杳無,去向不明。之后,漢武帝設置河西四郡,長安西望,是武威、張掖、酒泉和敦煌,四郡若珍珠般串聯(lián)在一起。
我們可以想象一個魔幻的電影場景:天空湛藍,白云朵朵,一匹馬展開寬大的羽翼,迎著萬里長風,自由自在飄弋、翱翔、騰躍……馬嘶嘶而鳴,叫聲震動山河大地。馬的翅膀下掠過西北的雪山、荒原、沙漠、綠洲,以及廢墟、老城、石窟、寺廟、村莊、漢墓群、古戰(zhàn)場。那時候,馬的眼睛深沉如夜,所有的夢幻往事和夐古歲月都在那海子般的瞳孔里沉淀,并發(fā)出光芒。在遼闊浩瀚的蒼穹之上,馬的視野里鋪展開血管似的驛道,那上面點綴著絲綢、茶葉、琥珀、玳瑁、香料、佛經、儒典,還有商賈和駝隊,詩人與僧侶……這就是絲綢之路,一條連接了東西方物質、財富、精神、信仰的文明大通道。蠶以心血結繭,吐出雪白的絲,然后再由人織出絲綢,它本來是一種生活物品,柔軟,美艷,色澤斑斕,穿著于身,便可顯出人的身份地位,代表了優(yōu)雅高貴,精致富麗的江南生活方式。然而,當十九世紀的李希霍芬把這種商品寫進《絲綢之路》后,它便從物質層面轉化為一種精神與氣象,成了拓荒、西進、光榮、犧牲、開放和胸襟的代名詞。
天馬行空,在文人筆下如同一個雄奇意象。罡風浩蕩、壯懷激烈的時代,突然閃現(xiàn)于夢境,于是就有了天馬的影子,它帶有神性和靈氣,或者說就是一首大氣磅礴的邊塞詩。有漢一代,武帝劉徹雄才大略,眼界闊大,他的胸襟與氣度,給整個社會帶來了一種積極進取的時代精神。借用當時文人的表述,這種時代精神體現(xiàn)出“奮迅”“騁馳”“奔揚”“馳騖”的節(jié)奏特征。漢武帝執(zhí)政,用事四夷,以武力拓邊,尚武之風益起,影響到社會生活節(jié)奏轉而更為快速、驟急。據《史記·貨殖列傳》和《漢書·東方朔傳》載,漢代宮廷盛行賽馬,而漢武帝極為熱衷這項游戲,經常下旨讓百官舉行“馳逐”活動。在出土的漢代畫像磚和陶俑中,有不少賽馬的形象:駿馬飛馳,互相追逐,騎手則抖韁揚鞭,躬身伏于馬背,做出與馬飛行的動作。《淮南子·說林》稱作“追速致遠”的這種追求高速度的競技形式,為社會上下普遍喜好。漢武帝同時喜歡騎馬狩獵,親手射殺黑熊和野豬,他挽弓縱馬,追逐野獸的放獷行為,也可以看作相關社會風尚的表現(xiàn)。《漢書·陳湯傳》記述西漢甘延壽、陳湯經營西域,克敵立功,有“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壯語。強烈的國家意識,應當是在漢武帝發(fā)動大規(guī)模的對外戰(zhàn)爭時開始形成的,而這種意識的心理基礎,是民族自尊心與自豪感。
雙翼凌空、扶搖而上霄壤的天馬,象征了一個時代的青春力量。衛(wèi)青、霍去病、李廣、趙破奴、張騫……一長串載入青史的名字,都有著天馬的品性與精神,他們智慧、勇毅、蓬勃、狂狷、豪邁,舍家別土,西行遠征。為了大漢的社稷江山,敢于校場點兵,長河飲馬,血染黃沙。黃鐘大呂的漢朝,主旋律昂揚向上,陽剛之氣充塞天宇,龍馬精神元氣淋漓,不聞靡靡之音,不見頹廢之態(tài),每一個熱血男兒都有機會張揚自己的才情與魄力,奔赴西部蒼茫大地,或縱騎馳騁于烽火狼煙之中,或行走于駝隊商旅之間。那個時代,青春擁抱著雪山荒原,弱水河畔,蘆花飛揚,西部的長河落日間,一直回蕩著青春少年的英雄浩歌。
多年前,我旅行至武威,在涼州博物館見到了“馬踏飛燕”的青銅雕塑。據當?shù)嘏笥阎v,這件文物出土于雷臺漢墓,是一個張姓將軍的陪葬品。那個早晨,陽光從巨大的玻璃窗上照進來,落到了銅奔馬身上,光與影或明或暗,游弋變幻,銅奔馬仿佛有了微微動感。我仔細觀察,發(fā)現(xiàn)這匹馬軀干壯實飽滿,四肢修長,勻稱輕捷,三蹄騰空、飛馳向前,一蹄踩踏著飛燕翅膀,而燕子吃驚地回過頭來張望,燕子與奔馬同時顯出一種凌空飛翔的姿勢,動作輕盈、迅捷,力量和速度,激情與夢幻,凝固于青銅造型之中,大氣磅礴,美輪美奐。
朋友告訴我,雷臺漢墓出土了大量陶俑,其中有一個馬俑胸前有銘文記載:“守張掖長張君”之墓,而從墓葬發(fā)現(xiàn)的銀制印章,由于深埋地下,印文銹蝕剝落,漫漶不清,僅可隱約辨識“將軍章”幾個字,專家、學者各述己見,聚訟紛云,有人認為是破羌將軍、武威太守張江;有人認為是度遼將軍、護匈奴中郎將、武威太守張奐;也有人認為是張奐的小兒子武威太守張猛;還有人提出是宣威侯、破羌將軍張繡或漢陽太守張貢。近年又出現(xiàn)新的觀點,說長眠于此的很可能是前涼國王張駿以及中國道教祖師張道陵。
其實,在我看來,墓主人為誰已不重要,二千多年歲月,陵闕坍塌,棺槨腐朽,肉體早化作一抔塵埃,即使考證出結果,其姓名稱謂也不過是冰涼的符號而已。我想到的是,張姓將軍駐守武威,戎馬一生,當肉身隕落之后,身邊的故舊部下定然為他舉行盛大葬禮,金銀玉石、綾羅綢緞并不稀罕,最要緊的是陪葬一匹青銅寶馬,讓它背負將軍的靈魂,在來生繼續(xù)飛行于浩瀚藍天……
渥洼池的天馬展翅飛翔,從大漢飛到了盛唐。
唐開盛世,駿馬立下了赫赫之功。在統(tǒng)一國家的戰(zhàn)爭中,太宗李世民親自出戰(zhàn),陷陣摧敵,追亡逐北,他先后參加了六次戰(zhàn)役,騎乘過六匹戰(zhàn)馬,它們的名字分別是:颯露紫、卷毛騧、白蹄烏、特勒驃、青騅和什伐赤。李世民登基后,開始為自己修建陵園,于貞觀十年下詔,將六匹馬的英姿琢刻于石屏之上,鑲嵌在昭陵北闕。同時親題贊辭,記載馬名、膚色、乘用時間、所負箭瘡等等。從此后,昭陵六駿聞名天下。
唐朝定鼎,天下一統(tǒng)。貞觀年間,唐太宗重新打通了絲綢之路,東西方文明交流融合達到了頂峰。當時有西域二十多國的君主及其代表集聚長安,奉太宗為“天可汗”。從此,由長安向西,可自由橫穿整個歐亞大陸,直驅地中海東岸的安都奧克,全長約七千多公里的驛路古道,商旅逶迆,馬幫駱隊絡繹不絕。作為絲綢之路的東方終點,七至八世紀的長安成了當時世界上最繁榮的城市,被稱為“世界性首都”。如同漢武帝一樣,唐太宗也酷愛良馬,他雖然沒有把“昭陵六駿”命名為天馬,但那些馬同樣具有天馬的氣質和精神。李白在他的《天馬歌》中寫道:
天馬來出月支窟,背為虎文龍翼骨。
嘶青云,振綠發(fā),蘭筋權奇走滅沒。
騰昆侖,歷西極,四足無一蹶……
詩人筆下,這匹長著虎文龍骨、綠鬢飄揚的天馬,所指即是蓬勃的時代氣象:博大、雄渾、深遠、超逸,充沛的活力、創(chuàng)造的愉悅、嶄新的體驗;詩人通過意象的運用、意境的呈現(xiàn),性情和聲色的結合,而形成新的美感。它涵蓋了盛唐文人在文學中表現(xiàn)出的開闊的眼界,自由活躍的思想,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激奮昂揚的氣概,展現(xiàn)了一個強大民族鼎盛時代的整體精神風貌。
弦月西沉,夜色彌漫開來,渥洼池水氣氤氳,一片迷濛渾沌。我抬起頭,看見天狼星座剛剛從西地平線升起。
敦煌已是萬家燈火,我該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