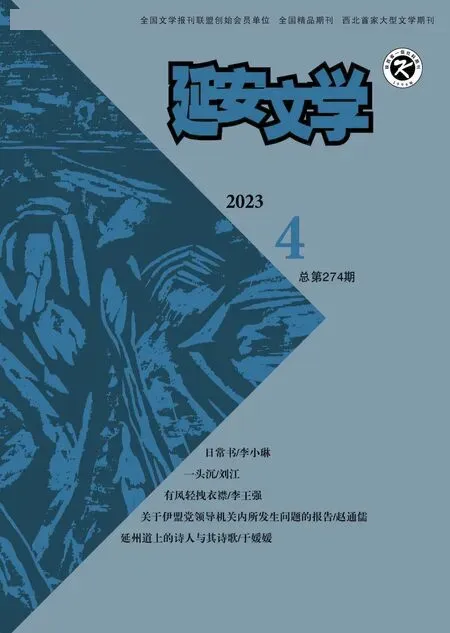我們村的北京知青
曠 野
我們村叫十甲村,座落于陜北延川縣青平川。
2009 年,一大批北京知青組團回到了這里,以此紀念他們插隊四十周年。
瞧吧,陸征、孫秋來、戴允林、周萱、曾偉、胡群海、楊西、喬淑秀、姜向陽、呂樹恒、劉德森……一個個熟悉的名字,一張張熟悉又陌生的面孔。
當年意氣風發戰天斗地的青年們,在歲月的洗禮下,現在都已變成了老人。但是他們的身子骨依舊像這里的大山一樣堅挺,渾濁的眼神雖然已不那么清澈明亮,但依舊堅毅。
拂去歲月的面紗,他們也認出了村里的老社員:張信、張明、劉玉信、王樹業……當得知村民們為了歡迎他們,在公路兩邊佇立了兩個多小時后,知青們熱淚盈眶,他們和老社員們緊緊地擁抱在一起。
他們重走村里的條條巷道,重登周圍的山山峁峁,從深井中打一桶井水,用半個葫蘆做的瓢舀一瓢甘泉狠狠地喝幾口,仿佛嬰兒重新回到母親的懷抱,重溫著母親甘甜的乳汁。
1969 年他們來的時候,還是十六七歲的小青年。村民們親切地稱他們為學生“心兒”(延川方言,意為孩子)。
大隊社員趕著驢拉車,從八九公里之外的關莊公社接回來一批北京學生,共32人,分配到我們大隊的4 個生產隊,每個生產隊8 名知青。從此,這些首都青年,過上了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耕生活。
記得我大約三四歲的時候,有一天一位講“洋話”的阿姨來到我家,拿出一套領子上帶紅領章的小軍裝,與我媽媽一起給我穿上,還給了我一把牛奶糖。我把奶糖放進嘴里,吧嗒著嘴,美滋滋地嚼起來。阿姨把我抱起來,親了一口,夸獎我穿上小軍裝像個小解放軍。媽媽說這套小軍裝是走了遠路的,是曾偉阿姨回北京探親時買的。曾阿姨是北京學生,比我媽媽小兩三歲吧,她們關系特別好。由于我爸在關莊供銷社工作,平時不在家,曾阿姨就經常來我家給媽媽作伴。
我們村名氣最大的知青要數北大校長陸平的兒子陸征,他是四隊的,是我們村的知青頭。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率領一批知青,提了一桶汽油,登上娘娘山,一把火將娘娘廟給燒了,引起了轟動。當時“破四舊”運動風起云涌,這座廟自然成了封建迷信的象征。不過,現在娘娘廟早已修葺一新,每年的廟會成了遠近鄉鄰朝拜的地方。
陸征和二隊的姜向陽學歷最高,是高中生,其余都是初中生。
姜向陽在知青里“受苦”(陜北人把干農活叫受苦)最能行,干農活絲毫不比社員們差,深得社員們的喜愛和肯定。
二隊的李玉純是著名的長跑健將,每天都要從我們村和鄰村之間跑個往返,風雨無阻,冬練三九,夏練三伏,成為鄉村公路上一道別致的風景。
二隊的戴允林是女知青,很能吃苦,擔糞、開拖拉機樣樣農活都能拿得起,竟然還學會了很多男知青都學不會的牛犁地。犁地翻起的土疙瘩得打碎才能播種。戴允林個子高,一般的打糞拐子(一種T形木制農具)手把太短,根本用不成,總要把腰彎得很低很低。村里木匠給她特制了一個長把的,用起來才得心應手。她打起土疙瘩來,真是“只見黃塵不見人”,經常趕著前面犁地的人一路小跑。
四隊的胡群山、胡群海是親兄弟。兄弟倆最擅長挑麥子,在崎嶇的山路上挑著沉重的麥捆行走,時間不長就把肩膀壓爛了,兄弟倆咬著牙,堅持挑,直到爛了的皮肉長好,這讓整天受苦的村人們自嘆不如,豎起大拇指夸贊:“兩個灰漢娃娃!”。
河里的低哨蓋是個沖積而成的深水潭,兩岸全是巨型青石,可以站在青石上跳水,是我們村的天然游泳池兼澡堂子,但只是男人們的天堂,與女人無關。每到夏天中午,勞累的男人們很多都泡在低哨蓋里,有的戲水,有的洗澡。男知青們自然成了主角,三隊的王虎、李樹恒潛水誰也比不了,他倆在少年游泳隊學過幾年,每次潛水都要爭個高下。
從1972 年開始,知青們陸陸續續通過招工、招干、升學、返城等途徑離開了我們村。
經過幾年戰天斗地的農民生活,知青們認識了農村,認識了生活的艱辛,認識到每一粒糧食都來之不易,學會了耕作、播種和收獲農作物,從初來乍到的韭麥不分到后來的行家里手,這本身就是一種很了不起的收獲。
陸征招工到寶雞電力機車車輛段,做了機修電工,技術非常好。如果對口調動的話,通過父親的關系回北京肯定不成問題。可他父親說,他在鐵路系統8 年,從沒有給自己辦過任何私事,現在也不能這么辦。最后,陸征通過自己的努力以及工作需要,先調到石家莊電機段工作了3 年,最后又找了個對調的機會,才回到北京。
曾偉先是招工到延長油礦供電車間,后來才回到了北京。戴允林和周萱是走得最晚的兩個女知青。
周萱當時是我們大隊的小學教師。我上二年級時,周老師是我們的班主任兼語文教師,讓我們跟她學普通話,要求讀課文一定要用普通話。我們這些“心兒”從7 歲上學起,就按照周老師的要求刷牙了,這在偏遠的陜北農村真是不敢想象。
村里很多家庭隔一段時間就會請老師吃頓飯,我們家也請過幾次。記得有一次要請老師吃午飯,去周老師的辦公室兼宿舍請她時,她正躺在放在炕上的床上午休。我當時想,好好的炕不睡,非要把床放到炕上睡,怎么這么怪呢。長大后慢慢理解了,從小在北京長大的她們,可能確實睡不慣陜北的土炕。
我們村每年正月都要唱戲,那可是周老師最拿手的,記得最清楚的是她導演、主演的革命樣板戲《杜鵑山》,吸引來周圍好幾個大隊的社員來看熱鬧。那真是人山人海,把戲臺圍得水泄不通。我們小孩子個子低,大人們索性把我們架在脖子上。周老師扮演的是柯湘,男教師劉成員扮演雷剛,在永坪中學讀書的我二爸張永海則扮演國民黨軍官。那時候我們小孩子最想看我二爸,穿一套軍官服,拿著道具手槍。我們經常搶過他的軍官帽歪戴著,一只腳踩在凳子上,手槍舉得高高的,拿腔拿調地學他說的臺詞:“團座有令,帶共黨!”
有時候晚上也演戲,由于那時還沒有拉上電燈,社員們發明了一種晚上照明的方法,就是在戲臺的兩端分別栽根粗木樁,拴上粗鐵絲,做三五個棉花團,按照一定間隔掛在鐵絲上,蘸上柴油,開始演戲的時候,把幾個棉花燈點上,頓時燈火通明。等柴油快燃燒完的時候,負責蘸柴油的社員端起盛有柴油的臉盆讓棉花團完全浸泡進來,浸泡好了,端著臉盆離開戲臺,不一會棉花團就又燃燒得很旺,恢復了明亮。
這就是我們村知青時代的春節晚會,周萱老師儼然成為我們青平川遠近聞名的“楊春霞”,在社員們心目中,絲毫不亞于現在的明星大腕。她后來回憶當年大搞文藝活動時說:“除了愛好,也還是有點私心的。那時每晚都學大寨修梯田,我搞文藝,就不用參加繁重的體力勞動了。”
1975 年,周老師也返城了,不過返的不是魂牽夢縈的北京城,而是另外一座城市——飛機城閻良,成了飛機制造廠的一名職工,直至退休。
戴允林則于1976 年直接返回北京,在某科研單位辛勤耕耘了幾十年。她在長達七年的插隊生涯中,與我們村學校的馮校長結下了很深的姐妹情,至今仍然保持聯系。
男知青走得最遲的是劉德森。我們都上三年級了,他還總在我們學校里出現,因為他住在學校旁邊的窯洞里。直到1977年,他才招了工,成了銅川礦務局的一名工人。
知青們把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華留在了這里,同時也吸收了這片土地的養分。他們把陜北當做自己的第二故鄉,盡力幫助著故鄉的親人,尤其是孫秋來,幫助的人最多。
孫秋來先是招工到子長縣郵電局,后來回了北京,辦了一個養殖場,靠養鴨子致了富。但他一刻也沒有忘記故鄉的親人們,資助很多村里的孩子上了大學。他還吸收村里十幾個后生到他的養殖基地工作,不僅讓這些祖祖輩輩在土里刨食的泥腿子到北京見了世面,同時還能取得一定的經濟收入。孫秋來還幫扶了村里創業的村民。他得知村民劉羅羅正在為辦養豬場缺資金而發愁時,二話沒說,立馬匯來6萬元。到目前為止,他前前后后資助給我們村的資金接近20 萬元。2017 年,孫秋來擔任執行董事的集團投資6000 萬元,在十甲村建起了鴨子現代化養殖、加工基地,建成了陜北第一座北京烤鴨爐。他說:“我只想低調地做點有意義的事,只想在晚年為養了我們八年,手把手教會我們生活,教會我們做人的陜北人民做點事……”
這次重回故地十甲村,知青們終于了卻了一樁心愿,回延安、回延川、回十甲,四十年漫長的歲月,山沒變,水沒變,鄉音沒變,鄉情更沒變。
幾天的再聚很快結束了,當知青們再一次離別時,是那樣地依依不舍。有人說:“咱們每人帶一袋泥土回去放在花盆養花吧,這樣就能天天和故鄉在一起了。”這個提議多好啊,大家不由分說找來袋子,裝了泥土。
知青們載著濃濃的鄉情和滿袋的泥土告別了,鄉親們和歡迎他們回來時一樣,簇擁在公路上不停地揮手,依依不舍。知青們的眼睛再一次濕潤了。請等待吧,這片深情的土地,這些深情的人們,我們還會再回來的,因為這是我們的第二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