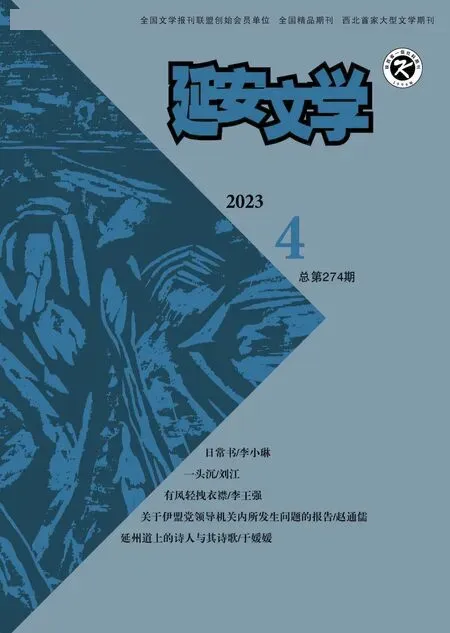幾回魂夢繞高堂
席 軍
父親是個文化人
故鄉有一口泉,清澈甘冽。它匆匆忙忙奔跑大約10 華里,匯入流經安塞縣城的延河。
1948 年3 月,宜川戰役結束后不久的一個下午,一位將領與他的衛士,騎馬路過安塞縣真武洞鄉廟灣村,突然被一陣隱隱約約的誦書聲所吸引。
這位首長側耳細聽,原來是有人大聲背誦王勃的《滕王閣序》。他頗覺驚奇,便循聲覓去,幾拐幾彎看到泉邊有個口中念念有詞的少年。
其時,延安大批干部隨全國解放走向各地,文化人奇缺。普通老百姓大多不識幾個字,更別說能背誦《滕王閣序》了。他好奇地向少年走去,兩人就攀談起來。
通過聊天,首長知道少年虛歲十五,名叫席保儒,小學畢業本來應該到延安上中學,但因為戰爭,在家里休學一年多了。這位首長走后不久,鄉長便來到了廟灣村,要讓這位15 歲的少年到鄉政府當文書。父親席保儒當年就這樣參加了工作。
兩年后,父親又被調到安塞縣委宣傳部當干事。后來,上級給縣委宣傳部配了一臺電子管收音機。那收音機如同現在的微波爐大小,能說能唱,在當時是個稀罕物件。每天下午下班后,縣委的干部們便聚集到父親辦公的窯洞里來聽收音機。附近的群眾知曉后,也跑來聽。那時的安塞縣委也就是幾排窯洞,有圍墻但沒有門衛,群眾可以隨意進出。后來,當來聽收音機的人在窯洞里擠不下的時候,父親便小心翼翼地把收音機從窯洞里抱出來放在門外一張桌子上讓大家聽。從收音機里大家知道抗美援朝我們又打勝仗了,社會主義的蘇聯人人都能吃上面包。有人聽了收音機后還嘖嘖嘆道:“收音機唱得比咱們縣劇團唱得好多了!”
母親后來曾回憶說:當年別人給她介紹對象,見面后得知男方是縣委管收音機的干部,她就毫不猶豫地答應啦。
那時候父親被大家看作文化人。縣委的好多材料,父親都參與起草。當時的《延安報》上,也不時登載父親寫的關于安塞縣的通訊報道。甚至過年時間,縣委大門上的對聯,也往往是由父親來書寫。
爺爺曾經拿著載有父親文章的報紙,在鄉親們面前炫耀,村里大多數人當然是贊嘆不已。但也有人說,現在公家人實行的是供給制,在縣政府工作掙不了幾個錢,那么一個大后生,還不如在家里種地收入多。
記得上小學的時候,有一次在放學的路上,我和幾個小伙伴發生了爭論:毛主席到底是住在北京還是住在中央?大家誰也說服不了誰。第二天我拿出一份《延安報》,指著一篇文章說,這篇文章是我爸寫的。我爸說毛主席住在北京。于是大家全服了。
還有一次,晚飯后在院子里我拿著一本小人書給小伙伴們講“普文公”的故事,在家里的父親突然隔窗叫我回來一下。我回家后父親笑著低聲對我說:“應該是晉文公,而不是普文公。以后看到不認識的字要養成查字典的習慣。”父親采取這樣的方式,不但糾正了我的錯誤,同時也在小伙伴們面前保留了我的“面子”。
父親也講故事。那時家里只住一孔窯洞。晚上入睡前,當我們五個孩子上炕各自鉆入被窩后,為了省油,家里早早地就熄滅了小油燈,然后父親就開始講起來:從父親緩慢的語調中,我們知道了秦漢以來長安城里的許多故事,知道了范仲淹怎么鎮守延州,知道了李自成怎么打進北京城,知道了許多毛主席在延安的故事……
父親酷愛讀書,涉獵非常廣泛。我在中學時,父親曾經給我講解過魯迅的《阿Q 正傳》、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和杜甫的“三吏三別”。父親在學習上,非常注重向別人請教。工作之余,父親經常到中學和老師們交流。有時他也像學生一樣,拿個凳子坐到教室后面聽老師講課。他還曾經把自己寫的文章,像學生一樣抄進作文本里,送去請老師批改。
在延安工作時,父親是延安大學圖書館的常客,不但去翻閱報紙雜志,而且常常借書閱讀。時間長了,他和圖書館館長牛振華成了好朋友。
我在大學時,父親曾經寫了一個“至善”的條幅送給我。父親說:“這兩個字出自《管子》,多數人理解為最崇高的善,我們可以賦予它新的意思:‘至’是達到,‘善’是完善完美。人無論做人還是做事,都應當以追求完美為目標。”
我大學畢業后,父親曾經和我一起聊過商鞅變法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以及馬恩合著的《共產黨宣言》。記得父親當時對我說:“寫《共產黨宣言》時,馬克思才30 歲,恩格斯只有28 歲。歷史進程往往是由年輕人決定的。”
記得有一次和父親討論歷史問題。父親說,中國自秦以后基本上實行的是郡縣制而不是分封制,不應該稱為封建社會;皇帝直接統治全國,應該是帝國社會(現在專家學者們也有“大秦帝國”“大唐帝國”的說法)。父親說,學歷史是為了知古鑒今。歷史研究的重點不應該是輪回往復的改朝換代,而應該是生產力的發展變化對社會發展的促進。歷史應該詳細討論商鞅變法及郡縣制和隋唐之后的科舉制對中國兩千年來政治體制的影響,應該詳細分析漢朝鹽鐵專營、宋朝王安石變法和明代“一條鞭法”對中國傳統經濟觀念的沖擊,應該重點講解中國“四大發明”及蒸汽機和電的發明等對社會進步的貢獻。父親還舉例說:“以前食鹽之所以珍貴,就是因為運輸困難。膽大的人才敢組織馬隊駝隊趕著牲口去寧夏鹽池運鹽,即使路上沒有遇到打劫,來回也往往需要半個多月,要花費多少人力、物力、精力、財力?如今汽車一天跑一趟就能拉回幾噸食鹽,價格當然便宜了,而且副食公司半個月也賣不完。原因就是社會平安了,生產力發展了嘛!”父親當年的這些說法,曾經讓我耳目一新。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作為行政干部的父親,盡管在1965 年就擔任了縣委財貿部部長,但此后職位一直在科級徘徊,直至退休。
一個人能做什么事,有時可能也是緣分。
盛世修志。上世紀80 年代,全國開始縣級“地名志”編纂工作。延安市(現寶塔區)一直找不到合適的主持人。到省里找了幾位專家,人家都推說不了解延安的具體情況,婉言謝絕。到延安大學找了幾位教授,人家以教學工作太忙為理由,禮貌推辭。三拖兩拖,到了1985 年,《延安市地名志》的編纂工作還沒有落實。
也不知是誰的推薦,有關部門找到了父親,請他主持編纂《延安市地名志》。我不知道父親是否也推辭過,但我知道這項任務最終落在了他的肩上。
那時的父親更忙碌了。開始是騎個自行車到處查資料,搞調查,往往是一大早出門到天黑才回來。進入撰寫階段后,父親常常是徹夜不眠,伏案寫作。
為了查清每一個地名的來歷,為了弄清每一段歷史沿革的細節,父親不但大量查閱有關資料,還多次到西安請教有關學者專家。陜西省圖書館和考古研究所及陜師大歷史系、地理系等單位的許多人,后來都成了父親的朋友。
功夫不負有心人。兩年后,父親終于完成了初稿。拿到省里審查,書稿很快通過。得知消息后,父親非常高興。從不喝酒的父親晚飯時舉著酒杯對我說:“我終于給咱延安完成了一件大事!”
人的一生是漫長的,雖然幾乎整天忙忙碌碌,但卻不一定能干成幾件大事。
父親雖然只有小學學歷,但我卻認為父親應該是一個文化人。學歷不等于學識,文憑不等于文化。
如果不是家鄉泉邊的那次偶遇,父親一輩子也許就是個農民。有時候,一次偶然的相遇,真的會決定人的一生啊!
我到深圳工作后,父親曾經前來和我同住。有一次我們站在大海邊,父親望著漫無邊際的大海感慨地說:“這大海里有家鄉的泉水和延河的水呀!”父親想家了!
父親晚年回到了家鄉。他在電話里對我說,家鄉貧瘠的黃土山溝已經變成了青山綠水,家鄉的泉水依然清澈甘冽。
于是,在我的夢里,父親似乎依然時常坐在泉邊的小院里和鄰人拉話,走在泉邊的小路上悠閑散步,伏在泉邊的大石上寫字讀書,站在泉邊的山峰上翹首遠望……
陜北老太太
因為退休了,因為清閑了,因為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因為想念在外地工作的子女,于是,這位老太太告別了家里天天下蛋的老母雞,告別了門前亭亭如蓋的老槐樹,告別了窗外情意綿綿的延河水,也告別了小區里戀戀不舍的老鄰居們,來到了西安,來到了北京,也來到了我所居住的深圳。
黃土高原上的陜北離大海邊的深圳太遙遠了,遙遠會使人感到陌生。老太太初到深圳時,因為語言交流障礙,很少與人交往。老太太曾經感嘆地說:我們陜北話毛主席都能聽懂,廣東人咋就解(hai)不開呢?
革命圣地延安在深圳人心目中太神圣了,神圣能使人產生親近。陜北人又居住在延安,在許多深圳人心目中如同是北京人又居住在天安門廣場附近一般。當人們知道這位老太太來自陜北延安后,紛紛以不同的方式表示友好:早上取酸奶的隊伍里會有人請她優先,傍晚散步的路上會有人向她問候;同時,有人操著生硬的廣東普通話主動來與老太太聊天。由于不很熟悉,大家都稱她“陜北老太太”。
與人聊天時,老太太很為自己的延安人身份而自豪:
“毛主席那時常常和我們延安的老百姓拉話呢……”
“毛主席在延安住過的地方離我們小區可近哩……”
這位老太太就是我的母親。本來,母親一貫為人低調,到老年后才有了這種近乎“自我炫耀”的表現,其實,這只是引以為傲的真情流露。實際上,母親的一生,大多時光都是在平凡、艱難、愁苦中度過的。
因為“陜北老太太”這個稱呼在小區太“知名”了,母親的名字反而知者甚少。其實,母親叫王義連,生于1936 年陰歷九月十三日。1952 年與父親結婚后,母親先后生育三男二女。由于父親工資很低,為了一家人的衣食住行,母親那時的艱辛想起來就令人心酸……
在深圳,母親常常與我們回憶起那難忘的過去:在上世紀60 年代困難時期,母親曾經種過地,砍過柴,挖過野菜,吃過樹皮。70 年代,為了解決家里的各種費用,母親起早貪黑去當零工,給楊家嶺的2 號工地挖過地基,給王家坪的革命紀念館砌過磚墻。到了80 年代,家里先后有四個孩子上了大學,母親又在延安地區醫院病員灶當炊事員,并把做好的飯擔到那座六層的住院大樓送給病人;那沉重的擔子壓在她的肩上,一日三餐,一餐幾趟。如此樓上樓下,樓下樓上,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一直到母親退休……
在我的記憶里,那時家里太困難了!我剛上中學時,只有十二三歲,仍要在假期和哥哥到建筑工地提泥、抱磚、拉沙子、背石頭……
在深圳,母親與我聊天時,仿佛我還是個小孩,常常不忘給我叮嚀“教育”。她所說的三句話讓我至今難忘。
母親說:“緊起鞋帶往前爬。”這句話囑咐我應該怎么工作。
母親說:“人存好心福自來。”這句話教育我應該怎么處世。
母親說:“讓人一步自己寬。”這句話告訴我應該怎么做人。
英國詩人喬治·赫伯特說:“一位好母親抵得上一百個教師。”母親沒有上過學,除了自己的名字外幾乎再不認識多少字。我常想,如果母親有點文化,也許會成為一名好老師,說不定能成為一名學識淵博的教授或學者。
在深圳,母親一口地道的陜北話,與人交流往往很不方便。于是,母親不但學習講普通話,而且盡力學習當地語言。久而久之,經常與母親接觸的那些人,逐漸明白了“圪拉拉”(縫隙)、“圪嶗嶗”(角落)、“爾格”(現在)等話的含義,而母親也能用“睇”(看)、“莫乖”(謝謝)等廣東話與當地人交流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母親應該算是一個陜北語言文化的傳播者。
在深圳,母親與當地人交往逐漸深入。一名姓樊的深圳籍香港退休法官回家鄉,登山時被一條竄出的毒蛇咬了。他掙扎著剛走下山便昏了過去,恰好被母親發現了。后來醫生說,再遲一會就沒命了。樊法官出院后宴請母親和救治人員吃飯。當服務員給每人端上一只價值500 塊的大鮑魚時,母親怎么也不吃,使得滿桌人面面相覷。母親說:“咱這一口下去吃的差不多是陜北農民幾畝地的收入,是陜北小孩幾年的學費……”后來,深圳幫延安建希望小學,樊法官知悉后,專程由香港趕回,捐出了數目不小的一筆。
在深圳,母親的眼界大為開闊,也感受到了國家近年來的巨大變化。當聽說深圳原來也很窮,甚至有些家庭夫妻兩人出門輪流穿一條褲子時,母親說:“剛解放時干部們說‘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就是共產主義,爾格早實現了。爾格的社會好!”母親說:“以前的人怕年老了沒人擔水,怕遭饑荒。爾格自來水接進家,白面豬肉盡管吃。爾格的人享福了!”母親甚至總結出了自己的“名言”:“毛主席讓老百姓有吃有穿,鄧小平讓老百姓吃好穿好。”
在深圳,母親也有不理解的。小區二巷住的小麗是搞舞蹈的,平時穿得極少。母親好心地對小麗說:“肚臍眼子都露出來了,小心著涼!”六巷住的小馬是炒股票的,天天在家上網。母親疑惑地問我說:“也沒見他上班,咋就那么多錢呢?”臨街有個“策劃公司”,母親說:“想不到出個主意,說幾句話也能掙錢賺錢。毛主席如果現在活著,他的話賣的錢不是幾十輩子也吃不完嗎?”……
在深圳,有位在大亞灣核電站工作的法國女專家,是法共黨員。她曾找到母親說,要聽革命圣地延安當年的故事。然而,當年母親還是小孩,并沒有加入到那支生氣勃勃的革命隊伍中。母親很遺憾,1948 年沒有跟部隊走。母親對漂亮的法國女專家說,那年冬天,外爺隨擔架隊走了,十三歲的她與十六歲的大姨和外婆沒日沒夜地給部隊趕做棉鞋。沒過幾天,就傳來了“宜川大捷”的消息,再不久就收復解放了延安。母親曾經認真而感慨地說:我如果那時那陣跟解放軍走了,現在說不定也能“牛”得像個老干部!
母親當年到底做了幾雙棉鞋我不知道,穿這些鞋的人到底后來成為將軍還是烈士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當年幾乎所有的陜北人都為革命做出過力所能及的貢獻。做幾雙軍棉鞋是件小事,但這與戰場馳騁流血具有同樣的意義。記得毛主席1935 年10 月率領的那支一路缺乏給養的紅軍隊伍剛到陜北時,部隊衣衫襤褸。在即將到來的冬天,沒有棉鞋穿的毛主席的腳也凍腫了。剛剛出獄的劉志丹將軍看到后,讓夫人同桂榮立馬給毛主席趕做了一雙。毛主席穿上棉鞋后曾動情地說:“陜北地方好,人更好!”
陜北人好!陜北老太太好!——我的左鄰右舍們在母親回延安后經常這么說。
林肯當選總統后說道:“我之所有,我之所能,都歸功于我慈愛的母親!”我們雖然沒有林肯那么大的成就,無法與林肯相比,但人類對母親的感情是相通的。我想說:每一位母親都是偉大的!
從一滴水珠可以認知一片大海,從一片綠葉能夠發現一個春天。在我們古老的陜北黃土高原,在革命圣地延安,生活著許多與我母親一樣的老太太。她們在這塊土地上年輕過,風光過,忙碌過,操勞過,哭過笑過,愛過恨過。陜北的每一條小路,都有過她們的足跡;陜北的每一個村落,都有過她們的身影。陜北民歌沒有她們不動聽,陜北剪紙沒有她們不生動,陜北的生活沒有她們不動情,陜北的故事沒有她們不感人。她們的酸甜苦辣,她們的喜怒哀樂,使得陜北這塊土地更加雄渾,更加瑰麗,更加蒼茫,更加壯美,更加迷人!陜北的歷史是男人們風風火火的歷史,也是女人們樸實勤勞生息繁衍的歷史。
太陽總是默默地從陜北的山頭走過,母親啊!您老人家啥時再來深圳呢?
月亮也會靜靜地在陜北的小河隱現,母親啊!您老人家能給我托個夢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