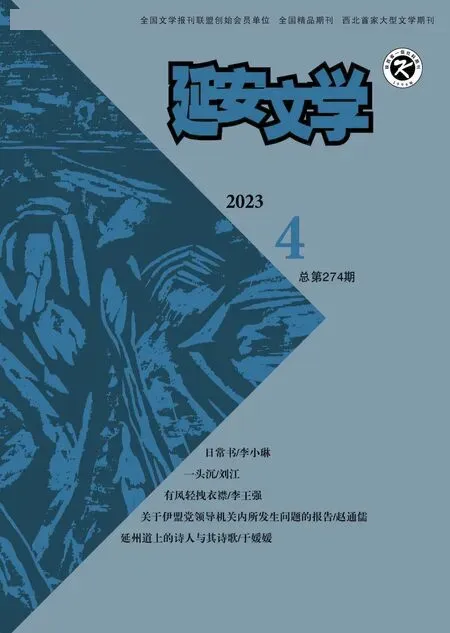那一夜
張曙光
一個破舊的門樓,上面寫著“窯上小學”四個大字,周圍半人高的土墻圍著,正中三間上房,高高的屋頂,黑瓦,四面土墻,里面青磚鋪地。村小只有一個老師,姓高,算術、語文、體育、唱歌都由高老師一人包攬。村里人都叫他高老師,以致于把他的名字都忘記了。
那個年代高老師的同齡人基本上都沒上過學堂,他只不過祖上家景好,上了幾年私塾而已。他教學生娃識字,漢語拼音都不標準,唱歌的譜子也不準確,反正也沒有人來校正。以致到現在,嚴順發的四聲都發不準。
高老師在閑暇時常愛一個人捧著一本老版本《水滸傳》看,嚴順發幾次去找老師的時候,高老師都在專注地讀它。
“老師,你讀的是什么書啊?”他好奇地伸長脖子,望著老師手上的書。
“一本很好看的書。”高老師撫摸著小順發的平頭,頭發很黑很濃,犟人犟頭發,顯得很有個性。
小順發接過那本磚頭一樣厚的書,打開,里面文字是豎排的,還是繁體字,密密麻麻的,他識不了幾個字。
“書里都講些什么啊?”他很好奇。
見小順發好奇的樣子,高老師頓了頓,拉著他坐在身邊,慢慢地講起了“水滸”的大概。書里情節像具有魔力一樣牢牢地抓住了他的心,一有空他就纏著老師講“水滸”。聽著不過癮,下學后,他就鉆在老師的小屋里,就著一盞豆油燈啃起來。但那厚磚頭一樣的繁體字書畢竟不是他一個小學生能啃得動的,常常看得一頭霧水。
于是,高老師把一些難以辨認的繁體字用鉛筆工整地標出簡體字,方便小順發閱讀。
即使這樣,小順發閱讀大部頭的《水滸傳》還是有很大的難度。他急于了解故事情節,遇到生字就順著意思讀個大概,把“水滸”讀成“水許”,把“李逵”讀成“李土”,把“鄭屠”讀成“鄭署”,把“一丈青扈三娘”讀成“巴三娘”等等。他不但愛啃,還和小伙伴分享他的讀書成果,啃完一節,就向小伙伴講述,講起“魯智深拳打鎮關西”,“鄭署(屠)”“魯提車(轄)”什么的錯別字就造出來了,一圈小伙伴聽得津津有味,個頭最高的“老干部”王大將、班長楊小貴、還有春妮等幾個女生都是他的忠實聽眾。春妮最入迷,每次聽他講“水許”,她總是睜著水靈靈的大眼睛,目不轉晴地盯著他的嘴,生怕漏掉一個字。
大嘴楊小貴見嚴順發一下課就講起水滸故事來吸引大家,他也愛聽,但見小朋友的注意力都在嚴順發的嘴上,像誰動了他的奶酪一樣,心里就有些酸溜溜的,順發正在講魯智深三拳打死鎮關西,他突然問:“魯提車(轄)是多大的官兒啊?”
“這個,這個……”順發撓撓頭發,顯然這是個不好回答的問題。
“管他是多大的官呢,反正能讓壞蛋怕的,就是個好官。”春妮幫著順發解圍。
提起春妮,嚴順發內心仍然隱隱作疼。在窯上村那個百十口人的小村里,他們從小一塊割草喂豬、打柴做飯,她那時個頭又低又瘦,扎兩條短辮兒,不愛說笑,干活卻不惜力。常見她背著一筐野草從山上回家,穿著方口布鞋,一步一步吃力地走在山道上。
楊小貴是個愛鬧的人,他在她必經的山道上弄一條蛇,等她靠近,突然竄出,大驚小怪地嚷:“好大一條蛇!”
春妮看到腳下的蛇,嚇得急往后退,背上的筐子摔在地上,豬草散落一地。
小伙伴看著春妮的狼狽樣兒,笑得前仰后合。小伙伴們玩起來,哪有不捉弄人的。誰玩的花樣多,那才有號召力。
而嚴順發覺得一點也不好笑。他默默地將春妮散落在地的筐子扶正,把豬草整理好。
“哼,裝好人。”王大將把矛頭對準嚴順發。王大將外號“老干部”,個頭比別的小伙伴高一截,身體也強壯些,只是學習不好,一上課就發呆,留了一級,學習還是趕不上,“老干部”綽號由此而來。他一直嚷嚷不上學了,對學習好、總受老師表揚的嚴順發有一種本能的不滿。
嚴順發做這一切時,也感到心虛氣短。畢竟,山里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平日里是很少和女孩子說話的,眾目睽睽之下,顯示和女孩子親昵的舉動,那就更顯得不合群兒。
“看古書,替古人流淚,自作多情。”楊小貴這時陰陽怪氣地說。
“走,我們走,”見嚴順發陷入一種孤立的難堪境地,春妮突然大方地拉他一把,彎腰背起筐子,催促猶豫不決的嚴順發,“別理他們。”
兩人在小伙伴們的嘲笑聲中,一前一后走出眾人目光可視的距離。
不知為什么,因為這件事,村里的小伙伴們見了嚴順發,表情怪怪的,都不主動和他搭話,也沒人聽他說“水許”的故事了,他厚著臉皮和別人說話,人家愛搭不理的。
當然,他知道,這是小貴存心讓他難堪,也只有小貴有這個號召力。
作為同齡人他很清楚這些小孩子們的心理。這也是楊小貴常用的一種小伎倆。以前,他也聽從小貴的安排,不和指定的小伙伴玩,大家都戲稱被孤立的那個人叫“獨立鬼”。沒想到,現在輪到自己了。
小學就要畢業了。對于王大將來說,那是一種解放,他終于可以不再受學不進去給他帶來的苦惱,他這個總是留級的“老干部”可以徹底離開這個讓他名聲掃地的鬼地方。
在高老師的引薦和努力下,嚴順發、春妮和楊小貴三個弟子進入了鎮上的中學。
鎮上離山村有幾十里的山路,每周回來一次,去時要自帶干糧。
一大早,春妮就背著書包,帶著干糧袋,蹦蹦跳跳來到順發家,熟練地推開那扇柴扉小門。
“要不要叫上小貴?”順發說。
春妮似乎沒聽到他的話,自顧走出了院子。
在村口,他們看到了小貴,他似乎在等他們,又似乎猶豫不決。
三個人就在這樣微妙的氣氛中踏上了到鎮上求學之路。楊小貴悶頭兒走在前面,嚴順發跟在后面,走在最后的春妮沉默著走路。
到了鎮上的學校,光是初一就有四個班級,數學、語文老師都是專職的,不像村小什么課都是高老師兼著。分班的時候,要求男女搭配,據說這是防止同桌相互干擾學習的一種方式,那時候男生、女生間很少說話,楚河漢界十分明顯。而在村小,教室很簡陋,兩個土墩子上面放一塊木板,就是一排學生的課桌,男學生坐一排,女同學坐一排。
春妮排隊的時候,悄悄地踮了踮腳尖,瞄著嚴順發的位置,兩個人坐在一條課桌上。表面上他們互不搭話,而在內心里,他們彼此間的一個眼神,一個無意識的動作,都心領神會。
上課學習他們專心致志,彼此像陌路人一樣,很少有語言交流,看起來和其他的男女同桌沒什么兩樣。只有他們倆知道,彼此的交流是無聲的,一個眼神,一個不經意的動作,他們都心有靈犀,配合默契。
到了周末,春妮早早收拾書包,先行離開學校,一直到離近山道的一棵歪脖子柳樹下等他。
不一會兒,順發背著書包走過來。兩個人自然地走在一起,有說有笑。尤其是春妮,仿佛要把一周在一塊卻不能說的話都補回來一般,像出籠的鳥兒,話很稠。聊學習,聊老師,聊同學之間的一些瑣碎事兒。
“你可別說,鎮上中學老師的發音真標準,糾正了我許多發音不準確的地方。”嚴順發對春妮說起了對語文老師朱婷婷的感受。
“是的,只是朱老師目光很犀利,”春妮常常擔心這個愛提問的老師點她的名,讓她在大庭廣眾之下站起來朗讀課文,她的口音也不標準,加上她天生又是個不善于出風頭的內秀性格。
他們的語文老師朱婷婷,是個中年女老師,也是他們的班主任,戴一幅近視鏡兒,說話不溫不火的,很有修養的樣子。說一口當地老師很少見的純正的普通話,她講課時聲音不高,但即使坐在最后一排的學生也能聽得很清楚。學生們單是聽她悅耳的普通話,就很崇拜這個大地方來的老師。朱老師上課前,先用粉筆在黑板上寫下本堂課的提綱,她個頭不高,在黑板最上方寫頭幾行字,要踮著腳努力伸長胳膊才能夠到。她這樣的動作同學們不但不感到別扭,反而覺得老師的背影很優雅,有一種職業的美。同學盯著老師的手,那粉筆在黑板的摩擦下發出輕微的吱吱聲,像一曲動聽的音樂。朱老師寫完一段,轉過身開始講課,同學們望著黑板上的楷體字一個個驚呆了,那是多么漂亮的字體啊,簡直像鉛字印刷一樣。等朱老師講完一堂課,再看那寫滿內容的整個板面,美觀大方,就像一件完整的藝術品。每次課間,嚴順發拿著黑板擦去擦黑板上的字,總要貼近再認真地看幾眼,實在不落忍把它擦掉。
聽朱老師講課,課堂上氣氛總是很活躍,中間有一個互動環節,朱老師先讓學生們站起來朗讀課文,那些急于表現自我的男生們總是很踴躍地舉手,楊小貴是個風云人物,已經站起來讀了好幾次了,每次聲音都很洪亮,被朱老師校正了幾次,發音越來越標準、口才越來越流暢,朱老師很滿意。嚴順發讀的聲音小一些,但很沉著,眾目睽睽之下,沒有一絲緊張。
“老師要點名讓我起來朗讀怎么辦?”春妮說著說著突然站住,望著順發,眼神里閃過一絲慌亂。
“不要怕,你行的!”他鼓勵她,“咱們班上有好幾位女生站起來朗讀,剛開始有點緊張,后來都控制住了,越讀越流暢。”
“可我從來沒有在同學們面前站起來朗讀,一想起來心就狂跳。”她把手放在胸口處,似乎在感受心臟的跳動。
“每個人第一次都這樣,經歷了第一次膽子就大了。”他望望前后,山道上沒有一個人影,就說:“咱們在這里預演一下,我是老師,四周的樹木都是聽眾,你站起來朗讀吧。”
春妮也覺得這是個好辦法,就從書包里掏出課本,朝著兩旁的樹木,清了清嗓子,開始了朗讀。
剛開始還有些磕磕巴巴,練了三遍后,她的發音越來越準確,語速控制適中,并且能夠抑揚頓挫,臉上因緊張而泛起的紅暈慢慢消褪。
總是這樣,幾十里的山路,兩個人走起來很快,不覺得累。
剛開始楊小貴在上學和放學時也和他們一起走,三人在一起走路,氣氛很別扭。楊小貴偏偏又是個自我表現欲望很強的人,可他一說話,春妮就一臉的不屑和反感,他的話題沒人響應,他也就閉了嘴,聽道兩旁的鳥兒叫。
好在,楊小貴結交了一批新朋友,包括一些家住在鎮上的學生,逢周末也不回去,就在鎮上和同學玩,周末放學的時候給順發說聲:“回來幫我捎些干糧。”每周日晚返校時,順發就到小貴家,帶著小貴娘備好的干糧、食物,送到學校。上下學的路上,沒有了楊小貴這個電燈泡,春妮和順發感到特別開心。
也真是巧合,禮拜一的語文課,朱婷婷第一個就點了春妮站起來朗讀。春妮站起來,捧著書本,大聲朗讀。她讀得那么流暢,聲情并茂,全班靜靜的,每一個同學都在認真聽她的朗讀。
一只百靈鳥兒在教室門口的梧桐樹上啁啾,是在為她的朗讀配樂嗎?
朱婷婷是正規師院中文專業畢業的,家住省城,獨自一人長期在外教書。朱老師的目光很快就關注到嚴順發。這個學生有著山里人特有的樸實、勤快,目光里有一種求知的渴望,他對老師的崇敬都體現在無言的行動中。冬天,他悄無聲息地幫朱老師做好取暖的土爐子,打好煤球,甚至幫老師糊好窗戶紙,嚴嚴密密的,一絲風也進不來。
朱老師安排他當語文課代表,師生之間接觸的機會更多,經常和他一塊探討《水滸傳》,嚴順發更多的是講述書里的故事,每一章節都講得頭頭是道,朱老師講的更多的是注重人物性格上的刻畫,名著的語言技巧,幫他分析應該借鑒的寫作方式。隨著一步步的引導,嚴順發由愛讀漸漸轉入愛寫。他的作文常常作為范文在班上朗讀,并且出現在學校的黑板報上。
在朱老師的推薦下,他的一篇作文還發表在《語文報》上,和朱老師的點評一同變成了鉛字。捧著散發著墨香的報紙,嚴順發感到鉛字是如此神奇,仿佛有一種奇特的力量,讓他更加愛好寫作。在學校里,嚴順發是公認的優秀學生。
對于春妮來說,鎮上讀書階段在她人生中太重要了,她一個在人前不會說話的山里女娃變成了一個熱衷于朗讀、有了自己獨到見解的人,她學會了獨立思考。
至于楊小貴,在鎮中學混得風生水起,他是籃球隊隊長,是全校的名人,在他的人生詞典里,追求聲名是他很看重的。在村里他是孩子王,在中學,他依然在學生里有號召力。
盡管千般不舍,萬般無奈,畢業的時間還是到了。從學校回到山村,徹底告別了學生時代,還是那山那人,那一方天地,三個中學畢業生卻感到了不適應。
嚴順發融入最快,白天和父親、哥哥們一塊下地勞作,晚上仍點起油燈讀書到很晚。楊小貴心野了,再也收不回來,天天在外瘋跑。而春妮,幾年的學生生活,村人一直把她當作學生,現在學成回村,人們驚訝地發覺,不知不覺間,春妮出脫成一個美麗的姑娘,雖然衣著樸素,依然扎著兩個小辮兒,但面龐紅潤白皙,彎彎的眉毛,清澈的眸子,文雅、內斂,周身透著一股和山里女孩子不一樣的氣質。上門提親的踏破了門檻,有的人家還提著厚禮,并許以各種誘人的條件,可她一個也不同意。
楊小貴的母親出馬了。她來到春妮家那個低矮的茅屋,不但拿出了五百元天價彩禮,還許出了優厚的條件:村小學招老師,要把春妮和小貴一同招到學校當老師。
這顯然是醞釀已久了。人們再看高老師,可不是,幾十年的教書育人工作,背也駝了,耳也有點背了,主要是他的發音也不準。是該換個有學識的年輕人來干了。楊小貴在鎮上中學是籃球隊隊長,十里八鄉都是出了名的,是見過大世面的;春妮呢,據說在學校演講比賽中獲得了好多次獎,作為一個女娃,也是難得的人才。
楊小貴父親是村支書,春妮呢,是楊家未過門的兒媳婦,當然是這兩個人的了。而那個嚴順發呢,父親是平頭巴腦的老百姓,自然只能像他父親一樣下地務農。
天價彩禮加上當老師的優厚條件,讓春妮父母受寵若驚,真是天上掉下了金元寶。春妮當初想到鎮上讀中學,父母心中不大情愿,女娃嘛,識幾個字就行了,讀那么多書有什么用?過幾年還不是找個人家嫁出門了?可春妮雖然平時聽話,在自個兒認準的事上卻很執拗,堅持要去求學。父母無奈才讓她去鎮上讀書。現在看來,當初閨女的堅持是正確的,是有遠見之明的。幾年書讀下來,姑娘變得知書達理,模樣兒出脫得水靈可人,和村里沒讀過中學的女娃比高人一頭。支書家里提親,又禮數如此周到,當然沒有拒絕的道理。
這個消息村里人幾乎都知道了,唯獨嚴順發蒙在鼓里。
正午,嚴順發和村里的勞力們一同在田間頂著大太陽干活,休息的時候,別人都到地頭的大楊樹下,有的坐著,有的半躺著,東扯葫蘆西扯瓢,放松一下。他卻在一邊拿起一本書看了起來,很快就進入了角色,把一切都拋在了腦后。
身材高大的王大將走過來,用滿是泥巴的大手一把抓過他手中的書:“看什么書,這么入神?”
王大將這個“老干部”從小學勉強畢業后,參加勞動幾年時間,臉膛紅里透黑,身材壯實,肩扛一百多斤的糧食袋走路腰不打彎,腿不發抖,什么樣的活路都拿得起放得下。
嚴順發見他滿是泥土的大手胡亂地翻著書,封面上留下幾道明顯的臟印痕,眼中流露出痛惜。
“你呀,真是個書蟲。”王大將把書丟給他,壓低聲音說,“你知道嗎?小貴和春妮要到村小當老師了。”
王大將雖然壓低了嗓門,但他的話,卻像一聲炸雷,在嚴順發腦門上轟然炸響,震得他頭皮發麻,木木呆呆。見他怔怔的樣子,王大將說:“這不公平,論學識,你才最有資格當老師。”
王大將離去了,嚴順發腦子里亂如一團麻,耳朵里嗡嗡作響,回村務農本來沒有什么意外,他的心本來已經漸漸平靜,慢慢適應這種生活,可突如其來的這一消息打破了他心中的平靜,讓他一時六神無主,無所適從。
下午,他躺在炕上,發燒,頭疼,昏昏沉沉。父親、母親也知道了這一消息,他們也沒有辦法改變這種結果。木匠父親鐵青著臉,使勁抽著旱煙鍋子,滿屋子充滿著嗆人辛辣的煙味兒,母親一旁眼淚汪汪,唉聲嘆氣。
天黑透了,嚴順發看著滿臉愁容的父母,覺得這么拖累父母于事無補,就起床了,寬慰了父母幾句,就走出了茅草屋。
他機械地,像有一只手推著他一樣,盲目地往前走,在一條山道上,在大山溝里,或快步疾行,或躊躇不前。天蒙蒙亮時,他在一處依稀亮著一點燈光的大門前站定。他竟然站在了班主任朱婷婷老師辦公室兼宿舍的門口。
朱老師一個人在小鎮上當教書匠,有早起晨練的習慣。她向往常一樣早早起床,推開門,呆住了:“嚴順發!”
她略帶驚詫地喊了一聲,看到他怔怔的樣子,連忙把他讓進了屋內。燈光下,她看到嚴順發頭發蓬亂,眼睛紅腫,才短短一段時間不見,一個純樸中略帶儒雅的農村小伙子外表上有了極大的變化,黑了瘦了,粗糙了。她摸著他的手的一瞬間,感到那雙手布滿了老繭,厚重得像一塊石頭。
朱老師知道,自己看到的變化只是外表,這個學生的內心一定經歷了更大的撞擊。
她給他倒了一杯熱茶,面帶微笑地望著他。他慢慢地喝著茶,望著慈愛的老師,把心里的話毫無保留地倒了出來。
“春妮,多好的姑娘啊!”朱老師說,她其實早就看出來了,春妮看他時有著不一般的眼神。
把心中的郁悶向朱老師作了一番傾訴,他的心一下子輕松了好多。“老師,你放心,我能扛得住。”起身告辭時,望著朱老師眼中的不忍和不舍,他說。
他心中就是這么想的,為了像父母、像朱老師這樣的真心牽掛他的人,他也一定要好好活下去,無論再大的創傷也擊不垮自己。
“等等!”朱老師叫住了他,用明亮的眸子望著他,像看著自己的孩子,“我伯伯在省里負責紡織系統,聽說他們那里正在招人,我給他寫封信看看。”
消息來得如此突然,嚴順發來找朱老師時,并沒有想請老師為自已找工作,沒想到一向嚴謹細致的老師給了他一個大大的驚喜。
朱老師把他送出校門,一直送出好遠好遠。他想,無論行與不行,這一輩子都要銘記老師知遇之恩。
在楊小貴和春妮走進窯上小學任教沒多久后,嚴順發接到了來自省城的通知:到國綿六廠當工人。
別說村里人沒有想到,就連嚴順發和他的父母作夢也想不到。
這是嚴順發第一次出遠門。
穿著媽媽精心漿洗過的衣服,背著簡單的行李卷兒,在父母、哥哥的注視下,一家人送他到村口。
好心的朱老師,他們之間遠遠超越了師生情誼,她是他的恩師,教給他知識,也教給他做人。人生是公平的,有時面臨的現實看似嚴酷,走投無路,又會峰回路轉。
到了省城,找到掛著國綿六廠大牌子的地方,這是一個多大的廠子啊,光是繞著高高的圍墻他就走了好長時間,門樓高大,不時有上下夜班的穿著白大褂的女工出入,偶爾還有小臥車出入,大門口把門人見有小臥車進出,立即立正,做著放行的手勢。
他找了個空檔,到門口的傳達室詢問,怎么到人事科報到。傳達室的師傅和善地告訴他:“小兄弟,這都什么點了,人事科早就下班了,先找個地兒住下來,明天八點上班以后再來。”
住店對于嚴順發來說太奢侈了,他從來就沒想過掏錢住店。現在天氣又不冷,在路邊隨便找個地兒就可以湊合一晚。他在大門口對面的一處路燈下一個排椅上坐下,緊挨著的是一處小吃攤,賣餛飩、湯圓。攤主是一對中年男女,不停忙碌著。來這里吃夜食的大部分是穿著白大褂的年輕紡織女工,上夜班的工人走了,下夜班的人來了,人聲喧嘩,熱鬧非凡。
嚴順發感到肚子里一陣咕咕叫,他一天沒有吃喝了。這會兒感到餓了,他望著就餐的人們,那時候他不知道他們吃的是什么,餛飩有點像家里過年時吃的餃子,而湯圓呢,他壓根沒見過,更叫不上名字。
他目光瞥了一下正靠近自己吃湯圓的一個女工,那女工一定感覺到他注視的目光,好奇地看一眼這個小伙子。
見女工回望自己,他連忙收回了目光,從干糧袋里掏出了煮雞蛋、蔥花煎餅。他剝開一個煮雞蛋,幾乎整個兒塞進嘴里,他咀嚼著,又大口大口地吃餅子。
他注意到身邊吃湯圓的女工在悄悄地打量他,看她一小口一小口吃湯圓的樣子,他本能地覺得自己吃相有些不雅。這么一想,心里一急,食物就堵在嗓子眼兒上,他連著咳了好幾下,聲音很大,也沒咳下那團堵在嗓子眼上的食物,連淚水都憋出來了。
“給你,喝點湯。”那女工不知什么時候又要了一碗餛飩,遞給他。
嚴順發一愣,看到姑娘臉上含著笑,目光清澈,那么清純質樸,連忙下意識地雙手接過。
“媛媛,趕快走了,”她的女伴在催促她上夜班,她匆匆離去,身影很快消失在廠子的大門內。
第二天,嚴順發隨著上班的人流進了工廠。
這是一個遠近聞名的大廠,女工居多,正是紡織行業紅火的年代,機器轟鳴,晝夜不停,工人分三班倒,一片繁忙景象。他按照一個工人的指引,上了辦公樓人事處,填了表,到技術辦報到。
“你新來乍到,先跟著沈媛媛師傅當徒弟。”技術辦主任劉安國中等身材,稍胖,臉上一直掛著笑意,只是鬢角有幾絲白發很顯眼。劉主任用目光掃了一眼另一側對面擺放的兩張辦公桌,詳細給他介紹說:“沈師傅是從一線車間成長起來的技工,坐不慣辦公室,大部分時間仍在一線,和各車間工人泡在一塊,發現問題,及時解決。這會她正下車間搞調研,等她回來你們好好聊聊。”這兩張辦公桌不像劉主任的辦公桌上堆放著各式報表和計劃表,顯得有些零亂,而是收拾得很整齊,其中一張桌子上放著文件柜和專業書籍,另一張空蕩蕩的,顯然還沒有人在此辦公。
“沈師傅已經把你的辦公桌準備好了,”劉主任指著那張空著的辦公桌說,“別看沈師傅年紀和你差不了多少,她是從紡織技校畢業的,又有一線車間工作的經驗,是廠里的技術改新能手,很有頭腦。現在廠里缺少技術骨干,尤其是年輕的技工更是青黃不接,所以廠里下決心培養一批年輕的技術人才。你趕上了好時機,要好好跟著師傅學,盡快勝任本職工作。”劉主任的話,讓新入廠的嚴順發感到了壓力和責任。
正說著,門外傳來一陣說話聲,三個穿著白色工作服的紡織女工一塊走了進來。
打頭一個身材嬌小、留著齊耳短發、皮膚白皙的女工,摘下手上帶著油污的白色線手套,脫下白色外套掛在衣帽鉤上,一邊對劉主任打著招呼,一邊招呼其她兩個女伴坐,她的臉上漾溢著笑意,眼睛水靈靈的,她的目光碰到有些生疏和怯意的嚴順發的目光,不等劉主任介紹,自然地對他說:“你是小嚴吧,我叫沈媛媛。”
“沈,師傅。”面對純樸自然、大方熱情的沈媛媛,嚴順發第一次叫這個稱呼,或許是緊張,或許是吃驚,加上普通話不流利,回答得有些別扭、口吃。
他驚訝地發現,面前的師傅,竟然是昨天晚上送給他一碗餛飩的女工!
從山村里步入工廠,成為一個國營廠的正式工,嚴順發心里像點燃了一團火,工作熱情澎湃燃燒。
作為師徒,在工作中,師傅言傳身教,耐心而嚴格。嚴順發不善言辭,總是認真聽,悉心領悟,嚴順發內心慶幸,自己遇到了一個好師傅。晚上,技術辦的燈光總是亮到很晚,師徒倆一個抓緊學專業知識,一個在研究發明,提高紡織產量。
工廠里工人多,那個時候一般的工人都住集體宿舍。師傅也和嚴順發一樣住集體宿舍。晚上,辦公室里很靜,師徒二人聚精會神學科技、鉆科技,像開展學習競賽似的。
沈媛媛勤奮工作,銳意創新,贏得了全廠的公認,被廠黨委表彰為先進個人、勞動模范和三八紅旗手。
但在嚴順發眼中,師傅似乎沒有什么變化,仍舊把自己當作普通的技工,下車間和工人一塊忙碌,檢修設備,研究改進生產線的方法。所不同的是,師傅經常有意把他推出,讓他獨立完成機械檢修和故障處理。漸漸,他可以獨當一面了。經過師傅的大力舉薦和實踐鍛煉,他從學徒工轉為正式技工。
對于這個徒弟,沈媛媛在工作中嚴格要求,毫不保留地傳授技術,從辦公室到車間,無論八小時之內和八小時之外,師傅二人接觸得很頻繁。
周末,她和他像往常一樣泡辦公室,她埋頭做一份報表,他坐在對面的辦公桌前鉆《無線電》雜志上的一篇文章。門半掩著,偶爾有加班的人在樓道里走過。她做完報表,抬起頭來,正好嚴順發站起來,拿著暖瓶給她面前的杯子加開水。
“這么長時間沒有回家,想家嗎?”她問。
“在廠里干很充實,”見師傅難得的好心情,聊起了個人話題,嚴順發也很高興,“父母身體很好,經常來信叮嚀我要好好跟著師傅學技藝。”
正聊著,技術辦劉安國主任一下子推門進來,兩個人都吃了一驚,下意識地站起來。劉主任看見沈媛媛和嚴順發兩個人都不自然的神情,先是一愣,隨即平靜下來,彌勒佛一樣胖乎乎的臉上仍舊掛著笑容:“坐嘛,坐嘛。”
劉主任是個熱心腸的領導,平素也觀察到這師徒二人的感情日益加深,只是沒有點破,似乎誰也不好意思先主動說出。從師徒二人的目光中,劉主任捕捉到他們真實的內心情感。劉主任走到辦公室門口,像離去的樣子,突然又扭回頭,像發現新大陸似的,朝兩人上下打量一番,說:“我看你倆挺般配的,毛遂自薦做一回紅娘,你倆愿意嗎?”
沈媛媛聽了此話,把頭垂到胸前,白皙的臉更紅了,一直紅到脖子根。
嚴順發站在一旁,一時也不知該說什么,看著師傅,心怦怦跳。
在劉安國主任的見證下,他們舉辦了婚禮。劉主任又幫助他們向廠里申請了一間單身宿舍當婚房。心靈手巧的沈媛媛把它布置得井井有條,物品擺放恰到好處,顯得很溫馨。
結婚后,為便于工作,廠里任命嚴順發到前紡車間任副主任兼技工。車間的工作更加忙碌,白天忙生產,晚上研究科研改新,心靈洋溢著幸福的火花,他很充實,仿佛有使不完的勁,他用一顆火熱的心投入工作中,用成績回報廠領導的關懷。
近來,沈媛媛總是覺得身體疲憊,精力不濟,伴隨著陣陣嘔吐。有時在衛生間吐得眼冒金花,虛弱無力。
隨著一聲嬰兒嘹亮的啼哭,一個女嬰順利誕生了。
小屋里多了一個叫沈玉蓮的女孩,常常傳出她的哭聲和笑聲。
人們看到嚴順發變了,早上起來有時頭發有些亂,眼里含有血絲,這是他白天加班工作,晚上照料妻子和小孩的印記。但整個人卻變得更有朝氣活力。一大早直奔早市,買活雞活魚和新鮮菜蔬,給沈媛媛煲湯熬粥,對著借來的菜譜認真地學著做一些沈媛媛愛吃的菜。他的烹調技術很一般,但妻子每次嘗一口總是說“好香”,這無疑是對他極高的獎賞。
在工作毫不放松的前提下,盡量做一個好丈夫,好父親。因為他愛她們,所以做這一切很開心。
形勢的發展變化有時誰也想不到。嚴順發所在的工廠遇到了困難。
一個曾經紅紅火火的國營大廠,突然之間生產的產品銷售不出去了。產品積壓,生產的越多,虧本越大。無奈之下,車間減產了,原先日夜倒班生產的景象再也不見了,甚至有時白天也是產產停停。
廠里的工作重點轉到如何擴大銷路上來。老廠長已上調到省廳,新廠長大會小會強調抓銷售、抓效益。銷售部門的人兵分多路,到全國各地去推銷,但收效甚微。工人的工資甚至都快發不出來。廠長把目光盯著已經成為工程師的嚴順發,他也心虛地低下頭。在產品銷路上,他也感到無能為力。
一天,沈媛媛下班,扛了一大包本廠生產的棉線手套回到家里。
“家里要這么多手套干嗎?”嚴順發有些不解。
“唉,”沈媛媛心情沉重地說,“廠里產品積壓,每個人都定了推銷指標。”
嚴順發無奈地伸開手,苦笑,在廠里這么些年,從來沒有面臨像現在的復雜形勢,產品銷量提升,不是靠技術革新就能拉動的,而是要適應轉型轉軌的發展趨勢。在廠里當了多年廠長的陸英升任省里紡織廳的領導,德高望重的技術辦劉安國主任也激流通退,被一家私企高薪聘走,離開了工廠。嚴順發望著一堆綿手套,有點迷茫。
“不要想那么多,人人都這樣,你沒看見有些姐妹在廠門口擺攤兒嗎?”
“咱也去擺攤兒?”他想起,現今最新流行的一個詞兒:練攤。真有意思,在路口擺個小攤還用練嗎?
“廠里已經開始裁員了,有一批姐妹下崗了。”沈媛媛嘆了一口氣,這個廠勞模、三八紅旗手,此刻一臉憂思,全然沒有了當年大比武奪第一名時的自信。
“總不能裁到我們頭上吧。”嚴順發自言自語地說。
沈媛媛太了解嚴順發了,他從小鄉村走來,廠子給了他施展人生價值的平臺,有了用武之地。多年來,他已經把自己整個身心融入工廠,以廠為家,打算把一生奉獻給這個國營大廠。即使當初老廠長陸英上調,要帶他去省廳當秘書,這在別人看來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機會,而他,內心除了對老廠長的知遇之恩充滿感激而外,自己靈魂深處對這個工廠充滿了依依不舍之情。后來,由于種種原因,他沒有跟隨老廠長上調,不少人為他婉惜,而他竟然還有點暗自慶幸。“真讓我離開咱們廠,我心里還真舍不得。”他私下里對媛媛表露心跡。
沈媛媛父親在印染廠當工程師,母親是廠里的技術骨干。印染業是傳統的優勢企業,隨著旅游業的興起,拉動了當地的經濟發展,具有上百年傳承的印染織品受到各地游客的青睞,產品常常供不應求,很快成為當地的支柱產業。這家私營企業的總經理姓梁,深知人才的重要性,千方百計吸引人才,重用高端人才。在沈媛媛父母的舉薦下,梁總很痛快就答應把沈媛媛和嚴順發一同招進廠。父母要女兒找機會給嚴順發吹吹風,好好考慮考慮,現在形勢不一樣了,在哪不是為國做貢獻呢?何必守著一個沒有發展前途的廠子干耗呢?況且孩子小,也沒有人幫著照看。但沈媛媛張不開這個嘴,她知道,雖然棉紡廠遇到了低谷,但要嚴順發離開這個廠,他還是不情愿的。
嚴順發開了一天的會議,全是資金短缺、產品積壓、尋找出路、產業轉型、裁減人員、精減機關等沉重的話題。看得出,廠領導也很焦慮,壓力大,爭論不出個辦法。在時代大變革的潮涌中,誰也無力回避這個現實,扭轉乾坤。
“我決定,下崗了。”一家人氣氛壓抑地吃過晚飯,媛媛望著他,目光平靜,沒有回避,沒有慌亂,顯然已經醞釀好久了,不管他同意不同意,她都要對他攤牌了。
“你是主動讓出來的嗎?”嚴順發很敏感,他們兩口子都在廠里當中層干部、技術人員,有人盯著他們呢。媛媛這是“丟車保帥”。
“對,”沈媛媛盡量以輕松的語氣說,“現在廠里發展形勢這樣,我又懷孕了,即使這批留下來,下批也……”
嚴順發望著沈媛媛隆起的小腹,重重地嘆了口氣。
夜晚,嚴順發走在空蕩蕩的工廠里,機器停止了轟鳴,也沒有了上下夜班工人的嘈雜和喧嘩,一切在平靜里顯示著無奈,這個曾經輝煌的大廠不可避免地走著下坡路。而他的心卻掀起著狂風暴雨,一個大膽的想法在腦子里醞釀。
在困苦窘迫中,他們的第二個女兒呱呱墜地了,取名沈玉珍。可是這個小屋的氣氛卻遠不如第一個孩子玉蓮出生的情景,那時,他們忙著工作,心里有激情,生活有熱度,而此刻,他們情緒低落,為廠子的前途和命運,也為自己的出路而焦慮。
無論嚴順發怎樣留戀這個廠,形勢的發展都不以他的意志為轉移。工廠連年虧損,一批下崗工人們買斷了工齡,懷揣著一次性補償金,離開了廠子。
沈媛媛進了父母所在的印染廠,嚴順發經過深思熟慮之后也一同過來了。那是一家私營企業,效益很好。房子是現成的,廠里就近給父母一套公寓房,家里的老宅子已為他們布置好,雖然外表看房子老了些,但里面裝飾一新,客廳、沙發、電視,這和他們在工廠的小屋子相比,真是天壤之別。玉蓮一頭扎進自己的小房間,就再沒出來。她已是個中學生了,太渴求這樣的獨立空間了。
嚴順發也被委以重任,擔任技術高管,工資是他原來的好幾倍。岳父是印染廠資深工程師,當然對自己的乘龍快婿用心盡力地傳授技藝,嚴順發本來就是成熟的技工,基本功扎實,所以很快就上路了。作為高管,工作不累,人際關系簡單,和在幾千人的大廠當一個車間主任的工作量相比那是小巫見大巫。每到月底,按期領到厚厚一疊子鈔票,什么績效工資、獎勵工資等名目繁多的獎項,他感到很不真實。他在綿紡廠當過學徒、正式技工,后來又下車間當副主任、主任,當總工程師,拿的工資基本上都是死工資,按級別一級一級調整,每升一級工資調整的幅度很小。到后來,還不能足額發放。而在私企里,似乎一切都變了樣。
嚴順發憑著自己扎實的技工功底,加之勤學聰敏,很快轉型,和岳父一道,研究發明新工藝,推出高端精印染產品,滿足市場需求,給印染廠帶來可觀效益,很快成為廠里的核心技術人才。
現在,心靈手巧、悟性很高的沈媛媛在父母的悉心指導下,很快學到了父母的真傳,掌握了印染業的核心工藝。印染業有幾百年的歷史,工廠生產的藍印花布,廣受游客喜愛。沈媛媛繼承了父母的靈氣和悟性,精準掌握了藍印花布的精髓。她頭腦活泛,關注市場供求信息,對傳統的藍印花布產品加以改良創新,如給衣服、頭巾、手袋、扇子融入卡通畫等時尚元素,別出心裁,成為游客競相購買的搶手貨。
嚴順發敬業、愛鉆研,他以敏感的目光,瞄準市場前沿,創新生產技術,為廠里帶來了極大的利潤,印染廠成了當地的支柱產業和納稅大戶。梁總是一個聰明的企業家,放手放膽使用技術人才,給科研人才創新發明搭建了寬廣的舞臺,使嚴順發有了施展技術的用武之地。
這天,嚴順發接到了一個陌生的電話。他對這種情況習以為常,他和外界接觸少,不善于社交,而他的知名度高,有好多人慕名打來電話。
他接通電話,習慣地說:“你好。”
對方回應了一聲“你好”。那口音像是南方話,又夾著普通話,嚴順發沒有聽出是誰,一般情況下,對方都會自報名姓的。他只好又問了一句:“你貴姓?”
“猜猜我是誰?”從對方對他那種異乎尋常的親熱口氣中,他感到這個人和他認識,并且關系應該不一般。
“你是,王大將?”他疑惑中帶點肯定。因為那種口音無論怎么改,總還是有一點熟悉的氣息,只是一時猜不出而已。
“哎呀,老同學,你還記得老干部啊!”沒想到對方竟然高興地喊了起來。
“你真是王大將?”嚴順發不完全相信。
“見個面吧,”對方說,“我住在錦江大酒店,來了你就知道了。”
既然知道王大將老干部的外號,那必然是和嚴順發有交集的老同學。他聽說過,王大將后來一直跟著父親干工程,近些年生活起色很大,結了婚,有了孩子,在城市里買了房,在市里定居了。但是,王大將再怎么變,也不會變成這樣一個油嘴滑舌的樣子啊?
嚴順發急忙打車趕到酒店,大廳里等候的竟不是王大將,而是楊小貴!小貴一身西裝革履,帶著名貴手表,抽著高檔香煙,言談舉止優雅瀟灑,一看就是個見過大世面的人。
“你沒怎么變啊。”楊小貴握著嚴順發的手,使勁地晃了幾下,“和我想象的差不多。”
“老了,頭發白了。”嚴順發掠一下稀疏的花發,望著楊小貴梳理得很齊整的黑發說,“你倒是越來越精神,頭發還是這樣黑,這樣濃。”
“染的。”楊小貴說,“歲月不饒人啊!”
楊小貴望著嚴順發,似乎在打量這位小時候的玩伴有多少變化,良久才說:“混得不錯啊,聽說你現在事業有成,成為大名鼎鼎的高科技人才,是家鄉引以為榮的驕子啊!”
“什么人才,你過獎了。”嚴順發打量著楊小貴保養得很好的皮膚,一身名貴的衣著,腳上锃亮的皮鞋,也打趣地說,“這哪像一個小學老師啊,一看就是大老板的派頭,要是在大街上相遇,撞個跟頭也認不出來了。”
兩個老同學在大廳里的茶吧坐下,喝著茶,聊著天,氣氛很好,楊小貴沒有提及春妮,嚴順發也沒有打聽。不覺間到了飯時,嚴順發拿出手機,要給媛媛打電話,招待老同學吃飯。
“不了。”楊小貴攔住他,“我還有事,馬上要飛海南。”
“這么急,”嚴順發是個實誠人,實心實意想請這位童年好友吃一頓飯,畢竟,一晃多年不見了。見楊小貴目光閃爍,似乎有什么話要說,他問:“有什么困難,需我幫助嗎?”
“還真有件事,需要你幫一把,”楊小貴搓了一下手,顯出有些為難的表情,“這會手頭有些緊,急缺資金周轉一下。”
“需要多少?”嚴順發想,既然老同學開口,那一定是要幫的。他沒有問楊小貴遇到什么急難事,像小貴這樣的人,張嘴借錢,一定是到了不得已的情境。
楊小貴沒有回答具體要多少,而是伸出了一個指頭。
“十萬?”嚴順發實在,他覺得以楊小貴現在的作派和氣度,住著這么高檔的酒店,不會是更小的數目。
“哎呀,到底是老同學,一猜便知。”楊小貴以一種輕松的口氣說。他知道,像嚴順發這樣的人,能說出十萬這個數目,已是上限。
嚴順發也莫名地松了一口氣。十萬不是一個小數目,但對于他目前的經濟狀況,也還拿得出手。于是,就給媛媛打電話,說老同學急需用錢。媛媛有些猶豫,但并沒有細問,嚴順發平時是不問家里財政大事的,都由她打理,一下子要這么大一筆數目,肯定不是一般的老同學。就說:“我馬上到銀行取,要現金還是轉賬?”
嚴順發目光轉向楊小貴,楊小貴用手機給他發了一個工行的賬號,他又轉給了沈媛媛。
楊小貴沒有多停留,謝絕了嚴順發提出的和沈媛媛一同吃飯、陪同游玩的挽留,行色匆匆,又消失在人海中。
嚴順發是個感情綿密細致的人,有些事,有些人,雖然嘴上講得少,而在內心深處,永遠占據非常重要的位置。
朱婷婷老師落實相關政策,從老家的中學調回省城,在教育系統上班,退休多年了,他們一直聯系著。雖然手機很普及,他和朱老師還保持著傳統的書信來往方式,每次給朱老師寫信,他都把自己關在書房,用心地一筆一劃地寫。
“咱們去看望老師吧。”沈媛媛知道他的心思。
他們購買了大包小包的禮品,乘車來到朱婷婷老師家。這是一個老式的六層灰磚樓房,他們步行上了四層。二人拎著東西,一級一級上臺階時,嚴順發心里一陣陣地發沉。到了四樓,他伸出按門鈴的手又收回來,望著同樣有些氣喘的媛媛,說:“朱老師上了年紀,住這么高的樓層,太不方便了。”
門開了,朱婷婷老師探出一張臉,見是他們,就打開門:“到家門口了,咋不進來說話?”
“朱老師。”嚴順發望著恩師,恭恭敬敬地叫了一聲,深深地鞠了一躬。朱老師頭發已經全部變白,目光依然那么平靜而溫和。
朱老師熱情地讓他們坐下,客廳不大,收拾得很利索,茶幾上擺放著水果,水杯里的茶剛泡上不久,掀開蓋兒,清香撲鼻。
“看到你們我真高興,”朱老師望著嚴順發夫婦,打心眼兒里開心,“順發上學時,勤奮刻苦,一看就是個有出息的人。”
“沒有老師的栽培,哪有他的今天?”沈媛媛見嚴順發因激動而紅著臉,知道他心里話一時不知怎么表達,就代丈夫說出心里話。
正聊著,朱老師的愛人、大學教授方敏拎著大包小袋回來了。看著嚴順發,又看看沈媛媛,笑著說:“朱老師聽說你們來訪,可開心了。我設計了幾種接待規格,找一家高檔的飯店,或是一家有特色的私家菜館。結果都被朱老師否決了。她的意思,哪里也不去,就在家里吃。”方敏指指剛帶來的袋子,“按照朱老師的圣旨,食材我都準備好了。”
“家宴好,有家的味道。”沈媛媛有一手好廚藝,拿著這些食材到廚房,她說:“你們聊,一會兒就好。”
“多好的媳婦啊,”方教授望著在廚房忙碌的沈媛媛,笑著對嚴順發說,“你有一個賢內助,她是你人生成功的幕后英雄。”
“真正的幕后英雄是朱老師,沒有朱老師,就沒有我的今天。”嚴順發說著,突然鼻尖一酸,熱淚盈眶,“朱老師,還記得那一夜嗎,當時我真覺得天塌了,走投無路。可峰回路轉,你給我的心靈打開一片光亮!”
“過去的都過去了,”善解人意的方教授給嚴順發遞過紙巾,安慰他。嚴順發接過紙巾,而那不爭氣的淚水,越擦越多,仿佛要把幾十年的淚都流出來似的。
“看你,小孩子似的。”沈媛媛干練利索地把炒好的菜肴端上桌,推推順發,“今天來看老師,是大喜的日子,要開心才是。”
嚴順發終于平靜下來,由衷地說:“朱老師交給我學識,更重要的是教給我人品,我一生都以老師的教誨為準繩,無論干什么,首先做一個好人。”
說話間,沈媛媛端著一盤盤菜肴上桌了。“真是大師級廚藝!”為活躍氣氛,方敏教授故意夸張地嗅了一下鼻子,豎起了大拇指。大家笑著,動起了筷子,吃著,品評著每道菜的味道。
臨別的時候,朱老師和方教授執意要送他們到樓下。
當他們坐上出租車,搖下車窗玻璃,看到朱老師和方教授在向他們揮手,風吹動著他們的白發……
接下來他們打算回一趟故鄉——那個叫窯上的鄉村。多年沒有回故鄉,但那是他的根,夢回縈繞的地方。做木匠的父親憑著自己的勤勞與智慧,經過多年打拼,已成為遠近聞名的建筑公司的老板。“老干部”王大將也在公司里當了項目經理。楊小貴辭職下海到海南發展,風光一時,后欠下巨額債務,至今不知下落,借給他的十萬元,很可能打水漂。至于春妮,小學合并后,她被調到縣重點高中任教,擔任年級組組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