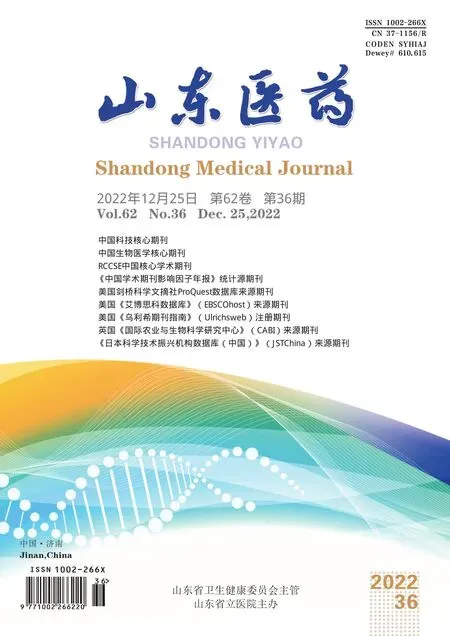癲癇患兒常見神經精神共患病的臨床特點及發病危險因素研究進展
康萌,楊欣偉
1 西安醫學院臨床醫學院,西安 710021;2 空軍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兒科
癲癇是一種常見的慢性兒童神經疾病,患病率常在 4/1 000~12/1 000[1-3],規范治療近半患者可擺脫抗癇藥物,但仍有約1/4的患者為難治性[4]。癲癇出現并發癥是常態,超50%患兒有一或多個額外問題,如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ADHD)、孤獨譜系障礙(ASD)、抽動障礙(TD)、智力障礙(ID)、情緒障礙(抑郁癥、焦慮癥)等,統稱神經精神共患病,增加癲癇兒童的疾病負擔,又使癲癇診斷更復雜。國際抗癲癇聯盟與國際癲癇病友聯合會于2005 年,聯合發布癲癇新定義,重點強調癲癇患者可能伴隨認知、精神心理、社會適應性等功能障礙。一項以全國為基礎的隊列研究[5]表明,癲癇兒童比對照組更容易合并疾病。癲癇兒童神經精神共患病的發病危險因素是多方面的,如一般因素(年齡、性別)、癲癇病理學、抗癇藥物因素等。現就癲癇患兒常見神經精神共患病的臨床特點及發病危險因素研究進展情況綜述如下。
1 ADHD的臨床特點及發病危險因素
ADHD 是一種常見的兒童期發育障礙,分為注意力不集中型、多動/沖動型和混合型三種亞型,在兒童和青少年中的患病率為7%~8%[6],而在癲癇患兒中 ADHD 的患病率要高出 2~3 倍[7]。ADHD 是一種常見且極具挑戰性的共患病,嚴重影響著兒童的學業成績、語言能力、幸福感以及社會交往的能力。在特殊癲癇綜合征中,兒童期失神癲癇(CAE)與伴中央顳區棘波的兒童良性癲癇(BECT)是最常見的癲癇綜合征,且二者與ADHD 都有著非常高的共病水平。近期一項研究[8]顯示,40%的CAE 患兒被診斷ADHD,并且發現合并ADHD 的CAE 患兒比單純CAE 患兒更容易犯遺漏性的錯誤。Rolandic 癲癇(BECT)的 ADHD 患病率在 12.5%~40%[9-10],與典型的BECT 相比,共患ADHD 的BECT 患者常起病年齡較早,病程較長,智商(IQ)較低。他們的癲癇樣放電更有可能會擴散到一個或兩個半球,且共患ADHD 的BECT 患者需要多種療法來控制癲癇發作的比例更高。兒童癲癇的神經精神合并癥也可能與神經影像的肉眼病理(復雜癲癇)相關,關于康涅狄格州癲癇隊列研究的分析發現,患有復雜癲癇的患者(IQ總分<80或存在結構性腦損傷)中38.4%有精神障礙,比例明顯高于無并發癥癲癇患者的26.6%[11],這一差異的主要驅動因素是復雜癲癇組中ADHD 和品行障礙等外在障礙的發生率明顯更高。近期有研究發現[12],共患 ADHD 的 BECT 患者在皮質和皮質下區域(包括額葉、舌梭形皮質、楔形和楔前、邊緣區和甲周皮質等)的磁共振成像掃描中顯示出現厚度變化。此份關于共患ADHD 的BECT兒童發現的皮質結構異常(皮質變薄)報告表明,這種皮質變薄也存在于沒有ADHD 的癲癇兒童中,但是共患ADHD的癲癇患兒與皮質區域變薄關聯性更強,這種新發現可能更好的解釋了這類患兒的認知和行為癥狀,如選擇性視覺注意力更差、言語障礙和沖動。這些問題的存在都會使得共患ADHD的癲癇兒童疾病負擔更重,因此臨床醫師在診斷癲癇的同時,也應更加注意ADHD的識別。
2 ASD的臨床特點及發病危險因素
ASD是一種典型的兒童時期診斷的神經發育障礙,特征是核心社會功能障礙、僵化和重復的行為、受限的興趣和異常的感官敏感性。近期一項對19個研究的薈萃分析顯示,癲癇患者的合并ASD 患病率為6.3%,按類型劃分時,全面性癲癇、嬰兒痙攣、局灶性癲癇發作和Dravet綜合征的ASD風險分別為4.7%、19.9%、41.9%和47.4%。對18 歲以下人群的研究顯示,ASD 的風險是18 歲以上研究人群的13.2 倍,大多數(>50%)智力障礙個體的樣本顯示,其風險是少數智力障礙個體的研究人群的4.9倍[13]。同時這些研究報告的共病危險因素主要包括智力障礙、性別、年齡和癲癇的癥狀性病因。另一項招募了 100 余例 ASD 兒童的橫斷面研究中[14],多達23%的人報告了癲癇,8%的人記錄了亞臨床腦電圖異常,女性性別、異常的神經系統檢測結果,圍產期不良事件同樣被認為是癲癇共患ASD 的危險因素,同時患兒腦電圖出現異常也得到較高的支持,ASD患者常出現癲癇樣腦電圖異常(棘波、棘波、慢波),雖然近期在不少涉及具體某種癲癇兒童神經精神共患病的研究[5,13-14]中有提及共患神經精神共患病的主要危險因素包括了性別、年齡等,但目前沒有一致的證據表明年齡、性別和社會經濟地位與神經精神共患病有確切的相關性,近期的一項薈萃分析[15]同樣持此觀點。另外,家庭成員共有基因以及環境因素也可能在癲癇與ASD 的共病中起到一定的因果作用。大量的基因提示癲癇與其神經精神共患病可能存在共同的潛在神經生物學機制,一些與癲癇和(或)其神經精神共患病發生相關的基因突變對神經元功能的各個方面都有影響,而且并不局限于離子通道和突觸生理學,這些突變會影響一些與神經元興奮性的各個階段有關的蛋白質:錨定突觸機制、管理突觸小泡的釋放、控制亞細胞信號通路、調節神經元的遷移以及網絡連接的組織[16]。PENT 基因(位于10 號染色體)是一種負調控磷脂酰肌醇-3-激酶(PI3K)/AKT 信號通路的抑癌基因,該基因編碼磷脂酰肌醇-3,4,5-三磷酸-3-磷酸酶,PTEN 基因雜合突變已在癲癇、自閉癥、智力殘疾和巨頭畸形患者中有發現[17]。RBFOX1 基因又稱 rna 結合 FOX1,位于染色體 16p13.3 上,編碼 ataxin 2 結合蛋白 1,在ASD、智力殘疾、癲癇、注意缺陷多動障礙和精神分裂癥中發現了RBFOX1的異常[18]。值得深思的是在臨床環境中癲癇兒童共患ASD 很常見,而在人類發展指數較高的國家卻較少見,此發現也為癲癇共患ASD 的患病率提供了批判性和創新性的觀點,在未來的臨床管理時應更加注意針對性的預防措施[19]。
3 抽動障礙的臨床特點及發病危險因素
抽動障礙是根據DSM-5 定義的一種“突然的、快速的、反復的、但非節律性的運動和(或)發聲,癥狀波動,持續數周至數月,可累積身體不同部位。它們被認為是無目的的,只能短暫地被抑制。抽動的發病主要集中在幼兒園早期和學齡期,發病年齡為3~11 歲,平均為 6~7 歲[20]。多數情況下抽動都是“暫時性抽動障礙”,呈現一過性癥狀。但也有過渡到慢性的風險,其定義是癥狀持續超過12 個月的“持續性抽動障礙”。雖然僅少數患者表現出持續的癥狀或功能損壞,但抽動障礙的連續性,特別是作為合并癥,可能會給患者帶來嚴重的社會功能障礙。近期一項利用中國臺灣全民醫療保險系統的資料庫,調查癲癇兒童患抽動障礙風險的研究[5]表明,癲癇組與對照組相比有更高的抽動障礙發生率(1.7%比0.2%),風險增加8.70 倍(調整后的危險比AHR 8.70,95%CI=4.26~16.37,P<0.001)。與女性相比,男性患者患抽動障礙的風險更高(AHR 1.90,95%CI=1.04~3.46,P<0.001)。接受多種抗癲癇藥物治療的患者發生抽動障礙的風險也較高,由于抗癲癇藥物主要在中樞神經系統發揮藥效學作用,因此抗癇藥物的不良反應通常涉及中樞神經系統。雖然繼發性抽動障礙被認為是抗癇藥物罕見的不良事件,但最近的一項系統評價[21]分析表明,卡馬西平、氯硝西泮、乳糖胺、拉莫三嗪、左乙拉西坦、苯妥英鈉、苯巴比妥等不同作用方式的抗癇藥物均為可能導致抽動障礙的藥物。超過1/3 的病例涉及卡馬西平(35%)和拉莫三嗪(41%)主要發生在第2 個抗癇藥物的背景下,加巴噴丁、托吡酯和丙戊酸鈉只有在存在第2個抗癇藥物的情況下才可能出現共患抽動障礙的情況,不被認為是最具風險的。因而共患抽動障礙的兒童在選擇抗癇藥物的時候應更為謹慎,盡量避免使用導致抽動風險較高的藥物以免加重病情。
4 ID的臨床特點及發病危險因素
ID 是一種兒童早期出現的神經發育狀況,也是一個標簽,用于描述一系列癥狀,包括個人在多個功能領域或領域發展技能的嚴重缺陷或限制:認知、語言、運動、聽覺、社會心理、道德判斷和特定的綜合適應性(即日常生活活動),當前智力障礙的診斷標準將能力分類為通過IQ 測試測量的能力。據估計,1/4 的癲癇患者都有ID[22],癲癇的管理需求也代表著許多ID 患者的重要醫療需求。癲癇和ID 共同發生通常伴有與頻繁的癲癇樣活動相關的發育停滯或退化,大多數情況下其明確原因未知。近期一項研究[23]采用單核苷酸多態性(SNP)芯片結合WES 對102 例兒童患者進行了全面、系統的分析,進一步比較了不同發病年齡和ID 嚴重程度的癲癇患者的拷貝數變異(CNV)和單核苷酸變異(SNV)的產率。得出遺傳異常的總診斷率為33.3%(34/102),其中CNV的診斷率為50.0%,SNV的診斷率為50.0%,雖然這一結果沒有統計學意義,但不可否定產率隨ID嚴重程度的增加而增加,隨癲癇發作年齡的增加而減少。癲癇和ID 患者治療不當可能導致過早死亡,這一點在國際癲癇專家最近的一次行動呼吁中也被重點強調,討論了在這一類人群中未能認識和預防癲癇的相關死亡問題[24]。鑒于明確的證據表明,患有ID 和癲癇的人往往健康和社會適應結果不佳[22],對醫療和護理費用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因此有很強的理由促進對這一弱勢群體的關注與研究。
5 情緒障礙的臨床特點及發病危險因素
情緒障礙對癲癇也是一種常見共病,與普通人群相比,癲癇同抑郁和焦慮的共病尤其普遍,并與各種不良后果相關。其中抑郁癥與癲癇的關系在現代調查始于 20 世紀 70 年代,TRIMBLE 等[25]發現了抗癲癇藥物的行為與認知并發癥,特別是苯妥英和巴比妥酸鹽。一項對基于人群研究進行的薈萃分析發現,癲癇患者抑郁癥的總體合并患病率為23.1%,與對照樣本相比,癲癇患者中患抑郁癥的概率顯著增加[26]。焦慮和抑郁障礙都與較差的生活質量和更高的醫療利用率有關,同時共病情況也可能影響醫療結果,如較差的癲癇控制和抗癲癇藥物相關的副作用增加[27]。一些研究認為,突觸后多巴胺受體敏感性的共同異常、GABA 周轉增加、齒狀回-CA3-CA1回路中突觸回路的異常、皮質發育不良或獲得性腦損傷可能會導致精神病和癲癇的并發[28]。也有研究集中在自身免疫性的病因上,如腦紅斑狼瘡、N-甲基-D-天冬氨酸腦炎和富含亮氨酸的膠質瘤滅活1腦炎同樣可能會導致精神病和癲癇的發作[29]。事實上有證據表明[30],社會支持水平和感覺到的恥辱等因素與抑郁和焦慮的癥狀之間存在關聯,同時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癲癇和精神障礙之間存在雙向關系,很可能是由于癲癇和精神共病相關的病理生理機制(如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過度活躍)[31]。癲癇可能會通過長期暴露于慢性壓力來促進抑郁癥的發展,癲癇發作的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可能會激起癲癇患者的悲傷、孤獨、絕望、低自尊和自責,并且導致社會孤立、恥辱或殘疾。通常抑郁癥與焦慮癥被視為對癲癇病恥辱和相關生活質量差的反應,與健康人群相比,癲癇患者的出現抑郁、焦慮和自殺的幾率明顯更高。抗癲癇藥物在癲癇患兒的神經精神共患病中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早在2008 年,FDA發布警告稱,服用抗癇藥物的患者自殺風險在統計上顯著增加了1.8 倍。隨后對癲癇患者的大型回顧性觀察隊列進行的生存分析和病例交叉研究證實了這一警告[32],同時也引起了人們對抗癇藥物可能潛在的行為副作用的關注。像苯巴比妥這樣較早期的藥物對導致患兒出現認知不良的情況存在一定的影響,新一代的抗癇藥物如左乙拉西坦、加巴噴丁、托吡酯和潘生丁更有可能引起易怒和攻擊性等行為不良反應[33-35]。因此,提高對癲癇共病抑郁和焦慮等情緒障礙的認識、發現和處理,對提升癲癇患者的生活質量至關重要。
綜上所述,癲癇兒童神經精神共患病尤以ADHD、ASD、TD、ID、情緒障礙較為常見,情緒和心理行為問題與癲癇存在著密切聯系,并且會對患兒的日常生活及心理健康造成嚴重的影響。同時多種風險因素如年齡、性別、抗癇藥物的使用、基因遺傳、突觸后多巴胺受體敏感性的共同異常、GABA 周轉增加、齒狀回-CA3-CA1回路中突觸回路的異常、自身免疫性病因、皮質發育不良或獲得性腦損傷等,均可能與兒童癲癇共患精神疾病的高患病率相關。因此,強烈建議注重對癲癇患兒神經精神共患病的篩查,新發癲癇兒童包括那些特發性綜合征,尤其是那些在診斷時表現出認知和行為等問題或存在神經精神共患病風險因素的兒童。雖然對癲癇發作本身和治療的密切關注是可以理解的,但也需要在診斷時,最好是在開始抗癲癇藥物治療之前,對認知及行為等問題進行及時、有效、成本效益高的評估與篩查,促進早預防、早診斷,早治療。而抗癇藥物并非對于癲癇的神經精神共患病是禁忌的,絕大多數精神類藥物也并不會加重癲癇的發作。分析抗癇藥物的不良反應和精神疾病并存可能是一項艱巨的任務,潛在的和未診斷的精神合并癥可能會與抗癇藥物副作用混淆,因此應更多的去關注這方面的研究,以便于更好的篩選各患兒最合適的抗癲癇藥物和精神類藥物,及時確定患兒是否需要進行心理治療,以期最大程度的改善患兒生活質量,減輕疾病負擔,達到一個較好的遠期預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