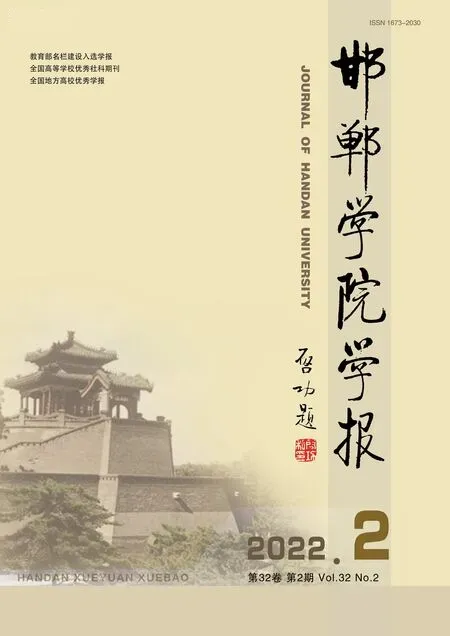論梵語戲劇經(jīng)典《結(jié)髻記》中的英勇味
焦振文
(河北農(nóng)業(yè)大學(xué) 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學(xué)院,河北 保定 071001)
取材于被譽(yù)為“印度的靈魂”的史詩《摩訶婆羅多》的梵語戲劇《結(jié)髻記》是跋吒·那羅延創(chuàng)作的一部經(jīng)典的六幕劇,該劇常常被后來的梵語詩學(xué)著作普遍當(dāng)作古典梵語戲劇和詩歌藝術(shù)的典范加以稱引。劇作家從規(guī)模宏大的印度“百科全書”式的古老史詩《摩訶婆羅多》中脫胎而出,巧妙的從般度與俱盧兩族之間18 天的大決戰(zhàn)切入,著力揭露難敵的荒淫暴戾與專橫跋扈,歌頌怖軍與黑公主不甘屈服、誓死斗爭的復(fù)仇精神。全劇在結(jié)構(gòu)緊湊,沖突激烈的過程中展開了正義與邪惡之間的殊死決斗,一改母體史詩原本的主味——平靜味,從而具有一種風(fēng)格剛健崇高、動(dòng)人心魄的英勇味。對(duì)此,恭多迦在其《曲語生命論》中指出:“在《結(jié)髻記》中,所依據(jù)的原作《摩訶婆羅多》充滿摒棄一切俗念的棄世思想。而劇作者拋棄原作結(jié)尾的平靜味,代之以英勇味,充滿驚奇,光彩熠熠,適合般度族故事。”[1]8
與中國一樣,“味”在印度古典藝術(shù)體系中也是一個(gè)非常重要的美學(xué)命題,而且居于核心地位。在印度現(xiàn)存的最早文獻(xiàn)《吠陀詩集》中,“味”(rasa)是被用作“汁”“水”和“奶”等意義的,后也被引申為“本質(zhì)”或“精華”。“味”作為美學(xué)范疇,抑或說作為一種藝術(shù)批評(píng)原則,首見于古代印度美學(xué)家婆羅多的著名藝術(shù)理論名著《樂舞論》(《演劇論》。這是用梵語詩體寫成的一部光輝的藝術(shù)美學(xué)經(jīng)典)。
婆羅多在《樂舞論》中,將生理意義上的“味”移植為美學(xué)意義上的“情味”。他所說的“味”是指戲劇表演的感情效應(yīng),即觀眾在觀劇時(shí)體驗(yàn)到的審美快感。按照婆羅多的規(guī)定,味共有8 種:艷情味、滑稽味、悲憫味、暴戾味、英勇味、恐怖味、厭惡味和奇異味。“味”產(chǎn)生于情,“情”在《樂舞論》中是指觀眾所能感受到的語言、形體和真情。可見,味與情密切相關(guān),觀眾們所產(chǎn)生的味源自情,如果說情是敘事的方式,是舞臺(tái)的表演,那么味就是敘事的效果。
這與中國古代文論家諸如鐘嶸所提出的“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2]的“滋味說”,以及劉勰《文心雕龍》中所列舉的“遺味”“余味”“精味”“義味”等美學(xué)概念有異曲同工之妙。更能說明這一問題的是印度七世紀(jì)時(shí)的檀丁或稱伏巴堅(jiān)所著的古代印度文學(xué)理論《詩鏡》傳入中國后影響很大,明代的陸時(shí)雍即據(jù)此撰《詩鏡總論》,并用“味”評(píng)詩,如“詩之佳者,在聲色臭味之俱備,庾(肩吾)、張(正見)是也。詩之妙者,在聲色臭味之俱無,陶淵明是也。”這顯然與《詩鏡》中所論“充滿情和味”“修飾得好的詩,能娛樂人們,將永存到劫盡”“甜蜜就是有味,在語言以及內(nèi)容方面都有味存在,由于這(味),智者迷醉,好像蜜蜂由花蜜(而醉)”等觀點(diǎn)不謀而合。優(yōu)秀的作品如同花蜜,可使閱讀者迷醉,在《結(jié)髻記》里也多有表現(xiàn)。比如序幕中“現(xiàn)在上演的這部劇作,猶如另外的一捧花朵,請(qǐng)你們品嘗其中的花蜜,即使蜜汁不多又稀薄。”再比如第二幕:[1]35
夜間綻放的花朵,花蜜和露水,
混合,花蜜隨同它們一起墜落,
在陽光下綻放的日蓮,花瓣中
散發(fā)甜蜜香味,密蜂飛向它們。
再比如,劇本的末尾還有“評(píng)論贊賞作品優(yōu)點(diǎn)的智者集會(huì)已經(jīng)散去,詩人的語言清澈甜美,充滿修辭和情味”的語言,同樣具有這樣的意思。然而,在《結(jié)髻記》這部經(jīng)典梵語戲劇中帶給我們更多的則是“英勇味”。“堅(jiān)戰(zhàn)代表公正、謙恭和仁義,而難敵則被塑造成貪婪、傲慢和殘忍的形象。堅(jiān)戰(zhàn)五兄弟為了避免流血戰(zhàn)爭,作出最大讓步,且獲得黑天的支持。在歷時(shí)18天的俱盧之戰(zhàn)中,充分表現(xiàn)了堅(jiān)戰(zhàn)五兄弟以及黑天獻(xiàn)身正義、勇敢戰(zhàn)斗的英勇味。”[3]婆羅多說,英勇味以上等人為本源。它通過鎮(zhèn)定、堅(jiān)韌、謀略、素養(yǎng)、曉勇、能力、威武和威力等情由產(chǎn)生。它應(yīng)該以堅(jiān)強(qiáng)、勇敢、剛毅、犧牲和精明等情態(tài)表演。婆羅多還將英勇味分為布施英勇味、正義英勇味和戰(zhàn)斗英勇味三類,即通過慷慨布施、獻(xiàn)身正義和勇敢戰(zhàn)斗顯示的英勇味。劇本中的這種英勇味來源于充滿驚奇、跌宕起伏的復(fù)仇情節(jié),來源于堅(jiān)忍不拔、匡扶正義的藝術(shù)形象,來源于恢弘悲壯、激蕩人心的戲劇場(chǎng)面與英雄情味。
《結(jié)髻記》取材的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以列國紛爭時(shí)代的印度社會(huì)為背景,講述了婆羅多族兩大后裔俱盧族與般度族爭奪王位繼承權(quán)的斗爭。俱盧族首領(lǐng)難敵作為邪惡的一方,屢次施用奸計(jì)迫害以堅(jiān)戰(zhàn)為首的般度族,尤其是通過設(shè)計(jì)擲骰子的騙局,誘使堅(jiān)戰(zhàn)輸?shù)羲胸?cái)產(chǎn)和王國,連同自己和4 個(gè)弟弟共有的妻子黑公主。更令般度族無法容忍的是難敵竟然揪住黑公主的頭發(fā),剝下她的衣服,在賭博大廳當(dāng)眾凌辱她。仇恨的怒火在般度族燃燒,他們發(fā)誓要報(bào)仇雪恨,歷盡艱難,最終通過與難敵進(jìn)行18 天決戰(zhàn),使得俱盧族幾乎全軍覆沒。然而,世事難料,由于俱盧族僅存的3 員大將夜襲毫無防范的般度族大營,致使整個(gè)般度族幾乎被斬盡殺絕,僅僅幸存了黑天和般度5 兄弟。面對(duì)兩大家族兩敗俱傷的悲慘結(jié)局,堅(jiān)戰(zhàn)心情沮喪,在眾人勸說之下,登基為王。36 年后,堅(jiān)戰(zhàn)與4 個(gè)弟弟以及他們共有的妻子黑天公主一起登山升天。這樣的結(jié)尾給以一種萬事皆空的虛無感,特別類似于中國古代的神仙道話劇,勝利者與失敗者皆無歡欣與悲哀可言,真的有一種“是非成敗轉(zhuǎn)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和“青史幾行名姓,北邙無數(shù)荒丘”的蒼涼。正如九世紀(jì)的印度學(xué)者兼詩人歡增在《韻光》中指出“在既有經(jīng)典形貌,又有詩歌風(fēng)采的《摩訶婆羅多》中,大牟尼(毗耶娑)安排苾濕尼族悲慘滅亡的結(jié)局,凄涼抑郁,表明他的這部作品的主要含義是離欲,其宗旨是以解脫為人生主要目的,以平靜味為主味。”[1]9
《結(jié)髻記》改變了原著題材的這種平靜味代之以英勇味。劇本以般度和俱盧族18 天大決戰(zhàn)為背景,圍繞怖軍發(fā)誓為黑公主報(bào)仇雪恨這個(gè)主題展開情節(jié)。劇本中反復(fù)出現(xiàn)的難敵揪住黑公主的發(fā)髻,剝?nèi)ヒ路谫€博大廳對(duì)其當(dāng)眾凌辱與怖軍發(fā)誓要打斷難敵的雙腿,用沾滿難敵鮮血的手親自為黑公主挽起發(fā)髻的陳訴實(shí)質(zhì)上也是在不斷強(qiáng)化要以正義戰(zhàn)勝邪惡的這一鮮明主題。
劇本集中批判了暴君難敵的荒淫殘暴與專橫跋扈。難敵一登場(chǎng)就顯示出了他的殘暴不仁與嗜殺成性。他說:“只要對(duì)怨敵造成殺害,無論由自己或靠別人,無論明暗,無論大小,都讓人感到莫大喜悅。”當(dāng)他聽到般度族的激昂已被德羅納和勝車殺死,“心中仿佛特別舒暢。”絲毫沒有悲憫情懷。不僅如此,難敵還是一個(gè)猜忌心十分重的暴君,他僅憑自己的王后夢(mèng)到了貓鼬就無端懷疑妻子與瑪徳利的兒子私通,稱自己被“這個(gè)淫婦欺騙”,而且心中咒罵她“這個(gè)邪惡女人的行為簡直像妓女”。在難敵面前,女人只是他肆意踐踏和欺凌的玩物,因此他還是一個(gè)荒淫的暴君。“這確實(shí)是旋風(fēng)給我的恩惠,我不用費(fèi)力勸說,往后就放棄了守戒,滿足我的心愿……現(xiàn)在,我的心愿滿足,可以隨意游戲。”劇作家通過怖軍之口,交代了難敵這個(gè)惡魔的結(jié)局:“他(難敵)已被我打倒在地,鮮血似油膏涂抹我身……大地之主啊,難敵現(xiàn)在只剩下你說的名字”“現(xiàn)在所有的敵人已被消滅,你(堅(jiān)戰(zhàn))是國王,怖軍和阿周那都活著”,而后,劇作者有不厭其煩地鋪敘般度族獲勝的慶祝,反復(fù)陳說黑公主被難敵羞辱的場(chǎng)景:
般度族五兄弟怒不可遏,
已殺死來自各地的國王們,
讓他們后宮婦女頭發(fā)披散,
黑公主被難降扯散的發(fā)髻,
猶如死神的朋友,俱盧族
災(zāi)星,現(xiàn)在終于已被挽起,
原國王們的殺戮從此停息,
祝愿剎帝利王族吉祥快樂![1]174
就在這種情節(jié)的巨大張力間讓讀者、觀眾共同享受正義戰(zhàn)勝邪惡的喜悅,品嘗到高貴與崇高的英勇味。
《結(jié)髻記》的英勇味還集中體現(xiàn)在怖軍這一鮮明藝術(shù)形象的塑造方面。在這位般度族的怖軍身上集中散發(fā)著堅(jiān)韌剛毅、驍勇善戰(zhàn)的英勇味。他一上場(chǎng),就表現(xiàn)出了與邪惡一方——難敵勢(shì)不兩立:
火燒紫膠宮,給食物下毒,進(jìn)入賭博廳,
剝奪我們的生命和財(cái)產(chǎn),強(qiáng)行拽拉
只要我還活著,遲國之子們?cè)鯐?huì)安寧?”[1]12
他聲稱“從小就和俱盧族結(jié)下深仇大恨”,堅(jiān)持即使堅(jiān)戰(zhàn)等人與難敵議和,他也決不屈服,“也要撕碎他,猶如撕碎妖連胸膛”。他指責(zé)堅(jiān)戰(zhàn)等弟兄:
在這世上,滿腔憤怒消滅
敵人家族,你們感到羞愧,
在大庭廣眾被揪住你們的
妻子發(fā)髻,卻不感到羞愧![1]20
怖軍向黑公主發(fā)誓:
在上述干擾場(chǎng)景和干擾參數(shù)下,采用四相位等分分段多相位分段調(diào)制干擾,相位值按照從小到大的順序進(jìn)行調(diào)制,與間歇采樣重復(fù)轉(zhuǎn)發(fā)干擾進(jìn)行以下3組仿真對(duì)比實(shí)驗(yàn),各實(shí)驗(yàn)進(jìn)行100次蒙特卡洛仿真,各組MTD結(jié)果取蒙特卡洛仿真結(jié)果均值的最大值對(duì)應(yīng)的距離和速度作為目標(biāo)信息。
王后啊,我將揮動(dòng)手臂,掄起
可怕的鐵杵,打斷難敵的雙腿,
我要用這雙被他的黏稠的鮮血
染紅的手,重新挽起你的發(fā)髻。
劇作者不僅直接表現(xiàn)怖軍的嫉惡如仇、英勇無畏、驍勇善戰(zhàn)的精神品質(zhì),而且還通過其他人物的視角來側(cè)面表現(xiàn)他的精神風(fēng)貌,為此,劇作者設(shè)計(jì)了斫婆迦謊報(bào)軍怖陣亡的噩耗這一情節(jié)。首先,借助斫婆迦之口,描繪了軍怖的英勇善戰(zhàn):“難敵和怖軍交戰(zhàn)的鐵杵發(fā)出可怕的碰撞聲,大力羅摩趕來,戰(zhàn)斗在他的前面持續(xù)很久……”而后,通過堅(jiān)戰(zhàn)之口,再次展示怖軍的英勇:“弟弟啊,你效忠我這癡迷賭博的無恥之人,雖然臂力堪比千萬頭大象,甘愿充當(dāng)奴仆”“他(怖軍)誅滅空竹、缽迦、希丁波和斑駁,如同雷電劈殺驕傲盲目的摩揭陀國王這頭瘋象。”無疑,怖軍展現(xiàn)在我們面前的以為名副其實(shí)的硬漢形象,他使得這部戲中的英勇味更加濃郁。
《結(jié)髻記》這出戲營造的氛圍同樣散發(fā)著英勇味。比如在第一幕,劇作者對(duì)幕后傳來的喧囂聲的描寫:“鼓聲深沉,似曼陀山攪動(dòng),海水灌滿山洞,每次撞擊,似世界毀滅之時(shí),雷云相互撞擊如同黑公主憤怒的信使,毀滅俱盧族的颶風(fēng),如同我們的獅子吼回聲,是誰擂起這戰(zhàn)鼓?”再比如,第一幕結(jié)尾時(shí),怖軍對(duì)戰(zhàn)場(chǎng)廝殺情境的想象:
大象相互撞擊,身體破碎,
血肉、脂肪和腦髓形成泥沼,
士兵成立的戰(zhàn)車陷入其中,
豺狼發(fā)出如同喇叭的嗥叫聲,
成群結(jié)隊(duì)吸吮流淌的鮮血,
那些無頭的身軀手舞足蹈,
英勇善戰(zhàn)的般度之子們擅長
在這樣的戰(zhàn)爭大海中搏斗。
這蒼涼悲壯的戰(zhàn)場(chǎng)與我國唐代文學(xué)家李華筆下“河水縈帶,群山糾紛。黯兮慘悴,風(fēng)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鋌亡群”“鼓衰兮力竭,矢盡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zhàn)矣哉,暴骨沙礫。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fēng)淅淅。魂魄結(jié)兮天沉沉,鬼神聚兮云冪冪”的古戰(zhàn)場(chǎng)有異曲同工之妙。真是在這種凄涼悲壯的戰(zhàn)場(chǎng)上才凸顯出以怖軍為代表的俱盧族將士的驍勇善戰(zhàn),不畏強(qiáng)暴,繼而使得讀者抑或觀眾獲得英勇味。
黃寶生先生在這部古老劇作的中文譯本前言中談到的“全劇風(fēng)格剛健,充滿激動(dòng)人心的戲劇場(chǎng)面和英雄情味”實(shí)為精警之論。